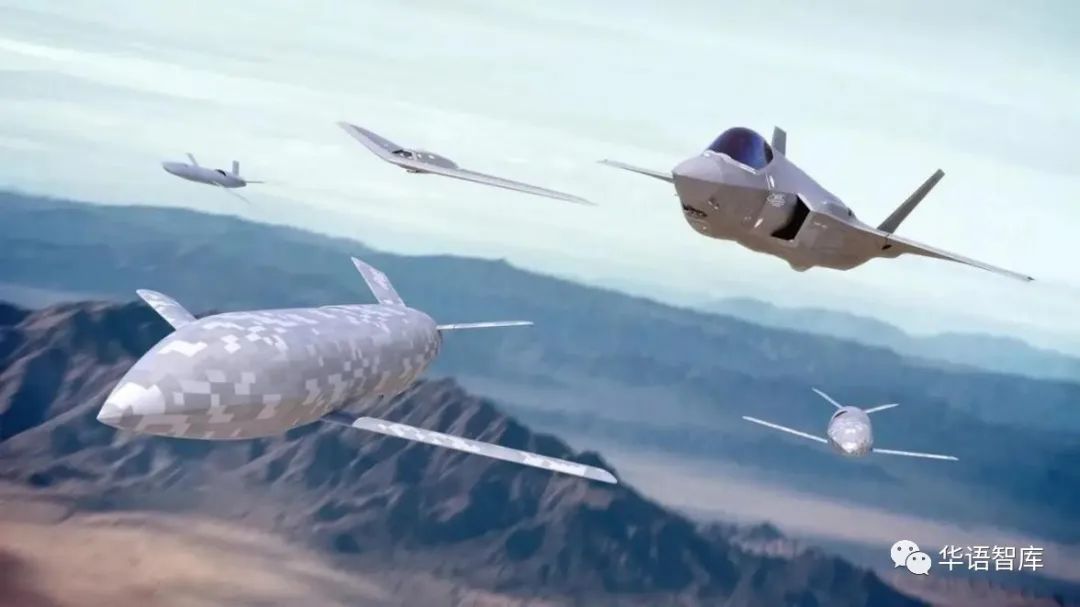作者近照
我所了解的張中行
作者 田永清
張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縣一個(gè)普通農(nóng)家,1931年畢業(yè)于通縣師范學(xué)校,1935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曾任教于中學(xué)、大學(xué),主編過佛學(xué)雜志。1951年2月起任職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從事中學(xué)語(yǔ)文教材編寫及教學(xué)研究工作,歷時(shí)半個(gè)世紀(jì)之久,為我國(guó)文化教育事業(yè)做出了重大貢獻(xiàn)。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長(zhǎng)期以來張老一直默默無(wú)聞。直到上個(gè)世紀(jì)80年代末90年代初,年已七八十歲的張中行先生的大名和一系列作品,才開始頻繁地出現(xiàn)在各大報(bào)紙和雜志上,并在當(dāng)代文壇上獨(dú)樹一幟,聲名鵲起。
我喜歡結(jié)交老人和文人,張中行正好符合這兩條,他既是老人,又是文人。但具體說來,張中行又不同于一般的老人和文人。首先,他身上有光環(huán),這種光環(huán)是由他的道德和文章交相輝映而成的;其次,他身上有陰影,這種陰影則是由楊沫那本小說《青春之歌》涂抹上的。張中行到底是一個(gè)怎樣的人?我就是帶著仰慕和好奇這樣兩種心情,于上個(gè)世紀(jì)90年代中期開始和張老交往的。這一交往就是十幾年,我們結(jié)成了關(guān)系比較密切的忘年交。在這些年里,我既讀張老的書,幾乎閱讀了張老數(shù)百萬(wàn)字的全部作品;通過多次接觸和交談,又認(rèn)真讀張老其人,使我不斷加深了對(duì)于他的了解。
今年2月24日,張老在解放軍305醫(yī)院安詳?shù)赝V沽撕粑砟?span lang="EN-US">98歲。張老逝世后,我很快趕到他的家中表示悼念,隨后又接受了中央電視臺(tái)的采訪,3月2日和眾多人們一起在八寶山向他的遺體告別。我悲痛的心情難以述說,我從內(nèi)心里深切地緬懷這位可敬可愛的世紀(jì)文化老人。
他是一位國(guó)學(xué)大師
冰心老人生前有句名言:“人生從80歲開始”。張中行先生的人生,就是這樣的人生。張老是在80歲左右的晚年才“暴得大名”的,人稱“文壇老旋風(fēng)”。
張老出名之后,前些年有人把他與季羨林、錢鐘書、施哲存并列,稱之為當(dāng)今中國(guó)的四位“國(guó)學(xué)大師”。也有人把他與季羨林、金克木、鄧廣銘并稱為北大的“未名四老”。這雖然不是正式評(píng)選(老實(shí)說也難以評(píng)選)的結(jié)果,但張老的確是為眾多人們所公認(rèn)的國(guó)學(xué)大師。
季羨林在一篇文章中,稱張中行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在談到張中行的文章時(shí),季先生還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常想,在現(xiàn)代作家中,人們讀他們的文章,只需讀上幾段就能認(rèn)出作者是誰(shuí)的人,極為罕見。在我眼中魯迅是一個(gè),沈從文是一個(gè),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與張老密切交往半個(gè)多世紀(jì)之久的啟功先生,稱張老既是“哲人”,又是“癡人”,贊他“說現(xiàn)象不拘于一點(diǎn),談學(xué)理不妄自尊大”。
一身傲骨、滿腹才華的吳祖光先生說:“我那點(diǎn)學(xué)問純粹是蒙事,張中行先生那才是真學(xué)問。”
比較年輕而又具有傳奇色彩的記者唐師曾(綽號(hào)“唐老鴨”)說:“沒讀張老的書,不知道他的學(xué)問有多大;讀了張老的書,更不知道他的學(xué)問有多大。”
上述這些評(píng)論,絕非溢美之詞。張中行在讀師范的時(shí)候,就開始接觸新文學(xué),博覽群書,追求新知。在沙灘紅樓的北大四年,他進(jìn)一步開闊了知識(shí)視野,接受了科學(xué)、民主思想。他終生孜孜不倦,廣泛涉獵,潛心研究國(guó)學(xué)、邏輯學(xué)、哲學(xué),不僅思索老莊、孔孟、佛學(xué),而且研究羅素、培根,這在當(dāng)代文人中并不多見,其成就令眾人仰視。過去說一個(gè)人學(xué)問大,往往說“學(xué)富五車,才高八斗”;現(xiàn)在說一個(gè)人學(xué)問大,又往往說“博通古今,學(xué)貫中西”。把這些說法用在張老身上,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肚子里有沒有墨水是一回事,能不能通過文筆表達(dá)出來又是一回事。一個(gè)人如果只是堆積了很多知識(shí),但卻不能創(chuàng)造性地表達(dá)出來,那就無(wú)異于魯迅筆下只會(huì)記憶的“兩腳書架”。張中行不但學(xué)識(shí)淵博,而且文筆奇高。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中國(guó)社會(huì)的逐漸清明,已屆耄耋之年的張中行亦如老樹發(fā)新芽,開始了散文隨筆的創(chuàng)作。這一寫竟如大河開凍,滾滾而下,陸續(xù)流出了以《負(fù)暄瑣話》、《負(fù)暄再話》、《負(fù)暄三話》、《順生論》、《禪外說禪》等為代表的數(shù)百萬(wàn)文字。一時(shí)舉國(guó)上下,書店書攤,到處擺放著張中行的著作,國(guó)人爭(zhēng)讀,影響巨大。有的地方還有專門閱讀和討論張中行書籍的自發(fā)性組織,名曰“張迷協(xié)會(huì)”,這不能不說是當(dāng)今出版業(yè)和讀書生活中的一大奇跡。
跨入新世紀(jì)以來,“國(guó)學(xué)熱”開始蔓延,各種各樣的“大師”也多如牛毛。但是,何謂國(guó)學(xué)?何謂大師?何謂國(guó)學(xué)大師?未必人人都能說得清楚,當(dāng)然我更講不明白。
著名歷史學(xué)家戴逸在一篇文章中談到,稱得上大師的人物,應(yīng)具備四個(gè)條件:一、學(xué)術(shù)上博大精深;二、有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貢獻(xiàn);三、桃李滿天下,學(xué)術(shù)上薪火相傳,有許多追隨者、繼承者;四、不僅學(xué)問高,道德也高。就張老的品德、學(xué)識(shí)、著作、影響而言,不管從哪個(gè)角度講,我們都可以肯定地說,張中行的確是一位“國(guó)學(xué)大師”。
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
人一出名,各種各樣的稱謂也就隨之而來。比如對(duì)于張中行,除稱為國(guó)學(xué)大師外,還有稱之為著名作家、著名學(xué)者的,也有稱他為雜家的,此外還有什么文學(xué)家、散文家、教育家、哲學(xué)家、編輯家,等等。的確,對(duì)于張老這樣的大師,確實(shí)很難用一個(gè)頭銜,比如用一個(gè)什么“家”來加以概括的。有人這樣問過張老:“總結(jié)一生,您認(rèn)為給你戴一頂什么‘帽子'比較適合?比方文學(xué)家、教育家、哲學(xué)家,等等。”張老這樣回答:“如果硬要戴一頂‘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這一生中我自認(rèn)為不糊涂。”張老的這個(gè)回答既令人意外,又發(fā)人深思。
思想之于人的確是最為重要的。去年9月29日,我和《光明日?qǐng)?bào)》的韓小蕙同志去305醫(yī)院探望張老。小蕙請(qǐng)教了張老幾個(gè)問題,其中一個(gè)問題是:“您覺得對(duì)于一個(gè)文人來說,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想了想,拼足力氣回答:“思想最重要!”并且在小蕙帶的本子上鄭重地寫下了這5個(gè)字。
張老的這個(gè)回答,和古今中外許多大人物的看法是一致的。馬克思說:“人是靠思想站立的。”法國(guó)哲學(xué)家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拿破倫說:“世界上只有兩種力量,一種是思想,一種是利劍,而思想最終總是戰(zhàn)勝利劍。”法國(guó)思想家伏爾泰有兩句名言:“笑和讓別人笑,思考和讓別人思考。”美國(guó)阿諾德·施瓦辛格說:“思想有多遠(yuǎn),我們就能走多遠(yuǎn)。”美國(guó)哈尼·魯賓說:“注意你的思想,它們會(huì)變成你的言語(yǔ);注意你的言語(yǔ),它們會(huì)變成你的行動(dòng);注意你的行動(dòng),它們會(huì)變成你的習(xí)慣;注意你的習(xí)慣,它們會(huì)變成你的性格;注意你的性格,它們會(huì)決定你的命運(yùn)。”在這個(gè)世界上,最寶貴的是思想,最令人敬佩的“富翁”是思想的富有者。一切大有作為的人,都有一個(gè)共同特點(diǎn),就是有思想、善思索。
張老是一個(gè)有“自己的思想”的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社會(huì)取向,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服從整體、下面服從上面,從而淹沒于整體、淹沒于上面。很多有思想、有個(gè)性的人才,就這樣被埋沒甚至被扼殺了。倘若一個(gè)人思想平庸,沒有獨(dú)立見解,阻擋者很少;倘若一個(gè)人很出色,很有思想,則阻擋者很多。真正敢于亮出“自己的思想”的人,是無(wú)私無(wú)畏的人。在張老“自己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點(diǎn)就是“存疑”,就是不盲從、不輕信。這種“存疑”,這種“不信”,是建立在淵博的知識(shí)和獨(dú)立思考的基礎(chǔ)之上的。一個(gè)人沒有知識(shí),沒有思想,就缺乏判斷力,就可能過于輕信。
張老的“自己的思想”,有許多是圍繞著“人應(yīng)該怎樣生活”這個(gè)主題的,因此顯得很博大、很整體,也很深刻。他曾經(jīng)這樣回憶說:“主要是兩點(diǎn)。其一,是大學(xué)畢業(yè)前后,忽然有了想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怎樣活才好的相當(dāng)強(qiáng)烈的求知欲。其二,‘欲'之后必隨來‘求',于是在治學(xué)方面就轉(zhuǎn)了方向,改為鉆研哲學(xué),尤其是人生哲學(xué)。”有人稱張老為哲學(xué)家,他主要研究的是人生哲學(xué),其結(jié)晶就是歷經(jīng)數(shù)十年學(xué)習(xí)、研究最終寫作而成的《順生論》這部書。在張老的“自己的思想”中,有一個(gè)很重要的內(nèi)容就是“順生”。概括地說,所謂“順生”,第一順其自然的生命規(guī)律,淡泊名利,不跟自己較勁;第二順從內(nèi)心的道德律令,不做違背良心的事,不與別人為難。這是他能長(zhǎng)壽的重要原因,這也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
張老的“自己的思想”,貫穿于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他的一些著作,堪稱經(jīng)典之作,必能傳之久遠(yuǎn)。好的文章不僅是詞藻華美、抒情動(dòng)人,更重要的是能表達(dá)思想。有些人的文章,長(zhǎng)篇大論,水份很多,看起來說南道北,想起來沒有東西。張老不是一般的作家,而是名副其實(shí)的大家,他在字里行間流露出來的文采、情感、深思、哲理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無(wú)窮余韻,在別的作家那里并不多見。正因?yàn)槿绱耍瑥埨系淖髌穼?duì)于廣大讀者有著一種獨(dú)特而又強(qiáng)大的吸引力。張老是一位思想多于行動(dòng)、思考多于言談的人。這樣的人一定會(huì)拿起筆來宣泄“自己的思想”,而使張老名揚(yáng)四海的,正是他的許多飽含人生哲理的著作。
他是一位大度君子
在當(dāng)代中國(guó)文壇,曾經(jīng)流傳過兩男兩女歷史恩怨和感情糾葛的故事。
一個(gè)是說,關(guān)于“張恨水”之名,有傳言說是張恨水曾經(jīng)追求冰心,但始終得不到青睞,失戀失意之余,憤而借用《紅樓夢(mèng)》中賈寶玉說的“女人是水做的”話,引申而成“恨水”。實(shí)際上這是根本沒有的事兒。他取“恨水”兩字為筆名,是借用了“自是人生長(zhǎng)恨,水長(zhǎng)東”(南唐后主李煜《烏夜啼》句)之本意,為的是時(shí)刻勉勵(lì)、提醒自己珍惜時(shí)間。事實(shí)上,張恨水的婚姻浪漫而美滿,他的妻子小他近20歲,原是北平春明女中的學(xué)生,因?yàn)樘貏e喜歡張恨水的長(zhǎng)篇小說《啼笑因緣》而對(duì)他產(chǎn)生愛慕之心,后來兩人結(jié)為秦晉之好。就冰心這方面而言,我的老戰(zhàn)友、曾任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辦公廳主任的李一信同志,曾于上個(gè)世紀(jì)80年代當(dāng)面向她詢問過這個(gè)問題。冰心老人并沒有因?yàn)橐恍诺奶仆欢鎺C色,她安詳而詼諧地說:“那些小道傳言都是沒根的事兒,我那時(shí)早已跟吳文藻戀愛定婚,他恨哪門子水呀!”
另一個(gè)傳言是,張中行與楊沫年輕時(shí)曾經(jīng)相愛并且同居。這個(gè)倒是確有其事,并且由此演繹出了許多故事。
大概是在1931年夏至1936年春,也就是張中行在北大中文系讀書期間和剛畢業(yè)從事中學(xué)教育之初,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年僅17歲的楊沫因抗婚而離家出走,在走投無(wú)路時(shí),請(qǐng)張中行幫她介紹工作。經(jīng)過一段接觸,因互有好感而從熱戀到同居,時(shí)間大概將近5年。其中的前兩年,即由相識(shí)到共朝夕的兩年,還被張老稱之為“婚姻的花期”,到老也是“難得忘卻的”。他們還有過兩個(gè)孩子,一個(gè)是男孩,出生不久便夭折了。一個(gè)是女孩,是他們離異之后才出生的,至今已是70歲的老人了。新中國(guó)成立后,楊沫從解放區(qū)回到北京,他們還見過面。對(duì)于這些,張老從不隱諱,誰(shuí)問到他有關(guān)情況,他都如實(shí)相告。因?yàn)檫@在那個(gè)大變動(dòng)的年代,本來是屬于極其正常的事情。
問題發(fā)生在后面。上個(gè)世紀(jì)50年代,楊沫寫了一部影響極大的小說《青春之歌》。實(shí)事求是地說,這部小說突破了當(dāng)時(shí)文藝上的禁錮,把一個(gè)本來小資產(chǎn)階級(jí)味道十足的知識(shí)女性林道靜當(dāng)作全書的主角,還大膽地描寫了作為革命者的她連續(xù)不斷的愛情,這都是反潮流的、先鋒的、叛逆的。后來,這部小說又由北京電影制片廠改編、拍攝成同名電影,由青春秀麗的謝芳扮演林道靜,電影一路綠燈、一片轟動(dòng),引起了更加強(qiáng)烈的反響。可以說小說和電影中的人物膾炙人口、家喻戶曉。周總理還親自邀請(qǐng)主創(chuàng)人員到家里看片,鄧大姐甚至這樣說:小說看到“忘食”,電影看過不止一次。
這本來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在小說和電影中,還塑造了另一個(gè)叫作余永澤的人物,此人與林道靜和其他革命者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是一個(gè)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而這個(gè)余永澤,據(jù)稱影射的就是張中行。在這之前的張老,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職員,雖然默默無(wú)聞,但還算平安無(wú)事。隨著《青春之歌》小說和電影引起的轟動(dòng)效應(yīng),張老的生活變得不平靜了,他在單位里被弄得灰頭土臉,也被社會(huì)有些人傳得沸沸揚(yáng)揚(yáng)。
其實(shí),真實(shí)的張中行與余永澤根本就不是一種類型的人。他有著中國(guó)文人的正直,他不僅作風(fēng)正派,學(xué)識(shí)淵博,也從不干告密、打小報(bào)告之類的事,更從不亂揭發(fā)別人,踩著別人往上爬。盡管楊沫在書中虛構(gòu)了許多他所沒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讓他戴上了一個(gè)落后分子的帽子,但他對(duì)楊沫的評(píng)價(jià)卻始終是肯定的、正面的,從沒有什么怨言。
也有人為他打抱不平,勸他寫文章為自己辯解。但張中行說,人家寫的是小說,又不是歷史回憶錄,何必當(dāng)真呢?就是把余永澤的名字改成張中行,那也是小說,我也不會(huì)出面解釋。更為感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是非顛倒的日子里,張老自己的日子已經(jīng)十分難過,他先是被發(fā)配到五七干校,幾次挨批斗,后來又被趕回農(nóng)村老家,甚至還停發(fā)了工資。與此同時(shí),也有人全面否定楊沫寫的《青春之歌》,并且誣蔑她是“假黨員”。在這種情況下,楊沫單位來人外調(diào),希望張中行說楊沫的壞話,造反派還對(duì)他進(jìn)行威嚇、辱罵,讓他按照他們的要求說。張中行寫了一份材料,大意是說,那時(shí)楊沫比我進(jìn)步、比我革命,還說楊沫“直爽、熱情,有濟(jì)世救民的思想,真的相信她所信仰的東西,并為之奮斗,比那些口頭主義者強(qiáng)多了!”據(jù)說后來?xiàng)钅吹搅诉@個(gè)材料,她很感動(dòng),并寫信向張中行表示感謝。
但到了上個(gè)世紀(jì)80年代,楊沫寫文章追述往事時(shí),言及當(dāng)年與張中行分手之事,又是明說或是暗示,張中行當(dāng)年負(fù)心兼落后,所以她才由幽谷而遷于喬木。聞聽此言,張中行笑曰:認(rèn)定我負(fù)心,是人各有見;認(rèn)定我落后,是人各有道。總之,“道不同不相為謀”,最后只得分手。張老在《流年碎影》中談到婚姻問題時(shí),把婚姻分為四個(gè)等級(jí):可意,可過,可忍,不可忍。張老與楊沫分手,當(dāng)年自然是有“不可忍”之處了。楊沫逝世之后,他們的女兒徐然給張老寫信,主要意思是說,生時(shí)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諒解吧。張老復(fù)信說,人在時(shí),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會(huì)說什么。
有人曾經(jīng)說過這樣四句話:“以德報(bào)德是常人,以怨報(bào)德是小人,以怨報(bào)怨是惡人,以德報(bào)怨是偉人。”從張老在困境和屈辱中對(duì)楊沫的態(tài)度而言,我們不必稱他是偉人,但我們應(yīng)該實(shí)事求是地承認(rèn),他的確是一位大度君子。
他是一個(gè)真正大寫的人
閱讀張老的作品,或與張老直接接觸,都給我這樣一個(gè)深刻的感覺:他是一個(gè)真正大寫的人,他是中國(guó)古典文人的典范。
“學(xué)問往上看,享受往下看”,這是張老經(jīng)常說的兩句話,他自己的確也是這樣做的。張老一生清貧,生活簡(jiǎn)樸,他85歲時(shí)才分到一套普通的小戶型三居室,沒有進(jìn)行任何裝修,屋里擺設(shè)也極為簡(jiǎn)陋,除了兩書柜書幾乎別無(wú)一物。可張老卻從無(wú)怨言,他甚至還為自己的住所起了個(gè)雅號(hào),叫作“都市柴門”,安于在“柴門”內(nèi)做他的布衣學(xué)者。
季羨林先生有個(gè)被北大新生當(dāng)成工人師傅,并請(qǐng)他臨時(shí)照看行李的故事。張中行也有個(gè)被當(dāng)成看門老頭的故事。張老還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時(shí),有一次在樓下,看到傳達(dá)室的人去買飯了,他就在傳達(dá)室那里坐著。這時(shí)來了一個(gè)人,說找人,具體找誰(shuí)也沒說。張老就說你等會(huì)兒,中午都休息呢!后來傳達(dá)室的人回來了,那個(gè)人說,我要找張中行,這個(gè)老師傅讓我等著。傳達(dá)室的人說,你知道他是誰(shuí)嗎?他就是張中行先生!說完.,那個(gè)人特別吃驚,哎呀!這就是我要拜訪的張老啊!然后又說了很多尊敬的話。張老回到家里對(duì)女兒說,你看這多好,人家把我看成個(gè)老師傅。就這樣他挺高興。季羨林、張中行這些著名學(xué)者,都有一個(gè)共同特點(diǎn),就是心無(wú)旁騖,專心治學(xué),淡泊名利,儉樸生活。
“言必信,行必果”,是張老終生奉行的信條。張老是“左撇子”,自謂“學(xué)書不成”。其實(shí),他的書法很見功力,書論也頗有獨(dú)見。他曾親口對(duì)我說過,在書畫創(chuàng)作上造詣深厚的人,一般具備三個(gè)條件:一是天賦,二是勤奮,三是學(xué)識(shí)。他還以啟功和趙樸初為例說明這個(gè)問題。我曾直接觀摩張老寫字,他握筆較低,運(yùn)筆舒緩,一筆一劃,一絲不茍,屬于文人字,書卷氣很濃。他曾給我寫過“行有余力,則以學(xué)文”、“聞雞起舞”、“奇石共欣賞”等幾幀條幅。在后面這幀條幅上,他還寫上了“永清先生有米顛愛石之癖書以奉之”一行小字。
特別令人感動(dòng)的是,張老知道我喜歡收藏“聞雞起舞”這四個(gè)大字,他就開列了一張名單,放在書桌上,并親自寫條子或打電話,先后給我求來了顧廷龍、梁樹年、任繼愈、歐陽(yáng)中石、劉炳森等名家的書法墨寶。我收藏的名家“聞雞起舞”墨跡多了,曾經(jīng)打算出一本集子。書名叫什么呢?我一時(shí)拿不定主意。張老說:“聞雞起舞”這個(gè)成語(yǔ),出自西晉時(shí)愛國(guó)將領(lǐng)祖逖和劉琨年輕時(shí)的故事,書名就叫作《祖劉遺韻》吧!我聽后連聲說好。不僅如此,那時(shí)已經(jīng)90多歲高齡的張老,有一天還帶著我、孫健民同志以及張老的三女兒張彩,直奔他的老朋友啟功先生家中,讓啟先生給我們寫字。啟老當(dāng)即給我寫了《祖劉遺韻》書名,給孫健民同志寫了“達(dá)觀”兩個(gè)大字,唯獨(dú)沒有給張彩寫,張老也根本沒有提出讓啟先生給她寫。這件事已經(jīng)過去多年了,有時(shí)我和孫健民同志說起來,還是念念不忘、感慨不已。
張老的夫人李芝鑾是舊時(shí)的大家閨秀,年輕時(shí)體態(tài)清秀而性格溫婉。妻比夫大一個(gè)半月,都屬猴,他們于1936年結(jié)婚,張老一直稱夫人為“姐”,兩人相濡以沫近70年。李芝鑾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平生志潔行芳,任勞任怨地操勞了一輩子,于2003年先張老而逝。兩位老人都在時(shí),我每次去探望,他們都十分高興、熱情接待,分別時(shí)還步履蹣跚地堅(jiān)持送到電梯門口,令人十分感動(dòng)。
張老與李芝鑾生了四個(gè)女兒,大女兒張靜,二女兒張文,三女兒張彩,四女兒張瑩。張老家風(fēng)很正,家教很好,四個(gè)女兒都受了高等教育,人人既傳統(tǒng)又現(xiàn)代,既事業(yè)有成又品德端正,頗具乃父遺風(fēng)。張老一家三代共有8人畢業(yè)于北大,除本人外,二女兒、二女婿,四女兒、四女婿,二女兒的女兒、三女兒的女兒、四女兒的女兒都畢業(yè)于北大。大女兒張靜畢業(yè)于河北醫(yī)學(xué)院,一直在張家口工作,經(jīng)過長(zhǎng)期孜孜不倦地學(xué)習(xí)和鉆研,終成名教授、醫(yī)學(xué)家,并且當(dāng)選為全國(guó)人大代表。這樣的家庭,這樣的后代,這樣的素質(zhì),不能說是絕無(wú)僅有,也是極為罕見的吧!
張老一生特立獨(dú)行,卓爾不群,從不趨炎附勢(shì),從不攀高結(jié)貴。他一輩子沒有正式參加過任何黨派、任何組織。上個(gè)世紀(jì)90年代,正是張老掀起的那股“文壇老旋風(fēng)”席卷全國(guó)的時(shí)候,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托人給他送去了入會(huì)申請(qǐng)表。張老考慮再三,決定放棄入會(huì)申請(qǐng)。他的解釋是,我這一輩子什么組織都沒有參加過,現(xiàn)在快成入土的廢物了,就不麻煩中國(guó)作協(xié)了。張老就是這樣淡泊名利,他對(duì)一切都看得很淡、很透。
張老雖然是國(guó)寶級(jí)的人物,但因?yàn)樗?ldquo;無(wú)冕名家”,無(wú)官無(wú)位,無(wú)權(quán)無(wú)勢(shì),所以到了遲暮之年在某些方面也確實(shí)遇到了不少困難和問題。有一件事雖然過去幾年了,但我想起來一直覺得心里非常難受。那一次是張老到地方某醫(yī)院看病,我派司機(jī)開著車早晨6:30就趕到了張老家里,司機(jī)和張老的二女兒張文陪著老人到了醫(yī)院,掛了專家號(hào),張老坐在輪椅里靜靜地等著,一直等了四五個(gè)小時(shí),那位專家說有別的重要事不再看了,就這樣把一位90多歲的國(guó)寶級(jí)人物甩到了一邊,只好白去一趟、嘆息而歸。司機(jī)回來給我說起這件事,我心里覺得又難過又氣憤,但這又有什么辦法呢?在我國(guó),“官本位”的影響還很嚴(yán)重,干什么都講究級(jí)別高低。對(duì)此,張老和張文倒顯得比較平靜,他們沒有過多抱怨。張老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gè)人能享大福不算真本事,能吃大苦才算真本事。”我想,他們對(duì)于這種現(xiàn)象大概已經(jīng)司空見慣、習(xí)以為常了。
張中行的養(yǎng)生之道和座右銘
近10年來,每到1月7日,我都到張老家中給他祝壽。其中印象最深、收獲最大的,是2005年1月7日給張老祝賀96歲華誕那一天。我把那天的情況,寫成《給張中行先生祝壽》一文,經(jīng)由韓小蕙同志發(fā)表在了《光明日?qǐng)?bào)》的文化副刊上。那天上午,我趕到張老家里,向他表示熱烈祝賀。我等了一會(huì)兒,張老的三女婿林教授喚醒他:“爸,田政委來看您了!”張老慢慢睜開眼睛,認(rèn)出是我之后,拱手作揖道:“將軍駕到,歡迎、歡迎!”我發(fā)現(xiàn)張老的身體和精力的確已大不如從前。家人說他臥床睡眠的時(shí)間明顯增多,在房間走動(dòng)也需要手拄拐杖或他人攙扶。但他的氣色還好,臉上沒有常見的老年斑,也沒有多少皺紋。他的思維還比較敏捷,說話也比較流利,而且還像過去那樣,與人見面之后喜歡開玩笑、說笑話。
張老起來之后,就坐在床上,靠著被子,和我們交談了起來。我覺得機(jī)會(huì)難得,就向張老請(qǐng)教了幾個(gè)問題。
我請(qǐng)教的第一個(gè)問題是:“張老,您一生歷經(jīng)坎坷,竟然活到如此高齡,請(qǐng)問您有什么養(yǎng)生之道?”
張老想了一會(huì)兒,回答說:“我沒有什么養(yǎng)生之道。要說有的話,就是我這一輩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發(fā)財(cái),只是一門心思讀書做學(xué)問。除此之外,我別無(wú)他求。”
我請(qǐng)教的第二個(gè)問題是:“張老,指導(dǎo)您一生言行的座右銘是什么?”
張老想了一會(huì)兒,回答說:“我也沒有什么座右銘。要說有還是剛才說的那兩句話:我這一輩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發(fā)財(cái),只是一門心思讀書做學(xué)問。除此之外,我別無(wú)他求。”
說起張老的座右銘,他的四女兒張瑩同志說:“我爸這幾句話哪里像什么座右銘呀!不過說實(shí)在話,他這一輩子的的確確是這樣做的。”
我請(qǐng)教的第三個(gè)問題是:“張老,您寫了那么多大作,您最喜歡、最滿意的是哪一部?”
張老想了一會(huì)兒,回答說:“多年來我涂涂抹抹,寫了些雜七雜八的東西,要問我最滿意的是哪一部,實(shí)在不好說。不過,我花費(fèi)時(shí)間和精力最多、寫得比較苦的是《順生論》這本書。我從上大學(xué)開始,至今70余年,一直致力于思考和研究人生哲學(xué)問題,這本書算是這方面的一個(gè)總結(jié)和成果吧!”
說到這里,我和張老的三女婿林教授以及前來為張老祝壽的劉德水老師都深有同感。正如有人所講,如果說張老的《負(fù)暄瑣話》、《負(fù)暄續(xù)話》、《負(fù)暄三話》是中國(guó)當(dāng)代《世說新語(yǔ)》的話,那么張老的《順生論》就堪稱中國(guó)當(dāng)代的《論語(yǔ)》,的確是一本值得人們用心研讀的人生哲學(xué)教科書。
我請(qǐng)教的第四個(gè)問題是:“張老,您對(duì)后生晚輩有什么希望和囑咐?”
張老想了一會(huì)兒,說了八個(gè)大字:“多讀好書,多做好事。”
張老那天言簡(jiǎn)意賅的談話,一直牢記我的心中。我認(rèn)為這既是張老一生為人、治學(xué)的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也是他留贈(zèng)給我們的珍貴遺言和精神財(cái)富。
張老逝世后,中央電視臺(tái)“東方時(shí)空”欄目緊急趕制了一部專題片,介紹了張老的生平事跡。在選擇采訪對(duì)象時(shí),張老的家人推薦了我。我想,這大概是把我看作軍隊(duì)中張老讀者兼友人的一位代表吧。專題片播出時(shí),使用了張老大女兒張靜、二女兒張文、魯迅博物館館長(zhǎng)孫郁、作家劉心武與我的畫面和言語(yǔ)。他們談得較多,都很好,我排在最后,作為結(jié)尾,說了這樣幾句話:“在這個(gè)世界上,有的人創(chuàng)造了生命的奇跡,但沒有創(chuàng)造學(xué)問的奇跡;有的人創(chuàng)造了學(xué)問的奇跡,但沒有創(chuàng)造生命的奇跡。只有為數(shù)不多的人,既創(chuàng)造了生命的奇跡,又創(chuàng)造了學(xué)問的奇跡。張老就是這樣一個(gè)人。”
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fēng),山高水長(zhǎng)。生前安居“都市柴門”,甘做“布衣學(xué)者”,成為“無(wú)冕名家”的張中行先生,其道德文章、仁者情懷、智者風(fēng)范,將永遠(yuǎn)銘刻在我們心中!
2006年4月3日—9日寫于北京圓夢(mèng)園
(作者系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原兵種部政委、少將;來源:接俸今日頭條號(hào))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gè)人觀點(diǎn),不代表本站觀點(diǎn),僅供大家學(xué)習(xí)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yíng)利性網(wǎng)站,如涉及版權(quán)和名譽(yù)問題,請(qǐng)及時(shí)與本站聯(lián)系,我們將及時(shí)做相應(yīng)處理;
3、歡迎各位網(wǎng)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wǎng),依法守規(guī),IP可查。
作者 相關(guān)信息
內(nèi)容 相關(guān)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wù) 新前景 ?

? 國(guó)策建言 ?

? 國(guó)資國(guó)企改革 ?

? 雄安新區(qū)建設(shè) ?

? 黨要管黨 從嚴(yán)治黨 ?

 剛剛,上級(jí)領(lǐng)導(dǎo)被抓!李鐵“腐敗清單”曝光,令人發(fā)指!
剛剛,上級(jí)領(lǐng)導(dǎo)被抓!李鐵“腐敗清單”曝光,令人發(fā)指! 國(guó)務(wù)院機(jī)構(gòu)改革方案背后的深意
國(guó)務(wù)院機(jī)構(gòu)改革方案背后的深意 2022年10月健在老紅軍統(tǒng)計(jì)
2022年10月健在老紅軍統(tǒng)計(jì)
 戚義明:毛澤東關(guān)于對(duì)美斗爭(zhēng)的六則論斷及其啟示
戚義明:毛澤東關(guān)于對(duì)美斗爭(zhēng)的六則論斷及其啟示 科研資助方式應(yīng)從“競(jìng)爭(zhēng)立項(xiàng)”逐步轉(zhuǎn)變?yōu)椤皳駜?yōu)選人”
科研資助方式應(yīng)從“競(jìng)爭(zhēng)立項(xiàng)”逐步轉(zhuǎn)變?yōu)椤皳駜?yōu)選人” 秦安:股市暴跌!三大原因,兩個(gè)跡象,說明我們必須要打好金融戰(zhàn)
秦安:股市暴跌!三大原因,兩個(gè)跡象,說明我們必須要打好金融戰(zhàn)? 社會(huì)調(diào)查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