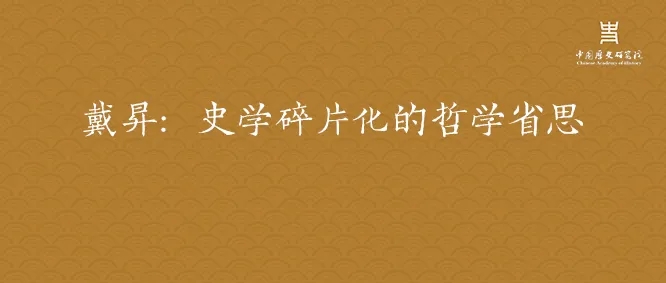史學碎片化產生的根本原因是治史者用孤立、靜止、片面的觀點觀察歷史現象、研究史學問題。
當前歷史學界尤其是新興社會史領域存在較為嚴重的碎片化風險,不少學者見孤木以為森林,拾芝麻以為珠璣,把細枝末節看作是整體全部,更有甚者將研究過程或手段視作學術研究的終極關懷。這種本末倒置的情況長此以往下去,勢必影響歷史研究事業的正常發展。史學碎片化產生的根本原因是治史者用孤立、靜止、片面的觀點觀察歷史現象、研究史學問題,而史學發展的內在理路與外在因素又為碎片化研究提供了發展契機。史學碎片化的實質就是以碎片代替整體,沒有處理好研究對象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其具體表現形式包括以零碎史料為中心的研究、以細碎個案為中心的研究、以表面現象為中心的研究、脫離整體的部分研究等。欲要跳脫出史學“碎片化”的泥沼,人們需要借鑒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有當治史者切實做到運用聯系、發展、辯證的觀點看問題、謀思路,他們方有可能真正成為高屋建瓴、見微知著、疏通知遠式的歷史學家。
在對現有史學碎片化現象進行觀察、分析與概括的基礎上,我們發現史學碎片化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種。包括以零碎史料為中心的研究、以細碎個案為中心的研究、以表面現象為中心的研究、脫離整體的部分研究。史料是史學工作者從事歷史研究活動的基本條件。俗語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可以說如果沒有充足史料作為前提,嚴肅的歷史研究是無法進行的。史料對于史學研究而言,它是不可或缺、十分關鍵的,但僅僅有史料的史學研究仍算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史學研究。因為史料本身是零碎的,是以支離破碎的狀態存在的。如果僅僅是對零碎史料本身的研究,它得出的結論同樣是碎片化的,是與更大的時空環境割裂開的。宋學勤就談到:“不少學者掌握某一區域的具體史料,如獲至寶,但寫出來的論文,卻是就史料言史料,陷進了史料堆里出不來”由于就史料言史料,導致這些學者的研究視野嚴重受限,他們“很少去考慮這些具體史料產生的國家時空背景與復雜因素,找不到‘小社會’變遷的‘大社會’的內在邏輯。”行龍同樣意識到這個問題:“就史料言史料,不能很好地將‘小地方與大歷史’的復雜關系全面客觀地訴諸筆端。”史料本身是零碎的,但史學研究不應該是零碎的。若要將零碎的史料連綴成整體,就需要史學工作者發揮主觀能動性,從中做一些穿針引線的工作,打通零碎史料之間的聯系。明確的史學問題意識是學者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重要表現,正如法國史學家勒高夫所提倡的問題史學一樣,它“不是一種讓史料自己說話,而是由史學家提出問題的史學。”很多碎片化研究的特征之一就是缺乏問題意識,將研究零碎史料作為終極目標,這其實嚴重背離了史學研究的宗旨。史學工作者需要將零碎的史料凝練成具有共性的問題,并將問題意識貫穿在這項史學研究之中。唯有如此,史學研究才會化碎為整。治學功力亦是克服零碎史料研究的重要因素。換言之,大量碎片化的研究只有史料的簡單堆砌,沒有鞭辟入里、發人省醒的歷史分析,原因就在于相關學者缺乏深厚的治學功力。歷史學家嚴耕望談到:“研究歷史最主要的是要運用頭腦長時期的下深入功夫,就舊史料推陳出新,不要愁著沒有好的新史料可以利用。新的史料總有出盡的一天,難道新史料出盡了,歷史研究的工作就不能做了嗎?”史家應該運用功力與智慧駕馭零碎的史料,而不是被零碎的史料牽著鼻子走。但同時我們也要防止以論代史、以理論或思想剪裁史料的情況。因為我們要遵循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即客觀歷史事實決定史學認識,而不是反之:“各種史料都是磚瓦,建立起來一座已往歷史的大廈的,則有待于歷史學家這位建筑師心目中所構思的藍圖。那是它思想勞動的成果,而不是所謂的事實在他心目之中現成的反映。”世界是一個普遍聯系的世界,歷史上每一個人、每一個村鎮、每一個團體、每一個國家都是與當時的世界歷史密切聯系的,不存在完全獨立的、脫離于歷史背景的個人、村鎮、團體與國家。個人是與國家、社會存在緊密聯系的:“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歷史學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將這種普遍聯系實事求是地揭示出來。但目前學界卻存在一些以細碎個案為中心的研究。區別于整體史關照下的典型個案研究,這類研究打著實證的幌子,無視人與人之間、個案與個案之間的聯系,忽視整體史的目標,將個案研究作為終極關懷。這就如恩格斯所言:“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了它們互相間的聯系……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類研究集中體現在新興的社會史領域,因為社會史研究對象下沉極易造成研究者“一葉障目”的風險。治社會史者一旦受功力、視野所限,就很有可能出現以碎片要素代替整體的現象:“碎片化鎖定歷史內容的某個或若干個要素,對其內部更加細化的要素進行愈加細化的逼視,不斷地向具體情境靠近,進而用要素換掉整體性的歷史。”歷史研究不能“撇開歷史的進程”,不能將歷史的細節看成是“抽象的”“孤立的”“單個人的”東西,而應當看成是“社會的產物”“普遍聯系的東西”。因為歷史時期的人與事是普遍聯系的,所以真正的歷史研究不會出現沒有聯系的個案研究。非細碎的個案研究都是以“見微知著”與“以小見大”為特征,以回應整體歷史所關切的學術問題為旨趣。換言之,具體個案研究都是在整體史的觀照下進行的,都是在正常學術史的脈絡下進行的,都是能回應并推進學術史演進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一些個案或碎片研究是在整體史觀或宏觀論述的倒逼之下完成的,所以它與生俱來就有著與學術史對話的性質,從而避免了碎片化。 現象是了解事物本質的關鍵要素,歷史學家功力的重要體現就是透過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看到歷史發展的本質。恢復歷史事實、呈現歷史現象并不意味著歷史研究工作的終結,因為在歷史認識當中除了考證性知識與抽象性知識之外,還有一項更為重要且復雜的知識,即價值性認識。沒有價值性認識的史學研究,就如沒有靈魂的人一樣,它是漂浮碎片化地存在。所以,李紅巖就曾指出所謂“碎片化”就是治史者僅僅停留在完成考證性知識與敘述性知識,放棄了價值性知識的追求:構成碎片化研究的兩個要素,一是選題缺乏與歷史研究相匹配的價值意義,二是認為具體的考據工作是史學研究的全部與最終目的。史學研究的價值性知識就是史家通向歷史發展本質的有效途徑:“‘碎片化’之所以存在不在于其區域研究的劃分,而在于其缺乏對各類社會現象所能表達的意義及其蘊含的社會變遷的內在機理的分析和理論抽象。”只有歷史現象的簡單描述、缺少理論分析與思想深度的史學作品必將列入碎片化的行列。李長莉強調:“如果所作論題僅止于對某種具體事象的實態描述,一味追求平面化的‘深描’與‘細述’,即使十分清晰地還原了事物的原貌,其意義仍然微弱。”史學工作者對歷史事實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如果沒有宏觀意義的闡釋,揭示其‘何以如此’的深層根源及邏輯關系,則只是缺乏意義關聯的歷史碎片。”有的學者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歷史學界內“仍然存在一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事實不見分析,只是講是什么而不講為什么的傾向。”為避免這種以表面現象為中心的史學研究,學者們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增強自身的理論思維,要努力探尋歷史深處的曲徑通幽:“已往的歷史研究大多只限于表層的記敘,只把歷史現象歸結為某些抽象的詞句或概念,就此止步。但歷史的主人是有血有肉的心靈,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或體現,歷史研究最后總需觸及人們靈魂深處的幽微,才能中肯”只有將隱藏在歷史現象深處的本質揭示出來,只有將社會發展的內在機理分析出來,只有將人們心靈深處的普世價值鉤沉出來,才可以算得上是史學研究工作的完成,不然的話就會陷入碎片化之流。部分與整體是一對辯證的相對概念。部分是整體的組成部分,整體是部分有機的集合體,兩者有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聯系。部分與整體是相對而言的,團體相對國家而言,是國家整體中的一部分;而個人相對團體而言,又是團體整體中的一部分。客觀世界不存在絕對的部分與整體,只有相對的部分與整體。在歷史研究中,斷代史是通代整體史的部分,區域史是國家全域史的部分。斷代史與通代整體史是密切相關的,每個斷代史都是通代整體史賴以成立的基礎,每個斷代史都深受通代整體史的影響,都帶有通代整體史的影子。區域史與國家全域史的關系也同樣如此。而目前學界卻存在一些區域史與國家全域史、斷代史與通代整體史完全割裂開來的現象,沒有很好地體現歷史研究中時間和空間的延續與聯系。在時間上,有的學者對于所處斷代較為熟稔,而對于前后朝代卻知之甚少,“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更是離司馬遷所倡導的史家“通古今之變”有很大的距離。在空間上,有的學者僅熟悉自己所研究的區域,對于其他區域或更大區域的發展狀況就無從知曉了。這種脫離于國家整體史的區域研究,其實質就是碎片化:“‘當地’畢竟總是整體中的‘當地’。不應當以‘當地’去消解整體。脫離了整體的‘當地’,即使地域再廣、范圍再大,也只能是孤島,因而在觀念本質上屬于碎片。”這些碎片化的區域史研究成果其實就是裹著學術外衣的地方史,無異于以時間與地域為斷限區隔的地方志,這就很大程度上就降低了區域史研究的學術價值。很多打著區域社會史口號的學者都將自己家鄉作為研究對象,并對其家鄉進行了一些田野調查,宋學勤譏諷這種碎片化的區域社會史研究為“家鄉歷史學”,她說到:“如果每個研究者都只專注于自己的地域,你的家鄉我不了解,我的家鄉你沒興趣,滿足于個人的‘自言自語’,這樣一來,中國社會史研究很難形成具有內在統一規范和使命的學術共同體,鮮有可以共同討論的話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無論是在研究人類整體歷史,還是在研究其有機組成部分的時候,皆強調從研究對象的整體出發,將部分置于整體中加以考量,密切關注研究對象及其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并運用聯系、發展、辯證的觀點審視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以探求事物的本質與規律性認識。概而論之,歷史研究過程中少不了零碎史料、細碎個案、表面現象與部分研究,但完全以上述內容為學術研究的終極目標的話,將不可避免地陷入史學碎片化的泥沼之中。勒高夫曾總結到:“史學最為常見的矛盾無疑便是它的目標是特定的,它可以是一個現象,一系列事件,也可以是某些人,而且其出現也只有一次,和所有其他科學一樣,其目的在于從中導出普遍性、規則性和常態性。”我們需要處理好碎片與整體、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整體研究需要建立在扎實的碎片研究之上,普遍性的規律與事物本質是通過眾多特殊性個案與事物表象進行歸納演繹而成的。同時,碎片、表象與特殊性也是寓于整體、本質與普遍性之中。
史學碎片化的產生,歸根結底還是由于史學工作者沒有自覺地運用唯物史觀與辯證思維來從事學術研究工作。除了治史者自身的因素外,內在的歷史學科發展路徑與外在的社會變遷因素也都為史學碎片化的產生提供了契機。現將史學碎片化產生的內在學術理路與外在社會因素作一歸納總結,以期深化對史學碎片化的認識。回顧史學碎片化產生的內在學術脈絡,我們可以從國外與國內兩條路徑找到其源頭。首先從國外來看,自上世紀70年代以后,后現代主義與反實證主義史學在西方興起。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核心就是去中心化、去真實性、去主體性,后現代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解構一切,將宏大的歷史事實與事物規律解構得七零八碎。波普爾就明確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總體論意義上的”或“關于社會狀態的”歷史學,他認為目前的史學研究只是所謂的“零碎技術學”“零碎修補學”“零碎社會技術學”等。更有甚者追求雜亂無章、沒有中心目標的研究計劃,他們不僅將研究對象割裂開來,還將一項項學術研究成果也完全孤立起來。如安克施密特指出:“在后現代主義的歷史觀范圍內,目標不再是整合、綜合和總體性,而是那些歷史片段成為注意的中心。”再從國內的學術界來看,隨著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史研究的復興,歷史學界發生了深刻的變革。新興的社會史不僅擴大了史學工作者的研究資料與對象,還為研究者提供了耳目一新的視野與方法。新興社會史的出現的確推動了歷史研究的深入發展,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與風險。社會史的復興與繁盛肇始于它的研究對象、研究資料、研究視野、研究方法,而社會史研究產生的問題也同樣與其研究的對象、資料、視野、方法相關。新時期社會史的興盛與問題是相互依存、相互聯結的,并在一定條件下會相互轉化、物極必反。社會史研究對象雖然得到了極大的拓寬,下層民眾與區域社會也前所未有地被學者們重視了起來。人們再也不只是關注并研究政治、制度與精英,諸如“歷史是帝王將相的家譜”“歷史是偉人的傳記”“歷史是社會精英的記述”等觀點也徹底地被人們所拋棄。但這并不意味著研究者就可以孤立、斷裂地研究下層民眾與區域社會,更不意味著相關學者就可以自說自話、封閉自守。再加上社會史研究對象一旦精深細化以后,不少青年學生乃至學者感慨重要的課題已被“各大山頭”所占據,自己研究的對象只能是更小更細的區域與民眾。如此以來,難免帶來了嚴重的碎片化風險。社會史研究資料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擴充,人們研究歷史的史料來源再也不僅僅是正史與文集了,碑刻資料、口述史料、田野調查等統統被納入史料范圍。這原本是一件對歷史研究大有裨益的事情,但部分學者卻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完全陷入了社會史史料的泥沼當中,以至于無法自拔。為此,有學者指出:“面對浩如煙海的檔案、文獻、文物、著述,我們直觀看到的,通常都是局部的東西,甚至大量的資料碎片。如果不懂得歷史思維,不掌握科學的方法論,極有可能迷失在資料與細節的汪洋大海中。”在社會史“自下而上”的視角與方法指引下,上下互視、多元觀察成為了史學工作者自覺的研究意識。正因為歷史研究視角與方法的多元化,使得歷史認識也無限地逼近了歷史的真實,也使得實現整體史的目標又近了一大步。但是無論社會史的視角與方法多么時髦新穎,它都不能背離社會史的目標是整體史這一初衷。而目前部分學者卻背道而馳地運用一些新奇的視角與方法,“這些新方法和新概念之間缺乏同學科的內在聯系,不僅無法借以架構社會史學的理論框架,反而使社會史研究日趨‘碎化’,背離了建造總體社會史、展示社會歷史全貌的初衷。”任何時代的學術研究都是與其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皆是現實生活的一種映照。前文所述的社會史復興與后現代主義產生都是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史學碎片化的產生同樣也有一定的現實因素。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國家的工作重心發生了巨大轉變,從以政治運動為中心轉向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轉向了相對自由靈活的市場經濟。時代命題也發生了變化,經濟社會發展取代了階級斗爭成為新的時代命題。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其中貢獻最大的當屬千千萬萬個普通人民群眾,人民群眾成為了歷史舞臺上真正的主角。在時代浪潮的影響下,學者們也從國家政治單一的視角中解放出來,開始關注社會的方方面面。部分歷史研究工作者更是從原先關注革命、政治轉向關注并研究社會經濟的變遷發展與人民群眾的社會生活。可以說,以社會史為代表的新興史學因應了時代發展的需求。然而,社會史的研究對象相對于政治史的研究對象而言,它天然地就帶有碎片化傾向。因為政治史研究的政治制度、人物、事件自始自終就帶有統攝全局的特征,其本身就是與更宏大的國家、社會、政局聯系起來的。而如果社會史的研究對象僅僅是普通的個體人物或個別現象,它就會不可避免地成為碎片化研究。李長莉指出:新興社會史研究對象轉向彌散式存在的基層民眾與社會生活,任何單一、具體而表象的社會文化事象所包涵的“單位意義”,與政治史所研究的事件、人物對于社會影響力的“單位意義”相比都要微弱很多,“因此如果只是對這些單一而具體的社會文化事象進行具體而細微的實證描述,單純地‘還原真相’,其意義相當微弱。”通過上述內容,我們知悉了史學碎片化的表現形式及其產生的原因。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只有充分認識、了解矛盾的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獲得化解矛盾的鑰匙。在深入了解史學碎片化是什么以及為什么的基礎上,我們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來破解史學碎片化危機。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物質決定意識,歷史認識必須是客觀存在的真實反映,而不是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歷史、用自己的主觀思想來剪裁史實。馬克思主義先賢談到要“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歷史是過去發生的、一去不復返的,是不能夠全知全解的。歷史學家要想盡可能多地了解、還原史實,他只能通過遺存下來的碎片史料來實現自己的研究目的。相關史料愈多,歷史認識就愈有可能真實且完整。“在科學歷史學中,任何東西都是證據,都是用來作為證據的。”客觀史料決定歷史認識,所以我們只有盡可能多地掌握相關史料,才有可能無限逼近真實的歷史。歷史學家們深諳史料對于史學研究的重要性,所以梁啟超曾說:“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傅斯年更是喊出了“史學就是史料學”的口號來強調史料對于史學研究的重要意義。后世歷史研究工作者還將他那句“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當做了治史的座右銘。充分地蒐集史料是歷史研究工作的必要不充分條件,若要完成歷史研究的整個過程,它還需要歷史學家在其中進行穿針引線、化碎為整的工作。正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李大釗所說:“種種歷史的記錄,都是很豐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須要廣搜,要精選,要確考,要整理。”豐富且完備的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必要材料與基礎條件,但史料并不代表就是過去發生的全部史實,“不能說他們就是歷史。這些卷帙,冊案,圖表,典籍,全是這活的歷史一部分的縮影,而不是這活的歷史的本體。”人們是無法完全復原過去發生過的歷史本體,我們只能通過這些遺留下來的“碎片”史料去盡可能描摹歷史本體的圖景。任何社會歷史現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深層次的本質與結構都是處于聯系之中。“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歷史學就是一門將過去與現代聯系起來的學問,馬克思曾說:“過時的東西總是力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復和鞏固。”所以,我們要善于找到歷史事物在空間與時間上的聯系,并將歷史遺留下來的史料碎片聯系起來。列寧也同樣談到:“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么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目前學界出現的碎片化問題很大程度上就是沒有運用聯系的觀點從事研究活動,部分學者就史料言史料,就個案言個案,就現象談現象,就部分談部分,沒有將零碎的史料、個案、現象、部分納入更大的聯系之中去考察。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先驅馮爾康先生曾指出:雖提倡多做微觀的題目,但這并不意味著把一個事情本身說清楚就結束了,而是要盡可能地把它和更廣闊的社會現象、宏觀問題聯系起來,看能否說明一個更大的問題。所以,我們在進行具體史學研究的時候,要避免就事論事,要將研究對象置于更廣闊的歷史時空環境之中。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將國家政策實施與基層社會反響割裂開來,才不會將革命運動發展與社會群體活動割裂開來,才不會將經濟發展變遷與日常社會生活割裂開來。事物不是一成不變的,歷史本體是不斷運動發展的。歷史上的人和事都會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變化而變化。“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蘊含的就是這個道理。研究者要始終關注研究對象本身的歷史發展變遷,要注重其內部的變化發展。要采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研究相關事物在時間上的延續與斷裂與空間上的延續與斷裂。此外,歷史認識也是不斷運動發展的。這里的“歷史認識”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因為歷史本體發生變化而引起的歷史認識的變化,第二種是歷史學家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體現。第一種歷史認識的變化是唯物史觀在歷史研究活動中的具體體現,客觀歷史本體決定歷史認識,歷史認識隨著歷史本體的變化而相應發生變化。恩格斯曾說到:“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任何歷史認識都是與其歷史史實相關聯的,不存在脫離于歷史本體的歷史認識。第二種歷史認識活動的變化是歷史學家根據時代發展需要而進行的。歷史是由活著的人和為了活著的人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我們是否研究過去,這對過去自身絕無影響。換言之,我們研究過去是為我們的緣故……我們是為自己的緣故研究過去。”每個時代因為有不同的社會現實,必然也會產生不同的學術問題、旨趣與關懷。“歷史學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它始終處在變化的過程中,不同時代歷史學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是由現實所提交的,從而每一時代都有屬于這個時代的歷史學。離開了對現實深切和真摯的關懷,歷史學將成為一潭死水。”歷史學研究的宗旨就是對人類歷史活動規律的總結,以求更好地服務于人類本身的美好生活。 整體是由部分組成的,部分是整體的部分。每一個人組成了社會,同時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社會的影響。用陳寅恪的話說就是:任何“具體之一人一事”,都始終反映著所處時代和社會文化那“抽象理想之通性”。整體史是由各個部分的歷史有機組成的,各個部分的歷史是在整體史的關照下演進的。但目前學界的現狀卻是將整體史與各個部分的歷史人為地割裂開,以致于整體史、通史沒有建立在扎實的專史之上;各個部分的歷史各自為戰,見孤木以為森林,拾芝麻以為珠璣,過分追求歷史的細枝末節,缺乏對全局的認識與把握,陷入了嚴重的碎片化之中。整體史應該建立在扎實的碎片、部分研究之上。我們反對的是碎片化研究,不是反對碎片研究。歷史學是一門實證的人文社會科學,它離不開詳細的考證與具體的個案研究。只有研究透每一個人、每一個村落,才能真正了解群體與地域之內的個體是否存在共性,是否能將其視為整體。我們必須了解“非碎無以貫通”的道理,顧頡剛談到:“必有零碎材料于先,進一步加以系統之編排,然后再進一步方可作系統之整理。”若只“要系統之知識,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猶欲吃飯而不欲煮米。”有些因時代因素而虛假繁榮的東西,一旦風云突變,其轉瞬間就會“煙消云散”,所以顧氏強調:“與其為虛假之偉大,不如作真實之瑣碎。”不以扎實碎片研究為基礎的整體研究就宛如空中樓閣,是經不起時間的長期考驗的。部分的歷史或碎片研究要在整體史的關照下進行,才會有意義,才不致于陷入碎片化的困境。如果就微觀言微觀、就部分談部分,它的研究意義畢竟有限,正如彼得·伯克所說:“微觀歷史研究若想規避回報遞減法則,那么其實踐者應多關注更大范圍的文化,并展示小社區和大歷史趨勢之間的關聯。”凡屬成功的部分的歷史或碎片研究,都是“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式的研究,都是從微觀研究中展現了其宏觀旨趣。馬克思、恩格斯在其自己的社會史研究中就強調以整體史的關懷進行區域史或群體史,如在《新發現的一個群婚實例》一文中,他就認為軍隊的歷史并非只是單純的軍隊歷史,而是“市民社會的全部歷史非常明顯地概括在軍隊之中。”王國維同樣強調做史學研究需要“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只有在整體視野下從事微觀研究,才不會造成微觀研究的碎片化:“雖好從事于個別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從一問題與他問題之關系上,見出最適當之理解,絕無支離破碎、專己守殘之敝”微觀研究與宏觀理論本是車之雙輪、鳥之雙翼,它們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但是目前學界卻存在不少將二者割裂開來的情況,從事微觀研究的學者打著自己系實證研究的幌子指責宏觀理論的空疏,而從事宏觀理論研究的學者卻對微觀研究嗤之以鼻、不屑一顧,認為對方的研究瑣碎、無意義。長期以往,學術交流勢必會受到嚴重干擾,最終會導致學術研究的停滯不前。微觀研究是宏觀理論的基石。只有建立在扎實的微觀實證研究基礎之上的理論體系,才會打動人心、令人信服。另外,學者們在進行微觀研究時,還要有建構宏觀體系的理論自覺,要適時總結相關規律性認識,并做出自己應有的理論貢獻。較為出色的微觀研究都是在進行扎實具體研究的同時,嘗試對更宏大的歷史進行解釋。譬如,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馬俊亞的《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1949)》都是從具體區域著手,深入探討研究對象,并將其放入大歷史的進程中進行考察。通過具體區域社會史研究,得出具有普遍共性的歷史認識。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探討的是中央官僚體制下的王朝歷史循環問題,雖然研究對象選取的是秦末漢初,詳細考察了劉邦集團如何漸進轉化為新的統治階層的歷程。最后落實到討論“軍功受益階層”究竟是漢初的特殊產物,還是中國幾千年歷史都始終貫穿的一個重要問題。
宏觀理論為微觀研究指明方向。理論體系在日常微觀研究活動中起到思想引領的作用,沒有宏觀理論的指導,微觀研究無異于盲人摸象。恩格斯說過:“對一切理論思維盡可以表示那么多的輕視,可是沒有理論思維,的確無法使自然界中的兩件事實聯系起來,或者洞察二者之間的既有的聯系。”在史學研究中,宏觀理論與體系框架是駕馭史料的工具,有助于人們在紛繁復雜的歷史表象背后洞察出事物的本質規律。錢乘旦指出:學者有了理論體系才有對史料的選擇,才有對歷史的梳理與書寫。因為史料本身是碎片的,是散亂的,需要歷史學家去收集、整理,并把散亂的史料整合起來,讓它們盡可能地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
在當下信息爆炸、資料碎片化的時代,掌握正確、合宜的理論比任何時代都迫切重要。因為隨著史學工作者們研究歷史的客觀條件大大地得到提升,人們獲取史料的難度極大地降低。在史料同等獲取的條件下,史家之間水平的高下更多取決于雙方的理論高度與功力水平。但是,我們不能將重視理論視為一切以理論為中心,更不能在不顧史實的前提下,用理論觀點剪裁史料、史實。“正確的理論必須結合具體情況并根據現存條件加以闡明和發揮。”理論不是萬能的,歷史研究中同樣不能以理論為旨歸。而要根據實際的史實狀況,在實事求是的前提下能動地運用理論。歷史學家是認識與解釋歷史的主體,歷史認識是歷史學者在研究史料基礎上的主體重構,歷史研究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活著的人與逝去的人、事之間復雜的交流互動。一名歷史學家永遠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思想水平與感受能力去解析歷史。換言之,歷史學者對歷史的理解與闡釋,是取決于他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歷史事件之作為事實,其本身并沒有高下之別,但是歷史學作為對史實的理解和闡釋則有高下之別,它是以史家本人思想與感受能力的水平為轉移的。”所以歷史學工作者不能總是埋頭于故紙堆中做盲目的考據工作,還要時刻進行反思活動,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加強自身的治史功力與技藝。客觀世界是復雜、變化且多元的,歷史學者若要理解客觀歷史世界,必須從其復雜性、多元性、變化性著手,以發揮學者的主觀能動作用。因為歷史本體是復雜的,所以我們要盡可能多地了解它、接觸它,才有可能認識它的復雜全貌。歷史本體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人類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慣性,所以我們能夠間接地通過今日的生活經歷來體悟昨日的事物變化。史家陳寅恪就善于此道,他“從歷史中尋一個與現實極為相似的史實加以發明,因為只有找到與現實相應同時也與個人經歷和情感能產生共鳴的歷史現象,才更適于抒發自己真實的現實感受。”為此,史學工作者要增加生活經驗,以提高對歷史本體的切身感受與深入認識。學者在不同時期閱讀同樣一批史料會有不同的感覺與發揮,就是因為隨著學者生活閱歷的增加,對生活本身有著不同的闡釋,連帶著對歷史現象的感悟也發生了變化。其背后的實質就是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循環往復。張爾田就曾將歷史研究比喻成修補破碎瓷碗,史家的生活經歷在其補碗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歷史事實,當初如一整碗,今已打碎。欲為之補全,其有縫可合者,固無問題;但終不免有破碎無從湊泊之處,即不能不用吾人經驗判斷所推得者,彌補完成。歷史本體也是變化的,畢竟昨日的事物與今日的事物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我們不能用今日的眼光來審視昨日的人、事變遷,也不能用后見之明來構建歷史的發展。所以,歷史學者必須回到歷史語境,用古人的眼光審視古代社會的發展變遷。唯有如此,才能實現歷史認識的相對準確。這就要求治史者必須有一種“了解之同情”的能力,即站在研究對象的角度思考問題,回到歷史場景。陳寅恪就強調史家要“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學者們只有真正的以“了解之同情”的姿態去研究歷史,他們得出來的歷史認識才有可能趨向真實。歷史本體還是多元的,它不是簡單的單面相存在的,而是有其豐富的多元面相。如果我們僅僅是看到了歷史的一個面相,而忽略了它其他面相。那么,我們很有可能就會被其表象所蒙蔽,而不能窺探到歷史的本質。所以歷史學者要善于用不同的視野來觀察歷史、解剖歷史的豐富面相,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當前歷史學界尤其是新興社會史領域存在較為嚴重的碎片化風險,不少學者見孤木以為森林,拾芝麻以為珠璣,將碎片誤認為整體,把細枝末節看作是整體全部,更有甚者將研究過程或手段視作學術研究的終極關懷。這種本末倒置的情況長此以往下去,勢必影響歷史研究事業的正常發展。在打著實證研究幌子的碎片化潮流影響之下,學術界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以零碎史料為中心的研究、以細碎個案為中心的研究、以表面現象為中心的研究、脫離整體的部分研究,凡此種種皆為史學碎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零碎史料、細碎個案、表面現象與部分研究是一項嚴肅的歷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我們不能用要素去替換整體,亦不能罔顧要素之間的聯系,更不能忽視事物要素的發展趨勢。如今,越來越多真正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發現:與表面上呈現繁榮景象的學術大躍進相反的是,近些年來真正能夠打動人心(這里包括學者與普通民眾)并且能夠真正存世的史學著作,諸如司馬遷的《史記》、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等經典著作愈來愈罕見。此外,細心的學者也會發現當今史學工作者彼此之間各說各話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哪怕是在一個范圍不大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團體之內都缺乏溝通、彼此漠視,遑論差別性更大的不同朝代時段研究、不同區域國別研究。更不用說,從事實證微觀研究的學者譏諷形而上理論的空疏;從事宏觀理論概括的學者對具體微觀研究的不屑一顧。以上現象看似可以用學術研究“后出轉精”的原則來解釋,但其實質仍逃脫不了史學“碎片化”的影響。因為“碎片化”式的研究大多不以問題意識與學術史為旨歸,而以史料的堆砌、個案的例舉、簡單現象的描述為特征,長此以往勢必助長“史料獨霸”“占山為王”等不良學術風氣。這既不符合真正學術研究需要相互欣賞、互為奧援的內在要求,也嚴重背離了“學術研究乃天下公器”的學問宗旨。要破解史學碎片化的危機,史學工作者應該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作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內化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將唯物史觀與辯證思維落實到自己的日常研究實踐中去。首先,要堅持唯物史觀,充分掌握史料。因為我們只有掌握了足夠多的史料,才不會將零碎的史料、孤立的個案、表面的現象視作歷史事物的整體。其次,要運用聯系、發展的觀點審視史學問題。人們只有尋繹并打通史料、個案、現象彼此之間的聯系與趨勢,才有可能完整地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才不致于陷入就事論事的泥沼之中。再次,要厘清整體史與各個部分歷史的辯證關系,整體史應該建立在各個部分歷史的基礎之上,各個部分的歷史應該在整體史的關照下進行。另外,要處理好微觀研究與宏觀理論之間的辯證關系。微觀研究是宏觀理論的基石,只有建立在扎實的微觀實證研究基礎之上的理論體系,才會打動人心、令人信服。宏觀理論在具體實證研究中起到思想引領的作用,沒有宏觀理論的指導,實證研究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最后,要發揮史學工作者的主觀能動性,提高其治史技藝。因為歷史研究歸結到底是歷史學者在研究史料基礎上的主體重構,歷史學者對歷史本身的理解與闡釋,取決于他自身的能力與水平。歷史學家的能力與水平愈高,也就愈有可能無限逼近歷史的真實。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中國近代社會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號,轉編自:“近世史研究”,原文刊載于《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報)》2021年第3期,原標題為:《破解之道: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史學碎片化省思》;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昆侖策網】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現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絡時代發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