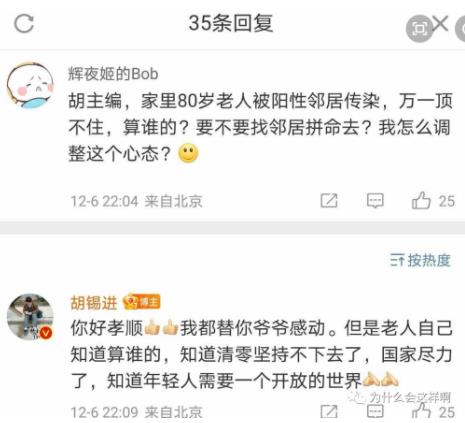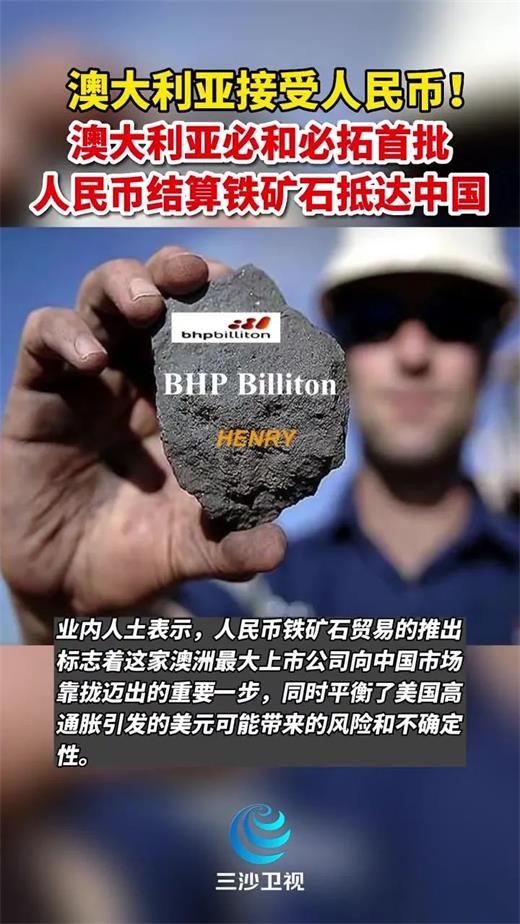每一個岔道上的被拯救者,都不應忘記另一條岔道上的被犧牲者。
01
這幾天,
我從來沒有在微博上,
密集見到這么多訃告。
02
因新冠死亡的,
有教授,
有專家,
有大師,
有院士,
有共和國英雄,
但更多的是,
叫不出名字的普通人。
03
現在看來,
奧密克戎的傷害性確實被低估了,
被專家低估了,
被我們低估了。
奧密克戎不是感冒、不是感冒、不是感冒。
04
我這么說,
并不是反對放開。
當下的中國,
除了放開,
其實已別無他路。
因為經濟矛盾及社會矛盾,
已接近崩潰的臨界點,
再不放開就要出大問題了。
05
關于政策,
社學會領域有一句名言:
政策只有次優解,沒有最優解。
這句話是什么意思?
就是任何一項政策的誕生,
它尋求的都不是對某個群體的最優解,
都不是對少數人的最優解,
而是對整個國家的最優解,
而是對整個社會的最優解。
也就是說,
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對100%的人都友好的政策,
任何一項政策,
對一部分人非常友好,
必然就會對有一部分人非常不友好,
怎么辦?
對于一個國家的政府而言,
他只能選擇對多數人更友好的政策,
只能選擇對整個社會更有利的政策,
這就是所謂的“從大局出發”。
所以一項政策誕生后,
總有一部分人會成為“委屈者”,
總有一部分人會成為“犧牲者”,
這是無法避免的事情。
政策只有次優解,沒有最優解。
06
一項政策誕生后,
總有一部分人會成為“委屈者”和“犧牲者”,
這是無法避免的事情。
那是不是就可以說:
“這是必要的代價。”
“這是必要的犧牲。”
“這就是自然法則。”
“輪到了,就活該倒霉。”
“人各有命,富貴在天。”
當然不可以。
沒有任何人本來就是應該被委屈的,
沒有任何人本來就是應該被犧牲的。
他們被委屈、被犧牲,
只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大局。
沒有他們的委屈和犧牲,
整個社會就不可能有穩定、進步、繁榮的大局。
所以,
越是政策的受益人群,
就越應該體恤政策的受損人群,
就越應該幫助政策的脆弱人群。
因為沒有他們的犧牲,
就不會我們的受益。
07
我為什么要說這件事情呢?
是因為當下很多人,
一點也不體恤疫情中的脆弱人群。
面對高齡老人和新冠亡者,
他們的嘴巴實在是太臭了:
“這是必要的犧牲。”
“這是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活了那么久死了是喜喪啊。”
“這個年紀了,也該壽終正寢了。”
“反正他們都有基礎病。”
“本來他們也有基礎病,又多活了三年。”
“老人本來就有病,新冠只是加速了而已,早死晚死都是死。”
…………
08
這些話真的要把人氣死。
現在我最討厭一種人,
就是一個人因新冠死亡后,
他首先就去看就去問這個人:
“他有沒有基礎病?”
“哦,他有基礎病啊?”
有基礎病怎么了?
有基礎病就活該死嗎?
有基礎病就活該成為代價嗎?
就像作家霜葉所說的:
“‘有基礎病’這幾個字,
不是代表他就該死。
糖尿病一輩子治不好,
但一樣可以活到高壽。
高血壓是挺危險的,
但平時只要正常吃藥,
他一樣可以壽命久長。
甚至很多癌癥患者,
也能靠藥物維持長期生存。
年紀大了,
絕大多數人都有點基礎病,
但他們不是就該死。
別弄得一說有人得了新冠之后死了,
先看‘有基礎病’四個字就覺得人家活該。
你們過了60歲,
絕大部分也會有基礎病的。”
沒有誰天生就該成為那個代價。
09
一輛電車剎車失靈,
它的前方有兩條軌道,
一條軌道上有1000個人,
另一條軌道上有1個人。
根據道德的“最小傷害”原則,
岔道工為了拯救那1000個人,
而把電車扳向了那1個人。
這1個人就活該死亡嗎?
這1個人就活該成為代價嗎?
他做錯什么事情了?
并沒有。
他只是不幸地成了“少數人”而已。
對于這樣的“少數人”,
我們不僅不應該調侃,
不僅不應該嘲諷,
不僅不應該輕視,
還應該施以最大的共情、體恤和照顧,
因為沒有這樣的“少數人”的犧牲,
就沒有我們大部分人的得救。
每一個岔道上的被拯救者,
都不應忘記另一條岔道上的被犧牲者。
10
再往大了一點說:
我們共情、體恤和關照疫情中的脆弱人群,
其實也是共情、體恤和關照“以后的自己”。
因為任何一項政策的誕生,
都會有他的脆弱人群。
這次是他們成為了這個政策的脆弱人群,
下次我們就會成為另一個政策的脆弱人群。
這一次我們共情、體恤和關照他們,
下一次他們就會共情、體恤和關照我們。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之所以能繁榮昌盛,
就在于我們能夠互相共情、體恤和關照吧。
11
如何共情、體恤和關照放開中的脆弱人群?
1、不要過多地去搶藥囤藥;
2、不要娛樂化新冠病毒;
3、把病毒現在的傷害性真實地告訴老人;
4、輕癥別去醫院,避免醫療擠兌;
5、為己為人都要戴好口罩,這個世界不是只有年輕人,還有很多老幼病殘;
6、分享多余的藥品、抗原等物資;
7、在身體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去獻血;
8、為脆弱群體多多發聲;
9、請給犧牲者最起碼的尊重;
…………
12
楊絳寫過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叫做《老王》。
老王是一個蹬三輪車的苦力,
楊絳經常坐老王蹬的三輪車。
作為大知識分子,
楊絳和錢鍾書,
并沒有高高在上,
他倆一直都對老王很好。
但老王去世之后,
盡管自己以前對老王很好,
但不知道為什么,
楊絳每每想起老王,
就會覺得心上不安,
她一直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終于有一天她想明白了,
“幾年過去了,我漸漸明白:
那是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
我們為何要共情、體恤和關照放開中的脆弱人群?
這是一個幸運的人對不幸者的愧怍。
作者:我是拾遺君;來源:拾遺微信號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國策建言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