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涅附言:
因為某種機緣,余涅獲得了毛遠新老師撰寫的《毛主席談科學技術(shù)》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發(fā)表在這里。由于余涅工作粗疏,昨天第一次發(fā)表時遺漏了一段文字,現(xiàn)修訂重發(fā)。特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題圖與文中照片為余涅所加。
~~~~~~~~~~~~
毛主席談科學技術(shù)
1975年12月,在政治局一次批鄧的會議上,主席后來指定列席會議的唐聞生發(fā)言,她說,當時主席的眼睛不能看文件,小平同志要她去把胡耀邦組織編寫的《科學院匯報提綱》讀給主席聽。當她讀到主席1963年在一個什么會議上曾經(jīng)說過:“科學技術(shù)也是生產(chǎn)力”時,主席“嗯?”了一聲,唐聞生以為主席沒聽清,她把這段話又重讀了一遍。主席說:“屁話,我沒說過。”唐聞生還說,小平同志想把他自己的觀點強加給主席。會后我向主席匯報每個人的發(fā)言,當匯報到唐聞生發(fā)言時講的話,我問:“你是說‘屁話’?”主席說:“就是屁話嘛。”主席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說:“(我們)好像討論過。”我當時只想到近幾年和主席的談話,一時想不起什么時候和主席討論過這個問題,就繼續(xù)匯報其他人的發(fā)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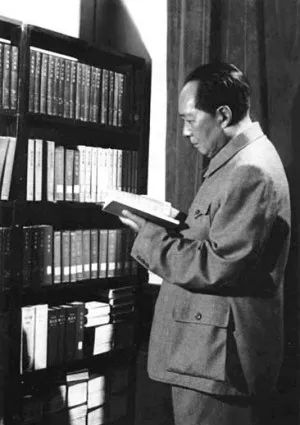
十多天后,我在我的抽屜里偶然翻到一本淺藍色封面的小冊子,才回憶起當年主席給我這本小冊子時,是對我講過科學技術(shù)問題。1965年春夏之交,我因病在北京檢查治療。同時,按照哈軍工導(dǎo)彈工程系戴其萼主任的指示,去七機部一些研究院所找我們系的部分畢業(yè)生開座談會,為導(dǎo)彈工程系下一步教改方案的制定作些調(diào)查研究。我聯(lián)系到七機部王秉璋部長,他幫我安排了幾次座談會,聽取學長們的意見。大約在六月初,王秉璋部長帶我到北京郊區(qū)某試驗場,觀看火箭、導(dǎo)彈的發(fā)動機臺架點火試驗。在返回城里的汽車上,王秉璋部長對我說:“七機部最近搞了個科技成果展覽,很想請主席來參觀一下,能不能替我向主席說說。”我答應(yīng)了他。主席從外地回京后,我到豐澤園北房去看主席。他剛吃完飯,坐在飯桌旁,聚精會神地看一本古舊的字帖拓本。主席先問了我檢查治療情況,接著我談到在七機部開教改座談會的情況。主席說:“你們學自然科學的,要學點辯證法。科學的發(fā)展,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fù)雜,但講課不必都按歷史發(fā)展的順序來講。講原子物理,不從那個玻爾理論講起,從日本的板田講起不行嗎?學習歷史,應(yīng)該主要學近代現(xiàn)代史。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歷史才三千多年,一萬年后,歷史課該怎么講呢?講近現(xiàn)代史,也不能只限于書本,還要到群眾中去了解村史、家史。”我談到王秉璋部長帶我去看了火箭、導(dǎo)彈發(fā)動機的臺架點火試驗,我說在試驗場見到了錢學森,他是哈軍工,特別是我們導(dǎo)彈系學員最敬佩的人。主席說:“錢學森這個人了不起,放棄美國的優(yōu)厚待遇,冒著生命危險跑回來,默默地為國防現(xiàn)代化工作。他讀懂了一些馬列主義,把個人的名和利看透了,把他的知識,無償?shù)孬I給國家和人民,是無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

我順便提道:“七機部最近搞了個科技成果展覽,王秉璋部長要我轉(zhuǎn)告,想請主席去看看。”“我是問你,是科學發(fā)現(xiàn)成果還是技術(shù)發(fā)明成果展覽?”主席放下手中的字帖,抬起頭望著我。“……”我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在我的頭腦中,科技成果就是科學技術(shù)的研究成果,從來不知道還要分什么“科學發(fā)現(xiàn)成果”和“技術(shù)發(fā)明成果”。何況王部長只說是科技成果展覽,也沒具體說是科學發(fā)現(xiàn)還是技術(shù)發(fā)明成果,我還能說什么呢?我說:“這……這不是一回事嗎?”主席說:“在實踐中,科學和技術(shù)的關(guān)系十分緊密,但從哲學概念上講,又不完全是一回事。”見我迷惑不解地望著他,主席放下手中字帖,站起身來端起他的茶杯,走到飯桌側(cè)后的沙發(fā)坐下,指了指他手邊茶幾另一側(cè)的沙發(fā),示意我過去坐下。主席說:“科學主要講的是怎么正確認識世界,而技術(shù)主要講的是怎么更有效地改造世界。科學常用的詞是探索發(fā)現(xiàn),科學探索發(fā)現(xiàn)的是本來就客觀存在,只是人類目前還不曉得的物質(zhì)運動規(guī)律。技術(shù)常用的詞是發(fā)明創(chuàng)造,是發(fā)明創(chuàng)造出世界上原本沒有的東西。探索發(fā)現(xiàn)在英文里是discovery,發(fā)明創(chuàng)造在英文里是invention,這兩個英文單詞在概念上分得很清楚,不是一回事。這是林克(主席的秘書兼英文教員一一作者注)告訴我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把科學技術(shù)分成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說法。發(fā)現(xiàn)我對他說的話很感興趣,主席撳了一下捌在茶幾臺布上的電鈴,叫衛(wèi)士給我也端來一杯茶。

主席說:“科學研究的是宇宙發(fā)展變化的客觀規(guī)律,這些規(guī)律本來就客觀存在,不是人創(chuàng)造出來的。人類所做的事就是去發(fā)現(xiàn)它,認識它。人類出現(xiàn)后,科學又包括了研究人類進化和社會發(fā)展的運動規(guī)律,還有人類思維的運動規(guī)律。探索發(fā)現(xiàn)這些規(guī)律,上升到理論,就是科學發(fā)現(xiàn)的成果。居里夫人發(fā)現(xiàn)了鐳的放射性,這是科學家做的事。但鐳的放射性不是她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從鐳這種物質(zhì)誕生那天起就客觀存在。根據(jù)放射性理論,有人發(fā)明制造出X光機,能檢查癆病。我看,發(fā)明X光機器的人叫技術(shù)專家或發(fā)明家是否更恰當些。”主席從茶幾上拿起火柴盒,晃了晃說:“物質(zhì)由分子組成,分子又是由原子組成,原子里邊又有原子核和外層電子,原子核里又有什么中子、質(zhì)子等等,這不是人類創(chuàng)造出來的,是物質(zhì)從它誕生那天起就客觀存在。科學家所做的就是發(fā)現(xiàn)原子的構(gòu)造,上升到理論就是原子物理,核物理學。而利用這些理論去改造世界,去造原子彈、核電站,這主要是工程技術(shù)專家的工作了。有人把質(zhì)子、中子稱作基本粒子,認為它們是最小的不能再分的粒子了,我看不見得。原子物理我是外行,但我曉得點辯證法,我就不信已經(jīng)分到頭了。古人說過: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就是辯證法。按元素周期表的說法,金銀銅鐵錫,不同元素之間的區(qū)別,主要就在于原子核里質(zhì)子中子的數(shù)量不同。你有本事把鐵的質(zhì)子數(shù)增加到金的質(zhì)子數(shù),你就發(fā)財嘍。難怪古代就有點石成金之說,大概是改變質(zhì)子中子數(shù)的技術(shù)實在太難了,幾千年來,那些方士術(shù)士道士,沒一個能把鐵從八卦爐里煉出金來。”我忍不住笑了,主席自己也笑了。我說:“我一直把科學技術(shù)當成一個概念,科技科技地講慣了。”

主席說:“什么是宇宙?宇者,空間也。宙者,時間也。空間,大到萬億光年之外,小到質(zhì)子中子之間。什么是時間?我也說不清,它似乎永遠流動著,沒有頭也找不到尾。所謂年、月、日、時的說法,是人們在觀測天象摸到點規(guī)律后,人為地規(guī)定出來的,也只適用于地球范圍,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的人作出的規(guī)定也不同,所以又有農(nóng)歷陰歷陽歷之分。隨著時間流動,所有物質(zhì)都在空間運動著,整個地球,在宇宙中也不過只有這么一點點。”他把左手的拇指尖,頂在小指尖上比劃著,“人類的歷史,從類人猿算起,也只有這么一點點時間。”他又把右手的拇指尖,頂在小指尖上,雙手同時上下晃動比劃著。主席說:“人類總想弄明白宇宙是怎么回事,總想找出點規(guī)律性的東西來。那么宇宙中的萬物運動變化,有沒有規(guī)律可循呢?人類社會發(fā)展變化有沒有規(guī)律可循呢?科學家認為是有的,我也相信有。探索這些規(guī)律,發(fā)現(xiàn)認識它們,這就是科學家的工作。我們說人定勝天,對不對呢?我看還是對的,總不能說聽天由命是對的吧?人類不斷探索大自然的運動規(guī)律,就是不愿意聽天由命。氣象學家摸到了一些天氣變化的規(guī)律,就可以預(yù)報陰晴風雨,可以發(fā)臺風警報,這不是人定勝天嗎?古人把月蝕說成是月亮被天狗吃了。哪有什么天狗哇,科學家就不相信,探索結(jié)果發(fā)現(xiàn),不過是地球的影子落在月亮上了。但是,人定勝天是有前提的,就是不能違背客觀規(guī)律,更不能隨意編造規(guī)律,那是要遭老天爺懲罰的。這位老天爺又是哪路神仙?有人說是上帝,有人說是菩薩。我看吶,老天爺就是客觀規(guī)律本身。”似乎想起了什么,主席從沙發(fā)上站了起來,我也跟著站起來。主席用手示意要我坐下,他自己走進旁邊臥室,在床上那半邊書堆中翻了翻,拿了一本淺藍色封面小冊子走出來,遞給我說:“你拿去讀讀。”我接過書,書名是《海陸的起源》,作者是奧地利的魏格納,李旭旦翻譯,商務(wù)印書館1964年出版。(見附件)

“這本書的作者叫……”主席一時想不起來,我忙把書遞過去,指著封面上的字說:“叫魏格納。”主席對封面只瞄了一眼,坐下來點燃了一支香煙說:“這個魏先生是個了不起的科學家。他的學說在半個世紀前曾有許多人反對,現(xiàn)在反對的人少了。他發(fā)現(xiàn)這個地球上,歐亞大陸和非洲、美洲原先都連在一起,沒有大西洋,也沒有地中海。后來,據(jù)說是因為潮汐與地球自轉(zhuǎn)的緣故才分裂成五大洲、四大洋。魏先生發(fā)現(xiàn)了地殼運動變化的規(guī)律,提出了地殼板塊移動的理論。但是,地殼運動變化規(guī)律,不是他創(chuàng)造的,是億萬年來就在我們腳板底下客觀存在著,所以地球上有地震,有火山。”主席朝我探過頭來:“說不定將來有一天,幾塊大陸又會合在一起。你說可能嗎?”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一時說不出話來。主席說:“我看是可能的。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他自己先笑了,我也笑了。主席接著說:“也許有一天,太平洋又沒有了,中國和美國粘在了一起。”主席朝我瞪大雙眼,故作一付嚴肅的神態(tài)說:“我看,有這個可能噢。”并很認真地連續(xù)點了兩下頭。只當是說說吧,我也故作一本正經(jīng)的樣子說:“中國和美國要是粘在一起,那日本列島怕要遭受滅頂之災(zāi)了。”我翻開書,發(fā)現(xiàn)該書前面幾頁,包括“譯者的話”及“序”等部分,主席用鉛筆畫了許多道道,想來他讀得很仔細。后面正文就沒有畫道了,估計文中專業(yè)術(shù)語太多,讀起來太吃力。也可能他就沒有繼續(xù)往下讀。“古生代石炭紀,距今有多少年了?”我翻著書隨口問道。主席搖了搖頭:“我也不曉得。”

回到王秉璋部長邀請的問題,我說:“我也說不清是科學發(fā)現(xiàn)成果還是技術(shù)發(fā)明成果,不過既然叫科技成果展覽,總是二者都有的意思吧。實際上二者也很難分開。”主席點頭,說:“實踐中有時是難分開的。我們有個科學院,就是郭老管的那個,我們沒有技術(shù)院。我是從哲學概念上講,二者不是一回事。”“那郭老也不是科學家,還當科學院院長呢。”我說。在我的印象里,郭老是歷史學家,是文學家,劇作家。“不對,”主席搖搖手說,“郭老是科學家呢。他是研究歷史,研究甲骨文的專家,怎么不算科學家呢?歷史學、考古學、文字學也都是一門科學,屬于社會科學范疇。社會科學的許多領(lǐng)域,往往都有意識形態(tài)的烙印。”主席說:“你可以讀讀郭老寫的《十批判書》。他在書中的第一批,先批判了他自己。郭老說,以前研究先秦古代史,都是根據(jù)東周以來儒家文人的著述。經(jīng)過對出土的牛骨頭上的甲骨文,青銅器上的銘文考證,發(fā)現(xiàn)自己對先秦歷史的許多結(jié)論是不當?shù)纳踔潦清e誤的。研究先秦古代史,應(yīng)該學學郭老,從考古入手,從烏龜殼牛骨頭,從青銅器入手,不要只停留在古人的故紙堆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有人類思維的科學都是科學,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還有天地之間的萬物和人類社會,凡是探索研究發(fā)現(xiàn)其客觀運動規(guī)律的人,都稱得上是科學家。我看,科學應(yīng)屬于上層建筑范疇。”我說:“科學屬于上層建筑,那技術(shù)就是生產(chǎn)力了。”主席點了下頭,停了一會兒,又說:“我看也不完全。先進的技術(shù)可以極大地提高生產(chǎn)力,如果說技術(shù)可以轉(zhuǎn)化為生產(chǎn)力,恐怕更恰當些。但是這個轉(zhuǎn)化還必須要有許多重要的前提要素,首先得要有勞動著的人,包括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人,這是生產(chǎn)力諸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躍的因素。我贊成林彪說的,人的因素第一。人不僅是部隊戰(zhàn)斗力的第一位要素,也是生產(chǎn)力諸要素中第一位的要素。另外,還得要有土地、森林、礦山,要有空氣要有水,要有生產(chǎn)的原料材料,還得要有廠房有機器設(shè)備,有動力、電力等等要素。離開這些要素,再好的技術(shù)恐怕也只能是紙上談兵,一堆廢紙,不能轉(zhuǎn)化為生產(chǎn)力。”我又提到七機部的科技成果展覽,說:“那我怎么向王部長……”主席搖搖手打斷我說:“再說吧。”他話鋒一轉(zhuǎn):“過去我就批評你,怎么只對科學技術(shù)問題感興趣,對政治不感興趣呢。我現(xiàn)在最擔心的是中國會不會走蘇聯(lián)的老路,復(fù)辟資本主義。看來你是不擔心的,不然為什么從不見你問這方面的問題?”主席揮了一下手打斷我的話:“你就對王秉璋同志說,我最近忙。”

我說:“好的。下個學期我們不上課了,按你的要求下鄉(xiāng)搞半年四清運動,然后回來搞畢業(yè)設(shè)計,明年這時候就該畢業(yè)了。”主席說:“明年就畢業(yè)了?我說過,學校說你畢業(yè),我不承認。因為你常年關(guān)在課堂里,沒有當過工人,不會做工;沒有當過農(nóng)民,不會種田;也沒有當過兵,不會打仗。對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都不了解,算什么大學畢業(yè)?”我說:“我從清華大學轉(zhuǎn)學到哈軍工就當兵了嘛。”主席:“那算什么兵,學生兵不算數(shù)。畢業(yè)后會安排到哪里去呢?”我說:“根據(jù)我的專業(yè)學習成績,很可能分配到七機部的研究機關(guān)。”主席搖頭說:“不好,不好,我不贊成。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又進機關(guān)門,就是脫離社會實際。還有其他分配方向嗎?”主席:“去部隊吧。現(xiàn)在美國正在轟炸越南,看來這個仗會越打越大,就去部隊吧。如果越南要我們幫助,你敢不敢去打一仗呢?”“好!”主席拍著沙發(fā)扶手說,“我們家就只有你一個壯丁了。”主席又問:“部隊裝備的武器你會用嗎?”我說:“我學的就是防空導(dǎo)彈的地面雷達控制,雖然沒有實際操作過,但基本原理我都學過,到部隊再實際操作訓(xùn)練一下,估計很快會使用的。”主席說:“防空導(dǎo)彈好,越南現(xiàn)在就缺防空部隊。步兵輕武器會用嗎?”我答道:“手槍、半自動步槍、沖鋒槍我都會用,但很長時間沒摸了,用起來不熟練。”主席說:“我通知汪東興,叫他把這些槍都拿來給你,一邊繼續(xù)治療,一邊熟悉一下各種槍支。到了戰(zhàn)場上,那可都是看家防身必須的。”“還有”,主席說,“你那個名字太招人注意了,下鄉(xiāng)下部隊不方便,還是換一個好。”(當時,全國都在傳達1964年主席和我在北戴河的談話紀要一一作者注)主席想了想,說:“我叫李得勝,李敏、李訥……你就叫李實吧。實事求是,實實在在,可以嗎?”我說:“沒意見,就叫李實。”第二天,中央警衛(wèi)團一大隊一中隊的中隊長陳長江,按汪東興指示,把手槍、半自動步槍、沖鋒槍都給我送到家來,還拿來槍支分解拆裝的操作說明和一張胸環(huán)靶紙,后來還帶我到靶場去打了靶。回到哈爾濱,我向系主任戴其萼匯報了座談會情況和主席要我畢業(yè)后下部隊并改名李實后,去黑龍江省巴彥縣臨城公社前進大隊搞四清。年底四清結(jié)束回到學院,得知畢業(yè)設(shè)計不作了,提前半年,于1966年1月畢業(yè)。我正式打報告申請更改姓名。經(jīng)軍工學院批準,我的畢業(yè)證書上就寫著“李實”這個名字,并被分配到了空軍。我到空軍司令部報到,吳法憲司令、余立金政委把我安排到軍委空軍司令部第二高炮(即防空導(dǎo)彈)指揮部當參謀。當我興沖沖地把這個消息報告主席時,主席說:“我是要你去當兵,不是去當官。”主席也笑了,說:“參謀不帶長,放屁也不響。算是最小的官了。我是要你離開北京這些大城市,到野戰(zhàn)部隊的基層連隊去當戰(zhàn)士。戰(zhàn)士當?shù)煤茫梢援敯嚅L,班長當?shù)煤眠€可以當連長,那時再考慮到指揮機關(guān)去當參謀。”我又去找了吳法憲司令,把主席的原話講了一遍。當時吳司令很激動,眼眶都紅了,說:“沒想到啊,主席要求得這么嚴。”最后決定,我被分配到空軍高射炮兵獨立四師三營一連三班當了戰(zhàn)士。

回憶當年和主席的談話,我知道了科學主要是如何認識世界,科學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類思維的科學。而技術(shù)主要是如何去改造世界,技術(shù)本身還不是生產(chǎn)力,還要在具備許多必要的前提要素后,才可能轉(zhuǎn)化為生產(chǎn)力。我理解了主席為什么不贊成唐聞生讀給他聽的那個《科學院匯報提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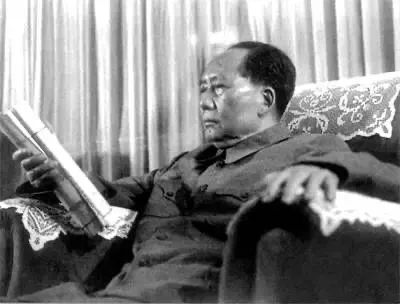
1993年10月,我被安排到上海汽車質(zhì)量檢測監(jiān)督研究所工作。我從報刊上經(jīng)常看到科學技術(shù)不僅是生產(chǎn)力,而且是“第一生產(chǎn)力”的說法。有時報紙頭版有“科學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的標題,而在第三或第四版上卻有文章講:我國有大量的科技成果不能轉(zhuǎn)化為生產(chǎn)力。例如2006年8月12日《中國青年報》第四版文章《我國八成科技成果在“睡大覺” 專家呼吁:盡快扭轉(zhuǎn)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率低的現(xiàn)狀》,作者是新華社記者董踐真。文中說:“人們不禁在問:一方面‘科學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的提出是那樣的令人振奮。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轉(zhuǎn)化卻如此難如人意。這種反差的背后究竟隔著一堵什么樣的‘圍墻’,至今就是打不開它。”既然科學技術(shù)已經(jīng)是第一生產(chǎn)力了,為什么還需要打開一堵“打不開的圍墻”才能轉(zhuǎn)化為生產(chǎn)力呢?這是否說明技術(shù)本身還不是生產(chǎn)力?錢學森的老師馮·卡門先生曾說過:“科學是去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存在的,而工程是要創(chuàng)造世界上從來沒有的。”這里說的“工程”,我個人理解,就是在具備各種必要前提要素的基礎(chǔ)上,多種相關(guān)技術(shù)的系統(tǒng)綜合。2002年11月1日上海《新聞晨報》,通欄大標題是某某人提出的“科學的本質(zhì)在創(chuàng)新”。我認為科學是發(fā)現(xiàn)原本就客觀存在的物質(zhì)運動規(guī)律,這些規(guī)律不是什么人主觀意志可以隨意“創(chuàng)新”創(chuàng)出來的。如果說“技術(shù)的本質(zhì)在創(chuàng)新”可能還說得過去。附件:《海陸的起源》一書的封面及書中的序、譯者的話(說明:書中的鉛筆劃道,都是毛主席閱讀此書時留下的手跡。)


(來源:“新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修訂發(fā)布;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侵刪)
【昆侖策網(wǎng)】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wǎng)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fā)現(xiàn)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wǎng)絡(luò)時代發(fā)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wǎng)》,網(wǎng)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wǎng)站,如涉及版權(quán)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lián)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yīng)處理;
3、歡迎各位網(wǎng)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wǎng),依法守規(guī),IP可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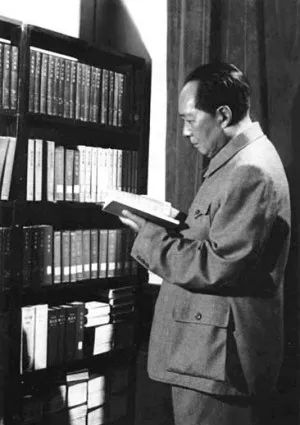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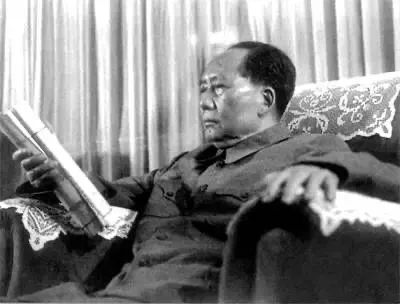









 盧克文:如何評價猶太人?
盧克文:如何評價猶太人? 吳鵬飛丨青島假藥案最終怎么判,全國都在看
吳鵬飛丨青島假藥案最終怎么判,全國都在看 李雪潔:群眾工作就講究個“將心比心”
李雪潔:群眾工作就講究個“將心比心” 何慶濤:黨建無小事 成長在個人
何慶濤:黨建無小事 成長在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