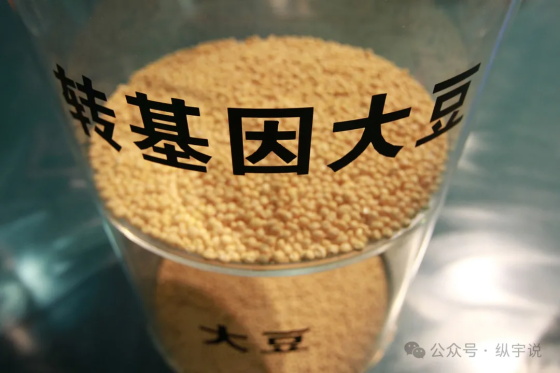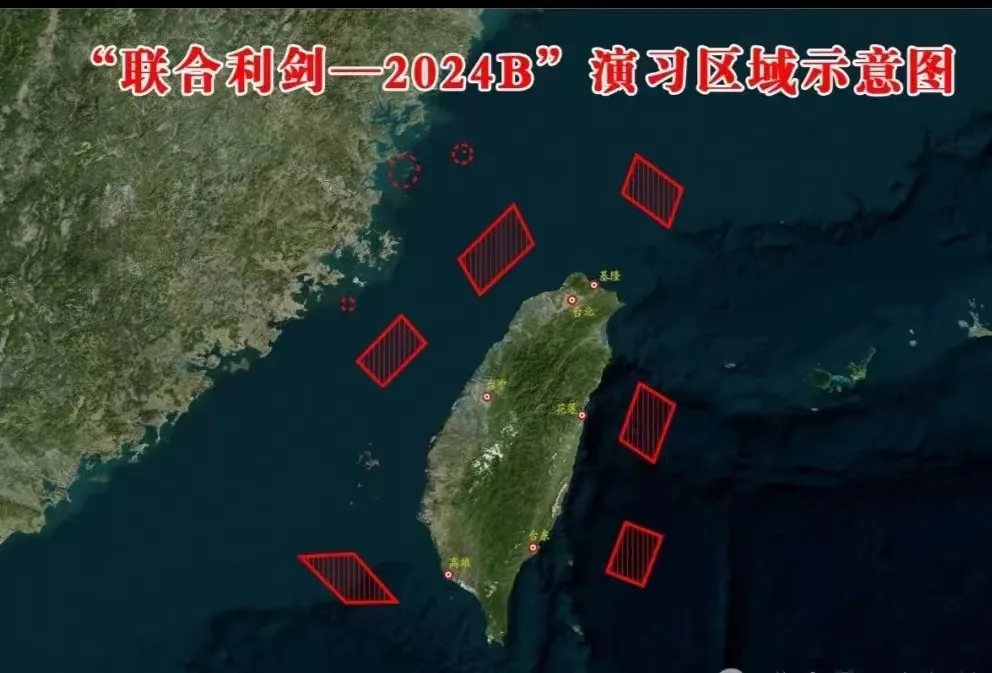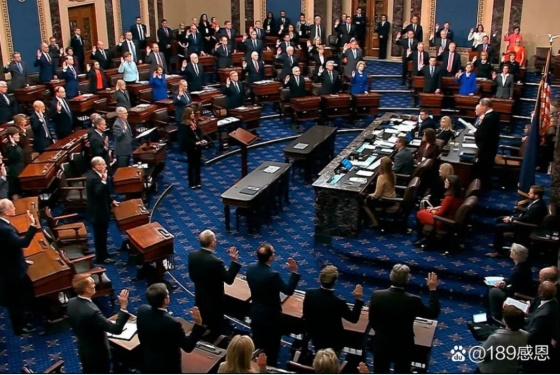【提要】作為歷史記憶重要文本的革命回憶錄,其史料價值、鑒別和利用值得探討。以華南抗日根據地史書寫為例,尤其是書寫南路和北江西岸抗日根據地史,以及瓊崖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等,革命回憶錄是最主要的資料,其史料價值是獨有的,甚至是唯一的。由于革命回憶錄存在“失真”問題,因此對它的鑒別尤為重要。通常的鑒別規(guī)則有:關于記述的時間和準確性,可利用大事記、萬年歷等綜合判定;關于記述的時間(日期)、數字(數量)、地點、人物,以及由上述要素和其他要素組成的歷史事件等,應以親歷者的回憶尤其是多數說法、離歷史事件時間最近的回憶、提及傳統(tǒng)節(jié)日和24節(jié)氣的回憶、得到其他文獻印證的回憶為準,兼以回憶者與歷史事件的親密程度、回憶詳細程度加以判斷。除此以外,研究者還要備齊相關資料和工具書,熟悉宏觀和地方歷史,熟練運用各種網絡工具和史料數據庫,依據人性、邏輯和歷史情境等,對革命回憶錄的內容、行文邏輯、作者的身份及其處境等作多方比較、嚴密推理和綜合判斷,去“非”采“是”。這樣才能利用好革命回憶錄,完成科學的歷史書寫。
與記憶相關的研究論題是近年中文學界的熱門話題。20世紀90年代,隨著記憶研究的引入,中國大陸學界不僅開展了有關記憶研究理論與方法的討論,而且有關于記憶的實證研究。此后,記憶史、口述史、紀念史、概念史、情感史等記憶及其相關研究在大陸學界蔚然興起,成果斐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陸學界的記憶研究似乎仍處于概念界定、學科介紹、理論和方法引介階段。這固然說明記憶研究的方興未艾,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凸顯了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其概念、方法和基礎理論等方面尚需深入探討和多方完善。
本文討論的就是記憶研究相關的理論與方法,即承載記憶的重要文本——革命回憶錄的史料價值及其鑒別利用。這里的革命回憶錄,主要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革命者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自己斗爭經歷的回憶,以及所見所聞所感的記錄。由于年深日久回憶者記憶不清、主觀或受外界因素影響和限制而致回憶錄“失真”等原因,學界有一種傾向,即認為革命回憶錄史料價值不高,甚至基于其意識形態(tài)宣傳因素而將其摒棄不用或極少利用。那么,革命回憶錄到底有沒有史料價值,有多大的史料價值,在實際研究中應如何加以鑒別和利用?對此,一些史料學著作從理論上論述了革命回憶錄的特點、作用和局限,以及利用時應把握的基本原則,部分回答了上述問題。盡管這對后來者極具啟發(fā),但由于不是針對性的論述,加上受寫作主旨限制缺乏案例進行實證。鑒于此,筆者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撰寫《華南抗日根據地史》所使用的資料為例,就上述問題對有關中共華南抗戰(zhàn)的革命回憶錄加以述論,以增進學界對記憶史料價值及其利用方法的認識。
一、中共華南抗戰(zhàn)革命回憶錄的史料價值
華南抗日根據地是對全民族抗戰(zhàn)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軍民在華南地區(qū)創(chuàng)建的東江、瓊崖、珠江、西江、中區(qū)、閩西南潮梅、南路、北江八塊抗日根據地的總稱。每一塊抗日根據地,又由若干塊根據地或游擊區(qū)所組成。撰寫華南抗日根據地史,必須占有豐富多元的史料。檔案史料是學界最為看重的,如1982—1992年中央檔案館和廣東省檔案館合編的《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其中全面抗戰(zhàn)時期的11冊,不僅有中共華南各級組織活動史料,也有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文件,還有華南抗日根據地的情況記載,是最核心、最原始的材料。改革開放后,為編寫中共華南抗戰(zhàn)各抗日縱隊史,相關部門編輯了一些專題史料集,如《東江縱隊資料》《瓊崖革命根據地財經稅收史料選編》《南路人民抗日斗爭史料》《華南抗日游擊隊》等。這類資料,既有檔案,也有報刊,還有革命回憶錄等。其中,不少資料尤其是檔案與《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有重復,但并不完全雷同,無疑是重要的補充。此外,中央檔案館編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南方局黨史資料征集小組編的《南方局黨史資料》叢書,也有一些關于中共華南抗戰(zhàn)的指示、報告、來往函電、報刊資料、革命回憶錄、專題資料和國民黨方面的相關參考資料。這些資料也是必不可少的。
問題是,上述這些資料夠不夠寫一部《華南抗日根據地史》?或者說,能不能勾勒出《華南抗日根據地史》的基本輪廓、基本史實?答案是否定的,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例如,南路抗日根據地。1996年出版的《南路人民抗日斗爭史料》是至今為止關于南路人民抗日斗爭最全的史料匯編。全書共660頁,除去第1—18頁的《南路人民抗日斗爭概述》,剩下的642頁中只有73頁是黨內文獻,包括黨的指示、報告、大會記錄、宣言、決定、來往函電等。這73頁的檔案中,只有23頁是關于南路抗日根據地的,且大部分是中共中央或南方局的指示、林平或中共廣東省臨時委員會和東江軍政委員會的報告、廣東區(qū)委員會的報告等,都是些外圍史料。關于南路抗日根據地的核心史料,其實只有兩篇文獻,一篇是1945年1月4日不足千字的《周楠關于南路情況給董必武及王若飛的報告》,另一篇是同年6月13日(成文時間4月30日)一千五百字左右的《周楠關于南路各縣武裝起義情況給中共中央的報告》。顯然,靠這六頁兩千多字的報告,不要說撰寫南路抗日根據地史,就是把南路人民抗日武裝斗爭寫好都不可能。所幸的是,《南路人民抗日斗爭史料》除了73頁的黨內文獻,還收錄了258頁回憶資料和140頁專題資料。專題資料中除五篇回憶資料外,大部分是地方黨史部門根據當地調查、回憶資料撰寫而成,相當于回憶性資料。只不過由調查時的多人回憶,變?yōu)辄h史部門的記述。筆者在撰寫南路抗日根據地的開辟和建立,以及根據地的政權、軍事、財經、民運、統(tǒng)戰(zhàn)、文教衛(wèi)等建設和工作時,主要依據的是上述回憶資料和專題資料。沒有這些抗日親歷者的回憶錄,顯然無法撰寫南路人民抗日武裝斗爭史,更不可能撰寫南路抗日根據地史。
再如,瓊崖抗日根據地。關于瓊崖縱隊六年多的抗日武裝斗爭史和瓊崖抗日根據地史,相關的黨內檔案史料主要有兩本,一是1986年編印的《瓊崖抗日斗爭史料選編》,一是1987年編印的《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共瓊崖特委文件)》。這兩本文獻無疑是重要的資料,盡管大部分重復。但是,如果僅僅依靠這兩本文獻,瓊崖抗日根據地開辟和建設的許多內容就無法撰寫。例如,關于瓊崖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建設,檔案資料非常缺乏。1984年編印的《瓊崖革命根據地財經稅收史料選編》(一),只有16頁16開本的檔案文獻資料。這16頁資料,大多是瓊崖特委關于財政經濟方面的會議記錄、指示、決定、報告、政策條文等,且沒有1943年的資料。這些資料的大部分在前述兩本檔案史料集中也有收錄。顯然,靠這16頁資料無法撰寫出瓊崖抗日根據地六年多的財政經濟變遷史。同樣的,《瓊崖革命根據地財經稅收史料選編》(二)收錄了80頁16開本的抗日親歷者的專題回憶史料(包括編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而內容屬于抗戰(zhàn)時期的五頁史料)。這些抗日親歷者,有的是瓊崖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的負責人如林詩耀和占力之,有的是地方黨政負責人如王月波、符思之、符風耀、邢保文、李大勛、王壯行等,有的是根據地公營企業(yè)的負責人如陳大新、吳坤寬、吳多武等,有的是稅收征收員或緝私隊員如李高泰、蔣益忠、鄭忠和、周光道、張榮發(fā)、周民鋒等。他們的回憶從不同角度、不同部門、不同地區(qū)反映了根據地的財政經濟狀況。筆者以這85頁的專題財經稅收回憶資料為核心,輔以前述16頁檔案資料,以及其他散在《瓊島星火》、黨史資料和文史資料中的回憶資料等,勉強完成了瓊崖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變遷史的撰寫任務。
相對來說,東江抗日根據地因長期是東江軍政委員會、廣東省臨時委員會、廣東區(qū)委員會等華南黨的領導機關駐地,又有電臺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保持日常聯絡,因此,關于東江縱隊和東江抗日根據地的檔案資料相對豐富一些。但是,這是否意味研究東江縱隊和東江抗日根據地不用革命回憶錄也可以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例如,關于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的“香港秘密大營救”,目前公開的檔案資料只有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員會、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之間來往的十多封電報,分散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共廣東省委文件)(1941—1945)》甲38、《東江縱隊志》之中,內容主要是關于營救的方針、對象、進展等簡要情況。靠這十多封電報是寫不好“香港秘密大營救”的。關于營救的具體決策、布置、路線、人員、詳細過程等,都必須依賴決策者、營救者和被救者的回憶錄資料。這些回憶性資料大部分收集在《東江黨史資料匯編(搶救文化人史料專輯)》第3輯,其他分散在地方黨史、文史資料、個人文集等文獻中。盡管各人所述不同、千人千面,但集腋成裘,正好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反映了營救的過程和面貌。
另外,北江抗日根據地中的北江西岸根據地是1945年2月廣東省臨時委員會決定由西北支隊開辟,并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的。現有大多數資料只是提及它,沒有展開記述,唯有呂蘇和葉培根詳細記錄了西北支隊在清遠的戰(zhàn)斗歷程。可以說,沒有呂、葉的回憶,根本無法撰寫北江西岸抗日根據地的開辟歷程及政權、財經、軍事等相關建設的內容。
總之,對于華南抗日根據地來說,革命回憶錄不是可有可無、可多可少的,而是必不可少的,是主要的資料之一。對有些抗日根據地史如南路、北江西岸抗日根據地史,或根據地史的某些方面如瓊崖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等研究來說,革命回憶錄的史料價值是獨有的,甚至是唯一的。因此,革命回憶錄的史料價值是毋庸置疑的,關鍵是應科學地加以鑒別和利用。
二、革命回憶錄的鑒別方法
盡管革命回憶錄很重要,但一些革命回憶錄確實存在偏離史實、歪曲甚至背離歷史事實等問題。因此,對于革命回憶錄,應該用長避短,科學鑒別,具體方法有五條。
(一)辨明回憶記述的農歷公歷日期及其準確性
作為時間計量單位的年、月、日是否準確,是利用革命回憶錄時必須關注的問題。其中,最易引人誤入歧途的是將農歷日期誤記作公歷日期,或是農歷公歷混用。那么,如何準確判定回憶錄記述的是公歷還是農歷日期呢?通常的辦法是手頭準備幾本地方歷史大事記,如《廣東人民武裝斗爭史(大事記)》《中共廣東黨史大事記(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瓊崖黨史紀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珠江縱隊大事年表》《民國廣東大事記》《廣州百年大事記》《上杭人民革命斗爭大事記》等,因為這些大事記的日期是公歷日期,且已經過編者的細心編訂和考證,錯誤相對少一些。只要將革命回憶錄記載的日期與地方歷史大事記中相應的歷史事件日期進行核對,就不難發(fā)現回憶錄記述的是公歷還是農歷日期。
若要進一步確定革命回憶錄記載的日期是否準確,則需要利用萬年歷,作綜合對比分析。以王濤支隊進軍龍巖為例,1944年10月王濤支隊成立后,部隊由上杭、永定進軍龍巖的日期,依據支隊長劉永生回憶推斷是11月初,支隊參謀長鄭金旺回憶也是11月初,支隊黨總支書記邱錦才回憶是12月中旬;關于部隊進軍龍巖后攻占何家陂炮樓和山狗凹戰(zhàn)斗的日期,劉永生回憶是11月8日,鄭金旺回憶是12月23日,邱錦才回憶是12月27日。以上回憶說明,對于同一歷史事件,其發(fā)生日期存在多種說法。依據邱錦才回憶的部隊是冬至前一天下午攻占湖邦連坑的炮樓后,應巖西北工委負責人吳潮芳派人聯系于12月25日連夜行軍趕到何家陂,而冬至這天是公歷12月22日等信息,可以判斷,劉永生回憶的日期是農歷日期,因為農歷十一月初八正是公歷12月22日。因鄭金旺回憶的日期與劉永生相同,應該也是農歷日期,而鄭回憶的攻占何家陂炮樓和山狗凹戰(zhàn)斗日期,與邱錦才的接近,應該是公歷日期。總之,邱錦才回憶中因明確記載冬至這一天,更具可信性;雖然劉、鄭、邱三人回憶的日期各不相同,但王濤支隊由上杭、永定進軍龍巖的日期在12月中旬、攻占何家陂炮樓和山狗凹戰(zhàn)斗發(fā)生在12月下旬,則是無疑義的。
關于同一歷史事件發(fā)生的時間,革命回憶錄看似有不同說法,但若以農歷日期和公歷日期互相換算,恰恰證實了該歷史事件發(fā)生時間的相對準確性。如,1944年東江縱隊海上中隊突襲日偽軍的“挺進隊”事件。海上中隊小隊長王錦、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和《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六個中隊隊史》(以下簡稱《隊史》)都記述是8月15日,而東江縱隊給上級的報告暨檔案資料記載是9月30日凌晨兩點,另曾生回憶和《隊史》記述的戰(zhàn)果和檔案資料記載不同。這是否意味著是兩次不同的戰(zhàn)斗呢?查萬年歷可知,1944年9月30日正是農歷八月十四,與“15日”相差一天。綜合判斷,筆者認為這是同一次戰(zhàn)斗,應該是王錦、曾生和《隊史》將農歷日期誤記為公歷日期,回憶的具體戰(zhàn)果則只能參照,應以檔案記載為準。
(二)以親歷者的回憶尤其是多數說法為準
除了農歷與公歷問題,當時間(日期)、數字(數量)、地點、人物及由上述要素和其他要素所組成的歷史事件出現多種說法時,通常以親歷者的回憶為準;如果多名親歷者有不同說法,則以多數說法為準,或以離歷史事件時間最近的回憶為準。
第一種情況,以親歷者的回憶為準。如,1941年瓊崖抗日軍事政治干部學校正式開學的時間。祝菊芬回憶為6月,瓊崖獨立總隊第四支隊政治委員陳青山回憶為8月。因祝氏為軍政干校的創(chuàng)辦人,擔任教育處教育長兼政治處總支書記、主任,因此祝的說法更為可信。
第二種情況,以親歷者中的多數說法為準。如,廣州市區(qū)游擊第二支隊(以下簡稱“廣游二支隊”)獨立第一中隊成立的時間。廣游二支隊政訓室主任劉向東回憶,是南番中順中心縣委成立時,即1940年6月第一次會議決定成立的。謝斌回憶,他和謝立全1940年9月到達順德西海,參加中心縣委第二次會議,會議宣布他倆擔任中心縣委委員,負責軍事工作;會議還決定,以林鏗云領導的順德游擊隊為基礎,從中山、番禺縣抽調一批黨員和青年,組成廣游二支隊獨立第一中隊,用黨的這支武裝去影響和改造廣游二支隊。林鏗云回憶,中心縣委第二次會議,決定“將我領導的部隊,編入在我黨影響下的抗日武裝——吳勤指揮的廣州市區(qū)游擊第二支隊(簡稱‘廣游二支隊’),成為這個支隊的獨立第一中隊”,會后派謝斌為參謀,林為中隊長。劉向東、謝斌、林鏗云都是南番中順中心縣委和廣游二支隊的領導,都是親歷者,對比他們回憶的內容,謝斌和林鏗云的回憶可以互證和補充,更為可靠。
第三種情況,以親歷者中離歷史事件時間最近的回憶為準。如,1945年5月潮澄饒抗日游擊隊奇襲彩塘的參戰(zhàn)人數。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韓江縱隊第一支隊政治委員吳健民回憶四十余人,游擊隊隊員許務回憶四十多人,隊員許云勤回憶三十多人。三人回憶中,許務回憶于1955年,離戰(zhàn)斗日期不過十年,而許云勤和吳健民回憶于20世紀80年代,且許務回憶的人數得到吳健民的證實。另外,許務還回憶,彩塘的偽區(qū)署駐有一個偽聯防中隊五十多人,警察所有三十多人。雖說游擊隊是突襲,但倘若人數過少,顯然難有勝算。加上許務詳細描述了戰(zhàn)斗的過程等細節(jié),他的回憶遠比許云勤的回憶詳細、豐富。綜合分析,許務的回憶更為準確。
(三)以提及傳統(tǒng)節(jié)日和24節(jié)氣的回憶為準
若回憶錄中提及春節(jié)、元宵節(jié)、端午節(jié)、七夕節(jié)、中元節(jié)、中秋節(jié)、重陽節(jié)、除夕等傳統(tǒng)節(jié)日和立春、清明、夏至、冬至等24節(jié)氣,則這種回憶相對而言更為可信。因為民國以后,盡管公歷紀事開始在中國采用,但并不普遍,且一年中的某日發(fā)生某事實難準確記憶,而傳統(tǒng)節(jié)日和24節(jié)氣將一年劃分成二三十個區(qū)段,且傳統(tǒng)節(jié)日和24節(jié)氣必將伴隨著相關日常慶典、具體農事等活動,這些活動構成了民國時人包括革命者的日常,令人印象深刻。
以1945年潮汕人民抗日游擊隊正式成立的日期為例。黃偉萍回憶是2月27日(舊歷正月半),揭陽三、五區(qū)的武裝在京溪園的田埔沙壩集中,嗣后同潮普惠、潮澄饒和潮揭豐的武裝匯合而形成。汪碩波回憶,大概是“陰歷元宵過后十天八天”,揭陽方面約一百人,經老虎徑、石牛埔沙犁潭、普寧的牛穴坑,第二天到白暮洋,在白暮洋宣布成立。方東平回憶,在“二、三月份”;黃佚農回憶,揭陽水流埔的隊伍于“元月二十一晚(公歷三月五日晚)在石牛埔”集中。林川和黃業(yè)在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韓江縱隊成立40周年的紀念講話中都說,2月28日部隊會師于白暮洋,正式成立。林、黃兩位的說法,可能來自地方黨史部門,因為中共汕頭市委黨史辦公室就是持2月28日成立說,并記述該日部隊發(fā)表了《潮汕人民抗日游擊隊宣言》。
從上述親歷者的回憶(黃業(yè)不是親歷者,他是東江縱隊的——筆者注)可以得出幾點認識:1.潮汕各地的部隊是元宵節(jié)(正月半)后,開始逐步集中的。過完元宵節(jié),部隊陸續(xù)集中,符合民間正常倫理和日常習慣。2.部隊是集中到白暮洋后,正式宣布成立的。3.部隊成立的具體日期不清楚。4.從汪碩波和黃佚農的回憶可以推斷,2月28日成立說是錯誤的。實際上,檔案文獻顯示,部隊發(fā)表宣言成立的日期是1945年3月13日,而這一天正是農歷元月二十九,與革命親歷者的回憶正好構成完整的證據鏈。寫于1946年的《韓江縱隊簡史》記述部隊成立日期是1945年1月25日,如果是農歷日期,其對應的公歷日期是3月9日,與13日比較接近,相對可信。顯然,黃偉萍回憶中提及的“舊歷正月半”和汪碩波回憶中提及的“陰歷元宵”是我們理順歷史事件時間順序的關鍵。
(四)以得到其他文獻印證的回憶為準
當親歷者有兩種以上不同的說法、難以確定時,通常以得到其他文獻印證的回憶說法為準。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
一是關于部隊人數。1945年潮汕人民抗日游擊隊在白暮洋村成立時的人數,林川個人以及林與古關賢、吳健民共同的回憶有三百多人槍。汪碩波回憶是兩百人左右,包括揭陽方面的一百人左右、普寧方面的一百人左右,另有潮梅黨組織負責人林美南等領導的各種各樣的工作隊。吳健民個人回憶是兩百余人。以上三種說法,難以判斷。關于這個問題,《韓江縱隊簡史》記述,“在普寧流沙成立二百余人的潮汕人民抗日游擊隊,當時配備約有長短好壞槍枝100桿左右”。因為該書寫于部隊成立后一年左右的1946年,人數和槍支數應該比較準確,且其人數得到吳健民、汪碩波的證實,比較可信。
二是關于日期。1943年2月廣州灣淪陷以后,原粵南省委組織部部長王均予與周楠先后由廉江赴重慶找南方局,請求指導工作,但他們回憶的出發(fā)時間,相差兩三個月。王均予由廉江出發(fā),王回憶是1943年5月,周回憶是7月;周赴重慶,王回憶是1943年冬,周自己回憶是1944年3月。另據南方局常委董必武1944年8月4日給周恩來電,周楠“三月來此,六月返南路”。據此可證明周楠回憶3月出發(fā)的準確性。既然周楠回憶中的日期比較準確,那么他回憶的重慶之行,就更為可信。
三是關于某次戰(zhàn)斗日期。1944年港九大隊海上中隊在黑巖角繳獲日軍電扒,生擒日偽兵等,班長曾佛新在戰(zhàn)斗中壯烈犧牲。曾生回憶,戰(zhàn)斗發(fā)生在7月,王錦回憶是11月30日。曾生是東江縱隊的司令員,而王錦是戰(zhàn)斗的參與者,相對來說,王錦的回憶更可靠。更關鍵的是,王錦的回憶得到《隊史》的證實。該書記載,曾佛新墓碑上銘刻的犧牲時間是“民國卅三年十一月卅日”,墓碑立于“民國卅三年十二月一日”。
(五)以符合人性、邏輯和歷史情境的回憶為準
還有一種情況是不僅革命回憶錄有不同說法,其他文獻也有各種說法。在這種情況下,應對其內容、行文邏輯、回憶者和文獻撰寫者的身份及其處境等作比較分析,秉著常情、常理、常性嚴密推理、綜合判斷,以符合人性、邏輯和歷史情境的回憶為準。例如,關于東莞抗日模范壯丁隊的成立日期,革命回憶錄有時任模范壯丁隊隊長王作堯的“11日說”和“15日說”,模范壯丁隊指導員袁鑒文、陳文慧的“15日說”,何佳的“10日前后說”,曾生的“13日說”;其他文獻有15日和13日兩種說法。眾所周知,日軍是10月12日在大亞灣登陸的,所以王作堯的11日日軍澳頭登陸、模范隊成立說是不成立的。同樣的,何佳的“10日前后說”也沒有什么實質意義。那么,到底是15日還是13日?從回憶者身份看,“15日說”的王作堯、袁鑒文、陳文慧都是親歷者,且王、袁是模范隊當時的領導人,而“13日說”的曾生只是同時代人,并非模范隊組建的親歷者。從回憶時間看,最早的“15日說”是1942年黨的文獻,離模范隊成立的時間比較近,相對來說更為可信。從回憶內容看,王作堯、袁鑒文、何佳、陳文慧四位親歷者盡管各有不同,但大部分相同,很多內容可以相互佐證。綜上分析,“15日說”更具可信性。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革命回憶錄和其他文獻說法大致相同,也不能盲聽盲信,還應作進一步分析。如,瓊崖華僑回鄉(xiāng)服務團抵瓊服務的總人數,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工作人員連貫、服務團特支書記符思之、香港團團長范世儒等都回憶說有二百四十多人。學界的研究也大多沿用此說。事實真是如此嗎?瓊崖華僑回鄉(xiāng)服務團下轄香港團、星洲團、暹羅團、越南團。其中,香港團包括硇洲隊,暹羅團回瓊后并入越南團。可是,同樣依據符思之、范世儒等的回憶,香港團第一批和第二批暨第一期、第二期訓練班成員偷渡成功的60人,加上硇洲隊共一百一十多人;星洲團60人、暹羅團10人(其中7人海上遇難)、越南團43人。即抵瓊服務的總人數是223人。如果去除符思之、許廷良、楊維堅回憶的幾個被瓊崖國民黨頑固派拉攏的不堅定分子,那么,瓊崖華僑回鄉(xiāng)服務團實際只有二百二十人左右。這與李德芳、程昭星等引用1940年王兆松報告書說的220人差不多,說明筆者的上述考證和推算是正確的。
三、革命回憶錄的利用
從史料價值看,史學家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指出,回憶錄、訪談、口述等經過中介的第二手史料,其缺陷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特定視角與材料類型帶來的局限性;二是內容的疏漏與缺失;三是必須要加以甄別的扭曲和錯誤。”誠然,作為一種主觀的“個體記憶”性質的革命回憶錄,確實存在希爾伯格所指出的三方面問題。但是,就撰寫華南抗日根據地史而言,它仍是最主要的資料,對南路和北江西岸抗日根據地史,以及瓊崖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等研究來說,革命回憶錄的史料價值是獨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與此同時,由于革命回憶錄是來自抗日根據地、淪陷區(qū)和國統(tǒng)區(qū)等多個區(qū)域不同身份、不同部門親歷者的觀察和記錄,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具有多元性、廣泛性、普遍性等特點,這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彌補希爾伯格所指三個缺陷中前兩個缺陷的不足。
從史料類型看,革命回憶錄是眾多史料類型中的一種;不同的史料類型,其價值難言高下貴賤。雖然檔案常被看作是珍貴無比和最為可靠的原始材料,但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函電、文牘甚至報刊等,若存放于圖書館則稱之為文獻,在博物館則成了文物,而保存于檔案館便是檔案。換言之,檔案不僅是一種史料的類型,也似乎是一種存放史料的方式,無需迷信。革命回憶錄與檔案一樣,既然是史料,就必須經過仔細鑒別才能使用。
本文研究指出,對于歷史記憶重要文本的革命回憶錄,通常鑒別的規(guī)則主要有:要利用地方歷史大事記、萬年歷等判定回憶錄記述的是公歷還是農歷日期,并對日期是否準確作出綜合對比分析;當時間(日期)、數字(數量)、地點、人物以及由上述要素和其他要素所組成的歷史事件出現多種說法時,應以親歷者的回憶尤其是多數說法為準,或以離歷史事件時間最近的回憶為準,或以提及傳統(tǒng)節(jié)日和24節(jié)氣的回憶為準,或以得到其他文獻印證的回憶為準,兼以親歷者與歷史事件的親密程度、回憶詳細程度為判斷標準,越親密的、越詳細的,可信度越高。以上規(guī)則通常情況下是適用的,但并非絕對。退一步而言,即使按照這些規(guī)則處理,仍然會有難解之謎和歷史未知。如,1941年底香港淪陷前后的人數。香港人陳謙記述,淪陷前“人口已將百萬”;茅盾1942年記載淪陷時有一百八十多萬,楊奇1961年回憶有一百八十多萬,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隊員李健行回憶有一百六十萬,戰(zhàn)后葉德偉記載有一百九十余萬。上述五人都是親歷者或當地居民,按說回憶可信度高。而且,根據離淪陷時越近數據可能越準確的鑒別規(guī)則,茅盾和葉德偉回憶最為可信。但即便這樣,五人回憶四種說法,且相差較大,研究者無法論斷。再如,1945年6月金豐會議后,王濤支隊主力南下閩南,在消滅平和高坑民團后,領導群眾破倉分糧。劉永生回憶,參加的群眾達一千多人;支隊政治部主任陳仲平回憶,兩天內分給農民的糧食有三百多萬斤。三百多萬斤糧食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小小的高坑鄉(xiāng)不太可能有這么大的糧倉儲存這么多的糧食。即便以劉永生回憶的一千多名群眾均分計算,一般的群眾根本無法儲存分得的3000斤糧食。顯然,上述兩個案例遺留的難題,僅僅依靠回憶錄無法解決。只有查找新的史料,才可能弄清楚。
必須強調的是,依據上述鑒別規(guī)則,被鑒別為錯誤、模糊或失真的時間(日期)、數字(數量)、地點、人物等,以及由上述要素和其他要素所組成的歷史事件,是僅就已鑒別的對象而言,并非是對該革命回憶錄整個內容的否定。須知革命回憶錄是革命者對自己所見所聞所感的記錄,是個人獨特經歷和視角的觀感記錄。事實上,每個革命者的經歷、位置、視角、觀感等都是不同的、獨特的,其回憶都是對歷史(事件)不同層面、不同角度、不同態(tài)度的反映和記錄,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有論者指出,如果將文獻與口述歷史視為“歷史記憶”,應該研究的是留下這記憶的“社會情境”(指社會人群的資源共享與競爭關系,與相關族群、性別或階級認同與區(qū)分)及“歷史心性”(指此“歷史記憶”所循的選材與敘事模式);社會情境與歷史心性及其變遷,都是應該研究的“歷史事實”;并進而提出“誰在回憶,誰被回憶”等社會記憶的本質問題。西方歷史學界正是“將記憶作為歷史研究對象的領域,研究記憶隨著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歷時性變化”,從而不僅應對了記憶的挑戰(zhàn),“使得歷史學超越記憶”,而且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即記憶史研究。正是從這個角度和意義上,有論者提出,應該開展“中共記憶史”研究,以拓展黨史研究的視野、提供研究的新范式,并回答黨史研究與歷史記憶的關系。這當然是一個富有意義的創(chuàng)見,值得深入開展。不過,本文的主旨仍在傳統(tǒng)的實證研究方面,即作為歷史記憶重要文本的革命回憶錄,恰恰是其不同和獨特的記錄,在現有史料條件下可最大程度地還原歷史,鑒別和利用后可以達至科學的歷史書寫。
當然,要鑒別和利用好革命回憶錄,達至科學的歷史書寫,僅僅運用上述鑒別規(guī)則遠遠不夠,除了備齊地方歷史大事記和運用好萬年歷等工具外,還需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要充分收集全革命回憶錄。只有足夠多的革命回憶錄,才能作比較分析和鑒定,從而更好地還原歷史。二是要對回憶錄的作者,即革命者的身世、經歷、工作和職務變遷、人際關系網絡等基本情況有一定的了解。這方面工作,通過百度、讀秀、超星等網絡搜索平臺,以及人物傳記、人物志等紙本工具書,比較好解決。三是要收集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史資料,如《中國共產黨廣東省組織史資料》《中國共產黨廣州市組織史資料》《中國共產黨廣東省海南行政區(qū)組織史資料》《中國共產黨福建省組織史資料》等。組織史資料對于搞清楚抗戰(zhàn)時期華南各級黨的組織、政權組織、軍事組織、群眾組織的變遷沿革及其隸屬關系、機構成員及其職務等必不可少,盡管其中也有一些錯訛。四是要熟悉宏觀和地方的歷史,如宏觀的中國近代史,廣東、海南、廣西、福建各省和香港的近代史、日偽活動史、抗日戰(zhàn)爭史等。五是要備齊相關地圖,例如廣東、海南、廣西、福建等各省和香港地圖冊,以及中共華南各部隊活動和各抗日根據地的示意圖。以上資料、工具書和著作等對于增進革命回憶錄的理解及其鑒別和利用都特別有效。
總之,在備齊相關資料和工具書,熟悉宏觀和地方歷史,熟練運用網絡查找工具和史料數據庫等情況下,應依據上述鑒別規(guī)則,對革命回憶錄的內容、行文邏輯、作者的身份和處境等,作多方比較,同時秉著常情、常理、常性作嚴密推理和綜合判斷。在此過程中,去除革命回憶錄中的“非”,兼采革命回憶錄中的“是”。只有這樣,才可能利用好革命回憶錄,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觀點,從而完成科學的歷史書寫。
作者:游海華,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暨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教授;來源:《史學理論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釋從略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guī),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國策建言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qū)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 社會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