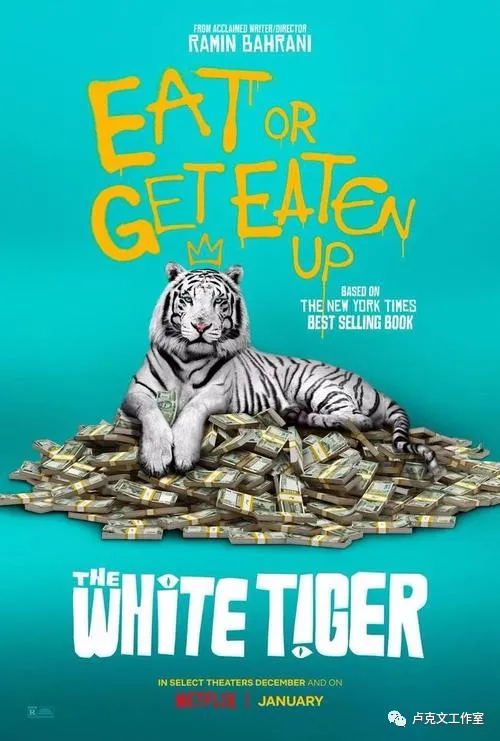韓啟德,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協名譽主席,北京大學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院長。
導讀
中國是否應該學習美國,把發展生物醫學放到最重要的戰略位置上?當前是否處于現代科學范式轉移的重大轉折期?
2020年12月12日,在全國首屆前沿交叉學科論壇暨前沿交叉研究院聯席會上,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院長韓啟德提出了以上兩個問題。
他認為,我們應該充分重視生物醫學的發展,但在我國當前發展階段是否要把發展生物醫學放到物質科學之上,值得斟酌;另外,科學發展到今天,歷經百年的 “傳統” 現代科學范式開始逐漸被打破,甚至可能正面臨巨大的轉變。
與此同時,生物醫學是催生新的科學范式的母體,因為其是巨型復雜系統,采用傳統科學范式難以進一步深入揭示其規律,因此科學家們必須去創造新的研究范式。韓啟德認為,各學科的研究前沿逐漸集中到生物醫學領域,反映了當今科學范式轉移的趨勢,但不能只解決生物醫學本身的問題,還應關注到推動整體科學范式的轉移。
演講|韓啟德
各位同道:
非常高興來參加全國首屆前沿交叉學科論壇暨前沿交叉研究院聯席會,這個聯席會是真正的學術共同體。
今天,我先大概談談我對交叉學科的認識,估計大家已有共識,所以我盡量講簡短些。
從科學發展的歷史來看,開始并沒有學科預設,人們只是有認識自然的樸素愿望和追求。比如仰望星空,從古希臘就開始了,人類從渴望認知自己生活的星球,進而發展到想要知道自己的身體是什么樣的。
牛頓可謂現代科學的創始人,在數學、力學、光學、天文學等方面都有劃時代的貢獻,但那時候的科學還沒有明確分科,他的研究都被劃入自然哲學范疇,他的經典力學著作的書名還是《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即使到了19世紀中期,像焦耳定律這樣的重大科學發現,也還是發表在英國的《哲學雜志》上。
隨著研究內容越來越多,成果越來越豐富,分工也越來越精細。開始時學者們的研究各有側重,比如一部分的學者研究這個多一點,一部分學者研究那個多一點,然后從事類似研究的學者之間的交流增加,慢慢就形成了學術共同體,他們共同研究的內容慢慢就形成了一個學科。
但是探索某一個規律,往往并不局限于某一群人——雖然某些人擅長對某一特定方向的深度挖掘,但在面對一些更大的問題時,就需要不同的學科聯合在一起共同解決,科學發展從來都是如此。
特別是18世紀以后,科學大發展,由于研究內容的迅速擴展,學科也不斷細分。但與此同時,單一學科無法解決的科學問題不斷出現,學科的邊界也在不斷被打破并不斷融合。
兩個世紀以來,學科的分化與融合總是保持著一種張力。例如,生物學的名詞到1800年才出現,當時僅包括地質學(古生物學)、分類學、動物學、植物學,達爾文自然演化理論的提出促進了遺傳學、胚胎學與生物統計學的形成,后來物質科學不斷融入生物學,產生了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細胞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等,到如今連生物學的名字都幾乎改成了生命科學,而生命科學又和醫學緊密結合……這是一個不間斷、動態的分化與整合過程。
學科的交叉與融合,是基于對重大科學問題的探索而促成的。實際上,學科的分類本來就是由研究的問題來決定的——為了解決某個問題,探究某個規律,漸漸形成了學科。因此,當原來的學科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如果相關的研究和技術條件已經成熟,自然會形成新的學科。學科交叉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們現在也多少認識到了這個規律。落實到具體做法,就是要以問題為導向,而不是人為劃界限。如果太著急的話,會造成拔苗助長的現象,或者是出現追風、一擁而上。如果本著以解決問題為出發點的話,自然會形成健康的學科交叉態勢。
在學科交叉當中,本學科是最重要的基礎。交叉需要依靠本學科里做得最好的學者,或者在本學科里有 “一招鮮” 技術的學者。這些人為了解決一些重大問題,逐漸形成交叉學科,而不是先忙著去劃定界限。
學科交叉的發起,從形式上來講,可以從上到下,也可以從下到上。從上到下就是提出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然后組織各有關學科一起研究;從下到上就是某些學科中站在前沿的學者或者掌握“一招鮮”技術的學者相互尋找合作對象,解決跨學科的科學問題。
組織學科交叉研究免不了同行評議問題。學科交叉做什么?怎么做?誰做得好?支持誰?表彰誰?誰出局?這些都需要同行評議,而交叉學科的同行評議特別不容易,需要采取一些特別的做法,如在評審專家的選擇、評審的過程、更多的申訴機會和渠道、評審專家的培訓,等等。這些問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正在研究,科技部、教育部等政府部門也會采取相應措施。未來越來越多的重大科技項目將是學科交叉的,所以改革和完善交叉學科同行評審機制體制刻不容緩。
說到底,要搞好學科交叉,最重要的基礎還是科學精神和科學文化的土壤,這在我們國家尤其缺乏。我認為學科交叉更要重視學風建設,搞好學術文化和科學文化的建設。如果不講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盡管可以組織一些學科交叉的項目,但都只能停留在技術層面上,到達不了更高的層面。
當然,除此之外,還需要國家的重視。學科交叉盡管現在漸漸得到認可和重視,但落實到政府財政投入、相關政策出臺,乃至交叉學會是否能夠盡快批準成立,都還需要努力。
以上講的都是些大家已經有共識的問題,我只是簡單歸納一下。
我今天發言的重點,是提出兩個問題來請大家討論:第一個問題是當前是不是應該把發展生物醫學放到最重要的戰略位置上;第二個問題是當前是不是處于現代科學范式轉移的重大轉折期。
當前生物醫學已經成為最熱門的學科,世界各國競相把發展生物醫學放到戰略重點位置上,我國顯然也是如此。今天會議的報告,基本上都是生物醫學內容。很多高校與科研機構也越來越多地把研究重點放到了生物醫學方向。我昨天下午到中科院先進技術研究院去調研,他們原來的學科布局是六大塊,現在他們開始放棄信息和機器人這兩塊,剩下重點發展的四塊都是生物醫學領域。我國自然科學基金委的經費盤子里醫學和生命科學占了近一半,并且在相關文件里面明確提出學科交叉的重點是生物醫學。我認為這個問題值得研討。具體來說,生物醫學是不是應該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重點?學術交叉的重點是不是應該落到生物醫學上?美國這么做,我們是不是也應該這么做?
我談談我的觀點,不一定對,供大家探討。如果從需求來講,似乎不應該這樣。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工業現代化還沒有完成,在制造業高端還有很多環節不能獨立,國家對物質科學技術的需求太多太大了!
人們可以說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現在我們生活好了,當然要考慮健康,要把生物醫學作為重點了。我認為這樣的說法其實是站不住的。為什么?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決定人類健康的主要因素不是醫學,而是經濟社會發展,是物質生活條件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進,以及教育與社會服務的公平。美國在醫藥衛生上投入那么多,它的生物醫學不可謂不發達,但公眾的各項主要健康指標卻只排在全球第三十幾到四十名。隨著磁共振技術的提高,醫生對人體內的結構能看得越來越清楚,發現的病灶越來越小,能讓更多的人去接受手術,但是這對人均期望壽命的影響卻微乎其微。
也有人說,現在全球范圍內醫療消費需求與市場份額增長迅速,醫藥產業經濟效益高,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支柱產業,所以要把生物醫學研究放到更重要的地位。這個理由同樣不夠充分。我國底子薄,人口多,人均收入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提高衣食住行和教育水平仍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群眾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提高公眾整體健康水平最重要的途徑。即使在發達國家,也不應該主要依靠產業來推動醫療健康事業的發展。當前存在醫藥產業盲目與過熱發展的情況,似乎與背后資本的逐利驅動脫不了干系。
因此,我們應該充分重視生物醫學的發展,但在我國當前發展階段是否要把發展生物醫學放到物質科學之上,我認為是值得斟酌的。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科學范式的轉移。始于16世紀的科學革命催生出現代科學。現代科學在古希臘科學的基礎上增加了幾個要素:一是要求實證,結論需要得到實驗證明;二是要求確定性,能精確定量,乃至用簡單數學公式概括普遍規律;三是要了解機制和因果關系。這些形成了現代科學的范式。
但是科學發展到今天,這樣的范式開始逐漸被打破。量子科學研究中發現很多不可確定性現象;大數據加上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在未經還原和不破解機制與因果關系的前提下發現新的規律;暗物質無法直接見到,人體內的很多功能找不到結構基礎,很多變化完全是隨機發生而無一定規律;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完成以及轉錄組、蛋白質組和代謝組等各種生命組學的進展,正在使假設驅動的實驗研究轉變為數據驅動的研究;甚至現在的研究發現某些規律無法通過實驗方式得到驗證;臨床研究中往往無法做到隨機對照和雙盲,人們開始摸索所謂的 “真實世界” 研究方法,等等。
所有這些,提示科學研究發展到了現今這個階段,由科學革命促成的、在過去幾百年內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范式,可能正面臨巨大的轉變。
說到這里,我的兩個問題就有一些交集了。由于生物,特別是人類,是最典型的巨復雜系統,采用傳統科學范式難以進一步深入揭示其規律,這就逼得我們必須去創造新的研究范式,可以說生物醫學是催生新的科學范式的母體,各學科的研究前沿逐漸集中到生物醫學領域反映了當今科學范式轉移的趨勢。既然各個學科的前沿都集中到生物醫學領域,生物醫學自然就成為眾多學科交叉的集中點了。
眾多學科前沿交叉匯集在生物領域,催生新的科學范式,結果不僅僅會推動生物醫學的發展,而且必然從根本上改變科學技術面貌,惠及所有學科,包括物質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物醫學的發展當然會對人類健康做出直接貢獻,而且可以預言,更加重要的是它將促進科學范式轉變和整體科學技術發展,進而通過經濟社會發展來對人類健康產生更為根本性的影響。
我還想再強調一下,人類演化過程是以萬年、幾十萬年的尺度計量的,從農業革命到現在才一萬年,工業革命到現在才幾百年,人類生活方式發生了如此巨大的根本性變化,人體結構和功能遠遠不能適應這種改變,這是當今人類疾病的根源。因此,解決人類健康問題,最根本的是改善生活方式,而不是依靠醫藥。
總之,我并不反對把交叉學科的重點放在生物醫學領域,但我認為其目的不僅僅限于解決生物醫學本身的問題,重點在于推動整體科學范式的轉移。我們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可能會對當前全世界都涌向這個方向,有一個更為清醒深刻的認識,有利于主動把握方向,有利于根據我國實際情況調控研究重點,也有利于防止受資本蠱惑而走入歧途。
當然,科學范式的轉移不會在短時期內突然完成。原來的范式還會繼續發展,而且新的范式一定是建立在舊范式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的,在相當長時期內新老范式之間將會處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經歷一個此消彼長的復雜過程。
人類從來難以預言未來,歷史從來都只是后人對前人的記錄和總結。伽利略和牛頓創建了現代科學的范式,但他們自己從來沒有總結和表述過這樣的范式,今人也不可能先預知當今是否正在實現科學范式的根本轉移。但是,對歷史與現實多一些考察,多一份自覺,卻是應做的努力。
以上只是我的一些粗淺思考,很不全面,甚至有可能是錯誤的。我這里提出問題,只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討論。
原文來源于《大學與學科》2021年第1期,轉載時略有刪減。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