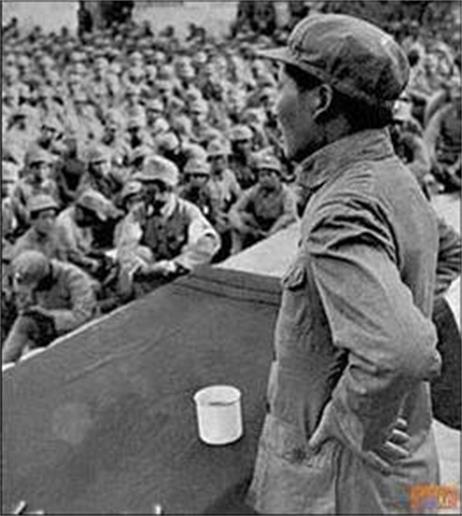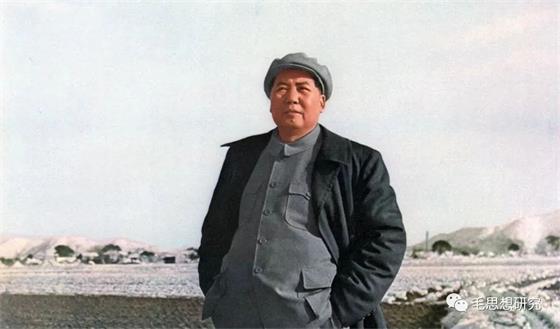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19日-星期六
羅馬斗獸場(圖源:《世界簡史: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
一、中古時代世界第二波文明興起
世界歷史上出現過多次文明興起浪潮。第一波浪潮無疑是在上古時代。就目前研究所知,上古文明的出現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止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在第一波浪潮中涌現的主要文明有:古代兩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國文明、古代希臘文明、古代羅馬文明。此外,還包括了古代西亞的赫梯文明、腓尼基文明、猶太文明、米底文明、波斯文明,以及非洲北部的迦太基文明等。美洲印第安文明最早也出現在上古時代。上古文明大多是農業文明,創建者是農耕民族;個別是商業文明,如腓尼基文明及支嗣迦太基文明。到公元5世紀,上古文明大多已經歷了從形成、興盛到衰落或消亡的全過程。
第二波文明興起浪潮是在中古時代。公元500—1000年間,新興的文明主要有日耳曼文明(即歐洲文明,后擴展成西方文明)、斯拉夫文明(主要是俄羅斯文明)、阿拉伯-伊斯蘭文明。日本文明和東南亞文明雖最早出現于上古末,但成型多是在中古時代6—7世紀以后。非洲各區(東、西、南)也在中古時期出現了不少孤立的文明點。人們通常認為世界有四大文化圈。其中有兩大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蘭文化圈)的形成與中古興起的文明直接相關。另一大文化圈(印度文化圈)雖然發祥于上古,但擴成大文化圈則是在中古時代,即7—12世紀印度文化向東南亞傳播,加快東南亞文明誕生并進入印度文化圈。四大文化圈中,唯有儒教文化圈(中華文化圈)在上古時期就形成了,并在中古時期持續發展,唐宋時再次達到高峰。相對于上古起源的文明來說,中古興起的幾個主要文明在現代世界有極大的影響。
在第二波文明興起浪潮中,以日耳曼文明最為矚目。日耳曼文明始于公元5世紀日耳曼族各部落從北方進入西歐大地,在原有西羅馬帝國版圖上建立諸多小國,包括西哥特王國、蘇維匯王國、汪達爾王國、法蘭克王國、勃艮第王國、東哥特王國、倫巴第王國、英吉利王國等。在文明成長過程中,日耳曼人不但延展著自身族群譜系的原生要素,更受到羅馬時代殘留的隸農制、大地產制的影響,并在后來吸收了羅馬法等因素,精神上皈依并信奉基督教,還創造了一系列新事物諸如采邑封建制、封建等級制、莊園制、農奴制、自治城市與市民社會、憲制與議會、資本主義關系等,最終在16世紀成型并形成力量,向全世界擴張。
也誕生于中古時代的斯拉夫文明,其中最有影響者當屬東斯拉夫文明,亦即俄羅斯文明。斯拉夫人有三支。南部斯拉夫人從今天的烏克蘭西部出發,南下多瑙河流域,公元523年第一次侵擾拜占庭帝國,六七世紀散布到巴爾干半島,逐漸從拜占庭帝國的騷擾者變成不馴服的臣民,不斷掀起反抗浪潮,鍥而不舍地尋求獨立,中古時期建立過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斯尼亞一眾國家,但未形成強大的統一體,影響有限。西部斯拉夫人有波蘭人和捷克人兩個分支。無論大波蘭還是小波蘭,雖然幾度統一,但也多次分裂,12—14世紀出現過五大公國。中世紀晚期,波蘭農業還和西歐綁在一起,成為歐洲世界經濟體系中輸送農產品的邊緣地帶,為此還出現了“再版農奴制”。波蘭在信仰上向西歐靠攏,篤信天主教。至于捷克(波希米亞),更是中世紀德意志神圣羅馬帝國的核心成員,國王是帝國“七大選侯”之一。最能代表斯拉夫民族和斯拉夫文明的,還是東斯拉夫人即俄羅斯民族和俄羅斯文明,包括俄羅斯、小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三個分支。俄羅斯文明始于公元9世紀基輔羅斯國家建立。境內各公國走向統一之際,俄羅斯遭到了草原游牧族蒙古人攻擊,結果臣服金帳汗國兩百余年。在反抗蒙古人統治的斗爭中俄羅斯獲得了解放,并逐漸強大起來。16世紀俄羅斯文明最終確立,并從此走向對外擴張之路,發展為世界上版圖最大的國家。
阿拉伯文明起源于公元7世紀早期阿拉伯半島穆罕默德創建伊斯蘭教。伊斯蘭教作為靈魂,在穆罕默德時期完成了阿拉伯神權國家的統一,阿拉伯文明正式誕生。哈里發時代阿拉伯開始擴張,“古蘭經和劍”成為阿拉伯人擴張的兩手利器。歷經大馬士革時代和巴格達時代,龐大的阿拉伯帝國版圖東到印度河流域,西至伊比利亞半島,北抵中亞深處,南面囊括北非全部地區,東西跨越萬余公里,是世界歷史上版圖僅次于蒙古的最大帝國。帝國解體后,阿拉伯人分布于西亞和北非。伊斯蘭教后來的傳播范圍更為廣泛,除阿拉伯人分布地區外,還包括西亞的奧斯曼、伊朗,中亞腹地,南亞、東南亞,以及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區等。
日本雖被歸入儒教文明圈,但其文明的起源還是有其自身路徑。日本人有多個來源,如土著阿伊奴人、馬來人等,主要族源是來自西伯利亞的游牧族通古斯人。通古斯人前后三批遷到日本,日本文化的根基元素即為通古斯文化。公元1世紀,日本境內出現100多個部落小國,邪馬臺國在3—4世紀較有影響。日本步入文明當在5世紀,其時大和國建立了系統完整的國家制度。7世紀大化改新,中古日本受到中國文化較多影響,同時也形成了自己的“半亞半歐式”特征。半亞指日本對中國文化和制度的學習與移植;半歐指日本人像日耳曼人一樣其遠祖是游牧族,中古某些制度和習俗類似西歐,如武士類似騎士,莊園所有權多元分割類似西歐采邑制,莊園“不輸不入”權類似西歐莊園特恩權,政權有公(國王)武(諸侯)寺院(教會)三大系統,還出現過西歐那樣的自治城市和行會(座)等。
東南亞基本上也是在中古時期踏入文明、誕生國家的。柬埔寨5世紀后出現了扶南國、真臘國,文明第一次繁盛是9—14世紀吳哥王朝時期。老撾在9世紀出現南掌等小國。緬甸實現統一是在11世紀蒲甘王朝初期。泰國最早于13世紀出現速古臺王國(暹羅)。印度尼西亞7世紀誕生許多小國,強者如蘇門答臘島上的三佛齊、爪哇島西部的訶陵。8世紀興起強大的夏連特拉王朝,控制了印尼大部分地方。越南因受中國影響而較早進入文明,從秦朝至10世紀,越南一直處于中國控制之下。939年越南打敗中國南漢軍隊,首次贏得獨立。
撒哈拉以南的東非、西非和南非,都在中古時代誕生了比較發達的文明。東非埃塞俄比亞的阿克蘇姆,4世紀達到鼎盛,國王被稱“萬王之王”。桑給巴爾在14—15世紀發展為帝國。索馬里的伊法特人曾于16世紀建立阿達爾國家。加納8世紀末建立的黑人通卡爾王朝是西非歷史上第一個強盛大國。13世紀取代加納的馬里,14世紀達到極盛。尼日爾河中上游的桑海王國于15、16世紀之交進入鼎盛狀態,首都廷巴克圖一度與巴格達、開羅并稱為伊斯蘭世界三大文化中心。在赤道以南非洲,剛果王國建立于14世紀前后,15世紀進入繁榮期,版圖寬闊,國家機構完整,手工業和貿易發達。“石頭城”(津巴布韋)從6世紀開始建設,是非洲南部最強大的國家,梯田農業發達,并因采煉金銀銅礦而富有。
二、中古興起的主要文明之游牧族本性
在中古時期興起的文明中,日耳曼文明、阿拉伯-伊斯蘭文明、俄羅斯文明這三個主要文明在今天仍影響極大。它們有不少共同特征。與上古文明相似,就文明的緣起過程和模式來說,中古這三個主要文明是獨立的原創性文明,即這些文明的發生是其創造者主體部族社會自然行程的結果,或用流行話語說,文明是按其自身譜系發展和繁衍而來。與上古文明不同的是,中古這三個主要文明都具有一定的游牧族背景,即是由游牧族或剛剛農耕化的游牧族創造的。日耳曼人是剛完成農耕化的游牧族,東斯拉夫人是走向農耕的游牧族,阿拉伯人以游牧為主、在文明創造過程中逐漸農耕化。它們必然帶有游牧人原生的本性。這與上古文明產生于農耕地帶、文明創造者均為本地原生型農耕民族迥然相異。
日耳曼人是剛剛完成農耕化的游牧族。在公元前四五個世紀的歐洲北部,分布著三四個原始族群,偏西為凱爾特人,偏東有斯基泰人、斯拉夫人。中間為日耳曼人,他們定居在從日德蘭半島到今天德國的東北部一帶。公元前后,他們處在從游牧族向初期農耕者轉化的過程中,其社會組織“百家村”可能就是從畜牧條件下所產生的土地(牧場)分區而來。一方面他們還有游牧族生活的許多遺風,如羅馬統帥凱撒在《高盧戰記》中說,“他們沒有私有的、或單獨保存的土地,而且在每一個地方也許僅居住一年。他們不多用谷物為食品,其主要食品為牛奶和家畜”;“他們對農業是沒有什么熱情的,大部分食品只是牛奶、乳酪、肉類。任何人都沒有自己的固定的土地或產業”。一個多世紀后的羅馬史家塔西佗也說,“日耳曼人以自己的羊群牛群互相炫耀;這是他們的唯一的財富,也是他們最喜歡的東西”。另一方面,即使他們已定居并從事農業,其生產水平也非常低。在公元100年左右的塔西佗看來,在和平的日子里,日耳曼的男人們“用許多時間去打獵,用更多的時間去睡覺......將管理家務、耕種田地的事情交予婦女、老人或家中體弱的人去做,他們自己袖手旁觀,不參加勞動”,當然談不上精耕細作了;即使耕地,“也不固定在一個地方,而是常常更換”。當然,按照經濟史家湯普遜的說法,這也許是日耳曼人已意識到連續耕作同一塊地會使地力枯竭,因而采取“田—草”交換輪作制。日耳曼人進入西歐時,把羅馬時期的先進生產力破壞殆盡,卻長期維持自己那種原始的農業生產水平,即使到8—9世紀法蘭克王國查理大帝時代,農業產量仍然極低。一般來說,游牧民族在邁入文明狀態時,他們的農耕水平乃至文明程度都是比較低下的。
斯拉夫人是印歐人的一支,原為游牧民族,起源于今天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波蘭相接的低洼潮濕地帶。作為正在農耕化的游牧族,他們進入文明狀態時社會水平甚至比日耳曼人更低。在遷徙浪潮中,斯拉夫人從公元6、7世紀起往東、西、南三個方向擴散。西支斯拉夫人以波蘭人和捷克人為代表,南支斯拉夫人遷至巴爾干半島。據6世紀中葉拜占庭著名史家普羅科比記載,斯拉夫人身材高大,健壯,渾身臟污,住著窩棚,喜歡徒步行走,作戰時直沖敵人,也不穿甲胄。他們用牛等動物祭祀神靈,說明其仍處游牧時期。略晚于普氏的史書也說,斯拉夫人徜徉于森林、沼澤及濕地之間,生存條件艱苦,組織性差,但又絕不接受奴役和壓迫。在其遷徙的過程中,甚至還以落后樸素的生活方式取代原住民先進的物質文化,如以沉于地面之下的小型木質建筑取代建于地面之上的樁柱式木屋、用手工陶器取代鐵器等。他們也不愿停留于游牧劫掠生活,而是想獲得土地、長期定居,實現成為農耕民族的愿景。東斯拉夫人6世紀前還處在氏族公社階段,共30多個部落,各部落以酋長為首。遷徙過程中,東斯拉夫人廣泛分布于東歐大平原,即西起德涅斯特河和喀爾巴阡山,東至頓河、奧卡河和伏爾加河,南到黑海,北抵拉多加湖的廣大地區。他們沿著幾條大河及支流散居在無數小村子里,少數建在河畔高地的村子可俯瞰兩邊、有防衛設施,大部分村子則是開放式的。東斯拉夫人散布的五大地帶,除了南方黑海岸邊開始出現城市文明外,其余分別是草原游牧區、森林農牧區、中部和中北森林區、遠北漁獵區。9世紀時,這一廣大地區出現了許多小公國。為了維持縱貫南北的通商大水路——“從瓦里亞格到希臘人之路”,9世紀后期,在北歐諾曼人幫助之下,羅斯國家——基輔羅斯形成,首都基輔位于森林草原農牧混合區的北緣。往北是更寒冷的森林區。在鄰近拜占廷的影響下,東斯拉夫人的經濟生活開始得到實質性進步。這時候,有了鐵制農具,學會了用牛馬耕地,還采用輪耕制。有零星的手工業和商業。直到10世紀中葉,第聶伯河東岸還棲息著4個游牧部落。每年開春雪融之時,他們便北上尋找牧場。秋天則返回南方,這里的冬雪不太厚,尚可放牧畜群。
阿拉伯人是亞洲大陸西南端阿拉伯半島上的游牧族。半島處于西亞北非大干旱地帶,屬于亞歐大陸南端農耕世界里的游牧地帶。半島西南沿紅海的北段有些許綠洲,水草豐盛,適合農業和牧業,稱為“希賈茲”(漢志)。希賈茲山擋住了西邊來的雨水,致使半島中部和東部的內陸完全沙漠化,稱之為“內志”,與農耕無緣。惡劣的生存環境,使社會發展極其緩慢。因此,在伊斯蘭教產生前幾千年里,不少族群北上西遷尋找生計。也有些人群繼續留在半島上繁衍、生息。從事游牧為生的人們,稱為“貝都因人”,意即“草原游牧人”或“沙漠之子”,以馴養駱駝和羊群為主。他們與綠洲上的半定居型農業部族相互依存,用畜牧產品與農業部族的武器等產品相交換,并依仗軍事優勢為農夫們提供保護。在阿拉伯-伊斯蘭文明擴張中,最終形成的阿拉伯帝國橫跨了四個古代農耕文明區域,從東到西為印度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尼羅河流域文明和古羅馬文明,還與更東邊的中國文明發生了接觸,因而在文明創造過程中大部分阿拉伯人逐漸農耕化。同時也有許多阿拉伯人仍以游牧為生計,飼養綿羊、山羊、馬匹和駱駝等。即便經商的阿拉伯商人,其陸地長途運輸主要靠“沙漠之舟”駱駝,短途運輸則主要用馬、騾、驢這些牲畜。耶穌時代在中東消失的車輛運輸,直到19世紀才在這一帶再現。
中古世界興起的這幾個主要文明,具有顯著的游牧族特征。
其一,它們都是征服者文明,在移動式擴張和征服中發展文明。這和游牧族的游動習性以及在軍事上的機動性優勢有關。蘭克曾稱日耳曼和拉丁共同體六大民族有三次移動三大呼吸。第一次呼吸是它們移動到西歐這塊土地上定居下來;第二次呼吸是十字軍東侵向東歐西亞小擴張,雖歷經二百年但鎩羽而歸;近代殖民則是向全球的大擴張,最終把全世界納入囊中。阿拉伯人也是在征服和擴張中形成帝國,而且帝國中心不斷因擴張而移動,從哈里發時代以阿拉伯半島麥加和雅特里布(麥地那)為中心,到倭馬亞王朝以敘利亞大馬士革為中心,再到阿巴斯帝國以伊拉克巴格達為中心。晚期阿拉伯帝國裂變為三個大食,中心分別位于西班牙、埃及和伊拉克,都遠離了阿拉伯發祥地。這和農耕帝國多以發祥地為中心、向四周擠壓的漫延式擴張有所不同。俄羅斯文明的創造者斯拉夫人原先居于今天的波蘭東部-烏克蘭西部一帶,后移動到據有東歐大平原,9—15世紀文明發展歷盡曲折和磨難,16世紀文明定型后迅速對外擴張,向東到達太平洋岸,向南翻越至外高加索和內亞腹地,從而奠定了世界第一版圖大國的基礎。
其二,它們都是宗教文明,信奉一神教。或許是游牧民族意識到自身文明底蘊太弱,一方面需要宗教大旗作為靈魂支柱,來增強本族群的凝聚力和認同感;另一方面或許是力圖借助宗教形成精神優勢來強壓先進的農耕文明。所以我們看到,中世紀初期日耳曼人南下西歐時紛紛皈依基督教,歐洲北部的日耳曼以及凱爾特(愛爾蘭)游牧族也快速接受基督教,兩三個世紀里基督教堂就布滿了歐洲大地。11—13世紀歐洲十字軍東侵,打著宗教幌子,聲稱要“收復主的墓地”。即使是地理大發現,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有向海外陌生世界傳播天主教的原初動力。至于阿拉伯文明,則是以伊斯蘭教為精神紐帶才形成的。伊斯蘭教作為嚴格的一神教,反映了阿拉伯社會統一的要求。在阿拉伯人的持續擴張中,他們借助宗教大旗,拿著《古蘭經》進行“圣戰”。所到之處,異教徒必須做出抉擇:要么皈依伊斯蘭教,要么滅亡。作為政教合一帝國,宗教領袖哈里發又是世俗國家最高統治者;作為伊斯蘭教經典的《古蘭經》和《圣訓》,是治理世俗國家的法律基礎。俄羅斯則是在文明形成過程中主動引進東正教,從而為文明成型奠定了核心層面的精神基石。即使到了近代,傳播自身宗教仍然是這些文明追逐的“神圣”目標,這在歐洲文明的天主教和新教那里,在亞洲的伊斯蘭教那里,表現得最為突出。
其三,它們的早期經濟社會制度明顯留有游牧半游牧生活痕跡。如日耳曼人初入西歐之時,由于移動的關系,原先的部族組織被沖散,新的社會共同體只能在新占領地按照地緣關系構建,于是一個個核心小家庭組成的農村公社(Mark馬爾克,本意為邊區,亦即新占領的地方)便成為日耳曼人的基礎單位。土地公有,定期進行分配;隨著私有觀念加深,土地分配間隔時間越來越長,終至不再分配、演化為私有財產,這是西歐封建化過程的基本內容,從5世紀一直持續到9世紀。其封建制的最終確立,還與8世紀的采邑制改革有關。而采邑制改革的人事基礎是日耳曼親兵(貴族)制度,這是游牧族獨有的軍事團隊習俗。因此,西歐的早期封建化過程幾乎與原土地上羅馬帝國的制度無甚關系。西歐莊園里的“敞地制”,即收割后土地和休耕地莊民們都可放牧牛羊,也是游牧族共享牧場習慣的遺存。至于其農業經濟中畜牧占有較大比重,更與游牧族食肉飲乳酪的原生習慣一脈相承。至于阿拉伯人帝國所擴張之地,都是原有的古代文明地區。雖然阿拉伯人保留了許多當地制度,但同樣也注入了自身游牧族的舊有元素。雖然奉行土地國有制,土地支配權在哈里發手中,但軍功貴族、清真寺廟、貴族地主以及個別農民都能擁有私有土地,甚至還有農村公社土地制的存在,土地權利呈多元趨向,社會矛盾尖銳。在社會結構中,阿拉伯人的等級意識分明。以哈里發為首的阿拉伯人貴族最為高貴,尤其是其中出身于阿拉伯半島的“南人”。非阿拉伯裔的穆斯林“麥瓦利”,地位自然比阿拉伯人低;未改信伊斯蘭教的異教徒“迪馬”,說是有宗教自由,但往往被強迫和誘導改宗。還有大量戰俘作為奴隸存在。各種矛盾錯綜交織,社會沖突此起彼伏,帝國早早就分崩離析,其實也是阿拉伯人作為游牧族在政治上先天不足、缺乏熟練治理國家能力的反映。至于俄羅斯,進入文明前夕也有類似于西歐馬爾克的農村公社“維爾福”,而且這一落后的村社制度在俄羅斯長期殘存,直到19世紀還成為科瓦列夫斯基和馬克思等人的研究對象。古羅斯國的成長一直碰碰磕磕,早期大公們頗似游牧族首領一樣,以“索貢巡行”方式實施松散統治。稀松的管理使國家一盤散沙、政治分離,這種狀態在外敵侵入下不堪一擊。蒙古人在200多年統治里實行“八思哈”制度,幾乎讓羅斯各公國氣息奄奄。在反抗蒙古人的斗爭中莫斯科大公國歷經磨礪而強盛起來,俄羅斯文明最終在16世紀成熟成型,由此戰斗性強也逐漸成為俄羅斯民族的特征之一。
三、中古興起諸主要文明成長的環境和時機
游牧族社會戰斗力雖強,但在征服農耕民族后,經濟和文化上卻很快融入了農耕世界,即使強悍的政治軍事統治也只是曇花一現。所以,所謂游牧文明實際上沒有完成其成長全過程就停滯了,只能降維為游牧文化而已。然而,由具游牧背景的部族所創造的中古這三個主要文明,卻未像斯基泰人、突厥人、蒙古人那樣停頓在游牧文化階段,而是能很快地轉化為農耕文明,并最終形成自身的文明本體及特色,歷經千年而不褪色,至今仍在世界上居于強勢地位。這三個中古文明興起之時,正是上古文明發展疲頓并呈現頹勢之日。當這些游牧族尚在第一代文明的邊緣區受文明濡化逐漸向農耕轉變之時,第一代文明的中心區卻因內部蛻變而不再維持繁盛局面,或處于低谷狀態而難以奮起,或對文明邊緣地帶失去控制力,由此便給了轉型中的游牧族以崛起的有利環境和時代機遇。
日耳曼文明興起前夜,古代羅馬文明經歷了公元2世紀“五賢帝”的黃金時代后,很快出現了“三世紀危機”,其最大特點是政治極端混亂,到處都是皇帝,最多時竟有“三十僭主”在位。到處都是奴隸和隸農起義,高盧的巴高達運動,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起義,經久不息。日耳曼人應羅馬統治者之邀,開始和平地進入帝國境內。基督教從早期在被奴役的下層群眾中傳播,變成社會中上層的寄托而爭相加入,動搖著羅馬統治的社會基礎。帝國經濟陷入了凋敝狀態,生產幾乎停滯,直接生產者難以為繼:以往作為社會主要勞動者的奴隸,隨著羅馬征服戰爭停止、戰俘減少而來源枯竭;以往的直接勞動者隸農,則被奴隸主視同于奴隸,其實際地位越來越接近奴隸,他們的勞動興趣也大減;至于原有的自由民,很多早就脫離了勞動,經常無所事事,在統治者縱容下成天游手好閑,沉浸于聲色犬馬,放肆揮霍著社會財富。三四世紀之交,雖有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等君主力圖“中興”,但不過回光返照而已。羅馬終于在四世紀末裂分為東西兩塊。東羅馬經濟實力尚存,并有皇帝駐守,蠻族人進入后自感力有不逮,旋即快速退出。而西羅馬早已家底空空,無力阻擋蠻族進攻,如羅馬城就幾度遭西哥特人、匈奴人和汪達爾人洗劫。寬廣的西歐大地便成了蠻族人的安家定居之所,蠻族國家林立,成為孕育日耳曼文明的搖籃。
與日耳曼人各族在三四個世紀的流動中尋找棲息之地不同,阿拉伯人則是在快速征服中建立龐大帝國。阿拉伯之所以能在亞歐大陸樞紐地帶突然崛起,也在于當時的環境和時機極為有利。從兩河流域到埃及的中東核心地區,是世界最早誕生文明的地區,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的波斯帝國成為西亞北非古代文明的終結者。其后中東進入亞歷山大帝國和希臘化時代。公元1—2世紀羅馬與安息在兩河流域長期對峙。5—6世紀東羅馬拜占庭帝國與薩珊波斯帝國長期交戰,兩敗俱傷,而6世紀拜占庭帝國的爭奪重心在歐洲和北非西部,7世紀又花費大量精力去對付南下巴爾干的斯拉夫人。這樣中東一帶實際上貌似形成了政治真空地帶,這就為阿拉伯的崛起并對外征服和擴張創造了極其有利的國際條件。
俄羅斯文明興起,其實也與有利的國際環境相關。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鄰近俄羅斯的拜占庭文明,9世紀以后正處于衰退期,經濟上無所創造,政治版圖日益萎縮,其觸角難以企及東北歐地區。古羅斯國家興起之地頗為苦寒,也難以引起拜占庭人的興趣。其二是這時正是北歐海盜四處侵掠之際。北歐人往東南方向開辟了“瓦希之路”,力圖打通北歐與拜占庭的聯系,俄羅斯人可以借助諾曼人之力發展自己,不然怎會有羅斯國家的“諾曼起源論”呢?
中古這三個主要文明也較多地受到了先在文明或同時代的鄰近文明之惠。即便它們是獨立的原創型文明,它們在興起和早期發展中也受到了其他文明較多影響,雖然受影響的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這幾個文明初興之時,亞歐大陸早已形成了文明世界,上古起源的各文明體大都延續了千年以上,文明機制和社會形態極為成熟。古老文明的曾經存在勢必對鄰近游牧族產生影響。當交往日益頻繁甚至這些游牧族成為農耕世界新主人時,它們的社會發展進程也大大加快。學界以往較多討論它們如何跳過所謂奴隸社會階段,從原始氏族公社直接過渡至封建社會,縮短了社會形態變換的歷史時間。當然,這個過渡期有長有短,封建化程度也有所差異。此外,我們還可超越社會形態的歷史文化視閾做些考察。
日耳曼文明來自三方面元素:日耳曼元素是其本體,基督教元素是其靈魂,羅馬元素是促其生長和完善的土壤。當日耳曼人口南下時,基督教則是文化北上,兩者交叉互動。基督教正好符合日耳曼蠻族的需要,即日耳曼人需要精神上的提升,要去掉身上“蠻族”的胎記;也需要精神上的統一,以利于將分散的日耳曼勢力整合起來。在日耳曼文明發展過程中,基督教教義原則又提供了許多營養,如各個教民可以直接與上帝或上帝代表(教士)對話(懺悔),有助于孕育日耳曼文明的精髓——個人主義、個人本體觀念。至于羅馬因素,日耳曼人則是經過較長一段時間冷卻后重拾的。如經濟方面,日耳曼人最初是低下的農牧業,而把羅馬發達的城市和工商業破壞殆盡,殘留的羅馬城市只是成了宗教聚集地點而已,工商業也只在地中海港口偶有殘存。在制度方面,日耳曼人最初的馬爾克農村公社,9世紀最終完成封建化過程,形成采邑制、農奴制和莊園制,雖然這基本上是日耳曼人自己的創造,但這也有羅馬末期隸農制、大地產制遺留的影響,在同一塊土地上難免無有記憶喚醒。雖然羅馬法是12世紀才在西歐復興,但羅馬法之精細,為西歐法制文明的成長提供了足夠多的營養。此外,西歐日耳曼文明也接受了同時代東歐拜占庭帝國諸多積極因素的影響,對此已有諸多學者予以論及,此處不再贅述。
阿拉伯文明產生于游牧地帶,它是在對外征服過程中逐步成熟的。而它擴張所及之地,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地區,與它們的接觸和碰撞,極快地提升了阿拉伯民族的社會發展水平。這些地區都在公元五六世紀基本完成了封建化過程,阿拉伯人面對這些先進于自身的生產方式時,一方面接受其先進性,另一方面也并非依樣畫葫蘆,而是注入了自己的想象和創造,形成有阿拉伯特色的封建經濟制度。同樣,這些古老文明又都各具文化特色,阿拉伯人持完全開放態度,對所有先進文化統統接受不拒,由此也形成其兼收并蓄、包容百納的文化風格。同時也堅持其精神本體——伊斯蘭教基本教義不受浸染,避免在新地區本土化;也默許當地人士予以不離其根本的一定改造,這實際上也是吸收伊斯蘭教之外養分的一種開放態度。
東斯拉夫人所在地區,早在公元前7世紀就有希臘人在黑海北岸建立了殖民點。公元后最初幾個世紀,羅馬人在這一帶取代了希臘人影響,帝國版圖伸展到了南布格河赫爾松一帶。因此古希臘羅馬文明在這一帶多少有些痕跡。俄羅斯文明產生于東斯拉夫人本土,羅斯國家起源與北歐人活動有關,但在文化上卻很少有諾曼文化的蹤影,因為諾曼人自身的海洋文化并不適合于俄羅斯陸地。俄羅斯文明發育過程中受鄰近拜占庭文明影響較大:它與拜占庭帝國保持商業上的交流,加快了古羅斯經濟的發展和循環;拜占庭先進的封建經濟政治制度,對俄羅斯社會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俄羅斯接受了來自拜占庭的東正教,將其作為精神旗幟來統一東斯拉夫人思想;拜占庭傳教士創造了斯拉夫文字,有利于俄羅斯擺脫野蠻痕跡,踏入文明社會。
這三個主要文明雖然都受他者文明影響,但受影響程度還是有不同的,致使它們呈現的文明特征也有差異。如果是文明主體民族移動幅度較大的,則受移動所至地區原有的先進文化影響較多。如歐洲南部即原羅馬帝國中心區意大利、法蘭克,促使日耳曼人進入封建社會的羅馬因素作用更多,故而這里的史學界更堅持西歐封建制度“羅馬起源論”。又如南部斯拉夫人移動到拜占庭帝國境內,成為帝國內部的異族成分;西斯拉夫人移動至中歐,其歷史發展便與毗鄰的西歐更多的糾結。再如伊斯蘭教擴張至阿拉伯之外的先進地區,也就較多地融進了當地因素。如果是移動幅度較小的,則自身族群和移動所至地兩方面的因素綜合起作用,如歐洲北部的德意志、尼德蘭和英格蘭等地區,原是羅馬文明的邊緣區或外緣區,所受羅馬因素之惠要小得多,故而這里的史學界更多的是強調西歐封建社會起源“綜合論”,甚至是“日耳曼起源論”。如果是非移動式的,則自身族群的因素更多些。如東斯拉夫人是在自行擴散的土地上發展文明。又如阿拉伯文明起源地阿拉伯半島,長期奉守早期游牧習慣和宗教原旨精義。
值得指出的是,這幾個文明在創立階段,在早期發展階段,是有生氣的,對外來養分是持開放態度的。但當文明定型后,文明的精神本體則走向固化,尤其是處在相較其他文明的有利位置時,它們對外部因素哪怕是積極因素也難以再呈開放態度,甚至轉而貶損之。這一點值得深入探究。如西方文明最深處的個體本位和個性自由精神,即使面臨窘境也沒人愿意改變,而且還過度張揚,甚至走樣。又如說俄羅斯是“戰斗民族”,基督教文明宣揚“普世價值”,伊斯蘭文明癡迷于“教化”他人。是不是游牧民族更具主動改變命運的精神(逐水草而居),由此更加迷之自信;而農耕民族更偏于被動順應自然(如農作物等待雨水),對外部因素會更多些遷就和包容呢?
四、中古歐洲文明何以能脫穎而出?
正因為中古興起的各主要文明有如此多的共同點,因而這些文明同樣都有強勁的生命力,都歷經了千年以上風雨,至今仍在世界上具有廣泛的影響力。當然這些文明各自逐漸煉就的本體特征,它們各自在千年發展中所走過的道路,以至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卻是迥然相異的。
文明本體特征是各文明的靈魂。文明本體形成后,除非內生要求迫使文明自身主動調整,外在力量很難將其扭轉。歐洲文明(日耳曼文明)的本體特征最為突出。歐洲文明雖在5世紀誕生于古羅馬文明的灰燼中,但在5—7世紀的好幾百年里徘徊不前,直至8—9世紀才確立新生的封建制度。其文明內在的社會機制和“元規則”,使其能不斷汲取多方面的養分,孕育全新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方面因素,經過上千年的提煉和磨礪,到16世紀基本成熟定型,17—19世紀繼續發展。它以人文主義為出發點,以理性和科學為核心,強調個體本位,重視個人發展,重視人對自然的斗爭,產生了諸如自由、自治、民主、平等、法治、進取、求真(科學)、理性計值等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觀念,以及個體奮斗、冒險、擴張、征服、功利、金錢崇拜等西方獨有的思想意識,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對立式、絕對化思維,這幾方面構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念體系,亦即其文明本體。當然,阿拉伯-伊斯蘭文明、俄羅斯文明也形成了自己的本體特征。只不過,歐洲文明之所以最終能在眾多農耕文明中脫穎而出,率先走向資本主義工業社會,更在于其孕育過程中也培育了不同于他者的文化土壤和社會機制。這一問題已有無數學者奉獻了無數觀點,人言人殊,本文僅從文明成長空間的宏觀角度略陳鄙見。
這三個文明興起的歷史機遇看起來相似,但實際上各文明利用機遇的主客觀條件卻不盡相同。在西歐,當日耳曼人進入時,羅馬制度已徹底崩塌,新的事物尚未出現,或者僅綻芽蕾而未成氣候,這樣就給日耳曼人留下了可以想象和創造的空間,而日耳曼人的社會機制易于或利于激發創新,于是便產生新的思想和制度、新的經濟社會因素。而阿拉伯文明擴張所及之地,在經濟、制度和文化上都比阿拉伯人先進,這可能會產生兩方面效應:一方面這些地區幅員寬廣,思想文化錯綜散亂,易于被伊斯蘭教義所整合;另一方面,由于這些地區經濟文化先進,阿拉伯人面對它們時難免自慚落后,故而樂于享其現成,而難以產生升級創造的沖動和想象力。因此,可以看到伊斯蘭國家的封建制多是當地原有制度的翻版或伊斯蘭化而已,而文化上的“兼容百納”從另一個意義上說也是被征服地區文化的“大拼盤”。至于俄羅斯,其民族原本就沒有固態的文化本體,版圖上面是制度和文化空白,沒有傳統可承繼,在制度創建過程中又受到更原始的蒙古人游牧文化沖擊干擾,因此俄羅斯文明成型時,并沒能達到一種高級形態。
三個文明都篤信宗教,但在宗教與社會之關系的處理上卻大相徑庭。西歐雖有統一教會天主教,教皇和教廷對教會實行中央集權化統治,世俗國王也由教皇加冕以表示“君權神授”,但奉行的基本原則是政教分離,世俗政治不受教會節制,更不是教會的工具。16世紀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更是主張“因信稱義”,人人都可直接與上帝交流,堅決拋棄教廷和教皇。同時,基督教教士也基本上不直接干預和介入教民的日常世俗生活。雖然教堂和神父遍及村鎮,但他們只是通過一次次祈禱和布道去引導俗人,每人都可通過教士指導下的懺悔直接與上帝溝通,這就有利于滋育個體本位意識。阿拉伯國家是政教合一,統治者先是宗教領袖,后才行使世俗權力,世俗政治受宗教教義束縛,也受教會組織支配。而伊斯蘭教“五功”、齋月等規定,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和控制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被框定后,其想象力和創造力勢必受到限制。俄羅斯介于兩者之間,世俗統治者將宗教作為精神旗幟博取人們的支持,也作為工具來統治人們、引領社會,其社會進步缺乏人民的首創性支持,而是依統治者意志來決定。種種因素使我們看到,中古時代亞歐大陸中西部出現的這三個主要文明,日耳曼文明成為現代社會的開創者,俄羅斯文明成為一個趔趄的追隨者,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區則在較長時期里成了歐洲人侵掠的對象。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作者:劉景華 系天津師范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來源:“經濟社會史評論”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于《經濟社會史評論》2023年第2期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國策建言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