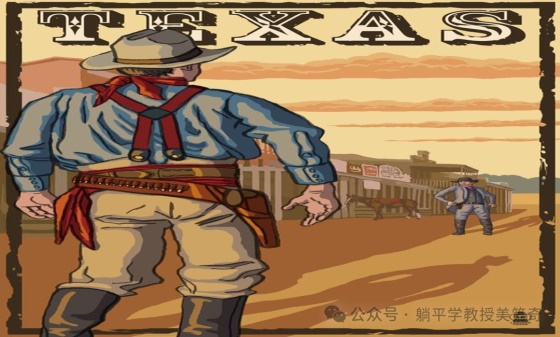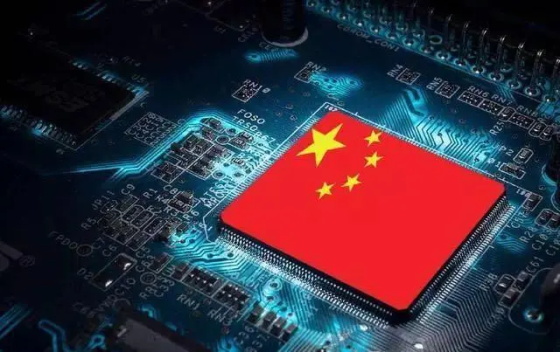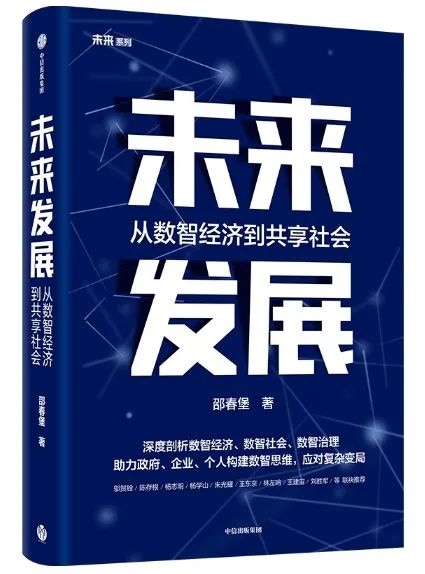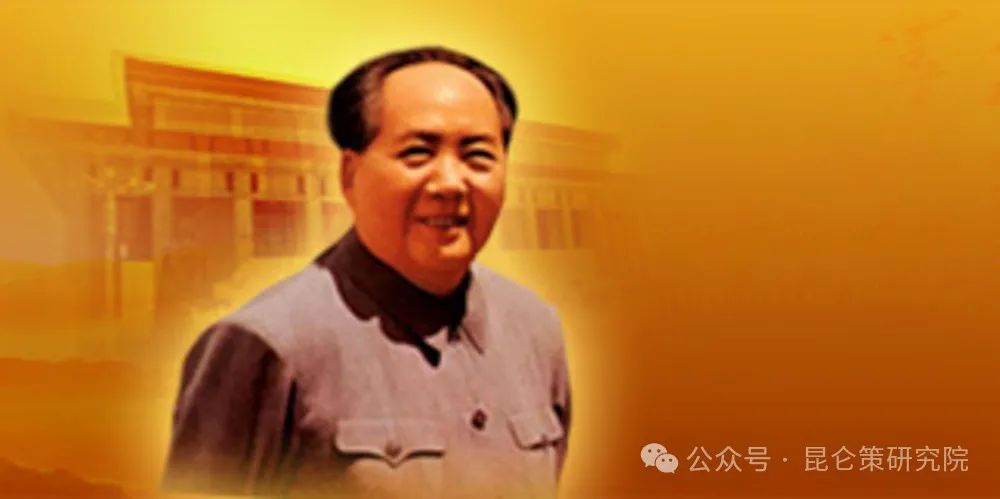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7日-星期三
里耶秦簡(圖源:“長沙博物館”微信公眾號)
秦漢墓葬出土的文字資料以簡牘為大宗。隨葬簡牘是這一歷史時段的葬俗之一。從目前的考古發現看,這種習俗雖上承戰國,不過埋藏簡牘的方式、簡牘編冊形式、性質和內容等已發生變化。漢承秦制,但這方面的葬俗也有不同特色。以往學者就此作過大量研究,取得豐碩成果,不過整體而言系統探研不多,缺少對簡牘隨葬方式的專門討論。就墓葬考古而言,江漢地區是出土秦漢簡牘批次最多、數量最大的區域,特別是近年陸續有新的考古發現,資料不斷豐富。本文即以江漢地區出土簡牘的秦漢墓葬為研究對象,從考古現象和物質形態入手,對這一區域簡牘的入葬方式、編冊形式及內涵作一全面梳理和考察,進而探討其所反映的時代、地域特征及民間習俗與信仰。
據正式公布的資料,江漢地區出土簡牘的秦漢墓葬不少于四十一座,時間大體在秦將白起拔郢(前278年)至西漢武帝早期(元狩五年,前118年)的一百多年間,集中于秦始皇統一六國至西漢景帝的八十年內。這些墓葬主要分布在今湖北省的三個轄區:一是荊州市一帶,主要位于市區以北的楚故都紀南城、秦漢郢城附近和荊州古城之西;一是云夢縣城一帶、古“楚王城”附近,秦漢屬安陸縣;一是隨州市區東北、古曾國遺址一帶。其他轄區共發現兩座。這些墓葬基本是長方形豎穴土坑墓,葬具大都是一槨一棺,秦墓槨室大多包括頭箱和棺室兩部分,漢墓則包括頭箱、邊箱和棺室三部分。形制略為特殊的墓葬,在葬具方面,如王家臺M15秦墓一棺無槨,鳳凰山M168漢墓一槨二棺;在墓葬分室方面,如謝家橋M1漢墓分為五室,胡家草場M12漢墓分為四室。但總體來看,墓主的社會身份差別不大,大體屬于中下層官吏或中小地主階層。出土簡牘的墓葬較多,墓主身份接近,地域相對集中,時間相去不遠但又有歷時性,那么這些墓葬可以視作一個整體,是對隨葬簡牘進行考古學觀察的難得的典型資料。江漢地區戰國墓葬考古出土竹簡的批次和數量在全國范圍內也是首屈一指,我們的考察會適當上溯至戰國。當然,文章還會引用到其他地區的戰國秦漢墓葬及非墓葬出土資料,非考古發掘出土的簡牘資料也適當予以參考。
這里先就本文體例作概括說明。本文討論的對象主要是考古發掘出土簡牘的墓葬(本文所收集墓葬資料截止于2020年)。對考古資料的介紹,按地域并結合墓葬年代、出土時間進行編排。同批(座)墓葬資料可能先公布發掘簡報,后出版發掘報告或簡牘報告,引述時一般以較后出版的報告為準,特殊情況予以說明。《秦簡牘合集》對七批秦簡牘資料進行了再整理,是本文的重要參考,為免繁瑣不出注說明。本文稱寫在簡上的隨葬品記錄為遣策,寫在牘上的隨葬品記錄為物疏或衣物疏。學者通常將簡牘資料區分為書籍(即“古書”)和文書兩類。張家山M247遣策稱隨葬在竹笥中的簡牘為“書”,這些簡牘除去現代意義上的書籍外,還包括文書,可見時人所謂“書”的內涵比較寬泛。還需注意的是,這座墓葬的遣策沒有跟“書”放在一起,而遣策、物疏、告地策一類喪葬文書確實具有特殊性。為方便稱引,這里作進一步區分,把簡牘資料分別為書籍、文書、喪葬策疏三類。文具、算籌與簡牘關系密切,且多與簡牘伴出,本文一并介紹、討論。
一、出土簡牘的秦墓
六座。其中荊州、云夢各三座。
(一)荊州市一帶
荊州市出土簡牘的秦墓集中在秦漢郢城周圍。
王家臺M15 王家臺墓地位于荊州區郢北村的一座土崗上,南距郢城北垣約1公里。在1993年的考古發掘中,秦墓M15出土了簡牘。該墓規模很小,葬具為一棺。隨葬器物十余件,其中三件陶器置于墓坑中,其余均置于棺內。墓葬年代上限不早于白起拔郢,下限不晚于秦代。竹簡放置在棺內足端,編號八百一十三個。出土時大都位于棺底板上,仍能看出原本分三層成卷疊放,包括《日書》、《歸藏》、《政事之常》和《效律》。竹牘一枚,出土于棺內頭端,殘甚,內容不詳。棺內還隨葬算籌六十支。
岳山M36 岳山墓地位于荊州城東北,北距郢城約500米。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此發掘了十座秦墓。這些秦墓葬具明確者皆為一棺一槨,墓主都屬于中下層官吏,墓葬年代與睡虎地秦墓大體一致。其中M36出土二枚木牘。該墓槨室分為前室和棺室。隨葬器物近六十件,多放置在前室。墓主身份與周家臺M30接近。二枚木牘均出自棺內,為日書。棺內隨葬算籌五十八支。
周家臺M30 周家臺墓地位于沙市區西北郊太湖港東岸,西距郢城東垣1.7公里。1993年發掘的秦墓M30出土了一批簡牘。該墓葬具為一棺一槨。隨葬器物四十四件,大多放置在棺槨間北端(相當于“頭箱”)。墓主約30至40歲,下葬于秦代末年,官秩低于睡虎地M11墓主。竹簡出土于“頭箱”西南部的一件竹笥里,共三百八十一枚,仍保持三卷竹簡疊壓存放的原貌,由上到下依次是《日書》、秦始皇《三十四年質日》和《病方及其他》。簡冊中含空白簡,其中《質日》四枚,位于簡冊末尾,簡冊由此開始收卷;《日書》十枚,穿插于章段之間。同件竹笥內還盛放有毛筆、竹墨盒和墨塊、鐵削、算籌等。木牘一枚,出土于“頭箱”西部,與盛放竹簡的竹笥毗鄰,內容是秦二世元年歷日。
(二)云夢縣城一帶
云夢縣城一帶出土簡牘的秦漢墓葬均位于楚王城附近。
睡虎地秦墓 睡虎地墓地位于云夢縣城西北部,東面靠近楚王城,與它南面的大墳頭、東南的龍崗等墓地毗鄰,墓葬時代和特征接近。1975年底至1976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此發掘十二座秦墓,其中M4和M11出土簡牘,而M11出土竹簡產生重要學術影響。
M4形制與M11接近,時代早于M11,在秦統一六國之前不遠。頭箱中部出土二封書信木牘,是從軍淮陽的黑夫、驚兩人寫給其在家的兄弟衷的。木牘旁邊放置有石硯和墨。推測M4墓主即衷,其身份大致相當于中小地主階層。M11葬具為一棺一槨,有壁龕一個。槨室分為頭箱和棺室。隨葬器物七十余件,主要放置在頭箱,少數置于棺內和壁龕里。據所出土竹簡《葉書》,墓主名喜,是低級官吏,歷任的官職多與刑法有關。《葉書》記事止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是年喜46歲。據尸骨鑒定,墓主是40至45歲的男性,因此秦始皇三十年很可能是M11的絕對年代。竹簡一千余枚,置于棺內墓主頭部、右側、腹部和足部。少數簡有散亂或殘斷,絕大部分保存完好,堆放有序,可以看出本來是成卷分別放置在墓主周圍。簡冊含多種法律文獻及《葉書》、《日書》、《語書》和《為吏之道》等。竹簡中混有毛筆二支,頭箱出土有毛筆、銅削等。
龍崗M6 龍崗墓地位于城關鎮建新村,是一處地勢平坦的坡地,北距楚王城南垣約450米。1989年,考古工作者在這里發掘九座秦漢墓,其中秦墓M6出土了簡牘。該墓葬具為一槨一棺。槨室分為頭箱和棺室。隨葬各類器物十余件,大多放置在頭箱。據簡牘資料,墓主名辟死,可能是低級吏員,墓葬年代下限為秦代末年。竹簡出自棺內足檔,多殘斷散亂,現場清理時編號二百九十三個,內容系法律條文。木牘一枚,可能屬于司法文書,因其內容與墓主身份有關而被放置在墓主腰部。
二、出土簡牘的漢墓
江漢地區出土簡牘的漢墓較多,從已公布的資料看約有三十五座。荊州一帶是集中出土地,共有二十九座,此外云夢、隨州各有二座,宜都、老河口各有一座。不少簡牘資料尚未全面刊布。
(一)荊州市一帶
荊州出土簡牘的漢墓集中在三個區域:其一是荊州古城之西的張家山墓地;其二是郢城以東的揚家山、蕭家草場、印臺、謝家橋和胡家草場墓地;其三在紀南城東南部城內外,包括鳳凰山、毛家園、松柏和高臺墓地。
張家山漢墓 張家山墓地位于荊州區紀南鎮一條東西走向的崗地上,東南距荊州古城約1.5公里,東北距楚故都紀南城約3.5公里。1983年底至1984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此清理了M247、M249、M258三座漢墓,出土竹簡一千余枚。1985年底和1988年初,先后清理M327、M336兩座漢墓,再次出土竹簡一千余枚。五座墓葬的葬具都是一棺一槨。M247槨室分為頭箱和棺室兩部分,其余各墓都分為頭箱、邊箱和棺室三部分。墓葬年代下限均不晚于漢景帝時期。
M247墓主是低級官吏,墓內隨葬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至呂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歷日和呂后二年律令,可知他在呂后二年或之后不久去世。隨葬品主要置于頭箱,計五十余件。其中竹簡一千二百余枚,分置兩處:一處位于頭箱西擋板處,系遣策;一處放置在頭箱緊靠南壁板的竹笥內,主要是各種書籍,其上疊壓有數枚空白木牘,竹書成卷堆放,由上至下依次是《歷譜》、《二年律令》、《奏讞書》、《脈書》、《算數書》、《蓋廬》和《引書》,遣策34號簡記作“書一笥”。頭箱還出土了筆管、石硯和算籌一捆。據發掘簡報圖五,筆管、石硯跟書笥位置非常接近,不排除筆、硯原與竹書一起放置在竹笥內,后因竹笥腐朽而滑出的可能。這些實物可與遣策記載相對應,如簡39記“筆一有管”、簡40記“研一有子”、簡2記“筭囊一”,簡34還記有“墨囊一”,但出土實物未見。張家山M247所出遣策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記錄隨葬文字資料和文具的遣策。
M336墓主身份與M247相當,年代屬西漢早期。隨葬品主要置于頭箱和邊箱,其中竹簡共八百二十七枚。絕大多數簡放置在頭箱的竹笥內,用麻織物包裹,出土時尚呈卷束形狀,內容為《功令》、《漢律十六章》、《徹谷食氣》、《盜跖》、《祠馬禖》和漢文帝《七年質日》;少數出土于邊箱,為遣策。
M249、M258、M327三墓資料僅有簡要報道。M249、M327竹簡出土于邊箱,都是日書。M258竹簡出土于頭箱,為歷日,墓葬年代在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或稍后。
謝家橋M1 謝家橋墓地位于沙市區關沮鎮清河村的一處崗地上,西距郢城約2公里,西北距紀南城約5.5公里。2007年發掘M1并出土簡牘。此墓葬具為一槨一棺。槨室分為東、南、西、北、棺室五部分,隨葬物品四百八十九件。據所出告地策,墓主是五大夫昌的母親恚,下葬時間為呂后五年(前18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從墓葬形制、出土遺物看,恚有較高的身份等級和地位。該墓東室主要隨葬銅禮器和日用器,簡牘也放置在此室,計竹簡二百零八枚、竹牘三枚,分別是遣策、告地策,出土時被一起包捆在蒲草內,保存完好。告地策出現于西漢早期,它模仿現實生活中的移徙公文,向地下官府(官吏)移送死者名籍及隨身之物等,以便死者在冥府立戶安家。遣策中的一百九十七枚竹簡記錄具體的隨葬器物,十一枚竹簡為分類統計。告地策記錄隨恚下葬之物“牒百九十七枚”,牒數正與條記隨葬品的簡數相合。謝家橋M1出土的告地策是迄今所見時代最早的。
揚家山M135 揚家山墓地位于荊州區黃山村一座南北走向的土崗上,西距郢城東垣約1.5公里,西北距紀南城約5公里。1990年發掘,M135出土了竹簡。該墓葬具是一槨兩棺,槨室分為頭箱、邊箱和棺室。隨葬器物九十余件,多放置在頭箱和邊箱。墓主為男性。竹簡位于邊箱靠頭箱一端,共七十五枚,絕大部分保存完好,內容是遣策。整理者認為M135是一座秦墓。陳振裕認為該墓出土器物與睡虎地M11有所區別,秦墓不出遣策,西漢則遣策常見,其年代似當在秦漢之際至西漢初年。陳說可從。
高臺M6、M18、M46 高臺墓地位于荊州區紀南鎮高臺村、紀南城東南角外,東南距郢城約3.5公里。1992年正式發掘高臺墓地,漢墓M6、M18出土簡牘。2009年,又在此地發掘M46,出土木牘。M6竹簡位于頭箱,共五十三枚,其中有字者十四枚,內容是遣策。M46曾遭盜擾,邊箱出土疊放的木牘九枚,屬于賬簿,墓葬年代為武帝初期。兩墓墓主社會身份均在第六級和第九級爵位之間。這里重點介紹M18出土資料。該墓葬具為一棺一槨,槨室分為頭箱、邊箱和棺室。隨葬器物三十余件,主要放置在邊箱,頭箱僅放置梳篦、木俑、木牘等物。木牘四枚,出土時基本疊置,構成一套移徙文書,牘甲在上,相當于文書封檢,比其他牘短而窄,牘乙、丙居中,正面相疊,背面有兩道絲繩捆縛痕跡,乙是告地策正文,丙是告地策所移名數,牘丁在下,為物疏。據告地策,墓主是大女燕,下葬于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十月二十五日。
毛家園M1 毛家園墓地位于紀南城東南部,西距鳳凰山110米。1985年11月至1986年3月發掘。葬具為一槨一棺。槨室分為頭箱、邊箱和棺室,放置隨葬器物二百三十余件。其中竹簡七十四枚、木牘一枚,分別為遣策、告地策。據告地策,墓主是關內侯寡精,下葬于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八月十八日。告地策記“牒書所與徙者七十三牒”,比出土遣策簡數少一枚,推測遣策中有一枚小結簡,而告地策不計,情形與謝家橋M1類同。
鳳凰山漢墓 鳳凰山墓地位于荊州區紀南鎮、紀南城的東南角,是一處平緩的崗地。在1973、1975年的考古工作中,鳳凰山墓地M8、M9、M10和M167、M168、M169出土了簡牘。從墓葬形制看,M168、M169帶墓道,M168一槨二棺,其他墓葬都是一槨一棺。槨室分為頭箱、邊箱和棺室,放置各類隨葬器物墓葬時代均屬于西漢文景時期。M8、M9、M10、M168墓主為男性,M167墓主為老年女性。M169的考古資料尚未正式公布。六座墓葬中,M10、M167、M168出土的文字和文具資料比較豐富。
M10出土器物二百多件。隨葬簡牘盛放在邊箱的一件竹笥里,大都屬于鄉里行政機構文書。其中竹簡一百七十余枚,出土時次序散亂。木牘六枚,出土時疊壓在一起,1號牘位于最下面,正面書物疏,背面寫告地策。結合簡牘資料,可知墓主是五大夫張偃,生前可能職司江陵西鄉有秩或嗇夫,下葬于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年)后九月八日。同一竹笥內還盛放有石硯、木尺(?)和木骰。
M167隨葬器物約二百件。在距槨頂板25厘米的青灰泥中出土木簡七十四枚,保存完好,尚呈卷狀,內容為遣策,所記器物與隨葬品基本相符。頭箱出土一件竹笥,盛放絲織品三十五卷,又置空白木牘二枚及鐵削、毛筆、算籌等物,遣策57號簡稱此笥作“繒笥”。
M168隨葬器物五百多件,主要放置在頭箱和邊箱。簡牘出土于邊箱中部,其中竹簡六十六枚、竹牘一枚,分別是遣策、告地策。墓主人骨骸保存完整,年齡約60歲。據告地策,墓主為五大夫遂,于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五月十三日下葬。邊箱中部出土竹笥一件,內置石硯、毛筆、銅削各一和墨塊、空白木牘六枚以及竹籌、天平衡桿、銅砝碼等,遣策59號簡記作“計、計笥一合”。
M8、M9和M169的頭箱都出土了竹簡遣策。M8遣策一百七十六枚。M9遣策有字簡六十九枚,又有與車器伴出的殘牘三枚,整理者認為是廢棄木牘改作為車器,所以M9實際上只隨葬了遣策。廢棄牘上的紀年是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年),是為該墓年代上限。M169遣策有字簡五十五枚。
胡家草場M12 胡家草場墓地位于紀南生態文化旅游區東北部的岳山村,西距郢城0.98公里,西北距紀南城5.2公里。在2018年的考古工作中,M12出土了簡牘。該墓葬具是一槨一棺。槨室分為頭箱、邊箱、足箱和棺室。隨葬器物一百余件,主要放置在頭箱、邊箱和足箱。綜合墓葬、器物形制及竹簡內容,整理者判斷M12是文帝時期墓葬,年代上限為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墓主社會身份與鳳凰山M168相當。簡牘總計約四千六百枚,放置在頭箱編號10、90的兩件竹笥內。10號笥盛滿簡牘,出土時部分簡牘脫落于竹笥外面,但大部分保存較好,尚呈卷束形狀,內容是歲紀、律令、歷日、日書、醫雜方和簿籍。90號笥裝有竹簡遣策和銅削、石硯等。
蕭家草場M26 蕭家草場墓地位于沙市區關沮鎮岳橋村,東臨印臺墓地,西南距周家臺墓地0.8公里。1990年底至1992年底,考古工作者在此發掘戰國秦漢墓葬二十七座,其中M26西漢墓出土竹簡。該墓葬具是一棺一槨,槨室分為頭箱、邊箱和棺室。隨葬器物一百零七件,主要放置在頭箱和邊箱。竹簡三十五枚,放置在頭箱南部的竹笥蓋上,為遣策。尸骨保存完好,男性,年齡40至45歲,社會身份低于官大夫。墓葬年代不晚于文景時期。
松柏M1 松柏墓地位于荊州區紀南鎮、紀南城東南部。M1西距鳳凰山M168約340米,2004年底發掘。該墓葬具為一棺一槨,隨葬器物三十余件。據簡牘記載,墓主是江陵西鄉有秩嗇夫公乘周偃,墓葬年代在武帝早期。從簡報的墓葬平面圖看,簡牘主要出土于槨室西北部,有木簡十枚、牘六十三枚,其中六枚牘無字。木牘內容有物疏、簿冊、葉書、令、歷日及周偃的功勞記錄、遷調文書等。木簡寫有如“右方四年功書”、“右方遣書”等文字。整理者推測木牘原系分類捆綁,空白牘作為上下封頁使用,木簡是置于各類木牘后面的標題。
印臺漢墓 印臺墓地屬于岳橋古墓群,該墓群位于沙市區關沮鎮岳橋村,西距郢城約2.7公里,西北距紀南城約5.7公里。2002年至2004年初,印臺M59、M60、M61、M62、M63、M83、M97、M112、M115等九座西漢墓發掘出土了簡牘,其中竹木簡共計二千三百余枚、木牘六十九枚,內容包括“文書、卒簿、歷譜、編年記、日書、律令以及遣策、器籍、告地書”等。這些墓葬都是小型墓,葬具為一棺一槨。除去M112竹簡出土于棺內,其余簡牘均置于頭箱(端)。M60簡牘盛放在竹笥里。簡牘中有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的官文書,編年記記錄秦昭襄王至西漢初年的編年和史實,相關墓葬年代于此可見一斑。
(二)云夢縣城一帶
大墳頭M1 大墳頭位于城關鎮西南角,是一片高出平地五米的坡地。M1西北距睡虎地M11約400米,1972年發掘,出土一枚木牘。該墓葬具是一槨一棺,槨室分為頭箱、邊箱和棺室。隨葬器物一百五十九件,主要放置在頭箱和邊箱。邊箱出土玉印一方,印文“遫”當是墓主之名。墓主社會地位介于鳳凰山M168與睡虎地M11之間。墓葬時代屬于西漢初期,早于鳳凰山M168。木牘出土于頭箱西北角,為物疏,所記與出土實物大體相合。
睡虎地M77 西距睡虎地M11不足百米,2006年發掘并出土簡牘。該墓葬具是一槨一棺。槨室分為棺室和邊箱,隨葬器物三十七件。據竹簡資料,墓主名越人,職司安陸縣官佐及該縣陽武鄉鄉佐,墓葬時代約在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簡牘盛放在邊箱中部的竹笥內。竹笥盛滿簡牘,大部分保存較好,計二千余枚,大致分三層成卷疊放,包含質日、官文書、私人簿籍、律、算術書、日書和故事書。笥內還盛放毛筆一支。邊箱東北角出土石硯一套。
(三)隨州市一帶
隨州市出土簡牘的漢墓位于隨州市區東北,附近有豐富的古曾國文化遺存。
孔家坡M8 孔家坡墓地位于隨州城關東北,是一條南北走向的崗地。西約1.5公里有?水自北向南流入涢水,?水西側有著名的曾侯乙墓。在2000年的考古工作中,漢墓M8出土了簡牘。該墓葬具為一棺一槨。棺放置在槨室西南側,北側和東面作為頭箱和邊箱,隨葬物品五十九件。據簡牘資料,墓主是庫嗇夫辟,下葬于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正月。簡牘在頭箱分兩處放置:位于東北角的竹簡約五百枚,內容是日書,出土時大致呈卷狀,有殘絹片附著,推測下葬時被絲織物包裹;西北部則包含簡和牘,其中有字簡六十枚,內容是景帝后元二年歷日。與歷日伴出的有空白簡七枚,比歷日簡短而寬。與歷日同出的還有木牘四枚,其中歷日簡下部的一枚是告地策,上部的三枚無字。
周家寨M8 周家寨墓地是孔家坡漢墓群的組成部分,M8距孔家坡M8不足500米,2014年發掘并出土了簡牘。該墓葬具是一槨一棺,槨室分為棺室、頭箱和邊箱。隨葬器物七十七件,大多放置在邊箱,少數放置在頭箱。據所出告地策,墓主為公乘路平,下葬時間是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或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后九月。竹簡立靠在邊箱東北端的隔板上,大致呈卷狀,保存較好,內容是日書。清理時編號五百六十六枚,另有少數未編號殘片。有一件銅環與日書伴出,整理者疑是捆綁竹簡的用具。木牘一枚置于邊箱中東部的竹笥內,為告地策。邊箱還出土筆管和石硯一套。從墓葬棺槨平面圖看,石硯與日書伴出,而筆管與石硯鄰近,大概本來是有意識地放置在一起。
(四)其他地點
中筆M1 位于宜都市陸城鎮中筆村,原是宜都城郊的一處崗地。2008年發掘,出土一枚木牘。葬具為一槨二棺,槨室分為頭箱、邊箱和棺室。隨葬器物八十余件,多放置在頭箱和邊箱。木牘為物疏。據尸骨鑒定,墓主為女性,年齡45至50歲。墓葬年代屬西漢早期。
五座墳M3 五座墳位于老河口市(原屬光化縣),位于漢水之東,是一座小土崗,早年間曾有高大的封土冢,五座墳或由此得名。1973年底至1974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此發掘七座漢墓,其中M3出土了竹簡。該墓葬具為一槨一棺。槨室內部是樓房式結構,棺置于樓上,棺底用八匹木馬承托,形式特殊。隨葬器物七百多件。竹簡出自棺外之東,已殘,約三十枚,只有五枚可見字跡,內容是遣策。墓葬年代為武帝時期。
三、簡牘的隨葬方式及其反映的葬俗
關于簡牘隨葬方式及其反映的葬俗,我們主要從出土位置和斂放方式兩方面進行考察,并重點討論喪葬策疏。為敘述方便,本文將槨內除棺室之外的其他器物箱(室)統稱為“槨箱”。
(一)簡牘出土位置及時代特征
江漢地區出土簡牘的秦墓共六座,簡牘放置在棺內或頭箱,其中棺內四座,占據多數。出土簡牘的西漢早期墓三十四座(五座墳M3年代或許較晚,姑且不論),簡牘放置在槨箱的三十二座,占據絕大多數。據正式公布的資料,江漢地區出土簡牘的戰國楚墓,簡牘大都放置在槨箱,位于棺室內的很少。那么整體上看,這一地區時代大體介于戰國與西漢早期之間的秦墓,多把簡牘放置在棺內的現象比較特別,應該是秦人習俗。具體來看,岳山M36、睡虎地M11、龍崗M6的隨葬器物多放置在槨箱,卻把法律、日書、葉書等書籍或文書簡牘置于棺內,與簡牘關系密切的文具或算籌往往也置于棺內。這固然不能排除墓主個人因素的影響,但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一定的習俗。出土簡牘的秦墓,除江漢地區外,四川、甘肅還各有一座。其中甘肅天水放馬灘M1秦墓隨葬器物大都置于槨箱,而日書等竹簡也出于棺內,可以作為佐證。看來秦人的這種葬俗,隨著秦的占領而在楚故地出現,同樣隨著秦的短祚而消弱,將簡牘置于槨箱的習俗再次流行。
出土簡牘的江漢地區西漢墓中,只有鳳凰山M167、印臺M112所出竹簡沒有放置在槨箱內。鳳凰山M167遣策出土于槨頂板之上的青灰泥中。無獨有偶,江陵雞公山M48戰國楚墓遣策出土于接近槨板的填土中,不過在戰國這也屬于個別現象。據印臺墓葬整理者的說明,M112的竹簡置于棺內,這是江漢地區西漢墓中唯一一例。從其他地區的資料看,隨著時代發展,西漢中期以后,簡牘隨葬位置又發生明顯變化,流行將簡牘置于棺內。印臺M112出土資料尚未全面公布,其具體年代以及墓主人身份尚待研究。
(二)簡牘的斂放與相關器具
江漢地區秦漢墓葬出土的簡牘,從斂放方式看大體分為有盛具和無盛具兩類,同一座墓葬可以兩類方式并存。兩類斂放方式與簡牘內容或性質存在一定關系。無論是否有盛具,簡通常編連成冊,牘有時候疊壓、捆綁在一起。我們主要結合盛具談簡牘的斂放。
1.簡牘的斂放 秦墓出土的簡牘只有周家臺M30所出書籍、文書盛放在竹笥內,其余都沒有盛具。周家臺M30的竹笥內還置有文具。竹笥旁邊原放置一件歷日牘,如果牘的位置未曾因外力發生變化,則說明該墓隨葬的簡、牘是分開放置的。這種簡、牘分開放置的現象也體現在其他秦墓中,如其他兩座棺內均出土簡和牘的墓葬,王家臺M15的書籍簡位于棺足端、竹牘位于棺頭端,龍崗M6的法律簡也位于棺足端,與墓主身份密切相關的木牘則放置在墓主腰部。盡管如此,這種現象恐怕與簡、牘形制本身關系不大,主要是受簡、牘文字內容或性質影響。
漢墓簡牘的斂放大體分為三種情形。其一,簡牘沒有使用盛具。十八座。其中僅出土遣策或物疏的十座:揚家山M135、高臺M6、鳳凰山M8、M9、M167和M169、蕭家草場M26、五座墳M3所出為遣策,大墳頭M1、中筆M1所出為物疏。遣策或物疏與告地策同出的三座:高臺M18、毛家園M1和鳳凰山M168。僅出土性質或內容單一的書籍或文書的四座:張家山M249、M327為日書,張家山M258為歷日,高臺M46是賬簿木牘。此外,松柏M1主要隨葬文書木牘和物疏,另有少量木簡書寫文書牘的小結或標題,就已披露的資料看難以明確該墓物疏與其他文書簡牘的位置關系。其二,簡牘有盛具和無盛具并存。四座。其中張家山M247的書籍、文書盛放在竹笥內;遣策無盛具,置于同箱他處。張家山M336的情形與M247相近,只是書笥、遣策分別位于頭箱、邊箱,笥內的竹簡斂以書衣。孔家坡M8日書也用書衣盛斂,歷日和告地策無盛具,一起置于同箱它處。周家寨M8的日書沒有使用盛具,反而是告地策用竹笥盛斂,置于同箱它處。其三,簡牘全部放置在盛具中。四座。其中三座使用竹笥,謝家橋M1簡牘使用蒲草包裹,比較特別,這里姑且按盛具計算。其中遣策與告地策同出的一座,即謝家橋M1;物疏、告地策與其他文書簡牘一起放置在竹笥里的一座,即鳳凰山M10。胡家草場M12簡牘分別放置在兩個竹笥內,10號笥盛放書籍和文書,90號笥斂放遣策。睡虎地M77的所有簡牘放置在同一件竹笥內,內容是書籍和文書。
由上可知,就批次而言,江漢地區漢墓隨葬的簡牘大多不使用盛具,同時使用盛具的也不在少數。第一種情形下,同一座墓葬所隨葬簡牘的內容相對單一,多數只是隨葬品記錄清單,有時清單和與之關系密切的告地策同出。第二種情形下的四座墓葬,其中三座的書籍、文書用盛具,遣策、告地策另外放置且無盛具;一座即周家寨M8比較特殊,日書無盛具,告地策用盛具。第三種情形下的四座墓葬顯示,無論是書還是喪葬策疏,都可以使用盛具。鳳凰山M10將包括文書、物疏在內的所有簡牘放置在同一件竹笥內,胡家草場M12則專門用一件竹笥盛放遣策,從而與置于另外一件竹笥里的大量書籍、文書區別開來。總體上看,同一座墓葬隨葬較多種類的書籍、文書時,往往會使用盛具收納,而與書籍、文書同時入葬的喪葬策疏大都與書籍、文書分開并且單獨放置。喪葬策疏也使用盛具但是例子顯然偏少。這似乎說明,在時人觀念里,書籍、文書與喪葬策疏是有區別的,后文將以專節進一步討論喪葬策疏。
2.盛斂簡牘的器具 盛斂簡牘的器具大體有兩種,即笥和囊。謝家橋M1的簡牘用蒲草包捆,蒲草的功用似與笥、囊有一定區別,姑且一并敘述。
笥 戰國秦漢時期常見的盛器。以竹質為主。《說文·竹部》:“笥,飯及衣之器也。”實際上笥的用途遠不止于此,如用笥盛斂簡牘的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就不算少見。就考古發現而言,戰國楚墓已經用笥盛斂竹簡,但目前不能確定楚墓遣策對所隨葬竹簡及其盛具作有記錄。張家山M247遣策34號簡記“書一笥”,明確說明該墓盛放書籍文書的竹器為“笥”。里耶秦簡中有“書笥”之語,見于9-1657“畜官書笥”,居延漢簡89:13B記有“書篋一”。《漢書·賈誼傳》:“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顏師古《注》:“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急就篇》卷三顏師古《注》:“篋,長笥也。”笥、篋屬于同類器具,用于盛“書”時即可稱“書笥”、“書篋”,其例與居延漢簡“錢笥”(EPT21:26)、“衣篋”(293.1+293.2)等稱謂類同。
周家臺M30、張家山M247和M336、胡家草場M12、鳳凰山M10、印臺M60、睡虎地M77、周家寨M8等八座墓葬出土有盛放簡牘的竹笥。其中只有胡家草場M12出有兩件笥,余者都是一件。胡家草場M12編號90的竹笥盛放遣策和文具,周家寨M8的笥里只見一枚告地策。如果把這兩件笥排除在外,則目前江漢地區秦漢墓葬考古共出土七件書笥。
其他地區西漢墓也可見用笥盛放簡牘,如阜陽雙古堆汝陰侯墓、定縣八角廊中山王墓、南昌海昏侯墓等。這三座墓葬等級較高,可見使用笥盛放簡牘是通行作法,沒有身份等級之別。《漢書·張安世傳》記“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情形與此相合。
在斂放圖書方面,笥的應用最為普遍,不分主人身份等級高低,無論書的官私性質,重要、普通與否。在具體斂藏方式上,重要與普通圖書之間則存在嚴格區分,前者須要分門別類單獨封藏。這種差異有律令明文規定。岳麓秦簡令文云:“獄有制書者,以它笥異盛制書,謹封藏之。勿令與其獄同笥。”規定制書要跟其他文書區別開來,用單獨的笥封藏。張家山《二年律令·戶律》簡331-332記:“民宅圖、戶籍、年?籍、田比地籍、田合籍、田租籍,謹副上縣廷,皆以篋若匣匱盛,緘閉,以令若丞、官嗇夫印封,獨別為府,封府戶。”規定田宅、戶籍等圖籍的副本,縣衙要用器具盛斂、密封并單獨收藏。海昏侯墓出土四件盛放簡牘的漆笥,其中三件主要盛放竹書;一件盛放公文牘,內容是海昏侯及其夫人上書皇帝、皇太后的奏牘以及朝中關于劉賀的議奏或詔書。這些公文牘單獨置于一件笥內,不排除受到了律令相關規定的影響。
囊 也稱書衣。目前考古發掘的秦墓未見書囊。從其他資料看,秦時已用囊盛裝簡牘。岳麓秦簡記秦規定“執法”向皇帝上計最的時候,需用“筭橐”盛裝相關文書,整理者在“筭橐”下注:“疑為專門用來裝計最簿籍的袋子。”張家山M336、孔家坡M8各隨葬一件書囊,前者可能保存較好,但是圖像尚未公布,后者僅存殘片。這樣,目前已知江漢地區二座漢墓各隨葬一件書囊。值得注意的是,張家山M336的書囊放置在竹笥里。孔家坡M8發掘簡報記述日書伴出殘竹笥和絲織品殘片,推測是用絲織品包裹放入竹笥內下葬,后來出版的簡牘報告刪去了有關竹笥的內容。較晚文獻中有“囊笥”一詞。《新唐書•蕭廩傳》:“書成不可露赍,必貯以囊笥。”柳宗元《與友人論為文書》:“間聞足下欲觀仆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于胸中。”推想其來源固然是因為囊、笥都是藏斂書籍的器具,不過與囊、笥配套藏書恐怕也不無關系。
在傳世文獻里,漢代又稱書囊為“方底”。《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顏師古《注》:“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幐耳。”連云港尹灣西漢晚期M6(墓主字君兄)出土自題“君兄繒方緹中物疏”、“君兄衣物疏”兩件物疏。據物疏所記,方緹內所盛物品主要是書籍、文書和文具,“方緹”或即書囊,當讀為“方底”。據物疏記載,該墓隨葬大量絲織衣物,但是發掘報告沒有提及,推測包括“方緹”在內的絲織物都已經腐朽。絲織品不易保存,從尹灣M6的情況看,隨葬書囊的數量肯定多于現在的發現。
植物包捆 謝家橋M1的遣策和告地策用蒲草捆縛、包裹在一起。西北地區漢簡記移徙文書,常見“蒲封”、“蒲封書”、“蒲書”之語。學者或疑“蒲封”的功用與書囊相同,黃浩波進一步提出謝家橋M1用蒲草包捆簡牘,是對現實“蒲封”形制的模仿,看法頗為新穎。西北地區漢簡所見“蒲封”文書,似乎都屬于移徙文書,而謝家橋M1用蒲草包裹、緘捆的遣策和告地策也是一套移徙文書。或許蒲草通常用于封斂移徙文書,而不用于日常存放、收藏的簡牘。
附帶提及,以草類植物纏書,秦已入律。睡虎地《秦律十八種·司空》簡131—132記:“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柔可用書者,方之以書,無方者乃用版。其縣山之多菅者,以菅纏書,無菅者以蒲、藺以枲![]() 之。”規定纏書首選用菅,無菅時以蒲、藺和枲,體現了因地制宜以及時人對菅及蒲、藺質性的認識。西北地區漢簡提到行書的保存狀況時,有與蒲繩相關的記錄,如“蒲繩解脫”(72ECC:13)、“蒲繩完”(72ECC:70)等。又作簿中可見“伐蒲廿四束”(161.11)、“得蒲四百五十束”(EPT52:57)一類的記載,可能其時其地多蒲,因此蒲草成為使用最多的一種植物。
之。”規定纏書首選用菅,無菅時以蒲、藺和枲,體現了因地制宜以及時人對菅及蒲、藺質性的認識。西北地區漢簡提到行書的保存狀況時,有與蒲繩相關的記錄,如“蒲繩解脫”(72ECC:13)、“蒲繩完”(72ECC:70)等。又作簿中可見“伐蒲廿四束”(161.11)、“得蒲四百五十束”(EPT52:57)一類的記載,可能其時其地多蒲,因此蒲草成為使用最多的一種植物。
(三)遣策、物疏與告地策
戰國楚墓和西漢墓中多見遣策。物疏由遣策發展而來,與告地策一樣都從西漢早期開始出現,而告地策主要通行于西漢早期的江漢地區,具有更明顯的時代和地域特征。
江漢地區出土喪葬類簡牘的漢墓不少于二十一座。其中只出遣策的墓葬十一座:張家山M247、M336,鳳凰山M8、M9、M167、M169,揚家山M135,蕭家草場M26,高臺M6,胡家草場M12和五座墳M3;只出物疏的有三座:大墳頭M1、中筆M1和松柏M1;只出告地策的有二座:孔家坡M8、周家寨M8;遣策與告地策同出的三座:謝家橋M1、毛家園M1和鳳凰山M168;物疏與告地策同出的有二座:高臺M18、鳳凰山M10。時代最晚的遣策出自武帝時期的五座墳M3。絕對年代明確、時代最早的物疏出自文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73年)的高臺M18。時代最早的告地策出自呂后五年謝家橋M1,最晚的是武帝早期周家寨M8。綜合這些信息可知,西漢早期物疏出現,不過遣策依然占據主要地位;告地策也已出現,但似乎沒有達到流行的程度。從告地策與遣策(物疏)的內容看,兩者關系密切,尤其當告地策和遣策(物疏)在同座墓葬伴出時,兩者間的位置關系和編冊形式,進一步凸顯了這一點。
遣策和告地策同出的三例中,毛家園M1兩者位置關系尚不明確。謝家橋M1的遣策和告地策用蒲草包裹在一起,少部分遣策和告地策已公布,從形制看應該是編為一冊,呈現簡、牘合編的現象。鳳凰山M168遣策和告地策出土位置鄰近,告地策牘下部有一道比較明顯的痕跡,或許是下葬時跟遣策捆縛在一起的繩索留下的印痕。物疏與告地策同出的兩例中,鳳凰山M10的1號牘正面是物疏,差一行書寫未盡而轉入背面接記,然后從背面第二行起書寫告地策。高臺M18的四枚告地策和物疏牘出土時次第疊壓,封檢、告地策正文、名籍和物疏依次組成一套完整的謁告安都丞的文書,這種情形可以類比編連成冊的竹簡。
鳳凰山M10的物疏書于告地策之前,而高臺M18物疏書于告地策之后,說明當告地策和遣策合成一套文書時,彼此的先后次序不是固定的。某些告地策的具體內容跟遣策有明顯對應關系,如謝家橋M1告地策概括記錄所移徙之人、物有“牒百九十七枚”,毛家園M1“牒書所與徙者七十三牒”,同墓出土記錄具體物品的遣策簡數正好與之相應。這種情形下,告地策大概不能脫離遣策而存在。不過告地策的主要目的不是移送遣策(物疏),而是使墓主通過官方認可而順利在地下安家立戶;所移徙之物中更看重奴婢、車馬牛,所以能夠看到更多告地策本身即具體記錄所移徙的奴婢、車馬牛及其數目,而省略其他物品,乃至脫離遣策(物疏)成為一份獨立的完整文書。隨州兩座出土簡牘的漢墓,都只有告地策而不見遣策(物疏);荊州出土的五例告地策都伴出有遣策(物疏),且年代略早于隨州的兩例。期待今后有更多考古發現,從而拓展、加深相關認知。
告地策對奴婢、車馬牛的重視來源于現實生活。《二年律令·戶律》簡334—335:“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財物,鄉部嗇夫身聽其令,皆參辨券書之,輒上如戶籍。”簡337:“民大父母、父母、子、孫、同產、同產子,欲相分予奴婢、馬牛羊、它財物者,皆許之,輒為定籍。”《漢書·武五子傳》記張敞向宣帝奏報昌邑王:“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漢代現實生活中的戶籍,除去家庭成員外,還要登報田宅、奴婢和財物,而馬牛羊屬于頭等財物,可以跟“它財物”對稱。遣策往往記奴婢和車馬牛,實物則以偶人偶車馬替代。
不少學者指出,告地策集中出土于江漢地區西漢早期墓葬,當與當地民俗信仰有密切關系。江漢地區戰國楚墓出土的竹簡中,卜筮祭禱文書比較常見,也是民間普遍信仰的反映。如果說秦滅楚后,遣策和卜筮祭禱文書鮮見于此地墓葬,是秦統治下秦俗的反映;可是漢取代秦后,此地遣策隨即復蘇,且發展出新形式物疏,卜筮祭禱文書卻依舊了然無蹤,而一種新文書告地策很快登場;除去現實戶籍制度的影響外,告地策所反映的信仰變化,值得進一步留意。
黃盛璋曾據高臺M18的資料指出,隨告地策登報的遣策是財戶簿,“已經不是禮經的遣策”。也就是說,跟告地策配套的遣策,與禮制規范下的戰國遣策性質有別,這自然是有其道理的。不過這種情形下的遣策,有的亦可見勾識符號,至少不能肯定完全與禮書記載的“讀遣”一類行為無關。西漢早期墓葬中不與告地策配套的遣策,更難肯定脫離了禮儀范疇。鳳凰山M167的遣策出土于槨頂板之上的青灰泥中,田天認為這提示遣策在最后階段入葬,至少能從側面證明當時“讀遣”一類環節的存在。由此看來,西漢早期遣策的性質和形式正在發生變化,但是新變中隱含著舊俗,且舊時禮俗可能依然占據上風。
四、簡與牘的應用及編冊形式
從考古發現看,江漢地區的簡以竹質為主,木質很少;牘則以木質為主,竹質較少。簡、牘的應用具有一定時代特征。大體而言,戰國時流行用竹簡,迄今只有包山M2發現一枚赗書竹牘。至秦,牘的應用顯然增多,書寫內容有日書、歷日、書信等。西漢早期,可見簡、牘合編為一冊或者同冊簡、牘并用而捆縛在一起的現象。為方便敘述,下文以簡牘合用統稱這兩種情形。
(一)簡牘合用
目前江漢地區漢墓出土的大體可以確定為簡牘合用的冊子,前文已經提到兩例,即謝家橋M1的竹簡遣策和竹牘告地策及松柏M1木牘官文書和木簡標題。此外,睡虎地M77簡牘合用冊似乎較多。如其編號N組的私人簿籍是由五十多枚竹簡和二件木牘構成,據已公布的圖版和內容,N1牘與N組竹簡都是兩道編繩,編繩間距基本一致,所以N組簿籍應該就是簡牘合編冊,N1牘很可能是這組簿籍內容的總計。編號L組和M組的文書也存在簡牘合編的現象。
這種簡牘合用冊在其他地區漢墓也能見到。馬王堆M3遣策包含竹簡四百枚、木牘五枚,簡、牘都是兩道編繩,間距一致,田天已經指出是混編成冊入葬。雙古堆M1出土多種竹木簡書籍,又有三枚抄寫書籍篇題的木牘,其中一枚牘的篇題確定與墓內書籍有關。
上述出自不同地區的簡牘合用冊涉及數種不同性質簡牘資料,可見應用比較廣泛。所用簡牘既有材質一致的,也有竹、木混合的。這種合用冊通常以一種載體為主,目前所見大都是用簡書寫正文,用牘書寫統計或總結性的內容、篇題或目錄等。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什么時候用簡,什么時候用牘,應該主要視文字內容和性質而定,且有一定“慣例”,比如書籍正文一般用簡,而迄今所見告地策都書寫在牘上。
應該提出,可能出土于江漢墓葬的北京大學藏秦簡存在簡牘合編冊,說明這種編冊秦始皇時期已經出現,這與牘的應用在秦時明顯增多是同步的。簡牘合用一直不是簡冊形式的主流,但存在時間較長。敦煌懸泉置出土的成帝陽朔二年(前23年)“車亶轝簿”、長沙五一廣場出土的東漢殤帝延平元年(106年)“調署伍長人名數書”,都是簡牘合編冊。
(二)空白簡牘
一些墓葬隨葬有完整的空白簡牘,有的和文具一起盛斂在竹笥內,有的跟文字資料伴出。這與葬俗和簡冊形式關系密切。其功用或性質,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書寫材料 作為書寫材料的空白簡牘,往往和其他文具一起盛放在竹笥內,整體上呈現出時人隨葬成套書寫用具的習俗。鳳凰山M167、M168各出土一件盛放空白木牘和文具及其他物品的竹笥。M167的竹笥存牘二枚和削刀、毛筆及與文具關系密切的算籌,同時盛放有三十五小卷絲織品,遣策稱之為“繒笥”,之后接記“合中繒值二千萬”,可見盛放絲織品是這件竹笥的主要用途,但笥內所置書寫用具品類著實不少。M168的竹笥有牘六枚和削刀、毛筆、墨、硯及算籌,其中四枚牘長23.1厘米,屬于尺牘;二枚長11.4厘米,大體相當于前者的一半。后世所謂“紙(牘)墨筆硯”,在M168的竹笥內一應俱全。該笥還盛放天平衡桿和砝碼,遣策稱之為“計笥”。嚴格說來天平、砝碼、算籌都可歸為計具,不過計具與文具的關系非常密切。
廣西貴縣羅泊灣M1是一座等級較高的西漢早期墓葬,出土木牘五枚,其中二枚完整,三枚殘損。整理者介紹有二枚牘無字,而所公布的三枚有字牘中的二枚有殘損,由此知道應有一枚完整的無字牘。該墓槨室早年被盜擾,木牘原位置無考。編號M161號牘自題“從器志”,其中一行記有“研筆刀二櫝,一笥,繒緣”,意思是研筆刀櫝都盛放在一件以繒緣邊的笥里。未知櫝是否用為“牘”,指笥內的空白牘,整理者認為“櫝”為文具盒。戰國楚墓中已有盛斂在竹笥內、與文具伴出的空白簡。長沙左家公山M15楚墓頭箱出土一件竹笥,內置空白簡一冊二十五枚,削刀、毛筆、小竹筒各一及算籌四十支。竹簡以上下兩道絲繩編連成冊,“然后用兩塊竹塊夾住,想是用以書寫的簡冊”。
羅泊灣M1、左家公山M15的資料顯示,隨葬成套書寫用具且以竹笥斂放的作法不是始自西漢,也不限于江漢地區。
封護編冊 跟有字簡牘伴出的、完整的空白簡牘,有的可能是起封護作用的。依整理者編排,周家臺M30所出《三十四年質日》冊末附有四枚空白簡。松柏M1出土木牘較多,其中的六枚空白牘,整理者認為是上下封頁。簡冊里的這種空白簡可以跟馬王堆M3帛書篇首的空白行,篇尾的某些留白相類比。
張家山M247竹書出土時一端被數枚空白木牘疊壓,由于書笥保存不好,竹書有移位、散亂,空白牘也存在移位的可能。這幾枚木牘有可能是在竹書斂入竹笥后,再放置在竹書上起保護作用的。孔家坡M8有一些空白簡、牘跟歷日簡冊伴出,其中位于歷日簡上部的三枚空白牘,功用或許與張家山M247的相同。我們的這種推測受到左家公山M15空白簡冊的啟發。從圖版看,該墓所謂夾住簡冊的“竹塊”類似竹牘(長度略短于竹簡),應該是起封護簡冊的作用。這種封護簡冊的空白牘,跟上述類似于今天封面、封底的空白簡牘性質不同。需要說明,這里所說的空白簡牘,除去左家公山M15的竹塊外,都不排除作為書寫材料的可能。
編冊中的分隔簡 周家臺M30所出《日書》共有二百四十枚簡(簡69—308),包含四幅線圖。簡155、182—186、280、294—295等十枚是空白簡,均與線圖有關。簡280、294—295分別位于圖二與圖三、圖三與圖四之間,整理者認為圖二至圖四原本屬于一節,圖與圖之間以空白簡分隔。圖一由簡156—181組成,155、182—186分別位于線圖一第一枚簡之前、最末一簡之后,依例也可以認為是起間隔作用。不過線圖一與下文之間設置五枚間隔簡,似乎偏多,那么這些簡是否單純起間隔作用,需要進一步斟酌。整理者的編排有竹簡原始出土位置關系作依據,比較可信。
(三)編冊的固定
上文提到的用笥、囊盛斂簡冊,特別是秦律規定的以草類植物“纏書”,客觀上都起到了固定編冊的作用。避免收卷的編冊松散,還有其他方式。陳夢家曾介紹武威磨咀子M6《儀禮》簡冊的束縛形式:“在整理殘碎簡中,曾見有數個薄狹竹條,外纏以絲綢物,似是竹圈的殘余。此物可能套在每卷之外,用以束縛木簡卷子。”銀雀山M1竹書中夾有數枚銅錢,有的殘存絲繩痕跡,吳九龍認為銅錢應該是“系在簡冊篇首的細絲繩上的,細絲繩繞住卷好的簡冊,銅錢插入兩簡之間,卷起的簡冊就不易散開了”。在江漢地區漢墓簡牘資料的整理中,可見類似報道,如周家寨M8與《日書》共存的銅環,可能與束縛簡冊有關。附加說明,左家公山M15的“竹塊”(竹牘)具有封護簡冊的作用,同時也能固定簡冊,目前出土的有字簡冊未見這種固定方式。編冊的固定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值得更加注意。
五、結語
就目前的考古發現看,江漢地區出土簡牘的秦墓共有六座。西漢早期,出土簡牘的墓葬明顯增多,達三十余座。秦、漢墓隨葬簡牘的方式和內容有同有異,最大不同是秦多將簡牘置于棺內,西漢早中期一般置于槨箱里;秦似乎不用遣策,漢則流行,并由戰國時期即存在的遣策發展出物疏這一新形式、受現實戶籍制度或者信仰變化的影響出現告地策。告地策主要出土于江漢地區的西漢早期墓葬里,遣策(物疏)與之關系密切,兩者通常放置在一起甚至組成一套簡、牘合用冊,往往跟書籍、文書分開放置,且很少使用盛具。結合其他地區出土或機構收藏的資料看,簡牘合用冊從秦出現,起碼沿用至東漢中期,其出現恐怕主要與實用性有關。盛具主要是笥和囊,而笥的應用更為普遍。從出土律令文獻看,重要文本不能與普通文本同笥,須分類單獨封藏。書囊發現較少,除去可能本來較少應用外,絲織品易腐朽以致書囊未能保存下來,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值得留意的是書囊常常與笥配合使用。為防止收卷的簡冊開散,時人還應用一些物件以達到固定簡冊的目的。完整的空白簡牘,有的是書寫材料,相當于空白紙張,往往跟其他文具一起收納于笥內,反映了古人隨葬成套書寫用具的習俗;有的是簡冊的組成部分,相當于封面、封底或隔頁,也是現實書籍制度的體現;有的疊壓在文字資料之上,或許是隨葬時有意放置,單純起保護簡冊的作用,也不排除示意書寫材料的可能。戰國楚遣策似乎不記錄隨葬的文字資料和文具,而這類內容在西漢初期的遣策中就可以見到,最好的例子出自張家山M247。這是遣策內容的一個變化,背后的原因值得考量。
最后附帶討論其他地區的西漢墓葬相關考古發現。據學者的研究和我們的初步考察,西漢早期出土簡牘的墓葬,除去江漢地區外,湖南、山東、安徽、四川、廣西等地也有發現。西漢中期到中晚期,出土簡牘的墓葬數量以江蘇、山東為最,甘肅、江西、安徽、河北、北京、陜西等地也有發現。西漢晚期,出土簡牘的墓葬數量仍然以江蘇和山東為首,甘肅、陜西、青海等地也有發現。總起來看,江蘇的此類墓葬集中在連云港市,山東發現于臨沂金雀山、銀雀山和日照海曲及青島土山屯,甘肅則集中在武威、永昌一帶。西漢中晚期開始,簡牘從流行置于槨箱轉而置于棺內,牘的應用進一步增多,物疏代替遣策。至西漢晚期,江蘇、山東絕大多數隨葬簡牘的墓葬都在棺內放置物疏或衣物疏,中小型墓葬所隨葬書籍、文書的數量有下降趨勢。西漢早期,同一座墓葬所隨葬的簡牘可以放置在不同的槨箱。隨著時代發展,當簡牘置于棺內時,槨箱就鮮少放置簡牘,也就是說同一座墓葬棺內與棺外放置簡牘的兩種情形通常不相共存。有學者指出西漢中后期開始物疏置于棺內,跟合葬墓的出現或葬儀制度、生死觀念的變化有關。如果放眼到所有性質的簡牘資料,或許能得到更全面的認識。西漢中晚期至王莽時期,甘肅出土簡牘的墓葬有約宣帝時期的水泉子M5和M8、王莽時期的磨咀子M6,似乎流行將簡牘放置在棺蓋上,且均不見物疏,與其他地區的葬俗有一定區別。
作者:李天虹
來源:“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于《考古學報》2023年第3期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國策建言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