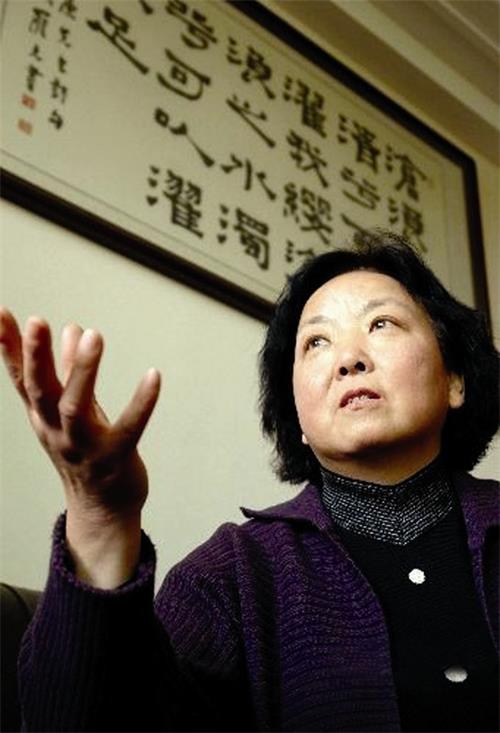一些史學研究者把所發現的某一個村莊、某一座廟、某一個舞廳、某一個飯店、某一本家譜、某一份“必須”錯缺的地圖、某個“足夠”另類的鄉賢的回憶,塑造成自己心中的敦煌,無限中心化其發現的價值,而其所在的時代、所處的自然和人文環境、重要政治變遷、歷史性事件的過程和震蕩、經濟社會的宏觀變化,被策略性回避。于是,跑馬圈地,成為一些人的狂歡,把“鄰貓生子”、別人無從置喙,當成絕學。史學在自我墮落中。

歷史研究的對象是過去。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的論斷,是習近平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此作的新的申說。
然而,歷史研究也在不斷遭遇挑戰乃至危機,這是歷史學反復跌入谷底又鳳凰涅槃的契機,但應當明了其中很多危機是史學家親手“制造”出來的,又必須由史學家親手終結。歷史和歷史學家互相成全,又互相考驗乃至敵對,在相互詰問中,歷史學獲得了永恒的生命。“碎片化”是當下中國史學面對的諸多問題之一。有人認為“碎片化”不成其為問題,“在中國歷史學界,我懷疑碎片化是否真的成為了一個問題”。這種意見并非沒有共鳴,但現有的眾多論說表明,大多數人將其視為“問題”。例如章開沅說:“‘碎片’一詞,易生誤解。或許可以說,我們所已知者無非是歷史的一鱗半爪,往往都是組成歷史的碎片,然而卻不能認為歷史本身就是一堆雜亂無章的碎片。”他主張,“重視細節研究,同時拒絕‘碎片化’”。錢乘旦直陳“碎片化”為史學重大危機,認為,“歷史學受到后現代主義的巨大沖擊,變得越來越碎片化……歷史學正遭遇后現代主義,它的體系正在被解構。這就是歷史學正在面臨的重大危機”。何為“碎片化”?成因何在?為何成為問題?穿行于“碎片”之中的中國歷史學應當如何?對此均有反思和論述的必要。
一、碎片、碎片性和碎片化
因為名詞之間曖昧難明的聯系,新近關于“碎片化”的討論多從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多斯1987年出版的《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開始立論,難怪多斯自詡該書“已成為眾多立論的源泉”。其實,無論問題提出之背景,還是所涉問題形成之過程,抑或是批評的對象,還是對史學未來的期許,當下中國史學界所討論的“碎片化”和多斯當年所指,均非一事。
但多斯對年鑒學派第三代沉溺于描繪和敘述,失去總體性、整體性、通貫性追求,甚至剝奪人類在史學研究中核心地位的批評,和中國史學界近來面臨之情勢有很多共同之處,語言的“所指”和“能指”錯舛而奇特地構合,也算一景。在中國史學界,“碎片化”作為問題的提出,先于“碎片”,因為前者是“問題”,而后者不是。但因為語言邏輯的關系,諸多論家多從確定歷史研究必須依賴“碎片”即史料開始鋪陳。李金錚說:“從主觀愿望上講,每一個歷史學者都可能希望對歷史現象‘一網打盡’。但由于人類社會極其復雜,而人的生命、精力和智力又非常有限,不可能對所有歷史內容進行全面研究,而只能選擇具體,選擇碎片。”羅志田說:“我們所面對的史料,不論古代近代,不論是稀少還是眾多,相對于原初狀態而言,其實都只是往昔所遺存的斷裂片段……可以說,史學從來就是一門以碎片為基礎的學問。”在此語境下,史料是“碎片”,史料即“碎片”,所以,從歷史哲學層面上講,歷史研究無法回避“碎片”。自然,“歷史是一個巨系統,即使是這個世界一天的歷史,要窮盡其中的所有,歷史學家也是無能為力的”。歷史研究確實是在無數“碎片”中穿行,但從邏輯上卻無法得出歷史研究應當“碎片化”的結論。“我們迄今賴以研究歷史的證據可能確實是歷史身上抖落的‘碎屑’,但我們既然可能從一個細胞中找到隱藏生物體全部秘密的基因,從這些‘碎屑’中找到歷史傳承的規律也非癡人說夢。”相對于歷史本體而言,史料本身所呈現出來的“碎片性”,無礙于歷史學家實踐自己的偉大使命——“究天人之際”,是空間維度;“通古今之變”,是時間維度。在萬古江河滄海桑田之變中,史學家力圖把握其中的結構,透視其間的因果,總結其中的規律,以為鏡鑒。司馬遷為史學家厘定的任務,抓住了人類作為生活在空間維度和時間維度中智慧生物的本能。正因為如此,從全球史角度看,史學幾乎是所有文明擺脫蒙昧之后的第一門精神性創造。然而,“碎片化”研究在中國史學界已成事實。李長莉說,“其意指研究問題細小瑣碎,且缺乏整體關聯性與普遍意義內涵,因而缺乏意義與價值”,考慮到李長莉的學術背景,以下的批評尤其直率:“這種‘碎片化’傾向尤其在近二十多年來新興的社會史和社會文化史(新文化史)領域表現最為突出。”回顧多斯對“碎片化”史學面目的描寫,對照當下中國史學界的某些現象,是時時讓人會心一笑的——“歷史學家對一切都表現出好奇,他們把注意力轉向社會邊緣、公認價值的負面、瘋人、巫師、離經叛道者”;“史學家把歷史上的重大時刻和人為的轉折拋在一邊,而唯獨看重百姓日常生活的記憶。……同樣,人們在描述村莊、婦女、移民或社會邊緣人物時,也賦予其一種新的美學形態”;“放棄布羅代爾的宏大經濟空間,從社會退縮到象征性的文化”;“人類的脈動被歸結為人類生存的生物或家族現象:出生、洗禮、結婚、死亡”。 中國“新興史學”研究的“碎片化”現象,李長莉總結為“論題小而微,缺乏大關懷與大問題”,“論題細碎而零散,缺乏大聯系與大序列”,“論題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論與大闡釋”。在當下的史學實踐中,一些史學研究者把所發現的某一個村莊、某一座廟、某一個舞廳、某一個飯店、某一本家譜、某一份“必須”錯缺的地圖、某個“足夠”另類的鄉賢的回憶,塑造成自己心中的敦煌,無限中心化其發現的價值,而其所在的時代、所處的自然和人文環境、重要政治變遷、歷史性事件的過程和震蕩、經濟社會的宏觀變化,被策略性回避。于是,跑馬圈地,成為一些人的狂歡,把“鄰貓生子”、別人無從置喙,當成絕學。史學在自我墮落中,“失去了樂隊指揮的身份,而淪落為井下的礦工,其職責是為其他社會科學提供研究‘原料’”。
很清楚的邏輯是,史料的“碎片”性質,并不是“碎片化”研究的理由,當然也不是其成因。然而,新近的討論中,無意中出現了一對誤讀:因為史學研究依賴于碎片性的史料,所以史學研究自然會“碎片化”;“碎片化”其實就是微觀化、精細化。如有論者說:“歷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在比較成熟的西方史學界也許存在,在當下中國大陸史學界,我們的微觀研究現狀遠未達到需要警惕細化的程度。”這種替代,在邏輯中是需要仔細辨別的。
從微觀入手,對歷史材料進行條分縷析的精細研究,是把握大歷史、解決大問題的必要前提。梁啟超評價明末清初學者閻若璩的歷史性貢獻:“《尚書古文疏證》,專辨東晉晚出之《古文尚書》十六篇及同時出現之孔安國《尚書傳》皆為偽書也。此書之偽,自宋朱熹、元吳澄以來,既有疑之者。顧雖積疑,然有所憚而莫敢斷。自若璩此書出而讞乃定。夫辨十數篇之偽書,則何關輕重?殊不知此偽書者,千余年來,舉國學子人人習之,七八歲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視為神圣不可侵犯;歷代帝王,經筵日講,臨軒發策,咸所依據尊尚。……而研究之結果,乃知疇昔所共奉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實糞土也,則人心之受刺激起驚愕而生變化,宜何如者?”梁啟超稱閻若璩的研究“誠思想界之一大解放”。閻若璩經考證而宣判“古文尚書”的死刑,在中國學術史、思想史、社會史乃至政治史上具有重大影響,其由“碎片”而始,卻非“碎片化”指向,這在中外史學數千年演化歷史中,實為百變常新的奧妙之一。事實上,即使是最嚴厲的“碎片化”批評者,也沒有誰否定精細微觀研究之價值,所以繼續相關名詞之糾纏實無必要。筆者認為,“碎片化”的成因,首在時代變化所引起之史學變化。多斯在論述年鑒學派日益流于“碎片化”研究時,分析了時代變局對史學研究的影響:“結構主義也在非殖民化的背景下風行起來,人種學的意識激發了對其他文明的關注,人們對這些社會的抵抗力、穩定結構和不同于西方的價值觀產生了興趣。對‘他者’和人類真相的發現動搖了歐洲中心論。生活在別的空間的他者也上升為一種典型。”中國當下的“碎片化”成因不同于此,它直接肇因于先前過度用力的不當做法,即把幾乎所有的歷史簡單地歸結于幾個問題,忽視了歷史非線性的復雜化和多層次。有論者回顧了某一時期近代史研究中排他性敘述框架的形成及其缺失:“政治史的內容占了極大的比重,而關于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的敘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適當的地位。”其實,不光近代史如此,整個歷史學界都曾被限定在有限的議題內。“碎片化”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是對這一現象的矯枉過正,乃至漸入歧路。其次,史學家對近代以來知識,特別是自然科學知識的爆炸性增長掌握不足,從而削弱了把握整體歷史發展的思維能力,在“碎片化”研究的“小確幸”中自承無力,耽美于“小知識”的自我審美。史學啟蒙時代為后世垂范的大家,幾乎掌握了當時那個時代大部分的知識,宏觀處,通天徹地;微觀處,芥子須彌。以《史記》言,內納八書、十表、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里,而其中的八書記天文、歷法、禮、樂、音律、封禪、水利、財用等,更有今日整體史的大模樣。以西方“歷史之父”希羅多德的《歷史》言,九卷皇皇,其前半部,全面闡述地中海東部西亞、北非及希臘地區約20個古代國家的自然地理、民族分布、經濟生活、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歷史變遷、風土人情;其后半部,主述波斯人和希臘人數十年間爭戰傳奇。其取材之豐富,結構之宏大,取向之總體,說布羅代爾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祖述于此也不為過。而今天之史者,確實可以歸因于知識的海量積累和增長,總的來說,只能圍繞專業掌握有限的知識。現代科學知識,尤其是近代以來物理學、天文學的飛速發展及其哲學含義,在史學界傳播甚微。即使是習慣嘗鮮的美、歐史學界,也不再能看到可以媲美前賢如牛頓、笛卡爾、玻爾、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家兼思想家,幾乎無人深究海森堡“測不準定理”“薛定諤的貓”、波粒二象性、“雙縫實驗”等的人文底色和哲學深度。無力感不僅充斥年鑒學派后人的心靈,也逼迫中國某些史學研究者在嚴厲的量化考核和榮譽追逐中急切地尋找出路,并把自身的“碎片化”研究正當化,在“逃跑”和“躲避”中致“碎片化”研究泛濫而漸成災情。“一些諸如氣味、想象、死亡、空間、夢、垃圾、屎、疼痛、疾病、姿態、眼淚、同性戀、手淫、食物、鹽、煤、火、鏡子、乳房、頭發、內衣、廁所、戒指等過去不入歷史研究者法眼的課題,現在都已經成為新文化史家的關注對象與研究內容。事實上,問題主要不在于這些東西被納入研究對象,而在于一些研究者把這些當作了歷史研究的主旨和樂趣。最后,特定的歷史研究,特別是某些社會史研究范式被神話,并對“經典”作了拙劣的模仿。王晴佳直陳:“我們探討國外史學研究‘碎片化’的形成,其實也就是要探究新文化史的興起”,他認為,新文化史是對社會史的一種反彈,是歷史研究“碎片化”的主要表現。池子華等人則認為“碎片化”問題適用于整個社會史。到底是僅僅在新文化史研究中,還是在整個社會史研究中,或是在“新興史學”中,抑或在整個歷史研究中存在“碎片化”問題,乃至嚴重到以“危機”相論,是可以繼續討論的。但就“始作俑者”而言,多斯是在年鑒學派的演進過程中提出“碎片化”概念的。他對年鑒學派的第一代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的崇敬自不待言,對第二代核心人物布羅代爾也贊佩有加,并將其和第三代的“碎片化”研究作了區隔,“布羅代爾本人始終不忘史學的基礎,而他的繼承者們則早已將此拋在腦后。布羅代爾在研究中重視總體性、時間參照的統一性、各層次現實間的互動性和社會史的地位”。這一論述序列表明,多斯所說的“碎片化”主要指曾經“收編”了其他諸多學派,以整體性的社會史研究為主要特征的年鑒學派,在以歷史人類學和社會文化史研究為主要特征的第三代一些人中出現了游移和墮落。中國當下的“碎片化”研究,顯然沒有這么復雜的譜系,它更像是反復出現的“一窩蜂”式史學“熱點”。而且,這種“熱點”是對新文化史名著諸如亨特的《法國大革命中政治、文化和階級》、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金茲堡的《乳酪與蟲子》、達恩頓的《屠貓記》等著述的拙劣模仿。當然,考慮到中外史學的映射互動關系,目前出現在國外史學中的一些“碎片化”研究所蘊含的歷史虛無主義尤其值得警惕。如有國外研究者“關注”販賣黑奴過程中當地黑人、北非人的“作用”,有人研究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中拿鴉片當藥品使用的“風俗”,等等。其“高級”的意識形態蘊含,說明某些人的所謂“新清史”研究并非孤立現象。
三、中國史學對“碎片化”的應有態度
如何走出“碎片化”研究?錢乘旦提出的要點是“體系”,“不管歷史學家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沒有體系就無法篩選史料,也無法書寫歷史。……就體系而言,框架是關鍵,框架的邊界就是理論”。李先明等人提出,“碎片”是史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要選擇有“歷史意義”的“碎片”進行研究。李金錚訴諸“整體史”,提出“宏觀史學是整體史的最高追求”。王學典等人則直接主張“重建”歷史的宏大敘事,他們認為,“碎片化”背后襯托著當前史學界宏觀思維能力的枯竭和理論抽象思維能力的退化。
筆者認為,對“意義”的追求,是人類所有學問的內在稟賦。意識流式的“碎片化”研究,對于破解某些故作高深的高頭講章不無微功,卻消解了史學的特征和使命,并將歷史研究化解為用美麗的腔調和輕曼的結構講細碎故事的技巧,有迷失在如汪洋大海、漫天雪花卻永遠只是“碎片”的史料之中的可能。“史學家如果不關注重大的歷史事件和基本的理論問題,以繁瑣考辨取代理論思維,以堆砌資料為博,以疊床架屋為精,拾芝麻以為珠璣,襲陳言而自詡多聞,以偏概全,見小遺大,歷史學就注定要喪失自己應有的精神境界。”時賢提出的各種角度診治“碎片化”的方案,在在均見對史學未來的關切。同時筆者想提出,要拒斥“碎片化”,須了解歷史的特性——人物、事件、整體的社會,在想象的“靜止”狀態中,必定處在一個三維“空間”結構中;但加上歷史的本質——“時間”維度后,它就成為“時—空”四維結構,這種結構賦予歷史整體性和延續性。“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時間以外的存在像空間以外的存在一樣,是非常荒謬的事情”,“運動是物質的存在方式”,也是歷史存在和演進的方式。布羅代爾揚言要將“歷史時間”與“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及“個人時間”區分開來,實際上,在人類產生并將整個世界對象化以后,所有的“時間”都不可分,且彌散、結合于人化自然和人類社會,是我們理解所有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歷史學家都是三維生物,但他們擁有值得驕傲和珍惜的技能,即理解四維“時—空”結構歷史的能力。視野、觀念、框架、模式、體系、理論等,廣義地、長時段地講,是歷史學家介入歷史的工具和方法。解讀、闡釋歷史的過程,就是歷史研究“意義”產生的過程,而且這些“意義”必須在歷史本身的整體性、延續性特征中才能得到理解,這就說明歷史研究在本質上是應當拒斥“碎片化”的。拒斥“碎片化”,須明了歷史學是“人”的學問,史學的中心,必定是人。人的歷史活動有三個方面的事實:其一,“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其二,“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其三,“每日都在重新生產自己生命的人們開始生產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而且,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人的“普遍交往”逐步發展起來,“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人的全球化,使得“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有了新的含義,決定全球史時代的歷史學,必須有普遍聯系的觀念。“碎片化”研究對此無能為力。“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的總要求,需要中國歷史學界作出回應。中國有5000年以上延綿不絕、不斷更新升級的文明史,構成人類史的宏大篇章;近代以來,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人更是在極短的時間里實現了多個層次螺旋遞進的發展跨越,其實踐和認知具有重大的世界歷史意義。這是中國歷史學家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基礎、機遇和鞭策。“碎片化”研究也許還未成氣候,卻應當終止了。
(作者系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號,原載《歷史研究》2019年第6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網】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現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絡時代發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