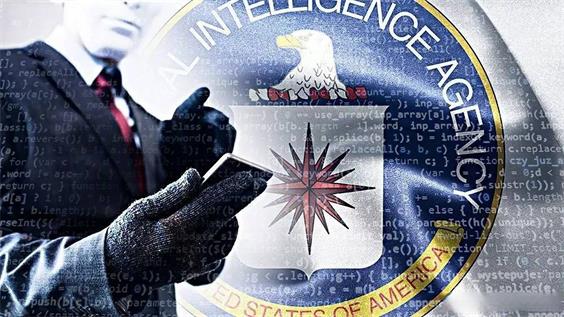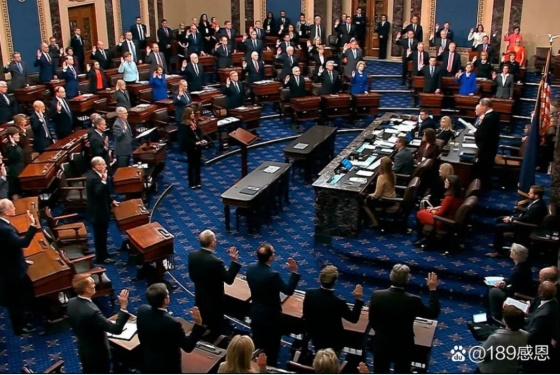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7日-星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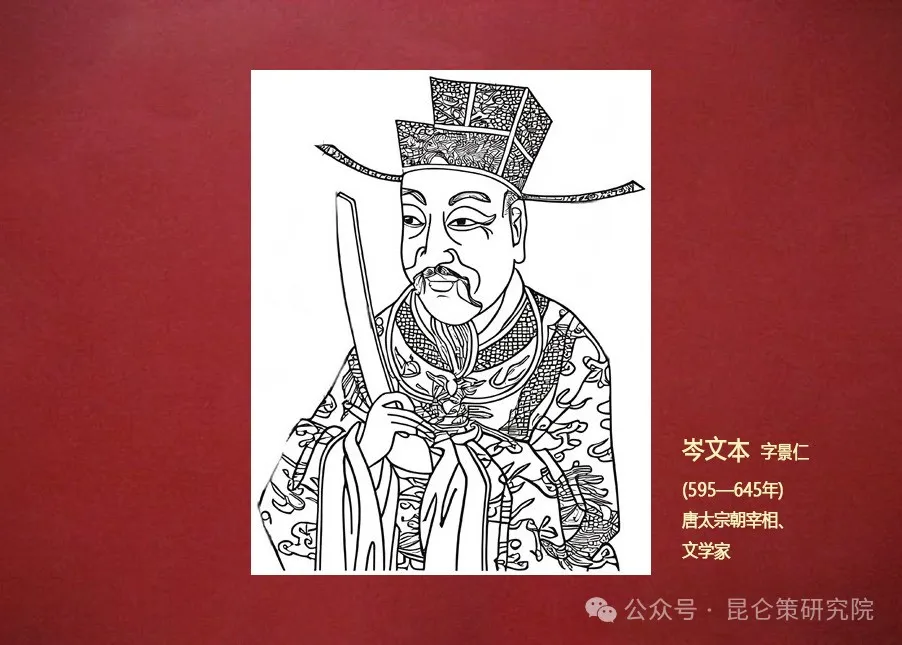
岑文本(595-645年),字景仁,鄧州棘陽縣(今河南省新野縣)人,唐太宗朝宰相、文學家。歷任秘書郎、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宰相等職。岑文本少年成名,“文傾江海,忠貫雪霜”,為官清正忠直,慎權節欲,榮升宰相,不喜反憂,以“憂懼宰相”名垂青史。
一、少年成名,勇闖官府為父昭雪
岑文本出生于一個世代官宦之家,成長于戰亂頻仍“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年代。其遠祖岑彭為東漢廷尉、征南大將軍,祖父岑善方為南朝西梁宣帝蕭詧朝吏部尚書,父親岑之象為隋末邯鄲縣令、虞部侍郎。“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博考經史,多所貫綜,美談論,善屬文。”[1]
岑文本少年成名。成名的緣由不只是他聰敏睿智,年紀輕輕便滿腹經綸,才華橫溢,寫得一手好文章,還因為他智勇兼備,14歲時便只身闖官府,為父親洗雪冤獄。
隋末,時任邯鄲縣令的父親遭人誣陷,身陷囹圄。岑文本無所畏懼,只身前往司隸府為父親鳴冤,大堂之上,面對冷顏怒目望之森森的滿堂官吏,岑文本從容不迫,侃然正色,辭情激昂懇切,并且“召對明辯,眾頗異之”。
主辦本案的官員見岑文本小小年紀,如此不同凡響,便想試試他的才氣,令其當堂作《蓮花賦》。岑文本握管在手,輕凝雙眉,“下筆立成,屬意甚佳,合臺莫不嘆賞。其父冤雪,由是知名。”[2]
雖然這篇《蓮花賦》早已化作歷史的煙塵,我們已無從觀賞其揚葩振藻,從當時滿堂官吏的“莫不嘆賞”,并且立即為其父平反昭雪,不難想象這篇文章的精美絕倫及其產生的征服人心的效應。
二、黑云壓城,勸唐將止殺棄擄掠
隋煬帝大業十四年(618年),蕭銑在荊州稱帝,依照梁朝舊例,設置百官,聘任岑文本為中書侍郎,主掌機密事務。其時,蕭銑的勢力范圍東至九江,西至三峽,南至交趾,北至漢水,地域廣袤,沃野千里,擁兵40萬,雄踞南方。
蕭銑是梁武帝蕭衍的六世孫,如今割據一方,面南稱帝,許多前朝舊將云集其門下,本可有一番作為。然而,這蕭銑卻是一個鼠肚雞腸的斗筲之徒,他表面上寬厚仁愛,內心卻氣量狹小,自負任氣,疑忌心極重,沒過多久,身邊大臣將領都大失所望,懷疑懼怕,人人自危,叛離事件不斷發生。蕭銑不能禁制,使得這個本來就先天不足的割據政權日漸走向衰弱。
岑文本明知蕭銑絕非帝王之才,也只能死馬當作活馬醫,竭誠盡臣子的本分,屢屢不避生死,直言切諫,無奈收效甚微。
武德四年(621年)九月,唐高祖李淵任命夔州總管、趙郡王李孝恭為荊湘道行軍總管,統率麾下水陸12支勁旅自巴蜀順流而下,擊破荊門、宜都,與黔州刺史田世康合兵,將江陵城圍了個水泄不通。
為避免城中百姓生靈涂炭,蕭銑在岑文本等大臣的勸諫下開城投降。
唐軍來勢兇猛,兵鋒正盛,將士耀武揚威,磨刀霍霍,急欲涌進城去大肆搶掠。“黑云壓城城欲摧”,江陵百姓籠罩在極度驚悸和恐懼之中!岑文本緊急求見李孝恭,勸諫他說:“自隋室無道,群雄鼎沸,四海延頸以望真主。今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降者,實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縱兵虜掠,誠非鄙州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以南,向化之心沮矣。”[3]
李孝恭聞言如夢初醒,額手稱慶,立即傳令三軍,嚴禁殺戮無辜,搶掠百姓,違者格殺勿論。于是唐軍秋毫無犯,江陵城百姓躲過了一場浩劫。南方各州縣聞訊,皆望風歸順。
岑文本歸唐后被任命為荊州別駕,后又任行臺考功郎中。
貞觀元年(627年),岑文本調任秘書郎,同時在中書省兼職。有一年春耕時節,太宗舉行藉田禮,親自耕田,以示重農,岑文本獻上《藉田頌》。新年之際,太宗在宮中大宴群臣,岑文本又獻上《三元頌》。兩篇文章都辭藻甚美,文采飛揚,使得岑文本才名大震。
尚書右仆射李靖十分欣賞岑文本的才華,將他推薦給太宗,不久,岑文本被擢升為中書舍人。中書舍人為天子親密近臣,掌管詔旨制敕、朝政機要,負責執掌詔誥、決策制命、決斷政務,此職歷來多為頗負盛名的文士擔任,故有“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之稱。
選擇岑文本任中書舍人可謂用得其人。據《舊唐書·岑文本列傳》,有一次,諸多政事擠到了一塊兒,需要同時起草多個詔令,岑文本成竹在胸,有條不紊,叫來六七個屬吏,命他們各自備好紙筆,他依次分別予以口授,娓娓道來,出口成章,一氣呵成,詔令草成復核,不易一字。
中書侍郎顏師古以名儒享譽當世,因事將被免職,宰相溫彥博向太宗為他求情說:“顏師古熟悉時事,文名蓋世,擅長草擬文誥,無人能及,誠望繼續留用。”太宗回答說:“朕自舉一人,絕不比他遜色,你大可不必為此事擔憂。”于是,任命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門掌管機要事務,封江陵縣子。
太宗嫡長子李承乾與四子李泰相繼被廢黜太子之位后,晉王李治于貞觀十七年(643年)被立為太子,東宮地位趨穩,不少名士都兼領東宮官職。太子一般是未來的皇帝,如果能在東宮兼職,不僅有利于自己將來的仕途發展,而且也能為子孫積累資本和人脈,朝臣們都十分期待但大都求之不得,只有少數寵臣能夠如愿。
太宗對岑文本非常寵信,主動提出請岑文本在東宮兼職,沒想到岑文本竟婉言謝絕。他直言不諱地上奏太宗說:“臣以庸才,久逾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時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愿更希東宮恩澤。”[4]
如此美差,別人搶都搶不到手,岑文本卻棄之如敝屣,太宗大感意外。看著岑文本那個誠惶誠恐的樣子,太宗也只好作罷,但依然要他每隔五日去東宮一次。每次覲見,太子李治都以賓友之禮待他。
貞觀十八年(644年),岑文本被擢升為中書令,位列宰相。
榮任宰相,位極人臣,亙古以來都是仕途中人的畢生夢想,是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然而,岑文本卻無論如何也高興不起來,終日愁眉緊鎖,郁郁不樂。母親見他陷入憂心忡忡的陰霾之中不能自拔,甚是心痛,問他個中原委,他回答說:“非勛非舊,濫荷寵榮,責重位高,所以憂懼。”[5] ——我既不是開國元勛,又不是先王舊臣,受此超級榮寵,如此位高權重,責任重大,兒子心里實在憂懼。
親朋好友紛紛前來登門祝賀,岑文本的回答更加驚世駭俗:“有什么好祝賀的!我只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賀!”當有人勸他趁這幾年官位顯要多置些產業時,岑文本揶揄道:“我本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當初的最高期望,不過是做個秘書郎或縣令而已。說實話,我并沒有立過什么汗馬功勞,僅僅因為擅長文墨而位至中書令,已是登峰造極。如今享受高官俸祿,時常惶懼不已,何必還去置辦什么產業?”
岑文本雖少年得志,23歲便被蕭銑聘為中書侍郎,主掌機密事務。入唐后仕途順遂,一路做到中書令,位極人臣,但卻始終保持著書生本色,保持著恭謹孝悌、儉約樸素的一貫生活作風。他貴為宰相,自奉儉約,居室低矮潮濕簡陋,室內連褥墊、帳幔之類的裝飾都沒有。太宗稱贊他“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6]
他特別孝敬老母,撫育弟侄竭誠盡責,以恭謹孝悌聞名遐邇。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篤愛至誠,平生的故人,即使是漂泊貧賤之輩,也一定以禮平等相待。
岑文本在中書令任上,弟弟岑文昭時任秘書郎,家中的一應事務都交給弟弟打理。岑文昭完全沒有哥哥的風范,每每與那些輕薄之徒廝混在一起,整出一些出丑冒泡兒的事來。有人把這事兒報告給太宗。太宗召來岑文本,對他說:“令弟過多交結,恐累卿名,朕將出之為外官,如何?”岑文本趕忙上奏說:“臣弟幼年喪父,甚得老母鐘愛惦念,不忍讓他連宿兩夜離開自己。若今外放,母必憂愁憔悴,倘若眼前看不見這個弟弟,恐不久也將沒有老母了。”
岑文本邊說邊垂淚啜泣。
太宗見狀,連忙安慰他,為他的孝心所感動,沒有把岑文昭調出京都,只傳命將他召來嚴加誡約,岑文昭也至此迷途知返。
岑文本身居要職,政務繁忙,日理萬機,依然手不釋卷,“博考經史,多所貫綜”。《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其文集60卷,可惜已散佚。《全唐文》錄存其文20篇,《全唐詩》錄存其詩4首。貞觀二年(628年),太宗降詔,命岑文本與令狐德芬撰寫《周史》,于貞觀十年(637年)撰成,《舊唐書·岑文本列傳》稱“其史論多出于文本”。
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親征遼東,命岑文本隨行,并且將此役所有的謀劃、籌措軍中輜重等重大事務都委托岑文本辦理。“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7] 不久病逝,享年51歲。追贈侍中、廣州都督,謚號為憲,陪葬昭陵。
古人云:“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規,行有所止。”一般人升官則欣喜,更有一些人升官則忘乎所以,則驕橫狂傲,則“迷一官而小天下”。岑文本面對升官,非但不喜,反以為憂,甚至榮升位極人臣的宰相,依舊心如止水,“只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賀”,宦海一生,清正廉明,生榮死哀,享譽千古。能不能樹立正確的權力觀,能不能出以公心正確地掌權用權,是為官從政者繞不開的永恒課題,在1300多年后的今天,岑文本這種心存敬畏、慎權遏欲的崇高境界,依然是我們學習和效仿的榜樣。
(作者系文史學者、原解放軍西安通信學院政教主任、教授,全軍優秀教師;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載“天津日報”)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國策建言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