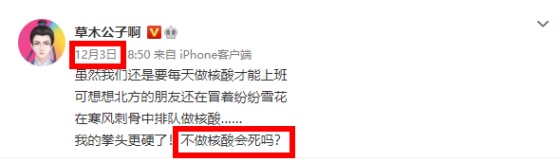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4日-星期日

自20世紀(jì)90年代中期中國(guó)就開(kāi)始從國(guó)家層面對(duì)科技創(chuàng)新戰(zhàn)略的重視和倡導(dǎo)。一直以來(lái),我們不缺從1-100的積累性、應(yīng)用型創(chuàng)新,缺的是0-1的原創(chuàng)性、基礎(chǔ)性、理論性的創(chuàng)新,或?qū)е乱坏┬纬赏庠诃h(huán)境的封閉和圍堵,其后果將難以預(yù)料。如果在科技創(chuàng)新上沒(méi)有重大的突破性進(jìn)展,單憑體量“虛胖”,很難在未來(lái)競(jìng)爭(zhēng)中立得住、站得穩(wěn)。
從清末開(kāi)始,我們學(xué)習(xí)“西學(xué)”特別是其中的科技知識(shí)。中華民族經(jīng)歷了長(zhǎng)期的學(xué)習(xí)和跟蹤,現(xiàn)在有條件進(jìn)入獨(dú)創(chuàng)階段。如何在宇宙、生命、意識(shí)本質(zhì)等醞釀革命性突破的問(wèn)題上,開(kāi)辟出新空間?如何在吸收人類科學(xué)與哲學(xué)優(yōu)秀成果基礎(chǔ)上,發(fā)揮我國(guó)傳統(tǒng)科學(xué)、哲學(xué)思想的獨(dú)特優(yōu)勢(shì)?這些問(wèn)題值得深入思考。
李約瑟肯定了中華有機(jī)形態(tài)的科學(xué)觀,認(rèn)為它對(duì)未來(lái)科學(xué)發(fā)展具有重大意義。西方與人文割裂的機(jī)械自然觀,難以兼顧生命自身的價(jià)值理性。而有機(jī)自然觀的核心,就是把生命作為中心點(diǎn),不違背人類乃至萬(wàn)物生發(fā)的規(guī)律,且以有機(jī)系統(tǒng)的立場(chǎng)看待宇宙,“萬(wàn)物并育而不相悖”,和和共生,共同沿著各自的“道”有序演化。
假設(shè)再過(guò)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當(dāng)后世人們反思我們今天引以為自豪的西方科學(xué)技術(shù)形態(tài)時(shí),或更能冷靜評(píng)價(jià)之:在創(chuàng)造巨大物質(zhì)文明的同時(shí),也創(chuàng)造出了毀滅這種文明的手段。看起來(lái)合乎理性發(fā)展的“科學(xué)”,其實(shí)犯了“方向性”引領(lǐng)的錯(cuò)誤。惜乎人類不僅把科學(xué)技術(shù)作為征服自然的工具,亦作為同類更大規(guī)模相互廝殺的武器。目前智能化科學(xué)技術(shù)、生物合成技術(shù)等應(yīng)用一旦無(wú)節(jié)制地展開(kāi),不確定性的命運(yùn)伴隨讓人覺(jué)得毛骨悚然。科學(xué)研究已經(jīng)踏入人文價(jià)值界域,不得不深入關(guān)切探索的前提與方向。1955年,獲得諾貝爾獎(jiǎng)的52位世界級(jí)科學(xué)家聯(lián)名發(fā)表《邁瑙宣言》,指出科學(xué)是通向人類幸福生活之路的同時(shí),也在向人類提供自殺手段。為何而創(chuàng)新?需不需要價(jià)值的內(nèi)在引領(lǐng)?
黨的二十大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cuò)誤,創(chuàng)新才能把握時(shí)代、引領(lǐng)時(shí)代。”“守正創(chuàng)新”在科技戰(zhàn)略規(guī)劃、科技重大創(chuàng)新等方面的意義同樣不可低估,“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讓科技更好增進(jìn)人類福祉”勢(shì)在必行。“守正”即深具價(jià)值規(guī)范、引導(dǎo)功能,符合科學(xué)人文化方向。西方近代以來(lái)的科學(xué)技術(shù),既創(chuàng)領(lǐng)了新的人文精神,也在更大程度上撕裂了與人文價(jià)值理性的關(guān)聯(lián):工具理性反對(duì)價(jià)值理性,成為脫韁的野馬而不能自控。“求真”占主導(dǎo)地位的西方理性傳統(tǒng),須用“求善”占主導(dǎo)地位的東方(尤其是中國(guó))價(jià)值傳統(tǒng)來(lái)校正,或可避免愈陷愈深的現(xiàn)代文明危機(jī)。開(kāi)展科學(xué)研究、技術(shù)開(kāi)發(fā)等科技活動(dòng)要遵循一定價(jià)值理念、行為規(guī)范。2020年我們成立了國(guó)家科技倫理委員會(huì),中共中央辦公廳、國(guó)務(wù)院辦公廳今年初還印發(fā)了《關(guān)于加強(qiáng)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jiàn)》,都在給科學(xué)注入價(jià)值,以使科學(xué)精神和道德理想結(jié)合、科學(xué)與人文精神相融。
我國(guó)古代“天人合一”觀念使人們?cè)谘芯俊⑻剿髯匀粫r(shí),顧及人的價(jià)值選擇,故“人文性”非常突出。確有對(duì)科技“有機(jī)械必有機(jī)心”的擔(dān)心,“奇技淫巧”的觀念亦不利科技的發(fā)展,但另一方面反映了對(duì)科技誤用的人文節(jié)制考量。“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人文本位思想的確定和不斷強(qiáng)化,對(duì)古代科技的一個(gè)顯著影響就是定向作用,即引導(dǎo)、制約和促成了古代科技朝著以服務(wù)人生為主要內(nèi)容的方向發(fā)展”。
李約瑟認(rèn)為,不應(yīng)把傳統(tǒng)的中國(guó)科學(xué)看作近代科學(xué)失敗的原型:雖然古代中國(guó)科學(xué)思想沒(méi)能產(chǎn)生來(lái)自西方的科學(xué)范式,但卻有可能為將來(lái)的新科學(xué)開(kāi)辟途徑。隨著現(xiàn)代人們對(duì)科學(xué)深入不斷的反思、對(duì)重新實(shí)現(xiàn)人文與科學(xué)平衡的不懈探索,科學(xué)發(fā)展新的模式正處于歷史建構(gòu)之中,道德與科學(xué)結(jié)合,以人文理性支配和引導(dǎo)科學(xué)理性,無(wú)疑將成為以后科學(xué)建構(gòu)的基本思路。重大科技創(chuàng)新應(yīng)該密切關(guān)注人類社會(huì)長(zhǎng)遠(yuǎn)的價(jià)值需求,盡力避免負(fù)面效應(yīng)的出現(xiàn),尤其在可以預(yù)知的發(fā)現(xiàn)、發(fā)明之初,不要打開(kāi)“潘多拉的魔盒”。西方近現(xiàn)代科學(xué)的發(fā)展歷史,讓人類充分見(jiàn)證了這個(gè)“魔盒”的威力。不關(guān)注價(jià)值方向的引領(lǐng),所謂創(chuàng)新愈多,或則危害愈深。影響乃至改變這種路徑依賴,“以善統(tǒng)真”的中華科技理念、中華人文思想大有可為。
馬克思從堅(jiān)持人與自然、社會(huì)、自我根本統(tǒng)一的信念出發(fā),強(qiáng)調(diào)“自然科學(xué)往后將包括關(guān)于人的科學(xué),正象關(guān)于人的科學(xué)包括自然科學(xué)一樣:這將是一門(mén)科學(xué)”。至于這是一門(mén)什么樣的科學(xué),馬克思沒(méi)有明確說(shuō)出——應(yīng)該是基于科學(xué)與人文的協(xié)調(diào)與統(tǒng)一,為綜合的、整體的大科學(xué)。近代科學(xué)應(yīng)用于技術(shù)生產(chǎn)的非人性化,表明它是和這個(gè)時(shí)期的制度階段相適應(yīng)的。而未來(lái)科學(xué)轉(zhuǎn)化應(yīng)用于技術(shù)生產(chǎn),要“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據(jù)自己本性的需要,來(lái)安排世界”。這一切最終是建立在既要認(rèn)識(shí)和利用“外部自然的規(guī)律”,還要認(rèn)識(shí)“支配人本身的肉體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規(guī)律”——涉及“意識(shí)本質(zhì)”乃至“生命起源”的整體科學(xué)基礎(chǔ)之上。因此,關(guān)聯(lián)制度的人文視野的擴(kuò)展,與科學(xué)方向的內(nèi)在定位相連,中華獨(dú)特的科技人文特征可發(fā)揮積極作用。
“中華民族是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民族”,“創(chuàng)新精神是中華民族最鮮明的稟賦”。指南針、火藥、印刷術(shù)等發(fā)明,預(yù)告了西方資產(chǎn)階級(jí)社會(huì)的到來(lái),變成了西方科學(xué)復(fù)興的手段,變成了對(duì)精神發(fā)展創(chuàng)造必要前提的最強(qiáng)大的杠桿。愛(ài)因斯坦驚奇于中國(guó)古代賢哲既缺乏西方科學(xué)中希臘哲學(xué)家發(fā)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又沒(méi)有通過(guò)系統(tǒng)實(shí)驗(yàn)發(fā)現(xiàn)因果關(guān)系的方法,卻在技術(shù)上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我們要問(wèn)的是,這些重大科技發(fā)明背后究竟是什么樣的創(chuàng)新思維在支配著?
實(shí)踐適用理性思維。“實(shí)用性”“實(shí)用理性”等觀點(diǎn),遍布學(xué)界對(duì)中國(guó)古代科技特征的論述之中,有學(xué)者甚至將之直接看作是“經(jīng)驗(yàn)實(shí)用型科學(xué)技術(shù)模式”“實(shí)用科技觀”。我主張以“適用”來(lái)替代之。因?yàn)?ldquo;實(shí)用”帶有強(qiáng)烈的功利化色彩,中性之“用”亦有可能將科技導(dǎo)向危害社會(huì)方面的歧途。鑒于我國(guó)古代科技強(qiáng)烈的人文傾向,以人文道理支配、控制科技之運(yùn)用,令其適于社會(huì)正當(dāng)之“用”,故稱之為“適用”更為恰切。
注重應(yīng)用,極大地提升了中國(guó)早期科技水平和能力(今天來(lái)看應(yīng)用仍是科技創(chuàng)新的主要?jiǎng)恿驮慈?wèn)題在于,過(guò)分注重科技的功利化運(yùn)用,導(dǎo)致抽象理論思維的不足(我國(guó)古代科技成果絕大部分集中在“技術(shù)”上),亦使處于經(jīng)驗(yàn)觀察階段的“實(shí)驗(yàn)”無(wú)法邏輯系統(tǒng)地貫通起來(lái),上升為基礎(chǔ)普遍性的數(shù)理規(guī)律,從而造成發(fā)展的后勁嚴(yán)重不足。當(dāng)然,這也與我國(guó)古代思維缺乏嚴(yán)密邏輯、公理化演繹有關(guān)。值得警醒的是,近現(xiàn)代以來(lái)我們學(xué)習(xí)西方科學(xué)以“救國(guó)”“興國(guó)”理念固然高大上,但有可能恰恰忽視了基礎(chǔ)研究“要遵循科學(xué)發(fā)現(xiàn)自身規(guī)律,以探索世界奧秘的好奇心來(lái)驅(qū)動(dòng)”、“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學(xué)家都是憑借執(zhí)著的好奇心、事業(yè)心,終身探索成就事業(yè)”等內(nèi)因。未來(lái)科技創(chuàng)新如何處理好“用”與“無(wú)用”(短期看似乎毫無(wú)功利可言)的關(guān)系,仍有很長(zhǎng)的路要走。
自然科學(xué)與實(shí)驗(yàn)、實(shí)證聯(lián)系在一起,故近代西方科學(xué)可稱之為實(shí)驗(yàn)科學(xué)、實(shí)證科學(xué)。但“實(shí)證”在中國(guó)文化里除了觀察和實(shí)驗(yàn),還有另外一層內(nèi)涵。比如,高攀龍言“此中境界無(wú)窮,階級(jí)無(wú)窮,非實(shí)修實(shí)證者”不能了解這一心性修為過(guò)程,這里的“實(shí)證”是一種內(nèi)向的實(shí)踐方法(不完全等同于倫理道德實(shí)踐),就是通過(guò)認(rèn)識(shí)、強(qiáng)化、更新自身生命歷程,從而認(rèn)識(shí)、改造人和自然的關(guān)系、大自然屬性的方法。它和注重改造外在客觀世界的西方觀念迥異,也與馬克思主義積極向外拓展的世界觀、方法論不同,是“求諸己”的過(guò)程和方法。將來(lái)科學(xué)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未嘗不可把內(nèi)外向?qū)嵺`方法結(jié)合起來(lái),如歐文·拉茲洛提出的廣義進(jìn)化論指出的:要努力通過(guò)改變?nèi)祟惖膬?nèi)在限度,為未來(lái)人類進(jìn)化指明道路。
直覺(jué)靈感整體思維。普遍性理論的重大創(chuàng)新往往表現(xiàn)為“邏輯的中斷”,直覺(jué)等非邏輯因素在思維發(fā)生躍遷和質(zhì)變中似乎更具有決定性。“我信任直覺(jué)”,愛(ài)因斯坦這句名言為人熟知,但他無(wú)法以邏輯語(yǔ)言一一揭示“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特征”。發(fā)明大師愛(ài)迪生也有句名言:“天才就是1%的靈感加上99%的汗水”,我們往往忽略了其后半句的轉(zhuǎn)承:“但那1%的靈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重要”。我理解,99%基本上是邏輯積累,真正的突破或者說(shuō)質(zhì)變,來(lái)自1%靈感的飛升。
對(duì)直覺(jué)作為一種知識(shí)、一種認(rèn)識(shí)能力、一種認(rèn)知過(guò)程,可以洞察自明的普遍真理的申明幾乎貫穿整個(gè)西方科學(xué)和哲學(xué)史。不過(guò),許多西方科學(xué)家、哲學(xué)家無(wú)法揭示直覺(jué)尤其是靈感的發(fā)生機(jī)理,而將其歸結(jié)為上帝的神秘啟示。倒是我國(guó)古代《管子·內(nèi)業(yè)》對(duì)此較早作了無(wú)神論的解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可見(jiàn),管仲認(rèn)為直覺(jué)并不是神鬼的作用,實(shí)際乃人的精神功能高度整合的結(jié)果。與古希臘人發(fā)明公理體系作為直覺(jué)運(yùn)用的經(jīng)典例子一樣,古代中國(guó)科學(xué)技術(shù)活動(dòng)包含著大量基于觀察經(jīng)驗(yàn)的直覺(jué)思維的運(yùn)用。西方強(qiáng)調(diào)的直覺(jué),多賴分析的方法,而我們則與事物的整體性關(guān)聯(lián)。直覺(jué)知識(shí)和方法論甚至在宗教或藝術(shù)哲學(xué)中推到了最高峰,比如道家的“玄覽”、禪宗的“頓悟”、山水畫(huà)的“意境”。此外,這種方法的開(kāi)拓與掌控,還與精神方面的內(nèi)修相關(guān)。如《荀子·勸學(xué)》中指出的,“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積累點(diǎn)滴善行,慢慢成美德,人的睿智就自然獲得,如圣人般心靈(慧眼)就具備了。《管子·內(nèi)業(yè)》中說(shuō),“德成而智出,萬(wàn)物果得”,一個(gè)人的大善心、大胸懷、大境界修成了,他的創(chuàng)新性智慧就自然流露出來(lái)了,萬(wàn)事萬(wàn)物的規(guī)律、道理即顯現(xiàn)于其精神世界而處理得宜。
20世紀(jì)以來(lái),隨著腦科學(xué)的進(jìn)展,人們對(duì)大腦分工有了一定程度的認(rèn)知。關(guān)于智力的創(chuàng)造性開(kāi)發(fā),提出了“右腦工程”之說(shuō)。諾貝爾獎(jiǎng)獲得者美國(guó)科學(xué)家斯佩里認(rèn)為,右腦記憶量是左腦100萬(wàn)倍。《腦內(nèi)革命》一書(shū)的作者日本春山茂雄認(rèn)為:右腦是祖先腦,儲(chǔ)存了人類500百萬(wàn)年進(jìn)化過(guò)程中所積累的智慧,賦予人以直覺(jué)、靈感、頓悟、創(chuàng)意等,信息量更高,為左腦十萬(wàn)百萬(wàn)乃至千萬(wàn)倍以上。研究表明,即便如愛(ài)因斯坦的大腦,一生開(kāi)發(fā)的潛力也只占到7-9%,一般人僅有3-5%。就是說(shuō),人的大腦90%以上沒(méi)有得到開(kāi)發(fā)利用。愛(ài)因斯坦在“關(guān)于數(shù)學(xué)領(lǐng)域的創(chuàng)造心理”這封給J.阿達(dá)馬的信中指出:“我以為你所講的完全意識(shí)是一種永不能完全達(dá)到的極限。我以為這同那種被稱為意識(shí)的狹隘性有關(guān)。”可以設(shè)想,如果能夠通過(guò)特定的方法,可以克服“意識(shí)的狹隘性”,開(kāi)發(fā)20-30%甚至70-80%的大腦潛力,或許我們與世界的相互作用方式完全改觀。人類將打開(kāi)直覺(jué)和靈感的神秘大門(mén),真正創(chuàng)新的涌流不是不可能的。古代中國(guó)探索了一條由知內(nèi)達(dá)外的思維途徑,或能給我們諸多啟迪。比如儒家經(jīng)典《大學(xué)》中有這樣的話語(yǔ):“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修養(yǎng)認(rèn)知主體本身,決定著能夠獲得客體真知的層次、深度和廣度。又如《荀子·解蔽》說(shuō)“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通過(guò)解除主體自身的障蔽,獲得對(duì)事物完全客觀的認(rèn)知。主客合一,在改造主觀世界的過(guò)程中改造客觀世界,德性控制理性,人文與科技的高度統(tǒng)一性就有了現(xiàn)實(shí)的根基。
20世紀(jì)以來(lái)大規(guī)模引進(jìn)和學(xué)習(xí)西方科學(xué)技術(shù),彌補(bǔ)了中國(guó)人邏輯思維的短板,但是科學(xué)發(fā)現(xiàn)、技術(shù)發(fā)明的特殊方法,像西方文化中同樣重視的直覺(jué)和靈感等創(chuàng)造性思維(屬于非理性內(nèi)在體驗(yàn)過(guò)程)則無(wú)法復(fù)制。不能學(xué)了別人的長(zhǎng)處,把自己的優(yōu)勢(shì)丟掉了。需要指出的是,歷史上運(yùn)用這些特殊方法我們往往更多體現(xiàn)在人文藝術(shù)、個(gè)人修養(yǎng)、宗教文化領(lǐng)域,如果能夠總結(jié)其中的經(jīng)驗(yàn)?zāi)酥烈?guī)律,將之廣泛推展應(yīng)用于今日科技創(chuàng)新,或能大大提升人才創(chuàng)新性思維的開(kāi)發(fā)。“在基礎(chǔ)研究領(lǐng)域,包括一些應(yīng)用科技領(lǐng)域,要尊重科學(xué)研究靈感瞬間性、方式隨意性、路徑不確定性的特點(diǎn)”。世人一般將“全知全能”賦予上帝和神明,但馬克思說(shuō),“我們要把宗教奪去的內(nèi)容——人的內(nèi)容,不是什么神的內(nèi)容——歸還給人,所謂歸還就是喚起他的自覺(jué)”,只要喚起人的自覺(jué),開(kāi)發(fā)出人固有創(chuàng)造潛力,靈感甚至能自覺(jué)運(yùn)用,人就有可能內(nèi)在地具有象“神”一樣的本領(lǐng)(當(dāng)代智能化實(shí)踐已經(jīng)外化實(shí)現(xiàn)了很多這方面的能力)。
類比類推意象思維。類概念是邏輯學(xué)賴以產(chǎn)生和建立的根基。它以事物或現(xiàn)象間屬性異同為依據(jù),發(fā)展到兩類事物間的比較、同類事物間的推理。有學(xué)者指出,“由于類比思維的濫用,造成中國(guó)科技史上比附大行其道,確實(shí)阻礙了中國(guó)古代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蛻變”。但另一方面我們則應(yīng)看到,中國(guó)古代推類方法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思維特點(diǎn)。將某個(gè)研究對(duì)象同已知事物的屬性進(jìn)行對(duì)比來(lái)推出結(jié)論,容易使人產(chǎn)生聯(lián)想,由已知事物推移到未知事物上,擴(kuò)大了認(rèn)識(shí)范圍。在對(duì)比中啟發(fā)、爆發(fā)思想火花或靈感,產(chǎn)生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通過(guò)類比推理,不僅使思想、進(jìn)行說(shuō)服教育具有形象性、生動(dòng)性,在仿生學(xué)領(lǐng)域曾做出了許多重大的科學(xué)發(fā)明。
取象比類,又稱援物比類,是古代中國(guó)科技研究方法中比較重要的一種方式,在天文、醫(yī)藥、農(nóng)學(xué)、化學(xué)、工程技術(shù)等領(lǐng)域有著廣泛運(yùn)用。所謂“取象”,乃指從事物的形象(包括屬性、形態(tài)、功能、系統(tǒng)等)中找到能反映本質(zhì)的特有征象,比類則是通過(guò)類比、類推的方法,探索已知之象與未知之象存在的共性,進(jìn)而找到相關(guān)事物的特性。這一科學(xué)方法輔有形象、直觀、感性的圖像、符號(hào)以及數(shù)字等象數(shù)工具揭示客觀事物規(guī)律,通過(guò)象征、類比等途徑把握世界聯(lián)系。我們之所以“長(zhǎng)期在科學(xué)技術(shù)方面有發(fā)明創(chuàng)造性,并且成就舉世無(wú)雙,這在相當(dāng)程度上都和類比思維之擅長(zhǎng)和保持相當(dāng)大的活力有關(guān),這種擅長(zhǎng)與活力,不僅是想象力的源泉,而且也是中華民族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源泉”。有學(xué)者進(jìn)一步認(rèn)為,“以物象之‘象’為中心,以時(shí)間流變的整體把握為主要特征,以‘取象比類’為基本的邏輯推演模式的意象思維,是中國(guó)古代科技曾在相當(dāng)長(zhǎng)的一個(gè)時(shí)間里取得領(lǐng)先地位的主要原因,也正是這種思維方式?jīng)Q定了中國(guó)近代不可能產(chǎn)生類似于西方的科學(xué)革命”。
把一切都習(xí)慣于比類陰陽(yáng)五行及其變化關(guān)系,制約了中國(guó)古代科學(xué)技術(shù)的深度發(fā)展。象征性思維的意會(huì)性、模糊性妨礙了向高度思辨階段演化,其結(jié)論的或然性更是遭到現(xiàn)代很多邏輯研究者的批評(píng)。但這并不是說(shuō),類比推理或推類邏輯在近代科學(xué)產(chǎn)生以后就失去效用。恩格斯即肯定了辯證法的這種功能:它“為一個(gè)研究領(lǐng)域向另一個(gè)研究領(lǐng)域過(guò)渡提供類比,從而提供說(shuō)明方法”。2016年11月9日,在《中國(guó)古代科技文化及其現(xiàn)代啟示》出版座談會(huì)上,中國(guó)科學(xué)院自然科學(xué)史研究所研究員董光璧指出,以歸納法和演繹法為支柱的邏輯體系只包含了從特殊到普遍和從普遍到特殊的推理,需要補(bǔ)充從特殊到特殊和從普遍到普遍的推理,中國(guó)傳統(tǒng)科學(xué)所普遍使用的類比推理和互補(bǔ)推理恰好能彌補(bǔ)形式邏輯的這種缺失。
類比中的意象思維本身包含著大量的形象元素。即使在高層次的理性思維中,也會(huì)時(shí)斷時(shí)續(xù)、多多少少地借助于或者不脫離形象。日本理論物理學(xué)家湯川秀樹(shù)認(rèn)為,在任何富有成效的科學(xué)思維中,不僅某種東西必須從我們豐富的、但多少有點(diǎn)模糊的直覺(jué)圖像中抽象出來(lái),且被當(dāng)作人類抽象能力的成果而建立的某種概念到最后也往往變成了我們直覺(jué)圖像的一部分;從這種新建立起來(lái)的直覺(jué)中,人們可以繼續(xù)作出進(jìn)一步的抽象。與形象思維的具體“形象”展示略有不同,它指的是具有某種程度抽象的、模式化了的“形象”,可稱之為“智力圖像”。這一切可概括為“想象力”。有調(diào)查顯示,我國(guó)教育培養(yǎng)的孩子在國(guó)際比賽中顯示了驚人的計(jì)算能力,而想象力、創(chuàng)造力的排名卻比較靠后。如何汲取并借鑒我國(guó)傳統(tǒng)的“意象”思維,強(qiáng)化想象力在科技創(chuàng)造中的作用,是一個(gè)值得進(jìn)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縱觀科技史上兩次大的科學(xué)革命以及之后產(chǎn)生的技術(shù)革新,一個(gè)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涉及物質(zhì)、能量、時(shí)間、空間等基礎(chǔ)概念的變化,進(jìn)而帶來(lái)人類哲學(xué)觀的進(jìn)步、科技層次的飛躍。“一切真正原創(chuàng)的知識(shí),都需要沖破現(xiàn)有的知識(shí)體系”,為世界貢獻(xiàn)了無(wú)數(shù)科技創(chuàng)新成果的5000多年中華文明,究竟還有多少能夠啟發(fā)“人類新文明”的元素?
關(guān)于物質(zhì)層次的新假說(shuō)。這里所說(shuō)的“層次”不是一個(gè)序列下的系統(tǒng)分層,而是基本物質(zhì)的種類劃分。在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物質(zhì)、能量、信息中,科學(xué)對(duì)有質(zhì)量的物質(zhì)以及無(wú)質(zhì)量的能量研究比較透徹,但對(duì)信息的看法存在著巨大分歧。控制論創(chuàng)始人維納曾說(shuō):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質(zhì)也不是能量;在今天不承認(rèn)這一點(diǎn),唯物論就不能存在下去。說(shuō)明信息是與物質(zhì)、能量相并列的一種全新實(shí)在。物理學(xué)家惠勒甚至提出,現(xiàn)實(shí)性的基礎(chǔ)可能并不是量子,而是比特(bit),以致可以說(shuō)是信息。我國(guó)學(xué)者創(chuàng)造性地作出了三層物質(zhì)理論假說(shuō)——一是具備理、化特征的實(shí)體物質(zhì)層面,指原子以上至宏觀實(shí)體物質(zhì)直至人,以質(zhì)量為存在形式,能量、信息寓于質(zhì)量之中;二是以能量為存在形式,質(zhì)量(處于隱微狀態(tài))、信息寓于能量之中,如電磁場(chǎng)與引力場(chǎng);三是時(shí)空結(jié)構(gòu)信息混融在一體的整體狀態(tài),質(zhì)量、能量均處于隱伏狀態(tài)。且三層物質(zhì)之間可以相互轉(zhuǎn)化。
與西方強(qiáng)調(diào)“信息”橫斷面的空間結(jié)構(gòu)分布屬性不同的是,我國(guó)學(xué)者發(fā)展了對(duì)信息作為時(shí)間延續(xù)屬性的功能性認(rèn)知,將“時(shí)空結(jié)構(gòu)信息混融在一體的整體狀態(tài)”作為第三層物質(zhì)的根本內(nèi)涵,并把它與中國(guó)古代科技公認(rèn)的“氣論”基礎(chǔ)結(jié)合起來(lái)。在我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氣”不僅是一個(gè)重要的哲學(xué)范疇,而且有真實(shí)的客觀存在性。思想家們認(rèn)為,氣是宇宙天地萬(wàn)物之原,人賴之以生、物賴之以成,無(wú)論是儒、道、醫(yī)、兵、法、農(nóng)等各家,還是文學(xué)、藝術(shù)、技藝等領(lǐng)域,無(wú)不烙下“氣”學(xué)的印記。古人對(duì)氣的作用做了方方面面非常深刻的論述,但對(duì)氣的實(shí)質(zhì)沒(méi)能做出精確的闡釋,致使現(xiàn)代人究詰“氣”是什么?可否為真實(shí)存在?中國(guó)哲學(xué)史學(xué)家張岱年先生認(rèn)為,“氣”可以說(shuō)是最細(xì)微流動(dòng)的物質(zhì);氣與近代物理學(xué)所謂的場(chǎng)有近似之處;水火草木各類動(dòng)物都屬氣,氣指有廣袤能運(yùn)動(dòng)的存在;一切物的構(gòu)成材料,則謂之氣,氣是萬(wàn)物本原;氣是中國(guó)哲學(xué)中的物質(zhì)概念。關(guān)于第三層物質(zhì)(信息或氣)向第二層物質(zhì)(能)、第一層物質(zhì)(質(zhì))的轉(zhuǎn)化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實(shí)驗(yàn),比如第三層物質(zhì)的“生磁”“生能”以及打破量子分布統(tǒng)計(jì)的實(shí)驗(yàn),還有向農(nóng)業(yè)延伸的對(duì)比實(shí)驗(yàn)(均屬于“第三層物質(zhì)”的存在性驗(yàn)證,且有向生產(chǎn)力轉(zhuǎn)化之趨向)。“科學(xué)發(fā)現(xiàn)是有關(guān)規(guī)律的,要容忍在科學(xué)問(wèn)題上的‘異端邪說(shuō)’”,從學(xué)術(shù)探討出發(fā),我們應(yīng)大力促進(jìn)這些基于中華科技理念又結(jié)合現(xiàn)代科技作出的假說(shuō)驗(yàn)證。
關(guān)于意識(shí)本質(zhì)的研究。西方哲學(xué)、科學(xué)一直采取對(duì)意識(shí)從外向內(nèi)的研究途徑(體現(xiàn)在腦科學(xué)的進(jìn)展中),這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一般來(lái)說(shuō),從方法論的角度看,認(rèn)識(shí)一個(gè)事物,我們用來(lái)測(cè)量的工具尺度要精確于被量度的對(duì)象才能有效。人的大腦作為宇宙間最為高端復(fù)雜的物質(zhì),即使最先進(jìn)的技術(shù)手段也很難弄清其機(jī)理功能。廣義進(jìn)化論分析了現(xiàn)代科學(xué)研究意識(shí)的方法論誤區(qū),認(rèn)為要揭示意識(shí)本質(zhì),我們面臨著人類科學(xué)認(rèn)識(shí)史上的一次偉大變革,它提出了“意識(shí)轉(zhuǎn)換狀態(tài)”“變更的意識(shí)狀態(tài)”“意識(shí)的非常狀態(tài)”乃更根本的方法(實(shí)際上是一種超越常態(tài)意識(shí)的“超意識(shí)”)。它特別推崇東方古老的“體驗(yàn)”和“反省”方法,我們可以進(jìn)一步將之概括為中華文化反求諸己的“內(nèi)向性”運(yùn)用意識(shí)的方法論,這與現(xiàn)代科學(xué)成熟的外求法既相互對(duì)立又相互補(bǔ)充。
研究信息這種實(shí)在,有助于我們進(jìn)一步弄清思想和大腦、精神和物質(zhì)的相互關(guān)系。上面提到的以信息為核心的第三層物質(zhì)假說(shuō)還關(guān)聯(lián)著對(duì)意識(shí)物質(zhì)性及對(duì)之開(kāi)展研究的可能性。由于哲學(xué)上我們很難確認(rèn)意識(shí)的物質(zhì)性,對(duì)之展開(kāi)實(shí)質(zhì)的研究遭遇到極大困難。意識(shí)成為意識(shí)研究的客觀對(duì)象,意識(shí)成為不依賴于意識(shí)的客觀存在,這是具體科學(xué)研究的根本前提。這和物質(zhì)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及物質(zhì)決定精神的原理并不矛盾。辯證唯物主義大師們對(duì)有關(guān)這一哲學(xué)核心問(wèn)題留下了許多原則性論述,認(rèn)為意識(shí)除了是物質(zhì)的一種“屬性”“機(jī)能”“內(nèi)部狀態(tài)”,還是最高的“產(chǎn)物”。毛澤東早在1943年就特地明確指出,“精神是一種特殊的物質(zhì)”。因此,需要建立“一種全新的實(shí)在模式,它把意識(shí)作為一種基本的實(shí)在包括在其中,要像時(shí)間、空間和物質(zhì)那樣基本,也許比它們更基本”。現(xiàn)代科學(xué)以實(shí)證方式肯定了精神現(xiàn)象作為一種相對(duì)獨(dú)立存在的事實(shí)。承認(rèn)腦和精神的相互作用,是當(dāng)代腦科學(xué)共同的研究綱領(lǐng)。
問(wèn)題在于,我們要另辟蹊徑,發(fā)揮自己文化蘊(yùn)含的特殊方法論優(yōu)勢(shì)。張岱年先生同樣指出,唯物論以為氣是最根本的;氣是無(wú)生命、無(wú)意識(shí),而為生命和意識(shí)的基礎(chǔ);所謂氣,泛指一切狀態(tài),物質(zhì)狀態(tài)是氣,精神狀態(tài)也是氣。他從哲學(xué)層面闡述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的氣與精神(心、意識(shí))的物質(zhì)屬性。“氣學(xué)”作為中醫(yī)學(xué)理論基礎(chǔ)和方法,與人之“神”有深刻的互動(dòng)影響。這一點(diǎn)根本無(wú)法融進(jìn)現(xiàn)代西方科學(xué)體系,當(dāng)把基于某種形態(tài)的科學(xué)技術(shù)作為唯一判斷標(biāo)準(zhǔn)時(shí),很有可能就將中醫(yī)藥學(xué)看成是“唯象科學(xué)”“前科學(xué)”,甚至被有些人污為“偽科學(xué)”。具有千百年實(shí)踐的驗(yàn)證,有不斷發(fā)展的理論體系,就是“科學(xué)”;謂之“古代科學(xué)”,并不否定它的現(xiàn)實(shí)作用。中醫(yī)藥學(xué)屬于中國(guó)獨(dú)特的科學(xué)技術(shù),從今天來(lái)看,乃具原創(chuàng)優(yōu)勢(shì)的科技資源;堅(jiān)持中醫(yī)藥原創(chuàng)思維,才能推動(dòng)其發(fā)展,而代替、否定只能阻滯其作用的發(fā)揮。“中醫(yī)藥學(xué)是中國(guó)古代科學(xué)的瑰寶,也是打開(kāi)中華文明寶庫(kù)的鑰匙”。不掌握中醫(yī)藥學(xué)文化這把“鑰匙”,不在新的層面認(rèn)識(shí)和理解生命,就無(wú)法真正打開(kāi)中華文明寶庫(kù)。運(yùn)用多學(xué)科方法開(kāi)展心藏神、氣的防御作用等中醫(yī)認(rèn)識(shí)人體、認(rèn)識(shí)生命現(xiàn)象的原創(chuàng)理論研究非常必要。超越養(yǎng)生和醫(yī)療并逐漸形成的中醫(yī)哲學(xué)、中華哲學(xué)理念,對(duì)推動(dòng)社會(huì)的整體進(jìn)步、科技的重大突破,意義不可小覷。
那么,中醫(yī)藥學(xué)究竟屬于什么樣的科學(xué)技術(shù)呢?“十三五”中醫(yī)藥科技創(chuàng)新專項(xiàng)規(guī)劃指出,它蘊(yùn)含著深厚的科學(xué)內(nèi)涵,具有引領(lǐng)生命科學(xué)未來(lái)發(fā)展的巨大潛力。“基礎(chǔ)研究是整個(gè)科學(xué)體系的源頭,是所有技術(shù)問(wèn)題的總機(jī)關(guān)”。對(duì)“氣”的奧秘的根本揭示,關(guān)聯(lián)著對(duì)“意識(shí)本質(zhì)”認(rèn)知的深入推進(jìn),關(guān)聯(lián)著新的物質(zhì)層次的假說(shuō)建立,關(guān)聯(lián)著新的時(shí)空觀的革新。人文本位傳統(tǒng)對(duì)中國(guó)古代科技發(fā)展有著特殊影響,造成了中國(guó)古代科學(xué)所特有的以人的生命和身心性命修養(yǎng)為研究重心的科學(xué)傳統(tǒng)。李約瑟把中華科學(xué)技術(shù)反映的世界觀稱之為“有機(jī)的自然觀”,盡管這一表述有相對(duì)西方“機(jī)械自然觀”的語(yǔ)境,但客觀上透露出,“有機(jī)的”中國(guó)古代的科學(xué)技術(shù),是關(guān)照生命的、不危害生命的科學(xué)技術(shù),形成的是系統(tǒng)整體的人文與生命科學(xué)相融的知識(shí)體系。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有大量身心健康養(yǎng)生的內(nèi)容,可能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中醫(yī)”的范圍,如果結(jié)合這些基礎(chǔ)性觀念,在現(xiàn)代科學(xué)基礎(chǔ)上加以挖掘、創(chuàng)新,帶來(lái)的將是如馬克思所說(shuō)的“人的科學(xué)”文明的提升。
(作者系天津大學(xué)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市習(xí)近平新時(shí)代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曾任中國(guó)實(shí)學(xué)研究會(huì)秘書(shū)長(zhǎng)、常務(wù)副會(huì)長(zhǎng),國(guó)際儒聯(lián)普及委員會(huì)副主任;來(lái)源:昆侖策網(wǎng)【作者授權(quán)】,原刊于《人民論壇·學(xué)術(shù)前沿》2022年10月下)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qǐng)看《昆侖策網(wǎng)》,網(wǎng)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gè)人觀點(diǎn),不代表本站觀點(diǎn),僅供大家學(xué)習(xí)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yíng)利性網(wǎng)站,如涉及版權(quán)和名譽(yù)問(wèn)題,請(qǐng)及時(shí)與本站聯(lián)系,我們將及時(shí)做相應(yīng)處理;
3、歡迎各位網(wǎng)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wǎng),依法守規(guī),IP可查。
內(nèi)容 相關(guān)信息
黨的二十大報(bào)告首次將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戰(zhàn)略擺在一起 官方解釋深意
2022-10-25答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qiáng)“時(shí)代考題”——院士專家熱議黨的二十大報(bào)告
2022-10-19?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wù) 新前景 ?

? 國(guó)策建言 ?

? 國(guó)資國(guó)企改革 ?

? 雄安新區(qū)建設(shè) ?

? 黨要管黨 從嚴(yán)治黨 ?

 收網(wǎng)開(kāi)始,勝利不遠(yuǎn)了
收網(wǎng)開(kāi)始,勝利不遠(yuǎn)了 沉痛哀悼!中組部原部長(zhǎng)張全景同志逝世
沉痛哀悼!中組部原部長(zhǎng)張全景同志逝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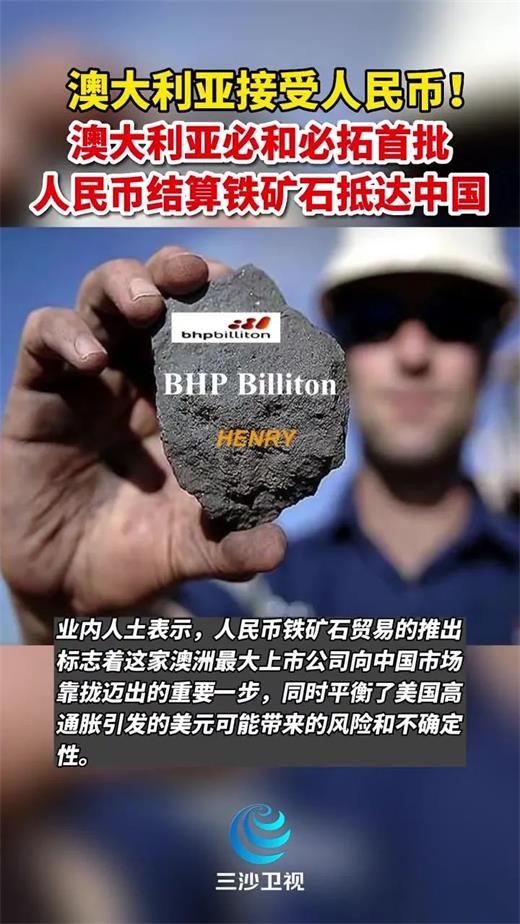 鐵礦石商全部投共,天地改換!
鐵礦石商全部投共,天地改換!
 明叔雜談:防疫共識(shí)被撕裂,警惕巨大潛在風(fēng)險(xiǎn)
明叔雜談:防疫共識(shí)被撕裂,警惕巨大潛在風(fēng)險(xiǎn) 李殿仁:向自身尋求“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答案
李殿仁:向自身尋求“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答案 習(xí)五一:互聯(lián)網(wǎng)管理規(guī)則應(yīng)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
習(xí)五一:互聯(lián)網(wǎng)管理規(guī)則應(yīng)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 社會(huì)調(diào)查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