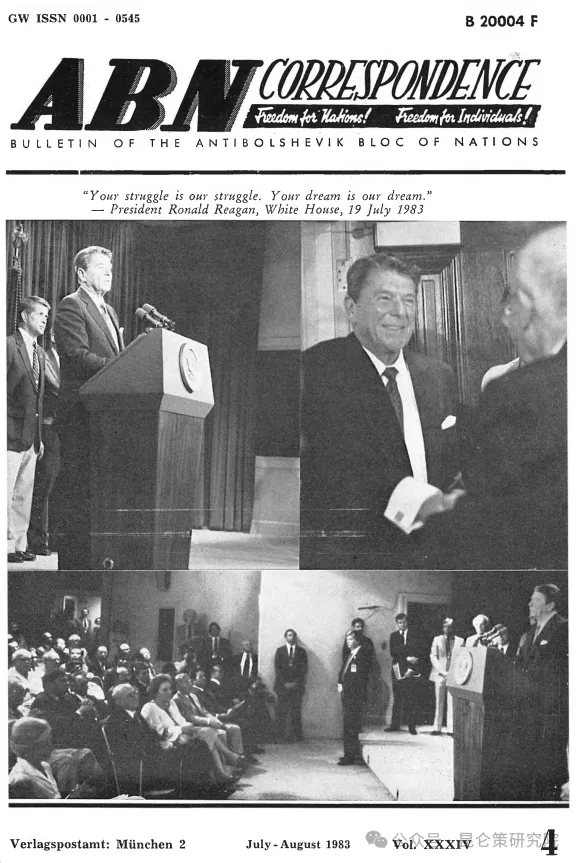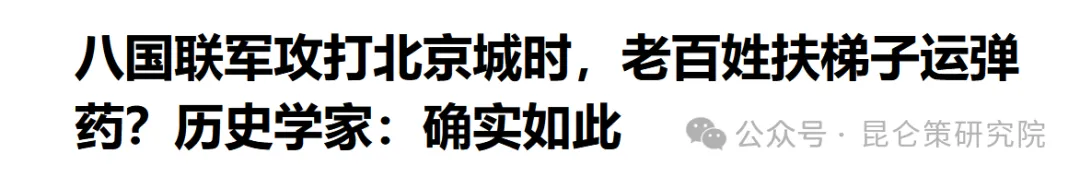此時此刻的世界,戰火燃燒,輿論同樣也在陷入激戰,孰正孰邪孰是孰非,各執一詞。例如,國際刑事法院5月20日就以色列總理及國防部長涉嫌戰爭罪申請逮捕令,以色列有高級官員宣稱,“把一個決心保衛本國不受恐怖襲擊的、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同一個嗜血恐怖組織的領導人相提并論,是對正義的嚴重歪曲和公然的道德敗壞。”抗辯邏輯令人咋舌,但在以色列支持者眼里甚是正確。巧了,前幾天發布的《中俄聯合聲明》有個很重要的一條,叫做“共同弘揚正確的二戰史觀”:“雙方將繼續堅定捍衛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以及載入《聯合國憲章》的戰后世界秩序,反對否定、歪曲和篡改二戰歷史。雙方指出,必須進行正確的歷史觀教育,保護好世界反法西斯紀念設施,保護其免遭褻瀆或破壞,嚴厲譴責美化甚至妄圖復活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行徑。雙方計劃于2025年隆重慶祝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蘇聯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共同弘揚正確的二戰史觀。”
為什么在當今世界,我們仍然需要回顧幾十年前的二戰,并且要進行正確的歷史觀教育?我們當今世界的基本框架仍然來自于二戰勝利的成果,而我們當下所面對的問題,其中很大一部分,也都來自于二戰期間的遺留問題,特別是對納粹及其意識形態的清算,未得到解決。學習和理解二戰歷史,培養正確的史觀,除了記錄和紀念之外,也在于正確理解當下發生的一切。錯誤的二戰史觀會帶來什么?我們可以從一個最近的例子說起,那就是烏克蘭的納粹問題。在俄烏沖突中,“去納粹化”是2022沖突爆發的一個原因。但是俄烏沖突不是從2022年開始的,烏克蘭的納粹問題也不是普京無中生有編出來的,而這一從時間和空間上看似與我們中國相距甚遠的問題,其實也是有著密切聯系的。實際上早在2021年,我就在觀察者網上發過一篇相關文章《這篇“反華宣言”,跟百年前的一群烏克蘭納粹流亡者有關》。在蘇聯成立之后,一群烏克蘭極端民族主義者一直在蘇聯和波蘭進行著恐怖主義活動,意圖建立由自身主導的烏克蘭國。這些人的首腦,就是班德拉——一個在2022年之后被頻繁提起的名字。而在二戰爆發之后,這些極端分子與納粹德國合作,在東歐幫助納粹德國建立傀儡政權,屠殺各地民眾,鎮壓反抗勢力——比如著名的沃倫大屠殺,就是他們的手筆。

【1943年烏克蘭納粹分子在波蘭進行的屠殺】
在納粹德國戰敗之后,這些烏克蘭納粹分子本來應該被徹底清算的,但由于冷戰開始,西方各國把反共擺到了比反法西斯更重要的地位,于是納粹余孽們又找到了新的市場。這些烏克蘭流亡者洗白了自己的納粹身份,把自己包裝成了反抗蘇聯暴政的自由斗士民族英雄,開始逐漸在西方特別是美國登堂入室,取得了相當大的影響力。在美國的扶植下,這些烏克蘭納粹一方面在西方各國國內進行著反蘇反共宣傳,一方面也和世界各地的反共組織合作,參與了各種對共產主義政權的顛覆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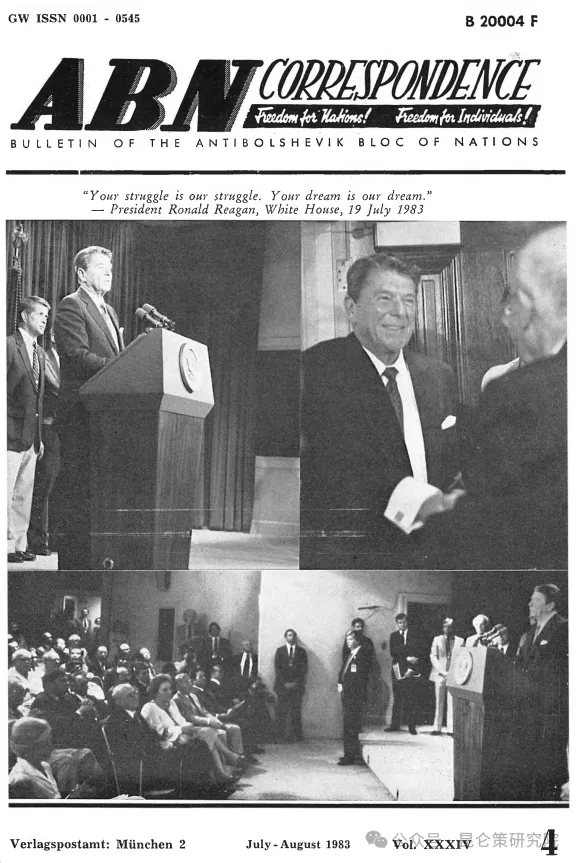
【1983年,里根在白宮會見“洗白”后的烏克蘭納粹流亡者】
那么你猜冷戰結束之后,這些人,以及這些人的徒子徒孫們又去了哪里呢?一部分人回到了烏克蘭繼續他們的極端民族主義事業,一部分人則留在美國繼續影響著美國政壇。自2014年之后,烏克蘭政府在逐步地迫害烏克蘭俄語區的民眾,將他們視為二等公民,并且系統性地將有關俄羅斯和蘇聯的一切從烏克蘭的歷史和現實中抹消掉。而如果烏克蘭政府和相當一部分民間的民族主義者不愿接受涉及蘇聯和俄羅斯的建國史,那么他們剩下的選擇,就只能是納粹德國和班德拉們合作下的傀儡政權了。

當我在2021年寫下相關文章的時候,烏克蘭政府招魂這些納粹余孽的努力已經非常明顯了:納粹分子的塑像作為民族英雄的紀念在廣場上聳立,新納粹分子揮舞著班德拉的旗幟和黨衛軍的旗幟在街上游行宣示著對國家的主權……當普京在2022年說烏克蘭需要“去納粹化”的時候,我們需要明白這些納粹是誰,怎么來的。而這,都要從二戰說起,從二戰期間的納粹在戰后沒有得到清算說起。當我在2021年寫烏克蘭納粹問題的時候,我的很多資料其實都是直接來自于西方,那時候西方的主流媒體和政客,還并不十分避諱談論烏克蘭的新納粹分子。而在2022年俄烏沖突全面爆發之后,盡管烏克蘭的新納粹勢力借著戰事獲得了極大的擴張,但是因為“烏克蘭存在納粹”這件事不符合西方的輿論,烏克蘭納粹問題一夜之間從西方輿論場消失了。即便新納粹分子的宣傳和活動在烏克蘭軍隊、政府和民間都越來越頻繁,但只要你指出來,你就要被視為“通俄”。所以有些事情就很有意思。比如美國國會在2022年接見了臭名昭著的“亞速營”,但是2018年美國國會可是明確禁止了美國政府將武器送給亞速營,因為亞速營與新納粹有勾結。那么是2022年的美國國會“通納粹”了,還是2018年的美國國會“通俄”了呢?


【2022年,美國國會將亞速營視為座上賓】
當然,隨著近期烏克蘭戰事不順,烏克蘭納粹又變得有些可以談的余地了。比如之前加拿大議會把烏克蘭老納粹請過來,至少還激起了一定的反對,逼著加拿大政客們至少跟明牌的納粹劃清界限。

【2023年加拿大政客們在議會里向烏克蘭納粹老兵起立鼓掌致敬,事后眾議院議長就下臺了】
但是問題來了啊:假如二戰之后,納粹分子及其意識形態得到了清算,我們還能看到一個納粹分子舒舒服服地活到老年,還被包裝成“反俄英雄”,被加拿大議會邀請嗎?其實這種事情沒什么奇怪的,在絕大部分西方國家,清算納粹都是一個偽命題,一個被輿論和敘事所掩蓋的神話。即便戰后有審判有清算有各種針對納粹分子的刑罰,但實際上大部分納粹分子及其意識形態都活得好好的。因為納粹分子及其支持者,再加上他們更廣泛的同情者,是個過于龐大的群體了。你能殺幾個首惡分子,但你能殺掉所有支持者嗎?把他們的觀念扭轉過來,讓他們正確地認識到納粹主義的危害,又需要怎樣的社會工程?而更重要的是,冷戰很快就開始了,反納粹要讓位給反共。二戰前的納粹得到歐美的支持和綏靖,就是因為他們認為納粹可以用于反共;而在二戰之后,納粹已經不再對歐美構成重大威脅,那么自然又可以被利用起來反共。比如德國,雖然我們聽到了大量反思納粹跟猶太人和解的故事,但這只是二戰后的一面。而另一面是,大量納粹德國的官員和軍人都被保留在了西德政權,而大量納粹黨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也都過著自己的安穩日子。我前面提到的烏克蘭納粹流亡者們集結的第一站就是慕尼黑,因為他們在西德能找到自己在納粹德國時合作的“老朋友”,而那些“老朋友”還是做著納粹德國時期的老本行,負責針對蘇聯的顛覆活動。德國尚且如此,別的國家更不用說了。比如意大利最新上臺的極右翼總理梅洛尼,她所在的黨派就跟二戰時期的意大利法西斯有著直接的歷史聯系。因為意大利壓根就沒怎么清算法西斯分子,法西斯主義者在二戰后仍然有著相當的群眾基礎和政界支持,能夠堂而皇之地維持組織并且影響政壇,只需要做點表面功夫掩蓋自己的黑歷史罷了——很多時候連表面功夫都不用。

【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黨(Fratelli d'Italia)”直接繼承自“意大利社會運動黨(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一個二戰后由墨索里尼支持者成立的老牌政黨】
如果你去翻西方極右翼的歷史溯源,大多都可以在納粹那里認祖歸宗,只是有的不避諱自己的家世,有的還顧及一點臉面——這些都是二戰清算納粹失敗所留下的歷史問題。不過,美國極右翼例外,他們的歷史淵源得上溯到美國內戰時期——正是因為聯邦政府無法清算南方邦聯的余黨,從而讓他們的種族主義等一系列極端思想得以延續至今。某種意義上講,美國種族主義者可能還比納粹高一個輩分,畢竟當初希特勒他們在策劃種族隔離和種族滅絕的時候,是從美國那里汲取的經驗。對于西方在清算納粹上的失敗,我們也可以反過來理解,之所以西方無法徹底清算納粹的人員和意識形態,是因為納粹的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本身就是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不是納粹分子太強大,而是西方社會總是有適合他們生存的土壤。二戰時的納粹分子宣揚的是從劣等民族那里奪取生存空間,現在的西方雖然明面上不說這些詞,但是干的還是一樣的事,只是包裝得好一點、文明一點。因為再往前追溯,納粹主義不過就是西方幾百年殖民主義的一種極端表現形式。當然,這些西方國家的納粹行徑也有完全不包裝、與人類文明逆行的時候,比如在侵略他國燒殺搶掠的時候。然而,今天總能聽到一些聲音宣稱戰爭中雙方互相殺害平民,似乎意味著要各打五十大板,難道被壓迫者的反抗也有錯嗎?二戰時期同盟國殺害了無數軸心國平民,那二戰就不是正義對非正義的戰爭了?但你別說,還真就不斷有人用這種邏輯來否認二戰的正義性。比如日本總是念叨原子彈殺死了多少日本平民,避而不談自己為什么挨原子彈。只要自己受一點委屈,那就是受害者,同時只要受害者不是完美受害者,他們的任何反抗就都有錯。這就是錯誤的二戰史觀,沒有看到德意日法西斯如何系統性地屠殺他國平民,沒有看到德意日的平民又如何從這種法西斯及軍國主義中取得實際利益,或是被意識形態的狂熱所裹挾,沒有看到那些不愿屈從法西斯及軍國主義的各國人民(包括德意日人民自己)又是如何被其所鎮壓……在此順帶發散一下,不光是二戰歷史,整個世界近代史,涉及殖民主義以及對殖民者的反抗,都有類似情況。比如,那些成天批判義和團犯下的錯誤,卻避而不談殖民者如何殘暴、義和團因何而起,抱有的是同樣錯誤的史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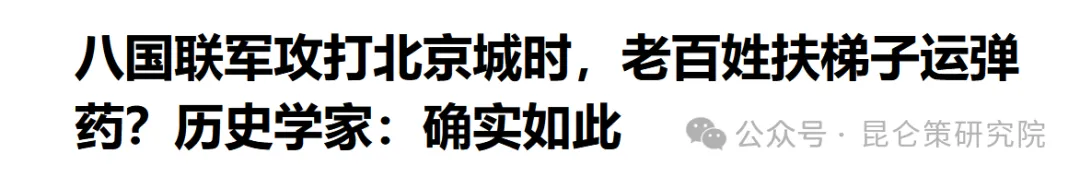
【一提當年的侵略,就總能見到這樣的歷史虛無主義奇談怪論,只提老百姓因為生活困難被侵略者的許諾吸引而幫助八國聯軍,一點不提八國聯軍如何在這之后撕破偽裝大肆燒殺搶掠老百姓】
如果我們對于歷史的理解永遠只限于聽故事,搞歷史發明和影射史學,像某些極右翼政府那樣通過從歷史中東拼西湊一些案例來支持自己的論點,沒有一套唯物主義史觀,那不僅看不清歷史,也看不清現實。世界當然是復雜的,意味著我們永遠都能找到支持不同角度、不同論點的例子。就好像二戰時期,法西斯們再邪惡,也不是從地獄里爬出來的,你也能從里面找某些個體的閃光點;同盟國再正義,也不是什么完美的圣人,你也總能找到他們犯下的罪行。但是,即便每一方都存在正義和非正義的部分,我們為什么依然要堅定地將二戰定義為一場正義勝利的戰爭?因為正義是中蘇美等各同盟國的主流,而非正義是德意日法西斯政權的主流。盡管二戰勝利之后的秩序遠非完美,但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解放了世界各國,帶來了更加平等與和平的世界秩序,避免了更多的死亡和奴役。試想如果是法西斯勝利,如果延續他們種族滅絕的路線,這個世界將陷入更加深重的災難。只有擁有正確的史觀以及世界觀,用整體的、發展的眼光去看問題,才能跳出各種輿論和敘事的引導,做出自己的判斷。當然,正確的史觀和世界觀也依賴于正確的史實和事實,這也是為什么否定和篡改二戰史實——要么抹殺中蘇的貢獻,要么美化侵略和殖民,都是極其危險的。以色列幾十年來鼓勵擴張所謂的“定居點”,大量侵蝕巴勒斯坦的土地,擠壓巴勒斯坦平民的生存空間,再加上一系列建立在宗教極端主義之上的意識形態不斷泛濫——甚至任何試圖反對的猶太人,也會變成敵人。

【即使是猶太人,只要稍微有點良心,也要挨以色列軍警的鐵拳】
然而就是這樣的以色列,以受害者身份,不斷引用二戰時猶太人遭遇屠殺的歷史,仿佛只要自己是猶太人,就永遠不可能是納粹,只要自己是猶太人,那么自己的敵人就是納粹。

【比如以色列駐聯合國代表就天天給自己戴黃星,強調猶太人被納粹德國屠殺的歷史】
這種按照種族身份而非實際行為來定義善惡的邏輯,難道不似曾相識嗎?本來俄烏沖突的時候,某些媒體拿澤連斯基是猶太人論證烏克蘭沒什么納粹、俄羅斯才是納粹的時候,我就已經覺得非常搞笑了。然而到了加沙戰爭,當有些以色列人綁架歷史上的大屠殺受害者,用猶太人身份來論證一切反對以色列的人都是納粹的時候,我已經笑不出來了,只是替那些死于納粹之手的猶太人嘆息。然而這一套變相種族主義的信徒非常多,他們總相信某些民族和種族天然就是正義的、先進的、文明的。在當今世界,最主流的種族主義就是相信,不管西方如何明面上殺戮平民或暗地里顛覆政權或明里暗里從經濟政治上脅迫他國,西方都代表了人類文明。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在受害的亞非拉諸國,也不乏這樣的逆向種族主義者。所以,雖然二戰之后亞非拉國家獲得了名義上的自由,但亞非拉人民仍然被視為低人一等,亞非拉的發展仍要服務于西方,仍要在經濟、文化和軍事上從屬于西方。任何試圖打破這一體系、試圖爭取平等權利的努力,永遠要被主流西方輿論污名化。同樣的話術和邏輯,比如中國提供廉價商品和勞動力是被鼓勵的,但當中國想要自己發展高端產業,那就成了“過剩產能”,就要被扣上破壞公平貿易的帽子。西方加稅是保護產業,但中國不能加稅,因為這是破壞規則。又要享受中國廉價商品,又怕中國商品太廉價危害西方產業,這哪里是什么自由資本主義,本質上還是種族主義——而且還是智力不太好的那種。

【幾年前拜登反對特朗普對中國打貿易戰的時候,還知道嘲諷:“任何一個經濟學新生都會告訴你美國人民在為他的關稅付費,而不是中國”】
所以,樹立正確的二戰歷史觀,跟我們中國是息息相關的。二戰前后發生的事情,也在不斷重演。比如前文提到的烏克蘭納粹流亡者,他們在美國的一項重要遺產,就是推動國會設立了一個“被奴役國家周(Captive Nations Week)”。顧名思義,就是東歐各國被蘇聯“奴役”,西方各國要反蘇反共來支持這些國家走向“自由”。順帶一提,這些國家的名單,和當初納粹德國意圖肢解蘇聯的設計圖,是高度吻合的。奇怪的是,冷戰之后,“被奴役國家周”也照樣每年都辦,相關組織也照樣發展。可是蘇聯解體了,那些國家終于“自由”了,下一批所謂的“被奴役國家”要從哪里找呢?那自然是中國,這個下一個等待肢解的目標。比如那個在新疆問題上聒噪的德國人鄭國恩(Adrian Zenz),他背后所謂的“共產主義受害者基金會”組織,就來自于“美國被奴役國家委員會”。每年7月美國總統的“被奴役國家周”講話,“藏獨”“疆獨”“港獨”“臺獨”等分裂勢力也從不缺席。你根本用不著知道什么“被奴役國家宣言”也能明白,美國想讓中國成為下一個蘇聯。因為美國用這一套贏了,自然就想著再贏一次。當年利用新老納粹反共反蘇,現在就繼續利用新老納粹反華,不管是輿論準備還是理論基礎,跟當年冷戰時期的老一套、甚至跟二戰前綏靖納粹的老一套,都差不多。所以烏克蘭的亞速營當年參與香港暴亂,也并非偶然,而是一套你可以上溯到百年前的歷史重演。不管是美國政客還是烏克蘭新納粹還是香港暴徒,大概率都不知道也不關心這段歷史,但不妨礙他們的行為邏輯與歷史形成呼應——因為在光鮮亮麗的所謂現代文明背后,某些東西一直沒有變。(作者系匹茲堡大學政治學系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后;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