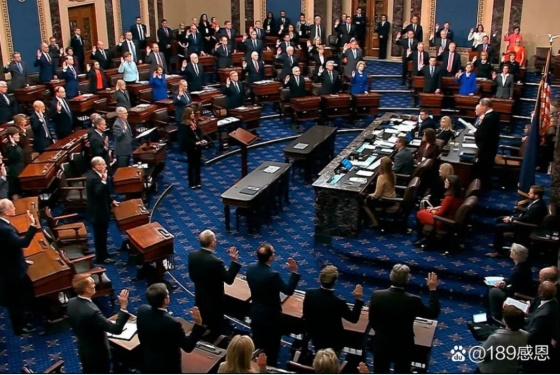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16日-星期三
光明日報“改進文風大家談”專欄刊發的系列文章中,有一篇是2025年2月20日山東大學講席教授、《文史哲》主編杜澤遜寫的《文字要給人以美的享受》。文章的最后兩段是這樣的:
我強烈感受到,目前的學術論文已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所謂規范文體,我叫它“期刊體”。毋庸諱言,這種“期刊體”,經過千錘百煉,對于表達科研成果非常好用。但是,作為一種文風,卻千篇一律,缺乏個性,以至于沒有審美的功能,不能吸引讀者閱讀,只能作為學者撰寫論文著作時不得不參考的對象。
我曾向學生推薦王國維的論文《肅霜滌場說》,這篇論文認為《詩經·七月》“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描繪的是九十月份秋高氣爽的景象。“肅霜”“滌場”都是聯綿詞,與字面意思無關。文章最后說:他從南方來到北方,“九十月之交,天高日晶,木葉盡脫,因會得‘肅霜’‘滌場’二語之妙”。這既是以科學角度觀察現實,也是從文學角度抬高文氣,這樣的文字給人以美的享受。我期望我們建設這樣一種科研論文的境界,一種有美感的學術境界。
這兩段文字給我以強烈震撼。其之所謂“期刊體”,讓我自然聯想起書法中所謂“館閣體”。“期刊體”“館閣體”雖然中規中矩四平八穩,但實在了無生趣,很難讓人喜歡。它甚至讓我聯想起《《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角色-----好人“卡列寧”,雖然安哪對自己說:“他畢竟是個好人,正直,善良,事業上有成就。”“我明明知道他是一個不多見的正派人,我抵不上他的一個小指頭,可我還是恨他,我恨就恨他的寬宏大量。”有人評論:“正派和寬宏大量并沒有讓卡列寧變得討人喜歡,而是正相反。不能說美德有問題,卡列寧的問題在于,他的美德是教條的、刻板的、過度的。”
杜澤遜老師的文章還讓我想起三年前網上熱傳的一篇題為《廢話的勝利:“精致而平庸”的論文是怎么發上頂級刊物的?》的文章,其中有這么一段:
“頂級學術期刊要求更多的理論貢獻,所發表論文聲稱重大理論不斷進展,而事實上,真正的新理論很少出現。頂級期刊對于理論貢獻的要求,與渴望在頂級期刊發表論文的學者的職業抱負相互作用,導致學術期刊充斥著聲稱貢獻了理論的無休止的闡述,而這些‘精致而平庸’的研究議題與研究發現,對大多數領域同行并無啟發,對廣大公眾和管理實踐者的讀者來說更是晦澀難懂。”“如今管理學主流期刊上的大多數論文,不論是量化分析的實證研究,還是批判理論領域的思辨討論,都是公式化的、謹慎的、枯燥的和晦澀的。”
該文對如今大量存在的一本正經說廢話的“論文”現象進行了抨擊。“精致而平庸的論文”這一說法,差不多堪比“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樣經典。
我初次讀到《廢話的勝利:“精致而平庸”的論文是怎么發上頂級刊物的?》這篇文章,第一時間想到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此我還特意發表了一篇題為《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語言特色》的文章。
我認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之所以耐讀,很大原因是用了許多形象生動的語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強烈的實證感和可讀性,還來自文中大量引用調查對象的話語;而更為報告添彩的是文中引用的大量對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還有一大語言特點,就是大量使用有湖南特色的俚語土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還有大量近乎小說筆法的現象、場景、心理描寫,形象地還原了現場感。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不是戲文、小說,但正是多種文學手法的不拘一格使用,才使報告避免了板著面孔說教,使“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權力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等結論雄辯有力不容辯駁。
今日閱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不得不感嘆----“原來,調查報告竟然還可以這樣寫!”換句話說,今日就算還有人敢按這樣的筆調來寫嚴肅的考察報告,又有幾位報刊編輯能夠接受?
漫說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即便如大名鼎鼎的《史記》,試問今天誰敢用司馬遷這樣的筆調編寫歷史教科書?司馬遷要是活在今天,寫出這樣的歷史教材,不被方家齒冷已屬幸運,遑論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樣的贊譽。即如毛主席親自撰寫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三句話追溯三段浩瀚歷史,似用如椽巨筆推開重重歷史之門,可如果擱一般人頭上,即便敢于如此簡潔,又有幾人愿意買賬?
杜澤遜老師第一次用“期刊體”如此精準地給當今的學術論文畫像,指斥其不足,并明確自己理想中的論文境界----“一種有美感的學術境界”,實在是“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筆下皆無”,讓人稱快。
1958年9月2日,毛澤東批示一份報告時震怒了,當即寫信表達氣憤:
“我讀了兩遍,不大懂,讀后腦中無印象。將一些觀點湊合起來,聚沙成堆,缺乏邏輯,準確性、鮮明性都看不見,文字又不通順,更無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之態。”“你們是下決心不叫人看的。”“我疑心作者對工業還不甚內行,還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現出來。”“講了一萬次了,依然紋風不動,靈臺如花崗之巖,筆下若玄冰之凍。哪一年稍稍松動一點,使讀者感覺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為延長一年兩年壽命呢!”
柏拉圖說過:“誰會講故事,誰就擁有世界。”把復雜的事變簡單,智慧;把簡單的事整復雜,麻煩(或可以說就是“忽悠”)。只要真心愿意如習總書記所說的那樣,“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把科研做在生產實踐中”,講故事,說人話,其實并不復雜。但愿杜澤遜老師的直言能引起學術界的足夠重視,從而真正改變“期刊體”泛濫的局面。
(作者:陶余來,常州大學紅色文化研究院(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來源:【原創】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國策建言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