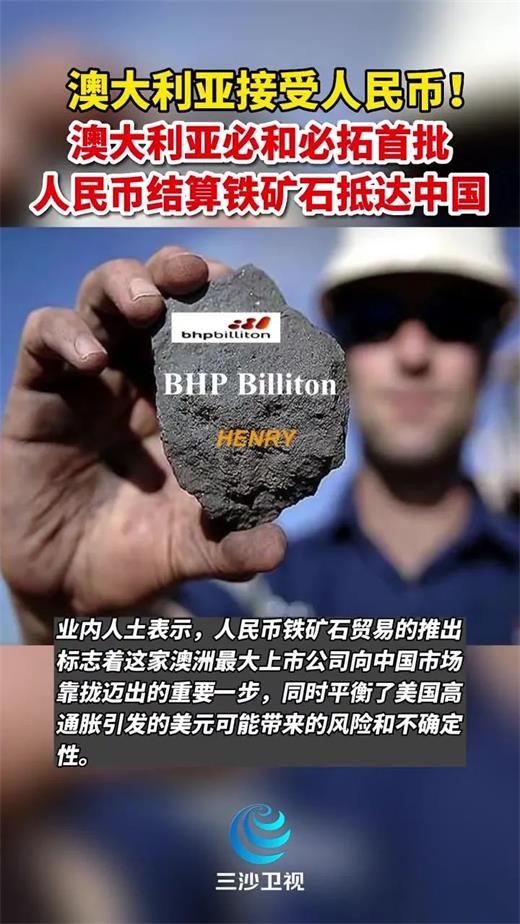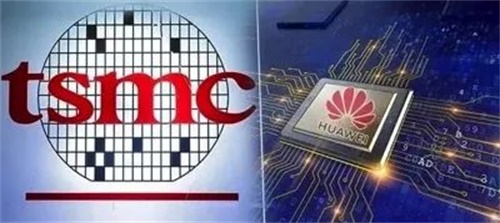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
冷戰后美國統治集團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主要觀點評析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為創建自己主導下的全球秩序,運用戰爭與和平兩種手段推行對外政策,以保 證美國及其盟友在全球范圍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美國政要們認為,戰爭是一種工具,是借以獲得權力和勢力、 增進國家利益的一種手段,沒有美國,和平和自由就沒有可能繼續保持下去。為保護美國的切身利益,必須把采取和平的辦法和堅決的行動結合起來,利用一切和平手段來誘導共產黨集團,20世紀在蘇聯和東歐擊敗共產主義,僅是21世紀“自由”在全世界獲勝的第一步。對于美國而言,21世紀最重大的挑戰之一,是處理信奉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的各國人民之間依然并將永遠存在的深刻分歧。
一、“戰爭是獲得權力和勢力的一種工具”
二、“真正的和平是容忍沖突的一種手段”
三、核武器大大改變了世界運行的方式
四、為保護美國切身利益,必須把采取和平的辦法和堅決的行動結合起來
五、必須利用一切和平手段來誘導共產黨集團
六、軍備不是引起戰爭的原因,軍備控制也不能實現和平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李慎明 等:冷戰后美國統治集團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主要觀點評析
2022-08-18劉典|全球金融動蕩,美國霸權遭遇危機,人民幣國際化未來如何前行?
2022-08-12?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