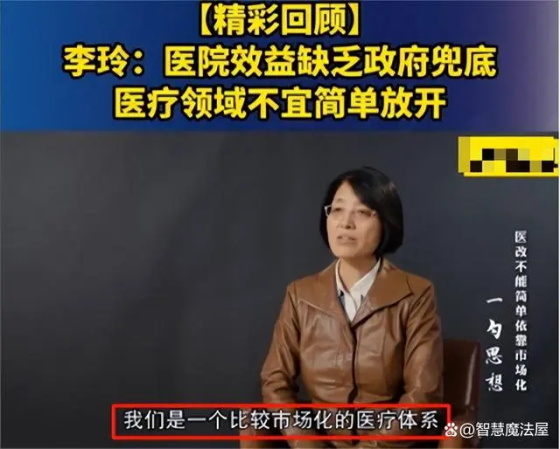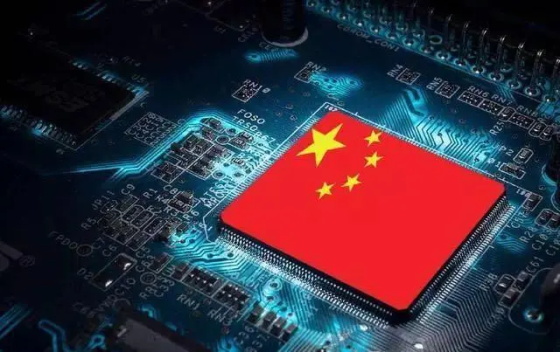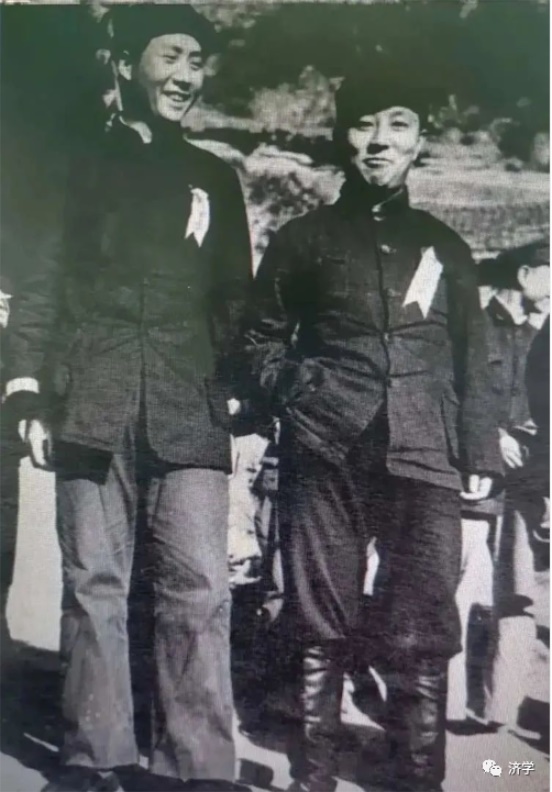有這樣一大批人,年輕時懷著火熱的革命激情,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離開城市,奔赴農村廣闊天地,將自己的青春毫無保留地奉獻給祖國建設最需要的地方;回城后又大多被分配到效益不太好的企業甚至是街道小集體企業工作;不多久又普遍陷入了下崗失業的困境,只得背起行囊四處去奮力打拼;年老后,退休金又比其他崗位退下來的同等經歷者少一半以上。要說這一群體的人沒有怨氣,無異于天方夜譚!當然,這種情況不只限于知青群體,但本文為專門探討知青中部分弱勢群體存在的問題,其他群體,雖有涉獵,但恕難顧全。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做到人人滿意。但當一個社會中相當多的人,由于政策變化原因而不是自我努力原因,導致社會對自己的嚴重不公時,就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政策、體制所導致的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此,在中央提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今天,對這一現象進行探源,不僅可以為高層決策提供社情民意,而且對緩解社會矛盾,消除社會戾氣,促進和諧穩定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試對此做一些探究。一、某些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出于某種政治需要,公開否定和詆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瓦解了知青參與新農村建設的斗志,為知青全面“返城”營造起巨大的不正常的輿論氛圍和社會氛圍不可否認,對于大多數知青而言,當初確實是滿懷一腔熱情,積極報名去上山下鄉的。在貧下中農的言傳身教下,大部分知青在農村社會主義建設中也確實做出了巨大貢獻,對推動農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正是由于包括1700多萬知青在內的農村全體勞動者的艱辛努力,使戰爭廢墟上支離破碎的農村自然條件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就農業生產而言,經過農業學大寨運動,不僅山區的農村普遍打造起大量的水平梯田和人造平原以及溝壩地,平原地帶的鹽堿地、沼澤地等也得到充分利用與改善,各地還興修了無數的水利工程和鄉村道路等。正是由于這種自然環境的極大改善以及農村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才使我國農業得以極大發展。據中國統計年鑒統計,我國的糧食總產量由1949年的1132.78億公斤提高到1979年的3315億公斤,增加近兩倍;在同期人口由5.42億增加到9.75億、增長近一倍的情況下,人均糧食卻從209公斤提高到340公斤,不僅有力地保障了城市供應,而且為加速城市工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逐步安排知青回城參與各種建設創造了充分的條件。如果此時,還仍然按照周總理生前“對知青國家關心、負責到底”的指示精神,有計劃地安排知青返城——假設,根據一些地方前期安排知青返城的成功經驗,按照全國各個城市可容納的勞動力,分地域和插隊來源,規定插隊多少年或達到多少勞動日的知青,可以由國家統一調度返城,就既不會陡然中斷知青上山下鄉,形成前后不同的城市青年步入社會的路徑不同、待遇不同等不公平現象,也不會為國家帶來巨大的就業安排壓力;更不會引發較為突出的社會紊亂。政治家都懂得,要動搖社會根基,必先摧毀社會信念。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風向逐步轉變。先是以批判“個人崇拜”的名義,在主導輿論陣地出現了一片聲討和質疑毛澤東時代思想和路線的聲音,導致社會上不少人不僅對毛主席個人的崇拜和信仰大打折扣,自然也對毛澤東思想開始質疑。由于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必然波及到對馬列主義的信仰。于是,全社會陷入了空前的信仰危機,對知青自然也不例外。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正是毛主席提出和著力倡導的、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在大前提都被否決的情況下,“上山下鄉”這條路對不對,自然就會引起不少人的思考和質疑。人是社會導向的追隨者,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細腰,宮中皆餓死”,在這種不正常的政治氛圍下,一些人和一些地方因為知青返城鬧事,也就成為事物發展之必然。而在此同時,不少文人也緊跟形勢需要,緊鑼密鼓地拋出了許多在文革中所謂干部下基層住“牛棚”、受“迫害”的控訴文章,同時出現了大量聲討文革,聲討上山下鄉的“傷痕文學”。一時間,好像億萬人民生活了幾千年的農村,簡直成為“人類不能生存的地方”,不僅知青自身感覺到落差,疼子心切的家長更感覺到痛心疾首。在這種情況下,據說上面還有人拋出知青上山下鄉“三個不滿意”......就這樣,不僅知青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斗志被一步步否定和瓦解,而且不少家長也對自己當初動員鼓勵子女到農村去感到后悔。如此便為知青一窩蜂的“大返城”營造起巨大的不正常的輿論氛圍和社會氛圍。
二、在條件尚未完全具備、準備工作尚不充分的情況下,無計劃地實行知青大返城,不僅導致很大一部分知青難以得到妥善安置,更加速了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敗壞
如前所述,在政治風向轉變后,社會已經普遍出現了信仰危機,毛澤東時代繼續革命理論指導下批判了多年的“資產階級法權”,再一次死灰復燃,請客送禮、走后門等不正之風遂即遍地興起。而知青集中無序返城,更使已經敗壞的這種黨風和社會風氣雪上加霜。當不正常的輿論氛圍和社會氛圍已經營造起來后,一些人向涉及的數萬家庭表示“恩賜”的時機也已經成熟。1980年,中央書記處批準了國務院知青辦《關于當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幾點意見》,提出“能夠做到不下鄉,可以不下” ,宣告了上山下鄉即將停止,各地開始了集中安排知青返城。這種返城,既包括仍然在農村插隊的知青,也包括已經由各插隊地就地安排工作,但未回到京津滬以及省會等大城市的知青。但這種安排,卻是在當時的大城市并未完全具備條件的情況下展開的。一種社會現象的發展恰似“滾雪球”,初開始由于體積小,因此不管是從所沾“雪”的絕對量還是增加率都會很少,只有當“雪球”大到一定程度后,才會進入快速增加的境地。筆者把這種現象稱之為“‘滾雪球’效應”。本來如果當時國家能夠如前所述,有計劃地安排知青回城,不僅在工業體系已經健全的情況下能夠更快地加速城市工業以及其他行業的發展,也可以為后續知青盡快返城創造充足的條件。但當時的決策者卻并未這樣,為了得到絕大多數知青及其家長的感激,采取了“復雜問題簡單處理”的辦法,即政策由高層制定,具體問題由基層克服困難,設法解決。但不管城市大小,對勞動力的容納量總是有限的,同時還有城市公共服務保障等一系列問題需要解決。大城市向心力強,這一矛盾更為突出。因此越到下面,越感到困難重重。在當時情況下,所涉及到的部門和單位中的領導干部公開“罵娘”的不在少數,但在“不換思想就換人”的壓力下,只能隨潮流、保烏紗。于是,各種形式的返城門道和七花八樣的安排方式應運而生,往往就憑關系、比背景了,有被安排到黨和政府機關的,有到事業單位的,有到央企的,有到各級國營集體企業的,也有到街道小企業的,還有安排不了工作的,回城后只能自主擇業,如當時大城市賣大碗茶的不少人就是知青。國人自古就有隨大流和好面子的習性,不僅城市各方面的條件確實比農村好得多,而且能不能回城、特別是能不能回到父母生活的大城市,能不能聯系分配到好一點的單位,更是自己面子和尊嚴的重要標志。這種普遍的心理狀態,必然導致知青們絞盡腦汁、想方設法、各顯神通,為回城而努力奮斗,并為爭取到一個“旱澇保收”的鐵飯碗而不惜一切代價。在許多情況下,這種“努力”全靠自己及其父母家人的關系,以及“工作是否做到位”。在筆者與當時返城的一些知青個別交談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承認,為了回城自己及家人“求過人”。在這種“求”的背后隱含著什么,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筆者第一次聽到“牙毒”這個詞,就是在這個時候,意指一些手握安置權力的人,接受請客送禮已經“成癮”。因此,知青無序返城,使走后門和請客送禮等不正之風急劇擴張,成為黨風和社會風氣嚴重惡化的助推器和加速器。
三、隨著企業改革逐步深化和工人階級地位下降,導致包括知青在內的企業職工成為改革成本的巨大承擔者,這部分人的切身利益受到巨大傷害
盡管在知青返城過程中每個人都各盡其能,但客觀上最能容納勞動力的地方還是企業。根據筆者所在縣的調查統計,回城后第一次安排到工商企業工作的知青,占到當時知青(剔除從插隊點直接入學及其參軍的)總數的83.6%。如果不是后來的政策改變,這些知青即使分配到企業,無非是比機關干部工作苦點累點,但在“多勞多得”的原則下,經濟收入還是比機關干部要高。從1956年至1985年,我國工廠一直實行的是八級工資制,據網查,一般工廠的“八級工”月工資高達126元(折合到今天為10000元左右),一個八級工的工資,比行政15級干部(124元/月,縣處級級別)的工資還稍高;工程師職稱則從102元起步,到207元;一般工人最低工資(五類地區一級工)為35.5元,比行政最低級別的23元高出54.3%。在這種工資制度下,工人即使退休后,只要自身努力,退休金也會高于同等條件下的機關干部,屬于社會上中等水平,而不會因為自己一輩子的辛勞,老年生活反而不如工作相對清閑的機關干部。但是,隨著政策導向的逐漸變化,企業職工的利益卻被一步步剝奪。首先是政治地位的變化。如果我們尊重歷史,就不會否認,在毛澤東時代,不僅黨和國家的大量領導人以及各級班子的領導干部,有很大一部分是出身于平民階層的老革命家,這部分老革命家和最普通的老百姓有著一種天然的感情。而在后來特別是文革中,又有一些工農出身的人直接進入各級領導班子乃至中央高層。盡管后來一些報道污蔑這些人沒有領導能力和水平等,但有一個作用是無疑的,即在高層以及各級決策層中,有了工農群眾的直接代言人。這是防止黨和國家的政策嚴重脫離群眾、傷害群眾利益的有效措施之一。但當這部分工農群眾的“代言人”逐漸從政治舞臺中退出后,大量“精英”成為政策草擬者或直接涌入決策層。由于這些“精英”絕大多數出身于條件比較優越的家庭,且大多數是從家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還有不少是“海歸派”,因而這些“精英”們既在感情上與最底層老百姓沒有水乳交融的血肉聯系,也難以感受和體諒到最底層老百姓生存的艱辛,因此,他們所拿出的“頂層設計”政策,必然是更多地傾向于自己所在群體的利益,而最底層老百姓的利益就會越來越被忽視。一個社會在一定時期內的社會財富是恒量的,蛋糕就是那么大,有人多吃就必然就會有人少吃。而在各級人大政協中的一線工農代表已經大量被“老板”“能人”所替代的情況下,更使許多重大政策再次失去了糾偏的機會,因此,底層群眾的利益被侵占就會成為一種體制必然。這種體制必然,首先是從工人階級地位急劇下降開始的,先是由領導階級變為“雇傭勞動力”(以合同制為其主要標記),直至最后由主人翁變為“勞動力市場”的商品。接著在企事業單位(行政單位當時未納入)又推開了以“繳多領多,繳少領少”為特征的“退休養老金制度改革”。事業單位一般都是財政撥款或有政策性收入,影響不是太大,但苦了的是企業職工。企業講究的是經濟效益,在“廠長經理負責制”以及后來的“承包”“租賃”經營等一系列“系統操作”下,每一分錢都直接涉及到廠長經理的個人利益,自然不會讓工人的工資高多少,更不會拿出大量的資金去為工人繳納企業應承擔的“單位繳費”部分。有的企業以經營困難為理由,干脆不繳納單位應該承擔的部分,有的即使繳納,也是按照最低標準去交。繳費基數低,必然導致工人將來的養老金受到影響。到后來,在改革的一步步深化下,除少數央企和壟斷性企業外,地方幾乎所有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均被改制私有化,市級以下企業職工普遍下崗失業,更沒有人去管今后的養老金問題。到這些人達到退休年齡時,不少職工“單位應繳納”的養老公積金部分,均由職工個人籌集資金繳納。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企業職工的養老金,肯定會與同期事業單位特別是行政單位的相同情況的人相差很多。在這里還須特別指出的是,在“高薪養廉”的政策導向下,行政單位即后來稱之為公務員隊伍的工資和各種補貼卻在快速提高。據了解,近幾年提高的速度更快。以筆者這一級別為例(公務員系列,正縣級實職崗位退休,屬于現行政策的相對受益者),在職人員每兩年提高一次,每次提高在千元左右以致更多。而像筆者這樣的退休人員,每次調整卻僅有100多元。因此,盡管國家對退休群體的養老金逐年增加,但由于單位性質不同,工資基數差異較大;且同一類人中資格越老、退休越早,工資基數越低,按工資比例調資時,每次增加的絕對額越少,因此,調資次數越多,與后邊退休的同類人員絕對額相差就越大。有的實際增加比例達不到物價上漲指數。這種差距,從一般干部到高級干部,從企業到事業、到行政,都嚴重存在。這種不合理現狀,必然給黨和國家的威信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
四、由于長期的輿論誤導,不少知青把自己后續的困境歸罪于上山下鄉,導致了極大的認知盲點
上山下鄉政策結束后,一大批傷痕文學特別是影視作品紛紛面世,其中有不少作品是聲討上山下鄉的。而一些輿論,也把知青引導到“由于上山下鄉,才耽誤了知青個人的升學就業等前途發展”上來,導致不少對歷史資料了解甚少或者沒有深入思考的知青,把自己后續的困境怪罪于上山下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一種“群體意識”。特別在當年黨風和社會風氣越來越不正的情況下,當回城當工人而后又被拋棄的這部分人,看到和自己一起下鄉的知青,因為有背景或依靠各種操作,先后調入行政單位或事業單位,則怨氣更大,對當初上山下鄉的抱怨也就越來越多。其實這是一種極大的認知盲點。且不說在建國初的前幾十年,我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依靠自力更生建設新中國,首先要把有限的資金積累用在確保國家安全上,“兩彈一星”、核潛艇等和幾百萬軍隊的建設,都必須優先保證。其次,為了保證國家的持續發展,還需要優先安排作為“工業之母”的重工業發展,然后才是其他發展。即便如此,在我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口劇增的情況下,還是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中學數量從1949年的4045所增加到1966年的55010所,增長了13.6倍;學生人數從1949年的103.9萬增加到1249.8萬,增長了12倍。但因為國家經濟基礎還整體上較為薄弱以及師資人才有限等原因,高中教育還不可能普及。而大學教育,1965年的毛入學率只有2%,至1991年前仍在2%左右徘徊,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難以滿足絕大多數人的教育需求。面對這種現實國情,即使不上山下鄉,又有多少人能夠擠入繼續升學的行列?退一萬步講,假設當時能夠全部升學,一個社會總是需要有大多數人到生產第一線的。作為廣大工農的一線勞動者如果收入待遇得不到合理保障,即使不上山下鄉,你又能怎么樣?難道城里不需要勞動者,人人都是老板或者都是國家干部?難道不是回城知青,企業改制就不會被下崗?在如今貧富分化的社會里,如果你所處的那個社會階層在“頂層設計”中沒有代表去為你發聲,你又能在社會發展的這塊大蛋糕中分到多少?所以,問題的關鍵還是工人階級和工農聯盟能否真正回歸到憲法定位上來,還在于改革政策導向是否真正堅持公平正義。否則,底層群體的利益將永遠處于被侵蝕的境地。欣喜的是,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再次把“人民利益為中心”作為黨的執政方針,使我們對類似問題的逐步解決看到了希望。
五.工資及退休金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是黨和政府脫離群眾的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應該引起高度警惕
工資收入政策是一個國家為了誰、依靠誰的重要風向標,也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黨是否脫離廣大群眾的一個重要標志。前蘇共之所以亡黨,一個重要的教訓,就是在長期執政下,出身條件優越家庭的人有更多機會捷足先登政治舞臺,致使黨的不少干部不知群眾艱辛,逐漸脫離群眾。這種脫離一般都是從最初感情脫離,到行動脫離,最后到體制政策脫離。其中,在工資政策上的表現就非常明顯。蘇聯建國初,在領導人中列寧的工資最高,為500盧布,但工人的最高工資為510盧布。斯大林時代略有提高,但規定機關干部的平均工資不得高于工人平均工資的1.5倍。而到赫魯曉夫年代就增長到30倍,以后更逐漸增至相差70倍,另外還有依仗權力侵吞所得。這就最終導致黨和民眾形成根本性對立,也決定了當克里姆林宮上高高飄揚了70多年的紅旗在無邊的夜色中被降下時,沒有一個人去反抗。工資制度及退休金制度,與絕大多數人生活質量與做人尊嚴直接相關,無疑是黨和政府能否凝聚民心一個很重要的措施。當一項涉及廣大群體的政策沒有公平合理性時,一大批人必然感到心理不平衡,也就必然形成一種負能量的社會心理暗示,這對黨和國家的誠信聲譽及其形象帶來極大的破壞作用。長期以往,必將聚集巨大的社會戾氣。而這種戾氣是會傳染的,當社會充滿戾氣的時候,我們的社會和諧穩定、長治久安就會失去基礎,就會影響到黨的凝聚力和號召力。倘若遇到戰爭等國家危機時,這種情況極為可怕。上述觀點,實屬筆者的“管中窺豹”。盡管知青弱勢群體只是社會各階層弱勢群體中的一部分,但他們所遇到的困難和心理狀態,與其他弱勢群體是一樣的。知青問題,在我們國家解決社會問題這盤大棋中,有著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必須汲取前蘇聯的教訓,認真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指示,盡快改革我國的工資及養老金等政策和制度,以使底層廣大弱勢群體的民心進一步回歸。
【相關閱讀】
張黎平:理直氣壯地為知青運動正名
(作者系山西省呂梁市黨建研究會常務理事、特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