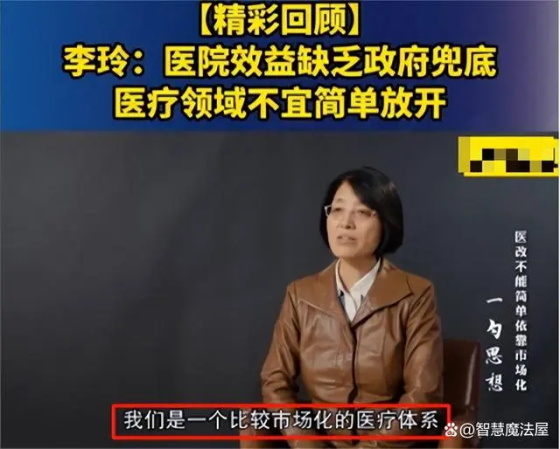《中國40年經濟繁榮落幕,接下來會怎樣?》、《中國青年就業市場宛如夢魘,國家面貌正在改變》、《中國經濟困境堪比30年前的日本?可能更甚》、《中國經濟惡化背后根源:民眾對政府政策沒有信心》……
近年來,西方政客、媒體與智庫正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一場“中國崛起頂峰論”,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在研究報告《荒謬的敘事:西方興起“中國崛起頂峰論”的梳理及應對建議》中,分析了這輪“中國崛起頂峰論”的四種荒謬邏輯,并指出其現實危害,呼吁打好針對“中國崛起頂峰論”的輿論反擊戰。
本文摘編自人大重陽“中美人文交流”系列研究報告《荒謬的敘事:西方興起“中國崛起頂峰論”的梳理及應對建議》。
【文/ 王文、陳修豪、魯東紅、查希】
自美國學者哈爾·布蘭(Hal Brands)和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于2021年秋季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等期刊發文撰書,提出“中國相對實力已經見頂”“中國崛起已終結”“中國衰退已開始”等觀點以來至今已兩年,外媒唱衰中國的聲音就不絕于耳,并且在2023年上半年以來愈演愈烈,呈明顯升級加強態勢。
以《華爾街日報》為例,其中文官網推出“中國經濟放緩”專題欄目,從2023年8月至2024年元旦,已發表160余篇文章,包括《中國40年經濟繁榮落幕,接下來會怎樣?》、《中國青年就業市場宛如夢魘,國家面貌正在改變》、《中國經濟困境堪比30年前的日本?可能更甚》、《中國經濟陷入惡性循環》、《中國經濟惡化背后根源:民眾對政府政策沒有信心》等在海外引起輿論共振、被廣泛傳播的多篇“爆款”文章。
事實上,該輪“中國崛起頂峰論”就是新版的“中國崩潰論”。但相比于過往25年層出不窮的“中國崩潰論”,這輪輿情規模最大、頻率最高、持續時間最長、范圍最大、來源最廣。
更值得關注的是,不同于以往集中在美國的“中國崩潰”論調,本輪“中國崛起頂峰論”荒謬的敘事正傳向歐洲、日本、韓國、印度等國的媒體與學者圈,質疑中國發展的規模、頻率、范圍等均遠超以往。近期,美方政府也進一步推波助瀾,如2023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就稱中國經濟為“定時炸彈”,對中國國際形象、聲譽進一步造成負面影響。
除了范圍大之外,本輪“中國崛起頂峰論”邏輯更為“精細”,讓有心為中國辯護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相比于之前針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政治崩潰論”,此輪崩潰論調聚焦中國疫情后經濟數據的低于預期的具體表現,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結構性、決策層的根本問題。雖然有媒體、學者對中國表示信心十足,但皆都難跳出“唯潛力論”,缺少對中國發展前景有效辯護。
本輪“中國崛起頂峰論”同時劍指中國決策層的誤判以及頂層設計的錯誤,認為中國經濟問題反映中國更深層次漏洞的暴露。他們認為,當前中國“重意識形態與安全”而“輕經濟增長”,更加集中的權力和深度的政府干預對民營企業等產生致命的打壓,加之疫情期間“封城”的政策選擇等,都折射了中國決策層在經濟政策與改革開放上“開倒車”。這種論調正在傳入國內,離間中國社會與政府、中國民眾與決策層的信任關系。
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達到預期
“中國崛起頂峰論”的敘事邏輯
對此,需要深度了解“中國崛起頂峰論”的敘事邏輯。尤其要注意這些敘事邏輯雖不能被中國主流人群所完全接受,但在國際輿情中卻有極高的穿透力。
敘事邏輯一:近年來中國經濟數據反映了深度結構與模式問題,且經濟下行是中長期必然趨勢。
這種敘事邏輯認為,當下中國經濟出現問題,是近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模型失衡的自然結果,印證了之前少數學者對于中國經濟模式的懷疑及預警。由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的增長模式在人口、債務、投資回報率降低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喪失繼續發展的空間。在經濟結構上,中國失去了之前的增長引擎,在沒有有效替代的前提下,見頂下行符合客觀規律,難以避免。舊發展模式缺陷凸顯、已經過時,但新模式需要的政策舉措和結構性、體制性改革又難以推進。
中國面臨一系列嚴峻的問題:生產力下降,生產成本高攀,基礎建設投資回報率下降,債務占GDP比重超過美國;總人口和勞動人口數量已經見頂并開始下滑,預計2035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7千萬,而老年人增加1.3億,本世紀末中國總人口降至8億人以下;老齡化持續加重,將造成財政問題、進一步拉低生產率;當下又出現青年失業問題,出現勞動人口和就業機會同時下降,反映中國經濟嚴重的需求和活力問題;人口紅利消失,加上當下房源供給失衡,大城市供給不足,總體分配不均,只會加劇房地產泡沫的破裂。
這些問題難以短時間內扭轉,疫情防控失誤加快了見頂的進程,但并非最終“病因”。地方債務問題、政府主導投資的發展模型、對房地產的過度依賴等不利因素的影響只是在疫情作用下加速凸顯。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增長為內外特殊機遇時期創造的不可持續的“奇跡”,見頂衰退乃是回歸常態。
敘事邏輯二:經濟問題反映中國決策層錯誤的估計和選擇,經濟政策及“穩信心”措施將持續搖擺無力,意識形態阻礙提振經濟。
這種敘事邏輯認為,中國政府有能力扭轉當下的經濟問題,但因對國內外環境和未來形勢的誤判,選擇維持現狀——經濟放緩或是中國決策層有意而為之。他們認為,讓年輕人學會“吃苦”反映了自上而下的不自信和低預期;政策搖擺無力造成了新的“信心危機”,造成經濟惡性循環,難以逆轉;疫情防控后期的錯誤反映了執政方式的短板,也是當下中國經濟問題的導火索;若決策層不做出改變,經濟問題或將影響社會穩定、威脅政權執政根基。
持此觀點的評論者同時認為,扭轉當下經濟頹勢,不僅需要及時、堅決的刺激措施,更需要經濟發展根本策略的轉換——維系高速增長的內外因素已不復存在,若不大力推進、深化必要的改革舉措,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極為暗淡。
評論者認為,中國國內專家早已形成政府需要采取強有力的行動來刺激經濟增長的共識,但近期出臺刺激措施皆為“擠牙膏式”的“零敲碎打”、“小修小補”,無法顯示出決策者對問題嚴重性的擔憂,繼續拉低社會對未來的預期;十八屆三中全會展現出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心,但是現實中改革受阻,在需要擴大支持民營經濟及推進市場化進程的時間節點上,反而出現嚴重的“國進民退”現象。有人表示,當下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避免中國陷入像日本上世紀九十年代陷入的衰退,但是出于意識形態等原因,選擇維持現狀及現有道路,陷入“政策癱瘓”,更有甚者宣稱中國經濟已經“僵尸化”,成為“僵化的中央集權經濟”。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國商務和經濟學高級顧問兼主管甘思德(Scott Kennedy)表示,過去一年內他三次來華調研,最明顯的感受就是民營企業家和消費者信心嚴重衰退,并歸結于三點原因:
一是疫情防控過度,特別是2022年3月后上海嚴厲的“封城”措施嚴重影響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2022年底“清零”政策突然的停止更加重了大家的疑慮。二是近年來對民營企業,特別是科技企業的管制及打壓;“共同富裕”的提出也降低了部分企業家及投資者對未來發展的預期。三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敵對氛圍的提升,使得不少中國投資者、企業家對未來與西方科技、市場、資本的交流、流通和發展產生很大擔憂,拉低了國內外對中國發展前景的預期。他表示,民眾感覺國家在向錯誤的方向前進,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導致投資減少、存款增多;信心危機已成為限制中國經濟最重要因素。
敘事邏輯三:中國經濟疫情后反彈疲軟,令人大失所望,且中、美兩國后疫情時代預期與現實產生極大反差,盲目看好中國經濟前景缺乏事實依據。
該敘事邏輯認為,疫情期間,看衰美國經濟成為美國民眾、媒體和學者的常態,海內外反而對中國后疫情時代經濟反彈高速增長形成預期。而在“清零”時代結束后的2023年,中美兩國經濟數據現實與預期反轉:中國經濟經歷短暫復蘇后,陷入增長乏力困境,數據遠不如預期,美國反而并沒有進入被預測的衰退——雇傭需求強勁、高通脹壓力不再、股市反彈。疫情前多數人認為,中國GDP會很快超越美國,可近期數據顯示,中國與美國差距在加速拉大。不少金融機構、學者、媒體重新評估先前的預測,甚至開始認為中國在經濟總量上永遠不會超越美國,重蹈日本覆轍,或陷入比日本當年更大的危機。
彭博經濟(Bloomberg Economics)最新預測,中國經濟將在21世紀40年代中葉以小額差距,短暫超越美國,但將很快重新被美國超越,經濟增速在2050年降至約1%——中國將永遠無法坐穩世界最大經濟體寶座。其表示,疫情后反彈疲軟,反映了房地產市場的日益低迷及外界對北京管理經濟信心的流失;中國已經早于預期地進入了更低速的增長道路,因為信心問題或已造成了長期的不良影響。反觀疫情前,彭博經濟曾預測中國經濟最早或在2030年代初始就超越美國。
疫情后,不少媒體、學者明確表示,疫情期間對中國經濟過于樂觀的預期已被證偽,之前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一直持懷疑態度的觀察者也認為自己的觀點獲得了新的數據、事實支持。“新冠后遺癥”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恐成為常態。
敘事邏輯四:外部環境對中國極為不利,美國綜合實力依舊,將有效遏制中國發展。
該敘事邏輯認為,美國有得天獨厚的硬配置及軟實力優勢。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認為,在地理上,美國兩個鄰國都為友好的盟友,中國與14個國家接壤,且領土爭端頻發;能源上,美國為能源凈出口國,中國卻日益依賴能源進口;金融實力上,美國控制大型國際金融機構,美元霸權也難以撼動,中國政府對人民幣的控制使得其難以代替美元成為世界貨幣;人口紅利上,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已在2014年見頂,十年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9%,而美國將增加5%;社會文化上,美國雖有諸多不足之處,但依舊開放包容,憑借實力吸引全球精英人才,而在中國“潤”(“跑”的英文拼音Run)已經成為上流文化。
美國對華科技封鎖等措施,加上中國周邊國家(日、韓、印等)日益增長的敵意,美國及其盟友的全球霸權難以被撼動,西方將有效制衡中國持續崛起;中國當下激進的外交方式也將持續限制其發展前景。
近期更有評論者認為,中國經濟當下的問題,代表了“中國模式”(the China Model)優越論、“中國例外論”的終結。持此觀點者認為,若中國經濟就此放緩甚至陷入泥潭,那么中國雖然不大可能陷入真正的大危機,可以維持自我發展,但“中國模式”在國際上就失去了特殊的吸引力。沒有持續發展、經濟增長的硬事實,即印證的就是之前部分學者的預測——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不可持續,是內外特殊機遇期的導致的“奇跡”,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也不存在特殊的優越性及借鑒意義。這將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影響力和全球合作帶來新的挑戰。
“中國崛起頂峰論”的現實危害及影響
目前看來,西方政客、媒體、智庫形成的“中國崛起頂峰論”論調正在與國內部分輿情形成共振,并通過各種所謂“專家”“研究機構”的背書,企圖全方位抑制、挑撥、影響我國經濟、社會、民生等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危害:
第一,放大市場悲觀預期。2023年二季度,受外需放緩,樓市轉弱,以及市場預期不穩等因素影響,實際經濟復蘇動能有所放緩。華爾街金融機構多次下調中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期,從2023年7月份中國經濟最新數據來看,包括生產、消費、投資、出口在內的幾乎所有經濟指標的增速都出現下滑。
總之,當前中國經濟動力不足,有效需求面臨長期結構性失衡問題,三駕馬車放緩,不及潛在增速。在這樣的經濟表現下,消費者不愿花錢,企業不愿投資,也不愿意創造就業機會,加之創業人員的大幅減少,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的恢復。
恰在此時,外媒開始在國際上大肆宣揚“中國崛起頂峰論”,以看似合理的推論、數據,實際上確是帶有主觀性、片面性的惡意評論,企圖通過這樣的方式放大投資者、企業和消費者對中國經濟的悲觀預期,使其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乃至轉向絕望,進而影響中國的經濟恢復和就業。
中國“新三樣”出口遙遙領先
第二,影響外資對中國的判斷,降低外商投資中國的意愿。根據《跨國公司投資中國40年》報告數據,40年來,外商投資企業數量占全國企業總數的不到3%,卻貢獻了近一半的對外貿易、四分之一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值和利潤、五分之一的稅收收入,已成為中國開放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眾所周知,在經濟體量達到一定規模后再想取得高速增長難上加難,疊加三年疫情的“疤痕效應”遠未消退。在此背景下,外媒所宣揚的“中國崩潰論”就有了一定的市場空間,以部分事實加上錯誤的推論引導,以此影響外國投資者和跨國企業對中國市場的信心,導致他們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持謹慎態度。這可能會減少外國直接投資和跨國企業在中國的擴張,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最典型的后果就是短期內外資投資減少和資本外逃。
此外,輿論的放大效應疊加政治因素,也造成了已投外資的加速撤離。這發生在我國尚未完成產業升級和價值鏈向高端躍升的背景下,構成產業空心化的潛在風險。2022年初,佳能關閉了在珠海的工廠,結束了在中國的32年歷史,遣散了最后的1300名員工;蘋果正在把部分生產線從中國轉移到印度、越南、泰國、印尼等國家;耐克的供應商將生產設施轉移到東南亞和非洲;富士康在印度大建工廠并稱隨時隨地轉移生產基地,戴爾不再使用中國造芯片并揚言外遷等。
外企的撤離對我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首先勢必會減少就業機會,減少稅收。其次我國還屬于技術轉型和學習的階段,一些高科技巨頭企業的離開,也會影響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第三,刺激投資者情緒,導致股市劇烈波動。相比于海外多以機構投資者為主導的成熟市場,中國A股仍以散戶投資者為主。大多數散戶缺乏專業知識、投資經驗和技術不足,在投資過程中往往情緒化,容易受到市場波動和媒體炒作的影響,做出沖動的投資決策。
而近期西方政客、媒體與智庫正在全球范圍內宣揚“中國崛起頂峰論”等論調,瘋狂宣傳經濟困局,加之各種小作文、小道消息齊飛,不斷刺激股民的情緒,導致市場交易激增,板塊輪動加速,股市波動劇烈。大部分股民賺不到錢,影響其投資信心,或將導致其退出資本市場,進而造成連鎖反應,影響上市公司的融資計劃,沖擊實體經濟。
此外,2023年以來,美股、日股強勁上漲的背景下,A股市場長期低迷,充斥其間的大量的外國資本受各種中國崛起頂峰論的宣傳影響,造成中國資產沒有投資價值的誤判,導致資本加速逃離,尋求更安全的市場。
第四,刺激富人移民潮的高企。中國富人的移民潮不是從疫情大流行開始的,而是在過去10年中一直存在。在中國富豪群體中,不少人都是白手起家,他們對于財產的累積很重視。為了將利益最大化,部分人會選擇另辟蹊徑,將資產轉移到國外或者是在外面設立基金保住自己的利益。
隨著國內經濟增速的放緩,富人再難以像以前一樣依托各種紅利實現財富的快速增值,加之外媒大肆炒作“中國崛起頂峰論”,這可能導致大量富人在中國看不到財富增長的機會,從而攜帶大量資本移民國外,直接導致國內投資下滑,就業崗位減少等后果。
亨氏顧問公司把擁有超過一百萬美元可投資資產的富翁定義為高凈值人士。其中,中國預計將有1.35萬高凈值人士外流,是印度的兩倍。盡管中國估計有80多萬百萬富翁,1.35萬名占比很少,可以想象的是這種外流的趨勢還在增強。除了數千萬美元的財富從中國流失之外,高級管理人才也在外流,還會讓經濟增長減緩的情況進一步惡化。
第五,掩蓋中國經濟發展成果。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國崛起頂峰論”的論調掩蓋了個別部門、行業的亮眼表現,如盡管現階段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均出現了下滑,但是拉動外貿出口的“新三樣”卻組成了中國經濟新的名片,表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不斷涌現,為推動經濟持續恢復向好注入了信心和活力。
當前盛行的“中國崛起頂峰論”不僅忽視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也忽略了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遠遠超過以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對經濟的刺激這一基本邏輯,將可能導致其他國家對中國未來發展潛力形成偏見和誤解。
第六,擾亂民心影響國內團結,進而引發社會動蕩。外媒大肆宣揚“中國崛起頂峰論”的初衷,是要以信息戰的方式,散布錯誤信息、虛假信息,營造出一種國家沒有未來的假象,并通過挑起階級矛盾,引發各種對立情緒,從而讓民眾逐漸對國家的前途失去信心,最終就像蘇聯一樣,從內部瓦解,導致自我崩潰。
此外,本輪“中國崛起頂峰論”劍指中國決策層的誤判以及頂層設計的錯誤。更具危害性的是,長此以往會造成民眾對社會和政府部門信任感消弱,導致社會不安定、民眾情緒波動和社會矛盾加劇,進而對中國的社會秩序和穩定產生威脅。
第七,影響國家形象和國際地位。當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中國崛起頂峰論”的敘事邏輯則認為之前一直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模型和內外機遇不復存在也不可復制,未來經濟將面臨更大困難。如果外界普遍認可了這種觀點,可能導致人們對中國的認可和尊重減少,對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產生負面影響。
此外,有這種論調還可能會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合作產生負面影響。其他國家可能對中國的可靠性和穩定性產生質疑,直接弱化中國的國際吸引力,減少與中國的合作和交流,動搖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心,增加中國發展的國際成本。
作為“中國崩潰論”新時期變種,“中國崛起頂峰論”并不是什么新鮮觀點。正如前幾輪“中國崩潰論”偃旗息鼓那樣,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勁復蘇,體現于進一步趕超美國的逆襲之勢,是對“中國崛起頂峰論”打臉、讓其破產的最好方式。對此,堅持深化改革、全方位對外開放,聚焦于如何做大經濟蛋糕、提升民眾普遍收獲感的經濟政策,用靚麗的經濟數據表現來回擊,是讓“中國崛起頂峰論”的荒謬敘事徹底破產的根本辦法。
此輪“中國崛起頂峰論”明顯是配合美國對華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的新一輪輿論綜合攻勢,試圖干擾與打壓中國經濟增長勢頭,需要以“殲滅戰”的方式還以顏色。
要打好針對“中國崛起頂峰論”的輿論反擊戰,中國應有大手筆的投入。中外輿論戰,既是領導力之戰、思想力之戰,也是財力、定力之戰。面對此輪美國發動的“政治宣傳”攻勢,進行一波又一波反攻心戰、反圍剿戰,一定能為拉回中國經濟信心的國際社會預期做出實質貢獻。
來源:底線思維微信號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國策建言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