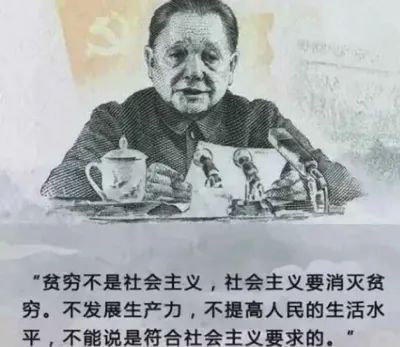改革的發(fā)展戰(zhàn)略邏輯與國企市場化改革中的邏輯問題
——從“貧窮不是社會(huì)主義”談起
摘要:貧窮不是社會(huì)主義造成的,改革開放前后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都將消除貧困作為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目標(biāo)。改革的邏輯內(nèi)生于國家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戰(zhàn)略的選擇。社會(huì)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的建立應(yīng)有助于消除相對貧困,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國有企業(yè)的市場化改革不能偏離自身使命性功能,提升國有企業(yè)的市場競爭力不等同于提升其利潤率。公有制經(jīng)濟(jì)在市場化生產(chǎn)中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是社會(huì)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改革成功的最終標(biāo)識。
一、對“貧窮不是社會(huì)主義”的演繹式新解
“貧窮不是社會(huì)主義”,這是改革開放之初全國人民最大的共識之一。然而,筆者在這里需要強(qiáng)調(diào),“貧困”這一概念在經(jīng)濟(jì)學(xué)中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絕對貧困”;二是“相對貧困”。對此,我們應(yīng)更加深入理解“貧窮不是社會(huì)主義”這句話中的“貧困”概念。
1988年5月25日,鄧小平在會(huì)見捷克斯洛伐克共產(chǎn)黨中央總書記雅克什時(shí)指出:“社會(huì)主義的特點(diǎn)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p.265)由此可清晰看到,“貧窮不是社會(huì)主義”對“貧困”概念的界定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基于此,我們可以先提煉出兩個(gè)尚不完備的命題,后文再對其進(jìn)行修正。
命題一:絕對貧困不是社會(huì)主義。
命題二:相對貧困也不是社會(huì)主義。
在經(jīng)濟(jì)學(xué)中,如果一項(xiàng)改革能夠帶來帕累托改進(jìn),就是一項(xiàng)合意的改革。綜合“命題一”和“命題二”可知,通過改革的方式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有著比帕累托改進(jìn)更高的標(biāo)準(zhǔn):依據(jù)“命題一”,當(dāng)改革消滅了絕對貧困,使所有人都更加富足時(shí),即達(dá)到了帕累托改進(jìn)的標(biāo)準(zhǔn);依據(jù)“命題二”,改革還應(yīng)當(dāng)最終消滅相對貧困,這是對完成什么樣的帕累托改進(jìn)所提出的要求,是基本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的標(biāo)準(zhǔn)。
通常認(rèn)為,改革開放前的絕對貧困是促成社會(huì)反思、凝聚改革共識、蓄積改革力量的重要因素。現(xiàn)在當(dāng)人們回想起“貧窮不是社會(huì)主義”這句話時(shí),腦海最先浮現(xiàn)的可能便是“絕對貧困”的場景。然而,如果改革即便完全消除“絕對貧困”,卻沒有消除“長期”且“嚴(yán)重”的“相對貧困”,由“命題二”可知,依然沒有成功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但是,由“命題一”,我們又很容易產(chǎn)生疑惑并進(jìn)行不恰當(dāng)?shù)耐普摚杭热辉?span lang="EN-US">1978年前的新中國國家建設(shè)過程中,在中國大地上出現(xiàn)了較普遍的絕對貧困現(xiàn)象,那么是否可判斷我們國家在當(dāng)時(shí)不是社會(huì)主義性質(zhì)的?答案當(dāng)然是否定的,即便在改革開放前新中國大地上出現(xiàn)過絕對貧困現(xiàn)象,我們國家也始終是社會(huì)主義性質(zhì)的。這是因?yàn)椋轮袊闪⒑蟮呢毨е饕怯晌覀儽池?fù)的貧困歷史包袱造成的。
為避免出現(xiàn)類似的由“命題一”導(dǎo)出的不恰當(dāng)推論,我們修正“命題一”,得到“命題三”:
“長期的絕對貧困不是社會(huì)主義,暫時(shí)的絕對貧困不能作為判斷社會(huì)性質(zhì)的依據(jù)”。
改革開放后的事實(shí),尤其是脫貧攻堅(jiān)的偉大勝利已經(jīng)證明,“改革開放前的絕對貧困是暫時(shí)的”。
相應(yīng)地,可以修正“命題二”,得到“命題四”:
“長期的相對貧困不是社會(huì)主義,暫時(shí)的相對貧困不能作為判斷社會(huì)性質(zhì)的依據(jù)”。
雖然當(dāng)前我國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依然存在相對貧困現(xiàn)象,但是我們國家的社會(huì)主義性質(zhì)決定了這種相對貧困應(yīng)當(dāng)是暫時(shí)的。我們要堅(jiān)信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在打贏扶貧攻堅(jiān)戰(zhàn)后,我們國家一定能扎實(shí)推動(dòng)共同富裕,不斷減少相對貧困、避免兩極分化。當(dāng)然,為保持國家的社會(huì)主義性質(zhì)不變,筑牢紅色江山,我們必須有效應(yīng)對來自內(nèi)部與外部的多種誘惑與挑戰(zhàn)。
二、改革內(nèi)生于國家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戰(zhàn)略選擇
在厘清上述較復(fù)雜的邏輯關(guān)系后,需要直面一個(gè)涉及改革對象與邏輯起點(diǎn)的問題:如果說新中國成立前的歷史包袱無可避免地使“絕對貧困”在新中國成立后暫時(shí)性延續(xù),那么就需要探討一個(gè)問題,即計(jì)劃經(jīng)濟(jì)制度本身是否是導(dǎo)致“絕對貧困”在新中國成立后延續(xù)的原因?
從學(xué)理性研究視角來看,這一問題意味著探究計(jì)劃經(jīng)濟(jì)制度與暫時(shí)性的絕對貧困現(xiàn)象之間“表面上”的因果關(guān)系,是否受到過于強(qiáng)調(diào)內(nèi)生變量的干擾,是否可能存在被遺漏的外生變量,同時(shí)導(dǎo)致計(jì)劃經(jīng)濟(jì)制度的選擇以及暫時(shí)性絕對貧困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
這類外生變量顯然是存在的。有學(xué)者就曾提出: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引致國防需求,迫使中國為加快重工業(yè)優(yōu)先的資源密集型的工業(yè)化進(jìn)程而選擇接受蘇聯(lián)援助,并向蘇聯(lián)學(xué)習(xí)建設(shè)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的經(jīng)驗(yàn)以管理這套工業(yè)經(jīng)濟(jì)體系;此外,蘇聯(lián)的工業(yè)援助不完全符合中國民用需求,這使工業(yè)化在提取勞動(dòng)剩余的同時(shí),對民用產(chǎn)業(yè)的正外部性補(bǔ)償在短期內(nèi)又難以顯現(xiàn),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就會(huì)有更明顯的“貧窮”感。[2](pp.163-164)在這一分析中,中國當(dāng)時(shí)的地緣政治環(huán)境正是這樣的外生變量。
上述分析雖然打破了從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到暫時(shí)性絕對貧困的直接因果鏈,但似乎將外因作為了主因。通常來說,內(nèi)因應(yīng)當(dāng)是主因。一個(gè)國家選擇怎樣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戰(zhàn)略,首要應(yīng)基于內(nèi)因。歷史上看,中國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戰(zhàn)略為:在推進(jìn)工業(yè)化初期階段,采用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在工業(yè)化中后期,采用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由于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和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不同的優(yōu)缺點(diǎn),[3]這種依據(jù)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不同階段而選擇與之相適應(yīng)的經(jīng)濟(jì)體制發(fā)展戰(zhàn)略,就是一種最優(yōu)戰(zhàn)略。
顯然,外因和內(nèi)因不是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外因?qū)?nèi)因的展開過程起加速作用。即使沒有外部嚴(yán)峻的地緣政治環(huán)境威脅,追求以工業(yè)化為關(guān)鍵特征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的新中國,只要選擇最優(yōu)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戰(zhàn)略,便會(huì)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前一階段選擇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并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nèi)“引致”國民經(jīng)濟(jì)中暫時(shí)性的絕對貧困。這是因?yàn)椋?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所擅長的生產(chǎn)建設(shè)場景是公共產(chǎn)品和準(zhǔn)公共產(chǎn)品生產(chǎn),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全國性交通工程等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這些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具有當(dāng)期投入大、收益低,但能在后期帶來持續(xù)性較高收益的特征。因此,這一時(shí)期的建設(shè)具有“為后人栽樹,讓后人乘涼”的性質(zhì)。
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下進(jìn)行的基礎(chǔ)性生產(chǎn)建設(shè),在為后期經(jīng)濟(jì)發(fā)展做好鋪墊的同時(shí),不得不使國民生活面對貧困問題。尤其是中國人民在這一階段不僅進(jìn)行了基礎(chǔ)設(shè)施生產(chǎn),還進(jìn)行了大規(guī)模的人口生產(chǎn),這也加劇了當(dāng)時(shí)的貧困,但同時(shí)為后一階段的經(jīng)濟(jì)騰飛蓄積了更多能量。簡言之,我們采取了“先苦后甜”式的符合中華民族優(yōu)良傳統(tǒng)道德價(jià)值取向的發(fā)展戰(zhàn)略。而在“苦”的階段,的確更需要一個(gè)具有凝聚力的政黨帶領(lǐng)全國人民共克時(shí)艱,中國共產(chǎn)黨以不斷的自我革命推動(dòng)偉大的社會(huì)革命,很好地完成了這一階段重要的歷史使命。在很大程度上,這一時(shí)期的勞動(dòng)人民也實(shí)現(xiàn)了“以苦為甜”的思想境界升華,這在根本上有助于保障隨后的市場化改革所導(dǎo)向的是社會(huì)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
至此可進(jìn)行初步總結(jié):雖然如今一些人可能會(huì)認(rèn)為“貧窮是促使改革發(fā)生的主因,貧窮也為改革凝聚了主觀共識,所謂‘不改革過不下去’”,但這只是一種表面化認(rèn)知。改革的邏輯起點(diǎn)并不能被歸結(jié)為暫時(shí)性的絕對貧困現(xiàn)象,并且這種現(xiàn)象的發(fā)生也并不能動(dòng)搖我們國家的社會(huì)主義性質(zhì)。改革,恰恰是由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的最優(yōu)發(fā)展戰(zhàn)略選擇所決定的;改革的對象是最優(yōu)發(fā)展戰(zhàn)略在前一階段所采用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目標(biāo)是實(shí)行社會(huì)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以更深入地執(zhí)行最優(yōu)發(fā)展戰(zhàn)略,推進(jìn)社會(huì)主義國家建設(shè)。由此,我們便可以水到渠成地得出一個(gè)重要的“命題五”:
“當(dāng)外生地選定了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國家的最優(yōu)發(fā)展戰(zhàn)略后,改革的發(fā)生就是內(nèi)生的,改革是必然的”。
“命題五”正是改革最基礎(chǔ)的邏輯起點(diǎn)。從這個(gè)邏輯出發(fā)就能在總體上比較順暢地理解為什么改革開放前后兩個(gè)階段不能互相否定。[4]改革的邏輯蘊(yùn)藏辯證法。如果依照前述表面化認(rèn)知,改革的發(fā)生就會(huì)被形式化地簡單理解為對改革前某種狀態(tài)的否定,這的確是一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見識。
三、市場化改革進(jìn)程中的相對貧困問題
前述討論重點(diǎn)在于改革的邏輯起點(diǎn)不是改革前的貧困問題,改革是內(nèi)生于國家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戰(zhàn)略的選擇。那么在改革后,我們應(yīng)當(dāng)如何看待市場化進(jìn)程中的相對貧困問題?
1978年以來的改革實(shí)踐是從推行農(nóng)村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開始的,通常認(rèn)為這種包干制改革解放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但在不解除人地關(guān)系緊張的自然約束或技術(shù)約束條件的情景下,難以想象僅靠這種制度安排就能使廣大農(nóng)民過上富裕生活。歷史實(shí)踐也證實(shí)了這種判斷,即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可以解決農(nóng)民的絕對貧困問題、實(shí)現(xiàn)溫飽,卻不足以解決相對貧困問題,在市場化改革進(jìn)程中,城鄉(xiāng)差距變大,農(nóng)村內(nèi)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變大了。在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被解散的同時(shí),也有很多城市國有企業(yè)與村鎮(zhèn)集體企業(yè)在市場化改革進(jìn)程中消失甚至轉(zhuǎn)變?yōu)槎喾N所有制企業(yè),這使貧富分化發(fā)生在一個(gè)更高位上。
因此,對于戰(zhàn)勝相對貧困,我們既要堅(jiān)定信心,又不能掉以輕心。
首先,依據(jù)“命題四”,只要我們國家的社會(huì)主義性質(zhì)不變,這種相對貧困就只能是暫時(shí)的。改革開放總設(shè)計(jì)師鄧小平提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最終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的偉大戰(zhàn)略構(gòu)想。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一部分人已經(jīng)先富起來,然而收入分配差距也急劇上升,相對貧困問題尤為嚴(yán)重。國外學(xué)者的研究可以做一定的參考,從1978年到2015年,占國民收入前10%人口的累計(jì)收入占國民收入總額的比例由27%上升到41%,與此同時(shí),占國民收入后50%人口的累計(jì)收入占國民收入總額的比例由27%下降到15%;這意味著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從曾經(jīng)具有“平均主義”傾向的情形快速上升到接近美國的水平。①
在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取得全面勝利、絕對貧困完全消滅后,“先富帶后富”將逐漸成為新發(fā)展階段的主旋律,這是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事實(shí)上,早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鄧小平就對解決貧富分化問題的時(shí)間點(diǎn)選擇提出過設(shè)想——“在本世紀(jì)末達(dá)到小康水平的時(shí)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gè)問題”。[1](p.374)
其次,相對貧困是一個(gè)自發(fā)產(chǎn)生的現(xiàn)象。鄧小平明確指出過“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shí)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xiàn)”。[5](p.1364)依據(jù)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學(xué)中效用論的相關(guān)研究,人們對相對消費(fèi)地位的追求是微觀經(jīng)濟(jì)行為的主要?jiǎng)訖C(jī)之一,被稱為“追趕瓊斯”效應(yīng),這也是經(jīng)濟(jì)活力的重要來源。市場經(jīng)濟(jì)制度能夠充分釋放這種活力,使人們追求相對消費(fèi)地位的動(dòng)機(jī)成為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引擎,具有積極意義。而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我們所追求的共同富裕也絕不是平均主義。
最后,如果說在改革初期,市場機(jī)制與微觀主體追求相對消費(fèi)地位動(dòng)機(jī)的結(jié)合是生產(chǎn)“建設(shè)性”的,那么當(dāng)貧富差距達(dá)到臨界值時(shí),這種結(jié)合則可能是生產(chǎn)“破壞性”的;臨界值的存在就意味著收入分配差距不能過小,也不能過大。當(dāng)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超過臨界值時(shí),相對貧困問題便產(chǎn)生。而微觀主體追求相對消費(fèi)地位的動(dòng)機(jī)由貧富差距較小時(shí)具有生產(chǎn)“建設(shè)性”轉(zhuǎn)變?yōu)樨毟徊罹噍^大時(shí)具有生產(chǎn)“破壞性”,則與非公市場主體的狹隘性相關(guān)。
微觀主體追求相對消費(fèi)地位的動(dòng)機(jī)滿足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自己創(chuàng)造并獲得更多的價(jià)值,二是阻止他人獲得價(jià)值。顯然被阻止獲得價(jià)值的人群的勞動(dòng)積極性與創(chuàng)造性會(huì)大幅下降,這在宏觀上造成了對生產(chǎn)能力的“破壞”。而當(dāng)存在持續(xù)的較大貧富差距時(shí),“先富者”可以積累較多的生產(chǎn)資料形成資本,獲得相對于作為勞動(dòng)力的“先貧者”的談判優(yōu)勢,從而繼續(xù)擴(kuò)大貧富差距,形成正反饋的惡性循環(huán)。發(fā)達(dá)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和現(xiàn)狀已經(jīng)證明,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無法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更不是適宜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的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形式。在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條件下,容易出現(xiàn)先富者阻礙后來者致富的不良情景。這種情景與在博弈論中已得到廣泛研究的“在位者障礙”的不同之處在于:博弈論研究的是市場競爭中的“在位者為后進(jìn)入者設(shè)置障礙”,屬于橫向的生產(chǎn)資料所有者之間的競爭,這在大部分情景中屬于可接受的市場行為;而本文討論的“先富壓制后富”,則屬于縱向的生產(chǎn)資料所有者與勞動(dòng)者之間不和諧的緊張關(guān)系,勞動(dòng)者通過勤勞致富的可能性降低,社會(huì)階層間的流動(dòng)性被削弱。顯然,社會(huì)階層間流動(dòng)性的減小,削弱了微觀經(jīng)濟(jì)主體的主觀動(dòng)能,降低了經(jīng)濟(jì)活力,繼而在宏觀上使?jié)撛诮?jīng)濟(jì)增速放緩。
2015年1月,《人民日報(bào)》刊載文章《不讓平均數(shù)掩蓋大多數(shù)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6]當(dāng)日,多家媒體對該文以《一些貧者從暫時(shí)貧困走向跨代貧窮》為標(biāo)題加以轉(zhuǎn)載。既然我們建設(shè)的是社會(huì)主義,那絕不允許在中國大地上,相對貧困普遍地由暫時(shí)性轉(zhuǎn)變?yōu)槌掷m(xù)性,特別是代際持續(xù)。
四、市場化改革進(jìn)程中的國企問題
宏觀層面的改革邏輯需要通過微觀主體的操作執(zhí)行才能被貫徹。前述分析已經(jīng)表明:包括民營企業(yè)在內(nèi)的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很難成為在長期過程中消除相對貧困的主要依靠力量。此時(shí),在社會(huì)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長期改革過程中,消除相對貧困的主責(zé)便落在了以國有企業(yè)為主體的公有制經(jīng)濟(jì)上。
然而,在我國市場化改革進(jìn)程中(尤其是早期),有種思潮認(rèn)為,作為改革對象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是與國有企業(yè)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的,中國的國有企業(yè)承載著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因而有觀點(diǎn)認(rèn)為: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導(dǎo)致貧困的具體執(zhí)行單元正是包括國有企業(yè)在內(nèi)的公有制經(jīng)濟(jì)成分,國有企業(yè)生產(chǎn)效率較低,難以提升生產(chǎn)效率,難以實(shí)現(xiàn)“致富”目標(biāo)。這種觀點(diǎn)暗含了一種假設(shè):國有與集體經(jīng)濟(jì)成分不宜采取市場化競爭機(jī)制。否則,改革的重點(diǎn)應(yīng)是使國有企業(yè)從適應(yīng)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轉(zhuǎn)向適應(yīng)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這種暗含假設(shè)的論證往往借用西方公司金融研究中的委托代理理論。這種論證的缺陷正在于“理性人假設(shè)”,②而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理論構(gòu)建中,人最根本的屬性是社會(huì)性。人的社會(huì)性存在削弱了委托代理問題的嚴(yán)重性,當(dāng)然削弱的程度存在多重均衡態(tài),這取決于具體社會(huì)制度構(gòu)建方式。③人的社會(huì)性是天然的,人具有集體生活的內(nèi)在需要,這種需要促使人建設(shè)并維護(hù)集體,在集體生活中實(shí)現(xiàn)個(gè)人自由。反過來說,對人的社會(huì)性的破壞,就會(huì)加劇委托代理問題。因此,當(dāng)私有化意識形態(tài)發(fā)展到一種異化模態(tài)時(shí),人際互信遭受嚴(yán)重?fù)p害,各類隱性交易成本急劇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國有企業(yè)的管理與生產(chǎn)效率會(huì)下降,而且民營企業(yè)的管理運(yùn)營成本也會(huì)上升。改革開放之初,有論者依據(jù)所謂“所有者缺位”理論,判定“國有企業(yè)內(nèi)的委托代理問題比民營企業(yè)更加嚴(yán)重”。而如今,發(fā)展壯大起來的民營企業(yè)呈現(xiàn)的內(nèi)部治理問題(包括貪腐),可能已經(jīng)說明:在其他影響因素接近的條件下,相較于所有制差異,企業(yè)規(guī)模對委托代理問題程度的影響應(yīng)該更大。在企業(yè)規(guī)模相同的情況下,尚無充分的實(shí)證材料能說明國有企業(yè)中的委托代理問題一定比民營企業(yè)嚴(yán)重。與此相關(guān),國有企業(yè)在市場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中的發(fā)展壯大也提供了與這一判定相反的證據(jù)。
然而,國有與集體經(jīng)濟(jì)成分不宜采取市場化競爭機(jī)制的觀點(diǎn),卻在改革的初始化進(jìn)程中產(chǎn)生了影響,事實(shí)上為國有資產(chǎn)的不合理流失提供了理論辯護(hù),集體經(jīng)濟(jì)的力量也相對削弱。在“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中,“放”并不等同于“放任”國有資產(chǎn)流失,即便這個(gè)國有或集體企業(yè)的規(guī)模相對較小。那些不合適、過分的“放”,恰恰削弱了人的社會(huì)性,過分地把人推向自利性的價(jià)值取向,為后來較嚴(yán)重的相對貧困埋下了隱患,在整體上不利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削弱潛在經(jīng)濟(jì)增長動(dòng)力。這也是反身性原理在社會(huì)運(yùn)行中的具體體現(xiàn)。如果改革被誤導(dǎo)走上“國有企業(yè)私有化”軌道,那么國有企業(yè)的確會(huì)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愈加不利的地位,相關(guān)思潮觀點(diǎn)所引導(dǎo)的預(yù)期便完成“自我實(shí)現(xiàn)”。國有企業(yè)的行為表現(xiàn)不應(yīng)被“孤立”觀察,而應(yīng)被置于與特定意識形態(tài)場域的關(guān)聯(lián)中。要理解國有企業(yè),并正確引導(dǎo)國有企業(yè)改革,我們還應(yīng)當(dāng)回到科學(xué)社會(huì)主義原理層面。
五、從科學(xué)社會(huì)主義原理看國有企業(yè)的使命性功能
解決企業(yè)經(jīng)營中的委托代理問題,最終目標(biāo)當(dāng)然是提升企業(yè)的市場競爭力。企業(yè)在市場競爭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高利潤率來體現(xiàn)的。然而,我們必須明確:高利潤率與強(qiáng)企業(yè)競爭力并不等價(jià)。這也可以成為區(qū)分社會(huì)主義企業(yè)和資本主義企業(yè)的關(guān)鍵:資本主義企業(yè)的直接目標(biāo)是追逐利潤,被迫通過提高生產(chǎn)率來提升企業(yè)競爭力;社會(huì)主義企業(yè)的直接目標(biāo)是提高生產(chǎn)率、提升企業(yè)競爭力,以提高利潤為中間手段。這就說明存在這樣的情況:如果一個(gè)社會(huì)主義企業(yè)通過其他非“利潤激勵(lì)”方式提高了生產(chǎn)率,強(qiáng)化了企業(yè)產(chǎn)品的市場競爭力后,并非一定要利用優(yōu)勢地位“攫取”高額利潤。
問題在于,利潤激勵(lì)是否是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有效激勵(lì)方式,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人的非異化自然狀態(tài)下,每個(gè)生產(chǎn)者是有“做好事情本身”的內(nèi)在激勵(lì)的,這是一種生命力的自然展現(xiàn),例如北京大學(xué)青年數(shù)學(xué)家韋東奕的事例。只是在資本主義邏輯的支配下,利潤目標(biāo)上升到“第一位”,勞動(dòng)者在這樣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體系下也被異化,勞動(dòng)從人的屬性式“需要”異化為人所逃避的“苦役”。從這個(gè)意義上說,以中國國有企業(yè)為代表的社會(huì)主義企業(yè)的歷史使命在于實(shí)現(xiàn)企業(yè)的解放,探索企業(yè)如何擺脫“利潤”與“行政指令”等外在的潛在異化體系來直接實(shí)現(xiàn)生產(chǎn)目的,最終解放人,讓“勞動(dòng)”回歸人的本能屬性。國有企業(yè)的最終目標(biāo)是成為“自由人的聯(lián)合體”的微觀單元;或者說國有企業(yè)是向“自由人聯(lián)合體”單元的過渡形態(tài),是人不斷增強(qiáng)的社會(huì)性在生產(chǎn)領(lǐng)域中得以呈現(xiàn)的載體。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前,我們以行政權(quán)力為工具初步建成國有企業(yè),實(shí)現(xiàn)了勞動(dòng)者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的生產(chǎn)和社會(huì)聯(lián)合,那么,國有企業(yè)的市場化改革理應(yīng)能促進(jìn)勞動(dòng)者在更大范圍和更高程度上的生產(chǎn)和社會(huì)聯(lián)合。
這就從科學(xué)社會(huì)主義原理出發(fā)說明了國有企業(yè)的功能必然不同于私有企業(yè),國有企業(yè)需要發(fā)揮自身特殊功能以完成其歷史使命。國有企業(yè)中的管理勞動(dòng)者和直接生產(chǎn)勞動(dòng)者都應(yīng)處于更加“解放”的狀態(tài)、更加“安全”的心理狀態(tài),更不容易為金錢和權(quán)力所異化。而國有企業(yè)能夠在社會(hu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最終取代私有企業(yè),是以其市場競爭力為基礎(chǔ)的。這種競爭力正確的體現(xiàn)方式應(yīng)是:國有企業(yè)能夠在實(shí)現(xiàn)對勞動(dòng)者更大程度“解放”的情況下保持競爭力。
如果國有企業(yè)為了保持市場競爭力,對待勞動(dòng)者的方式與私有企業(yè)類似,那么這種競爭力就仍陷于資本主義邏輯,并不能引發(fā)勞動(dòng)者內(nèi)心的情感認(rèn)同。我們提高國有企業(yè)的市場競爭力當(dāng)然是要服務(wù)于發(fā)展完善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的大目標(biāo),不能南轅北轍。國有企業(yè)對勞動(dòng)者的解放正是通過自身特殊功能來實(shí)現(xiàn)的,例如提供更穩(wěn)定的職業(yè)前景(曾被詬病為“鐵飯碗”)、更周全的福利保障(曾被詬病為“企業(yè)辦社會(huì)”)和更強(qiáng)的集體歸屬感(“愛廠如家”的主人翁意識曾較為普遍,而非“打工人”的自我定位)。當(dāng)然,此處羅列的國有企業(yè)特殊功能只是微觀層面的,國有企業(yè)的宏觀功能則體現(xiàn)為依照宏觀調(diào)控部門的逆經(jīng)濟(jì)周期政策而進(jìn)行的產(chǎn)能調(diào)節(jié)。顯然,民營企業(yè)的生產(chǎn)行為更具有順經(jīng)濟(jì)周期性。正因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在宏微觀功能上存在差異,如果像主流經(jīng)濟(jì)學(xué)那樣主要用利潤率高低來衡量國有企業(yè)的競爭力,則類似用小轎車的速度標(biāo)準(zhǔn)來評價(jià)拖拉機(jī)。反過來說,如果民營企業(yè)不能在某一評價(jià)維度(如利潤)上表現(xiàn)出一定優(yōu)勢,那么就不能體現(xiàn)競爭力了。這也意味著市場化條件下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應(yīng)當(dāng)具有不同的競爭力評價(jià)標(biāo)準(zhǔn)。“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當(dāng)然,在社會(huì)主義初級階段,國有企業(yè)也要考慮利潤,這也是為了對國有企業(yè)進(jìn)行財(cái)務(wù)“硬約束”。
在原則上,只要國有企業(yè)履行好其使命性功能,那么在市場化條件下就能有效承擔(dān)起在長期過程中消除相對貧困的中堅(jiān)力量的角色。然而,實(shí)踐中有些具體的改革措施及其理念,存在著使國有企業(yè)偏離其使命性功能的傾向。
六、利潤激勵(lì)的前提條件與國有企業(yè)改革中的邏輯悖論
從廣義上說,無論對于國有企業(yè)還是民營企業(yè),提高利潤率都應(yīng)是在履行好企業(yè)職責(zé)與實(shí)現(xiàn)好企業(yè)功能的前提條件下進(jìn)行的。在滿足“前提條件”的情況下,利潤率提高表征了競爭力的良性增強(qiáng),而如果為了提高利潤率而破壞“前提條件”,則最多實(shí)現(xiàn)短期競爭力的惡性增強(qiáng),且不可持續(xù)。
例如,如果一個(gè)在國內(nèi)擁有市場壟斷地位的民營企業(yè)通過降低產(chǎn)品質(zhì)量來提高利潤,則必然受到懲罰,因?yàn)檫@種高利潤不代表企業(yè)競爭能力的健康提升,且損害消費(fèi)者利益。以這種方式進(jìn)行市場競爭或保持市場地位的民營企業(yè),違背了保證產(chǎn)品質(zhì)量的企業(yè)職責(zé)。如果長期任由這種企業(yè)行為發(fā)生,則市場必然崩潰(劣幣驅(qū)逐良幣的最終結(jié)果)。
如果同樣的情況發(fā)生于國有企業(yè),則社會(huì)必然承受代價(jià),引發(fā)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以外的危機(jī)。遺憾的是,有些以市場化之名作用于國有企業(yè)的改革措施實(shí)有違背“前提條件”的嫌疑。國有企業(yè)市場化改革的目標(biāo)不應(yīng)也不可能是將國有企業(yè)變得與民營企業(yè)相同。如僅按照利潤導(dǎo)向標(biāo)準(zhǔn)對國有企業(yè)進(jìn)行市場化改革,與其說是“深化國有企業(yè)改革”,不如說是對國有企業(yè)“去神留形”。而除去特殊功能后的國有企業(yè)確實(shí)在企業(yè)行為上與民營企業(yè)相似,國有企業(yè)的順周期行為顯著增加,甚至在充當(dāng)?shù)胤秸谫Y平臺和扮演影子銀行的過程中“助推”了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的累積。因此,進(jìn)一步地,這樣“去神留形”的國有企業(yè)必然被資本化。事實(shí)上,為資本設(shè)置“紅綠燈”的監(jiān)管指向也包括國有資本,而防止國有資本“闖紅燈”的重要方式就是讓國有資本以國有企業(yè)的實(shí)體經(jīng)濟(jì)形態(tài)存在,切實(shí)履行體現(xiàn)社會(huì)主義本質(zhì)要求的宏微觀特殊功能。
事實(shí)上,當(dāng)前以市場化之名作用于國有企業(yè)的改革措施還存在邏輯悖論。例如,“國有企業(yè)辦社會(huì)”被長期視為歷史遺留問題,是國有企業(yè)改革中的所謂“硬骨頭”。國有企業(yè)“辦社會(huì)”的特殊功能之所以被視為“問題”“沉重包袱”,正是因?yàn)閺囊岳麧櫬屎饬扛偁幜Φ膯我凰季S出發(fā),把不同功能的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拉入同一“賽道”,從而得出“辦社會(huì)”功能使得國有企業(yè)不能與民營企業(yè)“公平”競爭的結(jié)論。然而,如果“辦社會(huì)”功能降低了國有企業(yè)的利潤率,使得國有企業(yè)不能與民營企業(yè)“公平”競爭,那么國有企業(yè)執(zhí)行政府的宏觀調(diào)控政策(無論社會(huì)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也會(huì)降低其利潤率。難道國有企業(yè)還要將宏觀調(diào)控功能也視為應(yīng)甩掉的“包袱”?這顯然是不能的,否則國有企業(yè)存在的合理性就被大大削弱了。這也說明:以提高利潤率增加競爭力為由,來除去國有企業(yè)“辦社會(huì)”功能,是不能成立的。
類似的,如果將“辦社會(huì)”視為政府的職能,而國有企業(yè)“辦社會(huì)”則是“政企不分”的表現(xiàn),那為什么國有企業(yè)執(zhí)行政府的宏觀調(diào)整政策就不被視為“政企不分”?這同樣說明當(dāng)前國有企業(yè)改革思路中存在邏輯悖論。
悖論的癥結(jié)正在于沒有認(rèn)清國有企業(yè)功能本就應(yīng)不同于民營企業(yè)的客觀事實(shí)。國有企業(yè)市場化改革應(yīng)向民營企業(yè)學(xué)習(xí)適應(yīng)市場的經(jīng)驗(yàn),但這絕不意味著將國有企業(yè)改造成國家控股的“大號”民營企業(yè)。習(xí)近平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7](p.500)在市場不能或不宜起作用的地方,政府往往通過國有企業(yè)的特殊功能來發(fā)揮作用,國有企業(yè)市場化改革絕不能把國有企業(yè)不同于民營企業(yè)的功能給改沒了。我國國有企業(yè)必須是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經(jīng)濟(jì)的“頂梁柱”,而不能成為其他主義的“頂梁柱”。
本文從對貧困與社會(huì)主義間關(guān)系的分析切入,說明貧困并非改革的邏輯起點(diǎn),改革是內(nèi)生于國家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戰(zhàn)略選擇的。然而,改革必須直面貧困問題的解決,以在長期過程中消除相對貧困,促進(jìn)共同富裕的實(shí)現(xiàn)。對此,筆者認(rèn)為需要強(qiáng)調(diào)以下三點(diǎn):
第一,改革的主要對象是發(fā)展社會(huì)主義國家的經(jīng)濟(jì)手段與方式,其在邏輯上與社會(huì)主義國家的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并無必然聯(lián)系。將市場化改革與生產(chǎn)資料私有化等同起來是一種有影響力的錯(cuò)誤思潮。當(dāng)然,為了利用市場經(jīng)濟(jì)這種手段與方式,我們可以合理利用多種所有制經(jīng)濟(jì),這也是改革的歷史進(jìn)程中辯證思維的體現(xiàn),改革的最終目的當(dāng)然是實(shí)現(xiàn)全民福利最大化,并使全民共享經(jīng)濟(jì)發(fā)展福利,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
第二,即便改革的對象是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也不意味著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可以在經(jīng)濟(jì)運(yùn)行過程中完全退出。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和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的有機(jī)結(jié)合與平衡運(yùn)用,在社會(huì)主義初級階段可能發(fā)揮出比單一經(jīng)濟(jì)體制更好的效果。這是因?yàn)榧词乖诟母锖螅?jīng)濟(jì)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也需要基礎(chǔ)設(shè)施不斷更新與升級,這意味著計(jì)劃手段依然有其效力空間。
第三,公有制經(jīng)濟(jì)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消除相對貧困的主責(zé),國有企業(yè)的使命性功能在于促進(jìn)勞動(dòng)者的“解放”。國有企業(yè)市場化改革的目標(biāo)在于提升企業(yè)競爭力,但這種競爭力不能被狹隘地理解為利潤率。我們應(yīng)當(dāng)吸取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更具創(chuàng)造性地探索公有制經(jīng)濟(jì)與市場化機(jī)制的有效結(jié)合方式。尤其是當(dāng)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多種所有制經(jīng)濟(jì)成分對生產(chǎn)的促進(jìn)作用下降時(shí),我們更應(yīng)大力發(fā)展公有制經(jīng)濟(jì),有效實(shí)現(xiàn)先富帶后富,促進(jìn)中國經(jīng)濟(jì)高質(zhì)量發(fā)展。
至此,可總結(jié)出全文最重要的結(jié)論——“三步走”最優(yōu)發(fā)展戰(zhàn)略:
第一階段,以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為主導(dǎo),進(jìn)行經(jīng)濟(jì)體系的基礎(chǔ)建設(shè),帶有暫時(shí)性絕對貧困的特征;
第二階段,開啟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的改革,利用多種所有制經(jīng)濟(jì)成分的積極性作用建設(shè)市場機(jī)制,帶有暫時(shí)性相對貧困的特征;
第三階段,開啟市場經(jīng)濟(jì)主體的改革,讓公有制經(jīng)濟(jì)在市場化生產(chǎn)中發(fā)揮主導(dǎo)作用,消滅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實(shí)現(xiàn)“先富帶后富,最終走向共同富裕”的歷史性偉大規(guī)劃。
作者:于鴻君,北京大學(xué)教授;吳文,北京大學(xué)習(xí)近平新時(shí)代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本文原載《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2年第8期
參考文獻(xiàn):
[1]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溫鐵軍.三農(nóng)問題與制度變遷[M].北京:中國經(jīng)濟(jì)出版社,2009.
[3]于鴻君.中國經(jīng)濟(jì)體制的選擇邏輯及其在全球化新時(shí)代的意義[J].世界社會(huì)主義研究,2018,(6).
[4]習(xí)近平.關(guān)于堅(jiān)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的幾個(gè)問題[J].求是,2019,(7).
[5]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 .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04.
[6]不讓平均數(shù)掩蓋大多數(shù) 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N].人民日報(bào),2015-01-23.
[7]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xiàn)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14.
注釋:
①參見Piketty,Thomas and Yang,Li and Zucman:Gabriel,Capital Accumulation,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1978—2015(April 2017),NBER Working Paper No. w23368。
②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界也意識到“理性人假設(shè)”的缺陷,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并發(fā)展出了行為經(jīng)濟(jì)(金融)學(xué),但是這種理論構(gòu)建使得其喪失了原本尚具有的“整體性”。
③區(qū)塊鏈也是一種削弱委托代理問題的局部的社會(huì)制度構(gòu)建場景,在數(shù)字技術(shù)開發(fā)中融入對人的社會(huì)屬性的考量。
來源:世界社會(huì)主義研究微信號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gè)人觀點(diǎn),不代表本站觀點(diǎn),僅供大家學(xué)習(xí)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wǎng)站,如涉及版權(quán)和名譽(yù)問題,請及時(shí)與本站聯(lián)系,我們將及時(shí)做相應(yīng)處理;
3、歡迎各位網(wǎng)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wǎng),依法守規(guī),IP可查。
作者 相關(guān)信息
于鴻君 吳文:公有制經(jīng)濟(jì)是否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決
2022-11-23內(nèi)容 相關(guān)信息
于鴻君 吳文:公有制經(jīng)濟(jì)是否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決定了改革成敗
2022-11-23李慎明:任何想把公有制或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否定掉的觀點(diǎn)都是錯(cuò)誤的
2016-04-26?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wù) 新前景 ?

? 國策建言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qū)建設(shè) ?

? 黨要管黨 從嚴(yán)治黨 ?

 李歡龍:石家莊“試驗(yàn)”失敗,又一次突然轉(zhuǎn)向!說明什么?
李歡龍:石家莊“試驗(yàn)”失敗,又一次突然轉(zhuǎn)向!說明什么? 此輪軍改被譽(yù)為“史上最牛軍改”,一文帶你了解都改了哪些東西
此輪軍改被譽(yù)為“史上最牛軍改”,一文帶你了解都改了哪些東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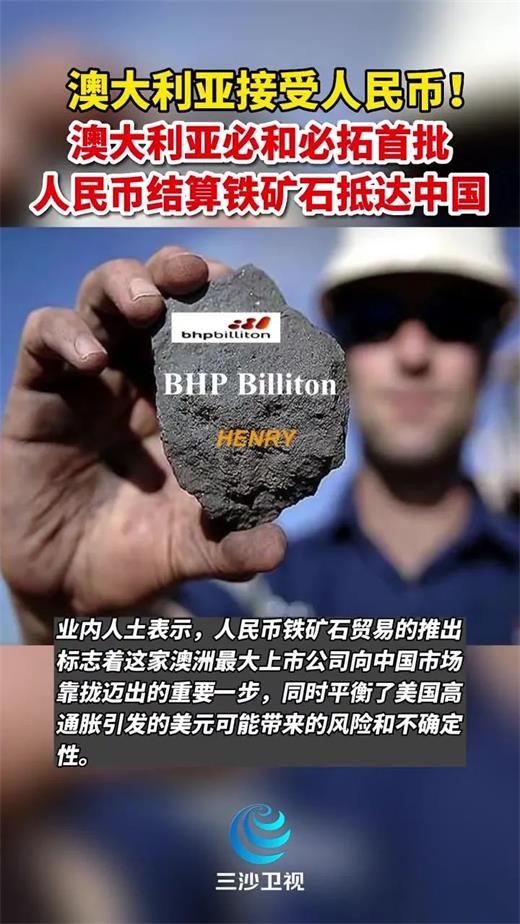 鐵礦石商全部投共,天地改換!
鐵礦石商全部投共,天地改換!
 黃衛(wèi)東:?應(yīng)對核戰(zhàn)等導(dǎo)致氣候?yàn)?zāi)難的對策
黃衛(wèi)東:?應(yīng)對核戰(zhàn)等導(dǎo)致氣候?yàn)?zāi)難的對策 秦安:股市暴跌!三大原因,兩個(gè)跡象,說明我們必須要打好金融戰(zhàn)
秦安:股市暴跌!三大原因,兩個(gè)跡象,說明我們必須要打好金融戰(zhàn) 習(xí)五一:互聯(lián)網(wǎng)管理規(guī)則應(yīng)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
習(xí)五一:互聯(lián)網(wǎng)管理規(guī)則應(yīng)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 社會(huì)調(diào)查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