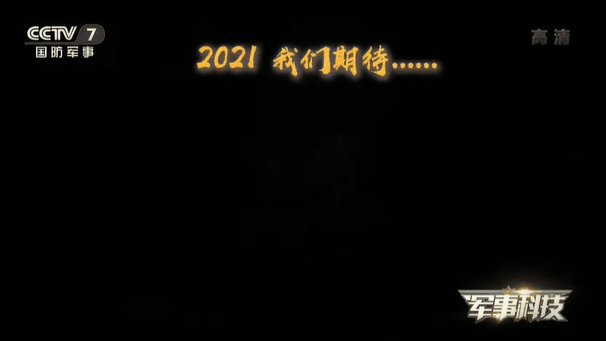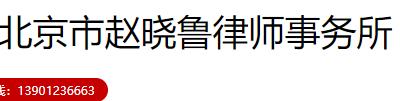長征中著名的“遵義會議”后,黨中央率中央紅軍原擬執行北渡長江計劃,但因川軍的堵截,計劃受挫,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向川滇黔邊地域轉移。在轉移途中的1935年2月3日~8日,又召開了一個被稱作“雞鳴三省會議”的重要會議。這次會議目前有一些爭議,筆者根據掌握的史料對這些問題作出了相應的辯析,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雞鳴三省”會議的召開時間和決定的事宜
目前史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延續,解決了遵義會議已決和待決、以及根據會議精神需要貫徹和落實的有關事宜。但對會議的日程界定和解決的問題,尚沒有比較明確和一致的意見。一般的看法主要是根據有關人士的回憶而集中在所謂“博古交權”[]的問題上,時間段也集中在一兩天的會議上。
筆者認為,這種界定過于狹義,而且未必嚴謹也未必準確。關于會議的若干界定,應該以遵義會議尚未決定或雖已決定但急需重新審議的問題為依據。比如,遵義會議雖然選出了新的政治局常委,但尚未進行具體分工;新舊領導子尚未進行工作移交;遵義會議決定的“北渡長江計劃”在受到挫折后急需重新審議;遵義會議的精神尚未向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項英、陳毅等領導同志傳達;遵義會議上委托張聞天起草的《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還未經政治局審議通過……
綜合各種史料,筆者認為,“雞鳴三省會議”決定了如下重大事宜:
⒈完成了領導班子的交接和分工
這個問題基本上沒有異議: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原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向新的總負責人張聞天移交作;新當選的政治局常委進行了分工,毛澤東成為“恩來同志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⒉經討論,向中央蘇區發出“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的指示。[]
⒊經討論,決定了改變遵義會議決定的“北渡長江計劃”,改取“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并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的新方針[]。
⒋經討論,通過了遵義會議委托張聞天起草的《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
除此之外,這次會議應該還討論了派人去白恢復工作并重新打通與共產國際聯系的問題,而這個使命,被委托給了潘漢年。
“雞鳴三省會議”結束的標志有二:
⒈1935年2月7日19時簽發的《中革軍委關于我軍改為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的方針給各軍團的指示,這個指示正式決定改變“北渡長江計劃”,改取“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并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的新方針[];
⒉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
如此或可判定,軍委縱隊進駐川境內的石廂子的1935年2月3日,到通過《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的2月8日,會議前后持續了6天。
2月9日,軍委縱隊移至扎西。當日,中央負責人在扎西老街江西會館繼續開會。但這次會議已屬于“扎西會議”的范疇。在這次會議上,政治局再次審議了“雞鳴三省會議”(滇境內石坎子召開)上剛決定的“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并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的新方針,對該方針中“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再度作出改變,決定采納毛澤東的意見,放棄經鎮雄入滇作戰的計劃,“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準備與薛岳兵團及黔敵為主要作戰目標”[]。
二、“雞鳴三省”會議召開的地點
這個問題,目前川、滇、黔三省各執一詞,各自都在自己認為是“雞鳴三省”的位置刊碑,建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迄今仍是相持不下。一件原本應該很嚴肅的認定工作,變成了各省的利益和名份之爭,真是令人扼腕蹉嘆!
目前三省各自刊碑且各執一辭的“雞鳴三省”的位置為:
⒈四川省瀘州市敘永縣石廂子(今石壩鄉政府所在地);
⒉云南省昭通市威信縣水田鄉水田村花房子(亦稱花屋子);
⒊貴州省畢節市林口鎮老鷹巖山崖邊(現在叫“雞鳴三省”村)。
三個省的有關部門各有各的理由,都能說出一堆道理來。
但筆者認為,要弄清這個問題,恐怕先得確定軍委縱隊在這段時間里的日程。
這個問題,最有證據效力的,應該是軍委有關行動部署和行軍日程的電報。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這些部署文電(從1935年2月2日~2月8日)
2月2日,朱德、周恩來關于2月3日行動部署給軍委縱隊指定的目的地是“石鄉子”:“軍委縱隊進到石鄉子”[];2月3日19時,朱德總司令作出的4日行動部署中為軍委縱隊指定的目的地是“水潦地域”[]。但當日22時即作出改變:“軍委縱隊明日仍在石廂子不動,準備開水田寨、扎西之間的地域”[];2月4日23時30分,朱德總司令作出的5日行動部署中為軍委縱隊指定的目的地是“水田寨”(即滇鏡內“花房子”所在地):“軍委縱隊應進到水田寨宿營”[];2月5日21時30分,朱德總司令在致紅一軍軍團長林彪電中稱:“軍委一梯隊今到滇境之水田寨”[];2月6日22時,朱德總司令在致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電中稱:“野戰軍司令部今晚宿營石坎子附近,明七日進至扎西”[];2月7日凌晨4時,朱德總司令在當日行動部署電中稱:“軍委在大河灘”[]。當日19時,朱德總司令作出8日行動部署中為軍委縱隊指定的目的地為“院子街”:“軍委縱隊經大河灘進至院子地域”[];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院子街通過《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
時任軍委三局政治委員的伍云甫日記可資佐證——通訊部門肯定隨中央和軍委行動。
二月二日 陰
由(八時)馬碲灘經張家壩、海螺鋪、千水橋,到達摩坭宿營(二十三點三十分到達)。越六座高山。(約八十里)
二月三日 晴
由達摩坭經安吉亭、樂洼溝,到石鄉子宿營,沒收彭姓土豪。(是日即舊歷除夕日——三十日)
二月四日 陰
駐石相子。
二月五日 晴
由石相子出發,經水田寨,團匪據炮摟二座擾亂,繞山道,至花屋子宿營,路甚難行(3里路行了約三小時),二十三時半才到。與二科合住房子。
二月六日 晴
由花屋子出發,至石坎子。出處炮樓內尚有土豪及武裝。據說,愿出款子,承認條件,只要不收槍。
二月七日 陰
駐石坎子街上,司令部駐莊子內,相距約五里路。是日下午,參加無線電營排長以上干部會。
二月八日 陰
由石坎子出發,經大河灘遏通信教導隊,取裝發報機的材料,至院子街上宿營(行程約三十里)。石痕調二科。[]
這個行軍日程為:摩坭——石廂子——水田寨——石坎子——大河灘——院子街,這條行軍軌跡,不經過黔省境內。倘無特珠及意外情況,中央及軍委,也不可能在行軍途中,轉到另一方向黔省境內的林口地域去開會——而且還要過赤水河。
鑒此,“雞鳴三省”會議在黔省境內召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值得注意的是,軍委縱隊在石廂子住了兩個晚上,這除了召開重要會議的需要外,很難有其他解釋。所以,“雞鳴三省”會議始于川境內的石廂子,可能性最大!但筆者同時也認為,這個會議是一個在行軍中持續召開的會議,在滇境內的花房子、石坎子、院子街,一直都在召開,直至2月8日(當天通過《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所以,可以這么認為:“雞鳴三省會議”從川境內的石廂子召開,持續了一個白天和兩個晚上,解決了一些當務之急的重要問題(如領導班子的移交手續,對常委作出分工等)。爾后,又在向滇境轉移途中,在滇境內的花房子、石坎子、大河灘、院子街持續召開,直至確立新的戰略方針和通過遵義會議《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
筆者認為:“雞鳴三省會議”是一個行軍移動中不斷召開的會議,會議從川境內的石廂子開始,爾后又在滇境內的花房子、石坎子、院子街持續召開,直至2月8日在滇境的院子街通過《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為止,前后持續了6天。川滇兩省不必為名份過多計較,在各自的紀念地刊碑時,可稱“雞鳴三省會議”石廂子會址,花房子會址,石坎子會址,大河灘會址,院子街會址。不必過份強調各自地域的標識。
三、“雞鳴三省會議”后潘漢年受領的特珠使命
關于潘漢年的這個特殊使命,《潘漢年傳(修訂版)》記載如下:
大約是在遵義會議之后一個月左右,部隊正在川滇交界處活動。有一天,張聞天找到潘漢年,代表中央和他談話:
“中央研究決定,讓你和陳云同志一起離開部隊到白區去,在上海長期埋伏,并設法打通上海和共產國際的關系。我們現在和國際的聯系電臺早已中斷了。你知道,我們對國際的聯系是至關重要的。你們如在上海聯系不上,就得設法到莫斯科去。總之,應當盡快地和國際打通聯絡線,向國際報告遵義會議的結果以及紅軍的近況。”
張聞天還說,遵義會議后,考慮到今后的軍事行動將更為艱難和嚴峻,中央曾考慮將黨中央機構轉移到南洋地區去活動。但沒有決定下來。現在派陳云和你先出去,就是要使黨中央保持著和國際國內的有效聯系,不致被長久地隔絕在邊遠、閉塞地區。
陳云也和潘漢年談了話,他們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時期已經有過很好的合作,彼此都很了解和信賴。陳云對潘漢年說,我們這次要分開走,中央決定你先行一步,到上海之后我們再設法會合。[]
“遵義會議之后一個月左右”即是1935年2月中旬,也就是“雞鳴三省”會議之后。
4個月后的6月20日,已在香港的潘漢年得悉了中央紅軍已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消息后,給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發出過一封信,信中對其所負使命,作出了更為明確和具體的詳陳:
中央認為,共產國際與國統區黨以及與[中共]中央之間這樣長時間地失去聯系會給工作帶來重大損失。如果有可能恢復這種聯系的話,那就應該立即這樣做。為此目的,我們受派遣來執行以下任務:
⒈我隨身攜帶了進行無線電聯系所必需的呼叫信號、波長和時段,應該直接同共產國際代表取得聯系,以設法恢復無線電聯系。[中共]中央制定的措施是:
⑴請你們為我們安排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無線電聯系。
⑵設立直接聯系的單獨電臺。他們不想讓我直接同中共上海中央局建立聯系,因為我們認為,既然中共上海中央局遭破壞,其內部必有暗藏的叛徒。如果我們先找到[共產國際]代表,那么地下工作將會更有保證。但這次我先找到了新的上海局,還沒有同你們見面。
⒉在同你們見面后,我應在適當地區[不一定在上海]建立穩定的聯絡點,同時建立同四川南部的信使聯系。[中共]中央看到中共上海中央局不斷遭到破壞和國統區群眾斗爭領導薄弱,決定加強領導。同時[中共]中央新的負責同志——波克利洛夫(他的中文名字叫張聞天)和陳云認為,鑒于紅軍進行長期行軍和長期內戰,同軍隊一起轉移的[中共]中央無力領導全國的工作,應該改變自己的領導方法。因此,他們要求我們同你們會面并討論這個問題。如果你們同意,我將在某些合適的地區設立代理人機構以做好準備工作,同時建立電臺和同川南的信使聯系。在我離開[中共]中央前往上海之前,曾專門派出一名同志去建立聯系,由于該同志到上海后先同中共上海中央局會了面,我也就同該局聯系上了。
我從[中共]中央出發前,黨已決定在云貴川邊區建立根據地。我出發后,看來,因為局勢發生變化他們放棄了原來的計劃。他們渡過金沙江同紅四[方面]軍會合了。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再次討論是否應該改變領導方法的問題。[]
這個陳述,與《潘漢年傳(修訂本)》中:“張聞天還說,遵義會議后,考慮到今后的軍事行動將更為艱難和嚴峻,中央曾考慮將黨中央機構轉移到南洋地區去活動。但沒有決定下來”,是有相當的互洽性的。之所以要潘漢年與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會面并討論這個問題”,一則是因為“茲事體大”,需要得到共產國際方面的首肯;二則,很可能是因此當時的中共中央決策層,也并未就此取得一致意見(沒有決定下來!)——所以潘漢年才在信中陳述了自己的基本任務后,將“中央負責同志”的意見單獨列出。而且還提出:“這種情況下,必須再次討論是否應該改變領導方法的問題”。
至于潘漢年是否如提議的那樣,與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見面并“再次計論”了這個問題,討論的結果是什么?目前筆者還沒有查證到更多的資料。不過可以確證的是:此后的中共中央,并沒有“改變領導方法”,而是繼續“同軍隊一起轉移”并領導全國工作。中央紅軍到達瀘定后的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正式決定派陳云去上海恢復黨的組織[]。陳云離開部隊后,于當年7月上旬安全抵達上海,在與正在香港的潘漢年取得聯系,于7月下旬在上海會面。[]爾后又先后去了蘇聯。
陳云和潘漢年見面后是否討論過“改變領導方法的問題”?他們先后到達蘇聯后,是否與共產國際方面討論過這個問題?目前仍然沒有足夠的史料可以說明。但中共中央長征到達陜北并與共產國際方面溝通了聯系后,這個“改變領導方法的問題”再也沒有提出討論過,則是不爭的事實。
那么這個事實意味著什么呢?
意味著毛澤東的軍事領導能力和地位,在當時尚未得到政治局成員心悅誠服的一致認同與確認,不少人對毛澤東等是否能帶領中央紅軍擺脫困境還缺乏足夠的信心,乃至于對“與軍隊一起轉移的”中共中央能否有效的領導全國工作還缺乏足夠的信心,對曾經遭受過重挫造成了極大損失的城市領導方式,尚有留戀或期盼。
四、回顧與反思
在遵義會議后的首戰——土城戰斗失利后,中央紅軍面臨著極其困難極其危險的處境:在敵人重兵的圍追堵截下,被迫在無根據地無后方的條件下,在沒有工作基礎的區域進行大幅度的機動和作戰。中央紅軍前途難卜,生機渺茫,乃至于在“雞鳴三省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新的負責同志”還不得不考慮如何應對最壞的情況。潘漢年的這個“使命外的使命”,實際上就是為中共中央在面臨“最壞的情況”時,“準備后路”!
也就是說,對毛澤東等開始擔負起的軍事領導責任,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信心的。既或是在中共中央新的領導集團和新的領導人中,也不是從一開始,就對“毛主席來掌舵”的前景充滿了信心。
“農村包圍城市”的大戰略,不僅僅是一個戰略問題,還是一個“領導工作方式”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在這個問題上,是走過不少彎路的,是得過不少教訓的——而且是血淋淋的教訓。黨中央在白色恐怖下的城市“領導全國工作”,那就只能是在“地下”而不能搬上地面。即或是在“中國工人階級發祥地”上海,號稱“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的中央,也得面對“空有十萬產業工人”彼此遇有危難卻彼此指望不上的尷尬局面。象“武裝保衛蘇聯”的“飛行集會”、“紅隊鋤奸”這種在街面兒上打打殺殺的“革命斗爭”,城市普通群眾并不了解甚至反感:看不出這種跟黑社會互相仇殺一個模樣的“斗爭”,跟自己打工掙錢養家糊口的生活有什么關系……
而且,這種“領導方式”,牽一發而動全身,動不動就要被敵人逼上走投無路不得不硬著頭皮去作“一家哭還是一路哭”的兩難選擇。比如被時人和后人們炒作得沸沸揚揚“顧順章滅門事件”,就是這種“城市領導方式”一個具體的惡果:要么吞咽“濫殺無辜”的苦果,忍受時人和后人來自人性高度的傲岸遣責,要么就承受被敵人順滕摸瓜一網打盡的結果……
而“農村領導方式”就大不一樣了:有土地革命的旗幟,有保護群眾和革命政權的軍隊,得到了實際利益的群眾知道這“革命”跟自己有啥關系,那些要來撲滅革命的人又跟自己有啥關系,殺土豪殺劣紳殺敵人那是人人都拍手稱快,敵人軍隊來“圍剿”了老百姓知道該幫哪邊。共產黨人有了武裝有了隊伍可以找準機會去繳敵人的槍,共產黨人有了政權有了群眾那就是站在地面上的“合法政權”,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也指得上,相互之間那是可以依賴也可以指望的……
既或是后來降格成為配合“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城市秘密工作”,汲取了教訓的中國共產黨人也作出了很大的改變,如不搞“紅隊”式的暗殺和“鋤奸”,不搞“美人計”,工作重點放在工運農運商運學運兵運上,注重在城市群眾中擴大黨的影響和同情面,地面上的斗爭也是以經濟斗爭為主或者以經濟斗爭的面目出現……
從“雞鳴三省會議”,到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沖過大渡河與紅四方面軍實現會師,實際上是一個重大選擇的重大轉折的樞紐。“雞鳴三省會議”后潘漢年所擔負的特殊使命中反映出來的疑惑和擔憂,以紅一、四方面軍實現會合為標志,得到了很好的回答!
我們還有理由認為:遵義會議后擔負起了實際軍事領導責任的人,已經在環境的重壓和對手的鍛擊下,通過了自己戰友和同志們各種懷疑和挑剔眼光的考量!而這樣的考量,幾無從中作弊弄巧行“弓弦”走捷徑的可能!
作者:雙石 來源:雙石茶社微信號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