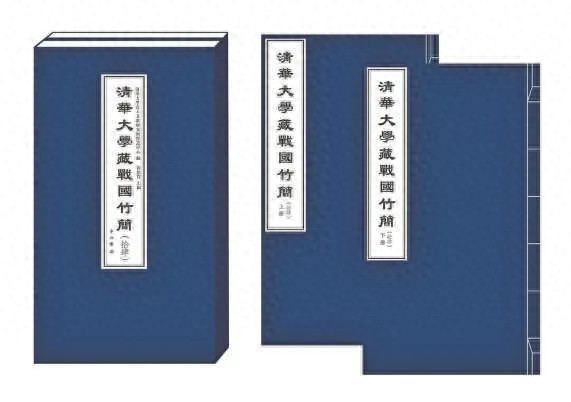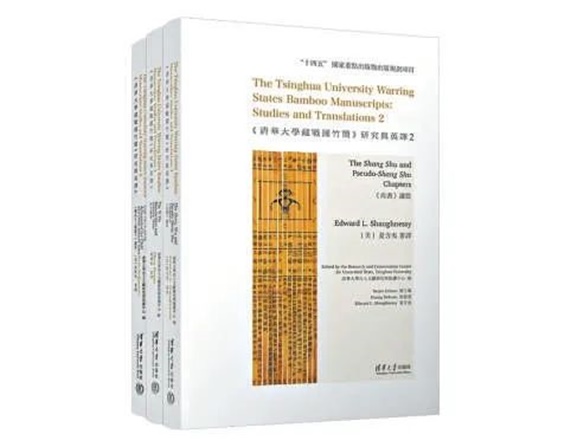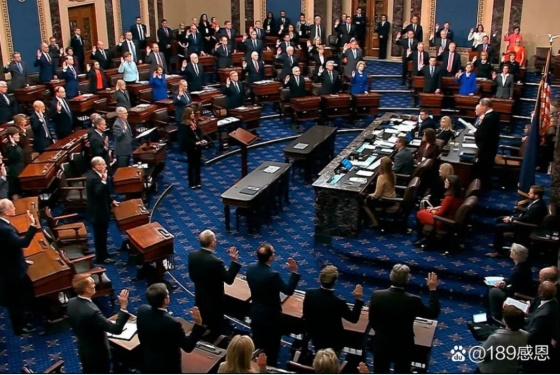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17日-星期四
2006年,一批兩千多年前的竹簡在香港神秘現身。然而,撲朔迷離的身世,假簡橫行的市場,讓它的命運一度危在旦夕。歷經波折之時,這批司馬遷也沒看過的典籍,幸運地遇到了“國寶級”學者李學勤。
千年竹簡入藏百年清華,冥冥之中找到了最好的歸宿。2500枚逃過秦火的歷史“碎片”得以復原,隨著十四輯整理報告陸續公布,清華簡顛覆的歷史越來越多:忠臣表率周文王竟早有滅商之心?烽火戲諸侯根本不存在?“臥薪嘗膽”另有新解……
曾經的“冷門絕學”被看見,然而,對于“簡帛圈”外的大眾而言,“高大上”的清華簡何以震撼?它重現了多少古書,重建了哪些古史?很多人可能不甚了了,甚至面對網絡上所謂的清華簡“真偽之爭”人云亦云。
今年4月,清華簡將再次走出國門,向全世界展示中國古代文明的璀璨光芒。最晚到明年,清華簡的全部整理工作也將完成。走近清華簡,還有很多值得講述的新故事。
2024年年底,清華簡公布了最新的第十四輯整理報告。
傳奇:司馬遷也沒見過的典籍
清華簡的入藏,緣于一次“大佬的飯局”。在《清華簡與古代文明》的課堂上,每每說起清華簡的傳奇身世,授課老師程浩總會講起這個故事。
2008年6月的一天,為歡迎中華書局原總編輯傅璇琮到校任教,清華大學校領導出面宴請,并特邀楊振寧夫婦和李學勤夫婦作陪。楊振寧作為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自然無需多言。李學勤早年就讀于清華,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用當下流行的說法,他堪稱一位“六邊形戰士”,在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等領域都造詣深厚。
上世紀70年代,在沙灘紅樓,李學勤(右一)參與了馬王堆漢墓帛書、定縣漢簡、睡虎地秦簡等多批簡帛資料的整理研究工作。
賓主暢談之時,李學勤提到了一件事:曾有人在香港見到一批流散的竹簡,盡管內容和年代尚不詳,但可能有重要價值。校領導問:“您能否用最簡潔的話概括一下這批竹簡的意義?”李學勤回答:“如果是真的,那就是連司馬遷也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
校領導聞言,頓覺此事重大,當機立斷——竹簡真偽,由李學勤來調查,是否購買,由學校來決策。
其實,在此之前,李學勤已經聽聞這批竹簡的消息。同樣是在一個飯局上,不過這次做東的是李學勤,客人則是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張光裕。在清華大學熙春園,兩位老友邊吃邊談,張光裕不經意間透露了一個重磅消息,繼上博簡后,香港又發現了秦、楚竹書。
張光裕口中的“上博簡”,即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這批竹簡的回歸,正是得益于他的敏銳與推動。1994年,在香港古玩市場,張光裕偶然見到浸泡在泥漿與濁水中的竹簡時,一眼認出上面的楚文字“周公曰”。他強壓住內心的激動,一邊不動聲色地與古玩商周旋,摹寫、考辨竹簡內容,一邊迅速聯系時任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最終,成就了一樁文物搶救與回歸的美談。
時隔十多年,香港市場再現珍貴竹書,不能不令人激動。但竹簡的具體情況如何,誰也不清楚。直到2006年年底,神秘的竹簡才初露真容。彼時,200余位學者齊聚香港,為慶祝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一眾老先生中,時年37歲的劉國忠還是青年一輩。他對那次研討會最深的印象是,“規模太大了,大得合影都不好拍,只能分批一撥一撥跟饒先生合影。”事后,他才后知后覺地發現,熱鬧的會議間隙,還有一件即將影響海內外學術界的大事正在發生——張光裕帶著幾位老友,悄悄去看了那批神秘竹簡。這其中,就有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的陳松長教授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李均明研究員。
不看不知道,原來神秘的竹簡竟有兩批:一批楚簡,一批秦簡。面對珍貴的竹簡實物,兩位老先生既感到心痛,又難掩激動。經多方努力,岳麓書院成功購回了價格相對較低的秦簡,這就是后來蜚聲海內外的岳麓秦簡。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原本有意收購楚簡,卻因種種原因未能如愿。于是,這批竹簡只能繼續流散于市場,處境岌岌可危。
普通讀者可能意識不到竹簡的脆弱性。竹簡一旦出土,如果沒有加以科學保護,很快就會滋生霉菌,這些霉菌甚至可能徹底毀掉保存了兩千年的竹簡。事實上,陳松長曾在訪談中披露,岳麓秦簡被購回前,“簡牘上已經有霉斑的痕跡,狀況很不樂觀”。
幸好,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危在旦夕的竹簡遇到了“國寶級”學者李學勤。在為岳麓秦簡擔任專家鑒定組組長時,岳麓書院的老師告訴他,香港古董商手中還有另外一批戰國簡。聯想到當年張光裕在熙春園所說,李學勤幾乎憑著直覺意識到,這批竹簡非同尋常。
然而,竹簡畢竟是因盜掘而重見天日,具體的出土時間和地點已無從考證。況且,彼時的香港文物市場假簡橫行,誰也不敢貿然出手購買這么大一批竹簡。即便是李學勤,也必須慎之又慎。
2008年6月,得到校領導委托的第二天,他找到了學術圈內流傳的8支樣簡照片。8支簡全部由戰國時期的楚文字書寫,其中一支簡的內容讓他大吃一驚,“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
“仇”,在這里的讀音念“qiú”,是晉文侯的名字。這個字的楚文字字形很特別,沒有深入研究的人根本不可能知道這種寫法。劉國忠是李學勤的弟子,自2008年起,一直跟隨老師研究清華簡,如今已是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主任。他向記者解釋:“這支簡說的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兩周之際,惠王被晉文侯仇殺于虢國。這一事件只在已經失傳的古本《竹書紀年》中有過記載,《史記》等其他古籍根本沒有提及。”
一個生僻的楚字,一段失傳的古史,都在告訴李學勤,這極有可能是真正的戰國竹簡。
事不宜遲,7月9日,李學勤專門去了一趟香港。穩妥起見,他特邀李均明研究員同行,然后在張光裕的陪同下,一起去觀摩竹簡實物。三位大咖意見一致,但為確保萬無一失,清華還是與古董商特別約定:先把竹簡交給清華,待確認全部為真之后,再付款購買;如果是假,清華可以把竹簡退回,不必付款。
一個星期后的7月15日,正值酷暑難耐的夏日,中午1點,劉國忠跟隨老師李學勤在清華圖書館老館靜靜等待。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這批竹簡終于從香港遠道而來——它們先是搭乘飛機,后又轉乘專車,風塵仆仆地抵達清華。從那一刻起,這批歷經波折的無名竹簡擁有了一個顯赫的名字——清華簡。
驚險:半天時間就能爛個小洞
清華簡入藏那天,暑假已經開始,老師們原本打算先對竹簡進行基本維護,等到秋季開學再正式清洗整理。
7月16日,劉國忠去檢查竹簡,一切看上去還算正常,與剛到時沒什么區別。然而,到了17日,他只看了一眼,就“感覺有點不太好”——竹簡表面的一些白色粉狀物似乎變多了,而且顏色變得更白。他立刻打電話給李學勤,并向學校匯報。
清華的效率相當高,當天就安排實驗人員,提取、檢測浸泡竹簡的液體。果然,白色粉狀物就是活體霉菌。為什么竹簡這么快就出現了霉菌?原來,這批竹簡屬于濕簡,出土后必須保持濕潤狀態。為此,古董商將竹簡連同濕泥用保鮮膜層層包裹,浸泡在了化學溶液中。
在地下水里泡了2000多年的竹簡是什么樣子?劉國忠打了個比方:“就跟開水里煮過的面條一樣,軟綿綿的,稍微碰一下就斷了、碎了。”古董商顯然也看到了這一點,但他們要兜售竹簡,就得向人展示。于是,他們自作聰明地在一些竹簡下面墊上新鮮竹片,再拿保鮮膜一裹,兩頭纏上透明膠帶。殊不知,這些簡單粗暴的“保護”措施,卻讓清華簡陷入了更大的危險——未經殺菌的新鮮竹片,成了微生物滋生的溫床。
“這太可怕了。”李學勤生前為學生講課時,回憶初見清華簡的情形,難掩心痛,“過去曾有過慘痛的教訓——半天時間,霉菌就能把竹簡爛出個小洞!”
搶救性保護刻不容緩,一場團體作戰迅速開始:去掉保鮮膜、去污、殺菌、重新浸泡……正值北京奧運會前夕,首都的安保工作前所未有地嚴格,偏偏清華簡的搶救急需各種化學藥品和器材,清華文科建設處的老師只能到處“刷臉”、找人幫忙。
竹簡尺寸特殊,需要一些特別尺寸的托盤來盛放,什么樣的托盤既環保、安全又耐用?情急之下,老師們靈機一動,從廣東定做了一批類似食堂盛菜用的平底盤,只是尺寸稍有不同,總算解了燃眉之急。“文物保護工作經常這樣就地取材。”在《清華簡與古代文明》課堂上,看到熟悉的平底盤,同學們忍俊不禁,程浩老師笑著解釋,“沒辦法,我們需要的器材量太小,經費又不多,沒有廠家愿意批量生產。”
清洗整理后的清華簡
李學勤年事已高,眼睛不好,手也容易抖,直接上手“搶救”竹簡的,除了最年輕的劉國忠,還有兩位外援——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李均明、趙桂芳夫婦。兩位老師一個專注研究,一個側重保護,兩人親眼見過、親手摸過的簡牘,估計是全國最多的。唯獨戰國簡,兩人一直沒機會參與整理。收到李學勤的邀請,這對剛剛退休的學術伉儷無縫銜接新工作,恨不得天天“長”在清華簡的庫房里。
整整三個月,李學勤幾乎每天都騎著自行車,直奔清華圖書館老館,了解清華簡的搶救性保護工作進展。在頂樓的一間彌漫著刺鼻化學氣味的房間里,李均明、趙桂芳、劉國忠三人小組用最細最軟的毛筆,輕輕除去竹簡表面的污物。第一次跟著李均明老師學習除污,劉國忠戲稱自己是“張飛繡花”,遇到頑固污物,一天只能清污一枚簡。見多識廣的李均明反倒一臉興奮,“這不正好說明簡是真的,有誰能造假造出幾千年前的污垢?”
當所有的搶救工作告一段落,緊繃許久的身心稍微放松,大家才感到一絲后怕:如果這些竹簡再流散幾個月,滋生的霉菌可能就會吞噬掉所有的竹簡,我們就再也看不到這批無價之寶了。
疑案:曠世之爭畫上句號
與老師李學勤相比,第一次見到清華簡的劉國忠,內心更多的是好奇。他研究過帛書,讀過上博簡,但見到觸手可及的竹簡實物,還是頭一回。對于清華簡中能發現什么內容,他起初有點將信將疑。然而,作為最早參與保護整理工作的成員之一,他很快體會到了老師內心的激動和震撼。
清華簡初期整理研究團隊,更像一個臨時的課題組。
8月13日,李均明和劉國忠正在清洗竹簡,一支簡背上的四個字躍入眼簾——“尃敚之命”。竹簡背面通常是沒有字的,這四個字很可能是文章的篇題。這會是一篇什么樣的文獻呢?劉國忠趕緊打電話報告,聞訊趕來的李學勤一看,激動不已,當即認出竹簡上的楚文字“尃敚”二字,就是“傅說(yuè)”。
傅說,商王武丁的賢臣,殷商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在中學語文課本中,我們都讀過有關他的故事,“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間”。傅說與舜并列,被孟子視為“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勵志榜樣。
不過,身為歷史學家的李學勤,看到這個名字,想到的卻是一樁關于《尚書》的千古疑案。他說,《傅說之命》就是傳世古文《尚書》中的《說命》。
眾所周知,《尚書》是古代科舉必讀的四書五經之一,內容多為上古時代國君的文告,以及君臣的談話記錄等,堪稱歷代帝王的教科書。
相傳,《尚書》是孔子編輯的。孔子周游列國,始終不得志,晚年干脆回到家鄉,轉型當了一個好編輯。他認認真真挑選了一百篇古代經典,整理成了百篇《尚書》。可惜,孔子精心編輯的經典問世之后,卻命途多舛。
先是秦始皇焚書,民間私藏的《詩》《書》等都要交出來集中燒毀。幸好,一位名叫伏生的博士,把自己那套《尚書》偷偷藏了起來。秦末大亂,至西漢初年,伏生藏匿的百篇《尚書》只殘留28篇。用漢代通行的隸書加以整理寫定后,成了后人口中的“今文《尚書》”。
悄悄藏書的不只伏生。面對焚書令,孔子的后人想了一個妙計,他們把《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藏在了老宅的墻壁里。按說這樣隱秘的地點應該天衣無縫,誰知遇到一個愛好營建宮室的奇葩鄰居。這位鄰居是漢景帝的兒子魯恭王,魯恭王是個結巴,不善言辭,下令拆毀孔子老宅時卻干脆利落。
被王國維譽為中國學問上三大發現之一的“孔壁中經”,就這樣在魯恭王“強拆”孔子故居時,重見天日。這批古籍用秦漢以前的文字書寫,相比隸書,算是“古文”,因此被稱為“古文《尚書》”。
令人唏噓的是,意外現身的古文《尚書》,又在魏晉時期毀于戰火。今天,我們能看到的通行《尚書》版本,源自東晉的一名官員梅賾。梅賾獻給朝廷的這版《尚書》共有58篇,其中今文《尚書》33篇是對伏生的傳本進行分合而成;而古文《尚書》25篇的來歷就有點撲朔迷離了,據說源自孔壁中經。然而,究竟是真是假,自宋代以后,學問官司就沒斷過,就連朱熹也半信半疑。到了清代,古文《尚書》前已經被不少學者加上了一個“偽”字。
不過,質疑也好,辨偽也罷,學者們都是基于學理論證,畢竟沒有真憑實據。正因如此,重新發現一本早期《尚書》的寫本,幾乎成了中國歷史學家們的一種情結。古代史大家張政烺先生,就經常不無遺憾地說,要是什么時候能夠挖出《尚書》就好了。
張政烺2005年辭世,他生前肯定想不到,僅僅三年后,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古文《尚書》,果真在清華簡中被發現了。
原本的奢望在不經意間變成了現實,李學勤對《傅說之命》的解釋,讓大家都興奮不已。劉國忠告訴記者,隨后幾天,他們又陸續清洗出一些《傅說之命》篇的竹簡,將竹簡與傳世的《國語》等先秦典籍相關引文對比,果然一字不差。
隨著進一步釋讀,大家愈發欣喜,清華簡《傅說之命》和梅賾古文《尚書》中的《說命》完全是兩回事兒。前者講了商王武丁依據天命尋找賢臣傅說,并讓他努力輔佐自己治理國家,后者卻是傅說對武丁進言治國之道。
有意思的是,二者也有一些相似的話語,但說話的主語卻不同。比如,《傅說之命》中有些傅說的話,在《說命》中卻被安在了武丁頭上。看來,“古人造假也不是憑空想象,很可能是根據傳世的一些引文,加以擴充,編出了新文章。”劉國忠說。
當然,這樣判斷的前提是,清華簡的確書寫于戰國時期。
2008年10月14日,在清華大學主樓的一間會議室,11位國內文字、考古、歷史學方面的頂級專家共同出具了一份《鑒定意見》,“從竹簡形制和文字看,鑒定組認為這批竹簡應是楚地出土的戰國時代簡冊”。
一個多月后,碳十四年代測定結果出爐,與專家們的判定完全一致,竹簡抄寫年代大致為公元前335年到公元前275年之間,相當于戰國中期的后半段,也就是孟子、莊子、屈原等先哲們生活的年代。
真偽已辨,一位清華校友個人出資,慷慨買下這批竹簡,并無償捐贈給學校。這樣的結果也意味著,早于秦始皇焚書、失傳2000余年的《尚書》,如今就在我們眼前。而一千多年來關于古文《尚書》的曠世之爭也畫上了句號,怎不令人欣喜異常?
爆料:周文王早有滅商之心?
2009年3月,清華簡的釋讀工作正式開始。年代久遠的楚文字很難釋讀,有時一個字就要考釋幾年,可想而知,釋讀進度并不會很快。即便如此,不斷出現的驚人發現,還是讓李學勤感嘆,“清華簡的內容讓人讀起來太激動,一天之內不能看太多,否則會讓人心臟受不了。”
此言不虛,清華簡的“爆料”著實有點多。在很多人印象中,商周之際的周文王,絕對是一位堪稱表率的忠臣。尤其是小說《封神演義》中,文王彌留之際,還不忘叮囑姜子牙切不可“以臣伐君”,告誡兒子姬發忠君愛民,哪怕紂王殘暴無道,也要恪守其職。
但在清華簡中,周文王遺囑《保訓》開篇五個字,便是“惟王五十年”。劉國忠告訴記者,第一次看到這支簡時,李學勤也沒敢往周文王身上想。畢竟,周文王在位時并未滅商,他的身份還是商的“西伯”。可是,周代各王中好像并沒有剛好在位五十年的,這里的“王”會是誰呢?騎著自行車回家的路上,李學勤思來想去,最終的答案還是指向了周文王。
清華簡中竟然有周文王的遺囑?劉國忠不敢想象,但新的證據很快出現了。28.5厘米的特殊長度(大部分竹簡為46厘米),帶點美術字風格的字體,這些典籍特征幫助大家很快找全了這篇文章的11支簡。通讀全文,這位王在說話中提到了“發”——周武王的名字。直接稱呼周武王名字的人,自然正是周文王。
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經稱王,從古以來就是一樁聚訟不已的歷史公案。孔子把周文王視為“至德”之人,因此宋朝之后的儒家學者都極力否認文王稱王。在他們看來,商朝還存在的情況下,若周文王敢自稱為王,無異于以下犯上。但唐朝之前的不少學者卻持相反意見,司馬遷《史記》就記載,文王晚年已經自稱為王。
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學者們對此依舊爭論不休。如今,《保訓》上的五個字,不說一錘定音,也是一個強有力的線索。劉國忠認為,“從清華簡《保訓》《程寤》等材料來看,周文王生前已經秘密稱王,積極從事滅商大業。”
他向記者解釋,在《保訓》中,周文王不無遺憾地對兒子周武王說過一句話,“不及爾身受大命”,意思是說,我等不到看你接受大命的那一天了。什么是“受大命”?周文王說得很含糊,但結合上下文及相關文獻,不難推測其真實含義——討伐商朝,建立周朝。
在《程寤》中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周文王說:“商慼在周,周慼在商。”顯而易見,在周文王心目中,周的最大敵人和對手是商,而商朝的憂患和危機則來自周,商、周之間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矛盾和斗爭。
“不僅如此,文王與商朝還有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古本《竹書紀年》曾記載,紂王的爺爺殺了周文王的父親。”在先秦文獻諳熟于心的劉國忠看來,所謂周文王形象的“顛覆”其實不難理解。
不僅顛覆了周文王的形象,清華簡中關于西周覆亡的記載,更是比小說還精彩。
提起西周亡國,人們最熟知的歷史故事莫過于周幽王為博褒姒一笑,烽火戲諸侯。在這個出自《史記·周本紀》的記載中,周幽王戲弄諸侯之后,有一次正宮王后的父親申侯聯合少數民族入侵,但再無諸侯肯來勤王,最終導致了西周的滅亡。
紅顏禍水的故事最為人津津樂道,但實際上,早有歷史學家指出,烽火制度在西周時期尚未出現,烽火戲諸侯很可能只是“小說家言”式的戲說。如果褒姒是冤枉的,那么西周究竟是怎么滅亡的?清華簡中的《系年》,講述了一個扣人心弦的新故事。
周幽王娶了個來自西申國的王后,生了太子宜臼,也就是后來的周平王。后來,幽王又娶了個美女,叫褒姒,生了個兒子叫伯盤。褒姒特別得寵,幽王愛屋及烏,就想廢了宜臼,改立伯盤為太子。宜臼一看大事不妙,只好逃回母親的老家西申國。
宜臼跑了,幽王還要斬草除根,就和伯盤一起帶兵殺向了西申國。西申國是個小國,卻不買幽王的賬,死活不愿交出宜臼。這時候,西申國的盟友繒國急中生智,拉來了第三個盟友西戎,一起攻打幽王。幽王和伯盤就這么丟掉了性命,西周也因此滅亡。
沒有烽火戲諸侯的橋段,導致西周滅亡的戰爭,則變成了周幽王主動進攻正宮王后的父親,之后對方才聯合少數民族將其打敗。這個新版本的故事,其實并非第一次出現。古書《竹書紀年》中有過零星記載,雖然不如清華簡細節豐富、生動清晰,但同樣沒有提及烽火戲諸侯。
劉國忠認為,“從整個事件的歷程可以判斷,當時根本沒有發生過烽火戲諸侯的事件。”而司馬遷關于烽火戲諸侯的記載,從史源角度分析,基礎史料應來自戰國時期成書的《呂氏春秋·疑似》。“《呂氏春秋·疑似》本身也屬于‘戲說’,司馬遷在此基礎上加工,可能離歷史的真相就更遠了。”
墓主:何人藏書如此“高大上”?
從2008年入藏清華,到2024年年底第十四輯整理報告發布,劉國忠與清華簡朝夕相伴了17載。17年光陰匆匆流逝,每當談及清華簡這座“富礦”,他依然喜歡用一個詞來形容——“震撼”。
與居延漢簡等西北地區出土的簡牘不同,清華簡中完全沒有文書一類的內容,全部都是名副其實的書籍,且是填補歷史空白的頂級文獻。“清華簡共包含70多篇文獻,其中真正能與流傳至今的古書對應上的只有4篇半,其余60多篇都是兩千多年來無人見過的。”
除了20多篇《尚書》類的歷代帝王“政治課本”,類似《竹書紀年》的編年體史書《系年》,約2500枚清華簡中還有類似《國語》的國別體史書、類似《儀禮》的禮書、與《周易》有關的書……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郭永秉的話說,清華簡的最大特色正是其內容的“高大上”。
“高大上”的清華簡不僅吸引了史學界目光,其中名氣最大的《算表》甚至引發了海內外數學史領域的熱烈討論。2017年4月,作為人類最早的十進制計算器,《算表》獲得了吉尼斯世界紀錄稱號。
2017年4月,清華簡《算表》獲吉尼斯世界紀錄認證。
清華簡《算表》篇正面圖版
劉國忠向記者介紹,《算表》由21支簡組成,簡比較寬,約1.2厘米,上面按規律寫著數字,每支簡的上端還有圓孔。這些與其他竹簡明顯不同的特征,讓整理團隊很早就注意到了它們。但真正著手整理,還要感謝楊振寧先生。
2009年初,楊振寧看到清華簡中竟然有寫滿數字的竹簡,興致盎然,一再催促他們盡早整理。于是,李學勤特邀了清華大學科技史與古文獻研究所所長馮立昇前來支援。簡牘高手李均明與數學史大腕馮立昇強強聯合,當年春天,《算表》即被復原。
最初,團隊把這21支簡稱為《數表》,因為簡上全是數字。復原之后,大家驚訝地發現,這明顯是一個計算工具。于是,在數學史專家們的建議下,《數表》更名為《算表》。
除了清華簡整理團隊,最早看到《算表》的“外人”之一還是楊振寧。“當時楊先生特別興奮,還問我們能不能給他打印一張,他要貼到床頭。”說起大師對《算表》毫不掩飾的好奇,劉國忠忍不住笑了。
不怪楊振寧連連稱奇,《算表》的功能的確驚人。運用這個“計算器”,不僅可以快速計算數值為495½以內的兩個整數的乘除,還能計算包括分數在內的乘法,甚至乘方、開方都不在話下。
在此之前,我國廣為人知的“九九乘法表”,來自秦代的里耶秦簡和漢代的張家界漢簡。清華簡的《算表》不僅時間大大提前到戰國,而且計算功能遠遠超過秦漢“九九乘法表”。
2014年初,《算表》一經公布,迅速蜚聲海內外。英國Nature雜志為此專門采訪了李均明和馮立昇,并在Nature網絡版做了專題報道。“全世界搞數學史的人只要來清華,一定要看《算表》。”研究先秦史的劉國忠從沒想到,有一天竟然還能向這么多數學史大家介紹學術成果。
既有“治國理政”的經史,又有打破世界紀錄的“計算器”,堪稱“兩千多年前圖書館”的清華簡,其主人到底是誰呢?
清華簡是盜掘而出,但它抵達清華時的狀態,以及豐富的文獻內容,還是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清污之前,竹簡已非常糟朽,但屬于不同篇目的竹簡往往緊密粘連在一起,極難剝離。整理團隊據此判斷,所有竹簡應該出土于同一座墓葬。
2008年搶救性保護完成后,李學勤已經初識清華簡的若干篇目,在向媒體描述自己的驚喜時,他笑稱:銀雀山漢簡主要是兵書,墓主顯然是位軍事家;郭店簡和上博簡,墓主可能是哲學家;這一次我們“挖”到一個歷史學家!李學勤認為,古人講究“事死如事生”,用來殉葬的書籍,必然是死者生前讀用或愛好的。
如今,隨著清華簡的整理和研究日益深入,對其主人的身份,學術界有了更多的猜測和推斷。
“這么多高規格的治國理政文獻,一般人誰能讀得懂?它的主人一定是一位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至少是屈原這個級別的。”在劉國忠看來,“這位主人絕不會僅是一位文獻檔案的搜集者,其身份更可能是一位楚國的高級貴族,甚至不排除是楚王的可能性。”
考古:絕非偽簡再添鐵證
或許是清華簡中顛覆性的內容太多,早在2009年,就有學者對其真實性提出疑問。盡管經歷了無字殘簡的碳十四年代測定,但其盜掘出土而后流散市場的隱秘身世,還是免不了讓人浮想聯翩。尤其是一些自媒體,語不驚人死不休,甚至把矛頭直指李學勤,聲稱清華簡的文章似乎太完美了,恐怕只有李學勤這樣的學者才能寫出來。
當記者把這些“質疑”拋給劉國忠時,他的回答相當直率:“2000多年前的文章,沒有任何人能寫得出來,李先生也寫不出來。”“我們平常各種各樣的表達,看起來平淡無奇,但很多思想觀念,只能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才有的。哪怕再精通古文字,現代人寫出來的文章也不可能與戰國時期人們的思想觀念完全吻合。”
在國家圖書館的一次講座中,提到清華簡,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胡平生也表達過類似觀點:“你把中國最好的古文字學家加在一起,都造不出這樣的文字來。”
長期從事出土簡牘帛書的整理與研究,胡平生摸過的真簡多,見過的假簡也不少。據他在講座中分享,十幾年間,親手一根根掰過的假簡就有二三十批,和朋友們一起去看過的,總不下100批。一次次辨識真偽,練就了他的“火眼金睛”。
事實證明,清華簡不僅經得起簡帛專家們“火眼金睛”的檢視,而且,時間越久,最新的科學研究與考古發現,反而越發證實了它的可靠性。
說來也巧,就在清華簡入藏的第二年,北大也獲贈了一批西漢竹簡,按照學術慣例,這批漢簡被命名為“北大簡”。參與整理北大簡的團隊里,有個考古系大一新生,名叫孫沛陽。別人整理竹簡,注意力都放在正面文字上,細心的孫沛陽卻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北大簡的背面,有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刻劃線,而且都是歪歪斜斜的。
這些劃痕有什么作用呢?孫沛陽心里從此多了一個疑問,直到2010年底,清華簡第一輯整理報告公開出版。不同于以往的簡牘整理只拍“正面照”,李學勤認為,除了文字,竹簡本身也是文物。正是在他的堅持下,清華簡首開先河,連竹簡背面也拍了高清大圖。
孫沛陽仔細研讀這些照片,發現清華簡背面居然也有刻劃線的痕跡。2011年初,岳麓秦簡首次公布整理報告,同樣的簡背刻劃線再次出現。他陷入了沉思,不同的竹簡,相似的刻劃線,這絕非偶然。在老師的幫助下,他調查了更多簡牘,最終形成了一篇震驚學界的論文《簡冊背劃線初探》。
在這篇論文中,孫沛陽論證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觀點:簡背劃線是解決竹簡編聯問題的一把鑰匙。簡單來說,簡牘是用編繩串成的,如果編繩斷了,竹簡就會散亂,怎么快捷高效地還原這本竹書?聰明的古人想了一個辦法,翻過來在背面用刀子或毛筆,沿對角線斜斜地劃一條線。
就是這么一個看似簡單卻極富創意的辦法,拯救了古人“韋編三絕”后的麻煩,讓孫沛陽成了北大考古系的一個“傳說”,也給清華簡的真實性增加了有力物證。
在此之前,學術界從未有人注意過簡背的斜線標記,只有1991年發表的《包山楚簡》導言提到“劃痕”,但并沒有任何照片。孫沛陽的研究開始于2009年,發表于2011年,而清華簡入藏是2008年,除非有人能穿越時空,預知未來,否則,怎么可能偽造出這些刻劃線?
劉國忠向記者坦言,第一次看到孫沛陽的論文時“很吃驚”,畢竟劃痕很淺,整理時即便看到了,大家也只是把它當成不小心的刻痕。事后去仔細翻閱清華簡,才發現果然如此。當然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清華簡整理公布時,清華簡整理團隊的成員,僅僅看到了清華簡的背面真容,沒有辦法獲得其他材料進行比對和研究。
2020年10月30日,湖北荊州紀南城遺址附近的棗林鋪造紙廠考古工地上,領隊趙曉斌從充滿積水的棺槨內撈出了幾百支軟綿綿的竹簡。那天發掘接近尾聲時,蒙蒙細雨飄落,但在水中站了大半天的趙曉斌卻興奮不已。
2020年10月30日,在荊州紀南城遺址附近的棗林鋪造紙廠考古工地,趙曉斌從充滿積水的棺槨內撈出竹簡。
他畢業于武漢大學考古系,到荊州博物館參加工作后,館里的老先生提點他:“挖楚墓、搞楚文化研究,不認識楚國的文字怎么行呢?”于是,趙曉斌一邊讀楚墓、漢墓發掘報告,一邊啃讀簡牘相關書籍。多年積淀,成竹于胸,竹簡出水的第一時間,他已經根據認出的文字斷定,這批竹簡很可能是歷史類書籍。
待到正式釋讀時,果然發現一篇《齊桓公自莒返于齊》,內容與傳世本《國語·齊語》基本相同。但另一篇《吳王夫差起師伐越》卻始終沒有頭緒,趙曉斌開始猜測可能是《國語·吳語》,對比后卻只有結尾一小部分能吻合,其余行文大不相同。他又翻閱了《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等,都不得要領。
苦苦思索時,突然想到,清華簡好像公布過一篇《越公其事》。“我們在湖北搞考古,以前最關注的是清華簡里的《楚居》,《越公其事》只是草草瀏覽過一遍釋文。”趙曉斌向記者回憶,抱著試試看的想法,他把《越公其事》翻了出來。這一看不得了,二者幾乎完全相同,僅有少量字形及用詞不同。
關于越王勾踐和吳王夫差,想必每個中國人都聽過他們爭霸的故事。“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勾踐忍辱負重、臥薪嘗膽甚至問疾嘗糞最終成功逆襲的事跡,更是中學生寫作文的常用素材。
同文異本的《越公其事》和《吳王夫差起師伐越》,卻講述了一個新版本的吳越爭霸。文章沒有提到臥薪嘗膽,而是花大筆墨總結了勾踐休養生息、實施“五政”的歷史經驗。而對越國兵敗、與吳王求和的敘述,則顛覆了歷史上囂張跋扈的夫差形象。他對勾踐沒有乘勝追擊、趕盡殺絕,不是因貪財好色,也不涉及拒用忠良伍子胥,而是因為“貴有自知之明”,估計自己實力不足,沒有制勝的把握。
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李守奎的研究中,“夫差何以不滅越?比起歷史文獻中的美人計、離間計等,實力估量之后的無奈選擇或許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又一個極具顛覆性的故事,但《吳王夫差起師伐越》2020年由考古發掘出土,無疑是真實的戰國文獻。在《越公其事》公布的2017年,《吳王夫差起師伐越》還埋藏在地下,而傳世文獻中從未見過這篇文章。顯而易見,考古發現的竹簡再次證明,清華簡絕非偽簡。
荊州出土竹簡與清華簡的勾連,至此還沒有結束。2024年,清華簡發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一篇名為《兩中》的文獻,成為媒體熱點。這篇文獻發現了夏啟為“天下王”的最新資料,文中假托兩個名叫“中”的人(圭中、祥中)與夏啟的對話,來闡發作者的治國理政思想。
而在荊州秦家嘴墓地出土的楚簡中,也有《兩中》。2024年,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黃德寬率隊到荊州訪問,趙曉斌代表秦家嘴楚簡整理項目小組接待,向他們展示了這批新出土的竹簡。他告訴記者,這批簡上的淤泥較多,還在清洗之中,已經釋讀出的文字還很有限。大家對竹簡上的“圭中”等字,一度搞不明白,直到看了清華簡的最新成果,才恍然大悟,原來也是同一篇文獻。
傳承:“冷門絕學”走出國門
2012年,程浩如愿以償考上了李學勤的博士生,一睹清華簡真容的愿望終于成真。當時,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還是一個小團隊,包括主任李學勤在內,僅有7位老師,且身份不是兼職就是外聘。那時,小小的團隊更像一個臨時組建的課題組,誰也沒想到,這個課題竟持續研究了十幾年,并且內容越來越廣博深厚。
清華簡團隊中,逐漸有了更多的中青年學者。
如今,小小的團隊已成長為二十多人的一流文科研究中心。85后的程浩接過前輩的衣缽,肩負起了為清華大一新生科普清華簡的任務。
2月18日,清華大學第六教學樓的一間教室里,《清華簡與古代文明》迎來了新學期的第一課。上課鈴還未響起,可容納四五十人的教室已座無虛席。教室門不斷被推開,背著書包的同學魚貫而入,環顧一周,沒有空座。
站在講臺上的程浩似乎早已習慣了這樣的“尷尬”:“沒有座位的同學可以去212教室搬椅子,那里現在沒課。”等到上課鈴響起,走道上也塞滿了椅子,程浩有點無奈:“不少想選課的同學沒選上,我會跟教務處申請換個更大的教室,擴容課程。”此言一出,不少同學總算松了一口氣。
對清華簡等出土簡牘和帛書的研究,被稱為簡帛學。別看如今選課人數爆滿,上世紀80年代,這卻是一門“冷門絕學”,當時全國范圍內從事相關研究的人不過兩三百人。“沒人愿意學,以至于一些學者專門呼吁國家搶救,讓那些老先生招幾個學生,把這門學術傳承下去。”劉國忠回憶道。
直到1993年郭店簡的發現,簡帛學才迎來了轉折點。后來,隨著上博簡、岳麓秦簡、清華簡、北大簡陸續發現與搶救,這門學科逐漸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尤其是清華簡,每次發布最新成果,都會引發學術界的熱潮。
2019年底,清華簡從圖書館老館“搬家”,“住”進了新的庫房。新家寬敞明亮,恒溫恒濕,可惜竹簡猶在,卻已不見當年讀簡人。2019年2月24日,慧眼識寶、一手創建清華簡團隊的李學勤因病逝世。
為了紀念他,清華新人文樓四樓東側專門開辟了一間李學勤先生紀念室。步入紀念室,一幅幅照片、一張張手稿,勾勒出了先生廣博而精深的學術生涯。1952年,他的學術生涯始于甲骨文研究。上世紀80年代,當戰國文字尚屬冷門中的冷門時,他就多次斷言,戰國文字研究大有可為。今天,清華簡上的戰國文字已然成為顯學,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的中青年學者們,在整理研究清華簡的同時,也開始了上到甲骨金文、下至秦漢簡帛的新探索。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研究與英譯系列叢書
而李學勤晚年傾注全部心血的清華簡,不僅成了清華的一張新名片,還走出國門,向全世界展示中國古代文明的璀璨光芒。2013年,“寫在竹簡上的中國經典——清華簡與中國古代文明”專題展覽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樓舉行。去年年底,與美國芝加哥大學夏含夷團隊合作編纂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研究與英譯系列叢書第6卷已經出版。
程浩向記者透露,下個月,清華簡將再次走進維也納聯合國總部,而在今年的日本大阪世博會中,清華簡也將擁有一個獨立展館。
來源:北京日報紀事;記者:楊麗娟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國策建言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