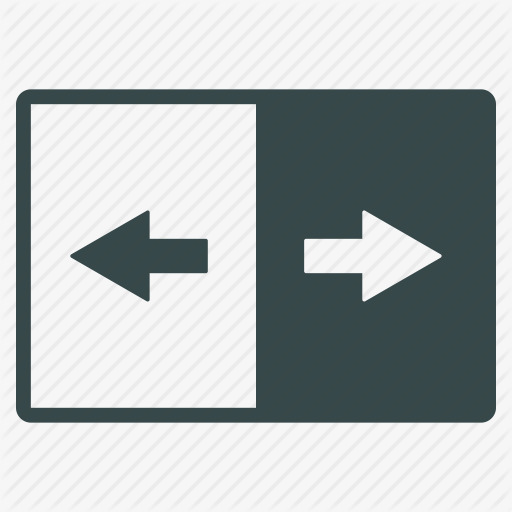孟溪君對“左”“右”這樣的話題原本木有啥興趣,若不是原湖北省作協主席方方在替原湖北省作協副主席、文學院院長陳應松洗地時,指認作家劉繼明是“極左”,我也不想趟這道渾水,更不會寫這篇文章。
方方那篇給自己惹上官司的博文《A和B的故事》,孟溪君曾專門寫文章分析過,這里只談“左”和“右”的問題。
在中國思想界,左和右之間都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和擁躉,隨便就可以列出一大串,如“右派”中的李銳、吳敬璉、秦暉、茅于軾、蕭功秦、錢理群、劉小楓、孫立平、許紀霖、朱大可、徐友漁、朱學勤、賀衛方、于建嶸等,“左派”中的鄧力群、馬賓、鞏獻田、溫鐵軍、張宏良、甘陽、汪暉、房寧、張承志、韓少功等。當然,這種劃分也不盡準確,比如對錢理群和劉小楓算不算右派,就存在爭議,有的把他們劃到了左派。這是由于思想認知本身的復雜性決定的。
文學界的狀況怎樣呢?以孟溪君觀察,中國文壇都由清一色的右派把持著,作家的立場也是嚴重右傾化滴,壓根兒不存在一個像思想界那樣壁壘分明的左右派陣營,作家中稱得上“左派”的作家實在是少之又少,如前面提到的張承志、韓少功。除他們之外,還有曹征路和劉繼明。
為了寫這篇文章,孟溪君惡補了一下功課。曹征路是深圳大學的教授,他被定義為“左翼作家”,是從那篇被稱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的小說《那兒》開始的,后來又寫了長篇小說《問蒼茫》《民主課》,影響都不如《那兒》,《民主課》主要寫文革,一直未在大陸正式發表和出版。據說,臺灣著名文學家陳映真還撰文推介過《那兒》。著名文學評論家李云雷將曹譽為“底層文學”首席代表作家,他認為,在底層文學作家中,真正繼承了現代文學史上左翼文學傳統的只有兩位:曹征路和劉繼明。
關于曹征路不多談,咱們今天重點談的是劉繼明。
劉繼明1990年代就在中國文壇享有盛名,孟溪君讀本科時,看到多個版本的中國新時期文學史教材,都是把劉作為“文化關懷小說”和“新生代”的代表作家介紹的。劉那一時期的創作如《前往黃村》《海底村莊》等具有濃厚的先鋒色彩,所以也有人稱他為“晚期先鋒派”。但到了2000年前后,劉的創作出現了較大的變化,從主要寫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到寫底層民眾,如中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放聲歌唱》,短篇小說《茶葉蛋》《回家的路究竟有多遠》等等,被一些評論家稱之為“先鋒的底層轉向”,并作為“底層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再次引起文壇注意。但劉真正作為“左翼作家”獲得超出文學圈影響的并不是小說,而是他的一系列思想隨筆。其中如《公共知識分子:告別還是開始》《80年代,或不合時宜的痛苦》《我們怎樣敘述底層》《回眸五七干校》《革命、暴力和“仇恨政治學”》《中國視野的米蘭昆德拉》等,主要發表在韓少功創辦的《天涯》及《東方》等思想類雜志上,并流布到網絡,在思想領域特別是一些青年文化群體中影響較大。
一篇題為《新左派陣營中的“60年代人”》的文章這樣寫道:“新左派主要由一批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唱主角,他們從各個領域為新左派奠定了一套完整的理論框架。新世紀以來,這批人漸漸從前沿退居二線,一批出生于60年代的年輕人走上前臺,開始充當主力軍的角色。他們主要是韓毓海 韓德強 曠新年 張廣天 孔慶東 祝東力 劉繼明 薛毅等。”左派這個概念還可以分為老左派、新左派、文革左派(或稱極左)和毛左派,再細分下去,還有學院左派、自由左派、網絡左派、草根左派等等。
摘錄一段關于新左派的解釋,算是給某些人做一點知識掃盲和普及工作:
“中國新左派的出現和興起與20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整個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語境的轉換密切相關,并伴隨知識界的分裂和整合。70年代末圍繞朦朧詩、人性、異化、商品經濟等問題,文學界和哲學社會科學界逐漸出現分歧,到80年代初期圍繞“精神污染”展開的討論表明這種觀念意識的裂痕已無法彌補。新舊知識界壁壘分明——一方是以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話語為指南的所謂的“老左派”;另一方則是以自由民主為訴求的所謂的“啟蒙”知識界。兩者彼此消長、互相攻訐,針對同一個問題(國家體制)的兩種不同的學理認同使得新時期初期的文化論爭趨于二元對立格局。論爭中流露出的現實關懷、體制思考和人文激情很大程度上成為此后啟蒙知識界內部三次分裂的歷史譜系和在場“演習”。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分野不可避免地投射到意識形態領域,使得體制、民生、自由、民主等成為各方面密切關注的緊迫問題。終于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引發了啟蒙知識界的第三次分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沖突和對決。”
由于長期被妖魔化,曾有人試圖為“左派”正名。一篇微博說:“好人在左的時代右,在右的時代左,總是不得煙抽。小人在左的時代極左,在右的時代極右,總是風生水起。”這讓孟溪君想起劉繼明接受訪談時說的一句話:“如果在50年代,我也許會成為右派,今天則可能成為一個左派。”
這也許只是劉繼明開的一句玩笑,但至少可以說明,在左派諸人中,劉談不上激進極端,或至少是比較理性溫和的,他從1990年代以來的創作和思想變化,都清晰可循,有其內在的邏輯。這是我讀劉一些文章和作品得出的印象。李云雷先生說劉是“少有的具有思想能力和知識分子氣質,能夠對思想文化乃至社會問題發言的當代作家之一”,并非謬贊。
幾年前,劉繼明自籌資金創辦的《天下》雜志,曾被媒體稱為“北有《讀書》,南有《天涯》,中部有《天下》”。孟溪君讀過幾期,上面的作者既有汪暉、黃紀蘇、孔慶東這樣的左派,也有蕭功秦、秦暉、許紀霖這樣的右派,編委構成也是如此,可見出劉“超越左右,重建共識”的良苦用心。遺憾的是,這個雜志辦了不到兩年就停刋了。
對于這樣一位理性溫和的“新左派”,方方為什么要給他扣上一頂“極左”的帽子呢?
孟溪君說過,文學界已經整體右傾化,思想右傾是正常,思想左傾會被視為異端;如果是一名體制內作家,那些權威的大刊物拒絕發表你的作品,重要的文學獎注定跟你無緣,并被打入另冊,成為一個文學和政治上的雙重冷藏人。而如果選擇了右,匯入到文學主流當中,很快就會有各種獎項和名利紛至沓來,甚至成為文學界呼風喚雨的領導。單從個人名利考慮,哪個作家不爭相跟隨潮流向“右”轉呢?所以,方方和陳應松的“右”是自然而然的。但他們只是大量隨波逐流的向右轉的作家之一二,還談不上是“右派”。只有具備清晰明確的價值觀才稱得上“派”。他們不過是在時代裹挾下,憑借小聰明和窺測投機,傷痕文學流行時寫“傷痕”,知青文學流行時寫知青,現代派流行時學現代派,新寫實文學流行是寫新寫實,神馬流行就寫神馬,以便在文壇上贏得一席之地。
陳應松也許并不像大地主家族背景的方方有明確的“政治抱負”,只是像許多人那樣染上了公知病,常在網上發表一些諸如“作為一個殘酷革命幾十年的國家是沒有人性的”的公知體言論。不知是才氣還是運氣的原因,差不多的寫作路子,差不多的年齡,論才氣兩個人貌似也不相上下,但方方上個世紀80年代就出名了,90年代更是以“新寫實”在文壇大紅大紫,成為全國知名的女作家,陳應松卻跟著各種文學潮流一路跌跌撞撞的,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還是一個籍籍無名的地方作家,連寫作資歷和年齡比他小一截的劉繼明,產生全國性影響的時間都比他早得多。直到21世紀初,底層文學崛起,陳作為這個重要文學思潮的代表作家,才在全國文壇“竄紅”。頗有戲劇性的是,劉繼明也是這個思潮的代表作家之一。兩個人還寫文章互贊過對方的作品。但究竟是神馬原因使這兩個同一文學思潮中的代表作家反目為仇、對簿公堂呢?
孟溪君覺得,根子恐怕主要還是出在政治上。
從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隨著中國社會結構不斷分化,各種矛盾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加劇了整個社會的撕裂。知識界和文化界也是這樣。在互聯網上,左右之爭到了勢不兩立的程度。左的更左,右的更右,社會戾氣上升,人際關系日趨緊張,普通人之間如此,作家之間何嘗不是?曹征路在批評《軟&埋》的文章中說,方方“遭遇不公正判決”時,他還曾通過朋友轉達慰問。但“這與作品的評價是兩回事。如同當下中國社會正在撕裂一樣,知識界的分裂也勢如破竹形同水火,這是令人惋惜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劉繼明認為,他同陳應松之間的關系,“也可作如是觀”。
《軟&埋》是方方2016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由于作者對新中國土改“基本否定“(黃紀蘇語)的立場,受到了民間思想界的強烈批評和批判。
孟溪君認為,無論人們怎么評價《軟&埋》,這部小說在方方個人的創作進程中都具有特別的意義,這并非因為它出版后引發了一起重大的文學和政治論爭,還因為通過它,作家方方第一次以“右派“的面目和姿態在公眾視野中亮相了。以前,她的小說也觸及到政治,如反右、文革,但都沒有超出當時文學和主流政治的規約,《軟&埋》則不同,她在題材、主題和人物塑造幾個方面,都大大超出了同樣描寫土改的《古船》《白鹿原》《生死疲勞》等小說的尺度,也超過了她自己以往的所有作品。
在前面提到的曹征路批評《軟&埋》文章中,曹先生指出:
“從《秧歌》到《軟&埋》,文學創作與批評領域的斗爭從來就沒有止過。站在翻身農民一邊還是站在被打倒的地主階級一邊,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價值觀問題,更是一個立場感情問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式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并不是真的‘虛無’,而是以虛無的文學姿態達到非常實在的目的。所謂‘告別革命’論,既是這種思潮的集中表現,又是它不加隱諱的真實目標。在鼓吹者看來,中國革命只起破壞性作用,沒有任何建設性意義,更談不上必然性合理性。一些人拼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和‘禍害’,所謂‘革命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性’,‘革命殘忍、黑暗、骯臟的一面,我們注意得很不夠’。歷史虛無主義在糟蹋、歪曲歷史的時候,卻聲稱自己是在進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實現所謂‘研究范式’的轉換。似乎只要戴上文學光環,就能名正言順地抓住歷史表達的話語權,中國革命就再也不具有正當性了。在劉再復《告別革命》一書迅速獲得主流思想界推崇的情況下,創作與批評中的顛覆歷史之作就一波接著一波,其核心內容便是‘去政治化的政治’,顛覆中國人的歷史記憶。”
這是孟溪君看到的對《軟&埋》最準確和深刻的批評之一。但方方確立自己的“右派”立場,不單是通過小說本身,還通過《軟&埋》受到批評和批判后她的“反批評”才完成的。
方方的“反批評”十分奇葩,正像郭松民先生說的,“汪芳主席(即方方)把所有批評她的作者一律稱為“左-棍-子”。”“汪芳主席的特點是,對嚴肅的政-治、文學問題堅決不予回應,直接就開始人身攻擊,并且完全不顧及自己身為女作家的身份,直接就奔下三路去了,可謂氣急敗壞,口不擇言。”直到最近,在看到一篇文章為《軟&埋》生不逢時,木有像同樣顛覆土改的小說《白鹿原》獲得茅盾文學獎而鳴不平時,方方還忘不了對批評她的“極左”和“工農兵群眾”又是一番詛咒,那副殺氣騰騰、秋后算帳的口氣,真像電影里的還鄉團。
方方動輒對批評者和劉繼明扣上“極左”大帽,除了她不擅思辨和不具備相應的理論素養和個人修為,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一個人或一群人的思想行為究竟到怎樣一種狀態才能稱得上“極左”?很遺憾,翻開歷史書也找不到一個可以參照的對象,當年的王明也不過被定為“左傾”而已。既然如此,方方為啥樂此不疲地把“極左”大棒掄向那些被她視為對手的人呢?孟溪君思忖再三,不外乎有四:
其一,本身懷有政治企圖,來反襯自己的政治正確,通過扣人“極左”帽子來構陷對手;
其二,自己思想極端,便近乎本能地將不同立場者視為另一種極端;
其三,動輒給人扣政治大帽這種行為,本身就證明了她自己的“右”或“極右”面目;
其四,神馬理由和依據都不需要,說你“極左”,不是也是,說你不是“極左”,是也不是。方方口口聲聲反文革,批“極左”,自己的言行卻和她想象中的“極左”如出一轍。難怪有人說,“極左”和“極右”原本就是一家人呢。
不僅如此,方方還給發表一篇報道陳劉案文章的網站也扣上了極左的帽子,理由是那篇文章“明顯偏向”劉。言外之意是只許她“偏向”陳,不許別人“偏向”劉,橫蠻跋扈的程度實屬罕見,誠如劉繼明在《我為什么要舉報陳應松――兼駁方方》中所說:
“方方爭取的不是什么批評的‘權利’,而是‘特權’。是的,特權。這種特權,只允許她批評或檢舉別人,而不允許別人批評她或檢舉她的朋友,否則就是陷害、構陷、誹謗;這種特權,可以任由她越過批評的界限,用各種侮辱性的字眼對‘批評對象’從人格、道德、職業進行全面的貶損和誹謗。”
方方還對在微博上轉發那篇報道的大V,同樣扣上極左帽子,向他們發出“死期到了”的威脅。這一招夠狠的,既達到了全面抹黑劉繼明的目的,又震懾了那些與劉持相同立場的人。按方方的邏輯,誰支持劉誰就是劉的“極左戰友”,夠嚇人的吧?左派本來就處于弱勢和邊緣,即使棲身體制,也像地下工作者那樣謹小慎微,生怕被抓住小辮子打入另冊,經方方這一番恫嚇,誰還敢公開支持劉?倒是前《南方周未》主筆鄢烈山怒懟了她一次:
“我真的不明白方方的超凡自信從哪里來。法盲一個,論事缺乏起碼的權力與權利邊界意識,是無知者無畏,還是表演欲太強而昏了頭?......我怎么覺得她7月26日微博罵我的話,像指著她梳妝臺上的鏡子在罵呢?詞曰:‘在很多事情上都缺乏常識,也缺乏基本判斷力。還經常耍出流氓嘴臉’!”
針對方方在湖北省作協換屆大會開幕,新任主席已經敲定的情況下上演的一出拙劣的“辭職秀”,知名時評家評論家童大煥也發文批評道:
“如果仔細推敲相關文本,會發現,這個聲明背后,骨子里不是有態度有風骨,而是陳腐濃郁的單位專制。……如此公然以單位主持人個人好惡來僭越法律之事,居然得到很多吃瓜群眾、乃至一些法律界人士叫好,令人匪夷所思。”
具有諷刺性的是,站出來公開批駁方方的這兩個人,并非她再三警告的所謂劉繼明的左派“戰友”,而是與她處在同一陣營的“右派”。
文章寫到這兒,可以小結一下了:
從根本上說,劉方陳案是“左右之爭”在體制內的一次集中引爆,看似偶然,實屬必然。
以劉繼明一慣的處世風格看,他不是那種老謀深算的權術家,而是僅憑一腔義憤行事,容易混淆理想與現實的一介文人,盡管他采用了舉報的合法斗爭形式,但具體手法并非無可挑剔。體制內眾多潛在的腐敗官員,即使出于自身的利益,也會以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義,對劉的網絡曝光行為予以打壓。這并不令人奇怪。奇怪的是“對手們”對劉的瘋狂詆毀與報復,至今未見有關部門進行追究。可見這些人是吃準了官方的“護短”心態,才有持無恐的。 因此,劉繼明對陳應松的舉報以及他同方、陳二人的訴訟結局,更像與風車作戰的唐.吉訶德,或一次草率實施的行為藝術,是兩種政治勢力搏弈的必然結果,也詮釋了左派在當下中國的真實處境。 (附記:據最新消息,湖北省紀委已對陳應松涉嫌違紀問題作出了“批評教育”“誡勉談話”的處理,劉繼明則因“違反組織原則,將陳應松的問題擴散到網上,造成不良影響”,受到“黨內警告處分”。盡管這個處理結果明顯有包庇陳應松之嫌,有網友直呼,對反映問題的人“警告處分”,對有問題的人卻只是“批評誡勉”,湖北紀委莫非吃錯了藥?但畢竟證實了陳應松并非方方一直在微博微信上叫喊的是被劉“誹謗構陷”,而的確有違紀問題在身。對于方方來說,這打臉的滋味八成也不好受吧。 (來源:龍之源文藝復興網)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蕭光畔:以“絲綢之路”為契機,打造中國西進大戰略
蕭光畔:以“絲綢之路”為契機,打造中國西進大戰略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