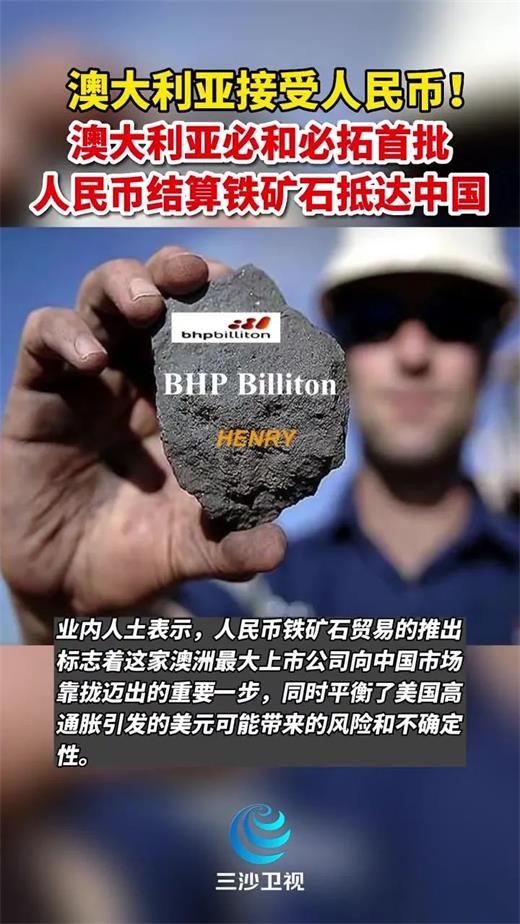【編者按】2022年7月,西南財經大學趙磊教授和政治經濟學專業教師、博士生以及碩士生,以鄧曉芒先生的“什么是自由”為案例,進行了線上交流。下面是交流紀要,供大家參考。
——“什么是自由?自由首先表現為生命活動,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里面多次提到,有意識的生命活動就是‘自由自覺的活動’(第50頁) , 這就不是單純的欲望了。相反,對欲望來說,人的自由是一種克制。我們經常以為對欲望不加克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這就是自由。其實自由在人這里一開始就是對欲望的克制,比如說勞動就是對欲望的克制。當我已經吃飽了時,為了生存我不能休息,還得去干活,甚至吃飽了就是為了去干活。還有克制食欲:雖然我很想放開肚皮吃一頓,但是不能,因為有的要留作種子。還有漁獵的誘餌,也是不能享用的。勞動首先就是對欲望的克制,這充分體現了人的生命活動是自由的,是對自然 (本能) 的超越。勞動也是創造:自然界里從來沒有過的東西要能夠把它創造出來,這就是對于自然的超越。自然包括外在的自然和內在的自然:克制欲望是超越內在自然,創造則是超越外在自然。我們今天的工業技術、飛機電視機等等,都是自然界從來沒有過的,單憑自然界是產生不出來的。在這兩者中,首先是對內在自然的超越構成了自由的源頭。真正的自由可以歸結為在一個普遍理性的層面上駕馭欲望。當然也包含滿足欲望,但跟動物的滿足欲望不一樣,它不是臨時性地滿足欲望,而是在一種普遍理性的層面上,有計劃有步驟地駕馭人的欲望、規劃人的欲望,并且通過克制欲望而更大地滿足欲望。動物看到什么想要的,就撲過去把它吃掉;它不會像人這樣設一個機關來捕捉別的動物。人借自己的理性而強過一切動物:他為什么能成為萬物之靈長?就因為他的機巧、他的理性、他的普遍性的設想能力,以及基于理性之上的克制欲望的能力, 通過克制欲望來滿足欲望的能力。”(鄧曉芒:《什么是自由?》,載《哲學研究》2012年第7期)
——“這個區別不在于制造工具,也不在于使用工具,而在于保存和攜帶工具:保存、攜帶工具比制造和使用工具更關鍵。很可能,人類最早就是由于要攜帶工具才學會了手腳分工和直立行走的。”
——“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斗爭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真正進入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一直作為異己的、支配著人們的自然規律而同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因而將聽從人們的支配。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于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至今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于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