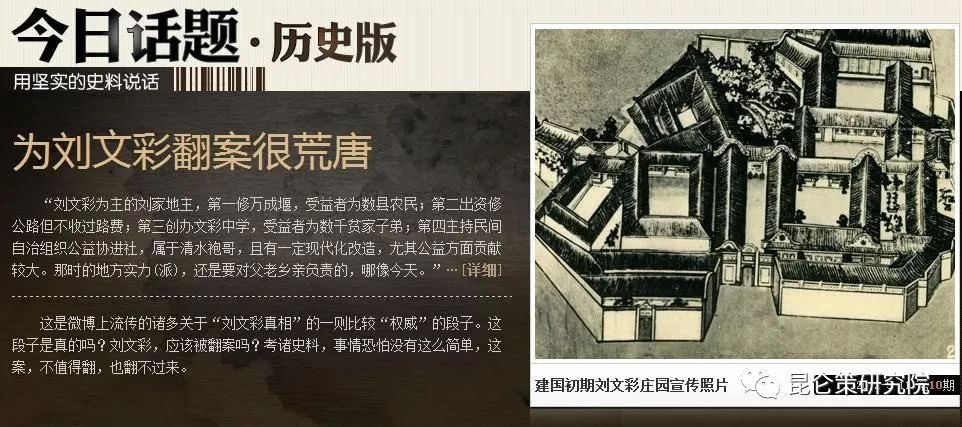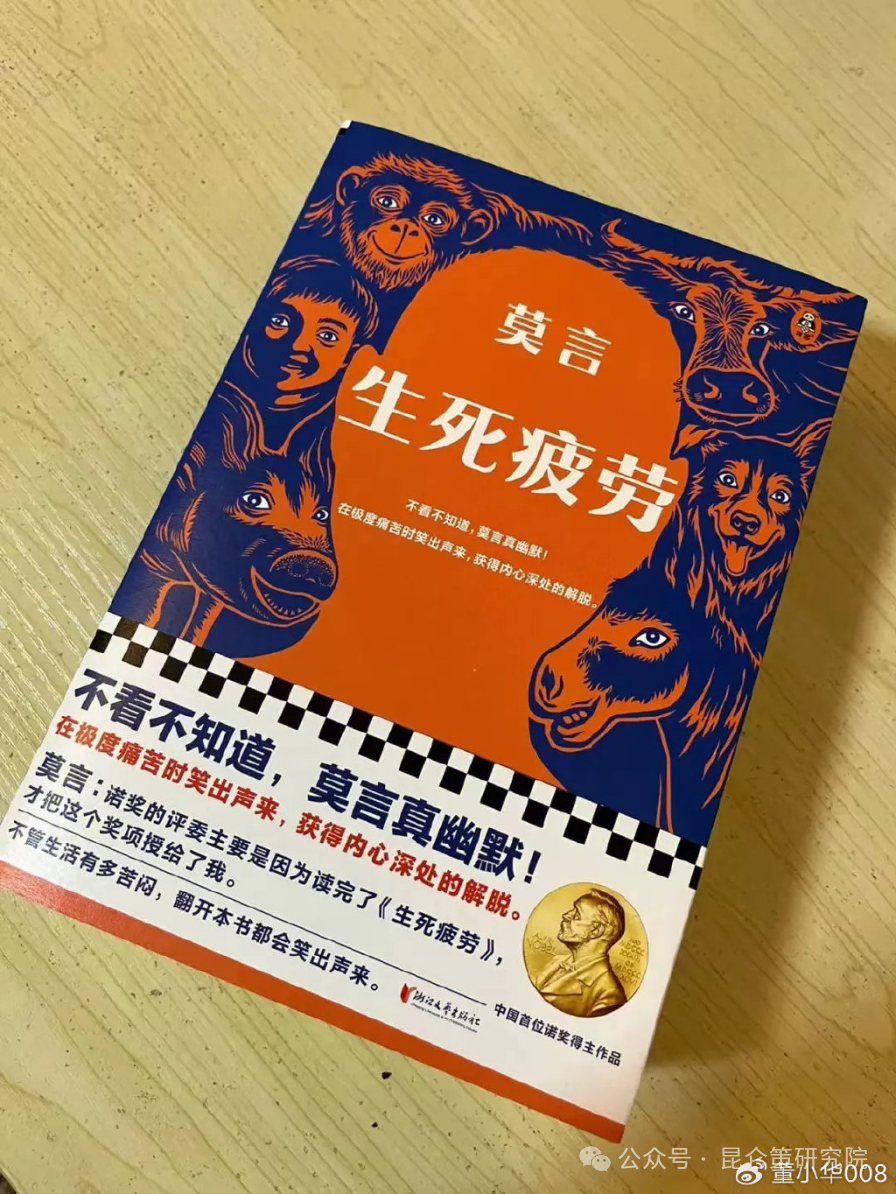莫言在提及他的小說《生死疲勞》時,曾不無得意地說:
“諾貝爾獎評審團之所以將獎項授予我,主要原因在于他們完整閱讀了《生死疲勞》這部作品。”

高密東北鄉體現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歷史,卻又超越這些進入一個國度,驢和豬的聲音淹沒人聲,愛與邪惡都呈現超乎自然的比例。莫言的幻想跳出人類生存現實。他善于描述自然;也徹底了解饑餓的含意,他筆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強盜,尤其是堅強不屈的母親們,令20世紀中國的殘酷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現,向我們展示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憐憫的國度,以及那里魯莽、無助和荒唐的人們。……莫言的故事用神話和寓言做掩飾,將價值觀置于故事的主題。在莫言筆下沒有毛時代中國的“標準人民”,而是充滿活力、不惜用不道德的手段來滿足他們的生活,打破被命運和政治劃下的牢籠。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報里的快樂歷史。他用夸張、滑稽模仿加上變異的神話和民間故事,對50年來的宣傳進行修正,并令人信服。……他語言辛辣,在他描述的中國近100年的畫卷中,既沒有跳舞的獨角獸和仙女,但他描述的豬圈式的生活,令人親歷其境。意識形態和改革運動來來去去,但人的自我和貪婪恒在。而莫言為所有小人物抱打不平,無論是日本侵華期間、毛式恐怖之下、還是今天的生產狂潮中面對不公的個體。
對這種評語,莫言很是贊同的,在致謝詞時,莫言說道:
“向瑞典皇家學院堅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摯的感謝。”

莫言所贊譽的瑞典文學院評委所謂堅守的信念,明擺著是抹黑中華民族的信念,可見其多么賣力地出賣中華民族!諾委會的頒獎詞就如同一份“DNA鑒定書”。DNA鑒定的是血緣關系,頒獎詞鑒定的是政治立場。措詞可以修改,結論是無法修改的。瑞典文學院頒獎詞說莫言的作品“對50年來的宣傳進行修正,并令人信服。”莫言在他最自鳴得意的小說《生死疲勞》中對共產黨的宣傳做了哪種“修正”呢?這種否定,與頒獎詞中的“毛式恐怖之下”評語是相契合的。按辨證法的觀點,現象有真象、假象之分,真象是指那些從正面直接表現本質的現象,假象是指那些以否定方式或從反面歪曲地表現本質的現象。更通俗地說,在現象中和本質完全相反的東西,就叫做假象,假象通常有很強的迷惑作用。莫言《生死疲勞》中所虛構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的高密東北鄉。當地的地主西門鬧修橋補路、接濟村民,是一個樸實善良,靠勤勞致富,以德服人的地主,他從未做過傷天害理之事。可是這樣的人也不行,只要是地主身份,不管是什么樣子的,一律一刀切。結果村民們非但不感激他,還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把他抄家,并且無故槍殺了他。到了陰間,他放不下前世恩怨,日夜鳴冤叫屈,拒絕投胎轉世。閻王見他執迷舊恨,便罰他墮入畜生道,歷經六世輪回之苦。

我焦干地趴在油汪里,身上發出肌肉爆裂的噼啪聲。我知道自己忍受痛苦的能力已經到達極限,如果不屈服,不知道這些貪官污吏們還會用什么樣的酷刑折磨我。但如果我就此屈服,前邊那些酷刑,豈不是白白忍受了嗎?我掙扎著仰起頭——頭顱似乎隨時會從脖子處折斷——往燭光里觀望,看到閻王和他身邊的判官們,臉上都汪著一層油滑的笑容。一股怒氣,陡然從我心中升起。豁出去了,我想,寧愿在他們的石磨里被研成粉末,寧愿在他們的鐵臼里被搗成肉醬,我也要喊叫:“冤枉!”
我噴吐著腥膻的油星子喊叫:冤枉!想我西門鬧,在人世間三十年,熱愛勞動,勤儉持家,修橋補路,樂善好施。高密東北鄉的每座廟里,都有我捐錢重塑的神像;高密東北鄉的每個窮人,都吃過我施舍的善糧。我家糧囤里的每粒糧食上,都沾著我的汗水;我家錢柜里的每個銅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勞動致富,用智慧發家。我自信平生沒有干過虧心事。可是——我尖厲地嘶叫著——像我這樣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大好人,竟被他們五花大綁著,推到橋頭上,槍斃了!……他們用一桿裝填了半葫蘆火藥、半碗鐵豌豆的土槍,在距離我只有半尺的地方開火,轟隆一聲巨響,將我的半個腦袋,打成了一攤血泥,涂抹在橋面上和橋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卵石上……我不服,我冤枉,我請求你們放我回去,讓我去當面問問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莫言通過描述西門鬧對閻王所說的一番話,其中承載了很大的信息量,這一信息現象所透射出來的本質則意味深長。

按照辨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現象與本質是辯證統一的。本質是現象的內在根據,本質決定著現象,現象從屬于本質,本質通過一定的現象顯示自己的存在。現象是本質的外部表現,總是從不同的側面表現事物的本質,可以為人的感覺器官直接感知。本質則是隱于內部的,只能靠人的理性思維才能把握。莫言通過描述西門鬧被冤殺這一現象,實際目的就是要借西門鬧的口,來表達和宣介莫言自己個人對土地改革的負面否定立場。其實他還是想通過小說來帶節奏,通過以偏概全影響讀者的政治認知,以此來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所領導土地革命的正當性!這就是問題的本質。要想否定土地革命可不是那么容易,首先要樹立起一個價值觀,那就是通過宣傳,樹立起地主全都是善良人的貞潔牌坊,都是靠勤勞致富起家的,都是大好人。只有大好人被殺,這樣才能證明土地革命是強盜和痞子的革命,是通過搶劫的方式奪取富人的土地來完成的。從而利用道德法庭,宣判這種不講仁義道德的行為,在道義上是反人類的。
盡管莫言充分利用他的刀筆,來證明土地革命的不義,但是歷史是不容掩蓋的!因此要確認事非曲直。而確認是非曲直,首先要確認:歷史學家說,“地主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農民鬧來鬧去反復進行農民起義,說到底就為了能擁有一塊能讓人填飽肚子的土地”。歷史學家的話說得有沒有道理,那就要看,在比較原始的農業生產條件下,農民靠種地到底能不能養活一家人?先看宋代,作為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富宋”,宋朝是中國古代農業史上“畝產大增長”時期。按學者吳慧、王通明等人的估算,宋代的糧食畝產達到了每畝278市斤,人均糧食占有量947市斤,甚至遠高于1980年時中國的人均糧食占有量。理論上說,在宋朝種地該“大有賺頭”才對。但另一面事實是:由于地主對土地的瘋狂兼并,導致宋朝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民,僅占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并且還要承擔絕大多數賦稅徭役,所以種地的好處根本享受不到。土地高度集中,導致少部分人養尊處優不勞動而獲得錦衣玉食,大多數人拼命勞動仍然衣食堪憂。所以在宋代,一面是糧食畝產的飛速提高,一面卻是農民生活的急劇貧困化。宋初宰相呂蒙正就嘆息“都城外數十里,饑寒死者甚重”。等于是天子腳下的農民,都沒解決溫飽。到了被當代“精英專家”推崇為“中國歷史最好四十年”的宋仁宗時代,以宋代名臣歐陽修的話說,當時的農民“一歲之耕,僅供公足,而民食不過數月”。也就是交完了賦稅后,農民連糊口都難,甚至“或采橡實,蓄菜根以延冬青”。趕上冬季,吃口糧食都是奢求。

相較于食不果腹的農民,地主們的生活是相當滋潤的。而地主們的錢都是從哪里來呢?我們可以先看看地主“發財”的一個日常套路:收租子。現在的人們對“地主收租”的理解,大多和“租房子交房租”差不多。但事實是,地主們的套路一直很深。就以“不遏兼并”的宋朝來說,宋朝地主們占有的土地,占宋代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佃農種他們一畝土地,就要把一半收成作為地租,如果佃農用了地主家的牛和農具,地租更要漲到八成。隨著宋代土地兼并加劇,失地佃農越來越多,宋代地主又多了新套路,那就是,經常以換佃戶為威脅,強行提高地租。

到了明末,地主對土地的兼并達到白熱化。所以明朝遺民顧炎武的嘆息說:蘇州、松江地區的農民,百分之九十都是佃農,有地者只有百分之十。而這“百分之十”里,絕大多數都是大地主。租種他們土地的佃農,一畝收成一兩石,地租竟要交到一石三斗,可憐許多佃農交完地租就兩手空空,甚至“今日完租,明日乞貸者”。
明代地主放債時,更把“大斗進,小斗出”套路用得熟練:放債時用“發秤”做量器,一石糧食只有90觔,收債時卻用“租秤”,一石糧食有220觔,單這一進一出,就賺足了130觔的差價。只看“收租”“放債”的套路,就知道這些享有特權的地主階層,幾乎是躺著享受農業生產的福利。地主們在逃避賦役方面,也是輕車熟路。結果就是“富豪之家賄賂公行,以計規免,中、下之戶被擾,不得休息。”甚至佃農繳納給地主的地租里,也包括了地主們該承擔的賦稅。明朝滅亡后,從清朝至民國的四個世紀里,盡管許多有識之士都在警惕著明朝亡國的教訓,但森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讓地主們的“發財模式”,翻新出更多花樣。拿劉文彩為例,劉文彩從他父親那里繼承到的田產只有32畝,但經過他短短數十年的“經營”,他家的田產就擴充到了12063畝。劉文彩不僅以收租、放債等各種方式剝削農民,還在農民從他手中租地之前,他們需要上交兩斗黃谷作為押金,然而,由于通貨膨脹的影響,這些押金往往會貶值。為了彌補這個損失,劉文彩要求佃農重新交押金。對于這些地主剝削窮苦農民的手段,有良心的人都會認為不公平,其中包括從地主階層分化出來的革命者。

近年來,劉文彩之孫劉小飛極力“挖掘”出許多劉文彩作為“大善人”的一面,如說劉文彩致力于提升老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不僅出資修繕街道、建造商鋪和住房,還以低廉的價格將這些地方租給貧困的民眾,受到了當地民眾的高度贊揚。勿庸諱言,這點和莫言筆下的西門鬧有相似之處。最重要的認知是,綜上所述,地主究竟有沒有剝削窮人?土地革命究竟是社會進步還是社會倒退?是不是心目中就已經有了答案了?新中國成立之初,占農戶總數不到7%的地主、富農,占有總耕地的50%以上,而占全國農戶57%以上的貧農、雇農,僅占有耕地總量的14%,處于無地少地狀態。地主人均占有耕地為貧雇農的二三十倍,農村存在著大量無地和少地的農民。盡管國民黨反動政權在大陸已被推翻,也有一部分中小地主和開明紳士表示愿意服從土改法令,但就整個地主階級而言,是不甘心失去其原來在農村的統治地位和經濟利益的。因此,必須放手發動群眾,與地主階級進行面對面的尖銳斗爭,而不能實行所謂“和平土改”。土地革命使中國世世代代貧苦農民和無數志士仁人夢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夙愿,終于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變成了現實!不僅如此,土地改革解放了生產力,大大提高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為國家實現工業化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這難道不是社會進步?

莫言的《生死疲勞》和方方的《軟埋》一樣,都在渲染地主“善”的一面,渲染土改“惡”的一面,以此帶偏讀者,讓人們誤以為土改就是一場政治和經濟上的浩劫。
“莫言和方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通過自己的作品否定土地革命。然而如果沒有土地革命,中國發展到現在,不過是另一個印度。
“中國和印度最大的差別就是中國發生了大革命,蕩滌了那么多腐朽的東西,而印度沒有,所以印度不但在文化上把種姓制度繼承了下來,而且因為土地仍然是私有制,掌握在各種地主和資本手里,印度的基礎建設遠遠落后于中國,嚴重阻礙了印度的工業化。印度作為糧食出口大國,同時還是高度饑餓的國家。因為糧食掌握在地主和農業資本手里,他們只關心出口有更高的利潤,至于有人吃不飽,他們才懶得關心。如果中國變成印度這樣,是誰所希望的?符合誰的利益?又是誰的災難?這不是已經顯而易見了嗎?”
莫言的《生死疲勞》以六道輪回為框架,從1950年土改寫到農村聯產承包改革,開篇就展示翻身貧農殘殺地主大善人的場景,以此徹底否定了土地改革的歷史性意義。最可惡的是,莫言對土地改革運動的寫法是有意地運用春秋筆法以偏概全、達到污名化土地革命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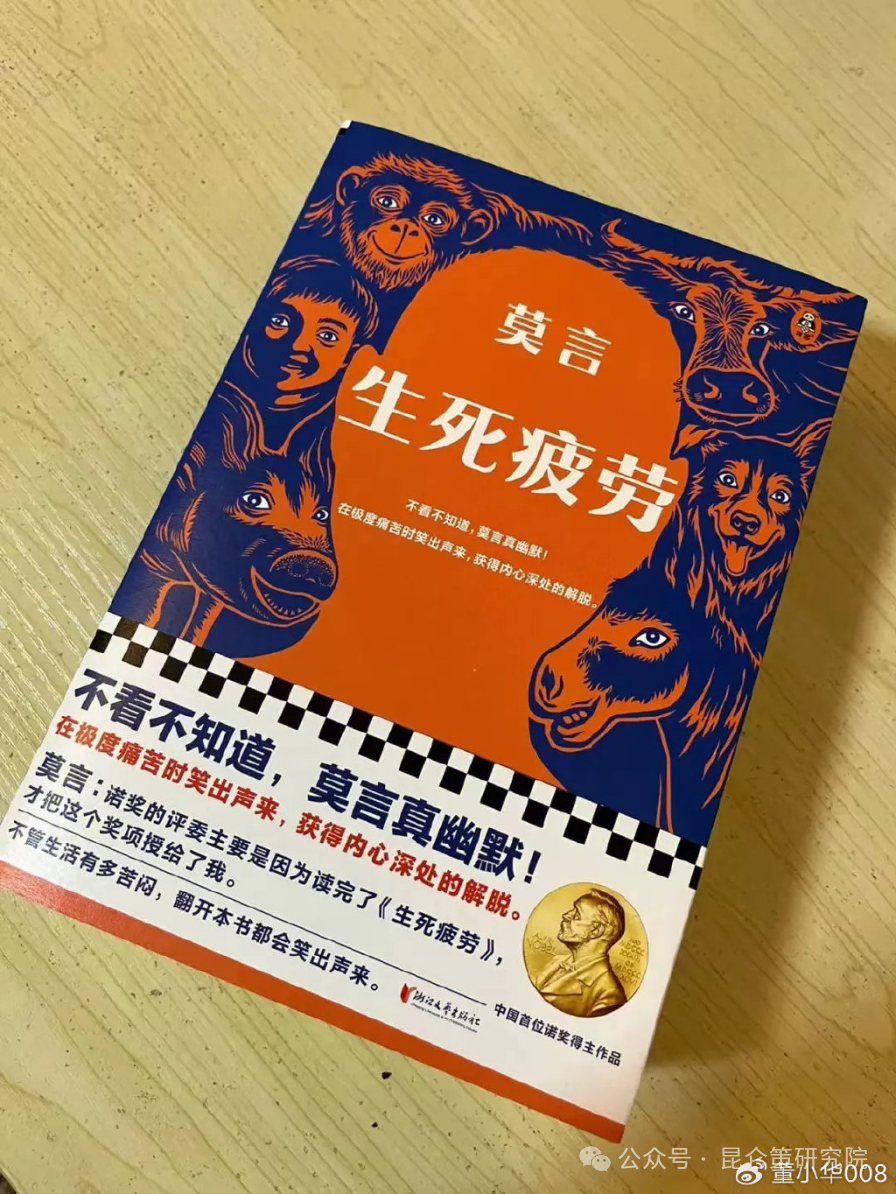
問題是,雖然歷史上確實局部出現過土改過火的現象,如某地土改時,因強調“群眾說了算,”錯斗錯殺了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好人,但是黨中央發現問題后及時進行了糾偏。問題出在,由于當時有些土改干部參加革命時間短,沒有工作經驗,簡單實行“群眾說了算”,因此出現偏差在所難免。更重要的是,黨中央及時發現了錯誤,同時總結經驗教訓,迅速調整政策,不斷自我完善,使之后的土改工作做得更規范。

例如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 ,中共中央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舉行中央擴大會議(十二月會議)。會議討論并通過毛主席《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并且還討論了解放區在土改和整黨過程中出現的“左”的偏向及其糾正的辦法。十二月會議決議提出,禁止亂打亂殺,強調“必須堅持不多殺,不亂殺,主張多殺亂殺的意見是完全錯誤的。”對“極少數罪大惡極分子”須經人民法庭審訊判決,“并經一定政府機關批準槍決公布。”一度下放的生殺予奪大權重新收歸政府,迅速遏止了各地的亂殺多殺現象。
劃分階級標準的原則是,“地主、富農、資本家、高利貸者等,主要是看他有沒有剝削。剝削方式,剝削的比例有多少。嚴格掌握這些規定就不會出大錯。”莫言通過大肆渲染土改中的個案現象,誘導讀者用“觀一葉而知秋”的視角來審視土地改革,以點帶面,有意識地利用支流來否定主流,其抹黑土地革命的用心昭然若揭。

與這個結論相互印證的是,莫言在為遼沈戰役紀念館所作的留言。

長期以來,人們都對莫言的留言感到莫名其妙,不知莫言如此眼光評價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內心是何意?顧凌英老師在昆侖策發文講得很透徹:
莫言的這個題詞,的確是很典型地公開暴露了他敵視和反對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的反動立場和態度。
“炮火連天,只為改朝換代;尸魂遍野,俱是農家子弟。”這八個字,非常陰險、十分惡毒。
“改朝換代”?我們改掉的是國民黨蔣介石所代表的封、資、帝在舊中國的一切反動統治“朝代”,換來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勞動者當家作主的“新天”,這能與舊中國剝削階級統治的“改朝換代”同日而語嗎?難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是和剝削階級統治“改朝換代”一樣,只是為自己打江山,而不是為了讓人民坐天下嗎?!
“農家子弟”?難道不區分是人民的革命戰士,還是反人民的反動派?革命戰爭的“尸魂遍野”,難道不值嗎?想想國民黨反動派屠殺了多少共產黨人、革命戰士和革命群眾,我們的解放戰爭就是為了結束這種反動階級的殘酷統治,換得人民的解放與和平幸福。為人民而犧牲,死的光榮;替反動派賣命,死的可恥!
根據中國軍網提供的歷史資料,三年人民解放戰爭中,人民軍隊共計犧牲26萬將士。這些犧牲的指戰員,大部分都是農家子弟。現在問題來了,他們為什么甘心粉身碎骨,為推倒三座大山而獻身?其實在我看來,這并不難解釋,其實根源還在于土地。土地是農民之根,農村實行土改后,獲得土地的大批農家子弟踴躍參軍,他們參軍的動機非常樸實,那就是保衛勝利果實,不能讓以蔣家王朝為靠山的還鄉團反攻倒算,重新奪回已經屬于自己的土地。

解放軍中不乏國民黨軍被俘和起義人員,他們經過階級訴苦教育,特別是聽說自己在解放區的家分得土地后,都迅速轉變成堅強的革命戰士。然而這些為保衛土地主權而犧牲的戰士,被莫言解讀成僅僅是為了”改朝換代“而獻祭的炮灰。這在邏輯上解釋了莫言內心對土地革命的切齒痛恨,在這種陰暗心理的主使下,莫言寫作《生死疲勞》的動力源泉便有了!

這也解釋了莫言為什么會在他的小說《豐乳肥臀》中,描寫解放戰爭中,一系列抹黑解放軍的情節。如:解放軍指導員打支前民夫王金的嘴巴子,逼得剃頭匠王超上吊自殺。如:解放軍潰兵搶劫老百姓,解放軍小戰士不愿意當炮灰而含槍自殺。如:解放軍強占了一位老太婆的家,逼得老太婆睡在棺材里并且逝去。莫言利用小說渲染土改的所謂“殘酷真相”,完全不顧及某些個案現象產生背后的復雜原因,一味地做簡單化政治解讀。這種政治解讀導致作品演變為控訴小說、社會批判小說,卻又不能深刻而準確地反映歷史真實。由于這種政治性解讀的掩蓋,導致共產黨領導窮苦農民反對剝削、翻身做主是善舉的正確認知被顛覆。這導致許多讀過莫言《生死疲勞》的人,認為小說對土改的解讀是原汁原味的,是和盤托出的,是力求還原真相的,是作品的歷史厚度和深度。在這里我要“呵呵”了!他們的這些見解,頗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意味,殊不知莫言的用心是叵測的。他是通過牲畜道的眼光,來看待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歷史發展演化的場景。

《生死疲勞》中所發生六道輪回其實就是一個歷史循環,寓意莊家輪流坐莊,暗示在歷史輪回中,“胡漢三”還會回來。在社會領域的思想博弈中,誰的思想意識形態占統治地位,誰就會主動擔負起維護自己本階級利益的責任。誰說沒有階級斗爭?現在的問題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你不想提階級斗爭,他們卻想翻歷史舊賬,總想把人民赴湯蹈火所建立的政治秩序用乾坤顛倒的方式反轉過來。(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