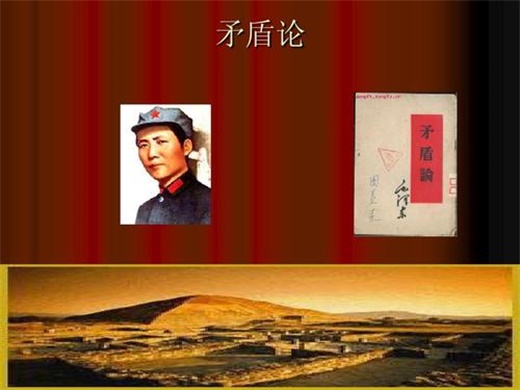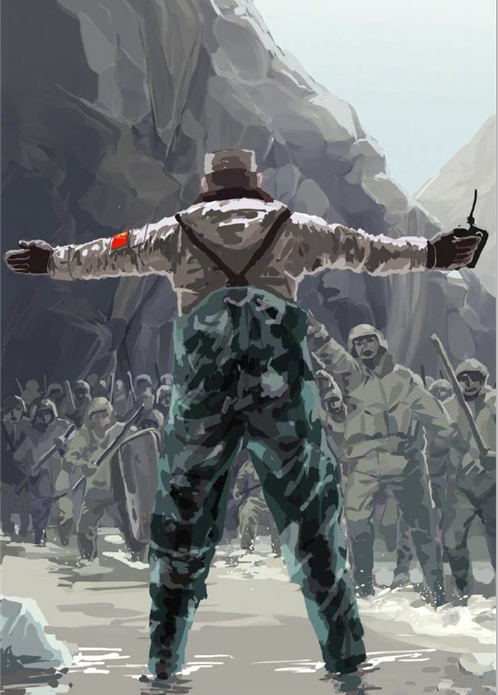行政訴訟是政府組織中的行政行為人與民間人士之間的官司,對農村的老百姓來講就是民告官,而且認為雞蛋碰石頭輸定。他們情愿上京上訪也不愿告官。糾其原因,農村中分田到戶后村民與行政發生關系的,往往是政府的支農惠農政策項目上的落實,土地征收產權糾紛等糾葛的發生,與貪官污吏在其中作祟有關。而司法實踐中,政府行政與貪官汚吏是同一體系,與老百姓對立。即使法理上不存在對立,但在現實中有家族政治、幫派政治中的腐敗分子必然與受害的老百姓形成水火不容的對立。這與政府組織行政行為混淆無法分解獨處。
支農惠農政策項目的落實,土地征收不動產確權等工作落實都涉及政府多部門的行政工作,某個環節有腐敗行為發生,法庭上沒有這樣多的司法資源去梳理,往往在維護政府形象中讓老百姓敗訴、息訴或者不能立案,實際的負面形象卻是維護了貪官、疏離了政府與百姓的關系。
所以,對行政訴訟要區別是政府組織行為還是行政工作人員的具體行為,具體操作的行為人違法違紀的不能代表組織行為,要以獨立的公民權上審判席。有違法事實證據確鑿的可先結案,把行政行為人的案件移交政府組織內部由紀委審理,梳理腐敗網絡與“政績”利潤的受益脈絡,審定賠償責任人,再償付受害原告的經濟損失。
下面舉二個行政訴訟中的實例進行分析:
金華市婺城區雅畈鎮政府由邵澤洲負責為235國道建設的征地中,被征地村的地類與面積弄虛作假,對失地農民的補償與安置不依法落實,像汪家村每人平均耕地1.4畝,要對村民征2.21畝才能有一名失地安置。因為鎮政府里掌權人為“政績”利潤虛報了耕地面積,單汪家村就增加了800畝,虛增的面積要由被征地村民買單才造成如此后果。
村民經上訪、行政復議、行政訴訟都不能解決,法院這一維護公民權益的最后依靠都無法指望,反而形成官民關系緊張。行政訴訟不能以司法公正來保護村民的權益。
原告訴求的失地安置是具體的行政行為,也有法可落實,但沒有具體的責任主體。像征地中村民失地與安置要涉及政府的上下級的多個部門行政行為,能追查各政府部門履行的職責?原告能夠逐個告各政府部門?這只能形成政府各部門共同防范抵制村民的維權。
政府各部門行政中難免那個環節存在腐敗,用“政績”獲得財政獎賞利潤,像土地整治、廢棄地復墾等,弄虛作假涉及財政、審計、監察、自然資源和規劃等部門,涉及鄉鎮立項、驗收、決算、審計。雅畈鎮有37個村,單汪家村就虛報了耕地800畝,只有不向村民透露一鱗半甲真相,才能一了百了。但村民的征地安置案關聯虛加的耕地,讓腐敗的沉渣泛浮出來,但到底那個環節是腐敗的豁口?靠村民是無力揭開的。
公民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行政訴訟法第八條“ 當事人在行政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平等的當事人應該有獨立的具體的公民權。行政訴訟的審判席上不應該是一個公民面對另一個虛擬的公民,他背后只是政府各部門的行政權力機構。
行政訴訟法第二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前款所稱行政行為,包括法律、法規、規章授權的組織作出的行政行為。”
說明政府組織的行政行為應該是指依法授權的,如果是不依法、違法的行為就不能代表是政府組織作出的行政行為,只能是其工作人員的非政府組織行為,或者是腐敗行為。但在社會現實中,腐敗往往有網絡,其工作人員應以獨立的具體的公民權上審判席,斬斷網絡關系。幕后有關聯、有網絡,就讓紀委插手工作。腐敗分子混淆在政府組織內與老百姓對簿公堂形成對立,只能產生民憤,分離出來才能使官民回歸魚水關系。
以造假的政績形成的利潤有其分配受益的脈絡,誰是得利人,只有依靠政府組織內部清查,民間無此權力。所以行政訴訟中,原告訴行政行為操作人為被告,經庭審有具體違法事實的證據,應該先結案,再由政府組織內部通過紀委調查另案審理。原告既無此能力解決案件深層次社會問題,否則被告以納稅人的、國家財政的資金與民間自食其力的原告打持久訴訟戰,原告雖傾家蕩產耗盡生存資源而不能打贏官司,一生背著寃情生存,讓被告為助長腐敗勢力而得寵。
以發生在婺城區雅畈鎮的二個案例來說明:
案例一、“(2020)浙07行初1號”中院行政裁定書:原告陳小達告婺城區區長黃國鈞、雅畈鎮鎮長趙朝陽,訴訟請求有三點:一是土地征收行為違法;二是賠償土地上附屬物損失;三是因人均面積的差錯造成(安置)費用多付。
原告認為被告征用土地首先是程序錯誤:2017年7月24日鎮政府為征地發布通告,要求在2017年8月15日之前自行搬遷、清理或者拆除,逾期將視為無主處理,而事實上征地審批時間是2018年12月6日,征地補償安置方案公告的時間2019年1月11日。二、認為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及其地上附著物,必須事先解決好被征地人就業、住房、社會保障,確保不低于原有生話水平。而被告在征用原告土地上的附屬物時,沒有經過公平、公正地給原告土地附屬物的評估、以及簽訂賠償協議等程序,給原告造成的損失10萬元。三、認為“事實上原告村人均面積171.5平方米,而被告統計錯誤數據是人均面積841.1平方米,因失地保險名額是以人均失地面積比例計算的,人均面積多,失地保險名額少。所以,原告就需要再向他人購買面積612.7平方米(指標),才能符合失地面積保險名額。因人均面積統計錯誤,還使第二原告受延誤退休時間2個月”的損失。
被告區政府出庭行政負責人楊旭鋒承認:鎮政府按區政府的相關批復“被確定為征收執行人,負責與被征收人簽訂安置補償協議、支付土地征用和房屋征收補償費用”。
被告鎮政府出庭行政負責人李慶華認為:“一是根據各級政府……等等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作為土地征收執行人,征收原告的土地。”“2017年7月24日發出通知要被征農戶將地面附著物在8月15日前搬遷清理完畢,逾期將視為無主處理。”“二是原告土地上附屬樹木損毀并非被告導致,系第三方(工程施工方)原因造成。”“三是被告已經按照法律規定履行自身行政職責,原告調劑平方所支付的費用不應向被告主張。”
法院經審理認為“土地征收行為包括土地征收審批、公告、補償安置及實施等一系列行為,涉及不同級別的多個行政機關的多個獨立的行政行為……原告提起的本案訴訟包含了多個可訴的行政行為,依法應分別起訴,而不能合并為一個訴訟。”“導致本案因原告的訴訟請求不具體、不明確而無法繼續審理”,要“一行為一訴訟”而裁定駁回起訴。
土地征收包括不同級別的多個行政機關的多個獨立的行政行為,但鎮政府根據區政府的批復已“被確定為征收執行人,負責與被征收人簽訂安置補償協議、支付土地征用和房屋征收補償費用。”也就是“多個行政機關的多個獨立的行政行為”都已綜合委托授權給鎮政府包攬執行,由鎮政府與被征地的“所有權人、使用權人就補償、安置等簽訂協議”。鎮政府沒有履行好、或者多個行政機關沒有監管好鎮政府與被征地方的簽約和履約,本是各行政機關與鎮政府的法律關系,但為了保護被委托人,也牽涉到各委托方與被委讬方的關聯關系,跳過被授權的鎮政府,卻要原告自己去向各權力部門問責?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官專業會議紀要”(以下簡稱“會議紀要”)會議紀要(五)中有提示:
“被征收人對補償標準、補償安置方案、被征收房屋和土地的地類與面積認定、地上附著物與青苗補償費計算等有異議的,可以在提起上述相關類型訴訟時一并提出;人民法院應當全面審查上述行為的合法性。”
但被告以“原告土地上附屬樹木損毀并非被告導致,系第三方(工程施工方)原因造成。”來推卸責任,法庭未表態。
施工方的選擇是經政府相關部門招投標選定,簽約后待政府土地征收完成后才按合同要求進場按設計圖施工的,政府負監管責任。
被告鎮政府方出庭人李慶華還認為,征地審批時間在2018年12月6日,而“地面附著物要在8月15日前搬遷清理完畢,逾期將視為無主處理。”是“已經按照法律規定履行自身行政職責”。
對征地“未批先用” 已采取補救措施的,“會議紀要”也有規定,其前提是:“已參照法定標準制定補償安置方案并實施補償安置”。但到目前都未按土地管理法的以人均耕地面積實施補償安置,征地中在地類、面積上的弄虛作假至今未糾正。未審查被告上述行為的合法性。對自詡己按法履行自身行政職責,法庭卻未否定。
案例2、又舉《(2019)浙07行初541號》行政判決書,原告請求依法判令撤銷被告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的“婺政復受決字(2019)3號”不予受理決定書,判令被告依法予以受理。
原告前行政復議中的復議請求是:“為建設金武公路的征地中,汪家村77.538畝耕地征用后失地農民安置名額35名。這35名安置名額如何產生的,是否對汪家村征地安置出現不公?望區政府對雅政〔2016〕63號文件中的雅畈鎮37個村的每人平均耕地數、被征地面積、安置名額及征地用途等統計分析一下,在征地與實際安置中是否有貓膩?希望能依法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數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單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數量計算。以法治國中汪家村民迫切希望區政府督促雅畈鎮政府尊重土地法的規定,維護失地農民的正當權益。”
原告是村民,行政復議中又未請律師,第一次在這申請訴求的實踐中文字表達雖不簡練,還是明確對鎮政府不依法征地的置疑,及同一征地案不依法征地涉及各村的第三者。要求維護失地農民的正當權益。但被告斷章取義,只截取原告復議請求中的隸書字部分,歪曲為只是要區政府對數字的統計分析,不屬于行政復議范圍。
原告被告雙方對證據的證明力不通過答辯,一方以政府形象自居,高傲地壟斷解釋權。裁判文書上沒有雙方對證據答辯置疑的記錄,讓解釋權只成一方專利。
“會議紀要”(四)認為:“當事人確認一系列征地行為違法,一般不宜認定為訴訟請求不明確”。
而在《(2019)浙07行初541號》行政判決書中,原告的的證據4、5、6分別用戶口本、征地地形圖中的原告承包地、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調查信息公示表證明原告一家7人只有5.68畝耕地,以每人只有0.8畝來證明征用2.21畝安置一人的荒謬;證據3給自然資源規劃分局的復函是陳述耕地與林地不能混淆問題;證據7給鎮干部的申訴書是陳述汪家村從1961年農村耕地所有權落實到生產隊以來的三次面積變化,但每人平均面積從未超過1.4畝。證據2是行政復議申請書的復議請求,以各條證據證明征地安置的不合理。
而原告請求依法判令撤銷被告的“婺政復受決字(2019)3號”不予受理決定書的訴訟請求,在庭上陳述如下的發言稿:
尊敬的審判長、合議庭審判員:
在建設金武公路的征地中,汪家村77.538畝耕地征用后、失地農民的安置名額為35名,每一安置名額征地指標為2.21畝,按此,汪家村農業人口998名就該有耕地二千二百畝,這出自“雅政〔2016〕63號”文件具體指導操作的行政行為嚴重背離汪家村的現實情況,讓失地農民在安置上帶來了生存危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二條明確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是行政復議范圍”。雅畈鎮政府對汪家村失地村民的上訪申訴無動于衷后,申請人就不得不走向行政復議。被申請人認為不屬于行政復議范圍,申請人不得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五)項:“對征收、征用決定及其補償決定不服的”的規定提起訴訟。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的規定:根據第(一)項:我們有明確的6名申請人;有符合規定的一名雅畈鎮政府行政法人為被申請人;第(二)項:被申請人的征地面積有誤、對申請人的失地不依法安置,這一具體行政行為損害了申請人、形成利害關系;第(三)項:申請人有具體的復議請求和理由,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安置失地的申請人;第(四)項,我們在申請期限15天之內提出符合法定程序;第(五)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二條,我們的復議要求,屬于行政復議法規定的行政復議范圍。所以申請人的行政復議符合法定受理條件。
被申請人的“雅政〔2016〕63號”文件,涉及到雅畈鎮的37個村的征地和安置,在這數字化管理時代,只許行政的數字化管理,但諱言數據的違法卻以“不屬于行政復議的受理范圍”為理由來作社會監督的擋箭牌,這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第一款、對作出的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的規定,(235國道)金武公路雅畈管轄路段土地審批在2018年12月06日,但在2017年5月開始征地9月開始施工的違法行為,申請人遵照行政復議法第一條“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的規定應該受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第四十六條規定:“被申請人未依照行政復議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提出書面答復、提交當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依據和其他有關材料的,視為該具行政行為沒有證據、依據,”當原告向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答辯人卻認為“被答辯人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法定受理條件”,答辯人根據的理由是編造了《行政復議法》第二十八條第五項這子虛鳥有不存在的規定。
法律是公正的,綜上所說,相信法庭依法判決能讓原告得到依法安置!
原告在法庭上作這篇“最后的陳述”后,法庭書記員不記錄原告的陳述在案,使得原告無法在法庭記錄上簽名,這才使書記員勉強收下書稿,但在判決書上消失了原告陳述證據的這一答辯內容。這樣,法庭上未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三條 “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并由當事人互相質證。”的規定;也未按“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對未采納的證據應當在裁判文書中說明理由。”的規定,法庭根本未釆納原告對證據的陳述,不出現在裁判書上不說明理由。
綜上分析,原告被告在證據的解釋權上有不公,或由一方壟斷,對各自的證據證明什么,不答辯、置疑,或裁判文書不記載,就能輕而易舉的得到與客觀事實相反的法定事實。任意的取舍,以抽象否定具體,以技節否定整體,抓住一點不及其余。就不能限止庭后對法定事實的任意發揮得出指鹿為馬的結論。這也是法庭在行證訴訟中對虛擬被告左顧右盼的無奈中出現的弊端。
綜上所述,行政訴訟的司法需要改革。
作者:馬渝生 男 回族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