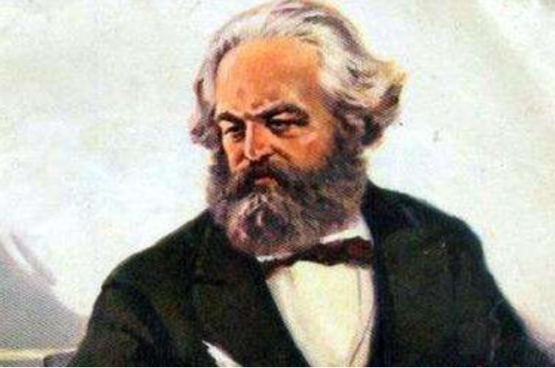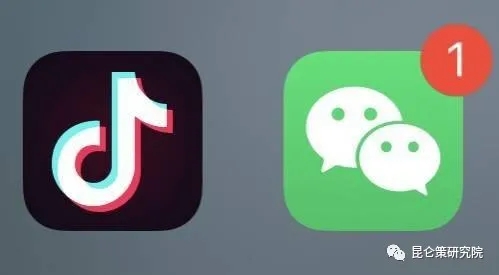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
自從人類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就如何組織現代工業社會的問題,逐漸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案,這也就是延續至今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散布在全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已經為此寫下浩如煙海的宏篇巨著,以各種不同方法、從各種不同角度,來分析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諸多弊端,在此不遑多論。本文僅從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主要層面——生產領域的高風險性及其在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具體體現——勞動者低下的抗風險性,來淺顯論述資本主義制度在社會關系領域的巨大弊端。
以資本主義形式組織起來的現代化大工業社會,是以市場為依托的商品經濟社會,具有極大的風險性和不穩定性。變化莫測的市場風云,要求企業必須根據市場供求關系的頻繁演變,不斷調整商業策略,隨時隨地變換更替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隨著企業的創立和倒閉、企業運營規模的擴大與縮減以及企業運作項目與日程安排的變動,企業員工的工作職責、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等也隨之頻頻而變。更為嚴重的是,企業的兼停并轉還經常造成大量的人員失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無休無止的變化,帶給企業員工的是工作環境極大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因此,在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職業風險始終存在,而且瞬間可以變為現實。動蕩不安的職業生涯廣泛影響著廣大勞動階層的日常生活,使得資本主義社會成為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最缺乏穩定感和安全感的社會。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那樣:“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
市場經濟的不穩定性要求勞動力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全球化的大潮更進一步擴大了人力資源的流動速度、流動規模和流動范圍,形成了人類歷史上流動性最強的社會,并因此引發了一系列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其中最突出的一個弊端表現為社會支撐體系的根本性斷裂。不僅傳統的地緣關系被徹底搗毀,向來牢不可破的家庭和家族等天然血緣紐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當血緣與地緣這兩種最重要的人際關系網絡被市場的破壞性力量瓦解之后,核心家庭便成了人類相互依存、相互慰籍的唯一社會單位。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進一步發展,社會的碎片化與原子化趨勢逐步加劇,就連社會最基本的細胞——核心家庭最終也無法幸免于難。“丁克家庭”、“單親家庭”以及“一人之家”等非傳統家庭模式,對核心家庭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并且已經取得西方主流社會的正式認可。美國學者克里南伯格在《單身社會》中提到:“獨居人口占到美國戶籍總數的28%,這意味著獨居者已經成為了僅次于無子女的夫妻家庭,成為了美國第二大戶籍形式,遠遠超越了核心家庭、多代復合式家庭模式、室友同居以及老人之家等其他形式。令人吃驚的是,獨居生活同時也是最為穩定的居住及生活方式。”
以家庭為代表的社會支撐體系的解體,代表著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徹底疏離與異化,其最極端的表現就是全世界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進入 “單身社會”和“無緣社會”。在孤獨的人群中獨自打保齡球,成為很多西方人日常生活的常態。這些現象明白無誤地表明,以個人主義和獨立自由相標榜的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已經分裂為不可能再分裂的最微小的分子,整個社會已經徹底淪為名副其實的一盤散沙。恩格斯在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時就已經觀察到這種景況:“人類分散成各個分子,每一個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則,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這種一盤散沙的世界在這里是發展到頂點了。”而這也正是美國著名學者帕特南所擔憂的社會資本的流失,它極大地提升了人類在危機和風險面前的脆弱性:“說得明白些,如果你有很多朋友,當你生病時,就會有人給你送來雞湯。或者說,當你老了,你摔倒在浴缸里,要是你有朋友的話,就會有人來照看你,救你這條老命。”
在已經微型到極致的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當中,人類的抗風險能力被嚴重削弱。俗話說一箭易斷,十箭難折 。無論是個體的人還是由一兩個成年人所組成的小型家庭,其抗風險能力都是非常之低的。當今資本主義社會可以說是人類有史以來抗風險能力最低劣的社會,只要家中有一個人無法實現充分就業或因身體健康原因需要照料,不管是核心家庭、丁克家庭或一人之家,都沒有足夠的人力與物力資源來抵御人生風雨與市場巨變,更遑論你死我活的職場競爭所必需的時間與精力消耗。因此,任何一個微小危機的降臨,對于當事人及其家庭的打擊都是毀滅性的。克里南伯格的研究表明:“獨自一人面對老年和孤獨不只是在生病或發生危機時使我們變得脆弱,它同樣也顯著地降低我們每天的生活質量。”西方國家的很多社會問題,如酗酒、吸毒、亂性、自殺、家庭暴力、心理變態以及精神疾病等,都和在險象環生的市場競爭中不幸遭遇危機的個體缺乏必要的物質與情感支撐有很大的關聯。
月自有陰晴陽缺,人本有旦夕禍福。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更無人有穩操勝券的把握。在天災人禍面前,社會支援體系完整健全的群體可以及時啟動渾然天成的人際互助機制,迅速向受災者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使人有驚無險地安然度過難關。對于遭受滅頂之災的人,聯結緊密的人際網絡無疑構成了一個具有諸多實際效用的壓力緩沖區。同時,人類之間的團結互助,也是對當事人最好的情感慰籍。然而,面對人類歷史上社會援助機制最薄弱的社會結構,西方人只得長期獨自應對隨時而至的各種艱難險阻。除非能夠通過自己的個人能力和依靠家庭的強有力支持化險為夷,就只能在孤立無援的凄苦無助中體會世態的炎涼和生命的無常。恩格斯曾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中嚴厲批判這種“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鐵石心腸的利己主義”:“只要疾病一發生,特別是家庭的主要供養者男人一病倒(由于他緊張地勞動,需要食物最多,所以第一個病倒的總是他),缺吃少穿的情況就特別嚴重起來,社會的殘酷性也特別鮮明地暴露出來:社會正是在自己的成員最需要它援助的時候拋棄了他們,讓他們去受命運的擺布。…… 這個一盤散沙的社會根本不關心他們。”
而這也正是我經過對西方社會長達二十多年的悉心觀察和切身體驗所得出的結論:痛在西方無人問。不僅如此,西方社會還存在這樣一個非常詭異的現象:承受著最殘酷的命運摧殘的人,往往也是最被社會所孤立的人。人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往往也是最有可能被社會所拋棄的時刻。出于自身的現實利益考慮,西方人不但對他人的痛苦置若罔聞,而且對陷入困境的人如同躲避瘟疫般避之唯恐不及。根據我的分析和觀察,西方人之所以故意疏遠急需救助的人,主要是基于以下兩個考慮。一是絕大多數人都在異常激烈的生存競爭中精疲力盡,被數不清的生存壓力逼壓到了極限,常常是自顧不暇。為了勉強保持住自己那點極其微弱的競爭力,生怕沾染上不必要的麻煩而難以脫身,實在是沒有閑情逸致來過問他人的死活了。二是唯恐被受難者的消極情緒所感染,令到自己也失去繼續搏殺的勇氣與斗志。命運的不幸者似乎總是在有意無意之間,用自己的悲慘經歷提醒著旁觀者,向他們昭示著每個人終將在劫難逃的不祥之兆:每一個人的幸福都危若累卵,災禍卻可能隨時不約而至。而這一令人極為不悅的現實,卻也正是那些暫時還安然無恙的人們所不愿也不敢正視的。正因為如此,命運的不幸者也就成了大家紛紛躲避的對象。但是,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周圍人這種事不關己和避而遠之的冷酷無情態度,很容易讓他們感到末日降臨般的絕望。
我并不否認,即使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一些天性善良的人,會不時對時運不濟的人施以援手。但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并沒有建立起一個穩固的互助友愛的集體,在每個社會成員需要的時候,都可以確定無疑地向其提供切實可靠的幫助。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也并沒有生活在一個個由家庭、鄰里、同事和親友所組成的、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自然形成的、每個成員都必須承擔特定義務并享受相應權利的社會共同體當中。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然狀態中,沒有任何個人和任何組織有任何義務和任何責任向任何人提供任何幫助。相反,資本主義制度極力阻撓社會個體之間依靠人的本能、直覺和自然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自行建立有實際意義的互助協作關系,以至于西方人總是盡量避免人與人之間利益與情感方面的深層聯結。普通人之間基于共同的現實物質利益和情感共鳴的固定集體,完全無處可尋。
資本主義制度嚴重腐蝕了人際關系的親密和諧,即使是在家庭成員之間也是各自為政、貌合神離,沒有形成傳統意義上肝膽相照、生死相依的利益聯盟和情感結合。在個人生存所面臨的各種基本風險面前,整個社會普遍感到愛莫能助。實際上,西方社會只不過是由一群為各自私利而苦戰的散兵游勇所組成的烏合之眾。人們必須單純依靠自身的個人魅力和社交能力,在日常生活和工作活動之外,自行搭建一個社交平臺,以期在需要時可以從中獲得某種形式的援助。對于那些由于各種原因缺乏這些能力和機遇的人,資本主義社會無異于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而這才是西方社會特別是底層社會的真實寫照。所以,德國馬克思主義者瓦爾特·本雅明在《作為宗教的資本主義》中稱,資本主義是“對一種沒有夢想也沒有憐憫〔sans reve et sans merci〕的崇拜的慶祝。”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一對無法克服的社會矛盾,即經濟結構的高風險性與社會結構低下的抗風險能力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產生和發展,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以獨立自由為準則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產物,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之一,貫穿于資本主義社會大生產的全過程。這一矛盾的對立存在,對于生活在現代社會的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產生了極為負面的影響。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社會風險,全部由缺乏社會支持體系和社會資本嚴重不足的普通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來獨自承擔,壓力之大足以將一個家庭及其成員推到徹底崩潰的深淵,而這也正是資本主義制度之弊端在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最真實的體現。
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在一個現實的社會里,一切需求的發展和滿足,也就是一切需求的同等發展和滿足是否有保障?如果有保障,那這個社會作為社會就是完善的;這并不意味著這個社會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標——按照我們的上述考察,這是不可能達到的——而是意味著它也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它必定越來越接近于自己的目標。如果這是沒有保障的,那么,這個社會雖然可以僥幸沿著文明道路前進,但這是靠不住的,因為它同樣也可以由于不幸而倒退回去。” 毫無疑問,缺乏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情感保障的資本主義社會,絕對不符合人類理想社會的標準,它在歷史某個特定階段所暫時呈現出來的某些令人炫目的光環,都是建立在極其不可靠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之上的。
作者:李建宏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畢業,現旅居加拿大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