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件四”:1953年4月18日原蘇聯(lián)駐朝鮮大使、軍事顧問主席拉祖瓦耶夫?qū)ω惱旁儐柕年愂觯?/section>
金日成和外交部長(zhǎng)就國(guó)際代表團(tuán)(按:法律團(tuán))到來一事與我聯(lián)系——在蘇聯(lián)顧問的協(xié)助下,衛(wèi)生部實(shí)施一項(xiàng)計(jì)劃有了好的結(jié)果。偽造了瘟疫地區(qū),對(duì)那些已經(jīng)死亡的尸體的埋葬和暴露進(jìn)行了布置,對(duì)瘟疫和霍亂病菌進(jìn)行了計(jì)算測(cè)定。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guó)內(nèi)務(wù)部向那些已經(jīng)被宣判死刑的瘟疫與霍亂病毒感染者提出征詢要求,以便在他們死后進(jìn)行與醫(yī)藥學(xué)要求相符合的準(zhǔn)備。在法學(xué)家代表團(tuán)到來之前,那些材料被送到北京進(jìn)行展覽。
斯利瓦諾夫的陳述,以自己不久回國(guó)為由,并沒有說出朝鮮造假的任何事實(shí)。拉祖瓦耶夫作為大使,當(dāng)然也不可能親自操作,所談也只是間接聽聞。實(shí)際情況是:“法律團(tuán)”是由奧地利、意大利、英國(guó)、法國(guó)、中國(guó)、比利時(shí)、巴西、波蘭等8國(guó)的著名的法學(xué)家組成的,在朝鮮活動(dòng)時(shí)間是1952年3月3日到3月19日,調(diào)查了美軍在朝鮮使用細(xì)菌武器、屠殺平民、破壞文物等一系列戰(zhàn)爭(zhēng)罪行。蘇聯(lián)情報(bào)官指控的“偽造疫區(qū)”事件,既然鎖定為“法律團(tuán)”到達(dá)朝鮮“前夕”,那么如果屬實(shí),則只能是在3月3日之前發(fā)生的霍亂和鼠疫案例。據(jù)法律團(tuán)的調(diào)查報(bào)告,所記載的疫病流行致死案例只有兩處:一是鐵原郡北面區(qū)的霍亂案例,二是安州郡發(fā)南里的鼠疫案例。原文是:
“第一個(gè)患霍亂的人是在2月20日發(fā)現(xiàn)的。這個(gè)人是江原道鐵原郡北面區(qū)的四十歲的金學(xué)文,他在2月23日死亡。2月25日,同村的三十五歲的金逑善也生病。”[1]718
“第一個(gè)患鼠疫的人是在2月25日發(fā)現(xiàn)的。他是安州郡發(fā)南里的黃利彩,年二十九歲。他的病勢(shì)垂危。2月29日,同村的樸善玉(二十六歲)生病了。在這個(gè)事件中,確定在2月28日發(fā)現(xiàn)含有鼠疫菌的蒼蠅。截止調(diào)查團(tuán)訪問安州時(shí)為止,這個(gè)村中患鼠疫的人數(shù)達(dá)五十人,其中有三十六人死亡。”[1]719
這兩個(gè)案例都發(fā)生在1952年2月中下旬。我們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這個(gè)時(shí)候反細(xì)菌戰(zhàn)斗爭(zhēng)還沒有正式開始。如周恩來總理所說,對(duì)美國(guó)的細(xì)菌戰(zhàn)我們是“倉(cāng)促應(yīng)戰(zhàn)”的。1952年1月28日志愿軍戰(zhàn)士第一次發(fā)現(xiàn)美軍撒布大量昆蟲,經(jīng)中朝軍民繼續(xù)觀察,到2月下旬,黨中央掌握了充分的證據(jù),才做出反細(xì)菌戰(zhàn)的決策。2月21日通告全軍全國(guó),正式開始反細(xì)菌戰(zhàn)斗爭(zhēng),建立各級(jí)防疫機(jī)構(gòu),組織防疫檢驗(yàn)力量。第一批由細(xì)菌學(xué)、昆蟲學(xué)、流行病學(xué)專家組成防疫檢驗(yàn)隊(duì),2月29日才自北京出發(fā),赴朝鮮開展工作。朝鮮基本和我國(guó)同步,2月20日頒發(fā)“關(guān)于對(duì)敵人細(xì)菌戰(zhàn)展開斗爭(zhēng)的對(duì)策”,2月29日,金日成向全國(guó)發(fā)布關(guān)于“與敵人的細(xì)菌戰(zhàn)進(jìn)行斗爭(zhēng)的對(duì)策”的命令,才正式建立防疫機(jī)構(gòu),明確防疫政策,組織和動(dòng)員力量,開展反細(xì)菌戰(zhàn)斗爭(zhēng)。

這個(gè)“時(shí)間表”說明,在1952年2月,中朝軍民對(duì)細(xì)菌戰(zhàn)的認(rèn)識(shí)還不明確,防疫檢驗(yàn)機(jī)制還沒有全面啟動(dòng),對(duì)于疫病患者、死亡者,也只能是倉(cāng)促處理,不可能按反細(xì)菌戰(zhàn)的要求來進(jìn)行。特別是對(duì)于感染而死亡者,及時(shí)埋葬,焚燒遺物,不可能留下完備的尸檢、病理資料。這種狀況,從在北京舉辦的“美國(guó)政府細(xì)菌戰(zhàn)罪行展覽會(huì)”的展出內(nèi)容便可反映出來:展出的“實(shí)物”,基本是1952年3月以后收集的;特別是“病理部分”,包括在朝鮮發(fā)生的霍亂、鼠疫死亡病例,全部是3月上旬及之后發(fā)生的案例資料[2]。因此,在2月末,朝鮮方面得知法律團(tuán)的要到來,起初擔(dān)心資料缺漏,向蘇聯(lián)顧問咨詢,這是可想而知的。對(duì)于朝鮮向“法律團(tuán)”的陳述報(bào)告,蘇聯(lián)顧問可能給了一些建議,然而所謂“偽造疫區(qū)”,則似乎并未發(fā)生。因?yàn)閺乃膫€(gè)月后“科學(xué)團(tuán)”的調(diào)查報(bào)告可知,“科學(xué)團(tuán)”專家在匯集、審查之前的細(xì)菌戰(zhàn)各種資料時(shí),肯定朝鮮方面對(duì)2月底之前發(fā)現(xiàn)的美軍撒布細(xì)菌媒介物、居民感染病死情況,當(dāng)時(shí)只給“法律團(tuán)”提供了一份綜合報(bào)告:
朝鮮保健省的第一個(gè)報(bào)告(SIA/1)是講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份至二月份的事件。這個(gè)報(bào)告所包含的材料,再度被國(guó)際民主法律 工作者協(xié)會(huì)調(diào)查團(tuán)報(bào)告書中整理過。這一報(bào)告書(按:指“法律 團(tuán)”最后的調(diào)查報(bào)告,代號(hào)S1A/4)增加了朝鮮發(fā)現(xiàn)鼠疫的資料,當(dāng)然還有這批國(guó)際人士親自詢問人證的結(jié)果。[3]7
也就是說,對(duì)兩個(gè)有感染死亡病例的“疫區(qū)”,其中鐵原郡北面區(qū)霍亂案例,可能因涉及人數(shù)較少,法律團(tuán)完全依照了朝鮮的綜合報(bào)告。對(duì)安州發(fā)南里的鼠疫案例的介紹,朝鮮方面也只是包括在這份對(duì)一、二月份的綜合報(bào)告中,并沒有提供其他材料。是“法律團(tuán)”的專家們,按照法律要求,對(duì)“鼠疫”疫區(qū),又親自詢問了證人,增加了資料,掌握了證據(jù),才予以確認(rèn)的。可以推想,這些法學(xué)家們完全理解,在一、二月份,那些居民感染死亡時(shí),朝鮮方面還沒有時(shí)間和條件進(jìn)行尸檢及細(xì)菌培養(yǎng)試驗(yàn)的。蘇聯(lián)情報(bào)官員所指控的,把已判死刑的鼠疫患者毒死、作病理檢驗(yàn)、細(xì)菌學(xué)檢驗(yàn)來提供資料,似乎是捕風(fēng)捉影、甚至是無中生有的。“科學(xué)團(tuán)”復(fù)審了朝鮮和“法律團(tuán)”的資料,認(rèn)可了他們的結(jié)論。對(duì)此,“法律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奧地利著名國(guó)際法學(xué)家布蘭德魏納教授說:
“我很高興地知道國(guó)際科學(xué)委員會(huì)的報(bào)告書完全證實(shí)了我們所見的一切。這也證明了中國(guó)和朝鮮的科學(xué)家們所發(fā)表的聲明是十分可靠的。......我也感到驕傲,因?yàn)閲?guó)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xié)會(huì)的調(diào)查團(tuán)是第一批打開了真理大門的人。我對(duì)于真理必勝是深信不疑的。”[4]
朝鮮方面沒有偽造,下面這件事也可作為旁證:1952年7月30日,“科學(xué)團(tuán)”專家審查朝鮮提供的各個(gè)重要案例資料時(shí),有針對(duì)性地提出了17個(gè)問題,要求朝鮮保健相作些準(zhǔn)備給予答復(fù)。關(guān)于安州發(fā)南里的鼠疫案例,“科學(xué)團(tuán)”提出,“關(guān)于這個(gè)案件,委員會(huì)能否得到一些更多的詳情?”21天之后,即8月20日,保健相逐條回答“科學(xué)團(tuán)”的問題時(shí),對(duì)安州發(fā)南里鼠疫問題的答復(fù)是:“鼠疫 唯一有關(guān)的補(bǔ)充資料就是鼠疫病例是在發(fā)現(xiàn)跳蚤三天之后出現(xiàn)。
“應(yīng)該提到的是最初的病例是腺鼠疫,后來才有肺鼠疫。疫病傳染的很快。”[3]146
朝鮮保健相并沒有利用這段準(zhǔn)備時(shí)間,去添加虛假證據(jù)資料。所以,按“抄件”之十,即蘇共中央監(jiān)察委員根據(jù)貝利亞的報(bào)告,質(zhì)詢伊格納季耶夫時(shí),伊格納季耶夫坦承,一年前收到了格魯霍夫和斯米爾諾夫的指控信,但是,他“沒有認(rèn)為這個(gè)備忘錄有任何重要性。他不相信這個(gè)備忘錄中包含真實(shí)可靠的信息。”而且,伊格納季耶夫還聲稱,他并沒有將這件事隱而未報(bào),在1952年七八月間,斯大林因事召見他,他當(dāng)時(shí)曾經(jīng)出示此備忘錄給斯大林。此情節(jié)因?yàn)樗勾罅秩ナ蓝鵁o法證實(shí),但這并不說明一定是伊格納季耶夫?yàn)樽约洪_脫的謊言。相反,從斯大林對(duì)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的一貫態(tài)度,可反證伊格納季耶夫所說是有可信性的。1952年2月21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通告美國(guó)開始在朝鮮使用細(xì)菌武器,以及我方的應(yīng)對(duì)措施。斯大林于2月23日回復(fù),明確指出,“對(duì)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必須做出回應(yīng)”,“以便使反對(duì)帝國(guó)主義的陣營(yíng)采取重大的反擊措施”,蘇聯(lián)將積極支持中國(guó)和朝鮮的行動(dòng)[5]178。1952年3月14日,斯大林致電周恩來,同意中國(guó)的請(qǐng)求,向中國(guó)派遣9名細(xì)菌學(xué)專家,4月10之前發(fā)送預(yù)防鼠疫疫苗500萬劑,霍亂疫苗380萬劑,傷寒副傷寒疫苗850萬劑,以及大量的消毒劑滴滴涕等,并盡快將一部分空運(yùn)到北京[5]192。后來蘇聯(lián)派茹科夫院士參加國(guó)際科學(xué)委員會(huì)赴中朝調(diào)查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1952年12月9日,包括茹科夫在內(nèi)的蘇聯(lián)著名科學(xué)家,參加即將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huì)前,對(duì)塔斯社發(fā)表談話,強(qiáng)烈譴責(zé)美帝國(guó)主義的侵略和細(xì)菌戰(zhàn)罪行[6]。直到1952年末、1953年初,中國(guó)保衛(wèi)和平委員會(huì)向蘇聯(lián)致送“科學(xué)團(tuán)”的調(diào)查報(bào)告,雙方關(guān)于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問題都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和一致的立場(chǎng)。所以,伊格納季耶夫說1952年七八月曾將格魯霍夫和斯米爾諾夫的報(bào)告給斯大林看過,當(dāng)然斯大林并不會(huì)相信其內(nèi)容。
二、1952年秋,國(guó)際科學(xué)委員會(huì)調(diào)查團(tuán)也受朝鮮欺騙了?
蘇聯(lián)情報(bào)官員指控的第二個(gè)事件,即1952年7月“科學(xué)團(tuán)”來朝鮮調(diào)查時(shí),朝鮮又制造了某種假象:1.“文件”二:1953年4月13日,蘇聯(lián)內(nèi)務(wù)部反間諜局副局長(zhǎng),前北朝鮮公安部顧問格魯霍夫致貝利亞:1952年6月到 7月,來自世界和平會(huì)議的一個(gè)細(xì)菌學(xué)專家代表團(tuán)抵達(dá)北朝鮮。兩個(gè)爆炸現(xiàn)場(chǎng)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準(zhǔn)備完畢。與此相關(guān)的是,朝鮮人堅(jiān)持要得到尸體上的霍亂細(xì)菌,這些尸體將來自中國(guó)。在包括研究院院士,前任國(guó)家安全部成員茹科夫在內(nèi)的這個(gè)代表團(tuán)的工作期間,經(jīng)我們的顧問的幫助,制造了一種非真實(shí)的情況,以便于嚇唬并逼走代表團(tuán)。在我們的人民軍工程技術(shù)部門的顧問彼得羅夫中尉領(lǐng)導(dǎo)下,爆炸地點(diǎn)被設(shè)在代表團(tuán)停留的地方附近,況且當(dāng)他們?cè)谄饺榔陂g,假空襲警報(bào)多次響起。
2. “文件”四,1953年4月18日,原蘇聯(lián)駐朝鮮大使、軍事顧問主席拉祖瓦耶夫致貝利雅的“備忘錄”:在第二個(gè)代表團(tuán)到來之前,衛(wèi)生部長(zhǎng)為獲得細(xì)菌樣品前往北京。然而,他們沒有給他。但是晚些時(shí)候,他們?cè)谀驴祟D[Mukden——按即沈陽(yáng)]給了他。此外,在平壤,一種純粹的霍亂菌樣品被采集。這種菌樣來自一個(gè)因食用腐爛食品而死亡的家庭成員的尸體。第二個(gè)國(guó)際代表團(tuán)當(dāng)時(shí)在北京,它沒有到訪北韓的特定地區(qū),因?yàn)椋表n的展覽設(shè)在北京。在代表團(tuán)調(diào)查的地區(qū),地雷(偽造的——原英譯注)沒有爆炸。……
這兩位蘇聯(lián)官員的指控,主要是兩個(gè)問題:
一是所謂細(xì)菌樣品(一說霍亂菌,一說鼠疫菌),朝鮮是從中國(guó)取來的。甚至聳人聽聞地說:“朝鮮人堅(jiān)持要得到尸體上的霍亂細(xì)菌,這些尸體將來自中國(guó)”!
這種編造實(shí)在太拙劣了。當(dāng)時(shí)的情況是,為了向全世界揭露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罪行,我國(guó)曾在北京和沈陽(yáng)舉辦了“美國(guó)政府細(xì)菌戰(zhàn)罪行展覽會(huì)”(1953年還在歐洲巡回展出),展出美國(guó)進(jìn)行細(xì)菌戰(zhàn)爭(zhēng)的史實(shí)、人證、物證,有關(guān)調(diào)查報(bào)告等。鑒于當(dāng)時(shí)形勢(shì),朝鮮的典型資料,也都送到中國(guó)這個(gè)展覽會(huì)中。展覽會(huì)備有顯微鏡,觀眾可以現(xiàn)場(chǎng)觀察案例的細(xì)菌涂片。從當(dāng)年新華社記者對(duì)展覽會(huì)的記述看,其中第四室專門陳列朝鮮發(fā)生的霍亂和鼠疫病例資料,如3月上旬,平壤居民韓相國(guó)感染霍亂、祖孫三口死亡案例;5月中旬大同郡農(nóng)民趙萬福夫婦誤食美軍投撒的蛤蜊而患霍亂致死案例;4月份江西郡農(nóng)民樸然浩接觸美軍投撒的跳蚤感染鼠疫致死案等[2]。所以,為迎接“科學(xué)團(tuán)”的調(diào)查,朝鮮官員擔(dān)心物證不足,特從中國(guó)取回細(xì)菌樣品,這并不奇怪,也絕非朝鮮與中國(guó)合謀造假。不過,此舉有點(diǎn)多余,因?yàn)檎{(diào)查團(tuán)在北京已經(jīng)參觀過展覽了。
二是,所謂偽造兩處“爆炸現(xiàn)場(chǎng)”(按:應(yīng)即疫區(qū))。明眼人一下就可看出,這純屬于無稽之談。當(dāng)時(shí)因?yàn)槲曳娇哲姷难杆侔l(fā)展、蘇聯(lián)部分空軍的參戰(zhàn),美軍已經(jīng)失去了對(duì)朝鮮北方和中國(guó)東北的部分制空權(quán),同時(shí)也為了掩蓋其罪行,美軍飛機(jī)投撒帶菌媒介物,一般都是夜間飛行悄悄施行的,投擲的多是“不爆炸的炸彈”,不存在劇烈“爆炸”問題。所謂在調(diào)查團(tuán)駐地附近,頻發(fā)假空襲警報(bào),制造假爆炸,形成恐怖氣氛,恐嚇、逼使調(diào)查團(tuán)草草從事、離開朝鮮等等,更似荒誕不經(jīng)的童話,不值一駁。
但是,“文件四”,即拉祖瓦耶夫?qū)ω惱麃喸儐柕幕貜?fù)中說到,“從1953年1月起,關(guān)于美國(guó)使用細(xì)菌武器的公開報(bào)道在朝鮮終止。1953年2月,中國(guó)再度向朝鮮呼吁揭露美國(guó)在細(xì)菌戰(zhàn)中的面目。朝鮮沒有接受這項(xiàng)建議。”
這是不符合實(shí)際的。朝鮮是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最直接的受害者,也是見證者,怎么會(huì)停止抨擊美國(guó)的罪行呢?
在朝鮮戰(zhàn)爭(zhēng)停戰(zhàn)前,朝鮮政府都和我國(guó)政府密切配合,揭露譴責(zé)美軍細(xì)菌戰(zhàn)罪行,即使在以后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間里,都是如此。如1956年4月舉行的朝鮮勞動(dòng)黨第三次代表大會(huì),金日成的總結(jié)報(bào)告和一些代表的發(fā)言,普遍抨擊美國(guó)的侵朝戰(zhàn)爭(zhēng),多次肯定戰(zhàn)勝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的斗爭(zhēng)。金日成指出:
“我們?nèi)w勞動(dòng)人民,在美帝主義的狂轟濫炸的環(huán)境下,甚至在殺人的毒氣彈和細(xì)菌彈炸裂的艱苦環(huán)境中,也寧死不屈,只為了扼守自己的崗位,展開了英勇的斗爭(zhēng)。”[7]
對(duì)于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也寫進(jìn)朝鮮的歷史著作中。朝鮮著名歷史學(xué)家金漢吉教授所著的《朝鮮現(xiàn)代史》,用近2000字設(shè)立“細(xì)菌戰(zhàn)”專節(jié),敘述粉碎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的歷史過程[8]。
三、“抄件”事件,是貝利亞政治策劃的一部分
對(duì)這12分“抄件”內(nèi)在聯(lián)系加以分析,可分成三組:第一組,對(duì)伊格納季耶夫的指控和貝利亞的調(diào)查。“文件二”1953年4月13日格魯霍夫致給貝利亞的“備忘錄”,揭露伊格納季耶夫隱瞞了他們一年前的一份報(bào)告,指控蘇聯(lián)駐朝鮮大使館官員,幫助朝鮮偽造細(xì)菌戰(zhàn)疫區(qū)等,由此引出貝利亞對(duì)有關(guān)人員詢問及反饋。“文件三”、“文件四”,即蘇聯(lián)原駐朝鮮大使及衛(wèi)生顧問對(duì)貝利亞詢問的反饋,陳述朝鮮在迎接兩個(gè)國(guó)際調(diào)查團(tuán)時(shí)的態(tài)度和活動(dòng)。第二組,即“文件五”、“文件六”、“文件十”、“文件十二”。在格魯霍夫揭發(fā)的8天后,1853年4月21日,貝利亞將伊格納季耶夫問題報(bào)告蘇聯(lián)部長(zhǎng)會(huì)議主席和蘇共中央主席團(tuán),認(rèn)定為伊格納季耶夫隱瞞了“具有特殊政治重要性的備忘錄報(bào)告”,損害了蘇聯(lián)國(guó)家的政治信譽(yù),要求中央對(duì)伊格納季耶夫進(jìn)行調(diào)查、懲處。“文件十”和“文件十二”,即蘇共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huì)報(bào)告對(duì)伊格納季耶夫詢問、調(diào)查結(jié)果及處分決定:撤銷其蘇共中央委員,開除出黨,繼而又“清除出黨”。第三組,“文件一”、“文件八”、“文件九”、“文件十一”,除“文件一”是1952年2月毛澤東主席致電斯大林,通報(bào)美軍開始細(xì)菌戰(zhàn)之外,其他則是蘇聯(lián)政府通知其駐中國(guó)和朝鮮大使,令中國(guó)和朝鮮政府停止對(duì)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的譴責(zé),以及中、朝態(tài)度的反饋。從這些文件明顯可以歸結(jié)出兩點(diǎn):第一,不管是格魯霍夫主動(dòng)揭發(fā),還是貝利亞獲知線索而引爆這一事件,操縱者明顯都是貝利亞。貝利亞長(zhǎng)期掌控內(nèi)務(wù)部,格魯霍夫是他的屬下,這自然使人想到,他的發(fā)難是貝利亞一手策劃的。接著,貝利亞調(diào)查、詢問了兩個(gè)人員,雖然兩人都不是所謂“偽造疫區(qū)”的直接在場(chǎng)者,但貝利亞就匆忙得出結(jié)論,報(bào)告蘇共中央。第二,貝利亞提供的證據(jù),并非有案可查的文件,而是在一周之內(nèi)產(chǎn)生的個(gè)人書寫,而且還不是直接在場(chǎng)者的證詞(1952年春格魯霍夫和斯米爾諾夫兩人的報(bào)告,沒見披露出來。當(dāng)然,他們兩人也并非直接在場(chǎng)者)。證據(jù)如此單薄,而蘇共中央在10天后,僅詢問了一下伊格納季耶夫,并沒有對(duì)朝鮮的實(shí)況作詳細(xì)調(diào)查,就倉(cāng)促做出兩項(xiàng)關(guān)乎國(guó)內(nèi)國(guó)際的重大決定——對(duì)伊格納季耶夫清除出黨;蘇聯(lián)政府改變對(duì)美國(guó)的態(tài)度,并要求中國(guó)和朝鮮停止譴責(zé)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這種草率處理,應(yīng)該是是貝利亞策劃要達(dá)到、也是有把握得到的結(jié)果。貝利亞長(zhǎng)期掌控蘇聯(lián)秘密警察部隊(duì),羅織罪名,致人死地,是他的看家本領(lǐng)。何況這時(shí)正值斯大林逝世后,蘇聯(lián)政府和黨都處在不正常的特殊情況下。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逝世(有一種說法認(rèn)為是貝利亞謀害的),并沒有安排好國(guó)家和黨領(lǐng)導(dǎo)權(quán)力的合理過渡,遂使蘇聯(lián)領(lǐng)導(dǎo)集團(tuán)展開了一場(chǎng)激烈、殘酷的權(quán)力角逐。綜合國(guó)內(nèi)外對(duì)蘇聯(lián)這特殊時(shí)期的研究,不難看出,貝利亞拿伊格納季耶夫開刀,其目的主要有三:第一,報(bào)復(fù)、打擊伊格納季耶夫,徹底消除其在原安全部的影響,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自己對(duì)內(nèi)務(wù)部及國(guó)家秘密警察部隊(duì)的掌控。貝利亞的地位是靠著斯大林的器重而迅速提升的。1938年,他39歲被任命為蘇聯(lián)國(guó)家內(nèi)務(wù)部長(zhǎng),之后又進(jìn)入國(guó)家和黨的領(lǐng)導(dǎo)核心,但仍掌控內(nèi)務(wù)部及安全部門。然而,斯大林晚年對(duì)貝利亞的野心已經(jīng)有所察覺,開始有計(jì)劃地削減貝利亞的勢(shì)力,甚至將其除掉。1951年底,貝利亞的親信阿巴庫(kù)莫夫突然被解除國(guó)家安全部長(zhǎng)職務(wù),接替他的是伊格納季耶夫。有人認(rèn)為,斯大林提名伊格納季耶夫任職,很可能意味著貝利亞末日的開始。這位新部長(zhǎng)上任后,立即在安全機(jī)關(guān)內(nèi)部進(jìn)行了清洗,削弱貝利亞的影響。同時(shí)大肆逮捕蘇聯(lián)在布拉格機(jī)構(gòu)里的人員,包括奉貝利亞的命令在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里工作的高級(jí)警官[9]405-406。緊接著,伊格納季耶夫又下令逮捕了格魯吉亞共產(chǎn)黨第一書記科捷·恰爾克維亞尼,他是貝利亞在第比利斯的最親密和最忠誠(chéng)的同事之一。由此炮制出所謂的“明格列爾民族主義分子陰謀案”,涉案人員都是貝利亞在格魯吉亞工作時(shí)期培植的親信和屬下,而貝利亞本人就是地道的明格列爾人。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說,明格列爾人案就是斯大林為了除掉貝利亞而捏造出來的[10]。但是,斯大林未及實(shí)現(xiàn)預(yù)定計(jì)劃就突然去世了。貝利亞重掌內(nèi)務(wù)部,并且安全部并入內(nèi)務(wù)部。伊格納季耶夫雖然離開了安全部,但還是黨中央主席團(tuán)成員,中央書記之一,分工監(jiān)管政法系統(tǒng)。所以,貝利亞必然要徹底打擊伊格納季耶夫,清除他在安全部系統(tǒng)遺留的影響。貝利亞首先為“克里姆林宮醫(yī)生謀殺案”平反,處死了經(jīng)手此案的原安全部副部長(zhǎng)伊格納季耶夫的副手柳明。接著便由格魯霍夫發(fā)難,捕風(fēng)捉影、夸大事實(shí),羅織罪名,以至將伊格納季耶夫清除出黨。幸而伊格納季耶夫依靠著赫魯曉夫,免了一死,在貝利亞垮臺(tái)后又得平反。第二,削弱赫魯曉夫的勢(shì)力,為攫取蘇聯(lián)最高權(quán)力作準(zhǔn)備。研究者一般都承認(rèn),貝利亞隨著地位的提升、權(quán)力的擴(kuò)大,政治野心迅速膨脹。斯大林去世后,蘇聯(lián)領(lǐng)導(dǎo)核心形成了兩派:一派是馬林科夫、貝利亞。當(dāng)時(shí)他們是國(guó)家一、二號(hào)人物,掌握著國(guó)家行政系統(tǒng)、內(nèi)衛(wèi)部隊(duì)和秘密警察,占居優(yōu)勢(shì)。二是赫魯曉夫、布爾加寧派,掌握著黨務(wù)系統(tǒng)和軍隊(duì)。伊格納季耶夫在任安全部長(zhǎng)之前,一直是黨務(wù)干部,與赫魯曉夫更為接近,甚至說是赫魯曉夫的親信[11],除掉他,自然就削弱了赫魯曉夫派的力量。第三,否認(rèn)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轉(zhuǎn)變對(duì)美國(guó)的外交政策,取悅美國(guó)和西方,同時(shí)改變自己的國(guó)內(nèi)、國(guó)際形象,為篡奪蘇聯(lián)最高領(lǐng)導(dǎo)地位創(chuàng)造條件。貝利亞是從“肅反”工作發(fā)跡、又一直是斯大林“肅反”工作的最有力助手,蘇聯(lián)肅反工作的嚴(yán)重?cái)U(kuò)大化,使貝利亞也被人們視為“劊子手”、“政治殺手”、“嗜血鷹犬”等等。這些稱號(hào),雖然帶著西方對(duì)斯大林時(shí)期蘇聯(lián)社會(huì)抹黑的因素,但也表明,不論在蘇聯(lián)還是在西方人眼里,貝利亞都是一個(gè)冷酷、殘忍、野心勃勃的形象。斯大林逝世,給貝利亞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登上蘇聯(lián)最高領(lǐng)導(dǎo)人地位的契機(jī)。可以說,貝利亞完全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在斯大林逝世后的短時(shí)間內(nèi),其他核心成員還耽思蘇聯(lián)走向的時(shí)候,貝利亞則表現(xiàn)得特別活躍,他不僅對(duì)自己主管的領(lǐng)域提出議案,而且跨領(lǐng)域地對(duì)黨建、政治、外交、民族、經(jīng)濟(jì)等等,都提出一系列議案,要中央通過。他利用馬林科夫名為國(guó)家第一號(hào)人物,但是軟弱、缺乏執(zhí)政能力的弱點(diǎn),自己頤指氣使,飛揚(yáng)跋扈,儼然就是國(guó)家和黨的第一號(hào)領(lǐng)導(dǎo)人。他提議的大赦百萬在押犯,為克里姆林宮醫(yī)生謀殺案、明格列爾人案平反,各民族地區(qū)主要領(lǐng)導(dǎo)必須由民族干部擔(dān)任等,也許有一定積極意義,同時(sh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在蘇聯(lián)人心目中給自己蒙上親民的色彩。在國(guó)際,他主張東德放棄社會(huì)主義道路、恢復(fù)和南斯拉夫黨和政府的關(guān)系,緩和與美國(guó)的關(guān)系,可以說都是意圖在西方建立自己新形象、取得西方廣泛支持。為達(dá)此目的,貝利亞不惜使用過去“大清洗”中栽贓陷害的方法,既整垮伊格納季耶夫,也一舉把中、朝反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的斗爭(zhēng)都說成是偽造,為蘇聯(lián)轉(zhuǎn)變對(duì)美國(guó)的外交政策制造合理借口。我們拋開蘇聯(lián)當(dāng)時(shí)內(nèi)部斗爭(zhēng)的是非、貝利亞的功過,單就對(duì)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一事,可以斷定,他未免太“天真”了:中國(guó)做出反細(xì)菌戰(zhàn)的決策,是建立在廣大軍民千百次發(fā)現(xiàn)、大量人證物證,科學(xué)家嚴(yán)格鑒定檢驗(yàn)基礎(chǔ)之上的,也是綜合了美國(guó)研發(fā)使用細(xì)菌武器的大量情報(bào)信息而認(rèn)定的,豈是憑一二人隨意編造就可否定?
同樣,朝鮮對(duì)1952年一、二月發(fā)生的案例沒有留下完備的資料,但是三月之后的案例都做了完備的記錄,經(jīng)過了科學(xué)鑒定、檢驗(yàn),怎么能由貝利亞策劃的那種指控將其一筆抹煞呢?
四、“抄件”主要并非嚴(yán)肅文件,帶著個(gè)人色彩
人們一看“抄件”來自于“蘇聯(lián)總統(tǒng)檔案館”,有的后來又出現(xiàn)在俄羅斯的解密檔案中,就以為它是內(nèi)部文件、絕對(duì)可靠,無可置疑。殊不知,其中大部分并非蘇、中、朝黨政機(jī)構(gòu)的正式文件,而是某些情報(bào)人員、官員倉(cāng)促之間的個(gè)人書寫,或者說是在蘇聯(lián)領(lǐng)導(dǎo)核心陷入內(nèi)斗、政治局面短暫混亂時(shí)期,作為內(nèi)爭(zhēng)手段的檢舉信、信息報(bào)告。其中屬于貝利亞策劃而來的,多是栽贓陷害的虛假不實(shí)之詞,即使蘇聯(lián)外交人員向蘇聯(lián)領(lǐng)導(dǎo)人的匯報(bào),也不免帶著明顯的個(gè)人色彩,對(duì)事實(shí)有所歪曲。如“文件九”,1953年5月11日,蘇聯(lián)大使受命向中國(guó)領(lǐng)導(dǎo)人通報(bào)蘇聯(lián)政府的意見,要求停止譴責(zé)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罪行,毛主席沒有用斬釘截鐵的話語(yǔ)馬上給頂回去,而是用稍模糊的、外交語(yǔ)言,婉轉(zhuǎn)地拒絕了蘇聯(lián)的意見。然而蘇聯(lián)大使在向蘇聯(lián)領(lǐng)導(dǎo)人匯報(bào)時(shí),卻把毛主席描繪成聽了蘇聯(lián)的意見,“顯示出某種程度的緊張,他吸煙很多,碾碎那些煙并喝下許多茶。”而且說出“中國(guó)反細(xì)菌戰(zhàn)的行動(dòng)是基于在朝鮮和東北的中國(guó)人民志愿軍指揮部的報(bào)告開始的;目前,要證明這些報(bào)告的確實(shí)性是困難的......”這種歪曲描述,以至造成某些人誤解,連朱正這樣的著名學(xué)者也認(rèn)為“最后毛澤東本人也對(duì)這件事情的真實(shí)性提出了質(zhì)疑。”[12] 真是天大的笑話!毛主席對(duì)于美國(guó)所實(shí)行的細(xì)菌戰(zhàn),何曾有過一時(shí)一刻的猶疑?再如,“文件第十一”,1953年6月1日,蘇聯(lián)外交人員向朝鮮領(lǐng)導(dǎo)人傳達(dá)蘇聯(lián)政府意見,要求停止揭露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金日成稱病未見,朝鮮勞動(dòng)黨樸成永聽了蘇聯(lián)外交官的傳達(dá),竟然發(fā)生了如下情況:“樸成永沒有排除下列可能:那些炸彈和里面的東西是從中國(guó)飛機(jī)上投下來的,況且里面也沒有細(xì)菌。”這除了是那位蘇聯(lián)外交官的歪曲甚至編造,還有別的解釋嗎?
好在蘇聯(lián)的其他領(lǐng)導(dǎo)人很快發(fā)現(xiàn)了貝利亞的陰謀,1953年6月26日將其逮捕,關(guān)于否定美國(guó)細(xì)菌戰(zhàn)的這出鬧劇也就中止。現(xiàn)在,一些人企圖推翻這樁歷史鐵案,也必將是徒勞的。
① 本文所引“抄件”來自網(wǎng)絡(luò)。有兩件參考了《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 中蘇關(guān)系 第4卷》中正式公布的譯文;全部標(biāo)題參考了《李約瑟大典 傳記學(xué)術(shù)年譜長(zhǎng)編事典 下》“俄羅斯藏朝鮮戰(zhàn)爭(zhēng)細(xì)菌戰(zhàn)事件檔案”,北京:中國(guó)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 , 2012.第930頁(yè)。[1] 國(guó)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xié)會(huì)調(diào)查團(tuán):關(guān)于美國(guó)在朝鮮的罪行的報(bào)告//中美關(guān)系 資料匯編第二輯 [2]新華社記者 林麟:斬?cái)嗝绹?guó)細(xì)菌戰(zhàn)犯?jìng)兊淖飷貉?mdash;—記美國(guó)政府細(xì)菌戰(zhàn)罪行展覽會(huì)的 病理部分//人民日?qǐng)?bào).1952年9月18日第3版[3]調(diào)查在朝鮮和中國(guó)的細(xì)菌戰(zhàn)事實(shí) 國(guó)際科學(xué)委員會(huì)報(bào)告書.1952。[4]黃季方:中國(guó)人民志愿軍是最好的和平保衛(wèi)者——布蘭德偉納教授訪問記// 世界知識(shí),1952年第40期[5]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 中蘇關(guān)系 第4卷 1951.9-1954.1//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01,第178頁(yè)[6]1952年12月16日新華社新聞稿,1952年12月896頁(yè)[7]金日成:朝鮮勞動(dòng)黨第三次代表大會(huì)文件集//平壤:外國(guó)文出版社,1956.,第18頁(yè)[8]金漢吉:朝鮮現(xiàn)代史//平壤:外國(guó)文出版社,1980,第359頁(yè)[9]威特林(Wittlin,T.)著;王 偉,張多一譯:政治殺手貝利亞//beijing :中國(guó) 華僑出版社,1989.02,第405—406頁(yè)[10] 愛德華·克蘭克肖:赫魯曉夫回憶錄 下//beijing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11]黃殿偉著,噬血鷹犬-貝利亞//北京:世界知識(shí)出版社,1999.02,第339頁(yè)[12]朱正,當(dāng)代學(xué)人精品 朱正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07,第143頁(yè)(來源:昆侖策網(wǎng)【原創(chuàng)】)【本公眾號(hào)所編發(fā)文章歡迎轉(zhuǎn)載,為尊重和維護(hù)原創(chuàng)權(quán)利,請(qǐng)轉(zhuǎn)載時(shí)務(wù)必注明原創(chuàng)作者、來源網(wǎng)站和公眾號(hào)。閱讀更多文章,請(qǐng)點(diǎn)擊微信號(hào)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zhàn)略研究和咨詢服務(wù)機(jī)構(gòu),遵循國(guó)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duì)國(guó)家、對(duì)社會(huì)、對(duì)客戶負(fù)責(zé),講真話、講實(shí)話的信條,追崇研究?jī)r(jià)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shí)情、獻(xiàn)明策,為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guó)夢(mèng)”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qǐng)看《昆侖策網(wǎng)》,網(wǎng)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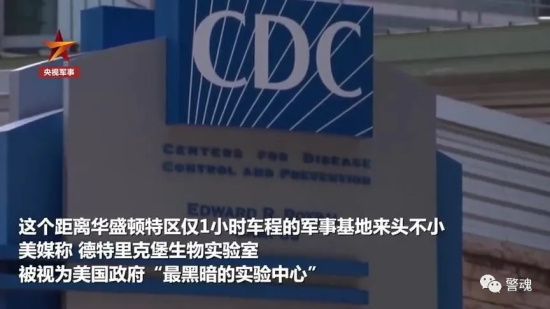 在美德堡工作的印裔曝光:病毒制造后泄露,導(dǎo)師及知情者被暗殺
在美德堡工作的印裔曝光:病毒制造后泄露,導(dǎo)師及知情者被暗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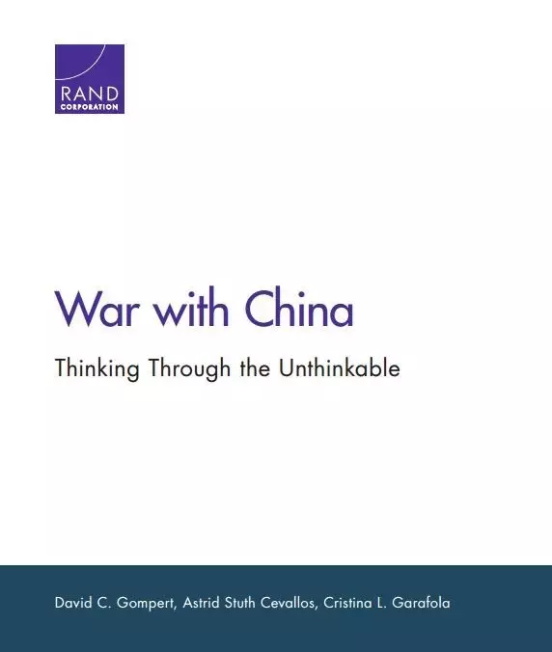 美國(guó)蘭德公司的最新報(bào)告《與中國(guó)開戰(zhàn)——想不敢想之事》
美國(guó)蘭德公司的最新報(bào)告《與中國(guó)開戰(zhàn)——想不敢想之事》 王立華:新冠疫災(zāi)嚴(yán)重警示我們,要盡快建立國(guó)家生化安全防衛(wèi)體系
王立華:新冠疫災(zāi)嚴(yán)重警示我們,要盡快建立國(guó)家生化安全防衛(wèi)體系 朱妙寬:完善干部人事制度 ——關(guān)于“十四五”規(guī)劃的十四條建議(二)
朱妙寬:完善干部人事制度 ——關(guān)于“十四五”規(guī)劃的十四條建議(二) 朱妙寬:完善干部人事制度 ——關(guān)于“十四五”規(guī)劃的十四條建議(二)
朱妙寬:完善干部人事制度 ——關(guān)于“十四五”規(guī)劃的十四條建議(二) 周新城:中央黨校教授董德剛,不懂馬列卻狠批馬列!
周新城:中央黨校教授董德剛,不懂馬列卻狠批馬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