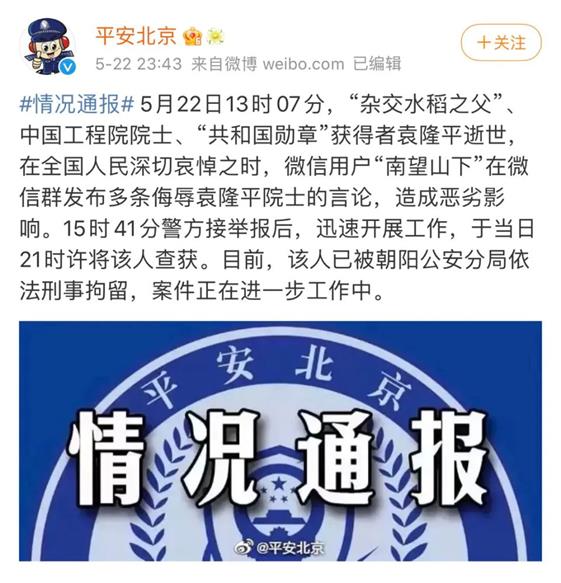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于受到國民黨的嚴密包圍和封鎖,加上國民黨宣傳工具的誹謗、丑化,無論是國統區百姓還是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人的認識都被嚴重歪曲。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著作《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中國》)第一次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向國統區和國際社會如實地報道了那些被嚴重污名化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

【1936年7月的這天,斯諾(右)把自己的新軍帽給毛澤東戴上,拍下了這張照片(左)。圖源:解放軍報】
中共領導人到底是些什么樣的人?經過實地采訪后,斯諾通過《西行漫記》,首次向世人披露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的真實生平經歷,并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當時國際上對紅區和中共領導人的偏見。
【2020年12月26日,天津博物館,1937年、1944年版《紅星照耀中國》(又稱《西行漫記》)書籍展出】
“軍心士氣和政治意志的堅強顯然一如往昔”。國民黨長期宣傳共產黨為“非法”組織。對外實行嚴密的新聞封鎖,對內進行種種污名化報道。尤其是長征時期,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隊伍往往被他們描述為“散兵游勇”。然而,斯諾發現“紅軍的西北長征,無疑是一場戰略撤退,但不能說是潰退,因為紅軍終于到達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無損,其軍心士氣和政治意志的堅強顯然一如往昔”。紅軍“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紅軍軍心士氣和政治意志的堅強”來自他們對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這種信念在《西行漫記》里,既有彭德懷、徐海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直接表達,也有作者的真實體會。
【中央紅軍長征戰斗勝利一覽表(資料照片)。新華社發(埃德加·斯諾攝)】
就像斯諾在《西行漫記》序言中說的那樣:“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西行漫記》中彭德懷率直地告訴斯諾:“以前我只是對社會不滿,看不到有什么進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讀了《共產黨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觀,開始懷著社會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通過和周恩來、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的接觸,斯諾切實體會到了他們及他們帶領的隊伍的那種堅定信念。見到周恩來前,斯諾曾經暗自想他一定是個狂熱分子,后來“卻沒有發覺出來”。年方二十八歲的周恩來奉命去上海準備起義,協助國民軍攻占上海。“他到上海的時候唯一的武裝是他的革命決心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在南方,周恩來“為了要保住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它沒有海港,甚至沒有鹽吃,不得不用鐵的意志來代替”。斯諾得出結論:“無可比擬的吃苦耐勞的能力;無私地忠于一種思想和從不承認失敗的不屈不撓精神——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這個紅軍的故事和參加創建紅軍的一個人的故事中。”
【紅軍的騎兵(資料照片)。新華社發(埃德加·斯諾攝)】
中國共產黨人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堅定信念和不畏艱難困苦的樂觀主義精神,以常人不可想象的勇氣和毅力,征服了種種困難。《西行漫記》對共產黨人的信念作了非常生活化的描述:“他們的堅韌不拔精神令人欽佩;你從來沒有聽到有人訴過苦,盡管他們大多數人都有某種疾病,很多人患胃潰瘍和其他腸胃病,這是多年吃了亂七八糟的東西所造成的。”經過與自己曾經的一次次“暗想”比對,斯諾表示:“對于這些男女戰士,我愿意和他們握手道賀。”通過斯諾本人對中國共產黨人態度的轉變,《西行漫記》把一群心懷紅星一如往昔堅強的中共領導人群體第一次展示給了世人。
“從最高級指揮員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樣”。延安時期,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樸實得和普通的老百姓并無兩樣。《西行漫記》描述了斯諾初到周恩來、毛澤東、彭德懷工作、生活場所的感受。在周恩來的司令部,“看到里面很干凈,陳設非常簡單。土炕上掛的一頂蚊帳,是惟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毛澤東夫婦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頂蚊帳”。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么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制服。”
【1936年,斯諾(右一)在陜北革命根據地(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指揮三萬多軍隊的彭德懷司令部,“不過是一間簡單的屋子,內設一張桌子和一條板凳,兩只鐵制的文件箱,紅軍自繪的地圖,一臺野戰電話,一條毛巾,一只臉盆,和鋪了他的毯子的炕。”斯諾同彭德懷一起吃過好幾頓飯,《西行漫記》記載彭德懷“吃的很少很簡單,伙食同部下一樣,一般是白菜、面條、豆、羊肉,有時有饅頭”。斯諾見到林祖涵時,曾驚嘆“這就是財政人民委員!”因為這位紅色理財家“身上穿著一套褪色的制服,紅星帽的帽檐軟垂,慈藹的眼睛上戴著一副眼鏡,一只腿架已經斷了,是用一根繩子系在耳朵上的”。《西行漫記》細致地描述了中共領導人融入普通百姓、士兵生活的現場,“曾幾次同毛澤東一起去參加過村民和紅軍學員的群眾大會,去過紅色劇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觀眾的中間,玩得很高興。”斯諾第二次見到他時,“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在做著手勢。”斯諾有點驚訝地發現,“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簡樸并真正融入百姓、士兵,和群眾打成一片的中共領導人贏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
《西行漫記》正是以歷史親身見證者的視角、態度和語言,通過一個個鮮活的畫面、人物、細節,斯諾向外界“綜合表達”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真實形象。“他們對于革命依然是高高興興的樂觀主義者!”在中國革命過程中,遇到了無數難以想象的困難和險阻,在這些困難險阻面前,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充滿著無懼無畏的樂觀主義精神。斯諾筆下的中共領導人幾乎毫無例外地具有樂觀的“孩子氣”。初次見面周恩來給斯諾留下的印象是:“他個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結實,盡管胡子又長又黑,外表上仍不脫孩子氣,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熱情。”
【1938年夏,周恩來和鄧穎超在武漢會見埃德加·斯諾】
毛澤東則“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復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通過面對面接觸,斯諾發現彭德懷“是個愉快愛笑的人,身體極為健康”“他有一件個人衣服,孩子氣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長征途上擊下敵機后用繳獲的降落傘做的背心”。斯諾還常常見到彭德懷身后“有一群孩子跟著”。樂觀的中共領導人帶出了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的隊伍。斯諾常常看到:“二十剛出頭的青年就丟了一只胳臂或一條腿,或者是手指被打掉了,或者是頭上或身上留有難看的傷痕——但是他們對于革命依然是高高興興的樂觀主義者!”有了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這種樂觀沒有因為遭遇艱苦磨難而改變。
【1937年,毛澤東(右三)與斯諾夫人海倫·斯諾(左一)等外國友人在延安合影】
“我的生平不過是紅軍歷史的一部分了”。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不斷融入大我,逐漸達到了無私無我的境界。他們心中只有人民、紅軍和組織。斯諾在對毛澤東的采訪中發現“毛澤東的敘述,已經開始脫離‘個人歷史’的范疇,有點不著痕跡地升華為一個偉大運動的事業了,雖然他在這個運動中處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為個人的存在。所敘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了;不再是毛澤東,而是紅軍了;不再是個人經歷的主觀印象,而是一個關心人類集體命運的盛衰的旁觀者的客觀史料記載了”。斯諾發現毛澤東“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個人在談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類似毛澤東只談紅軍不談自己的事同樣發生在韋爾斯女士對朱德的采訪中。斯諾引用了朱德對韋爾斯女士說的話:“毛澤東和我率部到了江西南部、福建、廣東、湖南去進行建立蘇維埃的長期斗爭。從此以后,我的生平不過是紅軍歷史的一部分了。”這種小我和大我在生活中融為一體時往往就是那么的自然。斯諾發現看演出時,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財政人民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以及其他干部和他們的妻子都分散在觀眾中間,像旁人一樣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演出一開始就再也沒有人去怎么注意他們了。
【1937年在陜北根據地,紅軍和農民在一起(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斯諾對于這種現象做了個小結:“共產黨人是能夠說出青少年時代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參加紅軍以后,他就把自己給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問他,就不會聽到更多關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聽到的只是關于紅軍、蘇維埃或黨的故事——這些名詞的第一個字母都是大寫的。”4個月的考察和旅行不僅顛覆了斯諾本人腦袋里在國統區裝下的對中國共產黨人及紅軍的印象,而且從思想感情上徹底改變了他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態度。以至于他離開“保安”時,“覺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離家。”“離家”后的斯諾通過《西行漫記》,把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的信念堅定、艱苦樸素、樂觀向上、無我境界的形象,真實、細致、充分地展示給世人。(作者:張豐清;來源:昆侖策網,原文載于《學習時報》2021年6月2日,原標題“共產黨人是一群忘記‘我’的人——讀〔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