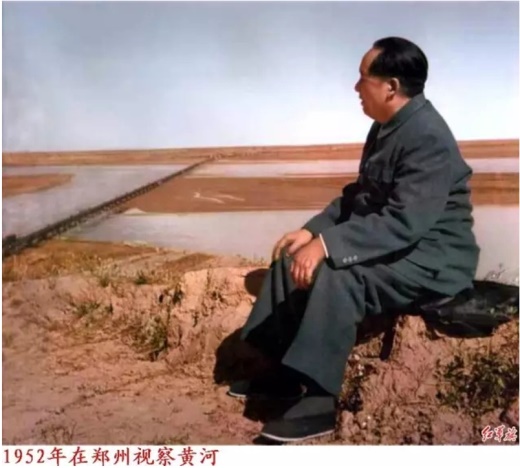圖片來自《左翼之聲》
“阿拉伯之春”得名于新聞界,并被大多數分析人士所接受。他們迅速而有效地將其與現代歷史上最著名的革命進程進行了類比:1848年的人民之春(即歐洲1848年革命)。它當年在巴黎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遍法國和歐洲的主要城市,如柏林、維也納、布達佩斯,甚至到波蘭的外圍地區、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島。
驅動力
阿拉伯之春并不是晴空霹靂。美國新保守派智庫的“新美國世紀計劃”將中東居民描述為“野蠻人”,無法憑一己之力實現“自由”。這證明有必要將西方政治制度“輸出”到那里,并“教育”社會尊重這些價值觀。9月11日雙子塔遭到的襲擊,是小布什在中東(再次)展開地面行動來輸出“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完美借口。通過“持久自由行動”,他入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目的是促進該地區的“民主”和打擊“恐怖主義”。這些戰爭的失敗打亂了這些國家的原本的社會結構,改變了內部政治和地緣政治平衡。一方面,它鼓勵伊朗和土耳其等區域大國,或俄羅斯等鄰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主導作用。另一方面,他們喚醒了古老的種族宗教爭端,由于種族分化和貧窮,這些爭端為席卷整個中東的空前的社會爆炸創造了條件。
2003年,伊拉克和該地區其他國家爆發了反對美國入侵的示威游行。結果,埃及政權承受著壓力,被迫做出極大政治讓步,以壓制不滿情緒。新自由主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不滿情緒。選舉改革的本意是轉移民眾因伊拉克戰爭而對政府產生的憤怒,結果給反對政府的政黨(例如“穆斯林兄弟會”)帶來了巨大的好處。這些出乎意料的選舉結果導致了針對媒體和示威者的政治鎮壓。
2005年,黎巴嫩總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q al-Hariri)被暗殺后,發生了所謂的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該革命驅逐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占領該國的敘利亞軍隊。然后,在2006年,黎巴嫩人民擊退了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的入侵,那里的真主黨變得越來越強大。
2010年底的動員颶風(hurricane of mobilizations)遠遠超過了這些進程,在地緣政治秩序中產生了更深的裂痕,并給該地區的大眾注入了新的政治認同和斗爭方法,激勵了全世界的年輕人、婦女和工人。
“面包暴動”的開端
中東地區有著巨大的社會、政治、種族、宗教和經濟異質性,但也有共同的相似之處和恥辱:北非國家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從千年農業文明變成了糧食凈進口國(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麥進口國)。由于氣候突變、過時的生產方法和政府對農業活動的漠視,敘利亞、黎巴嫩和伊拉克的農村也經歷了急劇的衰退。
由于荒漠化和農村地區的廢棄,糧食價格不斷上漲,這一情況在2008年經濟危機后不斷加劇,導致整個地區的水和糧食缺乏的情況非常嚴重。在突尼斯和埃及,所謂的“面包暴動”就是在那個年代誕生的;這些暴動加速了工會組織進程并使其獨立于大型工會(與國家關系密切)之外。這些組織在最重要的工人中心領導了原本由婦女領導的自發罷工,比如在埃及大邁哈萊市(El Mahalla El Kubra)和突尼斯加夫薩(Gafsa)的采礦盆地,那里的基本要求指向低工資和失業。罷工設法將這些要求國有化,并賦予了一種政治色彩,就像埃及的情況一樣,高呼口號的人都指向穆巴拉克。盡管這些運動沒有成功發展,但它們為阿拉伯之春提供了動力,我們將在下面看到。
阿拉伯之春中的革命與反革命
一名擁有大學學位的突尼斯年輕工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行為,為本·阿里獨裁統治的終結定下日期,開啟了21世紀最大規模的階級斗爭進程。在短短幾個月內,從摩洛哥到伊朗,中東和北非的所有政權都見證了史無前例的抗議運動從誕生到動搖了其統治根基的歷史進程。突尼斯、埃及、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威權共和國”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非殖民化進程中誕生;沙特阿拉伯、巴林和約旦的君主政體仍受部落條約和傳統帝國主義關系的統治;而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國家,土耳其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則面臨嚴重的政治動蕩,并試圖采取不同的戰略來鎮壓或轉移動員進程。這導致了革命、反革命和內戰的復雜運動狀態,在這一狀態中,政權垮臺、被改革,或發展出由帝國主義利益集團、地區勢力和地方自治行為者解決的國內沖突。
2011年,在突尼斯和埃及,民眾起義推翻了穆巴拉克和本·阿里終身獨裁統治。這些人是學生、工人階級和城市貧民,他們用在“面包暴動”期間學到的政治口號和方法發動了起義。“過渡”時期開始了,在這一時期中,傳統政治潮流凸顯:突尼斯的復興運動(Ennahda)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這些政黨來自與傳統主義資產階級有聯系的溫和政治伊斯蘭教。他們將伊斯蘭社會組織的原則與資本主義和現代社會的原則相結合,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確立了政權的確立。在獨裁統治下,他們建立了經濟、教育和社會援助網絡,這給了他們威望,使他們成為政治進程的可行方向。
在埃及,由軍隊和帝國主義監督的選舉使穆斯林兄弟會掌權。在執政兩年后,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試圖增加他的權力并使國家伊斯蘭化。人們以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拒絕了他的提議,重新占領了解放廣場,并發動了大罷工。但是,由于沒有一個可以通過打破帝國主義和當地資產階級來滿足工人的需求的替代方案。軍隊在2013年找到了發動政變的機會。獨裁者塞西(Al-Sisi)扼殺了示威者的“民主幻想”,一天屠殺800人,創下21世紀的最高紀錄。他的政權是通過迫害、監禁和折磨反對者、驅逐記者和活動人士、媒體審查和永久緊急狀態實施的社會控制來維持的。
突尼斯召開制憲會議以回應示威活動。復興運動(Ennahda )提議“使國家伊斯蘭化”,同時容納成千上萬沮喪、失業的年輕人。他們與世俗政黨建立了一個“民族團結”政府,直到2014年選舉失敗。但該國的結構性問題,如貧困和失業,已經加深,針對政府及其帝國主義計劃的罷工和示威活動已經周期性地爆發,危機仍然潛伏著。
在敘利亞、利比亞和也門,動員進程因曠日持久的內戰而夭折。帝國主義通過在利比亞組建類武裝組織和甚至與北約有直接聯系的組織進行干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區大國——它們剛剛用鮮血淹沒了巴林的起義——利用霸權計劃的權力真空,通過其領土以外的盟友進行“冷戰”。得益于不斷變化的聯盟體系,前軍隊、部落、伊斯蘭民兵組織、與非法經濟有關的部門以及自治社區的殘余力量成為了當地的行動者,使領土控制成為可能,并使這種控制維持下去。
在也門,長期執政的總統阿里·阿卜杜拉·薩利赫因示威活動下臺,一場內戰開始在副總統哈迪的政府支持者(沙特阿拉伯支持)和胡特叛亂分子(伊朗支持)之間展開,這些叛軍盤繞在首都薩那周圍的山區,該區域現在在他們的控制之下。盡管投入了數百萬美元用于戰爭和對平民的刑事封鎖,但沙特家族并未設法在利雅得實行偽政權,也未能阻止(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支持下)一支自治軍分支在亞丁和也門的出現。
在利比亞,班加西和的黎波里的民眾起義被穆罕默德•卡扎菲(Mahomar Gaddafi)鎮壓,卡扎菲曾在20世紀90年代與西方建立了友誼。這種罪惡的鎮壓迫使成千上萬的人加入了國家過渡委員會(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一個由北約發起的武裝運動——并粉碎了支持該政權的部落協議。卡扎菲的私刑導致了軍隊的崩潰,利比亞分裂成由部落、雇傭軍和圣戰分子控制的地區,他們有自己的國際聯盟。經過十年的沖突,他們得到各方支持的權力,以及與人口販運和武器走私有關的組織自由運作。在的黎波里,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NTC)要求在北約的監護下進行選舉,但未能在首都之外維護其權威。在俄羅斯的支持下,哈夫塔爾將軍占領了東部地區,并對首都進行了數月圍困,但在與土耳其資助的民兵進行了激烈戰斗后,目前的局勢已陷入停滯。
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者,隸屬于阿拉維派(Alawite)少數派。他在被逼到走投無路后,對叛亂分子進行了猛烈的鎮壓。在伊朗和俄羅斯的重要合作下,他發動了一場針對圣戰組織和與西方大國結盟的“叛亂分子”的內戰,從而保住了政權。盡管有數以十萬計的人死亡,有數以百萬計的難民以及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等反動勢力的出現,經濟危機還是在大馬士革掀起了新一輪的動員高潮,讓阿薩德家族政權再次進退兩難。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2011年的動員行動要么被粉碎,要么被各種策略轉移。“民主”改革剝奪了示威者的話語權,并沒有解決這場運動的結構原因,而是允許地方權力部門進行重組,并與帝國主義建立新的聯系。內戰開啟了更為復雜的局面,圣戰民兵的出現——與權力結構和地區利益的崩潰有關——給了獨裁政權合法性,使其能夠打著“反恐戰爭”的幌子,以一種反動的方式回應民眾的要求。
群眾沒有能力來構建自己的一個組織,獨立于當地資產階級領導人——它永遠不會與帝國主義正面對抗——是一個弱點,這使得統治階級能夠以高昂的代價重建他們的權威,即使是在2011年的颶風過后,他們在中東的霸權地位已經衰弱的情況下。然而,阿拉伯之春開創了潛伏的斗爭的象征和傳統,在這場世界危機中,他們正竭盡全力推動一場新的爆發。
北非戰火再現
在阿爾及利亞和蘇丹,動員行動從2019年初就開始了。這些國家都是一黨制政府,由封閉的權力圈(軍方、家庭和朋友組成)所支持,并控制著經濟戰略部門。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這兩個國家都經歷了漫長的內戰,并在2011年的浪潮中保持了相對穩定。
石油工業的危機促使阿爾及利亞總統阿卜杜勒阿齊茲•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大幅削減了工資和補貼的稅收,從而為起義創造了條件。這位無能為力的“紙總統”計劃在2019年的選舉中謀求第五次連任——在執政20年后——這一計劃點燃了燎原之火,引發了數百萬人的示威游行。在這些示威活動中,青年、工人、專業人士和婦女組織聚集在Hirak(阿拉伯語“運動”的意思)周圍,在該運動中成立了大量婦女參與的學生委員會。
自3月以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索納特拉赫(Sonatrach)石油公司的工人們開始了一系列的絕食和區域性罷工。他們支持迫使布特弗利卡辭職的運動,不顧雇主禁止罷工的威脅,也不顧與民族解放陣線(FLN)有聯系的阿爾及利亞工人總工會(UGTA)的官僚機構的威脅。4月2日,軍方開始了為期數月的旨在削弱希拉克(Hirak)的談判,以爭取權力,直到在其庇護下舉行選舉為止。盡管試圖抵制示威者,但其候選人阿卜杜拉德吉德•特博恩(Abdelmadjid Tebboune)贏得了選舉。盡管缺乏具體的計劃和明確的政治方向,希拉克仍然在衛生危機實施隔離下站穩腳跟,設法留在街頭示威,表明沖突仍在繼續。
在蘇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劃迫使奧馬爾·巴希爾準將削減面粉補貼。民眾的反應是進一步的“面包暴動”。2019年4月11日,當抗議者占領喀土穆中心廣場要求政權倒臺時,軍隊迫使執政30年的巴希爾下臺。自獨立以來,蘇丹一直在內戰,爭奪對自然資源的控制權,主要是位于南部的石油。南蘇丹于2011年獨立,長期存在的宗教、種族和部落緊張局勢正在顯現。自從占領喀土穆廣場以來,一個組織出現,并把包括共產黨在內的進步的自由黨派團結在一起。這個過程的新奇之處在于,它明顯克服了種族、宗教和性別差異。由于在這場斗爭中出現的政治組織和工會中,婦女發揮了核心作用——有阿拉·薩拉赫等國際知名人物——宗教集會也加入了示威活動,但沒有引發宗派暴力。
沙特阿拉伯等區域大國進行了干預,通過提供軍事貸款和軍事建議進行干預,支持軍隊,其目的是遏制示威進程,但未能阻止示威活動在全國蔓延。自由和變革聯盟參與的過渡委員會的組成與動員進程有關,其目的是同意在兩年內舉行選舉,從而為該運動提供一個體制渠道。它是否能控制疫情期間提出的社會需求仍有待觀察。
伊拉克和黎巴嫩
這兩個國家有不同的種族、民族和宗教派別,社會被分割成代理人網絡,而且與經濟和領土相關的地方和國際利益聯系在一起。他們的政治體系是根據宗教標準建立起來的。黎巴嫩的政治體系是在內戰結束時(1975-1991年)《塔伊夫協定》簽訂后建立起來的。而伊拉克的政治體系是2005年建立的,在美國入侵伊拉克期間,在庫爾德和什葉派領導人的配合下,引起與被排除在政治制度之外的部門的嚴重沖突。這兩個國家的人口大多是年輕人,受失業、文化世俗的影響,對保守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精英非常不滿。
伊拉克連續不斷的國際戰爭和內戰,包括目前仍在活躍的伊斯蘭國的興起,已經把數百萬人拖到了邊緣。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40%的年輕人失業,不穩定的就業機會比比皆是。2019年10月,在巴格達抗議驅逐一名反對伊斯蘭國斗爭的知名指揮官后,政府使用準國家民兵和軍隊進行鎮壓。抗議者被驅趕到家中并被殺害;最后,婦女和兒童被殺害。從那時起,無論政府和反動勢力做什么努力,都不足以讓憤怒的年輕人離開街頭。
數百名“無領導者的青年”在街頭喪生,他們與整個政權及其被稱為穆哈薩薩(Muhasasa)的種族-宗派政府體系進行斗爭,但未放棄結構上的要求:工作和獲得基本服務的權利。在他們的組織中心,比如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阿拉伯語為“獨立”),他們搭建帳篷休息,做飯。幾個教師工會在那里舉行公開課,醫生和護士幫助受傷的抗議者,婦女團體發揮了關鍵作用。殼牌公司和道達爾公司的工人(在巴斯拉的油井)進行了罷工,杜克(Tuk Tuk)的工人因在游行中救治受傷者而被視為英雄。
抗議者發自內心的需求是將伊朗軍隊趕出去,并譴責在抗議活動中充當軍隊力量的什葉派組織。針對外交總部和美國軍隊的行動是存在的,但被什葉派政黨和民兵所支配,他們靠近德黑蘭,對動員行動持敵對態度。帝國主義控制著經濟和金融的重要領域,反帝國主義主張的弱點可以被視為一項進程的主要限制,該進程并沒有隨著阿迪勒·阿卜杜勒-馬赫迪總理的辭職和健康危機而停止。
黎巴嫩的情況與此類似。示威活動的爆發源于對聊天軟件WhatsApp和網絡電話軟件Skype荒唐的稅收。他們聚集在貝魯特的烈士廣場,高呼“人民希望政權倒臺”和“他們都是故意的”。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將提到了黎巴嫩教派主義的特殊性,指向所有政治和宗教部門的領導人,在1990年內戰結束時,他們接管并分配了黎巴嫩經濟的杠桿,并在整個新自由主義期間與銀行系統進行了數百萬美元的交易。
最初的示威活動集中在控制經濟的大亨們的腐敗問題上,他們的財富大多分布在國外。人們認為他們應對高達國內生產總值150%的債務、調整計劃和貨幣貶值負有責任。作為這一寄生種姓的忠實代表,總理哈里里的辭職是這一進程的第一項重大成就。伊朗的盟友真主黨(Hezbollah)試圖利用這場運動,擴大其對政府的影響力。但示威活動仍在繼續,卻對真主黨領袖哈桑·納斯魯拉構成挑戰。作為回應,像在伊拉克一樣,什葉派試圖用武力阻止動員,這增加了對該國傳統政治家和波斯勢力的仇恨。
黎巴嫩的運動成規模并有世俗性,因此具有歷史意義。在橫向上,它關注所有民族和宗教社區的人口的共同要求,而政府沒有喚醒宗派仇恨來分裂它。難民問題是黎巴嫩進程中最具潛在爆炸性的因素,在這個問題中,約有600萬人口中的將近200萬是上一次沖突以來的敘利亞人和數十年來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這部分人口所忍受的貧困和歧視程度,但是直到現在,他們的要求在示威者的要求中起了次要作用。
結 論
2018年發起的民眾動員和反抗活動表明,由于新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數十年的剝奪,數百萬生活在邊緣的人已經厭倦了。無論是在2011年還是現在,與其他全球抗議運動類似的部門都參與其中:全球化的“相對輸家”,即沒有機會的受過教育的年輕人、被毀的中產階級和低工資的專業人士;以及“絕對輸家”,包括赤貧和邊緣化的人口,這些人在沖突之后出現了大量糧食不安全(也門霍亂和饑餓導致的死亡),以及世界上數量最多的難民和流離失所者。
需求的深度、邊緣青年的好斗性以及他們的自發性,這些元素都符合2019年整個世界出現的大規模反抗的特征。它們在一段時間內的可持續性是一個重要因素,表明對各國政府來說,這將是未來時期的中心問題。工人階級參加了大量的政治罷工,阿爾及利亞的國家石油公司和國家煤氣電力公司,或者伊拉克的巴士拉礦產(Bassora wells),或者蘇丹的工會。但是,作為示威活動的“參與者”之一,以“公民”身份而不試圖承擔領導權,它未能對自己的戰略地位產生影響。沒有任何一方提出與帝國主義決裂。伊斯蘭或進步黨派提議改變收入分配或者政治體制的改革。如果這些改革不改變這些國家作為西方大國的次要伙伴或像俄羅斯和伊朗這樣的國家的附庸角色(就敘利亞而言),那就是烏托邦式的改革。
在突尼斯經歷了多年的“民主”經驗之后,維持本·阿里獨裁統治的經濟結構和鎮壓機制仍然存在。如今,孱弱的共和國面臨著民眾的策略,政權的政黨正在失去合法性,而“街頭政治”正在地區舞臺上重獲威望。但缺乏反資本主義的領導和目標仍然是這場運動的特點。敘利亞的西庫德斯坦(Rojava)和艾因阿拉伯(Kobane)的經驗是,由于與美國軍隊的戰術聯盟,庫爾德民兵在過去幾年里實際上實現了自決。這是整個中東最民主和最激進的經歷之一,它因為世俗性質和婦女在軍事組織中的作用成為伊斯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敵人。在爭取民族自決的歷史斗爭中,這一步在2019年被土耳其軍隊對敘利亞北部的犯罪干預所粉碎。這次襲擊在“人民保衛軍”(YPG)的盟友唐納德·特朗普的監視下,造成了數千名村民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特朗普通過電話進行了談判,并將庫爾德人“一拼盤”交給了土耳其總統雷杰普·埃爾多安(Recep Erdogan)。
“人民之春”之后,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提出,如果勞動人民不參加獨立于資產階級之外的政治組織,就會增加被剝削者的痛苦,從而繼續奠定資本主義的根本基礎。阿拉伯之春彌合了歷史的鴻溝,展示了帝國主義和地方資產階級將如何通過將勝利擺在他們面前而以民主的面孔提出解決方案。因此,面對2019年爆發的起義,革命戰略必須從這些勞動人民獨立的結論出發,以打破壓迫他們的枷鎖。
(編譯:閆莉萍,華中師范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政黨研究中心;來源:“WorldCommunistParties”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網】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現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絡時代發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