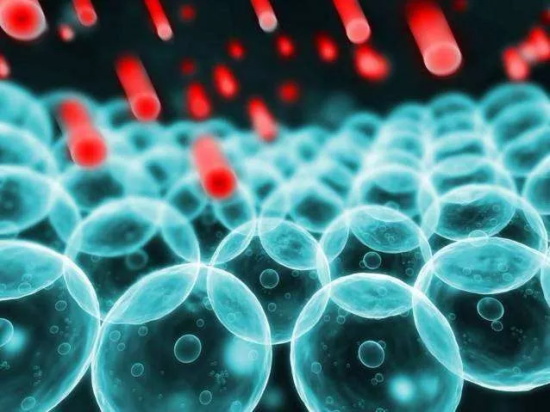工業(yè)機器人的亮相。圖自新華網。
在“卡脖子”成為熱詞的當下,工業(yè)軟件近年來持續(xù)引起我國產學研政界廣泛的關注。
作為工業(yè)領域里進行研發(fā)設計、業(yè)務管理、產品制造、生產調度和過程控制的相關軟件與系統(tǒng),工業(yè)軟件已經被公認為“工業(yè)制造的大腦和神經”,是工業(yè)領域的“皇冠”。
但在過去一段時間里,“國產工業(yè)軟件落后世界最高水平至少30年”“我國工業(yè)軟件市場被歐美軟件巨頭嚴重壟斷”“如果西方國家對我國全面實施工業(yè)軟件禁運,我國工業(yè)研發(fā)和生產將何去何從?”等呼吁和疑問,陸續(xù)登上輿論風口,觸目驚心,令人難以忽視。
為什么我國的工業(yè)軟件做不起來?國產工業(yè)軟件比國外差在哪?怎么才能加速工業(yè)軟件國產替代進程?國產工業(yè)軟件怎樣才能“打個翻身仗”?
帶著這一系列的問題,我們走訪了多家一線企業(yè),得到幾乎一致的回答:中國工業(yè)軟件人有信心絕地反擊,但需要耐心、耐力,“工業(yè)軟件沒有‘彎道超車’一說,沒有捷徑可走,否則一拐彎就是車禍。”
“中國企業(yè)都歧視中國企業(yè)”
十多年前的一個夜晚,北京市朝陽區(qū)惠新西街1號安徽大廈的咖啡廳里,在代理霍尼韋爾、艾默生軟件的李春燕,與國內某知名工業(yè)軟件品牌的一個創(chuàng)始人如約見面。
見面的目的并不復雜——后者想尋求李春燕的幫助,希望借助她積累多年的業(yè)內渠道資源,為自己公司的DCS產品進入石油石化領域推一把力。
交談間,產品價格免不了被提及。李春燕驚訝地發(fā)現(xiàn),該公司的軟件價格僅為國外軟件的十分之一,卻還是很難打開市場。“這點對我觸動太大了!國產工業(yè)軟件找個突破口太不容易了!”
此后十多年間,霍尼韋爾、艾默生、西門子等為了搶占中國市場,將價格降低了一半以上;李春燕創(chuàng)立了自己的工業(yè)軟件品牌“北京智通云聯(lián)科技有限公司”……時光輪轉間,這個行業(yè)里的人來來往往、起起伏伏。
然而很遺憾,十年后的現(xiàn)在,即便在價格上依舊遠低于國外軟件,國產軟件也仍然處在尋找市場突破口的困境中:市場份額在全球市場上僅為6%,在國內市場上不足10%。
為什么?因為縱然業(yè)界輿論大聲疾呼“獨立自主”,企業(yè)們上下求索“國產替代”,但在市場面前,這些熱情依舊免不了被兜頭澆來一盆冷水。
調研中我們發(fā)現(xiàn),部分國產軟件企業(yè)由于品牌、規(guī)模等問題資質受卡,手中的很多項目只能“躲在外企或者互聯(lián)網大公司背后”接下。
一位北京工業(yè)軟件企業(yè)高管透露,其公司產品在東南亞、日本、韓國市場都進展順利,但國內項目中很多只能以丙方的身份承接,“事情是我們干,功勞和名頭是別人的。”
某上海工廠IT采購人士也告訴記者,傳統(tǒng)生產制造領域的采購態(tài)度向來偏保守,一來大型企業(yè)的采購“不缺錢,要買就買最好的”,二來中小型企業(yè)“一分錢恨不得掰成八瓣花,畢竟試錯成本除了少則幾十萬元的金錢,還有寶貴的時間,根本耽擱不起。”
“中國的企業(yè)都歧視中國的企業(yè),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李春燕說。其他多家受訪的工業(yè)軟件企業(yè)高管也表達了類似的心聲。還有相當一部分高管擔憂,長此以往,如果不能在覆蓋研發(fā)成本的基礎上擴大利潤空間,企業(yè)很難實現(xiàn)健康、持續(xù)發(fā)展。
某加工廠正在生產乳制品。圖自新華社。
尷尬境地的由來
為什么國產工業(yè)軟件在國內市場上這么不吃香?
結合多方觀點,我們發(fā)現(xiàn),國產工業(yè)軟件之所以陷入這樣的尷尬境地,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國產工業(yè)軟件短期內的確難以超越國外同類產品,是許多制造業(yè)企業(yè)選擇后者的根本原因。
賽意信息副總裁、工業(yè)互聯(lián)網子公司總經理蔡勝龍表示,“國內工業(yè)軟件的標準其實不明確,一些系統(tǒng)的架構也比較落后,對外提供標準的集成能力也不是很強。在實施過程中,其實會影響到我們的一些信息系統(tǒng)和業(yè)務系統(tǒng),包括這種自動化系統(tǒng)的融合等。”
另一方面,即便國產軟件在某一領域技術水平不弱,且能夠保障可靠的售后服務,也鮮有采購方愿意“第一個吃螃蟹”。
安世亞太高級副總裁田鋒曾這樣分析制造業(yè)企業(yè)的采購心理:即使軟件功能和性能接近國外軟件,國內客戶為什么要拿你的軟件替換當前已經在用的國外軟件?價格可能是個變量,但低價甚至免費就能獲得客戶么?客戶反倒會懷疑這個商業(yè)模式的可持續(xù)性。
除此之外,更深刻的原因還在于,工業(yè)軟件研發(fā)周期比較長,技術壁壘比較高,回報比較慢,而工業(yè)軟件企業(yè)多是輕資產運營,加之許多企業(yè)自身無法提前鎖定軟件的長期服務價值,不僅難以得到資本市場的青睞,也無力改變國內由來已久的“看衰”心理。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互聯(lián)網初創(chuàng)公司動輒數(shù)千萬、上億融資的時代背景下,成立了22年的國內領先的工業(yè)軟件龍頭廠商——廣州中望龍騰軟件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底完成第一輪融資8000萬元,2019年10月完成第二輪融資1.4億元,這兩輪融資竟然均為國內研發(fā)設計類工業(yè)軟件領域彼時規(guī)模最大、估值最高的融資案例。
“很多企業(yè)在遭遇經濟下行壓力時,往往首先砍的預算就是信息化投入,他們寧愿買自動化設備,也不愿構建自己的‘心臟’和‘大腦’。”在某工業(yè)軟件國產化高層論壇上,一位行業(yè)人士的發(fā)言,引起在場多數(shù)人的共鳴。
多位工業(yè)軟件企業(yè)高管還談及,在BAT等互聯(lián)網巨頭進軍工業(yè)互聯(lián)網后,不僅工業(yè)軟件企業(yè)自身的人才發(fā)展遭遇沖擊,整個行業(yè)的泡沫也增加了不少。
一位高管舉例稱,剛畢業(yè)的碩士研究生在其單位的年薪在12萬到15萬元之間,工作七八年后的開發(fā)人員年收入也僅能達到20萬元,可一些互聯(lián)網、游戲公司輕易就能用數(shù)倍年薪挖人,有經驗的開發(fā)人員流失嚴重。
“更可惜的是,許多互聯(lián)網公司需要一支技術牛的團隊,是好去講故事、籌資源、撬資本。但有經驗的人才被挖過去之后才發(fā)現(xiàn),他們就像被養(yǎng)起來的‘吉祥物’,根本沒有切實的項目供他們發(fā)揮才干”,另一位被某互聯(lián)網巨頭挖走過重要開發(fā)人員的工業(yè)軟件企業(yè)負責人說,“可接受了高薪后,他們也不愿意再回到原來的圈子,最終因為無用武之地而抑郁,好好的人才就這樣被白白浪費了。”
走向智能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趙敏認為:“中國工業(yè)軟件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較差,不僅開發(fā)者、決策者、用戶之間存在較大認知差異,甚至在財務依據(jù)、稅收、資產評估、人才培養(yǎng)、投/融資、知識產權、同業(yè)競爭等方面,都有較多問題。”
可以說,相比國外,中國自主工業(yè)軟件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還任重道遠。
廣東提倡深化工業(yè)互聯(lián)網發(fā)展應用,扶持企業(yè)轉型。圖為工人在內地一家照明企業(yè)生產車間工作。圖自新華社。
未來已來,過去未去
當然,也并不是沒有國產工業(yè)軟件成功牽手國內客戶。只是,要想把產品落地到客戶的生產線上,遠比想象中要麻煩。
“一進入工廠車間,我們就發(fā)現(xiàn),未來已來,但過去未去——我們面對的,是許多工廠還處在傳統(tǒng)生產模式的狀況。”李春燕說。
北京亞控科技發(fā)展有限公司總經理鄭炳權提醒說,“工業(yè)互聯(lián)網不是“工業(yè)”和“互聯(lián)網”簡單地相加,兩者必須用一個符合工業(yè)生產的邏輯串聯(lián)起來,才能真正發(fā)揮工業(yè)軟件的應用價值。”
他表示,當前大量的工業(yè)互聯(lián)網企業(yè)僅停留在產業(yè)鏈協(xié)同層面,聚焦制造企業(yè)生產線各環(huán)節(jié)仍是少數(shù)。而且,企業(yè)制造中每個工廠都不一樣,要讓制造企業(yè)看到國產軟件在管控生產進度、成本管控等方面的價值問題,需要一個過程。
數(shù)據(jù)采集,是國產工業(yè)軟件要面對的第一道門檻。
眾所周知,設備廠商對自己設備的數(shù)據(jù)是嚴格控制的,工業(yè)軟件采集設備上的數(shù)據(jù)必須獲得設備廠商的授權。然而,我國絕大多數(shù)制造業(yè)廠房生產線上運轉著的機器,來自世界各國。這些“萬國設備”標準與非標混雜,要么不開放通信協(xié)議,要么過了質保期,要么連設備商都找不到,大量的基礎數(shù)據(jù)、應用數(shù)據(jù)禁錮在設備本身,難以被采集出來。
而且,除了設備本身的數(shù)據(jù),工業(yè)軟件供應商們還要采集設備保養(yǎng)、大修、生產關聯(lián)匹配度、關鍵供應參數(shù)等管理層面的數(shù)據(jù),采集難度大。
李春燕告訴記者,一個較大型制造業(yè)工廠的核心設備約有十七八類,設備總量在800~1000臺,數(shù)據(jù)采集點約有5萬到8萬個,“少一家設備廠商的數(shù)據(jù),整個數(shù)據(jù)采集都無法完成,各行各業(yè)都如此。而這恰恰是工業(yè)軟件第一步要解決的問題。”
第二道難題在于產線的智能化改造本身。
作為工業(yè)軟件進步的重要成果,工業(yè)互聯(lián)網的核心是工業(yè)云平臺。工業(yè)云平臺本身并不難搭建,真正難的是與設備本身和生產工藝、產品質檢等具體應用層面的結合。
工業(yè)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一級巡視員劉杰曾指出,工業(yè)互聯(lián)網需要把物理接入、大數(shù)據(jù)分析、知識圖譜管理、運營軟件管理等綜合運用聯(lián)結起來,才會形成真正落地的服務,如果單獨強調某一項就會存在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米打不通的情況,對廣大制造企業(yè)來說還是沒用。
以乳制品產線為例,食品質檢標準要高于國家標準,工廠的牛奶要求復雜,比如每半小時對原奶、半成品、待裝奶、罐裝奶做一次測樣,半成品從生產結束到質檢環(huán)節(jié)再到半成品轉續(xù)不能超過60分鐘,其中質檢時間約為30分鐘,半成品在質檢結果出來前不允許轉續(xù),等等。
如果將各環(huán)節(jié)隔離開來,這些復雜的檢驗及控制在各自的業(yè)務閉環(huán)內都很好實現(xiàn),但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不僅這些環(huán)節(jié)的把控要結合設備進行體現(xiàn),而且整個系統(tǒng)必須保證質檢環(huán)節(jié)、工藝控制、生產環(huán)節(jié)完全同步匹配、共同協(xié)作;任何一個小環(huán)節(jié)掉鏈子,就會給工廠帶來實打實的損失。
有人會說,當前市面上主打工業(yè)互聯(lián)網平臺的國內公司越來越多,還不能順利滿足企業(yè)向智能制造模式轉變嗎?
答案是,這一趨勢固然值得看好,但落地效果更值得長期考量。畢竟,任何工業(yè)互聯(lián)網平臺及運行其上的新型工業(yè)軟件(工業(yè)APP),都是以為工業(yè)提質增效的水平來衡量的,這需要工業(yè)軟件供應商對其服務的行業(yè)和具體業(yè)務場景有著非常深入的了解,相當于要成為半個“業(yè)內人”,才能開發(fā)出適用、好用的工業(yè)軟件,而這,至少要花上5~10年的時間,甚至更長。目前工業(yè)互聯(lián)網市場上,能用“一個符合工業(yè)生產的邏輯”把信息/網絡技術(ICT)與工業(yè)場景緊密串接起來、融為一體的工業(yè)互聯(lián)網平臺,數(shù)量較少,有價值的工業(yè)APP總計不多——到去年底預計實現(xiàn)“百萬工業(yè)APP”的目標只完成了30%。
前述北京工業(yè)軟件企業(yè)高管認為,IT互聯(lián)網企業(yè)暫時還難當IT和OT融合大任,“工業(yè)知識掌握在工業(yè)人的手中,工業(yè)軟件要服務好工業(yè)制造,一定由工業(yè)人去主導才能完成,因為只有工業(yè)人才會不計成本、孜孜不倦為工業(yè)制造賦能。”
搶救工業(yè)知識數(shù)據(jù)庫!
為什么要想實現(xiàn)工業(yè)軟件國產替代這么難呢?
在諸多相關描述中,工業(yè)軟件已經被公認為“雖然只占軟件很小的比例,卻是工業(yè)制造的大腦和神經”。但容易被人們忽略的一個“冷知識”是,沒有深厚的工業(yè)知識數(shù)據(jù)做支撐,工業(yè)軟件根本難以支撐工業(yè)制造的脫胎換骨。
工業(yè)軟件是工業(yè)和信息產業(yè)的結合體,做工業(yè)軟件,既要懂信息軟件開發(fā),又要對工業(yè)體系有系統(tǒng)性、深入性的了解,其中最大的難點不在于軟件開發(fā)技術本身,而是IT人員對工業(yè)知識數(shù)據(jù)的掌握和調用。
趙敏也曾說過:“沒有工業(yè)知識,沒有制造業(yè)經驗,只學過計算機軟件的工程師,是設計不出先進的工業(yè)軟件的。”
實際上,國外工業(yè)軟件巨頭之所以能夠持續(xù)發(fā)展強大,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積累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業(yè)生產的關鍵技術、流程、知識、工藝和數(shù)據(jù),形成了扎實的工業(yè)數(shù)據(jù)知識庫,具備了最重要、最核心、最底層的支撐。軟件開發(fā)時,一手是市場需求,一手是隨取隨用的知識數(shù)據(jù)庫,兩手交匯貫通間,軟件的優(yōu)化升級順利實現(xiàn)。
國產工業(yè)軟件缺乏的,正是這樣一個源頭支撐。
自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工業(yè)制造過程中的海量關鍵工藝流程、工業(yè)技術經驗及研發(fā)數(shù)據(jù),大都只鎖閉在技術人員頭腦中和企業(yè)的資料室里,隨著企業(yè)的變遷、人員的流動甚至消失,不斷耗散。
這就導致兩個結果,一來,制造企業(yè)自身的知識經驗及數(shù)據(jù)白白流失;二則,工業(yè)軟件企業(yè)進入制造企業(yè)所處領域時,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學習、消化基礎知識及參數(shù),弄懂“一個符合工業(yè)生產的邏輯”之后才能進入軟件開發(fā)階段。
以石油勘探開采技術為例,我國在這一領域的成就早已獲得世界認可。所謂“上天容易下地難”,人類對地下世界的持續(xù)探索離不開對過往經驗的參照。但由于老專家、熟練技工的退休、離世或離職,大量寶貴的經驗教訓沒有得到有效保存。
如果能利用工業(yè)軟件技術,將這些經驗教訓以數(shù)字化、知識化形式進行保存、調用,不僅年輕一代的技術人員可以盡量減少重復錯誤、無效做工等問題,工業(yè)軟件企業(yè)也可以根據(jù)勘探人員實時反饋的數(shù)據(jù)信息,對軟件進行更貼合實際應用需求的優(yōu)化升級。
“我國有大量的工業(yè)知識和數(shù)據(jù)亟須搶救,哪怕失敗的教訓也要留下來”,李春燕認為,“只有隱性知識顯性化,顯性知識組織化,殘缺知識完整化,人走知識留,使數(shù)據(jù)和知識成為單位集體財富,才能更便于后來者高效地學習、對照。”
多位業(yè)內人士也指出,國產工業(yè)軟件當前首要任務,是加快建立工業(yè)知識數(shù)據(jù)庫,讓大量的專家經驗、工藝流程、核心參數(shù)等保留下來,企業(yè)知識財富成為行業(yè)集體的寶貴財富,從源頭上為國產工業(yè)軟件的發(fā)展積蓄動能。
一步一個腳印
在此次調研中,記者不止一次拋出“彎道超車”一詞,但驚訝的是,大多數(shù)受訪的從業(yè)者都覺得,這個詞用在工業(yè)軟件上“略顯浮躁”。
李春燕更是直言:“國產工業(yè)軟件沒有‘彎道超車’一說,沒有捷徑可走,否則一拐彎就是車禍,只能一步一個腳印。”
鄭炳權也表示,工業(yè)軟件企業(yè)要有“老黃牛”精神,凝聚干實事、干大事的的正能量,不要只想從工業(yè)掙錢,要想怎么做能讓工業(yè)企業(yè)掙錢。
從長遠上看,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fā)展階段,尤其是外部勢力持續(xù)加大倒逼力量,中國制造由量向質的躍遷,各有關行政部門都陸續(xù)給出利好政策,這些形成的合力,必然會開創(chuàng)出國產工業(yè)軟件研發(fā)的春天。
但立足當下,考慮到國家近年來出臺的優(yōu)惠支持政策和國產工業(yè)軟件發(fā)展情況,下一步想要切實加快工業(yè)軟件國產替代進程,走到更廣闊的國際舞臺上,至少需要注意“兩手抓”:
一是政策監(jiān)督層面加強考察力度,對扶持企業(yè)設立考核指標,最好能跟蹤到產品投入、應用效果,保證優(yōu)惠與支持給到真正做技術研究的企業(yè),避免濫竽充數(shù);同時,堅持長期主義思想,鼓勵國企特別是央企帶頭使用自主工業(yè)軟件,鼓勵軟件企業(yè)進行探索性創(chuàng)新,對創(chuàng)新技術及人才進行定向獎勵支持。
二是工業(yè)軟件產業(yè)加強行業(yè)自律,自覺提高產品要求,形成自身驗證、客戶驗證、產品驗證、跨界驗證、同行驗證等層層錘煉的發(fā)展意識,全面提高產品及服務的市場競爭力。
山間有竹,前四載深埋地下,后破土而出,日漸瘋長,終成竹海。工業(yè)軟件國產替代也注定是這樣一場漫長的追光過程。
慶幸的是,許多從業(yè)者清醒地知道,“在中國搞工業(yè)軟件,必須要有信仰般堅定的意志。”
來源:《財經國家周刊》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lián)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guī),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qū)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美國農民:奇怪的中國大豆訂單
美國農民:奇怪的中國大豆訂單
? 社會調查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