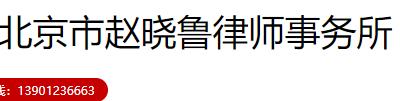一、張文宏醫(yī)生的言論及對(duì)群眾對(duì)防疫措施的疲憊
最近,張文宏醫(yī)生的言論引起了一些爭(zhēng)論,成了一個(gè)輿論焦點(diǎn)。對(duì)這個(gè)事情眾說(shuō)紛紜,我也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理解。
疫情已經(jīng)一年半了,再幾個(gè)月就快兩年了,很多人對(duì)于疫情管控政策覺(jué)得疲憊了、厭倦了,不知何時(shí)是頭。這次Delta疫情爆發(fā),來(lái)勢(shì)兇猛,各地的防疫工作又有所加碼,譬如作者前段去了一次上海,回北京后馬上被街道通過(guò)大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我是“到訪(fǎng)過(guò)中高風(fēng)險(xiǎn)地區(qū)所在市”,被街道拉去檢測(cè)核酸(要求回來(lái)一次,第7天時(shí)一次),還要求天天報(bào)體溫。社區(qū)工作者都非常不容易。
這個(gè)措施,比之前的政策是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的。它確實(shí)對(duì)群眾的工作和生活有些影響,也會(huì)影響到經(jīng)濟(jì)運(yùn)行。其實(shí)我們和朋友在一起聚會(huì)也經(jīng)常會(huì)議論:“哎呀這疫情何時(shí)到頭啊。”“這么搞長(zhǎng)期也不是辦法啊”;“國(guó)外一早躺平了,現(xiàn)在好,群體免疫了,人家不管不顧最后倒沒(méi)事了”;“咱們也不能永久不開(kāi)國(guó)門(mén)啊”;“這樣對(duì)經(jīng)濟(jì)影響確實(shí)很大啊”;“美國(guó)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復(fù)蘇強(qiáng)勁了,我們反而受影響”。……這些都是典型的抱怨。我身邊很多人都會(huì)這么說(shuō)。
另外還有悲觀和懷疑情緒:“這滅活疫苗也不知道對(duì)Delta管不管用”。有的人甚至?xí)f(shuō):“哎呀不如放開(kāi)算了,與病毒共存算了。國(guó)外也都這樣。”
這些坊間言論都挺有代表性的。筆者在與朋友聚會(huì)時(shí),偶爾也會(huì)附和說(shuō)說(shuō)。這就是大家疫情之下的情緒的正常表達(dá)。大家的討論并不旨在提供專(zhuān)業(yè)的意見(jiàn),更不是在表達(dá)什么政見(jiàn),都相信國(guó)家最終會(huì)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選擇。
而實(shí)際上,這些言論都屬于“站著說(shuō)話(huà)不腰疼”。為何?因?yàn)槲覀兛傮w上是享受到“堅(jiān)決清零”防疫措施的好處的:我們是全球疫情防控做得最好的國(guó)家,人民的生命安全得到了最大的保護(hù)。我們?nèi)ツ甑?span lang="EN-US">GDP是主要國(guó)家里唯一正增長(zhǎng)的。我們享受到了疫情防控的這些好處。我記得去年二月份李文亮逝世時(shí),疫情到了最低谷,但到了二月末三月初疫情得到控制,并在歐美廣泛爆發(fā)時(shí),人們的看法得到了根本扭轉(zhuǎn),看到只有中國(guó)政府才是真正關(guān)注人民生命安全的,并且看到了中國(guó)制度的優(yōu)越性。大家都慶幸自己在中國(guó)。
但一年多了,人們開(kāi)始倦怠了。因?yàn)椴《緦?shí)在離我們太遠(yuǎn)了。只是在新聞媒體上看到海外疫情如何嚴(yán)重。完全變成了一些數(shù)據(jù)。除了武漢市民之外,我們的全民其實(shí)對(duì)COVID-19都沒(méi)有什么直接體會(huì),只是因?yàn)閰⑴c疫情防控遇到了一些麻煩而已。
如果COVID-19疫情真的在中國(guó)再次爆發(fā),政府躺平,會(huì)如何?大規(guī)模的感染、住院率極速上升,醫(yī)院瀕臨崩潰,死亡人數(shù)數(shù)萬(wàn)、數(shù)十萬(wàn),無(wú)數(shù)家庭失去了老人。請(qǐng)注意,這是一個(gè)非常關(guān)注生命安全,非常尊重老人的儒家社會(huì)。請(qǐng)問(wèn)屆時(shí)會(huì)怎么樣?
毫無(wú)疑問(wèn),社會(huì)輿情會(huì)完全反轉(zhuǎn)。人們會(huì)把矛頭全部對(duì)準(zhǔn)政府,因?yàn)檎J(rèn)為全能政府要承擔(dān)一切責(zé)任,而且輿論還會(huì)政治化,轉(zhuǎn)化為對(duì)體制的不滿(mǎn)。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去年李文亮醫(yī)生逝世時(shí)的情形。
誰(shuí)又會(huì)是對(duì)政府最積極的批判者?我相信還是那些對(duì)中國(guó)體制一直懷疑和批評(píng),對(duì)西方比較向往的人。包括方方這樣的作家。我相信,同樣是這批人,在疫情以來(lái)相當(dāng)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對(duì)中國(guó)政府的治理能力已經(jīng)沒(méi)有什么話(huà)好說(shuō),但這個(gè)時(shí)候又會(huì)冒出來(lái)了,他們也更有可能是西方的“躺平”、“群體免疫”和“病毒共存論”的同情者。
二、實(shí)際問(wèn)題所在:不是和“病毒共存”,而是如何防止境外輸入
筆者只是作為一個(gè)普通公民(而非醫(yī)學(xué)界/衛(wèi)生界的專(zhuān)業(yè)人士)發(fā)表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國(guó)外防輸入、內(nèi)防擴(kuò)散的政策是可以執(zhí)行的,包括對(duì)Delta變種。
最近幾周,加強(qiáng)管控后,新增本土病例馬上就被壓下去了。作者經(jīng)常往來(lái)的幾個(gè)大城市——北上廣深,都沒(méi)有新的案例,事實(shí)上我們已經(jīng)把Delta初步控制住了,正在清零。所以,從控制疫情的角度看,外防輸入、內(nèi)防擴(kuò)散這個(gè)措施是可行的,包括針對(duì)Delta。只要我們?cè)敢獠扇〈胧覀兌伎梢苑雷?span lang="EN-US">Delta的,所要探討的只是社會(huì)代價(jià)問(wèn)題。
其實(shí)只要人們的生活恢復(fù)往常,短期的悲觀情緒和怨氣就會(huì)減少,輿情就會(huì)改善,討論的迫切性馬上又會(huì)削弱。疫情一反復(fù),人們因?yàn)榫氲【蜁?huì)開(kāi)始抱怨。
疫情防控是一項(xiàng)公共衛(wèi)生政策,這種政策不能跟著老百姓的情緒走。如果跟著老百姓情緒走,那怎么不在2020年1月武漢封城前夕來(lái)個(gè)武漢市民大投票呢。那誰(shuí)會(huì)同意封城呢?那還有什么專(zhuān)業(yè)性和科學(xué)可言呢?還有什么公共衛(wèi)生政策可言呢?
第二,不能泛泛地說(shuō)“和病毒共存”。
我理解這里所說(shuō)的所謂“共存”,并不是說(shuō)具體某個(gè)人和COVID-19的關(guān)系,而是指一種公共衛(wèi)生政策:我們?nèi)菰S病毒在人的世界里傳播,承擔(dān)一定的生命安全風(fēng)險(xiǎn),但不打算完全消滅它(eradication),也不會(huì)采取特別激進(jìn)的防控措施。
但要問(wèn)的正確問(wèn)題是:和什么樣的病毒“共存”?顯然,COVID-19 Delta變種這個(gè)具體的病毒是不能和我們“共存”的,因?yàn)樗膫魅拘浴⒅匕Y率、死亡率是初版COVID-19的數(shù)倍,對(duì)社會(huì)公共健康的危害極大。我們的社會(huì)沒(méi)有辦法承擔(dān)這樣的代價(jià)。
尤其是,COVID-19最主要傷害的是老年人群體——特別是高齡群體,而高齡群體注射疫苗的比例恰恰又是比較低的,因此他們?nèi)匀皇遣《靖呶H后w。我們一旦“躺平”,病毒就會(huì)首當(dāng)其沖地傷害這些人。
另外還有一個(gè)疫苗與Delta的關(guān)系。到底打了科興、國(guó)藥等國(guó)產(chǎn)滅活疫苗的人群面對(duì)Delta時(shí)的防護(hù)性如何。我覺(jué)得現(xiàn)在數(shù)據(jù)量可能還是不夠的。科學(xué)家還在動(dòng)態(tài)研究,需要有更大的數(shù)據(jù)支持。這種研究,是制定公共衛(wèi)生政策的一切基礎(chǔ)。在完全搞清楚之前,我們是不可能冒風(fēng)險(xiǎn)的。
何時(shí)可以談?wù)摬《竟泊妫科鋵?shí)是COVID-19病毒真正“流感化”的時(shí)候:病毒的毒性大大下降了——無(wú)論是打了疫苗的,還是沒(méi)有打疫苗的。這時(shí)我們才有可能去探討和它“共存”的可能性。但在Delta出現(xiàn)時(shí)討論這個(gè)是不合宜的。而且會(huì)造成輿論和見(jiàn)解上的混亂。
第三,公共衛(wèi)生政策反映了一國(guó)的制度、治理和價(jià)值觀。我們?nèi)ツ瓿跻呀?jīng)完成了公共選擇。
公共衛(wèi)生政策首先是要站在科學(xué)的基礎(chǔ)上的。針對(duì)這種烈性呼吸道傳染病,疫情管控肯定會(huì)有社會(huì)代價(jià)的,其實(shí)是一項(xiàng)有權(quán)衡取舍的公共選擇。要解決的問(wèn)題:
1)我想保什么,可以放棄什么(我的priority);
2)我的能力讓我能夠保什么,不能保什么(我的capability)。
顯然,不同國(guó)家和社會(huì)的選擇是不同的。
1)我想保什么:中國(guó)的選擇是:保全體民眾的健康。生命是第一位的,這是我們的基本底線(xiàn)。其中,與西方社會(huì)不同的是,我們是一個(gè)尊老社會(huì),特別關(guān)注老人的安康。我們的老人很多也是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的(而不像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一樣與子女分開(kāi),獨(dú)居或居于機(jī)構(gòu)養(yǎng)老場(chǎng)所)。中國(guó)社會(huì)愿意為了保護(hù)老人付出更大的代價(jià)——包括每個(gè)人讓渡一些自己的權(quán)利、自由、隱私,社會(huì)承擔(dān)一些經(jīng)濟(jì)上的損失。
那些覺(jué)得西方模式也不錯(cuò)的人,給你們一個(gè)選擇,你們?cè)敢鈳依闲。貏e是家里的高齡老人,一起去美國(guó)、英國(guó)居住么?我表示懷疑。因?yàn)樽鳛橹袊?guó)人,你們也是尊重老人的。所以這些連精致利己都不算,純粹就是站著說(shuō)話(huà)不腰疼。
西方是不同的,西方要保許多其他的東西。譬如說(shuō)保個(gè)人的各種自由,保個(gè)人的隱私,要大算經(jīng)濟(jì)賬,但老人是可以放棄、可以犧牲的。
2)我能保什么: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guó)的舉國(guó)體制、數(shù)字化治理、個(gè)人能夠讓渡部分的權(quán)利與自由、眾志成的心理,使得中國(guó)居然可以實(shí)現(xiàn)“清零”,并最終在各方面獲得一個(gè)均衡。
但西方實(shí)際上是沒(méi)有這個(gè)選擇,它做不到這些,不可能全面控制疫情,一定要付出巨大的人命代價(jià)。而且如果防疫效果也不佳,還要犧牲經(jīng)濟(jì),那還不如老早“躺平”,選擇“群體免疫”,但不惜犧牲老人。
中國(guó)還能做選擇,其實(shí)是能力的體現(xiàn),是一種“奢侈”,是“強(qiáng)者的煩惱”。而我們也早在2020年1月對(duì)武漢封城時(shí)就已經(jīng)做了這樣的公共選擇了:中國(guó)政府代表中國(guó)人民做出了公共選擇:我們將用最嚴(yán)格的方式對(duì)抗COVID-19(“SARS化”),而非“流感化”的應(yīng)對(duì)方法,以保證最廣大人民群體特別是老年群體的生命安全。這是一個(gè)歷史的選擇。
今天再翻過(guò)來(lái)討論這個(gè)問(wèn)題是有些莫名奇妙的。難道我們一開(kāi)始就選錯(cuò)了?難道搞了半天死了上百萬(wàn)人的西方是正確的?中國(guó)社會(huì)能夠接受死上百萬(wàn)老人么?現(xiàn)在討論這個(gè)問(wèn)題有什么意義呢?莫名奇妙。
第四,真正要討論的問(wèn)題是如何應(yīng)對(duì)國(guó)外的輸入性疫情。
我們不可能因?yàn)槲鞣缴鐣?huì)的制度、價(jià)值觀、能力、選擇(西方人想保什么、能保什么)去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公共衛(wèi)生政策。這其實(shí)本質(zhì)是個(gè)制度問(wèn)題、文化問(wèn)題、政治問(wèn)題。它就和西方不會(huì)采取中國(guó)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國(guó)也不會(huì)采取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一樣的。
現(xiàn)在中國(guó)能做的,就是繼續(xù)觀察海外疫情的發(fā)展,病毒本身的發(fā)展,做好嚴(yán)防死守。要看到現(xiàn)在的疫情全部都是海外輸入的,所以還是一個(gè)如何“給國(guó)門(mén)戴口罩”的問(wèn)題。至少在相當(dāng)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我們會(huì)延續(xù)這個(gè)政策。我們不可能冒著醫(yī)院崩潰、大量老年人死亡、穩(wěn)定出現(xiàn)問(wèn)題的風(fēng)險(xiǎn)去加強(qiáng)國(guó)際旅行。這根本就不是一個(gè)選擇!
中國(guó)有14億人。美國(guó)3億,大歐洲5億,日本1億多。整個(gè)發(fā)達(dá)國(guó)家經(jīng)濟(jì)體加在一起也就10億多,還不如中國(guó)人多。我們和那些依賴(lài)人口流動(dòng)的歐洲國(guó)家(譬如依賴(lài)旅游業(yè)的意大利)是不同的。所以,內(nèi)循環(huán)是可能的。總之,中國(guó)的操作空間更大,選擇更多。在可預(yù)見(jiàn)的未來(lái),中國(guó)的選擇顯然不是關(guān)閉國(guó)門(mén),而是為了應(yīng)對(duì)最壞的情況,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嚴(yán)防輸入,甚至進(jìn)入某種程度的關(guān)閉國(guó)門(mén),進(jìn)入更大的內(nèi)循環(huán)。
至于未來(lái)再怎么辦,譬如如果五年后疫情還在的話(huà)該怎么辦。那當(dāng)然是動(dòng)態(tài)觀察,到時(shí)再說(shuō),根本就不是現(xiàn)在要討論的問(wèn)題。
三、如果COVID-19出現(xiàn)在古代人的社會(huì)會(huì)怎么樣?——傳染病的社會(huì)學(xué)
有時(shí)我會(huì)思考這個(gè)問(wèn)題(但很可惜我還缺乏必要的知識(shí))。因?yàn)?span lang="EN-US">COVID-19主要是打擊中老年的,特別是7、80歲以上的人口。年輕人的重癥率、死亡率是非常低的。
原始人的平均壽命大概就20~30來(lái)歲吧。壯年就死了。遇到COVID-19的話(huà)根本不會(huì)是個(gè)“病”。如果發(fā)展到有城鎮(zhèn)出現(xiàn)的農(nóng)業(yè)社會(huì),人口居住更加密集,是會(huì)出現(xiàn)大規(guī)模傳染的。但假設(shè)人均壽命仍然是30~40歲,那這個(gè)病毒和“不存在”也是一樣的:可能許多人都感染了,但是沒(méi)有人因此而死亡。大多人的癥狀很輕。我們甚至可以說(shuō),從傳染病學(xué)的角度看,這個(gè)病存在,但從社會(huì)學(xué)的角度看,這個(gè)病根本不存在……同時(shí),人們很自然的就因?yàn)椴粩嗟貍魅径纬闪四撤N群體免疫,并且能夠代際相傳。
從病毒的角度而言,為了廣泛傳播,也要找到一個(gè)均衡點(diǎn)。如果宿主被很快殺死,是不利于傳播的。在完全自然的狀態(tài)下,假設(shè)大量的人被感染,且病毒的“毒性”更大。那在自然選擇下,一方面活下來(lái)的人會(huì)取得抗體,另一方面毒性更大的病毒也自然淘汰,更加溫和的變種留了下來(lái)。最后,與人類(lèi)找到某種“共存”的關(guān)系。
迄今我們還會(huì)感冒。造成感冒的病毒有兩百多種,包括許多類(lèi)別的冠狀病毒。我猜想,許多病毒是非常古老的,早就和人類(lèi)形成了“共生”關(guān)系。
但這是把人類(lèi)變成自然的試驗(yàn)田,讓病毒自然繁衍發(fā)展,讓人類(lèi)在病毒侵襲下自然的死亡、淘汰……最終形成這樣的關(guān)系。
病毒是古老的,但在COVID-19出現(xiàn)的二十一世紀(jì),人類(lèi)社會(huì)已經(jīng)大變樣了。
人類(lèi)非常的長(zhǎng)壽,出現(xiàn)了大量的70歲以上的高齡群體,一個(gè)在幾千年之前“非常溫和”,甚至可以“社會(huì)性不存在(socially non-existent)”的病毒會(huì)變成一個(gè)“毒性很大的烈性呼吸道傳染病”,專(zhuān)門(mén)打擊這部分群體。
人類(lèi)也有能力通過(guò)科學(xué)手段發(fā)現(xiàn)、識(shí)別這個(gè)病毒,并且不能放任不理,由其在人類(lèi)社會(huì)里蔓延、肆虐眾生,通過(guò)為數(shù)代人甚至更長(zhǎng)時(shí)間的大規(guī)模感染、大量的死亡(導(dǎo)致病毒轉(zhuǎn)向更加溫和的變種)以及自然的群體免疫去與病毒建立一個(gè)更溫和的關(guān)系。此時(shí)的人類(lèi),要在這個(gè)瞬間節(jié)點(diǎn)抑制這個(gè)病毒:人類(lèi)不僅僅會(huì)采用各種醫(yī)療手段(medicine)去應(yīng)對(duì),還要建立系統(tǒng)的公共衛(wèi)生(public health)政策與體系,開(kāi)展系統(tǒng)性的防控。
在古代人類(lèi)社會(huì),這是不可想象的。二十一世紀(jì)二零年代的中國(guó),是一個(gè)政府非常注重人民生命安全及福祉的社會(huì),也是一個(gè)非常尊老的社會(huì)。而政府又具備足夠的公共政策手段,那么可想而至它會(huì)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它一定會(huì)打破病毒在純自然狀態(tài)下與人類(lèi)的互動(dòng)發(fā)展的邏輯。過(guò)程中,它也會(huì)為這個(gè)選擇承擔(dān)一定的代價(jià)。而之所以有這個(gè)選擇,也是因?yàn)橹袊?guó)的社會(huì)發(fā)展了。
我覺(jué)得從這個(gè)大力士角度講,中國(guó)已經(jīng)比西方要更加先進(jìn)了。我們其實(shí)在做一些他們無(wú)法做的社會(huì)選擇。
四、關(guān)于張文宏醫(yī)生
跑題了。討論了這么多問(wèn)題,讓筆者回到張文宏醫(yī)生的爭(zhēng)議。
中國(guó)抗疫體制是非常特殊的,它體現(xiàn)了我們舉國(guó)體制的特征、能力與我們的文化。
這其中,堅(jiān)持、眾志成城是非常重要的一條。它需要所有人都擰成一股繩,共同應(yīng)對(duì)疫情。如果沒(méi)有這種眾志成城,沒(méi)有這種意志力,沒(méi)有政府自上而下的約束與加持,防疫抗疫早就失敗了。
為什么張文宏醫(yī)生的言論有如此大的爭(zhēng)議?筆者的理解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他的言論在這個(gè)關(guān)鍵的節(jié)點(diǎn)出來(lái),使得我們的防疫體系在心理上出現(xiàn)了一道裂縫。
我們不論他言論的初衷是什么,但當(dāng)下的時(shí)點(diǎn)是比較特殊的:Delta比較厲害,人們防疫很疲憊了、離真實(shí)的疫情太遠(yuǎn)了使得麻痹了、膽子大了,一些切身利益受到損害,等等。這就使得他的言論有了支持響應(yīng)者,并構(gòu)成了對(duì)我們防疫抗疫長(zhǎng)城的沖擊。筆者以為,言者可能無(wú)心,他并沒(méi)有想那么多,并不打算挑戰(zhàn)我們的防疫體系,而只是和我們一樣在發(fā)表一些見(jiàn)解。但他和我們的區(qū)別在于,他的身份是不一樣的,他被認(rèn)為是疫情防控權(quán)威,一言九鼎,可以帶動(dòng)輿論。一些抱有懷疑和悲觀情緒的人會(huì)被他的言論所帶動(dòng)。他直率的表達(dá)風(fēng)格更會(huì)讓受眾覺(jué)得他說(shuō)出了真話(huà)。
而實(shí)際上,我們看,張文宏是個(gè)醫(yī)生(復(fù)旦大學(xué)附屬華山醫(yī)院感染科主任)。醫(yī)生的領(lǐng)域是治病,個(gè)人醫(yī)療,medicine。
而傳染病防控屬于公共衛(wèi)生(public health),是一種公共政策,與經(jīng)濟(jì)、政治、社會(huì)其他政策高度相關(guān)。
張文宏醫(yī)生經(jīng)常提到美國(guó)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xué)(John Hopkins)。
實(shí)際上,霍普金斯大學(xué),公共衛(wèi)生學(xué)院(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https://www.jhsph.edu/ 與醫(yī)學(xué)院(School of Medicine)https://www.hopkinsmedicine.org/som/ 是兩個(gè)學(xué)院。這完全是兩個(gè)領(lǐng)域。
哈佛大學(xué),公共衛(wèi)生學(xué)院(Harvard T.H.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https://www.hsph.harvard.edu/ 與醫(yī)學(xué)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https://hms.harvard.edu/ 是兩個(gè)學(xué)院。
筆者之前也不了解的,在哈佛的時(shí)候接觸了兩個(gè)學(xué)院的學(xué)生,后來(lái)參與了一些行程培訓(xùn)課程,才發(fā)現(xiàn)內(nèi)容完全不同。雖然也有不少學(xué)生有醫(yī)療背景,但公共衛(wèi)生的領(lǐng)域更廣,完全是公共政策的范疇。
翻譯一下:怎么給一個(gè)病人治病,和一個(gè)國(guó)家或社會(huì)怎么制定一項(xiàng)合理的傳染病防控政策,是兩碼事。前者是medicine,后者是public health。
Public health依賴(lài)的不僅僅是醫(yī)療技術(shù),還要有政治制度賦能和支持的。
張文宏是個(gè)醫(yī)生,他醫(yī)術(shù)再精湛,對(duì)傳染病理解再深,也還不是公共衛(wèi)生領(lǐng)域的專(zhuān)家。我理解他可能都不屬于公共衛(wèi)生這個(gè)圈子的(衛(wèi)生部、衛(wèi)健委、CDC這些才是公共衛(wèi)生領(lǐng)域)。他的知識(shí)肯定是會(huì)有短板的,在成名后,他不可避免的會(huì)在媒體的邀請(qǐng)下,討論一下他并不是最專(zhuān)業(yè)的內(nèi)容,特別當(dāng)他有了足夠的自信,同時(shí)也有表達(dá)欲望的時(shí)候。例如政治、制度、治理、公共選擇、經(jīng)濟(jì),社會(huì),這些其實(shí)很難是一個(gè)專(zhuān)業(yè)領(lǐng)域醫(yī)生熟知的話(huà)題。
他在去年3月份對(duì)美國(guó)的一系列評(píng)論,說(shuō)美國(guó)的醫(yī)療多么先進(jìn),如何能夠從容應(yīng)對(duì)疫情,勸網(wǎng)友不要為美國(guó)操心。
“若是美國(guó)的疫情嚴(yán)重了,它們肯定也是會(huì)調(diào)整相應(yīng)的應(yīng)對(duì)措施的。所以說(shuō)美國(guó)是有把握應(yīng)對(duì)它們的疫情的。
所以說(shuō)美國(guó)自己都不用擔(dān)心的事情,中國(guó)網(wǎng)友也不用對(duì)它們操碎心的。畢竟他們比誰(shuí)都愛(ài)惜自己的性命。
若是美國(guó)民眾感覺(jué)形勢(shì)不對(duì)了,肯定會(huì)抄家伙搞事情的。所以,所有的事情,盡在美國(guó)掌控之中。”
顯然,張文宏醫(yī)生完全不了解美國(guó)的社會(huì)、文化、制度,更不了解美國(guó)的政治。他就是在想當(dāng)然。筆者去年的文章是(《美國(guó)對(duì)抗COVID-19無(wú)力的12個(gè)原因及疫病的“社會(huì)建構(gòu)”》)分析了為什么美國(guó)不可能很好的防疫。
他所討論的這是一個(gè)公共衛(wèi)生問(wèn)題,不是一個(gè)個(gè)人醫(yī)療問(wèn)題。
而實(shí)際上,防疫已經(jīng)不僅僅是一個(gè)公共衛(wèi)生問(wèn)題了,是一個(gè)大政治問(wèn)題。
張文宏是一個(gè)醫(yī)生,他的專(zhuān)業(yè)在細(xì)分的微觀領(lǐng)域。他肯定會(huì)認(rèn)為美國(guó)的醫(yī)療科技先進(jìn),從medicine的角度看這個(gè)判斷是對(duì)的。但是他不了解美國(guó)的政治和文化,因此會(huì)做出完全錯(cuò)誤的判斷。當(dāng)然,張醫(yī)生說(shuō)什么都可以,筆者只是在說(shuō)明,他是有知識(shí)短板的。事實(shí)已經(jīng)印證了他的錯(cuò)誤。所以他在其他公共政策問(wèn)題上也會(huì)錯(cuò)判。
每個(gè)人都有知識(shí)短板。關(guān)鍵是要能夠看到自己的短板,不要過(guò)于自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當(dāng)你不是一個(gè)公眾人物的時(shí)候,說(shuō)啥都可以。如果你是公眾人物的時(shí)候,言論就要注意了。
我們?cè)倏纯磸埼暮赆t(yī)生的其他言論,其實(shí)可以發(fā)現(xiàn),他是比較偏好美國(guó)的。按照他的醫(yī)學(xué)背景,以及年齡段(1969年生人),完全可以理解。這個(gè)年紀(jì)的人還是以崇尚西方居多的。這并不是什么政見(jiàn),只不過(guò)是一種傾向:他的成長(zhǎng)經(jīng)歷會(huì)使得他自然地認(rèn)為西方的東西普遍更科學(xué)、更好、更合理,政府也更強(qiáng)大,治理更人性,人民素質(zhì)也更高。這是根深蒂固的。它不是政見(jiàn),只是時(shí)代的烙印。筆者以為這其實(shí)就是某種代溝。
在今天的國(guó)際局勢(shì)下,以及巨大的代際變化(新一代年輕人對(duì)中國(guó)模式更加自信),張文宏醫(yī)生的說(shuō)法就會(huì)讓人有些不適了。我覺(jué)得我們既可以理解張文宏醫(yī)生的說(shuō)法,也不難理解那些對(duì)他有意見(jiàn)的人。
筆者覺(jué)得張文宏醫(yī)生一戰(zhàn)成名,接受各種訪(fǎng)談,成為一種流量經(jīng)濟(jì),其實(shí)是危險(xiǎn)的。很容易會(huì)介入自己不那么熟悉的話(huà)題并犯錯(cuò)誤。公共衛(wèi)生、中美制度比較這些也都是比較敏感的、涉關(guān)政治的話(huà)題,作為公眾人物,談?wù)撈饋?lái)要比較小心的。他畢竟是一個(gè)醫(yī)生,細(xì)分領(lǐng)域的專(zhuān)業(yè)人士,我覺(jué)得他很難有這么多的政治敏感度,看問(wèn)題總是難避免局限性的。也許他還被熱心的網(wǎng)友給“鼓勵(lì)”了,認(rèn)為尺度大一點(diǎn),講點(diǎn)自己的心里話(huà),會(huì)有更好的效果,社會(huì)也能歡迎和包容。但張醫(yī)生還是太單純了。
五、筆者再總結(jié)一下大的脈絡(luò):
1、中國(guó)的COVID-19防疫政策不是醫(yī)療(medicine),而是公共衛(wèi)生問(wèn)題(public health),隸屬公共政策
2、防疫公共衛(wèi)生政策還不僅僅是公共衛(wèi)生,關(guān)于國(guó)計(jì)民生、國(guó)家安全、各種底線(xiàn)思維,還與外交、地緣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掛鉤,早就上升為大政治了
3、國(guó)民享受了舉國(guó)體制下眾志成城疫情防控措施的以來(lái)的所有好處,對(duì)COVID-19有點(diǎn)麻痹放松,對(duì)防疫手段有點(diǎn)厭倦,也受到國(guó)外躺平主義下“病毒共存論”的影響
4、但實(shí)際上人們只是有所倦怠,疫情真的爆發(fā),導(dǎo)致生命健康的損失,人們立馬會(huì)開(kāi)始指責(zé)全能政府,甚至把問(wèn)題政治化
5、在這個(gè)關(guān)鍵節(jié)點(diǎn),必須堅(jiān)持中國(guó)一貫的防控政策,避免功虧一簣。必須教育好群眾,穩(wěn)住人心,不能有倦怠,更不能有戰(zhàn)敗主義
6、張文宏醫(yī)生發(fā)表了關(guān)于“與病毒共存”的說(shuō)法,剛好契合了一些民眾的想法,迎合了他們的倦怠心態(tài)和“厭戰(zhàn)主義”
7、張文宏醫(yī)生是抗疫以來(lái)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享有巨大的影響力的。他所發(fā)表的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超出了他的專(zhuān)業(yè)領(lǐng)域,對(duì)當(dāng)下的大國(guó)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迎合了民眾的想法,引發(fā)了討論。他的言論為我們的公共衛(wèi)生政策長(zhǎng)城上敲出了裂痕。這個(gè)裂痕一旦出現(xiàn),我們的防疫長(zhǎng)城就會(huì)被削弱:所有的人,從百姓到監(jiān)管機(jī)構(gòu)的基層人員都會(huì)動(dòng)員。這種影響是張文宏醫(yī)生沒(méi)有想到的
8、這是絕對(duì)不被允許的。有關(guān)部門(mén)也請(qǐng)高強(qiáng)等退休官員/老專(zhuān)家來(lái)發(fā)表意見(jiàn),正面回應(yīng)、駁斥張醫(yī)生的言論,引導(dǎo)輿論
9、張醫(yī)生過(guò)往的所謂“親美言論”也被一些網(wǎng)友摘抄出來(lái),對(duì)他本人發(fā)動(dòng)了責(zé)難與攻擊,質(zhì)疑他的根本立場(chǎng),還有挑戰(zhàn)他的博士論文的。其中有一些內(nèi)容,可以被歸為“網(wǎng)暴”范疇
10、喧囂之后,“與病毒共存”這個(gè)說(shuō)法也就不會(huì)再在公共領(lǐng)域出現(xiàn)了。政府要做的事是統(tǒng)一思想,讓大家眾志成城,繼續(xù)維護(hù)中國(guó)得來(lái)不易的抗疫成果。
六、關(guān)于言論空間的問(wèn)題
很多人覺(jué)得,現(xiàn)在輿論打擊張文宏醫(yī)生,有很大的問(wèn)題的。這樣好的醫(yī)生居然也因言而被攻擊。我看朋友圈,不少人在發(fā)文支持張文宏。
對(duì)此,筆者的看法如下。
1、人出了名,獲得了流量,在聚光燈下,就要承擔(dān)這樣的風(fēng)險(xiǎn)。任何說(shuō)錯(cuò)的東西都會(huì)被人們用放大鏡去檢視。這就是出名的代價(jià)。所以,發(fā)言務(wù)必要謹(jǐn)慎,要注重場(chǎng)合,不能什么都說(shuō),不要對(duì)不完全熟知的問(wèn)題發(fā)表言論。就算非要發(fā)表言論,也要免責(zé),“我真的是胡說(shuō)八道的啊”
2、在當(dāng)下的國(guó)際格局下,發(fā)表親美言論,特別是經(jīng)不起推敲、立場(chǎng)大于事實(shí)的對(duì)美國(guó)比較友好的言論,會(huì)引起不少人的不適。你發(fā)這樣的言論,就準(zhǔn)備好承擔(dān)后果。另外,現(xiàn)在中國(guó)年輕人對(duì)美國(guó)也不能說(shuō)就是不理解的。如果你也不算是這方面特別的專(zhuān)家,少說(shuō)
3、要有政治敏感度。公共衛(wèi)生政策現(xiàn)在是大政治,都已經(jīng)算是基本國(guó)策了,這是不能隨便去說(shuō)的。可以討論,但要注重場(chǎng)合。什么時(shí)候說(shuō)什么話(huà),要注意影響
4、我們的社會(huì)沒(méi)有討論空間?公共政策有沒(méi)有動(dòng)態(tài)修正的可能性?當(dāng)然有啊!參加閉門(mén)的專(zhuān)家研討會(huì),給衛(wèi)生部門(mén)提建議。上書(shū),寫(xiě)內(nèi)參。有無(wú)數(shù)的渠道。其實(sh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言論限制,政府是動(dòng)態(tài)研究觀察,吸收各方面的信息,以求做出最準(zhǔn)確的決策判斷的,以張文宏的身份地位,有大把的渠道可以向上遞送他的觀察和建議,都會(huì)受到重視,得到反饋。但涉及基本大政方針的東西是不適合在公共領(lǐng)域隨便說(shuō)的。因?yàn)榇蠖嗳藳](méi)有足夠的知識(shí)與判斷力。他們會(huì)認(rèn)為張文宏醫(yī)生都這么說(shuō)了,這就是代表正確的東西了。張文宏醫(yī)生的說(shuō)法可能在社會(huì)引發(fā)分歧甚至混亂。作為一個(gè)負(fù)責(zé)任的專(zhuān)業(yè)人士,他應(yīng)該在專(zhuān)業(yè)圈、決策圈的范圍內(nèi)提交他的專(zhuān)業(yè)建議,而不是在公開(kāi)場(chǎng)合下向不特定人群公開(kāi)表達(dá)可能本來(lái)也不太成熟的意見(jiàn)。他更關(guān)心的應(yīng)該是公共政策的研究與決策,而非滿(mǎn)足自己對(duì)外講演的一時(shí)快感。但無(wú)論如何,筆者以為張文宏醫(yī)生的渠道都是打通的
5、張文宏是共產(chǎn)黨員,他說(shuō)在關(guān)鍵時(shí)刻,共產(chǎn)黨員要先上,沖到一線(xiàn)。那么這個(gè)時(shí)候也一樣,這就是一個(gè)基本的紀(jì)律問(wèn)題。不能妄議大政。可以提意見(jiàn),但要遵循流程。最后要以大局為重的。這就是政治站位
6、他有沒(méi)有遭受網(wǎng)絡(luò)暴力?筆者以為,有就有吧。你有沒(méi)有在公眾場(chǎng)合被攻擊。網(wǎng)絡(luò)暴力是虛擬的,是鍵盤(pán)俠的戰(zhàn)役。出了名,有了流量,就做好準(zhǔn)備因?yàn)橐谎圆缓媳痪W(wǎng)友抨擊吧。筆者也被網(wǎng)友抨擊,這很正常,不算什么。網(wǎng)友可以捧你,也可以殺你如果這都不能承受,就不要加入到這樣的世界里
7、張文宏工作受到影響了么?肯定沒(méi)有啊。網(wǎng)上挨了挨罵而已。他的職級(jí)照舊,工作照舊,生活早就。他依然可以組織、發(fā)起、參與各種專(zhuān)業(yè)討論。他要發(fā)聲,我相信憑借他的影響力,中央都會(huì)聽(tīng)取。他的地位并沒(méi)有改變。只是他需要更加“內(nèi)斂”一點(diǎn),注意在什么場(chǎng)合說(shuō)什么話(huà)。這不是一個(gè)要證明你存在的議題,而是一個(gè)全國(guó)一統(tǒng)的整體布局。但無(wú)論如何,網(wǎng)友無(wú)需多慮。張文宏不會(huì)受到什么實(shí)質(zhì)影響,除了……
8、除了博士論文。這就是一碼歸一碼的問(wèn)題了。如果犯了錯(cuò)誤,那就要承擔(dān)代價(jià)。我看網(wǎng)上有說(shuō)“20年前的標(biāo)準(zhǔn)不同,難道要追溯應(yīng)用現(xiàn)在的標(biāo)準(zhǔn)么”?這就不對(duì)了,難道20年前就允許抄襲了?如果張文宏醫(yī)生確實(shí)犯了錯(cuò)誤,我們拿著一紙說(shuō)明,坐時(shí)光機(jī)飛回20年前,當(dāng)時(shí)的學(xué)校領(lǐng)導(dǎo)會(huì)承認(rèn)?當(dāng)然不會(huì)。學(xué)術(shù)標(biāo)準(zhǔn)是一貫的,只是存在一個(gè)能否驗(yàn)證及評(píng)價(jià)的專(zhuān)業(yè)問(wèn)題。對(duì)于張醫(yī)生的博士論文,筆者的看法是,交由復(fù)旦大學(xué)去研究、判斷、決策,做出結(jié)論。如果確有問(wèn)題,那就處理。不要試圖把自己的論文和國(guó)家聯(lián)系起來(lái),不要妄想責(zé)成國(guó)家為自己背書(shū)
9、國(guó)家如何決策?有關(guān)部門(mén)最后一定會(huì)做出符合國(guó)家利益的決定。要看到,張文宏醫(yī)生是疫情防控大計(jì)里有功之人,他其實(shí)沒(méi)有必要在公域發(fā)表各種不完全熟知和有把握的意見(jiàn),更不應(yīng)該隨便發(fā)表對(duì)中國(guó)大政不同的意見(jiàn)。如果他希望對(duì)國(guó)家更好,希望公共政策更加合理,希望自己改變政策制訂,就應(yīng)該多利用他的資源提建議,直接找到渠道為政府服務(wù),而非通過(guò)民間傳話(huà)
10、防疫公共衛(wèi)生一定會(huì)成為一個(gè)非常重要的政治政策領(lǐng)域。在未來(lái)的中央全會(huì)里,有可能就該問(wèn)題進(jìn)一步深化,使之成為當(dāng)前中央的核心部門(mén)。
以上是本篇。很困,晚安睡覺(jué)!
20210817
作者:兔主席 來(lái)源:tuzhuxi 微信號(hào)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gè)人觀點(diǎn),不代表本站觀點(diǎn),僅供大家學(xué)習(xí)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yíng)利性網(wǎng)站,如涉及版權(quán)和名譽(yù)問(wèn)題,請(qǐng)及時(shí)與本站聯(lián)系,我們將及時(shí)做相應(yīng)處理;
3、歡迎各位網(wǎng)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wǎng),依法守規(guī),IP可查。
作者 相關(guān)信息
內(nèi)容 相關(guān)信息
復(fù)旦大學(xué)啟動(dòng)張文宏論文抄襲調(diào)查
2021-08-16張文宏并非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而是抄襲和造假大王
2021-08-15? 昆侖專(zhuān)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wù) 新前景 ?

? 國(guó)資國(guó)企改革 ?

? 雄安新區(qū)建設(shè) ?

? 黨要管黨 從嚴(yán)治黨 ?

 習(xí)近平簽署主席令,《中醫(yī)藥法》正式頒布
習(xí)近平簽署主席令,《中醫(yī)藥法》正式頒布 習(xí)近平簽署主席令,《中醫(yī)藥法》正式頒布
習(xí)近平簽署主席令,《中醫(yī)藥法》正式頒布 821人注射疫苗后感染新冠,被中醫(yī)藥全部治愈,為何不廣為宣傳安定人心?
821人注射疫苗后感染新冠,被中醫(yī)藥全部治愈,為何不廣為宣傳安定人心?
 張志坤:如何研判評(píng)估當(dāng)前的國(guó)際政治與安全環(huán)境
張志坤:如何研判評(píng)估當(dāng)前的國(guó)際政治與安全環(huán)境 朱亞夫:謹(jǐn)防 “互聯(lián)網(wǎng)-”
朱亞夫:謹(jǐn)防 “互聯(lián)網(wǎng)-” 王毅:中美關(guān)系須撥亂反正,重回正軌(全文)
王毅:中美關(guān)系須撥亂反正,重回正軌(全文)? 社會(huì)調(diào)查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