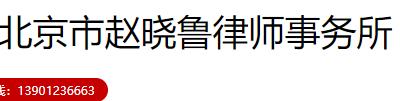1965年前后,時(shí)任國務(wù)院副總理的李伯伯在鄭州接見了非洲某國政府首腦,他將對(duì)方送的一把鋼刀轉(zhuǎn)送給我。那是一把又長又厚、沒有開刃的禮品刀,刀鞘是皮革的,花紋和顏色滿是異國情調(diào)。作為打小就喜歡舞刀弄?jiǎng)Φ哪泻⒆樱矣泻枚嗵於际菗еㄈ蝗雺舻摹?/section>1975年中,我的右小腿脛骨增生嚴(yán)重,鄭州的醫(yī)生診斷為骨癌。父親親自打電話聯(lián)系,讓我去北京住在李伯伯家里,林阿姨領(lǐng)著我去北醫(yī)三院等大醫(yī)院求醫(yī)問藥,最終確診不是癌癥,大人們才都放下心來。兒時(shí)的記憶雖然遙遠(yuǎn)懵懂,略顯稚氣滑稽,可卻真實(shí)永存!“周恩來是李先念一向敬重的老領(lǐng)導(dǎo),老戰(zhàn)友。從一九三五年懋功會(huì)師李先念和周恩來相識(shí),幾十年來風(fēng)雨同舟,患難與共,結(jié)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在周恩來住院期間,一有時(shí)間,李先念就去探望。據(jù)《周恩來年譜》記載,他去醫(yī)院請(qǐng)示匯報(bào)工作和探望有近百次,是去醫(yī)院次數(shù)最多的領(lǐng)導(dǎo)人之一。”(引自《李先念傳1949-1992》第887頁)1975年12月中下旬,李伯伯多次前往醫(yī)院看望周總理。鑒于他的病情,醫(yī)生建議到外地治療休養(yǎng)。報(bào)告轉(zhuǎn)給毛主席同意了。可李伯伯并沒有離京。1976年1月5日和6日,李伯伯還先后兩次探望了周總理。1月8日上午9時(shí)57分,敬愛的周總理在北京解放軍305醫(yī)院與世長辭。據(jù)我所知,住在中南海東花廳東側(cè)院的李伯伯是第一個(gè)趕到周總理身邊告別的中央領(lǐng)導(dǎo)同志。不僅如此,李伯伯還毫不畏懼已然嚴(yán)峻、緊張的形勢,以大無畏的精神和勇氣,挺身而出、仗義執(zhí)言、先聲奪人!他老人家第一個(gè)當(dāng)眾慷慨陳詞:“對(duì)總理,不能不搞追悼會(huì)。如果不搞追悼會(huì),這是違背民意的事,我們無法向人民群眾交代。”(引自《李先念年譜》第五卷第441-442頁)李伯伯的話語擲地有聲,李伯伯的忠誠永載史冊(cè)!在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出版的《李先念傳1949-1992》第888頁,完整記述了《李先念傳》編寫組采訪我的談話記錄:
“劉建勛之子劉立強(qiáng)來京出差,住在李先念家里,不知道周恩來已經(jīng)過世,看到李先念情緒低沉,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事。他回憶說:‘當(dāng)天的午飯和晚飯,李伯伯幾乎一言未發(fā),基本上沒動(dòng)過筷子。特別是晚飯時(shí),老人家坐下后很快就起身離去。沒過幾秒鐘,就聽見‘咣鐺’沉重的一聲響,緊接著聽到李伯伯急促地喊著小女兒小林的小名:‘小妹、小妹……’,我們馬上丟下碗筷跑過去,只見李伯伯已經(jīng)倒在走廊的地毯上。我們趕緊把李伯伯?dāng)v扶起來。年過花甲的老人家摔得這么重、這么突然,可是他依然還是一聲不吭。我的心里又緊張又奇怪。那時(shí)的李伯伯肯定是痛苦、難過到了心力交瘁的極點(diǎn)。他老人家就是這樣一位重感情、講情義,但又守紀(jì)律、顧全大局的革命老前輩。’”
第二天清晨,我從廣播里聽到周總理逝世的噩耗,猶如晴天霹靂一般,再聯(lián)想到昨天李伯伯的精神和身體狀況,懸著的心一下子繃得更緊、更高了。正在北京外國語學(xué)院學(xué)習(xí)的李平從學(xué)校匆匆趕回家。就在他的小屋里,我倆相對(duì)而泣,幾乎哭到中午。時(shí)至今日,我不知看過多少有關(guān)周總理離開我們那段日子的回憶和描述,最令我痛心和難忘的,卻永遠(yuǎn)是在1月8日,那個(gè)天地同悲、日月無光的時(shí)刻,李伯伯無聲勝有聲的身影和表情。
“在‘四人幫’極力壓制悼念活動(dòng)的情況下,一月十四日下午,李先念、紀(jì)登奎、華國鋒、陳錫聯(lián)、吳德等在國務(wù)院會(huì)議廳開會(huì),商定:通知國務(wù)院各單位可設(shè)靈堂,悼念周恩來……
李先念懷著極大的悲痛心情參加了周恩來的各項(xiàng)治喪活動(dòng),直至最后送別他一生敬仰的老領(lǐng)導(dǎo)周恩來。”(引自《李先念傳1949-1992》第889頁)
那幾天,林阿姨帶著我們?nèi)ノ挥谕醺谋本┦泄に嚸佬g(shù)總公司,挑選了許多懷念周總理的精美工藝品。在北京人民大會(huì)堂1月15日舉行周總理追悼大會(huì)前,林阿姨和子女,再加上我,以及幾位老前輩的夫人、孩子,共九個(gè)人擠進(jìn)一輛黑色的大“奔馳”車,參加了在北京醫(yī)院提前組織的一場小范圍告別儀式。而經(jīng)驗(yàn)老到、心思縝密的李伯伯則交代女兒李紫陽和我騎上自行車,利用夜色多次前去天安門廣場等處轉(zhuǎn)悠。我們把車子放在路邊,隨著悼念周總理的人群浩浩蕩蕩地緩慢前行,直到深夜……1976年的10月8日前后,我從部隊(duì)到北京出差,住在李伯伯家。那時(shí),“四人幫”剛剛被黨中央隔離審查沒兩天。李伯伯作為這個(gè)英明決定的核心決策人,雖然每天公務(wù)繁忙、日理萬機(jī),但精神卻格外的好。一天吃飯,他老人家與我們共同品嘗秋蟹,過來人都記得那可是當(dāng)時(shí)北京人的樂事。席間,老人家忽然話鋒陡轉(zhuǎn),問我看沒看過《反擊》這部電影,我答:“沒有!”李伯伯大聲地說:“要看看,這個(gè)電影是反你爸爸的!”忘了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的午后一、兩點(diǎn)鐘,辦公室秘書就來通知,讓我和周總理、鄧穎超媽媽的秘書趙煒阿姨乘坐一輛小車,去北京電影制片廠觀看了《反擊》。車上閑聊中,趙煒阿姨感慨地對(duì)我說:“年初那段日子里,我們給老同志送文件,王震同志憋不住,當(dāng)著我們的面就開罵‘四人幫’;可先念同志卻沉得住氣。給他送文件時(shí),有時(shí)遇見他正在院子里散步鍛煉身體,他總是笑瞇瞇地說,我已經(jīng)向中央請(qǐng)假休息,送么事文件啊!不要送了吧,送了也不一定看哦。其實(shí)他早已謀略在心、胸有成竹。關(guān)鍵時(shí)刻,他協(xié)助華主席、聯(lián)絡(luò)葉帥,選將排兵,能夠不費(fèi)一槍一彈,一下子就把‘四人幫’徹底解決了。真是太棒了……”回想起來,趙煒阿姨當(dāng)時(shí)那無比欽佩贊揚(yáng)的神情、語氣,猶在眼前。
當(dāng)天晚飯前,李伯伯一看到我就問道:“看《反擊》了嗎?”我回答說:“下午看的。”他追問道:“是不是反你爸爸的啊?”我接茬說:“我爸算老幾呀?實(shí)際上還不是對(duì)著你們中央來的啊!他們也忒下作了,什么黃河省,含沙射影!省委書記兒子的名字和我的小名一模一樣,也叫小強(qiáng)……”李伯伯一邊認(rèn)真聽著、一邊頻頻點(diǎn)頭,還沒等我天馬行空般“發(fā)表”完觀后感,老人家早已樂得開懷大笑不止。如今我只要一想起來,他那勝利的豪情,那爽朗的笑聲,還有那濃重的湖北鄉(xiāng)音,歷歷在目、聲聲入心。(引自筆者著《為了永不忘卻的紀(jì)念——獻(xiàn)給敬愛的父親劉建勛》,《劉建勛紀(jì)念文集》第456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發(fā)行)后來我寫了一篇數(shù)千字的文章,剖析、批判《反擊》影片的來龍去脈,曾被多家媒體刊登或轉(zhuǎn)載,好像現(xiàn)在還能在網(wǎng)上看到。前幾年,曾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xié)副秘書長的趙煒阿姨在一次紀(jì)念活動(dòng)上偶遇我愛人耿西林。當(dāng)?shù)弥覀z是一家子后,她非常高興,兩人聊得十分投緣。她還將回憶錄《西花廳歲月——我在周恩來 鄧穎超身邊三十七年》簽字送給了我們。我們心底珍藏的,都正是對(duì)那一代偉人的無限熱愛、敬仰和懷念!我們胸中篤信的,也都正是這種熱愛、敬仰和懷念必會(huì)永遠(yuǎn)傳承、賡續(xù)下去!在隨后的歲月里,我逐漸了解了更多李先念伯伯的偉大生平。為了撰寫此文,我重新認(rèn)真拜讀了林佳楣阿姨送的有關(guān)李伯伯的書籍,重點(diǎn)核實(shí)了一些老前輩的回憶,將自認(rèn)為重要的部分內(nèi)容整理出來,留在心中:1909年6月23日,李伯伯出身在大別山區(qū)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的一個(gè)貧苦農(nóng)民家庭。他只讀過兩年私塾,十五歲就到漢口壽器店做木工學(xué)徒。參加革命后,有人開玩笑說他是“做棺材出身的”,李伯伯則風(fēng)趣地答道:“我是給舊社會(huì)做棺材的。”1926年冬,他秘密加入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tuán)。1927年秋,他率眾參加了著名的“黃麻起義”。12月17日正式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在徐向前的領(lǐng)導(dǎo)和教育下,他身經(jīng)百戰(zhàn)、多次負(fù)傷,逐漸成長為英勇善戰(zhàn)的年輕紅軍指揮員。李伯伯在晚年與我聊天時(shí)回憶說:“剛開始,有的人不服氣,可打了第一仗,還是個(gè)大勝仗,就全服了!”1932年秋,李伯伯的二哥陳有元在“肅反”中受誣陷、被殺害。他留給李伯伯最后的話是:“先念兄弟……你在部隊(duì)要好好干呀,要革命到底!”“李先念深情地望著他點(diǎn)了點(diǎn)頭,便帶著部隊(duì)匆匆而去。”對(duì)當(dāng)時(shí)才23歲的李伯伯來說,二哥的被捕、母親的告別和上級(jí)、戰(zhàn)友甘濟(jì)時(shí)的犧牲這“三件震撼心靈的事,是使他終生難以忘懷的。”(引自《李先念傳1909-1949》第80-81頁)
“1934年1月,李先念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委員會(huì)執(zhí)行委員”,時(shí)年未滿25歲。當(dāng)時(sh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在報(bào)告中曾“高度評(píng)價(jià)川陜根據(jù)地的地位和作用。”他說李伯伯戰(zhàn)斗的“川陜蘇區(qū)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個(gè)大區(qū)域……在爭取蘇維埃新中國的戰(zhàn)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義。”
在震驚世界的偉大長征中,李伯伯所在的“紅四方面軍歷時(shí)十九個(gè)月,翻過數(shù)座雪山,三過草地,一度南下,兩次北進(jìn),所經(jīng)大小戰(zhàn)斗數(shù)百次,最終與紅一、紅二方面軍勝利會(huì)師。”(引自老紅軍前輩張毅的回憶)
革命征程戎馬倥傯,李伯伯一生矢志不移。他老人家歷經(jīng)的千辛萬苦、千難萬險(xiǎn)絕非我們能夠想象。他是用生命和熱血書寫大大“忠誠”的人!若問在李伯伯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是什么精神力量始終如一地鼓舞、支撐著李伯伯?我覺得,那就是他老人家為黨、為民的不改初衷!“1936年10月24日,紅四方面軍第30軍軍長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奉命率部西渡黃河。過河部隊(duì)共兩萬一千八百多將士(占當(dāng)時(shí)紅軍總數(shù)的五分之二)。當(dāng)時(shí)稱為“河西軍”,11月11日,根據(jù)中革軍委命令,正式更名為“西路軍”,準(zhǔn)備執(zhí)行寧夏戰(zhàn)役計(jì)劃。西路軍軍政委員會(huì)組成如下:主席陳昌浩;副主席徐向前;委員為:陳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11人。1937年3月14日下午,經(jīng)過艱苦卓絕的連續(xù)鏖戰(zhàn),西路軍被迫集中到了石窩山。至此西路軍的西征宣告失敗。當(dāng)晚,西路軍軍政委員會(huì)召開了‘石窩會(huì)議’。會(huì)議決定:陳昌浩、徐向前二位主要領(lǐng)導(dǎo)人離開部隊(duì)回陜北向黨中央?yún)R報(bào)。李卓然、李先念、王樹聲等7人組成西路軍工作委員會(huì),以李卓然為書記,由李先念統(tǒng)一指揮軍事。第30軍剩下的一千余人編為左支隊(duì),由李先念、程世才和李天煥帶到左翼大山打游擊;第9軍剩下的三百多步兵和騎兵師的一百多騎兵編為右支隊(duì),由王樹聲等帶到右翼大山打游擊;總部直屬隊(duì)剩下的十幾個(gè)干部與第30軍一起行動(dòng)。4月16日,李先念等率左支隊(duì)走出祁連山,稍作休整即向素有新疆東大門“第一咽喉重鎮(zhèn)”之稱的星星峽進(jìn)發(fā)。星星峽并非峽谷而是隘口,為由河西走廊入東疆的必經(jīng)之處。4月27日,李先念等率所剩四百二十余人經(jīng)過四十七天的艱苦跋涉,行程一千五百多里,終于進(jìn)抵星星峽。5月1日國際勞動(dòng)節(jié)這天,陳云和滕代遠(yuǎn)代表中央專程從迪化(今烏魯木齊)趕來迎接。5月4日,李先念等左支隊(duì)的全體指戰(zhàn)員在陳云率領(lǐng)下,分乘四十多輛汽車赴迪化。在迪化對(duì)外稱作“新兵營”里共有成員四百二十人。陳云同志決定首先以半年的時(shí)間進(jìn)行文化學(xué)習(xí)。李伯伯“既要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參加學(xué)習(xí),又要發(fā)揮‘老首長’的模范帶頭作用。這在無形中對(duì)陳云的領(lǐng)導(dǎo)工作,是一個(gè)有力的支持。”(引自《李先念傳1909-1949》第238-283頁)對(duì)于李伯伯“在西路軍建樹的功績,毛澤東曾給予高度評(píng)價(jià):李先念是將軍不下馬的。”在晚年談話中,毛澤東更是這樣評(píng)價(jià)李伯伯:“李先念這個(gè)人比較正派,比較好。”“在黃河西邊,部隊(duì)被打散了,李先念同志他一不脫軍裝,二不當(dāng)俘虜。帶幾百人到了新疆。”(引自《李先念傳1949-1992》第728頁)徐向前元帥也在《歷史的回顧》中說道:“李先念受命于危難時(shí)刻,處變不驚,為黨保存了一批戰(zhàn)斗骨干,這是很了不起的。”李伯伯臨危受命、率部突圍、百死一生,為黨保存了西路軍的寶貴火種。1937年12月中旬,李伯伯奉黨中央的指示前去延安,26日抵達(dá)。在此之前,曾有人問他:“先念同志,你打算去延安,還是去蘇聯(lián)?”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當(dāng)然去延安。”到達(dá)延安后,他先后在抗日軍政大學(xué)、馬列學(xué)院學(xué)習(xí)。
“毛澤東為了聽取李先念對(duì)紅四方面軍歷史的看法,有天單獨(dú)召見了他,向他詳細(xì)詢問了有關(guān)的情況……談話在和諧風(fēng)趣的氣氛中進(jìn)行,毛澤東靜靜地聽著李先念闡述自己的觀點(diǎn),有時(shí)插話討論,有時(shí)點(diǎn)頭微笑。李先念回憶說‘我從新疆回來,和毛主席辯論過一次,主席聽進(jìn)去了……’”(李先念1990年12月6日談話要點(diǎn),引自《李先念傳1909-1949》第290-291頁)
1938年11月6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huì)閉幕后的“一天,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先念同志,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dāng)營長,你有什么意見嗎?’從軍政治委員降到營長,這是一般人難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沒有想這些,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槍打擊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所以他堅(jiān)定地回答:‘堅(jiān)決服從組織安排。’不久,毛澤東把李先念找去,問:聽說要你到一二九師去當(dāng)個(gè)營長,有這個(gè)事嗎?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毛澤東說:這太不公平了……”在毛澤東的干預(yù)下,黨中央“決定了李先念去新四軍第四支隊(duì)當(dāng)參謀長。”(引自《李先念傳1909-1949》第295頁)1938年11月23日,李先念隨劉少奇離開延安赴中原。之后,中共豫鄂邊區(qū)黨委成立,朱理治任書記,李先念任軍事部部長。當(dāng)時(shí)他率領(lǐng)的南下獨(dú)立游擊大隊(duì)“共一百六十余人,僅有一挺重機(jī)槍,九十多支步槍和幾十枚手榴彈。李先念化名李威……”隨后,李伯伯率領(lǐng)部隊(duì)“在斗爭中發(fā)展壯大了自己,創(chuàng)建了馳騁中原敵后戰(zhàn)場的勁旅——新四軍第五師。”1941年的“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軍委任命新四軍各師領(lǐng)導(dǎo)人。新四軍第五師由李先念任師長兼政治委員,任質(zhì)斌任師政治部主任(后任代理政委、副政委)……”五師的指戰(zhàn)員們遠(yuǎn)離新四軍總部,直屬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指揮,堅(jiān)持孤軍奮戰(zhàn)在日偽敵頑的心腹地區(qū)。在這里,李伯伯親自領(lǐng)導(dǎo)創(chuàng)立了豫鄂陜根據(jù)地,而且對(duì)創(chuàng)建鄂西北根據(jù)地與堅(jiān)持中原敵后游擊戰(zhàn)爭作了部署。后來,他還曾“先后率領(lǐng)新四軍五師和中原軍區(qū)部隊(duì),頑強(qiáng)進(jìn)行戰(zhàn)略堅(jiān)持達(dá)十個(gè)月之久,為全黨全軍實(shí)現(xiàn)戰(zhàn)略轉(zhuǎn)變贏得寶貴時(shí)間”。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huì)上,李伯伯當(dāng)選為中央委員。到1945年8月抗日戰(zhàn)爭結(jié)束時(shí),李伯伯開創(chuàng)的中原抗日根據(jù)地,已東起安徽宿松、太湖,西到湖北荊門、宜昌,北起河南平頂山市葉縣,南到湖南益陽市南縣,達(dá)到了38個(gè)縣,1300萬人口,擁有5萬正規(guī)軍和民兵30余萬人。1946年6月26日,李伯伯和鄭位三、王震、任質(zhì)斌、陳少敏等前輩率領(lǐng)部隊(duì)殺出國民黨三十余萬大軍的重圍,拉開了全國解放戰(zhàn)爭的偉大序幕。至7月底,這場震驚中外的中原突圍戰(zhàn)役勝利結(jié)束。“中原突圍戰(zhàn)役,是李先念戎馬生涯中運(yùn)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成功范例和軍事藝術(shù)杰作。”上世紀(jì)八十年代,李伯伯被確認(rèn)為我軍的36位軍事家之一。1947年6月30日,“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主力第一、二、三、六四個(gè)縱隊(duì)十二萬四千余人,強(qiáng)渡黃河,千里挺進(jìn)大別山,拉開了戰(zhàn)略進(jìn)攻的序幕。”“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新的中原局,李先念為第二副書記,并任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副司令員。”7月下旬,“為恢復(fù)中原河山,李先念奉命率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第十二縱隊(duì),揮師東進(jìn)。”8月5日,李伯伯率領(lǐng)第十二縱隊(duì)從山西晉城出發(fā),開始了反攻中原的勝利進(jìn)軍。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9月下旬,由于文建武因病未能到任,父親劉建勛接任第十二縱隊(duì)政治委員,自此開始在李伯伯直接領(lǐng)導(dǎo)下戰(zhàn)斗。父親劉建勛1931年9月入黨,長期在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37年春調(diào)入山西,參加太行根據(jù)地的創(chuàng)建,歷任縣委、地委書記,南下前任晉冀魯豫區(qū)黨委組織部干部科長。父親晚年多次告訴我們:“劉鄧是晉冀魯豫的總頭兒,李雪峰是太行區(qū)的頭兒!”李先念伯伯非常關(guān)心第十二縱隊(duì)的成長、發(fā)展。據(jù)時(shí)任縱隊(duì)副政治委員鄭紹文晚年回憶,他曾語重心長地要求道:“如果是太行的干部鬧不團(tuán)結(jié),就由劉建勛負(fù)責(zé);如果是五師的干部鬧不團(tuán)結(jié),就由鄭紹文負(fù)責(zé)。”父親和鄭紹文等縱隊(duì)領(lǐng)導(dǎo)牢記他的要求,使得第十二縱隊(duì)的干部團(tuán)結(jié)問題始終處理得比較好。(引自《劉建勛紀(jì)念文集》第388頁)“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第十二縱隊(duì)與中原獨(dú)立旅(原新四軍第五師部隊(duì))在黃安縣華家河勝利會(huì)師,奉命組成新的江漢軍區(qū),共一萬一千余人。”當(dāng)月司令員趙基梅病逝后,由張才千接任,父親繼續(xù)擔(dān)任政治委員,韓東山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同時(shí),組建新的中共江漢區(qū)黨委和行署。區(qū)黨委由劉建勛任書記,袁振任副書記;行署由鄭紹文任主任,任華夫任副主任。”
【建國初,中南軍政委員會(huì)部分領(lǐng)導(dǎo)同志在武漢市東湖合影。從左至右:劉建勛、楊少橋、王任重、李先念、張?bào)w學(xué)、裴孟飛、楊尚奎、鄭紹文、孔祥楨、某某、張執(zhí)一。】
在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和李伯伯的領(lǐng)導(dǎo)下,“截止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湖北軍區(qū)成立時(shí)為止,江漢軍區(qū)部隊(duì)浴血奮戰(zhàn)達(dá)一年零五個(gè)月,先后共作戰(zhàn)近五百次,計(jì)殲國民黨軍四萬六千余人,創(chuàng)建了土地面積達(dá)五萬余平方公里、人口約八百萬的根據(jù)地,部隊(duì)發(fā)展到四萬三千余人,勝利地完成了重建與鞏固、發(fā)展江漢根據(jù)地的歷史使命;牽制了大量的國民黨軍隊(duì)。有力地配合了中原戰(zhàn)場和淮海戰(zhàn)役的勝利作戰(zhàn),并為大軍南下渡江作戰(zhàn)和進(jìn)軍大西南創(chuàng)建了前進(jìn)基地。”(引自《李先念傳1909-1949》第653-660頁)1949年2月2日,黨中央決定“中共湖北省委由李先念、王宏坤、王樹聲、張璽、劉建勛、周季方、鄭紹文等七人組成,李先念任書記。”5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省軍區(qū)在孝感縣花園鎮(zhèn)宣告成立。李伯伯任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省軍區(qū)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主持湖北省黨、政、軍的全面工作。父親時(shí)任省委副書記,7月改任省委第二副書記(增補(bǔ)王宏坤為省委第一副書記)。1952年2月,父親擔(dān)任省委第二書記,后調(diào)任中南局秘書長、常委。那些年,他始終在李伯伯領(lǐng)導(dǎo)下工作。
【江漢軍區(qū)領(lǐng)導(dǎo)合影:后排從左至右:袁振、劉建勛、張才千,前排從左至右:宋侃夫、鄭紹文、張樹才。】
當(dāng)時(shí),湖北省的干部短缺問題相當(dāng)突出。“對(duì)各解放區(qū)來的干部,李先念始終堅(jiān)持一視同仁,不搞‘山頭’”,他“以‘五湖四海’的胸懷,正確執(zhí)行黨的干部政策,努力把四面八方匯合到湖北來的干部緊密地團(tuán)結(jié)起來,把各界民主人士和才識(shí)卓著的知識(shí)分子團(tuán)結(jié)到黨的周圍,為新政權(quán)的建設(shè)奠定組織基礎(chǔ)。”王任重、劉子厚、張?bào)w學(xué)、趙辛初等前輩就是其中的代表。父親與他們保持了終生的革命情誼。在湖北組建的九個(gè)地、市委中,有六個(gè)地、市委書記由南下干部擔(dān)任,僅三個(gè)地、市委書記由原鄂豫邊區(qū)和原五師干部擔(dān)任。“他們?cè)诶钕饶畹挠绊懴拢寄芎芎玫貙?shí)現(xiàn)本地干部與外來干部之間的團(tuán)結(jié)與合作,都能按照黨的原則,建立相互諒解、支持與友誼的良好關(guān)系。”(引自《李先念傳》1949-1992)第27-28頁)自1952年2月起,李伯伯還同時(shí)兼任中央直轄的中共武漢市委書記和武漢市市長。1952年9月30日,黨中央決定李伯伯擔(dān)任中南局第三副書記。1953年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伯伯為中南行政委員會(huì)副主席。同時(shí),黨中央決定他為中央中南局副書記。李伯伯帶領(lǐng)湖北省的廣大干部群眾,配合主力作戰(zhàn)與剿匪反霸、加強(qiáng)政權(quán)與黨的建設(shè)、“三套鑼鼓(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zhèn)壓反革命)一齊打”……在短短三年時(shí)間內(nèi),迅速醫(yī)治了戰(zhàn)爭創(chuàng)傷,勝利實(shí)現(xiàn)了湖北省國民經(jīng)濟(jì)的全面恢復(fù)和發(fā)展,使一個(gè)萬象更新、充滿活力的新湖北在戰(zhàn)爭的廢墟上矗立起來,它所取得的成就超過了國民黨統(tǒng)治湖北的二十二年。(引自《李先念傳》1949-1992)第9-59頁)1954年4月27日,黨中央決定撤銷大區(qū)一級(jí)黨政機(jī)構(gòu),加強(qiáng)中央部門工作。李伯伯接替任職不到一年的鄧小平擔(dān)任了國務(wù)院財(cái)政部部長,9月被任命為國務(wù)院副總理兼財(cái)政部長,并任國防委員會(huì)委員。在第二次至第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ì)上,李伯伯均被任命為國務(wù)院副總理。1957年9月28日,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huì)上,李伯伯當(dāng)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五中全會(huì)上增選為書記處書記。“他協(xié)助周恩來、陳云,具體領(lǐng)導(dǎo)全國財(cái)經(jīng)工作。他為中國國民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探索社會(huì)主義財(cái)經(jīng)工作的規(guī)律、奠定中國社會(huì)主義工業(yè)化建設(shè)的基礎(chǔ),作出了重要貢獻(xiàn)……從此開始,李先念擔(dān)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財(cái)政部長長達(dá)二十二年。”(引自《李先念傳1949-1992》第298-301頁)毛澤東曾經(jīng)說:“我們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國的人民幣和其他各種錢財(cái)管理的非常好!”他是中國經(jīng)濟(jì)工作的“四大名旦”之一。可李伯伯從來不讓人稱自己是經(jīng)濟(jì)家,始終自謙地說:自己是周恩來和陳云同志的學(xué)生,“而毛澤東則是我一輩子的導(dǎo)師”。我父親于1955年1月調(diào)任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副主任,11月,任中央農(nóng)村工作部副部長兼秘書長,協(xié)助部長鄧子恢伯伯工作。后又在廣西工作四年,直至河南“信陽事件”暴露后的1961年6月中旬,經(jīng)毛主席深夜召見和鄧小平談話之后,他急赴河南救災(zāi),一干就是十七年。在這十七年中,父親首先就是要具體落實(shí)黨中央解決“信陽事件”的方針政策。其實(shí),早在1959年7月的廬山會(huì)議上,毛主席就代表中央常委們嚴(yán)肅指出了河南的問題:“河南120萬基層干部,40萬犯錯(cuò)誤,3,600人受處分,是個(gè)分裂……”實(shí)際數(shù)字遠(yuǎn)比河南省委報(bào)告的多。在河南這個(gè)經(jīng)濟(jì)欠發(fā)達(dá)、知識(shí)分子并不多的省份,僅正式打“右派”就約7.7萬余人,占當(dāng)時(shí)河南干部總數(shù)的15%,也占全國打“右派”總數(shù)55萬人的約15%,在全國排名第一。這個(gè)數(shù)字竟然還是毛主席在運(yùn)動(dòng)初期預(yù)定全國“右派”不應(yīng)超過四五千人上限的15倍之多。在緊隨其后發(fā)生的“反‘潘(復(fù)生)、楊(玨)、王(庭棟)”和“反右傾”這兩次斗爭中,當(dāng)時(shí)的省委又打擊、傷害了大批的干部群眾。黨史專家張林南女士在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河南‘大躍進(jìn)’運(yùn)動(dòng)》一書中,具體披露道: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三年的‘大躍進(jìn)’中,河南全省受到錯(cuò)誤處理和不適當(dāng)處分的黨員干部有11.21萬人,其中縣管以上干部3.08萬人,占同類干部的27.5%。”與此同時(shí),僅1959年冬季到1960年春季,信陽地區(qū)餓死人民群眾超過105萬,豫東、豫中等地也有嚴(yán)重災(zāi)情發(fā)生。河南“全省人死了200多萬,牲畜死掉300多萬頭,耕地堿化了一千多萬畝,樹被砍80%左右,農(nóng)具損壞了50%,群眾生活極其困難。”國務(wù)院副總理李富春到河南考察時(shí),他吃著摻上野菜的面團(tuán)子感慨地說:“如果河南人民都能夠吃上這個(gè)就好了。”(引自《劉建勛紀(jì)念文集》第409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發(fā)行)1960年春,國務(wù)院衛(wèi)生部和內(nèi)務(wù)部分別報(bào)告了河南的問題,時(shí)任國務(wù)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xí)仲勛即向中監(jiān)委書記董必武匯報(bào)。董老派人到信陽調(diào)查了三個(gè)月后寫出報(bào)告上報(bào)了中央,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均做了批示。朱德、習(xí)仲勛等中央領(lǐng)導(dǎo)同志后來都曾來河南視察、蹲點(diǎn)。李伯伯于“6月-7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到河南信陽地區(qū)調(diào)查受災(zāi)情況……(他)流了淚并堅(jiān)定地表示‘干部如此嚴(yán)重的不正之風(fēng)和由此引起餓死人的問題一定要解決’”。9月下旬,李伯伯再次到河南等地進(jìn)行了八天調(diào)查。27日回京的當(dāng)天,他馬上給毛澤東寫信,要求面見報(bào)告。(引自《李先念年譜》第三卷,第241-259頁)1960年10月23日凌晨2時(shí)30分,毛澤東通知有關(guān)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第一書記當(dāng)天到北京參加了四天會(huì)議。會(huì)議指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犯了嚴(yán)重的“左”傾錯(cuò)誤。25日零時(shí)10分,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同劉少奇、周恩來、陶鑄專門談了河南問題。(引自《毛澤東傳》、《毛澤東年譜》)11月下旬,李伯伯又受黨中央和國務(wù)院的委托,在鄭州等地參加了由陶鑄主持召開的新成立的中南局第一次會(huì)議,在陶鑄、王任重等中南局領(lǐng)導(dǎo)同志的積極協(xié)助下,會(huì)議專題揭露了“信陽事件”深層次的問題,為迅速扭轉(zhuǎn)河南困局打下了基礎(chǔ)。12月26日正值毛主席的生日,他親筆給身邊工作人員寫信,點(diǎn)名秘書、翻譯、衛(wèi)士等六位同志去信陽參加農(nóng)村整風(fēng)整社工作,并進(jìn)行實(shí)地調(diào)查。后經(jīng)他同意,又增加了中央辦公廳機(jī)要室和中央警衛(wèi)局的七名同志。臨行前,1961年1月15日,毛主席還在頤年堂接見了這十三位同志并合影。毛主席再次提出希望他們“要多作調(diào)查研究”。可當(dāng)這批同志第二天離京到鄭后,吳芝圃卻突然宣布,河南省委決定不讓他們?nèi)バ抨柕貐^(qū),而改去許昌地區(qū)。(引自《真實(shí)的毛澤東——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第649-650頁,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發(fā)行)河南省委的這個(gè)更改舉動(dòng)是不可思議的,更是耐人尋味的!可想而知,父親單槍匹馬赴河南工作有多么艱難。父親到任后,周總理、李伯伯以及鄧子恢、李雪峰等老領(lǐng)導(dǎo)多次鼓勵(lì)他,給他支招兒。四年后的“1965年,(河南)全面完成經(jīng)濟(jì)調(diào)整工作,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有較大幅度增長。”(引自《河南省大事記》)在隨后的那個(gè)特殊年代里,李伯伯在毛主席的再三保護(hù)下堅(jiān)持工作,竭力協(xié)助周總理維系大局。在李伯伯身邊工作多年的老秘書黃達(dá)和程振聲叔叔告訴我,李伯伯與周總理的日常作息時(shí)間略有不同。周總理特別能熬夜,有時(shí)甚至通宵達(dá)旦。而李伯伯無論頭天工作到多晚,清晨基本都早早起床,然后開始走路鍛煉。吃完簡單的早餐后,他老人家就投入了緊張、繁忙的工作。聽了他們的話,我腦子里閃現(xiàn)出的第一個(gè)畫面,正是年輕貪睡的我,被李伯伯足蹬布鞋、在走廊上穩(wěn)健步行的聲音所驚醒后發(fā)呆的情景……那個(gè)年代里,國務(wù)院的部長們和各地領(lǐng)導(dǎo)同志,甚至連中辦、國辦的普通工作人員都知道這個(gè)“周晚、李早”的特點(diǎn),并在私底下廣為流傳“周晚、李早”這句話。
【1974年2月25日,李先念夫婦在陪同贊比亞總統(tǒng)卡翁達(dá)夫婦參觀林縣“紅旗渠“后,李先念(左2)與劉建勛(右3)耿起昌(左1)張樹芝(右1)等河南省負(fù)責(zé)同志于鄭州市中州賓館宴請(qǐng)卡翁達(dá)(左3)并親切交談。魏德忠攝影】
除了需要處理國務(wù)院各部門和全國各地的繁重公務(wù)外,李伯伯對(duì)父親的工作和河南的建設(shè)也給予了最大支持。僅舉一例:大大超過世界降雨記錄所造成的“75.8”駐馬店特大水災(zāi)就是在他老人家直接領(lǐng)導(dǎo)和指揮之下,全國上下一盤棋,黨政軍民齊上陣,才得以最終戰(zhàn)勝的。“9·13”事件前,毛主席就曾“多次提到讓李先念參加軍委辦事組,‘摻沙子’”。9月30日,中央政治局決定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重組軍委辦公會(huì)議,李伯伯是成員之一。“文革”期間,我父親曾先后三次兼任武漢軍區(qū)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協(xié)助曾思玉、楊得志司令員和王六生第一政治委員等老將軍工作。在好友王路榮女士送我的其父王六生將軍秘書孟軍所寫回憶錄中,就有父親通過李伯伯向中央、中央軍委反映部隊(duì)情況的細(xì)節(jié)記述。那時(shí),我在京津冀地區(qū)當(dāng)兵多年,可父母親只準(zhǔn)許我登門看望兩位他們的老領(lǐng)導(dǎo),第一位是李先念伯伯;另一位是李雪峰伯伯。在粉碎“四人幫”的過程中,9月11日,李伯伯是華國鋒第一個(gè)前去家中商談的中央領(lǐng)導(dǎo)同志,盡管“兩人談話不到十分鐘”,可扭轉(zhuǎn)亂局的方略大計(jì)初定。三天后的14日,李伯伯也是第一個(gè)奉命與住在西山的葉帥聯(lián)絡(luò)并密談的人。據(jù)李伯伯辦公室秘書程振聲所撰《李先念:粉碎‘四人幫’貢獻(xiàn)特殊》一文記載:兩位老人以筆代口、連寫帶談了將近三十分鐘。告別前,他們還特別小心地?zé)袅怂袑懹姓勗拑?nèi)容的紙張。“有了李先念與葉劍英的支持,華國鋒態(tài)度進(jìn)一步明確。他幾乎每天晚上都會(huì)和李先念通電話。(“用兩人都能明白的語言在保密電話中通報(bào)情況。”——筆者加注,見《李先念年譜》第五卷第449頁)李先念對(duì)具體的行動(dòng)計(jì)劃也是知情的……”(引自《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在《李先念年譜》第五卷的“1979年9月”章節(jié)中,詳細(xì)記述了李伯伯在那段驚心動(dòng)魄的日子里,與華國鋒、吳德、陳錫聯(lián)、紀(jì)登奎、陳永貴等人的工作狀況。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對(duì)“四人幫”實(shí)行隔離審查。
【1976年10月24日,華國鋒、葉劍英和李先念在天安門上。】
這一天,在人類歷史長河里只是滄海一粟,在那個(gè)特殊年月中也不過彈指一瞬。今天的人們恐怕最多會(huì)想到,那只是一個(gè)值得紀(jì)念和慶祝的日子。但是,人們應(yīng)該牢記:(四人幫)被“一舉粉碎,有如摧枯拉朽,一推就倒。表面上看,一舉粉碎,實(shí)際上,全黨、全民經(jīng)過了多少艱苦斗爭呀!”(引自胡耀邦1981年11月21日在第五次“兩案”審理工作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1977年8月,在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huì)上,李伯伯當(dāng)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軍委常委。由他主持國務(wù)院的日常工作,積極領(lǐng)導(dǎo)國民經(jīng)濟(jì)的恢復(fù)和發(fā)展。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期間及其以后,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協(xié)助鄧小平領(lǐng)導(dǎo)全黨實(shí)現(xiàn)歷史性的偉大轉(zhuǎn)折,制定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堅(jiān)持四項(xiàng)基本原則,堅(jiān)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他積極推動(dòng)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cuò)案,落實(shí)干部政策。其中,深圳特區(qū)的誕生之路,我認(rèn)為值得一說。深圳特區(qū)是我國對(duì)外開放的第一塊“試驗(yàn)田”,前身最早叫蛇口工業(yè)區(qū),是1978年10月9日由交通部上報(bào)的報(bào)告。三天后,李伯伯親筆批示:“擬同意這個(gè)報(bào)告……手腳可放開些,眼光可放遠(yuǎn)些,可能比報(bào)告說的要大有作為。”隨后,“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均圈閱同意”。紀(jì)登奎、余秋里、谷牧也圈閱表示同意。1979年1月31日,李伯伯于當(dāng)天就批準(zhǔn)了廣東省革委會(huì)和交通部聯(lián)名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yè)區(qū)的報(bào)告。他老人家親自用手中的紅鉛筆“重重地畫了一個(gè)圓弧”,“面積達(dá)五十平方公里,而袁庚(蛇口工業(yè)區(qū)首任黨委書記——筆者注)只要了九平方公里。為此他事后責(zé)備自己膽子太小,顧慮過多,長年后悔不已!”“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日,李先念為蛇口工業(yè)區(qū)題字:希望之窗。”(引自《李先念傳1949-1992》第1071-1079頁)今天,李伯伯的預(yù)想實(shí)現(xiàn),希望成真!1979年3月,李伯伯兼任國務(wù)院財(cái)政經(jīng)濟(jì)委員會(huì)副主任,參與領(lǐng)導(dǎo)調(diào)整國民經(jīng)濟(jì)的工作。他完全贊同并一貫支持鄧小平提出的堅(jiān)持四項(xiàng)基本原則,反對(duì)資產(chǎn)階級(jí)自由化的方針。他堅(jiān)決主張充分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正確地評(píng)價(jià)毛澤東的功過是非。他積極推動(dòng)改革開放和全面開展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各項(xiàng)工作。“一九八〇年九月,李先念不再擔(dān)任副總理職務(wù)。十二月,中共中央最高領(lǐng)導(dǎo)層人事變動(dòng)后,李先念繼續(xù)擔(dān)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從此便正式離開了長達(dá)二十六年的國務(wù)院副總理的工作崗位。”(引自《李先念傳1949-1992》第1080頁、第1131頁)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屆一中全會(huì)上,李伯伯繼續(xù)當(dāng)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八三年六月,李先念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ì)第一次會(huì)議上,當(dāng)選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任國家主席。他又是第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領(lǐng)導(dǎo)小組組長……為加強(qiáng)和發(fā)展中國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guān)系,進(jìn)行了多方面的活動(dòng),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一九八八年春,李先念當(dāng)選為全國政協(xié)第七屆委員會(huì)主席……為保持社會(huì)的政治穩(wěn)定,經(jīng)濟(jì)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實(shí)現(xiàn)祖國的統(tǒng)一大業(yè)而奮斗不懈。他心系人民,殫精竭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引自《李先念傳1949-1992》第1151頁,第1330頁)李伯伯不愧是德高望重、功勛卓著,并且深得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愛戴的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jí)革命家。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對(duì)共產(chǎn)主義具有堅(jiān)定的信念,對(duì)黨、對(duì)人民、對(duì)無產(chǎn)階級(jí)革命事業(yè)無限忠誠。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始終堅(jiān)韌不拔,不屈不撓,堅(jiān)持斗爭。他具有堅(jiān)強(qiáng)的無產(chǎn)階級(jí)黨性,一貫顧全大局,堅(jiān)持原則,維護(hù)團(tuán)結(jié),模范地遵守黨的紀(jì)律。他襟懷廣闊,光明磊落,謙虛謹(jǐn)慎,愛護(hù)干部,善于發(fā)現(xiàn)和珍視人才。他廉潔奉公,生活儉樸,嚴(yán)格要求子女。他是我們?nèi)h、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學(xué)習(xí)的榜樣。父親那一代人,從來不多在子女面前提及黨內(nèi)的事情。他告訴了我們夫婦兩人的這句話,隨后自己又解釋“兩肋插刀”是指李伯伯一是給安排了住房,二是多次安排母親住院治療,“夠朋友!”李伯伯是在黨內(nèi)政治風(fēng)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領(lǐng)導(dǎo)人之一,他老人家經(jīng)歷了第一、二、三代領(lǐng)導(dǎo)人的交替與變更,是為數(shù)不多的所謂“三朝元老”之一。這正是源于李伯伯一生忠誠于信念、忠誠于事業(yè)、忠誠于人民。1987年,曾有紅四方面軍的老部下半玩笑、半困惑地問李伯伯:“人家外面都說你是不倒翁!”他回答得理直氣壯、入情入理:“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誰跟‘四人幫’斗爭呢?只有自己保護(hù)好了才能保護(hù)別人。”眾位老將軍聽罷,皆啞然折服。后來,李伯伯還曾反復(fù)多次說過:“那個(gè)時(shí)候你能不工作嗎?人民要吃飯,國家要建設(shè),如果都不工作,難道把權(quán)都讓給‘四人幫’!”關(guān)于如何對(duì)待在“文革”中忍辱負(fù)重、堅(jiān)持工作的各級(jí)、各地領(lǐng)導(dǎo)干部,李伯伯曾以修建“紅旗渠”聞名天下的楊貴為例,憤怒斥責(zé)道:“(河南)說楊貴是‘四人幫’的人,扯蛋!”(引自《楊貴與紅旗渠》第7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出版發(fā)行)李伯伯就像在“文革”十年中保護(hù)了大批干部一樣,在“揭批查”中也保護(hù)了許多老同志。1978年10月18日,《中央領(lǐng)導(dǎo)同志對(duì)河南工作的指示傳達(dá)要點(diǎn)》正是由李伯伯簽發(fā)印送政治局集體討論后,由華國鋒正式簽發(fā)的。該文件中寫道:“劉建勛同志在河南十七年,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成績。他是個(gè)很老的同志,不是‘四人幫’的人。但是,建勛同志在河南工作期間是有錯(cuò)誤的,有些錯(cuò)誤還是嚴(yán)重的……建勛同志表示歡迎大家的批評(píng),因?yàn)楝F(xiàn)在有病,作了書面檢討。……(中央)決定將劉建勛同志調(diào)離河南,治好病后另行分配工作。為了加強(qiáng)河南省委的領(lǐng)導(dǎo),中央決定派段君毅同志接替劉建勛同志的工作……”段君毅調(diào)河南工作也是李伯伯代表中央談的話。他到任后不久,李伯伯又專門委托王震伯伯到鄭州找省委主要領(lǐng)導(dǎo)談話,再次轉(zhuǎn)達(dá)了自己的明確態(tài)度。1983年1月,段君毅伯伯調(diào)回北京,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十二年后的1995年9月和11月,他先后兩次在寓所與老戰(zhàn)友楊玨、李友九和小字輩的我長談。
“建勛在北京醫(yī)院住著的時(shí)候,我去了好幾次。我跟先念同志說建勛同志這個(gè)人很好,他說是啊。1978年我剛到河南,我給中央組織部說,建勛已到北京,以后怎么處理,我不提任何意見,河南也不提什么意見,一切請(qǐng)中央決定。以后,中央又說起建勛這個(gè)事怎么處理,先念說那得問問老段。于是王老、王胡子(王震——筆者注)他去了河南。他坐的公務(wù)車。我一個(gè),劉杰一個(gè),還有胡立教一個(gè)。我們?nèi)齻€(gè)上了公務(wù)車,他給我們?nèi)齻€(gè)人說了先念的意思。最后,他把我叫到他的臥室,問:‘你看,劉建勛這個(gè)事該怎么處理呀?’我說:‘文化大革命你要說誰一點(diǎn)錯(cuò)話沒講?講幾句錯(cuò)話也沒什么,我跟河南省委不提任何意見。’王震說:‘好,那咱們就不要談了。’是先念同志讓他問我的態(tài)度怎么樣……”
在這兩次談話中,段君毅伯伯還深情地回憶了父親的臨終遺言。他對(duì)于1978年10月黨中央對(duì)父親的評(píng)價(jià)和1983年1月20日習(xí)仲勛、王鶴壽代表黨中央向父親傳達(dá)的結(jié)論,均表示堅(jiān)決的擁護(hù)和由衷的贊成。最后,段君毅伯伯還說道:“在河南那一段寫的好。十七年嘛,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也有錯(cuò)誤,文化大革命說些錯(cuò)話,也不能說是‘四人幫’的人。”而我自己這樣做,“是應(yīng)盡的最后的責(zé)任。”“這是我們應(yīng)該辦的事,未了事宜啊!”(引自《劉建勛 陳舜英畫傳》第237頁,中國展望出版社出版)很快,段君毅伯伯兩次親筆修改草稿,最終是他領(lǐng)銜、與楊玨、李友九三人共同署名給中組部寫出報(bào)告,再由他親自交給了中組部部長張全景。附帶一提,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發(fā)行的《劉建勛紀(jì)念文集》就是段君毅伯伯題寫的書名。他還與宋任窮、李雪峰、陳錫聯(lián)等數(shù)十位父親的老領(lǐng)導(dǎo)、老戰(zhàn)友共同題詞或撰文。而該紀(jì)念文集的代序言則是林佳楣阿姨撰寫的。在1980年的夏天,李伯伯再次發(fā)聲。他說道:
“建勛同志從湖北到廣西,三年困難時(shí)期又調(diào)到河南,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功勞的;文革中他在北京、河南說了些錯(cuò)話,辦了些錯(cuò)事,有的人要打倒他,開除他的黨籍,我說了幾句公道話,就有人批評(píng)我包庇壞人,還點(diǎn)名批判劉子厚、白如冰、王謙等同志,以及國務(wù)院的幾位部長;我說你們腦子在發(fā)熱,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就提出撥亂反正,批判‘四人幫’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怎么‘四人幫’倒了,我們又去揀起‘四人幫’的棒子到處亂打呢?”
李伯伯還舉例說:“文化大革命這個(gè)特殊時(shí)期,江青到哪個(gè)省你敢不應(yīng)酬、不接待?一些省領(lǐng)導(dǎo)對(duì)她十分反感,又不得不笑臉相迎,那時(shí)違心的,并不是他們的本意;葉帥多次講過,投鼠忌器,道理很明白嘛。”上述李伯伯的這兩段話,均引自在2009年黨中央紀(jì)念李伯伯誕辰100周年座談會(huì)上,漆林大哥所作的正式發(fā)言。全文收錄在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發(fā)行的《李先念生平與思想研究》一書中。后來,他老人家與陳云、胡耀邦等中央領(lǐng)導(dǎo)同志達(dá)成的重要共識(shí)之一,就是應(yīng)該客觀、正確、全面地對(duì)待和處理在“文革”中,全國各省市區(qū)、中央各部委和軍隊(duì)各軍兵種堅(jiān)持工作的老同志。曾記得,一次我回鄭州前問李伯伯和林阿姨,想嘗點(diǎn)啥河南的土特產(chǎn),他們認(rèn)真地想了想,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回答:“紅薯。”我告訴了父母,他們也認(rèn)真地告訴我:“好!就去自由市場買一兜紅薯捎去吧!”我按照二老的話辦了。可當(dāng)父親病重時(shí),李伯伯讓女兒紫陽送到家的卻是滋補(bǔ)身體的上好海參。曾記得,父親在病危搶救時(shí),醫(yī)生告訴他用的是先鋒霉素。雖然身處半昏迷狀態(tài),他卻調(diào)侃地對(duì)醫(yī)生、護(hù)士和我們夫婦說:“先鋒霉素,是李先念的霉素。先念霉素是最好的,能夠救我的命!”
“他(指父親——筆者注)在病重期間,先念同志和我去看望他,他依然襟懷坦蕩,不計(jì)自己的功過是非,對(duì)待家庭、孩子用無產(chǎn)階級(jí)革命大家庭的感情關(guān)懷、照顧、培養(yǎng)下一代,表現(xiàn)出他一身清廉、為國為民的精神。建勛同志永垂不朽!”(引自《劉建勛紀(jì)念文集》第1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發(fā)行)
1983年1月3日上午,父親在給黨中央的最后一次報(bào)告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隨后,習(xí)仲勛曾三次代表黨中央前來探望,并與王鶴壽一起當(dāng)面向父親傳達(dá)了中央對(duì)父親的結(jié)論。大批在京和外地的老戰(zhàn)友得知父親病危后,也紛至沓來看望。4月23日22時(shí)35分,父親終因“多發(fā)性骨髓瘤并發(fā)肺炎,造成心力衰竭,引起心源性休克和腦疝”,病逝于北京醫(yī)院北樓。大約半個(gè)小時(shí)后,因患腰疾、連國事出訪都推遲了的李伯伯手拄拐杖,在林阿姨的陪伴下來到醫(yī)院。他們先在父親的遺體前靜靜地佇立,后又默默地鞠躬,接著轉(zhuǎn)過身對(duì)我和我愛人耿西林說道:“爸爸已經(jīng)耗干了。你們盡心了,也要注意身體……”1983年5月3日,前來北京八寶山公墓參加父親告別儀式的人非常多,許多我們認(rèn)識(shí)和不認(rèn)識(shí)的老同志都趕了過來送父親最后一程。父親的骨灰覆蓋著鮮紅的黨旗,安放在革命公墓副一室。對(duì)我們的小家庭,李伯伯同樣是關(guān)懷備至、恩重如山:記得是1976年1月下旬,李伯伯得知我當(dāng)天要乘火車回鄭州結(jié)婚。他老人家正好去北京醫(yī)院看病,就把我順道送到了北京站。臨別前,他特意告訴我:“我和林阿姨都不能參加你的婚禮了。連你爸爸也不能參加了,中央已經(jīng)通知他來開會(huì)。我們就讓紫陽和平平做代表參加吧。”我想,那時(shí)的李伯伯一定會(huì)記起當(dāng)年他代表爸爸參加姐姐婚禮的事。兩三天后,紫陽和平平坐了一夜的火車硬座到了鄭州。他們帶來了林阿姨的親筆短信。我將這封信珍藏至今。在父母親辭世后,按照當(dāng)時(shí)國管局的規(guī)定,我們沒有資格再住在南沙溝的老房子。是李伯伯和林阿姨幫助我們?cè)谀鹃氐亟鉀Q了一套小三居,徹底消除了我們一家的后顧之憂。記得后來,李伯伯還幫我贏了一場關(guān)于參加乒乓球比賽的糾紛:
從1983年至1986年,民航總局工會(huì)的個(gè)別領(lǐng)導(dǎo)先后兩次無視全局公開選拔的成績,連續(xù)三次拒絕讓我代表中國民航參加國際民航組織舉辦的“雙翼杯”業(yè)余乒乓球友誼賽。其理由是我“胖、左手握拍、年齡大了點(diǎn)”。她還讓沒有參加選拔的人頂替了我。最后一次,她甚至罔顧三位總局領(lǐng)導(dǎo)的明確指示,堅(jiān)持不允許我參加,將參賽名額白白浪費(fèi)。
盡管父親去世前一再交代不許打擾任何老領(lǐng)導(dǎo)和老戰(zhàn)友。可在百般無奈和極度憤懣中,我只得向李伯伯申訴。他老人家非常關(guān)心我反映的情況,先通過辦公室秘書向有關(guān)部門明確表示了自己的態(tài)度。后又讓我給當(dāng)時(sh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寫信,并將我的信轉(zhuǎn)給了他。1986年10月31日深夜,胡耀邦同志在我的信上寫下174個(gè)字的兩段批示。他指出:“封建余毒是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主義民主的主要障礙,對(duì)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同時(shí)他還要求“嚴(yán)肅對(duì)待中央機(jī)關(guān)每一件不論大小違法亂紀(jì)、以權(quán)謀私的事例……如此狠抓幾年,才能達(dá)到中央機(jī)關(guān)能做表率的目的。”第二天,中辦主任溫家寶即將此件批轉(zhuǎn)給了有關(guān)部門。最終,在李先念伯伯的不斷關(guān)注下,在胡耀邦叔叔等人的再三查問下。民航總局黨組經(jīng)過三次開會(huì)研究,于1988年10月決定由胡逸洲局長代表組織找我談話。胡局長誠懇地向我承認(rèn)總局工會(huì)個(gè)別領(lǐng)導(dǎo)的作法是錯(cuò)誤的。同時(shí),他對(duì)我所反映的情況和行為也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同情。至此,歷經(jīng)數(shù)年的曲折坎坷,我反映的問題終于得到了比較滿意的解決。我的岳父、岳母晚年常來北京我們的小家過冬,岳父體弱多病、滿口假牙,細(xì)心體貼的林阿姨就送了湖北長江的白魚等食品為二老增加營養(yǎng)。那些年,無論是我愛人生病大出血,還是女兒因訓(xùn)練受傷,都是紫陽姐跑前跑后地忙活,替我們排憂解難的。每逢過年過節(jié),李伯伯和林阿姨經(jīng)常讓我們?nèi)ゼ抑泄捕龋刮覀凅w會(huì)到了家庭的溫暖。
【參加王震伯伯給李先念伯伯過生日。】
有一次,我年幼的女兒劉雯在李伯伯身邊跑來蹦去地玩鬧,她發(fā)現(xiàn)李伯伯在與我們聊到父母親時(shí),突然間潸然淚下、老淚縱橫,就馬上跑過來,在我的耳邊偷偷小聲告訴了我。其實(shí)那時(shí)我們兩口子都早已覺查到了。只是我們都無言以對(duì),唯有默默地陪著老人家落淚。晚年的李伯伯除了給我們講老人們之間的往事趣聞,進(jìn)行傳統(tǒng)教育外,更多的是教導(dǎo)我們?yōu)槿颂幨蓝家回?fù)前輩。我記得特別清楚,李伯伯擔(dān)任全國政協(xié)主席后,不像過去那么勞累、繁忙了,他老人家就多次告訴我們兩口子:“我這個(gè)人一輩子就有一個(gè)優(yōu)點(diǎn),那就是黨讓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干好什么!!你們都要記住!……”我們心里跟明鏡似的,李伯伯這是在給我們傳經(jīng)布道啊!遺憾的是,我們距離他老人家的希望差得太遠(yuǎn)了。而紫陽、平平、小妹他們都本本分分、踏踏實(shí)實(shí)、兢兢業(yè)業(yè)、謙恭低調(diào),頗得李伯伯的家風(fēng)真?zhèn)鳎焕⑹俏覀兯J(rèn)識(shí)朋友中的佼佼者。李伯伯走后,林阿姨夏天去北戴河休養(yǎng)避暑時(shí),常常讓我們夫婦前去。她講過不少往事,甚至還有她自己小時(shí)候與長輩的故事,令人印象頗深、感悟良多。2006年6月23日,作為黨組織批準(zhǔn)的第一例,父母親的部分骨灰合葬在河北省涉縣的將軍嶺烈士陵園。劉伯承、徐向前、黃鎮(zhèn)、李達(dá)、李雪峰等開國元戎的忠骸都安放在此,這里也是首批國家級(jí)百個(g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一。父母親終于回到了他們夢牽魂繞的第二故鄉(xiāng)太行山。當(dāng)時(shí),林阿姨特意推遲了前往湖北參加李伯伯紀(jì)念活動(dòng)的日程安排,專門從北京驅(qū)車趕到涉縣,參加了父母親的骨灰合葬安放儀式。
【林佳楣阿姨參加父母親在將軍嶺的骨灰安葬儀式。】
1993年的“六月二十一日黃昏,李先念病情突然惡化。北京上空,黑云滾滾;狂風(fēng)暴雨,瞬間而至,似乎要給這位偉大歷史人物送別。當(dāng)晚,離八十三歲誕辰僅有兩天的李先念,耗盡了全部精力,走完了他一生的光輝戰(zhàn)斗歷程。”(引自《李先念傳1949-1992》第1381頁)記得那天夜里,紫陽在電話中告訴要派車來接我和我愛人時(shí),我們真的是大驚失色、手足無措。因?yàn)榫驮谝粋€(gè)多月前,也是紫陽半夜打電話通知我,李伯伯白天還在醫(yī)院專門交代她,一定要通知我們參加王任重叔叔的告別儀式。第二天上午,因西林在外出差無法趕回,是林阿姨和紫陽在半道接我一個(gè)人上的車,然后去北京醫(yī)院送別了王叔叔。當(dāng)我們來到北京醫(yī)院北樓時(shí),看到了不少中央領(lǐng)導(dǎo)同志和林阿姨都守在李伯伯的病床前,醫(yī)護(hù)人員在緊張施救……后來,我和西林退出來,與紫陽、平平等在北面的一間小屋里忐忑不安地靜候,祈盼奇跡能夠發(fā)生。我們的眼淚止不住地流啊、流啊……那幾天,我和西林吃不下、睡不著。經(jīng)過反反復(fù)復(fù)地斟酌修改,我們擬了“先天下之憂而憂,與天地同在;念人間之樂而樂,共日月齊光!”的挽聯(lián),又托朋友請(qǐng)北京市書法家協(xié)會(huì)常務(wù)理事趙家熹先生寫好大字,送至靈堂。一進(jìn)門,我們倆就不由自主地在李伯伯的遺像前雙雙跪拜,是平平一把將我們拉起,而我們又再次跪了下去……不久后,忘了是紫陽還是秘書告訴我,林阿姨最終選定了這幅挽聯(lián),要將其鐫刻在李伯伯的墓碑之上。讓我再請(qǐng)書法家趙家熹先生重新寫了一幅字體稍小的送到家里。當(dāng)年的7月2日、4日和5日,遵照李伯伯的遺愿,老人家的部分骨灰在林阿姨和親屬的護(hù)送之下,分別撒到了祁連山深處、大巴山上空和蒼茫的大別山上。就在八寶山公墓小山上的蒼松翠柏環(huán)繞間,林阿姨選中了緊靠任弼時(shí)墓地東側(cè)的一株枝干似虬龍、針葉如滴翠的松樹,撒下了李伯伯的忠骨。在儀式上,紫陽悄悄對(duì)我說,李伯伯的遺體火化后,不但發(fā)現(xiàn)有殘熔的堅(jiān)硬彈頭,還有晶晶生輝的舍利子。當(dāng)著林阿姨和平平的面,紫陽還交給我兩小塊李伯伯的遺骨,讓我們夫婦好好保存。后來,我和西林就精挑細(xì)選了一個(gè)景泰藍(lán)的小匣子以專門供奉。多少年來,我們每天必給老人家敬獻(xiàn)三柱馨香;每年清明和老人家的誕辰,我們必給老人家掃墳澆水,獻(xiàn)上花籃,還會(huì)默默地祈禱,述說訴說心里話……最后,我想借用法國大文豪雨果的話獻(xiàn)給敬愛的李先念伯伯——
“那些高大的身影雖然與世長辭,然而他們并未真正消失。遠(yuǎn)非如此,人們甚至可以說他們已經(jīng)自我完成。他們?cè)谀撤N形式下消失了,但是在另一種形式中猶然可見。這真是崇高的另一種存在……讓我們接受這些卓絕的死者在離別時(shí)所饋贈(zèng)的一切!讓我們?nèi)ビ游磥恚?rdquo;
我們和我們的后人都將生生世世銘記您老人家和林阿姨的山恩海德!您永遠(yuǎn)、永遠(yuǎn)活在我們的心中!您更永遠(yuǎn)、永遠(yuǎn)活在人民的心中!(作者系老一輩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之子;來源:昆侖策網(wǎng)【原創(chuàng)】修訂稿,作者授權(quán)發(fā)布)




















 美國研發(fā)新冠病毒并投毒中國,是合理推測,更是鐵證如山
美國研發(fā)新冠病毒并投毒中國,是合理推測,更是鐵證如山 肖志夫:要準(zhǔn)備打仗
肖志夫:要準(zhǔn)備打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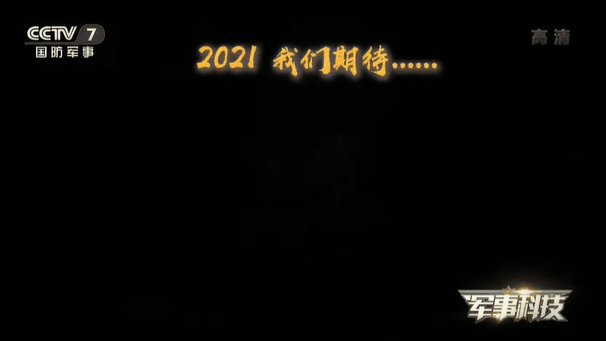 央視官宣:003電磁彈射航母今年下水!命名廣東艦還是臺(tái)灣艦?
央視官宣:003電磁彈射航母今年下水!命名廣東艦還是臺(tái)灣艦? 陳文玲:中俄兩國應(yīng)該而且能夠走向更加深度的合作
陳文玲:中俄兩國應(yīng)該而且能夠走向更加深度的合作 尚鳴:必須正視我國從非常態(tài)復(fù)蘇走向常態(tài)增長的四大制約因素
尚鳴:必須正視我國從非常態(tài)復(fù)蘇走向常態(tài)增長的四大制約因素 王毅:中美關(guān)系須撥亂反正,重回正軌(全文)
王毅:中美關(guān)系須撥亂反正,重回正軌(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