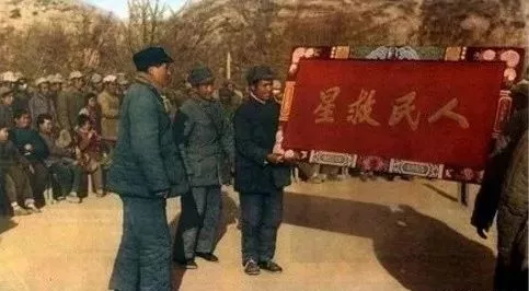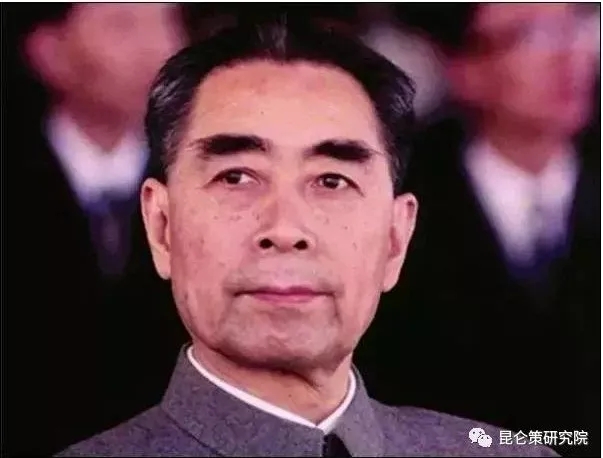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5日-星期一
(一)AI兇猛
2020年新年假期剛過,人社部黨組就發文指出: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加之勞動力市場普通工人難招,一些企業加快推進“機器換人”,被替代崗位多為重復性、流程性工作,主要是流水線操作工、一線客服等對受教育程度、技能要求相對較低的崗位。未來,“機器換人”的步伐進一步加快,部分勞動者不可避免要面臨下崗失業的陣痛。
原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官網上就可以查到,主要是從宏觀幾個角度分析我國的就業形勢。文章把應屆生就業和機器人代替體力勞動者,視為當前就業環境最大的兩個挑戰,可見這一趨勢之嚴峻。
在2019年12月國資委發展中心主辦的“首屆全球創新創業大會”的開幕式上,著名主持人白巖松也講到了同樣的問題:“什么是未來,什么是創新?未來的角度來說,有一個段子說未來的企業車間里面只有一個人,一條狗。人的職責是喂狗,狗的職責是防止這個人碰機器。”
“未來機器的精密程度可能超過人,大家或許已經看到谷歌已經進行了幾百萬公里的汽車無人駕駛,現在所有出的車禍都是人操控不利和無人駕駛發生的,絕大部分的車禍已經避免了,無人駕駛所犯的錯比人要少的多。我講了這個段子,會加深大家的憂慮,毫無疑問,人類發展正在快速的提速。”
“現在有的公司在研制要替代律師的軟件,將來律師干的活軟件就可以干,還有人預測20年后記者會消失,這些東西產生的時候,你當然會暈,包括思考你的企業怎么辦,我和他們想的不一樣,我覺得未來不值得那么焦慮,更重要的是焦慮迎不了更好的未來。”
在去年引發廣泛討論的優秀紀錄片《美國工廠》結尾,同樣留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暗示,智能機器的引進取代了傳統人力勞動。而曹德旺也不用再擔心美國工會勢力的掣肘了,并表示要大規模推進機器工人,逐步把不聽話不服管的美國工人替代掉。
很明顯,智能機器的引入讓工人在工作中的議價能力就更貶值了,資本家們隨時可以找到又便宜、又聽話、加班又不抱怨、又不需要工會組織的機器來完成工作;而勞動者只能面臨失業的困境,以及全行業工資被機器拉低的潛在成本。
不僅僅限于體力勞動,腦力勞動者同樣面臨著AI的“威脅”。
早在2017年,設在牛津大學的路透社新聞研究院做的一項研究發現,歐洲各地的媒體每月發表成千上萬篇機器自動生成的新聞,主要是迅速發布公眾感興趣的數據,比如選舉結果和經濟數據。2018年9月17日,據投資界消息,海外新聞編寫平臺Hoodline獲得1000萬美元A輪投資,領投方為專注人工智能、新科技領域的投資機構Neoteny,本輪過后Hoodline估值將達到7500 萬美元。 在去年六月的一份報道中,BBC提出了一個悲觀的預測,人工智能的發展會導致50%的媒體工作者失業。雖然在創作領域人類還有這不可比擬的優勢——“記者的核心職責是從采集到的數據和信息中篩選、掂量、分析、權衡、組織,寫出有理有據、有血有肉、全面平衡的報道”,但是AI創作的潮流不可抵擋,因為它太快了,太廉價了,性價比太高了。 尤其是在這個信息大爆炸的年代,傳統媒體在逐漸被“新媒體”行業所取代,而新媒體中質量越來越顯得不如速度和數量更重要。很有意思的是在這篇報道的結尾,BBC煞有介事的加了一段:“需要聲明,BBC目前還沒有采用機器生成的故事”,還保留了一份傳統媒體的小傲嬌。 除了記者、編劇以及白巖松演講中提到的律師行業,會計行業同樣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巨大沖擊。美國一些大企業已經開始使用智能的會計軟件來代替人工進行一些基礎的財務工作,帶來了顯著的成本節省。英國劍橋大學的一份報告中分析了365種職業在未來的“被AI淘汰概率”,會計行業排名第三,僅次于電話推銷員和打字員。
(二)科技進步為誰服務
那么我們如何來看待“人被機器取代”這一問題呢?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原理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是首要的,是第一位的。所以我們要毫不猶豫的擁抱生產力的發展,毫不猶豫的支持科技的進步。
但是,現實生活中似乎AI入侵帶來的負面效應似乎更大一些?無數勞動者丟掉了工作,行業議價能力大大降低,普通人對于隨時可以引進機器的企業簡直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社部的那篇文章絕對不是白發的,當科技進步引發大規模生產革新后,勞動者丟了工作,社會保障和再就業培訓的成本丟給了國家,所有人民都承擔了失業潮帶來的潛在治安風險與動蕩。那么只有誰賺到了?資本家。
這個道理就像現在各種垃圾公司搞996,年輕人搞壞了身體,整個國家承擔醫保成本;年輕人被剝削太慘,沒有生育養育孩子的時間與經濟基礎,整個民族陷入低生育率和老齡化的危機——這就是我在《我們年輕人不愿意生孩子,但問題的根源不在年輕人身上》這篇文章中所分析的問題。那么只有誰賺到了?資本家。這些好事全讓他們沾了光了,再把成本丟給所有勞動者和國家,這個道理不太合適吧?
這些問題的核心就在于,科技進步為誰服務?至少在現階段來看,勞動者和資方的地位極端不平等,那么科技進步帶來的紅利也自然就會被資方攫取。就像我上文所說的,對于一個資本家來說,把所有員工換成不抱怨、不漲工資、不生病、不生孩子、隨便加班的AI,簡直做夢都要笑出來。
用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原理解釋這個問題,根源就在于:無產階級不掌握生產資料,因此無法享受科技進步帶來的便利。科技進步反而讓無產者與資本家的地位更加不平等,讓工人的處境更加困難,讓貧富差距和階級固化更加嚴重。
“科技進步為誰服務”?舉兩個去年非常新鮮的新聞,一個是亞馬遜用AI解雇員工:亞馬遜的“機器人經理”在今年年中解雇了900多名未達到生產率指標的倉庫物流中心員工。這名“機器人經理”是一種自動化系統,它可以追蹤每一名員工的生產效率。一旦系統發現員工過于頻繁地休息或未完成生產目標,無需經過人類高管的意見,該系統將自動發出與質量或生產率相關的警告或崗位終止信息。
另外一個是環衛工人的智能手環:“最近,南京河西區域的環衛工人被配發了一款有定位功能的智能手表。工人們只要在原地停留休息20分鐘以上,手表就會自動發出“加油”的聲音……這聲“加油”不是鼓勵,而是警告。原地停留20分鐘被管理人員定義為“違規停留”,一旦發現環衛工人有任何摸魚的跡象,手表就會自動給環衛監控指揮中心報警,處罰也就跟著來了……不管是不是午休時間、不管工作做沒做完,只要停留就等于偷懶的邏輯,也難免有一刀切之嫌。用這位環衛工人的話說:‘如果半小時內路上都干干凈凈的,難不成我還要專門來回跑不成?’”
所以人社部新年第一篇文章就提到這個問題絕不是空穴來風,資本家確實賺的盆滿缽滿,但是把所有成本都丟給國家、社會和勞動者,國家能不重視么?萬一哪天失業潮來了,巨額的社保資金怎么解決?巨大的社會治安潛在威脅怎么處理?現在他們也不是沒干過啊,比如外賣平臺,把通過控制成本,把外賣員的數量定在將將夠用的水平,讓他們不得不拼盡全力冒著危險才能完成所規定的工作。那潛在的交通風險誰來承擔?還不是外賣員和整個社會嘛。
相關的例子還有很多:英國著名吸塵器(和吹風機)生產商戴森公司在2002年關閉了它所有位于英國本土的工廠和車間,并把生產地遷入了馬來西亞。這很明顯是出于更低生產成本的考慮,雖然英國政府對于戴森遷廠一事提出了明確的反對,但無濟于事。政府只能對戴森廠大量的失業工人進行失業補助和再培訓,這就相當于用英國納稅人的錢,為跨國企業追逐更高利潤而擦屁股。我們只需要這樣類比一下即可:把第三世界廉價勞動力當成機器人,所以說這個問題遲早要提上日程。
(三)“一只腳在冰水里,一只腳在火中”
美國社會學家、工人運動領袖布雷弗曼小家境貧寒,家里無力支持他的教育,只能輟學打工,先后在海軍造船廠、鐵道修配廠、基礎鋼鐵工業設備廠等企業工作了14年,擔任過銅匠、管工、金屬片工……高等教育的缺失并沒有影響布雷弗曼走向學術道路,而“社會大學”的經驗成為了他理論最好的支撐基礎。
布雷弗曼的理論體系關注于科技進步對于無產階級的沖擊,他提煉出了當代企業管理的幾大本質:第一,將勞動過程與工人技能分離;第二,將概念與執行分離;第三,利用壟斷權力對知識和勞動的控制——控制勞動過程的每一步,控制知識的執行方式。 布雷弗曼認為技術的進步非但沒有改變無產階級的命運,反而成為了限制無產階級的新枷鎖。先進的技術讓無產階級工作更加“去技能化”,讓他們喪失了與資方議價的能力;無論在工廠流水線上,還是在白領辦公室中,勞動者的工作整體性在退化,工廠和企業需要的只是不用思考與反思、不停重復執行去技能化任務的“身體”而已。
布雷弗曼指出,雖然管理學和技術進步都是“中性”的,但是在資本主義剝削體制下,它們都成為了助長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工具。比如說所謂的“辦公軟件釘釘”,我在很多文章里都批判過它對勞動者巨大的負面作用:《互聯網科技革命與無產階級的新枷鎖》。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者們根本無法享受到技術進步、組織優化所帶來的福利,反而這些新技術成為了勞動者身上的新枷鎖——比如上文中環衛工人的“智能手環”。
布雷弗曼無不憂慮地指出,曾經勞動者們只是借助機器進行生產,在當今工人的技能轉變為照料機器。他用一個非常俏皮的比喻,來解釋在階級不平等下技術進步的現象:“……‘平均’提高了,那就是接受了統計學家的邏輯——統計學家們把一只腳放在火中,而另一只腳放在冰水里,然后告訴你:‘平均而言’,他感到非常舒服。”
(四)張屠戶與帶毛豬
文章的最后我要反駁一種觀點:用腳趾頭想一想,一定會有腦子不好使的人評論“沒有資本,哪來這些科技進步”“你這樣攻擊資本,沒人投資研發新技術了怎么辦”?諸如此類的言論我已經見怪不怪了,如果哪天沒出現我倒是會覺得挺奇怪。
國產良心電影《我不是藥神》上映之后引發了不小爭議,其中一個普遍立場是:藥廠花了大成本去研發,因此他們有“資格”把救命藥定這么高的價格。另外違法就是違法,公安機關對走私的打擊、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都是情理之中。那我們不禁要問,病人吃不起藥瀕死的困境,究竟要歸罪于誰呢?
專利制度、知識產權保護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發明創造的積極性,為規范市場行為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但也產生了天價救命藥或一些大型跨國企業靠“專利壟斷”打壓新興企業的副作用。就像資本主義制度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但也伴隨著征服、奴役、掠奪、殺戮、剝削等黑暗歷程。這些都是一頁紙的正反面。 最關鍵的問題是,專利制度保護究竟是科研人員的權益,還是醫藥巨頭跨國資本的權益?說句通俗點的話就是,這個藥賣的再貴,科研人員也不會多拿多少錢。考慮到各大跨國公司對于“科研民工”的激勵程度,專利制度對于創造發明的積極性的正面意義也不能過高估計。這是我微博上《我不是藥神》影評下的一些評論,其實很說明問題:
美國等發達國家,對藥品的研發都是有大量的財政資金的支持的,新藥研發失敗的成本并不是醫藥公司完全負擔的,但是成果卻被醫藥公司獨占。曾經有議員提出過公共資金參與研發的藥物不設專利一說,但是在醫藥公司支持的游說集團的操作下胎死腹中。用納稅人的錢支持開發新藥,專利歸醫藥公司所有,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這是赤裸裸的資本主義精神啊。
“資”本主義顧名思義,就是以資本增殖為首要目標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收集了上萬條數據,橫跨人類經濟發展數百年,得出的一個核心結論就是資本收益遠超于勞動收益,甚至遠超于經濟增長——即那個核心公式“r>g”。從另一個角度這就意味著,經濟增長的絕大多數紅利都被資本,以及其人化的體現——資本家所占有了。
有人說,你總是批判資本收益,但是沒有人投資誰會搞科研呢?沒有跨國資本和大公司投入這筆資金,你連成果都出不來,科研工作者都沒人養活,還談什么收益呢。這我要舉一個經典的反例了:諾貝爾獎獲得者屠呦呦,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科研體制下,研發出了青蒿素,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1960年開始雜交水稻研究,66年成功培育出三系雜交水稻,讓無數人能夠吃得太飽在網上去瞎逼逼了。
人類世界四千多年的文明史,對于科學技術的探索與創新、對于藝術的追求與創作一直在孜孜不倦地進行,近現代來資本和資本主義只不過是一個催化劑式的存在。發明改良蒸汽機這算是資本主義的“爸爸”了吧,也沒見誰“投資”啊。這不過是資本主義價值觀長期對我們精神奴役下,所有人都潛意識地神話資本、崇拜財富:“因為存在,所以理所當然;因為流行,所以就是好的”。前幾天還有人在微博上留言杠我,說沒有消費主義的洗腦,大家就都不會消費了,經濟就會崩潰。
毛主席曾經教導我們:“死了張屠夫,就吃帶毛豬?”(《關于軍事工作落實與培養革命接班人的講話》一九六四年)這背后還有一則民間寓言故事:張屠夫用武力壟斷屠宰行業,不但強買強賣而且缺斤短兩肉有毛。還常常自夸“沒有張屠夫,就沒有豬肉吃”。不少老百姓都信以為真。直到一天張屠夫暴病身亡,老百姓們心想:壞了,這下可沒肉吃了。結果,街上出現了更多賣肉的,肉好價廉且沒毛。大家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都是張屠夫作怪啊!
這個故事無論是愿意還是引申義用在這里都再恰當不過了,沒有了野蠻生長的資本,沒有了血盆大口的資本家,沒有了收割韭菜的符號溢價,歷史的車輪終究會滾滾向前,說不定還滾地更順暢。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千鈞棒 | “吳市場”的反對發展芯片產業和美國的用“舉國體制”發展AI——兼評美國和西方常常打公知的嘴巴
2019-02-18? 昆侖專題 ?
? 十九大報告深度談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