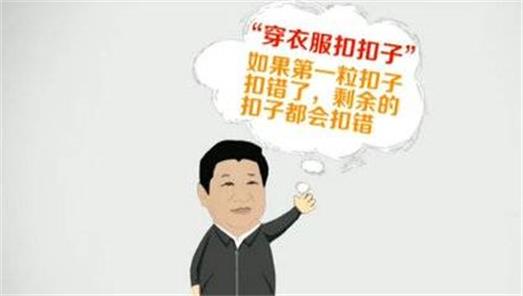【編者按】建黨百年,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走出的社會主義道路,成為今年的重要命題。為此,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謝茂松撰寫萬字長文,以“百年大黨,其命維新”為核心,從文明的角度,探討中國共產黨長盛不衰的秘訣,以此總結中國共產黨如何自我革命,如何保持初心,并提出中國共產黨是新型的文明型政黨這一論斷。本文原由觀察者網分三篇連載,為便于閱讀,昆侖策網和“昆侖策研究院”授權全文轉發,以饗讀者。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的重大歷史時刻,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的重要講話,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全黨、全國人民以及全世界的莊嚴宣言、莊嚴承諾,同時也是向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同時期的老一輩革命家、革命先烈、革命烈士,向近代以來的所有仁人志士,向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歷代先圣先賢、民族英雄豪杰的致敬。這一切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所擁有的“百年大黨,其命維新”這一高度自覺的歷史文明意識。
一、百年大黨,其命維新:百年大黨的“可大可久之道”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乃是擁有9500多萬名黨員、領導著14億多人口大國、具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百年大黨。大黨之為“大”,是“大就要有大的樣子”;百年是“久”,百年大黨意味著大而能久。既大且久,則必有其理,必有其道,這就是“可大可久之道”,而這也正是中國文明傳統一以貫之的文明原理。中國共產黨自覺繼承中國文明傳統并發揚光大,這就是毛澤東所說“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即“其命維新”。“維新”之要義,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可大可久之道”也意味著自覺的深厚歷史意識。故欲究百年大黨何以能大而又能久之道,則必須在大歷史、文明史的視野下觀其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這就是要在文明史、大歷史視野下,深刻思考中國共產黨是在怎樣的歷史大勢、國內國際形勢下產生的?中國共產黨又是如何發展、壯大,如何由小到大、由弱變強?中國共產黨能夠發展、壯大,又是看到了在歷史中潛藏的什么社會力量,依靠著什么社會力量?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事業又是怎樣的事業,又如何是正義的事業、偉大的事業?這一切的目的,乃是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守住黨領導人民創立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世世代代傳承下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可大可久之道。
【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圖片來源:新華網】
二、“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共產黨對于近代遇到的國家困境、社會困境、文明困境三重困境的克服
大國要有歷史,要經歷起落,中國文明在歷史上經歷了一次次興衰起落,其中有“四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的文明危機,這主要是來自北方游牧民族及其草原帝國的沖擊,但中國文明在歷史上每一次都能衰而復興。鴉片戰爭以后的近代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及其背后西方文明的侵略,面臨著文明困境、國家困境、社會困境的三重困境,這也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遇到的三重困境。如此我們才能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到的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是“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共產黨正是為解決這三重困境應運而生,毛澤東總結黨的創建的歷史時說:“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從此以后,中國改換了方向。”解決文明困境的問題要先通過解決最大的國家困境的問題,然后是解決社會困境的問題,最終文明困境才能得以解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反對內外敵人的雙重革命性質,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使得國家獨立、人民解放,解決了國家困境。中國的革命、人民解放戰爭也是通過最廣泛的社會組織動員的方式,同時進行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改變中國社會結構的社會革命,其中的關鍵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所發揮的高度組織力、凝聚力,中國共產黨深深地融入于社會。新中國的成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國家就要解決社會問題,以解決社會困境。這個過程中也走過一些彎路,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但也制造了一些新的問題。改革開放的今天雖然有有錢人與窮人,但再也沒有強固的資產階級力量。中國雖然開放市場、金融,但也不會放任資本的野蠻生長,因為這樣的話,最后必然會走向美國的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也不會讓國內資本成為跨國資本的買辦,因為這樣的話,中國就可能在實質上、結構上回到舊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必須維護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為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原因所在。馬克思針對的是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結構,所以中國共產黨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形成過程中始終有馬克思主義邏輯的存在,但在實踐中具有中國化的品格。
當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最終以中國社會主義的方式完成現代化,同時也以社會主義的方式解決現代化所有的問題。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結合為一體、走社會主義道路,最終將形塑新的文明,這就是對于近代以來文明困境的克服。中國近代文明困境、國家困境、社會困境的三大困境至此徹底克服,中國共產黨成功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建構了中國共產黨這一新文明,在長時段而言將取代西方過去五百年文明,開創未來五百年的文明想象,甚至是新的千年文明想象。唯有在中國共產黨開創新文明的意義上,建黨百年之際,今天的我們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提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改變了五千年中國歷史方向的重大歷史論斷,他說:“一九二一年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就改變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改變了方向。我們共產黨是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政黨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覺悟,最有預見,能夠看清前途。”
三、中國共產黨高度自覺的文明意識:憂患鍛煉斗爭精神,憂患檢驗磨練“初心”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根本上是必須完成文明的復興。歷史、人民為何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根本上是在于中國共產黨人具有高度自覺的文明意識、歷史意識。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意識是一種歷史憂患意識,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是生于憂患、成長于憂患、壯大于憂患的政黨”,歷史憂患意識貫穿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憂患、危機中鍛煉出“永遠奮斗”的“斗爭精神”。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經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長征途中的湘江血戰、抗日戰爭時期日本殘酷的大掃蕩、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后發動內戰等各種內憂外患的挑戰,在新中國成立后經歷了抗美援朝、美國封鎖、蘇聯成兵百萬等外患的挑戰,改革開放時期則遇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初美國制裁,新時代則遇到美國發動的貿易戰以及去年的抗疫,但中國共產黨越是在憂患中,越是能激發出其內在的斗爭精神與斗爭能力,誠如孟子所言“生于憂患”。毛澤東20世紀60年代曾說《毛澤東選集》“是血的著作”,《毛澤東選集》可以說無一字不是偉大的斗爭精神。習近平總書記精辟地總結斗爭精神貫穿于百年黨史:“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在斗爭中誕生、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壯大的”。“憂患”與“斗爭”在中國共產黨的辭典中可謂是孿生詞。這種憂患意識還體現在中國共產黨行將解放全中國時,毛澤東極端冷靜地提出上京趕考與“兩個務必”,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出了“新的趕考”。憂患意識包含著安不忘危與轉危為安的安危互相轉化的兩面性,故而“生于憂患”的反面則是“死于安樂”。中國共產黨的憂患意識深深植根于中國文明傳統,作為五經之首的《周易》被認為是“憂患之書”,憂患考驗、鍛煉、增進著德性;而德性的本源所在,就是與中國共產黨的憂患意識一體相生的中國共產黨的“初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守初心,就是要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中國共產黨的“初心”深深植根于中國文明傳統。“初心”是發心、發愿,發的是宏大誓愿。初心是覺悟之發心,首先是自我覺悟,進而是要引導廣大眾生覺悟,也就是普度眾生,這尤其是中國大乘佛教之根本要義所在。《大智度論》說:“初心未攝,未能深愛眾生故。”《宗鏡錄》說:“若離初發心,則不成無上道。所以云一切功德,皆在初心。”佛教之初心,與儒家、道家的赤子之心是相通的。《孟子·離婁下》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道德經》說:“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原本來自梵語的初心被翻譯為“人之初性本善”之“初心”也是有所取自儒家。“初心”不止來自于佛教中國化的中國大乘佛教、來自于儒家、道家,在根本上更來自于《五經》之首的《周易》,這就是《周易》首卦代表創生天地萬物的乾卦卦辭所說的“元亨利貞”之“元”。“元”代表初始,是純粹、至善、無私的初心、仁心,“亨”是事業的不斷亨通廣大;唯有葆有“元”之初心,方能至于廣大。事業大發展則有大利益,“利者,義之和”,“利”不是少部分人的一己私利,而是天下最廣大百姓的普遍利益、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是純粹利他而毫無特殊利益的;“貞”是慎終如始、永久保持初心。“元亨利貞”作為整體,唯有始終保有初心,方能“可大可久“。“元亨利貞”是不僅大還要能久的可大可久之道。這是來自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初心,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大心量。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之純粹,使得中國共產黨能由1921年的五十幾位黨員而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發展成為今天世界第一大黨、第一強黨。
四、“我”與“我們”:“初心”在百年黨史的具體歷史中的顯現
中國文明作為世界史上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文明,一直以來以大一統的大國政治為常態,而分裂是暫時的、是非常態的;西方文明從古希臘開始就是以城邦小國政治為常態,羅馬帝國是非常態,崩潰之后則再不可合,所以歐洲由中世紀的一個個公國、城市共和國等演變為近代歐洲一個個民族國家。中國文明傳統維系大一統國家,靠的是以儒家思想作為國家指導思想,法家在實際政治運作、道家在救儒家之弊等方面則與儒家形成補充與張力。維系大一統國家,還靠的是通過以儒家經典為考試內容而通過科舉考試產生的儒家士大夫政治,士大夫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強調士大夫自身的內圣外王之道的德性。作為“治法”的士大夫政治制度,與作為“治人”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二者缺一不可。士從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產生,尤其從最大多數的農民中產生,“耕讀傳家”成為傳統中國人的理想,士具有當時世界上最為廣泛的普遍代表性。近代以前中世紀的西方是封建社會,掌握政治、軍事、政治權力的國王、領主、騎士都是世襲的,文化則掌握在基督教教士身上,再下面則是農民、農奴,充滿著階級對立,到近代則演化出多等級會議。西方不存在中國代表全體四民社會的一元的、具有最大代表性以及整體性的士階層。面對高度組織起來的現代工業文明時代的西方侵略,一步步將中國變為半殖民地,一盤散沙的中國也必須高度組織起來,現代的政黨組織應運產生,而現代政黨又必須最終能適合于中國固有的大一統的大國政治,唯有大黨方能領導大國。大是要能最大地普遍及于全體民眾,是要最大地轉化中國文明傳統中“士”的廣大代表性,同時能克服傳統士大夫政治黨爭與紀律性不足等弊病。中國共產黨正是滿足了中國的這一內在歷史需求,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正是領導大國的大黨所需要的最具元初、大本大源性的出發點,即能“亨利貞”、能大能久之“元”。“初心”在百年黨史的具體歷史中展開、顯現,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不忘歷史,不忘初心”的深意所在。初心不是抽象、高懸、脫離歷史而存在的,黨史是涌動著歷史精神,初心就是黨史中生生不息的歷史精神。【河南防汛救災當中,黨員干部沖鋒在前(視頻截圖)】1. “初心”在百年黨史中的具體顯現:看到未來、看到歷史大勢的戰略思維與政治的優先性(1)看到未來、看到歷史大勢的政治遠見,在本源上非出自于初心不可初心不是一時,是要堅定、不動搖而始終持守的,有此不動搖之初心,才能在困難的時候看到光明、看到未來,才有把握歷史大勢的政治遠見。毛澤東要求共產黨員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他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中生動形象地闡明了沒有預見就不叫領導,他說:“什么叫做領導?領導和預見有什么關系?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人們通常看得見大東西,看不見小東西,但是有些大東西,也看不見。……陳獨秀那個時期,農民要土地,這是一個大東西吧,土地問題是一個大量的普遍存在的東西吧,但是那時候也看不見。凡是政策上犯錯誤的,一定是大東西看不見。”
毛澤東深刻地揭示了所謂預見是要在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就能看到其未來的普遍意義,他說:“所謂預見,不是指某種東西已經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現了,在眼前出現了,這時才預見;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遠,就是說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這就是《周易》所說“知幾,其神乎”,即在大家都還沒看到時,卻獨能把握事物變化先兆的預見性,也就是《周易》坤卦所說“履霜,堅冰至”。真正地看到未來、看到歷史大勢的政治遠見,在本源上非出自于初心不可。毛澤東在偏遠的井岡山山溝溝里看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客觀大勢,深刻、全面分析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點,確立中國革命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質,同時分析革命政權存在所需要的主觀條件,最終充滿預見、充滿自信地指出小片工農武裝割據政權存在的可能以及最終奪取全國勝利的可能,這給當時很多處于失敗、困難中的同志們帶來了信心。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答了在山溝里是否可以有馬克思主義的疑問。山溝里有馬克思主義,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創造性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深刻地理解了中國大歷史,是冷靜分析了當時中國內外的種種政治、經濟形勢,揭示中國紅色政權發生的獨特原因及其存在和發展所需要的相當的主客觀條件,從而令人信服革命高潮有快要到來的可能,這完全是建立在毛澤東一再強調的“知己知彼”、充分認識自己與對手的基礎之上的。毛澤東看到了中國長時段歷史中深深潛藏的社會力量,那就是占當時中國最大多數的農民。明清以來存在的最大社會問題就是人口劇增、土地兼并帶來的農民失去土地的問題;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卷入到西方帝國主義主導的全球市場中,農民加劇失去土地,新老問題疊加,這也為中國革命準備了最大的社會力量。毛澤東具有大歷史意識,所以最早地認識到中國革命一定要是農民革命、土地革命。中國這一場革命同時也必須是改變中國社會結構的社會革命,這才是最為徹底的革命,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才具有革命的徹底性。看到未來、看到歷史大勢,方能具備全局性的戰略思維。戰略思維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斗爭中形成的優良傳統,毛澤東在1936年12月寫下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以及一年半后寫下的《論持久戰》被印成小冊子后,成為鼓舞廣大民眾、指導中國革命、中國抗戰的經典文本。中國共產黨的一代代領導人秉承了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看到未來、看到歷史大勢、統籌國內國際大勢的戰略思維的優良政治傳統。鄧小平作為毛澤東之后的第二代領導人,提出“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一心一意搞建設”,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才能在大力發展生產力中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否則“社會主義怎么能戰勝資本主義”,因此“我們把改革當做一種革命”,“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鄧小平明確提出“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主要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自己的條件,以自力更生為主”。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3)看到數字文明時的未來:“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在改革開放三四十年后的新的歷史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要領導人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他早在2000年任福建省省長時,就敏銳捕捉到未來信息化、數字化的大趨勢并作出了建設”數字福建”的部署,指出建設“數字福建”就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制高點之一。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看到未來、把握大勢,作出建設數字中國的戰略決策。就像當年毛澤東在井岡山看到中國革命的未來一樣,習近平總書記在21年前的2000年就高瞻遠矚地看到了數字文明時代的未來。而這正是前面提到的毛澤東所說的預見,“所謂預見”,“不是指某種東西已經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現了,在眼前出現了,這時才預見;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遠,就是說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由此,習近平總書記提醒全黨同志“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這句話就如千鈞般重。
現在正在看到,未來更加會看到,“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這句話,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句話具有同等分量,代表著中國共產黨人在不同歷史階段始終能極端清醒、高瞻遠矚地看到未來。(4)與“初心”相應,中國共產黨人把政治放在最優先的考慮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相應的,是把政治放在最為優先的考慮,政治在中國一直以來就是一篇最大的文章。初心之志向是要落實為政治,落實為黨與人民一體不可分離的政治。毛澤東指出:“一切問題的關鍵在于政治,一切政治的關鍵在于民眾。”又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何謂政治?一般人將政治庸俗地、狹隘化地簡單理解為權力與政府,其實三人就有政治,民間說法兩個和尚挑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就是對于政治最生動、直觀的描述。政治不是庸俗理解的權力與政府,而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無所不在。政治,最簡單的來說,就是組織動員最大多數的民眾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奮斗,共同意味著是“我們共同的”。這一切為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所深刻揭示,他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習近平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出為了領導救亡,中國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新的組織,新的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進入中國后,如同傳統中國的儒學一樣,是具有根本指導性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提出共產主義就是共產黨人的信仰。毛澤東直截了當地點出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非有不可,但“要把馬克思主義當做工具看待,沒有什么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這完全是中國文明傳統“體用合一”的哲學思維。一方面,“用”離不開“體”,“用”是“體”之“用”;另一方面,“用”中顯“體”,沒有無“用”之“體”,無“用”之“體”就只是虛“體”。(5)“黨組織”取代中國傳統士大夫階層所具有的文明意義政治需要組織、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就是新的組織。相信黨、相信組織的思想深入黨員干部的骨髓,“組織”、“黨組織”取代了中國傳統的士大夫階層,成為中國文明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今天的我們有可能、有能力來真正理解毛澤東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中,對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上的定位,他說:“我們共產黨是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政黨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覺悟,最有預見,能夠看清前途。”唯有通貫地深刻理解中國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深刻理解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中的定位。這是熟讀二十四史、熟讀《資治通鑒》,尤其是以政治家眼光來讀歷史的政治家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為了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不惜犧牲一切”的“英勇奮斗”做歷史的定位。2. “我”與“我們”:“初心”在百年黨史的具體歷史中顯現為黨員的覺悟帶動民眾的覺悟作為政治組織的領導者、組織者,如何能夠組織動員最廣大的民眾為了民眾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大家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奮斗呢?這來自于中國共產黨建黨時的先鋒隊意識,中國共產黨人只有高度地發揮其先鋒的模范作用,才能動員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先鋒隊意識來自于列寧,但深層次地是根植于中國文明傳統,即“政者,正也”,以上率下。(1)“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政治的最為深刻的洞察先鋒的模范作用,內在“覺悟”的激發至關重要,要以黨員干部的自我覺悟帶動群眾的覺悟,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是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政黨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覺悟”,而覺悟正來自于初心。政治在根本上的動力是政治覺悟,通過每個人的自發、自覺的積極主動性來達到政治上的高度團結與統一。而這種團結、統一,因為是出自每個人自發的覺悟,因而是充滿喜悅、活力與創造力的團結、統一,而這種團結、統一是最為有機的團結、統一,這是政治的共同奮斗的最大保證所在。由此我們能深刻理解毛澤東所說的兩段話:“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一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政治的最為深刻的洞察,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可大可久之道”的關鍵所在。這里的“人”不是離開各種共同體關系的抽象的、原子式的個人,而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帶領的人民的共同體。人民既是最大的復數,同時又是最大的單數。“最大的單數”是“我”,意謂每一個個體的“我”為了“我們”、為了“我們大家”的“共同的理想”而“共同奮斗”的自我覺悟;“最大的復數”是由一個個“我”最終有機構成的“我們”,乃是如大海一樣匯集每一條江河、匯聚每一條溪流,根本上是匯聚每一滴水而成其為大海。中國文明傳統的家國意識,強調個人離不開家庭,家庭離不開國家,所以“我”也不能脫離而要深深融入、參與到“我們”、“我們大家”的“大我”的事業之中,否則“小我”的“我”就是殘缺而不成為真正意義上完整的“我”。同樣,“大我”的“我們”若是輕忽了具體的一個個“我”,也將是有欠缺而不圓滿的“我們”。這就像西南的彝族、納西族等少數民族圍著篝火跳組成一個個大圓圈鍋莊舞,少一個人,圓圈就是縮小的,而每一個的加入都使得圓圈擴大。“我們”能成其為“我們”,是要看到每一個“我”。從中國共產黨黨史來看,每一位普通群眾融入到中國共產黨的事業中,其神圣意義的獲得,不也是與佛教相通嗎?中國共產黨人的事業是人間事業、是人間奇跡,但也是神圣事業。這也是由中國文明早在西周就脫離了早期文明的宗教性而以人文性為特質所決定的。人間事業具有神圣意義,這是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但中國文明做到了,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更是做到了。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文明、中國共產黨最深刻地理解了“人”。由同時成就“我”與“我們”,由中國共產黨最深刻地理解了“人”,我們就能在文明史的視野下,更深地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勛章”頒授儀式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七一勛章’獲得者都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職、默默奉獻的平凡英雄。尤其是他們的事跡可學可做,他們的精神可追可及”所具有的歷史文明意識。事跡可學可做、精神可追可及,不就是孔子在《論語》中所說的“下學而上達”,不就是毛澤東《為人民服務》中的張思德以及新中國的雷鋒等的可學可及嗎?這不就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歷史文明傳統的接續不斷嗎?中國文明傳統是如流水一樣活著的傳統,是連接過去、現在、未來之水。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聯歡活動,“人民萬歲”造型煙花照亮廣場。攝影 蘭紅光/新華社】
3. “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人民,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共產黨”:中國文明與中國共產黨對于“人”、“人民”的相信及其文明原理(1)中國共產黨最徹底地繼承、發揚中國文明相信人、相信人能團聚人心的偉大傳統中國共產黨在現代中國的各種政治團體中,是以在根本上能最大、最徹底地繼承、發揚光大中國文明一以貫之的相信人,相信人能團聚人心的偉大傳統,所以才能最終為歷史與人民所選擇。中國文明從西周“制禮做樂”的周公開始,歷代盛世都會聯系到政治家,像漢文帝、漢景帝與文景之治、唐太宗與貞觀之治。這并非是所謂個人的人治,而是說唐太宗等最高領導者作為大政治家,最關鍵的是能識人、用人,中央、朝廷有殫精竭慮為國謀的大臣團隊來輔佐,地方官府則有循吏,即具有政治意識與高度執行力的地方官隊伍來讓中央決策落地,最基層還有士紳鄉賢,上下同心,最大地組織動員全國上下、四方民眾,這才能創造盛世。深刻地理解“人”、相信人、相信人能團聚人心,在今天的新時代則具體落實、體現為黨管干部、黨管人才、黨的全面領導的原則,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發揮統攬全局、協調四方的政治功能。深刻地理解了“人”從而相信“人”,創造一個個人間奇跡,使每一個參與人間事業者都具有神圣意義,這也就使其具有廣大的普遍性,也就是毛澤東所說如太陽普照大地之普遍性。(2)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來理解“相信人民”:人民覺悟被激發出來的潛力如佛教所說佛性被激發出來后的無窮無盡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中國共產黨始終相信人民的力量,毛澤東形象地打比喻,“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何始終如此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佛教的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說法,可以對這一問題有別樣的領悟。佛菩薩如果視自己為佛菩薩,而視面對的眾生是眾生,作如此判然分別,那佛菩薩就已經不是佛菩薩;佛菩薩只有在看到面對的眾生同自己無別,尤其要在眾生看到佛、看到佛性,這才成其為佛菩薩。毛澤東如此相信人民,就是相信人民就是我。如果不相信人民有其一樣的覺悟之巨大潛能,那毛澤東也就不成為毛澤東了。相信人民與我一樣,激發人民的覺悟的無限潛能,就是黨要做的工作。毛澤東同時批評對待群眾的命令主義與尾巴主義兩種錯誤傾向。1945年黨的七大閉幕后,黨中央主辦的《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團結的大會 勝利的大會》,一方面提出共產黨員要“虛心向人民學習”,“站在人民之中,做人民的模范,與人民一起堅持下去,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同時又提出,“如果沒有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共產黨員作為領導者,人民的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這顯示了黨與人民的關系的深刻辯證法,即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共產黨員先做人民的模范,然后才能領導人民提升自己的覺悟從而自己解放自己。人民的普遍覺悟,就像眾生本有的佛性被激發出來一樣,當人民的覺悟被激發出來時,其潛力一如佛教所說佛性被激發出來后的無窮無盡。如此我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對于燒炭的普通戰士張思德的追思,直抵革命隊伍中的每一位成員的心田。(3)《為人民服務》成為世界政治的經典文本:與《共產黨宣言》同等的普遍意義《為人民服務》不僅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現代中國人的經典政治文本,也成為世界政治的經典文本,其普遍意義是可以與《共產黨宣言》同等看待的。《共產黨宣言》的普遍性更多是理論性的,《為人民服務》的理論性則是具體而微、理事合一的,這也是中國文明的運思方式。以佛、法、眾生三無差別理解了中國共產黨為何如此相信人民,就能理解黨和人民休戚與共的一體關系。這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自述“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甚深的要義精微所在。(4)概括百年大黨百年偉業:“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人民,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共產黨”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偉業,或許可以用1945年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報告中提出的一句話來概括,這句話是——“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人民,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共產黨”;這句話進而延伸之,可以說——沒有這樣的人民,就沒有這樣的共產黨;沒有這樣的共產黨,就沒有這樣的人民。將“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人民,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共產黨”這段話與前面提及的毛澤東的另一段話,即“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兩段話一起合參,就會對黨與人民一體不可分離的關系有更深的領悟。
4. 自我革命精神就是初心:初心、自我革命精神所具有的文明普遍意義中國共產黨繼承并發揚中國文明固有的強調嚴于修身、自我革命的偉大的德性政治傳統,極端重視“黨要管黨”的黨的自身建設。黨的建設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將依規治黨的制度建設貫穿于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作風建設、組織建設、紀律建設、反腐倡廉建設之中。其中政治建設被放到了“黨的根本性建設”的首要位置,正在于中國文明傳統與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傳統這兩個新、老傳統對于政治優先性的強調。作為政治與教化的治統與道統,乃是中國文明最為重要的兩端,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建設放在“新治統的建構”的文明史視野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在新老兩個傳統中,政治離不開教化,政治在根本上離不開思想教育、思想覺悟,中國共產黨強調思想建黨,這就是思想建設作為黨的基礎性建設的要義所在,而黨的思想建設同樣要放在與“新治統的建構”一體的“新道統的建構”的文明史視野中,才能得到更全面、深刻的理解。政治建設、思想建設最終要落實到黨員干部的作風建設上來,黨的作風建設包括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生活作風。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斗爭實踐過程中,形成了黨的優良作風,并在黨的七大上被總結、提升到理論的高度,這就是毛澤東概括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和“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三大作風的形成殊為不易,有如王陽明當年自述其“良知”之說乃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中國共產黨得出三大優良作風所經歷的百死千難,較之當年的王陽明,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黨的作風問題根本上是黨性問題,所以作風建設根本上是黨性修養問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作風的直接而迅疾的影響力,猶如風吹在草上的作用一樣,黨員干部的作風對于廣大群眾而言是最直觀的,體現了黨員對于群眾的先鋒模范作用,并最終落實在具體工作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作風關乎“黨的形象和威望”,“黨的作風就是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自我革命精神是黨的建設的最根本的精神,延安整風運動成為黨的自我革命精神的典范,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道統”。正是從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中國共產黨形成了通過黨員干部的集中教育、集中學習來改變作風的傳統。“細致”的“延安整風教育了干部,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作風問題具有反復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所以作風建設需要像延安整風一樣來進行經常性、集中性教育學習活動,從而不斷保持、增強黨員干部的覺悟,這是一種自我革命的精神,是永葆“初心”的根本保證。
【從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中國共產黨形成了通過黨員干部的集中教育、集中學習來改變作風的傳統】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地指出,“強大的政黨是在自我革命中鍛造出來的”。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永葆初心,正是中國共產黨“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的自我革命精神,中國共產黨才能成為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所說“中國共產黨立志于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包括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內的“自我革命”以及“全面從嚴治黨”,正是作為中國文明核心原典《五經》之首的《周易》首卦乾卦《大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文明原理,所謂“自強不息”乃是“嚴于求己”;而這也是對《大學》所說“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日新其德”的偉大文明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廣大。“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乃是對乾卦卦辭“元亨利貞”的解釋,“元”是初心,“全面從嚴治黨”的自我革命精神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員的初心。乾卦代表“天”,中國文明的“天人合一”意謂人道取法天道,具有著文明普遍性意義。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自我革命精神,乃是對中國文明傳統在現代的繼承與發揚光大,同樣具有古今連續的文明普遍意義。5. 新內圣外王之道:新時代黨的建設形成了“新道統”、“新治統”與“新政教傳統”新時代黨的建設一以貫之的一條主線是“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文明“內圣外王之道”的繼承與發展,也就是建構黨的新內圣外王之道。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為“內圣”,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為“外王”。“內圣”是為了“外王”,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最終也要落實為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中國共產黨在黨的建設中形成了新道統、新治統,形成了新的政教傳統,但又是在繼承中國文明傳統基礎上對“其命維新”的新創造。6. 政策與方法來自根本態度以及“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與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政策和策略是生命線,政策需要執行、落地,而政策的執行、落地則需要工作方法,“政策”與“方法”二者同等重要。中國共產黨從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開始,就形成了極端重視工作方法的優良傳統。翻開《毛澤東選集》,我們看到《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一篇篇強調工作方法的文章,工作方法也就是領導方法。新中國成立后,到1958年1月毛澤東則寫下了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方法從哪里來,方法是技術問題嗎?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于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政策和方法都是來自尊重人民的態度,也就是今天講的初心。毛澤東在1960年11月在《徹底糾正“五風”》一文中要求“干部真正學懂政策”,同時“又把政策交給群眾”。(3)“高屋建瓴”的主動權來自于“實事求是”與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毛澤東多次強調“方法對”,而“方法對”這一條的前面又排著另外兩條,即“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情況明”,擺在第一條的位置,是因為“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無從著手。因此要摸清情況,要做調查研究”。“決心大”是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毛澤東指出,有了好的政策,還要有建立在實事求是、“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基礎上的“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他說:“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做調查研究比較認真一些,注意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通過調查研究,情況明了來下決心,決心就大,方法也就對。方法就是措施、辦法,實現方針、政策要有一套方法。這三條里頭沒有提方針、政策,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方針、政策。有了好的方針、政策,你情況不明,決心不大,方法不對,還是等于沒有。”毛澤東強調“高屋建瓴”的主動權來自于“實事求是”:“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反映,即人們對于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毛澤東要求“共產黨員是實事求是的典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典范”。毛澤東以第二次反“圍剿”的切身例子來生動說明,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他說:
“要鼓起群眾的干勁。同時鼓起干部的干勁。干部一到群眾里頭去,干勁就來了。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打仗也是這樣,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圍剿’的時候,兵少覺得很不好辦,開頭不了解情況,每天憂愁,我跟彭德懷兩個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對彭德懷說,紅一軍團的四軍、三軍打正面,打兩路,你的紅三軍團全部打包抄,敵人一定會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憂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調查研究就會有辦法,大家回去試試看。”
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中國共產黨注重工作方法的優良傳統,2016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做了學習《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的重要批示,對各級黨委(黨組)領導班子成員特別是主要負責同志重溫這篇著作提出明確要求。這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首次向全黨推薦毛澤東同志的單篇著作,這也與習近平特別重視“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有關,他對此深刻地解釋說:“這是因為,對于我們這么一個大黨來講,不僅要靠黨章和紀律,還得靠黨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這些規矩看著沒有白紙黑字的規定,但都是一種傳統、一種范式、一種要求。”
五、古今“中國”之為“中國”的文明普遍性: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及其底層結構的中國文明的三重普遍性
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開宗明義講到我們共產黨的革命隊伍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是為解放人民的,他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又飽含感情地說到共產黨人解救中國人民的責任以及我們為人民而死的神圣意義,他說:“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為人民服務》中這些由平凡而入于神圣的日常話語,同時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話語,正是最好地詮釋了中國革命所具有的普遍性。中國革命既是近現代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具有革命的普遍性意義,即世界革命所具有的普遍性意義;同時又以中國五千多年文明、中國近現代史自身的特點,使得中國革命具有了現代中國的革命特質。【《為人民服務》開宗明義講到共產黨革命隊伍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圖源:百度百科)】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后建立了新中國,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同樣具有社會主義的普遍性意義,即世界社會主義的普遍性意義;同時也以中國自身五千多年文明以及中國近現代史自身的特點,使得中國社會主義具有了現代中國的的社會主義特質。歐洲的社會主義進入中國,就如同當年印度的佛教進入中國一樣,佛教在印度消亡,卻在中國發揚廣大,尤其是中國發展出了大乘佛教,這是因為佛教的平等心契合中國文明儒家、道家的內在精神。同時,大乘佛教強調依據眾生不同根器發展出各種方便法門,則與中國作為大國強調政治家的高度政治智慧亦有深層次的契合。中國具有大乘佛教發展的最好社會、政治土壤。從西周以來三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來看,西周分封制是中國文明的第一次創制,秦漢以下的郡縣制是第二次創制,中國共產黨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則是繼前兩次創制之后的第三次偉大創制。(3)中國文明具有的普遍性更增強了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的普遍性中國革命所具有的普遍性,中國社會主義所具有的普遍性,根本上是來自于作為二者底層結構的中國文明的普遍性。考古學家張光直將世界文明分為原生道路文明與次生道路文明,中國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則是一次次斷裂的次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作為斷裂的次生道路文明,并沒有其近代以來自詡的普遍性,反而是屬于例外。中國作為唯一的原生道路文明,恰恰更具有普遍性。中國文明作為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文明,給世界提供了最為完整的文明發展樣態,美國日裔學者福山提出中國早在2千年前的秦朝就確立了西方近代才有的現代國家官僚體制。中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也是從秦漢以下一直延續至今,歐洲在羅馬帝國崩潰后就再也沒有出現歐洲一統的帝國,現在的歐盟試圖如此來做,內部卻充滿分裂,困難重重,未來難以預料。中國文明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帶來的普遍性,更增強了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的普遍性。也可以說,中國革命的普遍性、中國社會主義的普遍性,本身就是從中國文明的普遍性中內在、自然而演化、生長出來。古今“中國”之為“中國”,具有古今一體連續的文明普遍性,由此中國文明、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形成了內在一體的三重普遍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同時也是“百年大黨,其命維新”的最本質體現。
六、以“理一分殊”、“時位中”來理解“普遍性”的動態變化:中國社會主義的原則性與高度的靈活性以及階段性
佛教進入中國后,最終被中國接納、吸收的標志是佛教中國化的完成,中國產生了中國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強調根據不同根器而發展出各種方便法門,佛之為佛在于覺悟,但進入的門徑卻不是唯一的,而是針對不同特點的根器對應有不同的方便法門,所以不能執著,要無所住相。佛的覺悟是原則性的,但方便法門卻是高度靈活的。社會主義進入中國之后,與當年佛教進入中國一樣,同樣有中國化的過程。中國社會主義保持了原則性與高度靈活性的統一,由此我們則不難理解為何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同樣我們也可以理解社會主義相對于共產主義的階段論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這與《周易》“時位中”的核心原理的動態思維有著深層次的關系。
對比古希臘,它的原子式思維是靜態的,總是試圖找到最小的、不變的實體構成,這是屬于靜態的思維。而《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由六爻組成,六爻中任何一爻的變化,就使得該卦變成另外一卦,這是希臘原子式的靜態思維所沒有的。“時”在《周易》中、在中國文明中具有著根本性意義。由此我們能更深層次地理解鄧小平區分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靈活性與政治智慧。既然有初級,未來就可能有中級、高級,但具體是到什么時候,甚至是否一定就要有中級、高級,也如禪宗這一中國化佛教所強調指出的,不能完全墮于字下,而是具有高度的動態靈活性。中國在現代學習、接受世界社會主義而成就中國社會主義,世界社會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二者的關系,是宋明理學所說的“理一分殊”的關系。而今天的中國社會主義之于現在、未來學習中國社會主義的世界各國,同樣是理一分殊的關系。也如同當年的中國不能照搬別國的經驗一樣,其他各國學習中國社會主義,也同樣不能照搬中國的經驗,而要依據各自文明、歷史的特點加以各自的因時因地的轉化、創新。
七、中國共產黨的三層文明意義:中國共產黨是新型的文明型政黨,本身也將型塑新文明,進而成為新文明
天安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與“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與中國文明的“治國平天下”的精神具有內在關聯。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堅持其獨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同時其繼承中國文明“天下一家”的思想,使得中國共產黨將其共同富裕、共同發展的理念擴展于全球化下的共贏共享,最終將超越西方過去五百年贏者通吃的霸道思維。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圖源:人民視覺)】
中國共產黨在第二個一百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日,就是中國文明的全面復興之日,中國進而則延展出面向未來的新文明的想象力。而這首先要深刻中國共產黨的文明意義,要突破簡單地以政黨尤其是套用西方的政黨來理解中國共產黨而出現各種捍格不通的限制,要以文明來想象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新型的文明型政黨,本身也將型塑新文明,進而成為新文明,必須意識到中國文明所具有的生長性,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文明意義不斷深入、延展的三層文明意義。中國在農業文明時代長期領先于世界,在工業文明時代則落后、挨打而趕超。在工業文明之后最新的數字文明,與中國的農業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西方工業文明具有對于自然等的巨大破壞性,中國文明因而在對其學習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抵觸、沖突。但數字文明則不一樣,中國對于數字化真是如魚得水,中國在數字化技術的最新發展尤其是5G上,第一次與西方站在差不多的起點上。數字文明互聯互通的思維與中國農業文明的思維具有高度的相通性。中國文明過往是一種農業大國文明,它所具有的“天人相應”文明原理天然地具有整體、循環的思維方式,這在工業文明時代一度被認為是落后的,而在數字文明時代則將重新空前地激發其內在的活力。“天人相應”中最直接的是人與土地、大地、陸地的緊密一體關系,與大地相應的“風土人情”具有文明意涵。數字化也與中國文明的大一統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數字化的技術將使大一統更為徹底化。中國在農業文明時代長期領先于世界,在工業文明時代則落后挨打、奮起趕超,而在數字文明時代則有可能重新領先于世界,從而“回到歷史的中國”。這同時也意味著面向未來的新文明想象力,即對于下一個五百年乃至千年的文明想象力。中國共產黨熔鑄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數字文明以及生態文明為一體的中國新文明,將會以農業大文明的思維結合數字文明的思維來發展工商業,發展數字經濟,并將重建人與土地不可分離的共生關系,這其中也包括人在具體時空中的歷史感。這一切涉及新文明的遠大抱負,而雄安新區作為千年大計,其未來的文明史意義正在于此。習近平總書記提醒全黨同志,“網絡安全和信息化事關黨的長期執政,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福祉,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這一方面是如當年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一樣地看到未來的預見性,即看到了數字文明的未來;另一方面也是代表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新文明的歷史文明的自覺意識。從毛澤東到今天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始終能預見性地看到未來,而始終能預見性地看到未來則來自于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保持初心,初心在百年黨史的具體歷史中展開,誠所謂“百年大黨,其命維新”。(作者系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修訂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