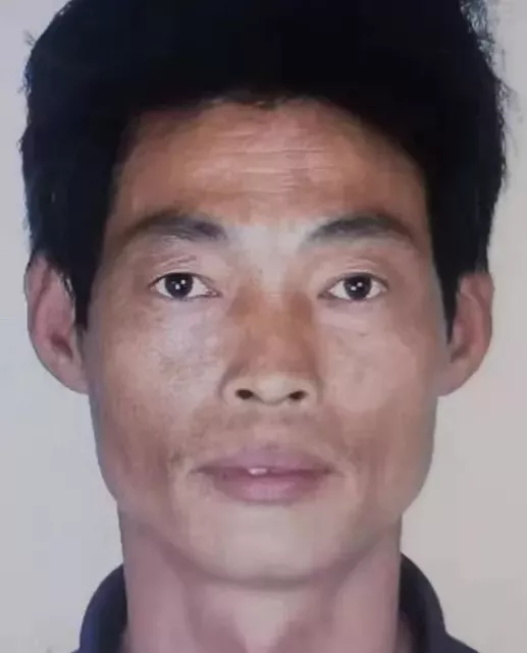1、我們常說要敢于說真話,這不完全,確切地說,我們不僅要敢于說真話,更要善于找到并敢于堅(jiān)持真理。真話是只是找到了“事實(shí)”,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從事實(shí)中的“求是”。說出真相很難,說出真相后的真理更難。確切地說,堅(jiān)持說實(shí)事求是的話,才是我們需要的正確態(tài)度。
毛澤東同志說:“真理往往是隱蔽在現(xiàn)象后面的。如果只是眼睛可以見到的現(xiàn)象就是真理,那就不需要科學(xué)了。本質(zhì)的東西是眼睛看不見的,現(xiàn)象的東西是可以看得見的。本質(zhì)是需要經(jīng)過一個(gè)長期的過程才能夠認(rèn)識到的。”【1】
2、脫離大道,一味窮究歷史的細(xì)節(jié)真實(shí)——這是我們目前許多學(xué)者的致命短處——是沒有意義的。道理,道理,有道即孟子說的“義”——才能有理。做學(xué)問的第一要義,不是掌握實(shí)事,而是“知道”實(shí)事。“知道”,即知事實(shí)中的“大道理”。
孔夫子、孟夫子都痛罵那種不知大道只究細(xì)節(jié)的人,說他們“小人哉”。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論語·子路》);孟子也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孔子和孟子不是不讓人講真話,而是讓人不要講沒有意義的“真話”。
“講真話,不如講真理。”【2】說棍子在水中是“彎”的,這是真話,但不是真理。講真話需要勇氣,而講真理則需要過腦子。說了真話,只是說出了“事實(shí)”,這遠(yuǎn)遠(yuǎn)不夠,還要說事實(shí)中的“是”即真理,只有真理才能賦予真話以意義。沒有意義的“真話”,正如沒有季節(jié)的落葉,也是沒有意義的。
3、“講真話”的真實(shí)含義應(yīng)該是鼓勵(lì)講過腦子的話。前者講的是“實(shí)事”,后者講的是“求是”;前者講的是準(zhǔn)確地“格物”,后者講的是格物后的“致知”;前者講的是認(rèn)識的起點(diǎn),后者講的是認(rèn)識的方向和歸宿。不經(jīng)“求是”的“真話”,與不經(jīng)“真話”即“實(shí)事”的“求是”一樣,在許多時(shí)候是要壞事的。
說真話是為了成事而不是為了壞事,不用于成事的“真話”就是不著調(diào)的胡話。“遠(yuǎn)取諸物,近取諸身”【3】,說人事,應(yīng)將自己的“真話”先在自身試驗(yàn);說國事,應(yīng)將自己的“真話”先在自家試驗(yàn)。如能用身家性命試驗(yàn)過的“真話”,大體才可應(yīng)用于國事。
4、說真話不如說正確的話。在大事特別是決定國家命運(yùn)的大事前,司馬遷的問題就是在大兵出發(fā)前話太多。司馬遷說的是真話,但不是正確的話。當(dāng)時(shí)正確的話不是個(gè)人是非,而是匈奴的威脅,國家要凝聚共識,形成壓倒和打敗匈奴的絕對力量。
5、有的學(xué)者做學(xué)問只止于是和非,這遠(yuǎn)遠(yuǎn)不夠。有些事——比如湘江戰(zhàn)役前的王明路線——知道是錯(cuò)的,但解決它的其他條件如不成熟,解決它可能帶來問題更多,只有先放一放。而湘江之戰(zhàn)后,解決王明路線的條件和時(shí)機(jī)也就瓜熟蒂落了。
只知是非而不考慮如何解決的學(xué)者不講這些條件,他們滿腦子的學(xué)問只止于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cuò)的,這樣的學(xué)問對國家政治而言基本沒用,如再死磕,那就有害了。
小孩知道皇帝沒穿衣服,很多人其實(shí)也知道,為什么不說透,那是政治需要。父母吵架,孩子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要是我早就離了。”為什么父母不離,不是不敢,是大局需要。小孩他不考慮這些,可愛,但他的話只能聽聽,不能采納。我們許多學(xué)者的學(xué)問單純得像個(gè)孩子。
我常說,說真話不難,難在說正確的話。正確的話就是符合大局的話。夫妻的是非,是在婚姻條件下確立的,為了揪誰是誰非而弄得離婚了,那是非就沒有意義了。不離婚——對國家而言就是不能分裂和混亂,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就是大局,它高于是非。前者需要非凡勇氣,后者需要政治判斷。為此我專門寫過一篇《談?wù)剬W(xué)術(shù)與政治的寬容與和諧》【4】。
毛澤東說杜甫的詩是政治詩【5】,為什么?杜甫有大局意識。比如杜詩《春夜喜雨》,前四句告訴人們:做事要把握時(shí)機(jī)和恰到好處(“好雨知時(shí)節(jié),當(dāng)春乃發(fā)生”);解決問題要借勢卻不事聲張(“隨風(fēng)潛入夜,潤物細(xì)無聲”)。后四句告訴人們: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dú)明”);堅(jiān)持下去,待風(fēng)雨過后,回首來路已是碩果累累(“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注 釋:
【1】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頁。
【2】張文木:《戰(zhàn)略學(xué)札記》,海洋出版社2018年版,第333頁。
【3】南懷瑾、徐芹庭譯注:《白話易經(jīng)》,岳麓書社1988年版,第379頁。
【4】張文木:《談?wù)剬W(xué)術(shù)與政治的寬容與和諧》 《世界經(jīng)濟(jì)與政治》 2006年第2期
【5】1958年,毛澤東在成都游覽杜甫草堂時(shí),望著陳列在櫥內(nèi)的杜甫詩集說:“是政治詩。”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