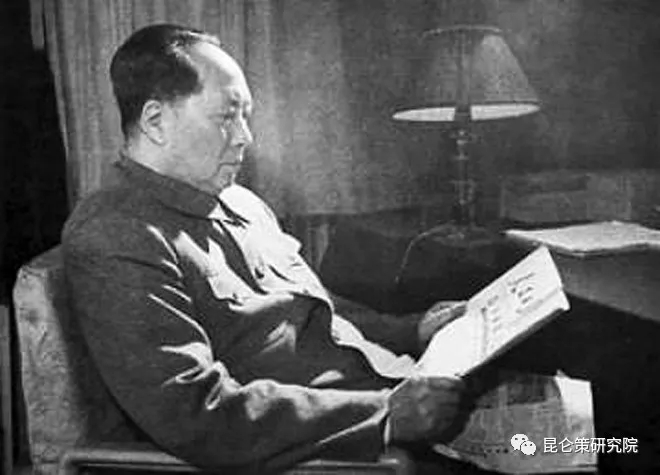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4日-星期日
第五章 誰的橋?誰的路?(下)
五、題外話:兩個“猛料”的辨析

多年后,在“是誰奪取了瀘定橋”的問題上,又有一些“猛料”爆出且引出了諸多是非。
一個“猛料”源于1979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長征日記》——這也是出版最早的長征日記。這本日記的作者稱,他率紅三團偵察排在紅四團突擊隊奪橋的同時趕到了瀘定橋,在敵人即將炸橋的一瞬間掐斷了敵人的炸藥包,紅四團突擊隊始得順利過橋。[1]按一般人通常的認知來看,這種說法比“冒著槍林彈雨攀鐵索奪橋”顯得更為合乎情理,于是也就因此而產生了非常廣泛的影響。之后,也有史籍和文章不斷地引用這本日記中的內容——包括筆者本人,以及許多當事人的子女撰寫父輩傳記時也將其當作信史引用甚至還作了更為夸張的發揮。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文獻史料的公布,再加上十余年來在大渡河兩岸沿線實地踏勘的補充,筆者最后還是不得不非常不情愿地面對這樣一個結論:這本日記并不是當年的歷史記錄,而是多年后根據有限的史料補寫甚至編撰的“革命故事”,完全不具備歷史文獻資料的分量。
而且,這樣的“猛料”即便是當作“革命故事”來傳播,那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首先,這本日記的日程與有足夠依據并能互洽互證的歷史事件發生的日期,難以契合,離散性大得驚人;其次,這本日記的地名非常混亂且相互混淆,甚至還夾雜著諸多解放后更改、遷徙、合并過的地名,里程上的錯訛更是比比皆是;其三,每日日記的篇幅很長,而且有非常多的文學性描繪語句,不太像是天天長途行軍者的記錄。后來出版的諸如《賴傳珠日記》、《伍云甫日記》、《童小鵬日記》等雖然每日記錄篇幅很小,有些甚至就是今天打哪兒出發到哪兒宿營一句話,但反而更能接近作者所處的真實環境,給出的恰恰是最有效的信息。當然,也有如《陳伯鈞日記》這樣的有篇幅較長的日程記錄,但這與作者的文化素養和所擔任的職責(作者在長征中長期擔任參謀長職務),以及養成的良好習慣有關。更何況,這些較長篇幅的記錄也多是有事件、人物的有效信息,而且與有關原始檔案文獻能夠互洽。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這本《長征日記》作者自陳:大渡河之役時他擔任紅三團總支書記。但近年在香港出版的《吳法憲回憶錄》卻提出了反證:時任紅三團總支書記的是吳法憲。[2]這本《長征日記》出版之時吳法憲正在接受審查準備接受審判,當然也難以對日記作者的說辭提出質疑。但這兩人各執一辭究竟孰真孰偽,那不是還需要更多的旁證佐證來進行進一步的辨析么?
至于大渡河之役紅三團戰斗活動的陳述,吳、肖兩人也是各執一詞。吳的回憶稱:
五月二十九日,先頭部隊二師四團在團長黃開湘、政委劉亞樓(筆者注:應為楊成武)的帶領下,經過三天的急行軍,來到瀘定橋邊,冒著對岸敵人點燃橋板的熊熊大火,在濃煙烈火中發起強攻,終于占領了瀘定橋。與此同時,我們一師部隊也在大渡河右岸,即敵人的背后發起攻擊,消滅了守敵,有力地配合了對岸二師奪取瀘定橋。[3]
吳法憲這段回憶中所稱“大渡河右岸,即敵人的背后發起攻擊”,指的就是瓦斯溝—石門坎—海子山—龍八埠等一系列戰斗,這些戰斗的確都是在瀘定橋守軍的“背后”發起的,而且千真萬確,也“有力地配合了對岸二師奪取瀘定橋”!服刑后回家的吳法憲,至少在這個問題上,除了記錯紅四團政治委員的名字外,的的確確是沒有哪個字是說錯了的!

吳法憲,時任紅三團總支書記——海子山戰斗的參加者
而這本《長征日記》的作者所執之詞那就是一個乃至一串“猛料”!比如,除開道路里程地名上存在的問題外,日記作者還寫出了一段傳奇:紅三團一天之內從安順場趕到瀘定橋,并在紅四團突擊隊奪橋時成功阻止了敵人的炸橋陰謀!而且這個說法在此后還多有變化:最早的版本是《長征日記》的作者指揮紅三團偵察排的戰士掐斷了敵人炸藥包的導火索,作者到達瀘定橋的當天便隨紅三團翻越馬鞍山追擊逃敵,一直追到二郎山那頭的紫石關[4];而后來出版的回憶錄還將故事更加延展:紅三團到達安樂壩時消滅敵軍一營,而后化裝混入瀘定城,奪取了東橋樓,當晚又跟隨紅一師隊伍翻越二郎山……[5]
后來的網絡版文字更傳奇,掐滅敵人炸藥包的干脆就成了《長征日記》作者本人。
其實,與饒杰那個口述一樣,這本《長征日記》這段記載也是很容易證偽的:其一,從安順場到瀘定橋的行程在三百里以上,行軍序列在紅二團之后的紅三團在一天之內無論如何也趕不到瀘定橋——這還不說走在紅三團前面的紅二團在瓦斯溝—石門坎—海子山延續了大半天兒的戰斗。其二,紅二團和紅三團各一部趕到瀘定橋時,“我們四團的哨兵已在那里叫‘口令’”[6]了,所以不可能有掐炸藥包導火索的故事發生。其三,紅三團不可能在到達瀘定橋的當日即追擊敵第三十八團潰兵到達幾百里外的紫石關——下面我們將要談到,中革軍委在5月30日的確有過這樣的部署,但這個部署隨即就被改變而并沒有執行。紅三團是與中央紅軍主力一起,又沿東岸來路往回走了50里,經龍八埠、化林坪,翻越飛越嶺脫離大渡河峽谷的,而翻越馬鞍山(不是二郎山!)向天全前進的,是最后趕到瀘定橋的紅九軍團部隊。
1993年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對紅一師在東岸的行動曾經有過這樣的陳述:“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的紅一師和干部團,在劉伯承、聶榮臻率領下,也日夜兼程向北急進。紅三團的五個連和紅二團一個營于29日14時由冷磧一直打到瀘定城,有力地配合了右岸紅四團行動。”[7]這個陳述的依據,是林彪、劉伯承、聶榮臻在瀘定會面后向中央報告戰況的電報[8]。而筆者經過實地踏勘,又將相關地理要素、時間及敵方、我方和當地群眾提供的情況與該電內容進行了對比判讀,認為:林、劉、聶在倉促中發出的這份電報陳述的有關信息是不準確也不可靠的。28日晚,紅二團宿營加郡河口,一師主力(三團、師部及劉、聶)宿營德妥——兩者之前相距20里即兩個小時行程。加郡河口到瀘定如今的公路行程45公里,德妥距瀘定55公里——當年翻山走崎嶇小路,經實地踏勘約為49公里。正常情況下——既或是排除途中作戰的時間,紅一師部隊從加郡河口—得妥一線趕到瀘定,需要9至11小時時間。而向瀘定前進過程中翻山越嶺且經過苦戰的紅一師主力,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當日14時”就“打到瀘定城”:當年從冷磧到瀘定的行程在20公里以上(如今的公路行程為19公里),而龍八埠或沈村到瀘定的行程約為25公里左右,紅一師部隊既或是14時從冷磧出發,要“打”到20公里外的瀘定城,也只能是在傍晚以后。而且,當地群眾口碑和史志資料均可證明,紅一師部隊是在當天16時后才進至沈村、龍八埠一線并分兵向瀘定城前進的。
后來,上海版《長征日記》的作者還出版過了一部回憶錄,而在這部名為《十年百戰親歷記》回憶錄中,作者還杜撰出了一個該作者與“紅四團特派員張國華”的對話,對話中還涉及了對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的非議[9]。筆者之所以判定這段“回憶”純屬杜撰,是因為紅四團、紅六團有關當事人的回憶足以證明:當時的張國華并非“紅四團特派員”,而在紅六團任總支書記[10]。再者,作為紅軍基層政治工作干部的他們,當時是不可能對一位他們此前并不了解的友軍最高領導人作輕率評議的。

張國華,時任紅六團總支書記,化林坪戰斗的參加者
另外,這本《長征日記》還有諸多極不可靠的“記錄”,直接誤導了一些地方黨史部門。比如,該日記稱:紅一師是由寶興經隴東翻越夾金山直接進抵懋功的,沒有經過磽磧,[11]此說亦為當地黨史部門及很多史籍采信,甚至載入了雅安、四川等地地方和省級黨史部門編纂的長征史志。筆者根據《李聚奎回憶錄》、《耿飚回憶錄》、《楊得志回憶錄》及此間軍委部署文電等多方查證,此說不能成立!中央紅軍翻越夾金山只有一條路線,即由寶興經磽磧,翻越夾金山王母寨埡口進至達維。紅一師緊隨紅二師之后,都是翻越王母寨埡口,經達維而轉向懋功的。
另一個“猛料”出自覃應機的回憶錄《硝煙歲月》。覃老先生在這部回憶錄中稱,時任紅三軍團第十三團偵察連政治指導員的他和連長韋杰一起,在團長彭雪楓指揮下率領本連十二名勇士奪取了瀘定橋——文中還提供了那十二名勇士中大部分人的姓名,以及彭雪楓的指揮位置“天主教堂”。[12]這段文字也使某些人士大為興奮,并為此添油加醋炮制了出了如“黃(開湘)彭(雪楓)爭功秘聞”這樣的離奇文章來……
其實這個問題仍然是非常容易證偽的:這幾天中革軍委的部署文電都明明白白地標示了紅三軍團每日進止位置。紅三軍團在中央紅軍左縱隊(西岸)行軍序列中屬于“倒數第二”位置:他們前面是軍委縱隊,軍委縱隊前面是紅五軍團,紅五軍團前面是紅一軍團……覃老先生所在的紅十三團與紅一軍團前衛紅四團在行程上形成的時間差,至少也在兩個晝夜以上!奪橋戰斗發生時,紅十三團距離瀘定橋還有二百多里,當然也就完全沒有參加這場戰斗的可能了……
不過,筆者在詳研了中央紅軍在這段日子里經歷過的戰斗后認為,《硝煙歲月》爆出的這個“猛料”應該不屬于“刻意編造”,而的確是因作者本人當時的文化、視野局限所產生的“認知錯位”:瀘定橋戰斗一周后紅三軍團進抵了天全河畔,中革軍委賦予了他們“奪取天全之龍衣、沙壩頭兩鐵索橋,并相機襲占天全的任務”[13],而這兩個地方中的沙壩頭索橋附近(與瀘定橋附近的沙壩村同名)也的確發生過戰斗[14]。當年文化程度不高的覃應機老先生很可能把這次戰斗與瀘定橋戰斗弄混淆了。長征中紅軍跨越雄關險道無數,雖然大渡河上只有這么一座鐵索橋,但他們經過的其他鐵索橋其實還是很多的——特別是在云貴川康地區,只不過不像瀘定橋那么有名罷了!
筆者對紅軍方面這些惹出了諸多是非的“猛料”進行認真辨析,并不是為了顯擺紅四團的功勞而貶低其他部隊的作用,而是恰恰相反!比如,紅一師對瀘定橋之戰的勝利所起的作用那就是絕對不可抹殺的:紅一師在東岸前進途中遭遇的是川軍第四旅袁鏞部的主力,紅一師以堅決頑強的戰斗打垮了敵人的主力!迫使瀘定橋守軍陷入了前后受敵的窘迫處境,大大地震撼和動搖了瀘定橋守敵的守橋信心,迫使他們在戰斗的重要關頭作出了無可奈何的選擇!這極其有力地配合了西岸部隊的奪橋戰斗——這也是紅四團能夠順利奪橋的重要原因之一!瀘定橋戰斗的勝利是中央紅軍左右兩個縱隊夾河而進這兩個進取矢量的合成效果!時任紅二師政治部干事并隨紅四團行動,參加過瀘定橋戰斗的王東保將軍后來也說:“奪取瀘定橋沒有一師也是不行的,兩路夾擊,敵人被迫逃竄[15]”。

李聚奎,紅一師師長,化林坪-飛越嶺戰斗指揮員之一
還有,李聚奎所率紅一師一部在占領龍八埠后又轉向東進,繼續向化林坪、飛越嶺方向發展進攻,并于30日占領鹽水溪,為中央紅軍爾后打開這條脫離大渡河上游峽谷的通路,又墊上了一個起跳的臺階。隨后趕到的紅一團(31日左右趕到龍八埠)也參加了進攻化林坪、飛越嶺的戰斗,而軍委干部團主力此間一直在東岸節節阻滯跟進的的川康軍部隊,6月2日左右才趕到龍八埠。他們都沒有到過瀘定橋,但他們的功勞苦勞也應該是不可忽視的——大渡河之役并不是以奪取了瀘定橋而畫上句號的!
如果不盡快脫離這條狹窄的險峻河谷,中央紅軍的處境照樣非常危險!
中革軍委首長們前往瀘定橋的途中,就已經在作這樣的考慮了。
六、橋有了,路何在?
5月30日22時,中革軍委作出脫離大渡河上游峽谷的部署:
林、聶、劉、彭、楊、董、李、羅、何、左、劉、陳、宋、鄧、蔡:
A.我一軍團先頭部隊昨已攻占瀘定橋,敵向天全退。劉敵約一旅昨向巖子上我干部團陣地攻擊,并迂回我右側高山,我干部團退守鋪沙崗。
B.我野戰軍以迅速過河集中天全地域、尋求作戰機動之目的,定明三十一日開始行動如下:
⒈一軍團(缺兩個團)應向天全(瀘定橋至天全二百四十五里)前進,行程可走七十至八十里,在門坎上、昌河壩、兩路口之線,并偵察天全方向敵情及其附近地形、人家、給養條件,電告軍委。二師應留一個團并帶電臺在化林、龍八布之線繼續警戒,以掩護干部團北進。劉參謀長則留瀘定橋待歸總部。
⒉五軍團仍歸林、聶指揮,其主力應經瀘定橋跟一軍團后跟進,宿營地點由林、聶規定。五軍團應另留一個營,以主力在瀘定橋西岸前出至二里[壩]向康定警戒,以一個連監護鐵索橋。
⒊軍委縱隊前進至瀘定橋、沙壩之線。
⒋三軍團進至芝泥壩、楂維、科五之線。
⒌第五團應趕至摩西面[16]。
⒍九軍團、游擊隊及干部團第三營均歸羅、何指揮,進至灣東、施藥坪之線。
⒎干部團(缺第三營)沿河北岸進至德拖地域,向來路嚴密警戒,并扼阻追敵。
C.各部須沿途補充糧米。
朱
三十日廿二時[17]
這個部署是在什么地方作出的?有關史料各說不一,筆者考據起來很費了一些功夫。
據時任軍委三局政治委員的伍云甫日記記載,軍委縱隊從灣東進至磨西面后休息了幾個小時后繼續出發,5月30日晚宿磨杠嶺東麓的奎武村。[18]毛澤東當時的警衛員陳昌奉、闕中一則回憶說:5月29日毛澤東在磨西面宿營,30日凌晨4時從磨西面出發去瀘定,“出發后就接到通訊員送來的捷報,說瀘定橋已經打下了”。當日下午4時左右,毛澤東等到達瀘定橋,并在沙壩村天主教堂外的一棵大樹下聽取了紅一軍團首長匯報的戰斗情況,因為天主教堂里住著傷員,毛澤東等沒有進教堂而只是在樹蔭下休息幾個小時……[19]
陳昌奉還回憶說,毛澤東沒有在瀘定城里住宿,而是直接去了化林坪。[20]
這個回憶說到這兒可能就有點問題了,從行程上看也不太可能:從磨西到瀘定橋約120里,毛澤東等凌晨出發能在當日下午到達,那就已然算是“收早工”了。在瀘定休息兩小時后還要繼續趕路到化林坪,那就還得跑七八十里山路——還得走夜路,這番鞍馬勞頓實在是有點大了去了不說,而且毛澤東他們那天根本就進不了化林坪!——那天紅一師一部跟追川軍第四旅第十一團楊開誠部殘部占領了鹽水溪,然而在向化林坪仰攻時受挫,所以這天晚上化林坪的主人仍然還是川康軍第四旅第十團上校團座謝洪康。
更重要的是,這個回憶與30日22時中革軍委作出的那個部署內容,不洽。毛澤東等不可能在那個部署還沒有改變之前,就貿然奔另一條道而去!如此,筆者或可確認:30日晚上毛澤東等應該是住在瀘定或瀘定附近——而且還不止住一天,而中革軍委30日22時的部署,有可能是那天在磨西與灣東趕來的軍委縱隊會合后一起行動的朱德總司令等中央首長作出的。[21]不過這并不意味著這個部署是朱總司令的個人意圖——這個意圖很可能是這些領導人當天碰頭會上共同商量后確定的。
這個部署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標示了中央紅軍脫離大渡河上游峽谷的路線——實際上也就是瀘定守軍李全山團的潰逃路線:紅一軍團為前衛,由瀘定經四灣、五里溝,翻越馬鞍山,進至門坎山、長河壩、兩路口[22]一線,紅五軍團隨后跟進……
而就在毛澤東等到達瀘定橋之前的30日上午時分,林彪、聶榮臻、劉伯承等前方首長就已然作出了一個與朱德總司令當晚22時部署意圖有所不同的“臨機措置”:紅六團當日由瀘定出發,趕赴龍八埠、鹽水溪,與李聚奎所率紅一師一部相互配合,攻占化林坪。陳光率紅二師主力亦隨后跟進,打通化林坪—飛越嶺這條“川康要道”。[23]
時任紅六團政治委員的鄧飛老人回憶道:
我團剛剛進到瀘定城休息,就收到了團偵察員送來的情報。情報說:敵軍在冷磧、龍巴鋪(今興隆),化林等地有兩團的兵力駐守.為了阻擊紅軍北上,敵軍在瀘定橋一帶布防一個旅三個團,是新五師第四旅,旅部駐在龍巴鋪。三十八團駐瀘定、咱里、盆道一帶,團長李全山,已被紅四團于奪取瀘定橋后擊潰。十一團駐冷磧、海子山一帶,團長楊開誠,亦被右路紅軍紅一師擊潰,退往龍巴捕。十團駐龍巴鋪、化林坪、飛越嶺一帶,團長謝洪康。以上敵人均屬于國民黨二十四軍劉文輝部。
由于四團已經完成了奪取瀘定橋的重要任務,所以我們意識到我團即將擔負前衛任務。我和朱水秋團長商定,要各營連抓緊時間吃飯、休息。并要帶一頓飯,等候命令,準備出發。早晨八時,我們接到騎兵通訊員送來的師長陳光、政委劉亞樓的手令:
“朱、鄧:你團進至瀘定橋后迅速吃飯,稍加休息,于上午十時出發,經冷磧、龍巴鋪、化林坪、飛越嶺向天全前進。中途遇敵應堅決消滅或擊潰之。我師指揮所和五團隨你團后跟進。我野戰軍主力隨后也從瀘定橋通過。”
五月三十日,遵照師首長的命令,我團按預定時間出發。
我們采取了戰備行軍隊列——非戰斗人員由供給處主任胡弼亮率領,在全團的后面跟進。戰斗人員的行軍次序是:一營、團部、三營、二營。政工人員分別下到各營,團的黨總支書記張國華和一營長曾保堂同前衛一連前進,時刻做好打仗的準備。那一天是陰天,我團全體指戰員步履匆匆先后經過了大壩、瓦窯崗、挖腳、甘露寺、幸福壩、向陽坡于下午三點多鐘接近冷磧。這時,天空下起小雨。[24]
鄧飛的這個回憶也有一個問題:左權、劉亞樓率紅五團還在沿大渡河西岸趕赴瀘定的路上——中革軍委當日22時部署中要求他們31日到達的位置是“磨西面”[25],所以鄧飛得到的這個“手令”只能是師長陳光一人簽署,而且手令中的“五團”應為“四團”,“天全”應為“漢源”。
史載:30日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們還在瀘定召開了一個碰頭短會。
會議決定兩件大事:
“㈠中央紅軍將走雪山一線,避開人口稠密地區;
㈡派陳云去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26]
會后不久,陳云由當地地下黨組織護送,經成都、重慶前往上海。
陳云到上海后,使用“廉臣”的筆名,假托一個被俘國民黨軍醫的身份,撰寫了《隨軍西行見聞錄》一書,在中國共產黨駐巴黎黨組織辦的《全民月刊》上發表,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單行本,向海內外介紹和宣傳了紅軍長征的偉大業績。同年10月15日,陳云又在共產國際書記處執委會會議上作了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報告。

在這兩份歷史文獻中,都將安順場和瀘定橋發生的戰斗作為典型事例道出。[27]
同一天里,蔣公也通過劉文輝的報告得悉了瀘定發生戰事的信息,但對“匪之動向”的判斷卻與中央紅軍方面的意圖大相徑庭:“昨日朱匪已到瀘定攻城,其主力必出丹巴乎”,而且認定“朱毛殘匪之末路不出三途:⒈由康北經青海甘州竄內蒙。⒉由康定丹巴入川西,與徐匪會合后,經松潘西區入甘肅臨潭縣或西固或定西靖遠出寧夏。⒊由川北經嘉陵江、昭廣、隴東出寧夏以至內蒙。以俄寇與第三國際決令其入藏或入新疆。彼為本身利害計,不愿引起世人之注目也。”[28]。
蔣公和劉自公在信息掌控方面的滯后實際上也是可以理解的:瀘定守軍最高長官李全山與其上司袁鏞的最后一次通電話是在5月29日16時左右——也就是紅四團發起奪橋戰斗和紅一師一部進攻第四旅旅部所在地龍八埠之時,而后電話即被中斷,瀘定守軍也與第四旅旅部失去聯系。所以川康軍第四旅旅長袁鏞,乃至當日午后才進至漢源縣城(今清溪鎮)的劉文輝,當天得悉且能確認的信息也只能是兩岸紅軍正分別在瀘定橋和海子山與袁旅部隊激戰中,而并不知道瀘定橋實際上已于當晚失守且李團主力正經過馬鞍山撤向天全。[29]而最高統帥蔣介石得悉此事的時間當然更為滯后——他是在30日晚上才得悉這個信息的,而且同樣不知道瀘定橋日前就已更換了主人。[30]
31日,朱德等率軍委縱隊到達瀘定橋與毛澤東會合后,應該掌握了更為詳盡的道路信息:馬鞍山小道崎嶇難行,“秋冬春三季積雪”[31],連牲畜都難通過,沿途人煙稀少,大部隊就糧非常困難,只有那些買不起騾馬的腳伕們才背負茶包往返此間[32]。而經化林坪、飛越嶺那條“川康要道”的情況則相對要好得多,這條道至少還能行騾馬,而且一出飛越嶺就可以直下宜東,威脅漢源縣城(今漢源縣清溪鎮)……
當晚22時,中革軍委致電各部首長,同意了林、聶、劉日前的“臨機措置”:
我野戰軍以攻占化林坪,迅速前進清溪,各個擊破兩劉(劉湘、劉文輝)部隊約三個旅,并迅速控制富林渡口,拒阻中央軍北渡之任務,定明六月一日行動如次:
一軍團(缺第五團)及五軍團于攻占化林坪后即戰備前進至坭頭地域,并準備二號攻占清溪,以一部續向富林前進;軍委縱隊進到化林坪;三軍團趕到甘露寺、瀘定橋之線,并全部渡河完畢;九軍團等部趕到魁五、磨西面之線。[33]
這個新的部署還對中央紅軍脫離大渡河上游峽谷的路線作出了改變:取消紅一軍團經馬鞍山去天全的行動,紅一軍團乃至中央紅軍主力將經化林坪、飛越嶺東進至漢源(今清溪)及富林地區,以“拒止中央軍北渡”——與蔣公互換一下攻守的角色。這一來可能是抱有在繼續北進前拿下漢源城(今漢源縣清溪鎮)以獲得物資糧草的打算,二來也是因為計較著中央軍追兵臨近的日程,準備將其拒止于大渡河南岸而贏得從容轉向北進的空間與時間:中央紅軍奪取了瀘定橋的信息這幾天肯定會送達蔣公耳中,蔣公有可能會更加嚴厲地督促中央軍各部加快“跟追”的步伐,以求壓迫中央紅軍在大渡河上游峽谷地域以“根本剿滅”!而“朱毛”的這番盤算真還不是沒有一點道理——就在“朱毛”作出這個部署的當天,蔣公真就給薛岳發出了一個旨在“加快步伐”的“世巳手令”:
薛總指揮:
一、殘匪艷午已到瀘定與我守城劉部激戰中。
二、大樹堡之匪全向瀘定退竄。
三、楊森部正向安順場上游推進中。
四、匪蹤既明,我軍前進不須如前日各電之持重,應令李抱冰縱隊除酌留防守冕寧守城部隊之外,其余直向康定急進。兄率其余各部經越嶲至大樹堡候令。對于德昌、西昌不必留隊防守,惟在越嶲須酌留一二團兵力候令再撤。切盼灰日(6月10日)以前能到達大樹堡集中,如何!
中正,世巳手令[34]


[圖5-6-1:蔣介石5月31日手令影印件1;圖5-6-2:蔣介石5月31日手令影印件2(均占半幅)]
看來這一天里蔣公瞅明白了“朱毛”的動向,恐怕也瞄出了劉自公那幾個雙槍兵肯定擋不住“朱毛”沖過大渡河向“徐匪”靠攏的苗頭,所以才令第五十三師李韞珩部不再“穩進”而是經大渡河上游峽谷向康定“急進”,同時也令薛岳部主力集中在“寧雅正道”方向,準備壓迫“朱毛”于他自己已然扯松了的那條口袋的袋底——“名山、蘆山、天全、雅安”地帶,與前來接應的“徐匪”一起打包處理,予以“聚殲”。
與蔣公初衷不同的是,直到這會兒,他仍然在“隨匪轉移”,毫無主動性可言!
站在“剿共”的立場,他老人家當年給薛岳開出的時間表尤其令人沮喪:6月10日(灰日)將主力集中于大樹堡。而薛岳按這個手令作出的部署則是:“吳縱隊歐(震)師江日(6月3日)從西昌出發,虞日(6月7日)到越嶲,此后經海棠、平夷鋪[35]、富林,限元日(6月13日)追達漢源(今漢源縣清溪鎮)。梁(華盛)師支日(6月4日)由西昌出發,循歐(震)師經路前進,限寒日(6月14日)到達漢源(今漢源縣清溪鎮)”,“周(渾元)部除萬(耀煌)師留一旅駐西昌,分派一團駐瀘沽,建碉守備,維護交通外,其余魚日(6月6日)由西昌出發,經越嶲循吳(吳奇偉)部經路,限銑日(6月16日)到漢源”,“本部及周旅,微日(6月5日)由西昌出發,經越嶲在梁師后跟進,刪日(6月15日)到漢源”。[36]
這將帥倆,還在按部就班地挪棋子兒啊。
而“朱毛”這邊的動作,就麻溜多啦!
不麻溜也不成,他們得趕緊脫離大渡河上游峽谷,否則危殆處境依舊。
注釋
[1]肖鋒:《長征日記》第82~第8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2]《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第72~第73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3]《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第72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4]肖鋒:《長征日記》第82~第8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5]肖鋒:《十年百戰親歷記》第183~第185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6]鄧華:《鐵絲溝戰斗》,《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劉統整理注釋)第36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7]《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第54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8]該電原件存中央檔案館。雖然原始文獻電報作為史證的確有較高權重,但也不是絕對不會出問題,特別是在倉促間很難掌握全面可靠信息的情況下——筆者遇到的相類的情況還有很多。
[9]肖鋒:《十年百戰親歷記》第185~第18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10]鄧飛口述,文有仁記錄:《紅六團過瀘定》,《瀘定縣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第57頁。
[11]肖鋒:《長征日記》第87~第8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12]覃應機:《硝煙歲月》第62~第63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13]《朱德關于我軍突破敵雅州、蘆山、天全防線的部署(1935年6月5日2時30分)》,《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6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4]《于無聲處咱驚雷——紅軍長征第一次過天全》,《天全文史資料·第1輯》第1頁。
[15]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紅軍長征革命歷史調查小組王永模、文榮普1975年9月18日訪問王東保記錄,王東保時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長征時曾任紅二師政治部干事),瀘定縣紅軍紀念館存檔。
[16]磨西面:今磨西古鎮的古稱,海螺溝冰川風景區入口。
[17]《朱德關于我軍迅速通過大渡河向天全地域集中的部署致各軍團電(1935年5月30日22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61~第36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8]《伍云甫日記》,《紅軍長征日記》第195頁,檔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19]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紅軍長征革命歷史調查小組王永模、梅俊懷、文榮普]1975年8月7日訪問闕中一記錄;1975年8月29日王永模、梅俊懷、文榮普訪問陳昌奉記錄,瀘定縣紅軍紀念館存檔。
[20]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紅軍長征革命歷史調查小組王永模、梅俊懷、文榮普1975年8月29日訪問陳昌奉記錄,瀘定縣紅軍紀念館存檔。
[21]根據時任軍委三局政委的伍云甫日記記載,1935年5月30日晚,軍委縱隊在奎武宿營(《紅軍長征日記》第195頁,檔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朱德年譜·上》(新編本)第501頁亦稱,朱德5月31日與軍委縱隊一起抵達瀘定縣城(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22]門坎上,即門坎山的音譯;昌河壩,即長河壩的音譯;兩路口,今名新溝。位于二郎山東麓。
[23]鄧飛口述,文有仁記錄:《紅六團過瀘定》,《瀘定縣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第57頁。
[24]鄧飛口述,文有仁記錄:《紅六團過瀘定》,《瀘定縣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第57頁。
[25]《朱德關于我軍迅速通過大渡河向天全地域集中的部署致各軍團電(1935年5月30日22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6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6]《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496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27]廉臣:《隨軍西行見聞錄》,《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劉統整理注釋)第41~第43頁;陳云:《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報告》,《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劉統整理注釋)第10~第1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28]《蔣中正1935年5月30日所擬“注意”事項》,《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臺灣]高素蘭編著)第170~第171頁,國史館2008年11月初版。
[29]《劉文輝轉報袁鏞稱殘匪到達瀘定橋向李團猛撲均未得逞等情致蔣介石電(1935年5月29日未時于漢源[有線電報發出])》,[臺]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300-00030-022;《劉文輝轉呈袁鏞稱瀘定橋李團與沿河之匪奮戰等情報致蔣介石電(1935年5月29日戌時于漢源)》,[臺]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300-00030-021。
[30]根據1935年6月3日劉文輝派人向李全山“探送”令李團回防雅安的命令可知,李團沒有配備電臺(《川軍二十四軍川康邊防步四旅急調李紹云團進駐雅安電(1935年6月3日)》,《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四川部分》第160頁,檔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31]任乃強:民國川邊游蹤之《瀘定考察記》第25頁,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32]高上佺:《二郎山公路選線的由來》(《天全文史資料·第3期》第19頁)稱:由天全到瀘定的行人都是走的翻越馬鞍山的山路。其山懸巖峭壁、路陡難行。尤其冬季大雪滿山,山頂的雪鍋崗積雪滿山,路又很窄,行人稍有不慎,即落入幾丈深的雪窖?中,直待第二年夏季雪化時始能見到尸體。翻山后還須經過二十四盤,坡陡路窄,人行其間,如在走壁,一般視為畏途。
[33]《朱德關于攻占化林坪致各軍團、軍委縱隊及干部團首長電(節錄)(1935年5月31日22時)》,《朱德年譜(1886~1976)·上》(新編本)第50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34]賀國光編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大事記》第168~第169頁,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圖書館1986年9月翻印。
[35]又名平彝堡,古地名,今名平等村,位于今漢源縣河南站與大灣之間。另有一平夷堡者,位于今峨邊縣金口河地區。
[36]薛岳編:《剿匪紀實•滇黔川南追剿》第67~第68頁,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雙石:“耳熟能詳”背后的“不為人知”——從國民黨軍檔案透析紅軍強渡大渡河成功后的“骨牌效應”
2020-06-09白晨皓|國民黨眼中的大渡河戰役:劉文輝說,共產黨找上我這窮光蛋,拼也完,不拼也完
2020-04-23臺灣果國史館公布關于1935年大渡河之役的一批檔案成了打臉利器
2019-03-01?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