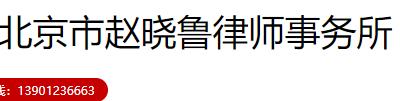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7日-星期一
張維為:西方爭辯“文明型國家”
點擊:5179 作者:張維為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22-10-03 11:07:38

“‘文明型國家’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比較強勢的中國話語,它對西方‘民族國家’觀念是一種‘范式解構’和‘降維打擊’。”
“為什么同樣擁有著古老文明的埃及、印度沒有最終形成一個‘文明型國家’呢?”
“你看湯因比對不同文明的論述,他曾經反復地講,如果我還能夠繼續活,我愿意活在中國。”
“文明型國家”這一政治敘事正被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和國家所關注,西方內部也有不少學者開始關注并爭論。在東方衛視9月26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61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上海社科院宗教所宗教學研究室主任邱文平老師一同探討了西方對“文明型國家”這一概念的關注。
“一個幽靈,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幽靈,正在自由主義西方徘徊。隨著美國政治力量的減弱和道德權威的崩潰,歐亞大陸崛起的挑戰者采用文明型國家模式,以區別于日益癱瘓的西方自由主義秩序。”
“中國學者張維為審視著衰落的西方,冷靜地指出: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并能通過現代國家的轉型,那么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這只能是一種推演和假設。”
“文明型國家”今天成了時髦概念,中國學者宣布中國是唯一的文明型國家,而不是那種已經過時的19世紀的民族-國家。俄羅斯總統普京也跟著中國(hopped on the bandwagon)宣布,俄羅斯作為文明型國家的特質使其免于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解體。印度正在爭論自己是否是文明型國家。文明型國家的候選國還包括土耳其、美國,甚至歐盟等,這個名單還在擴大。
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的“文明型國家”,我們倒是可以回頭來看看西方的觀念,看看所謂由傳統的“文明-國家”進入“民族-國家”才能成為現代國家這種西方觀念的局限性和破壞性:這種觀念帶來的結果往往是國家不停地分裂,越分越小,每次分裂都會造成許多流血沖突。且不提歷史上數百年的廝殺,單是過去數十年中發生的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崩潰、今天印度內部紛亂不斷的情況,某種程度上都反映出西方“民族國家”觀念的偏執性。
“歐洲整合談何容易,畢竟歐洲已經分裂了上千年。歐洲整合也已進行了半個多世紀,但其整體實力還是面臨嚴峻挑戰。如果歐洲國家無法真正聯合起來,歐洲的總體衰退的命運將難以扭轉。所以我們應該為我們自己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感到自豪。”
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這些新興經濟體不僅是經濟強國,如一些人所述,他們認為自己是‘真正的文明型國家’……他們確實擾亂了我們的國際秩序,影響著經濟秩序,重塑著政治秩序。……但他們比今天的歐洲人具有更多的政治靈感,他們有一套我們歐洲人某種程度上已經失去的真正的邏輯、哲學和想象力”。




(主講嘉賓:張維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邱文平,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上海社科院宗教所宗教學研究室主任。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東方衛視”)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責任編輯:紅星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建言點贊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