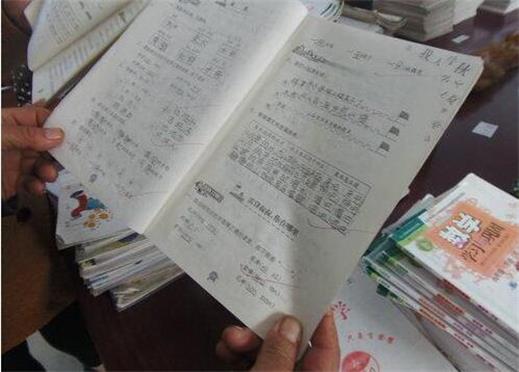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1日-星期四

對14億中國人來說,中國高新技術必須自主自立,已是根本性的共識。
這一點從最新出爐的“十四五”規劃到社交媒體上極其廣泛的討論,都有著直接體現。也因此,舉全國之力,無論是高等院校、國有科研院所還是技術型企業,都在加大對基礎科研的投入力度。
一、心臟病和神經病
石墨烯的發現者、2010年諾貝爾物理學家得主安德烈·蓋姆近期說過一句話:“中國的應用科學世界第一,但基礎科學還在追趕之中。”

英籍科學家安德烈·蓋姆出身在前蘇聯,父母均為德國人。
這位對中國十分友好的教授是中國科學院的外籍院士,他委婉地指出中美之間的科技差距主要存在于基礎科研層面,但卻沒有告訴我們,基礎科學發展彎道超車的概率極低。
作為一個幸運兒,蓋姆從發現石墨烯到獲得諾獎,只花了不到7年時間,但大部分基礎科學獲獎都需要20年、30年甚至40年的時間。諾獎對研究發現的認可時間,客觀上也表明了基礎科研所要消耗的時間:這并不是一個可以輕易追趕的領域。
已經離世的前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長張國寶曾提到:“中國的裝備制造業有‘兩個病’,一個是‘心臟病’,一個是‘神經病’。‘心臟’就是發動機,比如飛機的發動機(以及芯片);‘神經’是指機械設備里面的控制系統。”
張國寶說這話的時候是在2011年。彼時,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日本不久,此后數年,隨著中國硬件創新能力的持續增強,中美經濟總量差距的不斷縮小,相當多的中國人陷入了“G2”的幻象。

張國寶退休后撰寫的《篳路藍縷》一書,詳細回憶了重點工程決策建設的過程。
直到中國高科技代表企業華為被美國政府用一系列爭議手段進行斷供、封殺,“芯片”短缺的問題才被瞬間放大,張國寶所提到的“心臟病”又回到大眾視野。
事實上,從研發投入的數據來看,中國已經在加速追趕階段。2019年,評估各國創新最重要的指標R&D 經費投入總量,中國為22143.6億元,比上年增加2465.7億元,首次突破2萬億元。
此外,2019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為1335.6億元,占R&D經費比重為6.03%,比上年提高0.49個百分點,這也是我國基礎研究占比首次突破6%。
R&D經費總量首次破2萬億元,位居世界第二,并接近歐盟15國水平,基礎研究占比首次突破6%,都意味著,中國基礎科研已經達到了一個關鍵節點。

圖片來源:國家統計局
就在這個關鍵節點,中美科技開始脫鉤。
正如眾多國際關系專家所分析的,華為事件的發生,恰恰是中國基礎科研投入不斷增加,并且在一些領域開始呈現追趕之勢的背景下所發生的。從2015年開始,美國的精英階層逐漸開始出現科技封鎖中國的呼聲,并在特朗普上臺之后得到加速實施。
也是在2018年,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明確要加大中央財政對基礎研究的穩定支持力度,構建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機制,引導鼓勵地方、企業和社會力量增加基礎研究投入。
這份《意見》直白地指出:我國基礎科學研究短板依然突出,數學等基礎學科仍是最薄弱的環節,重大原創性成果缺乏,基礎研究投入不足、結構不合理,頂尖人才和團隊匱乏,評價激勵制度亟待完善,企業重視不夠,全社會支持基礎研究的環境需要進一步優化。
二、自由派與進取派
無論是“李約瑟之問”還是“錢學森之問”,回應上述兩個世紀之問時,大部分答案都會落在“大學該如何辦”上面。
這里的邏輯接近高等教育辦好了,我們的科研就上去了,繼而華為就不會被美國卡脖子了。但實際情況很可能是反過來,當企業給予科研更多的投入,與高校一同協作,才能更好地布局基礎科研。
在前文提到的《意見》中,提到了“建立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機制”和“促進科技資源開放共享”兩個方面,而這兩點都指向企業進一步參與基礎科學研究。
對于處在中美科技角力一線的華為、騰訊和阿里來說,它們也的確比大學和國有科研機構更有動力地去回應危機,去解決問題。
而從企業投身基礎科研的歷史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兩條路徑:一是以大名鼎鼎的貝爾實驗室為代表的“自由派”,二是以英特爾、華為為典型的“進取派”。
身為美國最大的科研機構之一,貝爾實驗室為推動美國科技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僅僅看數據就可以管中窺豹:85年的時間里,實驗室產生了近3萬項專利——幾乎每天1項專利,11位科學家問鼎7項諾貝爾物理學獎,并榮膺9項美國國家科學獎、8項美國國家科技獎等。

貝爾實驗室的科學家,攝于1947年12月。
貝爾實驗室興與衰,幾乎可以歸結為同一點,那就是“自由放任”。對于科研工作者來說,貝爾實驗室就是他們的伊甸園,借助強大的經濟能力,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可以像“搞藝術”一樣搞科研,全身心投入其中,待遇優厚不說,大量的行政事務也被外包。
關鍵性的發明和創造,在實驗室內部也被鼓勵“自由交流”,這使得實驗室提供了一個最大程度開放的學術探討平臺。對于其他科研人員來說,這是極其迷人的,甚至是無法拒絕的。
但與此同時,因為要維持科研人員的充分自由,向四面八方散開的科研議題和成果無法有效回歸企業的基本面。一定程度上,貝爾實驗室承擔了極強的公共職能,卻最終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因為成本過高無法維持現狀而不得不走向衰落。
貝爾實驗室的衰落,可以說是“經濟理性主導企業科研”的必然后果。針對貝爾實驗室“自由派”風格的弊端,以英特爾、華為為代表的的企業,則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即更符合經濟理性,可以稱之為“進取派”。
“進取派”企業投入基礎科研更有目標感,即便愿意資助一些超出現有應用范圍的科研,最終也會確保科研成果落在自己搭建的盤子上。
以英特爾中國研究院為例,它成立于1998年,目前由六大團隊組成,包括機器人系統研究實驗室、機器人交互研究實驗室、認知計算實驗室、智能存儲實驗室、通信架構實驗室和新技術中心。
可以發現,這些實驗室主攻人工智能技術、智能自主系統和智能互聯基礎設施研究,聚焦的目標高度重合。
英特爾還與世界各大一流大學形成合作機制,它與卡內基梅隆大學合作云計算,與南加州大學合作視覺&經驗計算,與清華大學合作移動通信與網絡,與以色列希伯來大學合作計算智能等等。
華為的做法與英特爾類似,著名的諾亞方舟實驗室設立在香港科學園,實驗室主任由香港當地大學教授出任,并聘用內地和全球其他地區科研人員從事基礎研究工作。

設在中國香港的華為諾亞方舟實驗室,成立于2012年。
此外,華為在全球設有16個全球研發中心,28個聯合創新中心,并網羅了大量頂級科學家加入華為的科研網絡。
2020年5月,任正非在回應996工作制時提到“少數科學家、少數特別高端的人員……他們經常去櫻花的國家在樹下開會,在法國熏衣草叢中開學術會,半休息、半開會、半聊天……”實際上也表明,華為與科學家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
“進取派”的做法符合經濟理性,但人類常常高估自己的理性,畢竟歷史上許多著名的發現其實不是“計劃的”,而是“發生的”。貝爾實驗室鼓勵科學家自由探索,有其存在的價值,這一點并不能因為該模式不可持續,而被全部放棄。
二、第三條道路:共享派
在自由派和進取派之間,是否存在企業投入基礎科研的第三條道路。現在看來,這條道路已經顯示出一些端倪,其代表企業為騰訊。
2013年,騰訊在贏得3Q大戰慘勝3年之后,以“開放”之名義推出了“WE大會”。WE——Way to Evolve,意為進化之路。
盡管這看起來是一個高端科普活動,類似溫伯格、霍金這樣的頂級理論物理學家都在WE大會上發表過演講,但WE大會的意義在于建立起中國科學家、普通民眾和世界前沿科學探索者之間的聯系,更重要的是,背后的組織者毫無商業意圖。

2013年首屆WE大會的宣傳海報。
首屆WE大會上,馬化騰在演講時說,“這次論壇沒有談及商業或者公司之間的競爭,這與我過去參加很多的論壇非常不一樣。我們談的是未來如何用科技改變人類生活,如何解決我們可能現在想不到的未來的很多問題。”
6年之后,在楊振寧、饒毅等人的介入下,騰訊發起了“科學探索獎”,以每年1.5億元的資金規模,支持50位45歲以下的中國青年基礎科研工作者,每人可以分5年獲得300萬元稅后資助。

2019年科學探索獎獲獎者合影
與諾獎關注已有成就不同,“科學探索獎”的特點是“面向未來”,所資助的科學家分布在數學物理學、生命科學、天文和地學、化學新材料、信息電子、能源環保、先進制造、交通建筑、前沿交叉等9個具體領域。他們中以大學老師為主,也不乏其他社會機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按照資本市場的邏輯,一個科學家拿到諾獎等于上市的話,那么拿到“科學探索獎”則相當于拿到了風險投資。諾獎更像是對一個科學家的肯定,而科學探索獎則希望紓解獲獎者的實際困境。
豐厚的資助額度,寬松的用途規定,對青年科學家學術共同體的促成和搭建,使得科學探索獎一定程度上繼承了貝爾實驗室的衣缽。
更值得一提的是,與貝爾實驗室的科研成果惠及全體人類有關系,科學探索獎資助的科學家并不需要對資助者負責,其科研成果最終落在科技行業、中國社會乃至全體人類的盤子上。
基于此,第三條道路可以稱之為“共享派”。
“共享派”的做法在企業界缺乏參照對象,但可以與洛克菲勒基金會進行對比。上世紀20年代,洛克菲勒曾經以750萬美金的天價支持了協和醫學院的建設,至今,協和醫科大學依然是中國最好的醫學院。
2018年,馬化騰等人發起了“西湖大學”的資助,首任校長施一公表態要把“西湖大學”打造成中國的“加州理工”,此豪言狀語雖然不容易實現,但其路徑是類似的。
此外,從20世紀20年代到1959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投入到分子生物學上的資助高達5000萬美元。據統計,從1954年到1965年的11年間,共有18位科學家因從事分子生物方面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獎學金,其中有15位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
“科學探索獎”是否參考過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方式,筆者不得而知,但用“天使投資”的做法來資助青年科學家,既對資助方的篩選能力提出了超高要求,也往往可以獲得極高的回報率——雖然受益者并非是企業本身。

第二屆“科學探索獎”獲獎名單
今年是WE大會的第8年,科學探索獎的第2年。本質上,科普教育和基礎科學研發都是一門時間的藝術。信息領域的“摩爾定律”和互聯網創業上的“幾何級增長”現象,在上述兩者的發展軌跡中都沒有施展空間,從洛克菲勒到馬化騰,他們都必須明白等待的價值。
回到中美科技競賽的主題,科研交流的黏性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與生活水平、衛生觀念一旦提升之后難以下降非常類似,跨國學術交流很容易“上癮”。一旦有過密切交流,“科學無國界”的召喚就會在無數科研工作者內心生根發芽。
從這一層面出發,“共享派”應該向“自由派”和“進取派”學習,將資助的范圍擴大至全球,歡迎全球的青年科學家為中國科技企業所資助,這應該是一個繼續發力的方向所在。
可以預見,當中國企業資助多位他國學者獲得諾獎之際,“科學探索獎”的價值也就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體現和放大,中國基礎科研的實力也一定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
參考文獻:
1. 《世界主要國家近10年科學與創新投入態勢分析》2018 姜桂興 許婧
2. 《美國企業基礎研究投入情況分析》王煉 《全球科技經濟瞭望》2018年11-12月號
3. 《中國企業研發投入現狀與問題研究》 玄兆輝 呂永波 第6 期 《中國科技論壇》 2013年6月
4. 《我國企業研發投入現狀及問題分析》 張春穎 尹麗娜 《長春大學學報》2018
5. 《發達國家促進財政科技研發投入的經驗與借鑒》 李方毅 《科技管理研究》 2015
6.《篳路藍縷——世紀工程決策建設記述》 張國寶,人民出版社2018
(來源:“瞭望智庫”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網】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現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絡時代發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