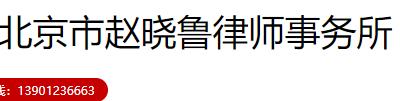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4日-星期日
白桂思原著中諸多攻擊中國(guó)主權(quán)、煽動(dòng)中國(guó)邊疆地區(qū)“獨(dú)立”的狂悖之言,在中譯本里均被節(jié)譯、改寫(xiě),甚至直接刪而不譯。這種做法具有很大的誤導(dǎo)性和危害性,不僅使白桂思這樣一位對(duì)中國(guó)偏見(jiàn)頗多的人士搖身一變?yōu)?ldquo;中立學(xué)者”,還容易使讀者喪失對(duì)該書(shū)其他內(nèi)容和全書(shū)主題的應(yīng)有警惕。
2009 年,美國(guó)印第安納大學(xué)歐亞研究者白桂思(Christopher I.Beckwith)的英文著作《絲綢之路上的帝國(guó):青銅時(shí)代至今的中央歐亞史》(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以下簡(jiǎn)稱(chēng)《絲綢之路上的帝國(guó)》)由普林斯頓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原著甫一出版,筆者便閱讀了該書(shū),讀后深感這是一本打著學(xué)術(shù)旗號(hào)惡意攻擊中國(guó)主權(quán)、煽動(dòng)邊疆地區(qū)“獨(dú)立”的書(shū)籍。2020年10 月,某出版集團(tuán)出版了該書(shū)中譯本,使筆者頗為疑惑。筆者比對(duì)中譯本和原著后發(fā)現(xiàn),譯者顯然已經(jīng)意識(shí)到原著涉及中國(guó)的內(nèi)容存在許多歪曲歷史事實(shí)、甚至無(wú)視中國(guó)領(lǐng)土主權(quán)的嚴(yán)重問(wèn)題,因此對(duì)相關(guān)內(nèi)容進(jìn)行了大幅度刪改。由于譯者未對(duì)原著的謬誤及刪改情況進(jìn)行必要的說(shuō)明,這種改譯不啻為一種對(duì)原著和作者“真面目”的偽裝或“漂白”,使無(wú)暇或無(wú)力閱讀原著的讀者受到欺騙和蒙蔽。除此之外,原著的另一重嚴(yán)重危害——宣揚(yáng)印歐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論調(diào)——卻被完全保留下來(lái)。本文將對(duì)此作一澄清。
散布分裂中國(guó)言論
《絲綢之路上的帝國(guó)》最嚴(yán)重的現(xiàn)實(shí)危害在于,全書(shū)充斥著大肆攻擊中國(guó)主權(quán)、分裂中國(guó)領(lǐng)土的狂悖之言。如原著第281頁(yè)在談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的中國(guó)革命形勢(shì)及新中國(guó)的民族政策時(shí),謬說(shuō)連連。但在中譯本中,這些內(nèi)容均被改寫(xiě),甚至直接被刪除。
在談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時(shí),白桂思只字不提20世紀(jì)20年代以來(lái)內(nèi)蒙古各族人民在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斗爭(zhēng)的光輝歷史,徑稱(chēng):
Mongolian and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aries had already taken control of Inner Mongolia by 1949. On December 3, 1949, Mao declared the country to be a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而在譯著中,上述內(nèi)容被改寫(xiě)為:
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在1949年已經(jīng)解放了內(nèi)蒙古。1949年12月2日,內(nèi)蒙古自治政府改稱(chēng)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人民政府。
譯文與原文表達(dá)的意思完全相反。白氏用的是“控制”(take control of )而非“解放”(free/liberate)來(lái)定性新中國(guó)對(duì)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的主權(quán),同時(shí)刻意將內(nèi)蒙古界定為“國(guó)家”(country),即“在1949年12月3日,毛(澤東)宣布這個(gè)國(guó)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的一部分”。這種表述顯然反映了白氏一貫所持的中國(guó)邊疆地區(qū)不屬于中國(guó)的政治立場(chǎng),而這卻被中譯本完全抹去了。不僅如此,中譯本所謂“內(nèi)蒙古自治政府改稱(chēng)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人民政府”,根本就不見(jiàn)于原文。
原著在述及西藏時(shí)稱(chēng):
The Tibetans became increasingly nervous about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ho openly threatened to invade their country. Internal politics and the youth of the new Dalai Lama prevented any effective measures being taken until it was too late.
In 1950-1951 the Chinese invaded Tibet with an enormous modern army. The Tibetans, outmanned and outgunned, were forced to surrender. But the Tibetans could not in any case have withstoo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ho by the time of their victory over the Nationalists in 1949 had one of the largest, most modern, battle-hardened armies in the world.
在譯著中,上述文字被表述為:
1950年至1951年,人民解放軍開(kāi)進(jìn)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到1949年解放戰(zhàn)爭(zhēng)勝利之時(shí),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已經(jīng)是當(dāng)世人數(shù)最多、裝備最精良、作戰(zhàn)經(jīng)驗(yàn)最豐富的陸軍之一。當(dāng)時(shí)西藏的地方實(shí)力斷無(wú)任何機(jī)會(huì)阻擋他們解放西藏的步伐。
對(duì)比可知,原文中根本沒(méi)有使用譯文中兩度出現(xiàn)的“人民解放軍”(PLA)一詞,而采用“中國(guó)人”(the Chinese)和“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人”(the Chinese communists)的表述。白桂思將解放軍進(jìn)藏一事定性為所謂的“中國(guó)人入侵西藏”,還詐稱(chēng)在此之前“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人已經(jīng)公開(kāi)威脅要入侵西藏”,其反華政治傾向昭然若揭。白氏描述解放軍進(jìn)藏的關(guān)鍵性動(dòng)詞“invade”,是“入侵”或“侵略”之意,但譯文中統(tǒng)統(tǒng)被改成政治意義和感情色彩完全相反的“解放”一詞。
白桂思在述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時(shí),更是變本加厲,妄稱(chēng):
The East Turkistan Republic survived until late 1949, when the communist Chinese army marched in and occupied the country. It was incorporated back into the colony of Sinkiang (Xinjiang).
而在譯著中僅僅只有一句與原文意思完全相反的話(huà):
1949年底,人民解放軍進(jìn)入新疆,新疆解放。
原文主語(yǔ)是無(wú)視中國(guó)主權(quán)并具有殖民主義色彩的“東突厥斯坦”,并將解放軍進(jìn)入新疆描述成英語(yǔ)的“occupy”,即中文“占領(lǐng)”之義,而“解放”一詞在整段表述中并未出現(xiàn)。可見(jiàn),白氏根本不認(rèn)同解放軍解放新疆,故其隨后就污蔑新疆的政治地位相當(dāng)于“殖民地”(colony)。
除了歪曲史實(shí)外,白桂思還“發(fā)明歷史”,他在原著第281頁(yè)最后一段寫(xiě)道:
Similarly, East Turkistan was soon flooded with millions of Chinese. They took over the country from the Uighurs and other peoples, who had nowhere to flee to and no sympathy from major world power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or other world organizations.The Uighurs periodically attempted to fight back, but the Chinese outnumbered them and freely used their overpowering military force against them.
中譯本中完全沒(méi)有這段內(nèi)容,因?yàn)樵谋磉_(dá)的是“數(shù)百萬(wàn)計(jì)中國(guó)人接管了‘東突厥斯坦’這個(gè)‘國(guó)家’,導(dǎo)致當(dāng)?shù)孛癖娂葻o(wú)路可逃,又得不到其他大國(guó)或世界組織的同情,只能周期性地自發(fā)反抗,結(jié)果遭到人數(shù)上遠(yuǎn)遠(yuǎn)多于他們的中國(guó)人及其武裝力量的肆意鎮(zhèn)壓”。
除了上揭例證外,原著第263、282、286、292、306、310、312頁(yè)等,也存在諸多攻擊中國(guó)主權(quán)、煽動(dòng)中國(guó)邊疆地區(qū)“獨(dú)立”的狂悖之言,在中譯本里均被節(jié)譯、改寫(xiě),甚至直接刪而不譯。這種做法具有很大的誤導(dǎo)性和危害性,不僅使白桂思這樣一位對(duì)中國(guó)偏見(jiàn)頗多的人士搖身一變?yōu)?ldquo;中立學(xué)者”,還容易使讀者喪失對(duì)該書(shū)其他內(nèi)容和全書(shū)主題應(yīng)有的警惕。
以印歐人中心主義貶低其他文化
白桂思寫(xiě)作此書(shū)的另一個(gè)目的,是宣揚(yáng)印歐人中心主義。
首先,白桂思以殷墟出土的馬車(chē)乃外國(guó)輸入的假說(shuō)為基礎(chǔ),臆想當(dāng)時(shí)有一小群操印歐語(yǔ)的雙輪戰(zhàn)車(chē)武士進(jìn)入黃河中游地區(qū),與當(dāng)?shù)厝送ɑ椋l(fā)生語(yǔ)言的融合,最終使得上古漢語(yǔ)中有大量印歐語(yǔ)成分。因此,他臆斷殷周時(shí)期漢語(yǔ)的系屬有兩種可能:一是其本身就是印歐語(yǔ),二是受到了印歐語(yǔ)深度影響的東亞本土語(yǔ)言。當(dāng)白氏作出如上判斷時(shí),并沒(méi)有舉出任何實(shí)證,僅用一句“最近對(duì)于上古漢語(yǔ)的研究成果支持如下觀點(diǎn),即在商代甲骨文中有大量印歐語(yǔ)成分,且與原始印歐語(yǔ)清晰相關(guān)”(原著第47頁(yè)),就輕易搪塞過(guò)去。
值得注意的是,白桂思在其他研究如《漢藏問(wèn)題》(“The Sino-Tibetan Problem,” 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 Leiden: Brill,2002, pp. 113-157)中,承認(rèn)自己所提出的原始漢語(yǔ)與印歐語(yǔ)存在起源聯(lián)系的觀點(diǎn)并未得到確證。然而在《絲綢之路上的帝國(guó)》中,他以近乎肯定的語(yǔ)氣,發(fā)表這一既未被自己證實(shí)、亦未得到學(xué)界公認(rèn)的偏激之說(shuō),可見(jiàn)其治學(xué)態(tài)度頗不嚴(yán)謹(jǐn)。因此,該書(shū)根本不是嚴(yán)謹(jǐn)可信的學(xué)術(shù)研究成果,而是試圖對(duì)讀者灌輸錯(cuò)誤意識(shí)形態(tài)的洗腦之作。
即便商代馬車(chē)的制作及使用原理確實(shí)來(lái)自域外,也不能說(shuō)明當(dāng)時(shí)黃河中游地區(qū)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頗有作為的印歐人移民群體,更不像白桂思在書(shū)中別有用心的宣傳——“外來(lái)的印歐人帶來(lái)了戰(zhàn)車(chē),對(duì)商文化產(chǎn)生了強(qiáng)勢(shì)的影響乃至商王朝的建立可能與他們有關(guān)”。這就如同在中世紀(jì),包括四大發(fā)明在內(nèi)的不少中國(guó)科技成果傳入歐洲,并不等于當(dāng)時(shí)歐洲已有大量中國(guó)移民定居。
其次,該書(shū)世界史觀也完全有違基本歷史事實(shí)。白桂思罔顧史實(shí),荒誕不經(jīng)地臆造出了一個(gè)所謂的“現(xiàn)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概念,而且,這個(gè)“現(xiàn)代文明”又不等于人們通常理解的工業(yè)文明。他提出,“現(xiàn)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4000 年前印歐人在歐亞大陸中心地帶發(fā)起的大遷徙”,這些“原始印歐人”具有活力(dynamic)、不安現(xiàn)狀(restless),從中央歐亞一路遷徙,對(duì)外到處征服,結(jié)果才創(chuàng)造出延續(xù)至今的“現(xiàn)代文明”或“現(xiàn)代世界的文化”(modern world culture),并中斷了包括中國(guó)在內(nèi)的四大文明古國(guó)的繼續(xù)發(fā)展(原著第318—320頁(yè))。
事實(shí)上,除了中華文明從未因印歐人等任何因素中斷之外,上述觀點(diǎn)至少還有三個(gè)錯(cuò)誤。
第一,在當(dāng)下學(xué)界,原始印歐人和原始印歐語(yǔ)概念的適用時(shí)段為公元前3500年前后,遠(yuǎn)遠(yuǎn)早于原著中所說(shuō)的公元前2千紀(jì)。這一常識(shí)性錯(cuò)誤,說(shuō)明白桂思對(duì)這一領(lǐng)域完全不熟悉。
第二,伊斯蘭教興起后,從伊朗以西(包括古埃及和古巴比倫文明所在區(qū)域),到北非摩洛哥等馬格里布地區(qū)的主體文化、語(yǔ)言,是與印歐人及印歐語(yǔ)皆無(wú)關(guān)系的閃米特系阿拉伯文明及阿拉伯語(yǔ),而閃米特人并非起源于“中央歐亞”地區(qū)。
第三,書(shū)中被白桂思極度夸大的雅利安系印度—伊朗人創(chuàng)造的文明,在近代以來(lái)同樣經(jīng)歷了衰落,以致人們實(shí)在無(wú)法將其與“現(xiàn)代文明”對(duì)應(yīng)起來(lái),其中以印度為主的南亞次大陸更是完全淪為英國(guó)的殖民地,伊朗也長(zhǎng)期處于半殖民地社會(huì)。
筆者認(rèn)為,這種一方面在翻譯中大量刪改原著中某些明顯的敏感文字,極力“漂白”書(shū)中錯(cuò)誤觀點(diǎn),另一方面又在根本觀點(diǎn)(如印歐人中心論、中華文明斷裂論等)上一仍原著之舊的做法,極不可取。這不僅導(dǎo)致了不明就里的自媒體推薦該書(shū)中譯本為“好書(shū)”,甚至個(gè)別報(bào)刊還以中譯本的出版為由頭,專(zhuān)門(mén)組織對(duì)白桂思的所謂“學(xué)術(shù)”專(zhuān)訪(fǎng),并發(fā)布于網(wǎng)絡(luò)媒體以咸使知聞。對(duì)這種為害深遠(yuǎn)的舶來(lái)的歷史觀,我們不可不慎;而對(du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翻譯和推介,我們更應(yīng)警惕。
作者:鐘焓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 來(lái)源:《歷史評(píng)論》2021年第6期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gè)人觀點(diǎn),不代表本站觀點(diǎn),僅供大家學(xué)習(xí)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yíng)利性網(wǎng)站,如涉及版權(quán)和名譽(yù)問(wèn)題,請(qǐng)及時(shí)與本站聯(lián)系,我們將及時(shí)做相應(yīng)處理;
3、歡迎各位網(wǎng)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wǎng),依法守規(guī),IP可查。
作者 相關(guān)信息
內(nèi)容 相關(guān)信息
? 昆侖專(zhuān)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wù) 新前景 ?

? 國(guó)資國(guó)企改革 ?

? 雄安新區(qū)建設(shè) ?

? 黨要管黨 從嚴(yán)治黨 ?

 組團(tuán)發(fā)“反戰(zhàn)宣言”的北大教授,稱(chēng)美國(guó)打朝鮮戰(zhàn)爭(zhēng)是為了大國(guó)信譽(yù)
組團(tuán)發(fā)“反戰(zhàn)宣言”的北大教授,稱(chēng)美國(guó)打朝鮮戰(zhàn)爭(zhēng)是為了大國(guó)信譽(yù) 王立華:全社會(huì)深刻反思聯(lián)想有利于不犯顛覆性錯(cuò)誤
王立華:全社會(huì)深刻反思聯(lián)想有利于不犯顛覆性錯(cuò)誤 撕開(kāi)西安疫情慘狀的外皮,是一段血淋淋的國(guó)資私有化歷史
撕開(kāi)西安疫情慘狀的外皮,是一段血淋淋的國(guó)資私有化歷史
 郝貴生:不能用蒲魯東的所謂“辯證法”解讀今天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
郝貴生:不能用蒲魯東的所謂“辯證法”解讀今天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 郝貴生:不能用蒲魯東的所謂“辯證法”解讀今天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
郝貴生:不能用蒲魯東的所謂“辯證法”解讀今天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 張文木 : 湯因比歷史研究肩負(fù)“特別文化使命”,中國(guó)應(yīng)知己知彼
張文木 : 湯因比歷史研究肩負(fù)“特別文化使命”,中國(guó)應(yīng)知己知彼? 社會(huì)調(diào)查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