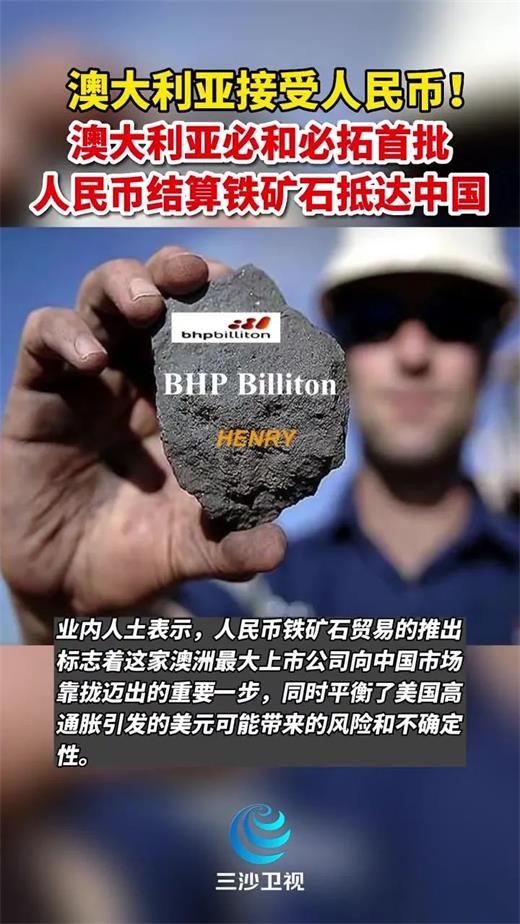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10日-星期四
一、俄烏網絡作戰的實質是俄美網信戰爭對壘
俄美之間在網絡信息空間的明爭暗戰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美國與前蘇聯的冷戰時期。
1、美蘇冷戰下的網信戰略競爭
1957年,蘇聯發射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顯示了蘇聯軍方負責的計算機控制系統的強大能力。受到刺激的美國,1958年成立了國防部高級研究項目署(AR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其核心之一是信息處理(IPTO,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iques Office),關注電腦圖形、網絡通訊、超級計算機等研究課題。
1959年,蘇聯科學家提出,建設用于改善全國經濟自動化管理的計算機網絡系統。OGAS項目(國家自動化會計和信息處理系統,俄語Общ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автоматизированная система учёта и обработки информации)是其中之一。
OGAS項目起始于1962年,是一個三級網絡結構:由位于莫斯科的網絡中心、約200個位于其他主要城市的中級中心,以及約20,000個位于經濟重要部門的終端組成;這些計算機利用已有的電話設施進行實時通信,各終端之間也可以相互通信;進而,設計者還提出可利用該系統廢除紙幣、采用電子支付的設想。1970年10月,OGAS項目申請經費遭到拒絕;1971年,蘇聯共產黨第24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認可了OGAS計劃,最后僅贊同發展本地信息管理系統,致使OGAS不進則退,最終失敗。從而,蘇聯為美國阿帕網80年代延伸擴張為軍民兩用的因特網(Internet,下同)、90年代演進為走向世界的互聯網(internet,下同),讓開了通衢大道和全球空間。
必須清楚地看到,蘇聯具有先發優勢的自主可控的OGAS計算機信息網絡計劃下馬,并不是美國當時的網絡信息技術已經超越蘇聯、優于蘇聯,而是美蘇冷戰導致的重大結果之一,是蘇共中央網信空間戰略判斷和決策失誤的嚴重后果。
1962年10月爆發的古巴導彈危機,被認為將美蘇冷戰推向了頂峰和轉折點,美蘇戰略競爭也達到高潮。美國基于二次核反擊戰略目的構建多指揮控制點計算機網絡系統的謀劃加快。
1969年11月,由美國國防部負責的阿帕網(ARPAnet)計劃實施。
1975年,在幾乎沒有競爭對手的情勢下,美國開始重點解決第二代網絡互聯計劃的設計。TCP/IP協議族的開發利用,奠定了由阿帕網向因特網轉化發展的重要基礎,
1983年,阿帕網分為純軍事用途的MILnet和非軍事用途的ARPAnet兩部分。
1990年,NSFnet成為因特網重要的骨干網之一。局域網和廣域網技術,推動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建立的NSFnet快速發展。
1994年,萬維網技術的推廣和普及,促進因特網向互聯網演進并迅速走向世界。同年,中國公眾網絡全功能接入因特網。
2、俄羅斯“主權互聯網”東山再起
1991年,前蘇聯解體,俄羅斯繼承了前蘇聯的經濟、科技、軍事等重要成果。俄羅斯開始構建、發展因特網。1993年,俄羅斯科教網絡形成和發展。2000年,俄羅斯的因特網服務商和用戶在全國發展到一定規模。
但是,由前蘇聯解體重生的俄羅斯,在網絡信息空間領域從一開始就不信任美國。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支持創建“互聯網終止開關”(Internet Kill Switch),到積極推進制定信息安全條例,俄羅斯對美國提出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張互聯網”,一直保持警惕和防范。
瑞典國防研究局2021年4月的一份報告指出,俄羅斯推行的旨在建立其網信空間主權的政策,至少在20年的時間里建立起了網信作戰(行動)的執行能力,并自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爭取和促成一項信息安全國際條約。報告指出,俄羅斯的情報和安全部門敏銳地意識到,全球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架構直接影響情報能力的平衡,斯諾登泄密事件,更加暴露了美國及其盟友通過互聯網收集情報的能動優勢,使俄羅斯的擔憂更加強烈。報告認為,俄羅斯長期協調性的網信戰略政策,難以變化。
2014年,普京明確提出建立俄羅斯主權互聯網(sovereign internet),并在必要時將獨立于全球互聯網基礎設施。2019年,俄羅斯“主權互聯網”(RUnet)通過立法并生效。
本世紀初,俄羅斯信息安全條例規定的優先重點領域是:保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減少國家對進口技術的依賴,包括硬件、軟件和電子元器件;控制“互聯網在俄羅斯國內部分”的傳輸交換內容;在國際上宣傳和推廣俄羅斯的信息安全觀。
瑞典國防研究局指出,俄羅斯明確將信息安全的概念劃分為技術性和心理性兩方面,通過國家“數字經濟”的“數字安全”子項目,精心打造用于檢測、對抗和排除信息通信和技術(ICT)威脅的系統,明顯提高了實施網絡作戰(行動)的能力。
俄羅斯的《主權互聯網法》,不僅對建設俄羅斯境內的域名系統(DNS)提出了要求,并規定,負責監督通信和媒體的機構聯邦通信信息技術和大眾傳媒監督局(Roskomnadzor),將在監督俄羅斯境內互聯網流量的路由路徑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發生緊急情況時接管并指揮俄羅斯境內的網絡數據流通。2020年之前,俄羅斯至少進行了3次自主可控的全國性“斷網”演習。
美西方認為,俄羅斯的網信空間入侵能力排名世界前五。前蘇聯時期,德國黑客就向克格勃出售網絡漏洞。從2007年對愛沙尼亞的分布式拒絕服務攻擊(DDoS),到2020年通過更新太陽風(Solar Winds)軟件對美國大約250個聯邦機構和企業的黑客攻擊,充分體現俄羅斯軍事情報局(GRU)等專業機構的網信入侵和作戰(行動)能力,同時表明,俄羅斯網信戰略中的攻擊性長期與戰略層面相協調。
可見,俄羅斯的“主權互聯網”,就是為在網絡信息空間對抗美西方而東山再起,并在不斷地對抗中積累了網信作戰的經驗,鍛造了行動能力、增強了作戰意志。
3、俄烏網信戰本質是美俄交鋒
(1)美國一直以來都在幫助烏克蘭加強網絡防御。
美西方媒體報道,俄烏戰爭爆發前幾個月,包括美國陸軍網絡司令部官兵、民用承包商和美國專業公司雇員的美國“網軍”,就已經分散進入烏克蘭各地,協助保護關鍵基礎設施。俄羅斯實際上面對的,是專業實力極強的美國網絡安全部隊和網絡安全承包商(雇傭軍)。
日裔美軍上將、美國網絡司令部司令兼國家安全局局長保羅·中曾根在接受采訪時承認,俄烏危機中,美國曾對俄羅斯發起多次網絡攻擊,以支持烏克蘭。中曾根表示,2021年12月美方就向烏克蘭派遣了網軍,在當地停留了近三個月。
媒體報道,在美國國會參議院4月5日的聽證會上,中曾根也曾透露,美方曾于去年年底派遣“前出狩獵”小組前往烏克蘭。所謂“前出狩獵”,是指通過向海外派遣網絡力量,采取情報共享等行動,并進行主動攻擊;是2018年開始部署的美國“網絡戰”的行動框架和步驟。據美國網絡司令部公布的消息,截至2022年5月,已在全球16個國家開展了28次“前出狩獵”行動,其中包括愛沙尼亞、立陶宛、黑山、北馬其頓和烏克蘭。從地理位置、地緣政治等多元因素綜合分析,這些“前出狩獵”行動的目的和針對目標,都是俄羅斯。
顯然,烏克蘭不是美國打擊俄羅斯網絡戰爭的遮羞布或代理人,而是為美國直接面對俄羅斯在網絡信息空間交戰,提供了“網絡戰”、“信息戰”、“混合戰”等的充分必要條件,提供了各種作戰(行動)便利,提供了有利于美西方的真實網絡戰爭、軍事戰爭的戰場場景。
(2)美國乘蘇聯OGAS項目下馬之利,明確針對蘇聯實施二次核反擊為目的、精心策劃和積極推進由阿帕網延伸演進到因特網、互聯網的全面戰略部署和全球戰術布局。
美國在歐洲部署了因特網的I、K兩個根域名服務器系統,并將最初設在英國的K根域名服務器轉移到荷蘭;美國為首的北約在愛沙尼亞建立針對俄羅斯的“合作網絡防御卓越中心”,都是重要例證。
荷蘭是歐亞大陸橋的歐洲始發點,是歐盟和北約的創始國之一。近代被稱為“海上馬車夫”的荷蘭人,同俄羅斯人的貿易往來可追溯1000年。17世紀,兩國在外交、科技(尤其是航海)、文化等方面的關系大發展,俄語吸收了大量荷蘭語匯,荷蘭成為彼得大帝西向歐洲戰略、俄羅斯融入歐洲國際社會的引路人。18世紀末19世紀初,俄羅斯帝國躋身歐洲強國,荷蘭開始依賴俄羅斯的實力背書;19世紀,荷蘭與俄羅斯的關系聚焦經濟領域,俄羅斯將部分黃金儲備存放荷蘭。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羅斯是荷蘭最大的外國投資者;時至今日,荷蘭仍是歐盟國家中對俄羅斯最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顯然,K根域名服務器設在荷蘭,并采用任播技術,更有利于滲透俄羅斯的經濟、社會、文化、科技領域。
波羅的海沿岸國家之一的愛沙尼亞,在彼得大帝時期就被俄羅斯統治了200余年;由前蘇聯解體獨立后,1994年2月加入北約;歷史上與俄羅斯不睦,且有領土爭端。2007年,愛沙尼亞指責俄羅斯發動網絡攻擊,使愛沙尼亞的政府、議會、軍隊、銀行業和媒體業的信息技術設施及相關數據網絡陷入癱瘓。2008年,愛沙尼亞國防部與北約聯合成立了“北約合作網絡防御卓越中心”。該中心實際上是一個軍事指揮機構,主要為北約成員國提供全方位的網絡防御控制與協調服務,涉及技術、戰略、作戰和法律各方面。北約授權該中心負責網絡防御作戰的教育和培訓,與位于美國弗吉尼亞州的轉型與改革司令部密切合作。該中心編纂的著名的《塔林手冊》強調,允許通過常規打擊來反擊造成人員傷亡和重大財產損失的網絡攻擊行為。
二、俄美烏網戰對我國網信安全的警醒和啟示
1、這是在美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精心策劃、潛心設計、悉心構建的全球“同一張網”內、同一個網絡信息空間發生的、以摧毀對方的國家意志和數據資產為目的戰爭。
從某種意義上說,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場美國人為制造的“囚籠戰爭”或“圈套戰爭”。
21世紀以來,美國政府和軍方不斷深化認知及擴大宣傳,聲稱“賽博空間”就是全球的“信息環境域”,包括各國家和地區的國際互聯網、電信網、計算機系統以及嵌入式處理器和控制器等,還包括影響人們交流的“虛擬心理環境”。
美西方認為,“賽博空間”完成了從抽象到具體、從單純虛擬空間到物理、信息、意識、社會多維空間的認識轉變;以人造的網絡為平臺,以信息控制為目的,通過網絡將信息滲透、充斥到陸、海、空、天實體空間,依托電磁信號,傳遞無形信息,控制實體行為,從而構成實體層、電磁層、虛擬層相互貫通、無所不在、無所不控、虛實結合、多域融合的復雜系統空間。今天同樣是從美國流出的關于“元宇宙”的某些解釋和說法,與此不謀而合、驚人相似。
簡言之,“賽博空間”是控制論(cybernetics)和空間(space)兩個英文單詞的組合;是美國臆想、設計、規范、控制的網絡信息空間;從理論到實踐的全球化,都是為實現美國的全球網絡信息空間一體化,為實現美國對全球網絡信息空間的全面、多維、多元、多重、多層次的絕對控制。
換言之,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網絡戰爭,就是在美國設定、劃定和控制的網絡信息空間進行的戰爭;是全面受制于美國(房東)的戰爭;是租用美國域名空間和讓渡主權網絡信息空間(房客)之間的戰爭;是不分地域、沒有國界、目標精準、目的明確、無差別攻擊,美國全方位指揮與控制打擊對手的全球性網絡戰爭。美西方媒體稱,全球30萬黑客卷入了美俄烏網絡戰爭,其中包括主要分散在美國的“匿名者”等職業性、政治性黑客組織。
長期以來,DDoS攻擊防不勝防,大多來自美國、來自美西方網絡信息聯盟。無論政府網站、軍隊通信、基礎設施、電信運營等等,凡是與美國指揮控制的武器化互聯網關聯的計算機系統,指哪打哪、非癱即宕,即便是“物理隔離”也難以幸免;平時高調宣揚的數字加密、防火墻、“零信任”等等,都顯得蒼白無力、無可奈何。
俄羅斯作為曾經創建OGAS計算機信息網絡系統的繼承者,對此早有警覺和防范意識。俄羅斯構建主權互聯網(RUnet)的同時,利用俄語33個字母與英語26個字母并不完全對稱的微妙和讀寫拼音差異,利用俄語在歐洲(特別是東歐)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的影響與滲透,不僅在國內和歐洲推廣俄文頂級域名“.рф”及操作系統、辦公軟件(Office),而且重構國(境)內的ASN自治域、DNS解析系統,重構引導數據信息流的監控系統,盡可能地在現有互聯網環境條件下,保持和發揮了維護俄羅斯“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獨立性、自主性與創造性,同時,形成了對美西方網絡信息系統的對抗和制衡。其中對我國的警醒和啟示,積極、深刻、富有現實意義。
2、美國從阿帕網到因特網再到互聯網人為編織的網絡信息空間,關鍵、基礎、根本的兩個特征,就是:
第一,域名、地址、ASN自治域及其構成的DNS域名解析系統。
無論IPv4還是IPv6,都沒有改變美國設計、規范、分(支)配、嚴密控制的從因特網到互聯網的DNS域名解析系統。
美國長期向世界各國和全球網民灌輸的理念,即脫離了因特網或互聯網的DNS規范與控制,就不能享用網絡信息空間的任何數字化、現代化服務,就將回到無網絡的“原始”狀態。實際上,“全功能”接入因特網或互聯網,意味著全身心陷入美國構建的軍事化的“賽博空間”,意味著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全方位、多元化、多層次的讓渡。
亞太地區網絡信息中心(APNIC)首席科學家杰夫•休斯頓(Geoff Huston)強調:DNS就是互聯網,而不是互聯網的某種可有可無的屬性(The DNS is the Internet,not a selectively accessible attribute of the Internet)。
杰夫•休斯頓一語點破了互聯網的本質,即:域名·解析·系統。其中,域名空間是人為設計編織的,解析是按照人為賦予的算法和算力控制運行的,系統是人為構建的計算機互聯互通的路由體系。互聯網的“人為”,主要是美國,主體是美國,主導也是美國。因此,凡“全功能接入”互聯網的國家和地區,不得不、不能不陷入美國設計編織的域名空間及解析控制的計算機網絡信息系統。
業界稱為互聯網“灰色地帶”的遞歸域名系統(Recursive DNS),是“域名空間的入口”,近些年來,被敵意滲透或惡意劫持對用戶信息遠程“重定向”的事件層出不窮、愈演愈烈,充分暴露了設計和應用中的嚴重弊端。
第二,基于TCP/IP協議和協議族單一結構信息通信技術供應鏈構成的指揮與控制(C2)系統。
這是構成美國“第五作戰域”理論的根本依據,是美國政府主張“互聯網武器化”、“數據作為武器系統”的技術基礎。
美軍從網絡武器研發、網絡戰演訓、信息戰平臺、網絡戰規劃和實施、跨域作戰管理,到作戰指揮、控制和管理,構筑了完整的網絡戰武器系統。可以分為指揮與控制作戰的管理平臺、基礎平臺、訓練平臺、武器研發項目,以及信息戰平臺。其中:聯合網絡指揮與控制(JCC2)、統一平臺(UP),均屬網絡空間作戰的指揮控制和管理系統,旨在向網絡部隊提供網絡空間指揮控制、決策規劃、態勢感知、攻防行動等作戰能力,從而能夠執行同步的全頻譜網絡空間作戰,JCC2指揮層級高于UP,網絡作戰任務從UP開始然后轉至JCC2。
坦率地說,只要是采用了美國設計、支配及其DNS解析控制的域名和地址,只要是采用了美國規定和規范的TCP/IP協議和協議族技術標準、運行規則,就難以擺脫美國互聯網武器化的指揮與控制系統。
無論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網絡戰爭如何史無前例地激烈和錯綜復雜,都沒有脫離美國互聯網關鍵、根本的基礎平臺和框架,沒有脫離美國互聯網DNS解析和TCP/IP供應鏈對武器系統的控制。
迄今為止的俄烏網絡戰爭,仍然是美俄烏(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絞殺戰,掠奪對方數據資源和信息情報的白刃戰,尋求精準打擊、“刺刀見紅”的肉搏戰。
3、俄羅斯頂住了美國政府(軍隊)與美國互聯網大資本對俄羅斯全面發動的“軍民聯合作戰”,美國迫使俄羅斯主動斷網、妥協(投降)的圖謀未能奏效。
俄烏網絡戰爭中,美國互聯網大資本控制的提供虛擬疊加網絡和信息通信供應鏈(硬件和軟件)應用服務的跨國公司,興師動眾地聯手對俄羅斯實施切斷或中止服務的(作戰)行動,試圖造成俄羅斯網絡普遍或大面積“斷服”,迫使俄羅斯失去網絡信息空間的行動(作戰)能力,被迫同美西方互聯網主動斷開,被迫啟動俄羅斯幾經演習構建的“主權互聯網”(RUnet),進而摧毀RUnet。但是,美西方的圖謀迄今并沒有得逞。
甲骨文(Oracle)、蘋果(Apple)、谷歌(Google)、微軟(Microsoft)等停止在俄羅斯境內的產品銷售和運營服務,關閉了應用工具功能,刪除了移動應用程序;推特(Twitter)、臉譜(Facebook)、優兔(YouTube)、照片墻(Instagram)等主流社交平臺,中止俄羅斯本地服務,禁止發布信息,限制投放廣告。迄今,并沒有任何信息表明,俄羅斯因此網絡服務器就關閉了,路由器就失去導航能力了,移動終端(手機、平板電腦等)就上不了網了,操作系統和辦公系統就失靈了,用戶之間的信息通信交流就不存在了。除了俄羅斯掌握了一定程度自主修復和維護網絡系統正常運轉的替代或置換能力,又能如何解釋?
雖然美西方媒體曾宣稱掌握了俄羅斯軍隊官兵的大量個人數據信息等,但是,并未產生預期的心理戰效應和戰場捕獲,俄軍反而增強了契而不舍攻占烏克蘭馬里烏波爾亞速鋼鐵廠的戰斗意志,并迫使固守的烏軍和雇傭軍全部“投降”或被俘虜。
俄烏戰爭危機持續近半年了,英特爾(Intel)、超威(AMD)暫停向俄羅斯供應芯片、處理器等產品;戴爾(Dell)暫停在俄羅斯的產品銷售;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有選擇性地”關閉了俄羅斯部分銀行的 SWIFT交易系統。但是,俄羅斯互聯網還是沒有關閉,沒有與歐洲互聯網、美國互聯網主動“斷網”,沒有被逼到啟動“主權互聯網”(RUnet)自我封閉運行的最后困境。
實際上,俄羅斯的主權數據信息在戰前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安全保護,而烏克蘭方面的大量敏感數據信息,卻顯然被俄羅斯方面及時截獲、精準分析,不失時機地有效采用。俄羅斯居然頂住了、扛住了、制住了美西方的全面“斷服”,迄今沒有啟動作為現代網絡戰爭國家自衛戰、民族自衛戰的戰略備份和戰略威懾的俄羅斯主權互聯網(RUnet),不能不說是個奇跡。這不僅具有權衡戰略相持的積極示范意義,而且體現出戰術格局應對得當,戰前準備(預案)充分、保障有力。
在前所未有的網絡戰爭優勢一邊倒的大環境下,俄羅斯充分發揮自身強化數據保護的網絡特點,創建小環境制衡壁壘及相互之間的聯動游擊作戰,反客為主、出其不意、堅決反擊、各自為戰,有許多寶貴的經驗教訓值得探究、學習和借鑒。
我們注意到,俄羅斯“.RU”(和“. рф”)國家頂級域名注冊數量占比超過80%,基本上對互聯網域名(業務和應用)可管可控;俄羅斯的5個國家頂級域名解析系統都部署在國內,確保了對域名服務的管轄權、控制權和數據的同一性。
還應該清醒地看到,盡管烏克蘭請求美國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和歐洲互聯網協調中心(RIPE NCC)從互聯網中刪除俄羅斯“.RU”、“.рф”、“.su”等頂級域名,在DNS根域名服務器中關閉對俄羅斯的解析服務,并促成撤銷這些域名的相關TLS/SSL證書,且得到了頂級域名控股公司(Top Level Domain Holdings)、域名注冊商Namecheap的支持。但是,全球最大的頂級域名服務商威瑞信(VeriSign),作為互聯網A、J根域名服務器系統的管理、控制方和運營商,實際處在互聯網商業運營的頂端及核心位置,卻一直沒有呼應針對俄羅斯采取制裁行動。美國政府實際主導的各互聯網管理機構,如ICANN、RIPE NCC也公開聲明“不贊成”烏克蘭的呼吁。
一個必須正視的現實是,俄羅斯的領土和領空橫跨歐亞,扼守全球互聯網樞紐(北美地區)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美國西海岸到日本海的海底光纜通道,擁有足以切斷美國與亞太地區和歐洲的空域、海域、陸域聯系的軍事與科技能力,這不能不使美國及其歐亞盟國心生忌憚。一旦將俄羅斯逼上與美歐“同生共死”的梁山泊,美國政府(軍隊)及互聯網大資本的“王牌”或也將不復存在。也就是說,啟動RUnet的真正戰略威懾意義在于,俄羅斯主動切斷境外互聯網將意味著,同時切斷全球互聯網之間、美國與全球互聯網之間的所有物理通道。美國在俄烏網絡戰爭中的最大收獲,也許正是看清了、明白了這一點。
俄烏戰爭危機中,馬斯克與美國軍方合作啟用“星鏈互聯網”,是網絡信息空間領域的一個重要事件。“星鏈互聯網”在作戰中,除了數據的接收、中繼和發送,還具備“跟蹤、遙測和控制(簡稱“TT&C”)的功能。美國網戰司令部和太空司令部是“星鏈互聯網”直接和最大的受眾。“星鏈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美軍曾經的某些“官僚式”自戀意識,推動了美軍的軍改和概念更新,以及美軍以轉變理念和作戰方式的做法,進一步加強了軍民合作與融合。
可以預見,美國必然會對“星鏈互聯網”在俄烏戰爭危機中的表現進行完善和強化,未來必然將用于威懾中國。太空間的“星鏈互聯網”與微軟、臉譜等地面網絡信息公司銜接,與到處移動的特斯拉機動車輛相配合,必將構成對我國網絡信息空間安全、社會安全、人身安全、軍事安全以及全局性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和嚴重危害。
三、美中網信作戰我方頹勢和逆勢反省與思考
2020年8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及美國國務院公布了主要針對中國的“清潔網絡計劃”,包括清潔網絡運營商、清潔網絡應用程序、清潔網絡商店、清潔網絡“云”、清潔網絡線路、清潔網絡路徑6個方面的內容。明確要求: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的電信運營商不與美國電信網絡連接。這類公司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不應提供來往美國的國際電信服務。
美國政府單方面“莫須有”地以中國國有電信運營商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為由推出針對性的“清潔網絡計劃”,事實上是美國政府對中國實施網絡信息作戰的公開“宣戰”,且氣勢洶洶、咄咄逼人。
2021年6月3日,拜登政府的美國聯邦財政部,將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移動列入綜合制裁名單(“非SDN中國軍事綜合體企業”清單,Non-SDN)。“清潔網絡計劃”被實質性推進。
2022年1月3日零時,以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撤銷中國電信美洲公司(CTA)“214條款”的授權命令正式生效為標志,美國對中國網絡信息空間實施“步步為營、全面封殺”的制裁、打壓、扼制、圍困,進入了“清潔網絡”全覆蓋的新階段,美中網信作戰短兵相接的局面一觸即發。
俄烏戰爭危機期間(3月23日),FCC強制性地最終全部撤銷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移動、太平洋網絡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美國國內及國際運營的“214條款”授權,毫不掩飾隨時將針對中國“斷網斷服”的圖謀,彰顯美國在互聯網信息空間的霸權和霸道。
美國對中國的網絡戰爭,事實上已經開始,正在進行時。
中國被動地處在美中網絡戰爭的頹勢一方,面臨逆勢扭轉的巨大壓力和阻力。
1、中國最大的頹勢在于,公眾網絡信息空間領域全面受制于美國。
自1994年我國公眾網絡全功能接入美國互聯網,自上而下,將“全功能接入”當作“引進先進技術”,將“受制于人”當作“韜光養晦”,將“主權讓渡”當作“互聯互通”,將“追隨”當作“追趕”,漸漸地放松、放緩、放棄了創建自主自立自強網絡的努力和奮斗,漸漸地陷入了美國設計、規范、支配、控制的桎梏、陷阱和圈套。即便是2020年8月美國公開推出“清潔網絡計劃”后,我國各界也沒有引起應有警覺、足夠重視、認真戒備。
特別嚴重的網信安全問題是:
(1)國家頂級域名受制于人
互聯網的數字化空間基石,主要由域名(和IP地址)、域名系統(DNS)、自治系統(ASN)三個相互依存的部分組成。大量理論與實踐的數據分析證明:域名系統DNS是“固有政治”技術且在事實上受控和受制于人(美國)。我國的域名及域名服務系統DNS存在嚴重(和遺留)的安全隱患,我國的自治系統保有量和統籌應用,呈現組網“扁平化”和“集中式”等安全弱點,抗打擊承受力(彈性)差。
2002年12月3日,由著名軍火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分拆出來的美國紐斯達(Neustar)公司宣布,已經成為中國海外銷售“.CN”的唯一總代理商,是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海外銷售“.CN”域名的門戶(Gateway)。外媒指出,紐斯達不僅是一個通過“隱性網絡”監控數據和信息的公司,而且是“一個龐大、復雜和潛在的可怕機構”。據披露,僅2002年12月9日至2009年的7年間,紐斯達就先后發展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在內的110多家海外“.CN”域名注冊商,境外法人注冊中國國家頂級域名“.CN”的數量高達200萬個。
截至2020年12月,CNNIC公布的“.CN”域名注冊數量為1,897萬個,但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公布的“.CN”域名注冊數量為2,000萬個,多出103萬個。而據美國政府授權的互聯網A根、J根管理運營商威瑞信公司(Verisign)的監測報告,截至2021年9月底,“.CN”注冊數量僅為1,530萬個,比CNNIC上述公布數量少367萬個,比CAICT上述公布數量少470萬個。
是美國的統計數有所隱瞞,還是中國的統計數有所夸張?無論如何,國內外權威機構數以百萬計“.CN”中國國家頂級域名注冊數量的差距,令人不可思議;中國國家頂級域名“.CN”管理失控,已顯而易見。
多國監測發現,大量“.CN”域名被用于暗網“黃、賭、毒”和軍火等非法交易機構,或被黑客組織機構控制。如果數以百萬計的“.CN”國家頂級域名事實上已不可控,甚至搞不清隱匿在哪里作祟或將在何時伺機作亂,危害及危險豈不難以預測、防不勝防?
不久前在紐約持槍殺人的罪犯,曾在今年4月份偽造一家中國公司注冊了“.CN”域名進行恐怖宣傳。我國“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CNCERT)監測報告稱,境外組織通過控制中國境內的計算機,對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進行網絡攻擊(87%的攻擊目標是俄羅斯),攻擊地址主要來自美國(其中來自紐約的就有10余個)。如果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失控的“.CN”域名,直接以假亂真禍害中國用戶和網民,直接攻擊中國黨政機關、央企國企、金融機構、要害部門,又會是怎樣的情景?
這種被稱為“MitM 攻擊”的中間人攻擊模式,即是在信息發出方與接收方之間攔截通訊,篡改信息內容實施欺騙,或偽裝發信人實施攻擊,是網絡攻擊的慣用手法之一。境外組織“繞道”中國、假手中國域名對俄羅斯、白俄羅斯等他國目標實施欺騙性攻擊,不僅可以嫁禍中國,也是因為中國網絡確實存在境外滲透和有利于中間人攻擊的明顯脆弱性。
我國應用域名中,超過51%的活躍域名(如“.COM”、“.NET”等)是CNNIC不負責注冊和管理的,或明知“分類域名”的存在而不管理(或不作為)。中國網信領域長期存在“兩股道上跑的車(域名)”,形成了事實上涇渭分明、堂而皇之的我國公眾網絡信息空間的外國“租界”。微軟、IBM、英特爾、亞馬遜等美國公司的中國總部,都有各自的專線(網)直通美國,直通日本、臺灣,直通中國境外各國家地區的明網和暗網!
如此,中國的公眾網絡信息空間,如何能不受制于美國、不受制于美西方圍困中國的網絡信息數據聯盟(如“五眼聯盟”)?
建議:各地各級網信部門,在公安、國安及相關軍事國防單位的配合下,對所有注冊使用“.CN”等頂級域名的情況,限期境內外各實體單位和機構重新申報登記核實,逾期未經核實核準的域名、重復交替使用的域名、來路不明注冊使用的域名一律作廢(停止使用,或重新申請注冊核準),再經發現按非法使用域名、擾亂和危害國家安全,從嚴從重處理。
(2)DNS解析受制于人
不能通過常規搜索引擎訪問和鏈接的互聯網專屬局域網及其內容,構成深網系統,如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專網、黨政機關專網、金融業專網、公安專網等等。深網的規模和內容,被認為至少是在明網的500倍以上。
深網中的暗網網絡(Dark Net),是疊加在電信網絡之上可以隱瞞真實通信身份的私有網絡(系統)平臺;暗網系統(Dark Web),是暗網網絡所承載的匿名交互和隱藏服務的網站及內容。所有的黑客,都深藏于暗網;所有的漏洞,都深埋于暗網;所有的木馬,都受到來自暗網的引擎引導牽制。
暗網網絡和系統,需要使用特殊的軟件(如被稱為洋蔥路由即疊加路由的TOR)才能訪問。支撐暗網網絡和系統的本源,是可替代的、異類的互聯網域名解析核心樞紐DNS。換句話說,DNS域名解析系統既是互聯網通信的中樞,也是危及互聯網安全的結構性關鍵、基礎、根本所在。誰掌握了DNS,誰就掌握了制導網絡數據信息的主動權、控制權、管轄權、處分權。
俄羅斯主權互聯網(RUnet)對構建自主可控的DNS解析系統,確保95%以上的數據信息在俄羅斯境內實現和完成解析服務,進行了大膽調整、嘗試和創新。中國的情況很不樂觀。
首先,國家頂級域名“.CN”配置了八個域名系統(DNS“頂級門戶”),分別被命名為:a.dns.cn,b.dns.cn,c.dns.cn,d.dns.cn,e.dns.cn,f.dns.cn,g.dns.cn,以及被托管在中國教育和科研網的ns.cernet.net。這八個域名系統的DNS解析服務及其數據必須保持同步,以確保域名解析和映射的唯一性、排他性和同一性。
但是,其中的“f.dns.cn”和“g.dns.cn”,卻長期被分別托管(設置)在美國和英國,專屬印度塔塔(Tata)電信公司的自治系統(ASN 6453)。也就是說,中國本應擁有主權的國家頂級域名的兩個DNS解析系統的“頂級門戶”,其管轄權和控制權早就被“讓渡”給了美國、英國和印度。換句話說,中國對這兩個DNS解析系統的頂級門戶無權管理、無權監控、無權干預,遑論必須對中國政府、中國網絡信息空間領域負責的八個域名系統的唯一性、排他性和同一性。
事實上,讓渡一個“頂級門戶”,就相等于讓渡了全部的頂級門戶,只有美國、英國和印度有權和有能力決定、指揮與控制所有的路由表、信息通信供應鏈等,大量敏感數據被泄露、曝光和利用(包括修改、偽造)無可避免。
建議:立即收回被托管的DNS域名系統“頂級門戶”,交國家安全部門控制管理。
其次,中國大量的“專網”、“內網”及工業控制網絡(工控網),被認為實行了“物理隔離”,實現了“零信任”,“萬無一失”。實質是誤判、誤導,盲目樂觀、自欺欺人。其中潛藏的數據泄露安全問題甚至更加嚴重。
全球網信安全聯盟(GCA)指出,五個常見且不切實際的安全誤解(或“迷信”)認知包括:物理隔離網絡;專用的系統和協議;不可逾越的防火墻;端到端的電路通信;網信攻擊以牟利為動機。
GCA警告,在互聯互通的世界,不再存在真正的物理隔離網絡。隨著數字化(工業4.0和智能電網)的發展,“物理隔離”的作用逐漸消失或已經消失。運營技術(OT)和信息技術(IT)網絡正在融合,導致了新的安全威脅格局的演變。
近些年來,被敵意滲透或惡意劫持對用戶信息實施DNS遠程“重定向”的事件層出不窮、愈演愈烈。美國2020年12月大選期間,通過DNS域名重定向實施網絡攻擊的“太陽風”安全事件,被美國政府稱為“精心策劃的罕見‘網絡戰役’”。GDA指出,在“太陽風”事件中,攻擊者通過虛假域名(以及域名系統DNS的重定向),誘導用戶下載已植入惡意代碼的偽造升級軟件,導致近30萬用戶受到影響,包括9個美國政府部門。
俄烏網絡戰爭中,俄美類似“太陽風”事件的交鋒更加激烈。烏媒稱,烏克蘭的內政部、能源部、國防部、安全局、武裝部隊、金融機構等網絡信息資源被癱瘓;俄媒稱,克里姆林宮、國防部、外交部等網站曾無法訪問;黑客揚言,掌握了國際著名反病毒軟件(俄羅斯)卡巴斯基的源代碼。
在國內與公眾網絡“物理隔離”或“邏輯隔離”的許多黨政機關、金融機構、國企央企,卻將“內網”、“專網”的服務器托管、代管到境外(主要是美國和臺灣),是導致中國網絡信息空間重大安全危機的本質原因之一。大量國家主權數據、安全數據、敏感數據長期被裸置于境外,受境外實時隨機監控、操控,已經造成、正在造成以及未來必然更加嚴重地造成全局性的國家安全危機,后果不堪設想。
美國已經形成了主要由亞馬遜、谷歌、阿卡邁、颶風電子等形成的托管、代管中國服務器的多個數據庫集群產業鏈,以遠程控制與內容推送(CDN)模式,實時掌握和操縱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科技各方面的幾乎所有數據。
典型安全事件的案例包括但不限于:中國鐵路12306的客戶服務、出行、無線通信、電子支付、圖像、廣告、旅館、測試等8個方面的服務器,被臺灣中華電信和美國阿卡邁公司同步、實時、全方位系統控制;重慶電網數據被傳送(或被引導)到美軍管制的互聯網H根域名服務器系統;交通銀行、建設銀行大量數據在暗網被拍賣;光明會、美國國家安全局滲透中國工商銀行等重要中國單位托管在阿卡邁的服務器集群等。
網宿科技、首都在線等多家企業,公開提供國內服務器托管到境外、國外信息內容分發推送到國內的(CDN)服務,毫無顧忌,毫不避諱。國家主管部門存在重大治理和監管疏漏、瀆職問題,其中,濫發CDN牌照且疏于管理、治理和監控,后果很嚴重。或有主管官員有意放縱、內外串通。
建議:嚴查黨政機關、央企國企、金融機構、要害部門服務器托管、代管問題,查清底數、理清路徑、分清責任、肅清內患;限期整改、嚴懲腐敗,嚴格執法,杜絕后患。
(3)國家強制性標準受制于人
在網信業界,利用“國際標準”限制、束縛、打壓競爭對手,是美國的一貫做法。各國家和地區地域性組織都有所不滿、有所抵觸、有自己獨立的立場和看法。
2020年5月5日出臺的歐洲議會制定的《數字化服務法》,其中三項具體行動計劃之一,即建設“歐洲互聯網”(European Internet),提出:歐洲“數字云”(即歐洲互聯網)將促進基于數據和創新的歐洲數字生態系統;將推動競爭和標準制定;外國的網絡服務可以成為這種數字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但必須遵守歐盟的規則和標準,例如民主價值觀、數據保護、數據可訪問性、透明性和用戶友好性。
瑞典國防研究局報告認為,俄羅斯構建“主權互聯網”,事實上已經形成(俄美)“兩大陣營”(camps) 之間,從軍事、外交到標準組織和互聯網管理機構,在戰略上博弈、競爭和斗爭的網信空間戰場。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撤銷中國電信美洲公司的“214條款” 授權后不久,美國商務部所轄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再度要求美國各組織機構,配合“調查”中國過去10年參與有關國際標準制定中,影響新興技術國際標準制訂的“問題”;并在“聯邦資訊網”發表文章,要求拜登政府從“重建美國在全球標準制定中的影響力”等六個方面,對中國進行“標準政策行動”全方位的圍、追、堵、截,指責“世界貿易組織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條約,沒有能夠阻止中國11年前推出與Wi-Fi競爭的WAPI標準”,詭稱(中國)“可能認為推出多個相互競爭的標準最符合其利益。”
我國無線局域網安全機制強制性標準WAPI,與美國的 Wi-Fi并列,早已成為全球無線局域網領域僅有的兩個世界標準之一,早已有20多個國家超過2,000家公司采用,最終用戶產品型號早已超過2萬個,芯片型號早已超過500款(累計約170億顆)。但是,美國政府、司法、企業、媒體聯手,長期蠻橫地施壓中國政府,干預中國司法,威脅中國企業,阻撓打壓WAPI團隊,就是不準中國企業和用戶,采用中國政府2003年就已經明確發布的國家強制性標準WAPI,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小布什總統執政時期,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商務部長埃文斯、貿易代表佐利克曾聯名致信中國領導人,蠻橫要求中國放棄WAPI技術標準。
盡管WAPI的基礎框架方法作為國際標準正式批準發布已經10多年,盡管包括美國高通、博通、思科、蘋果、摩托羅拉等2,000多家企業的設計和產品已經融入WAPI,盡管WAPI已經嵌入全球超過50億臺設備,盡管……;但是,美國的Wi-Fi早已覆蓋中國,中國擁有全部自主知識產權的WAPI卻迄今不能在自己的祖國旗幟鮮明地推廣、理直氣壯地使用。
WAPI包括WAI(WLAN Authentication Infrastructure)和WPI(LAN Privacy Infrastructure)兩部分系統構成,分別實現對用戶身份的鑒別和對傳輸的業務數據加密。與Wi-Fi只是單向加密認證不同,WAPI是雙向加密認證,采用公鑰密碼技術,在無線客戶端(如手機、手提電腦等)與無線接入點AP上,都安裝有公鑰證書,從而多重保障數據信息的安全傳輸。換言之,身份識別和密鑰協商、報文封裝和加密解密,是WAPI技術優于Wi-Fi的基本功能和基礎保障,尤其在安全性方面表現突出。
正因為此,WAPI是中國網信業界保家衛國的創新北斗,是反擊和制衡美國壟斷網絡信息空間領域標準的重器,是讓美國霸權緊張、害怕,視作“眼中釘、肉中刺”的中國自強不息的重大成果。
WAPI的遭遇揭示了一個十分深刻的真理性認知,標準就是主權,標準就是安全,標準就是國家和企業的發展利益。
美國全面遏制與扼殺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發展的網絡信息戰爭已在進行時,我國網信空間安全牽動國家全局性安全的危機態勢十分明顯。沖破所有不合理、莫須有、欲置中華民族于困境死地的壁壘,全面啟動自主可控、自立自強的WAPI,就是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就是重新振奮我國網信業界“兩彈一星”精神,就是新時代建設網絡強國的偉大科學實踐和創新戰略導向。
建議:舉國上下,立即全面啟用WAPI!凡黨政機關、央企國企、金融單位、要害部門,必須優先使用WAPI,必須堅決抵制Wi-Fi!
2、我國對美國的網信作戰,必須逆勢而起,變被動為主動,化消極為積極,以不變應萬變。
俄美網絡戰爭深刻表明,網絡戰爭是前所未有的戰爭,也是持久彌新的戰爭;是科技實力的戰爭,也是智慧較量的戰爭;是走向未來的現代戰爭,也是未來已來的現代戰爭。
美中網絡戰爭,中國沒有退身步,只能應戰不能怯戰,只能逆勢而起,只能軍民聯手奮起抗爭。國家和業界必須不拘一格降人才;必須根治受制于人的弊端;必須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戰爭中建設網絡強國。
美國對中國網信作戰的目的很明確,就是不斷深化和強化對中國網絡(地緣)政治化、數據武器化的系統性威懾和威脅,形成隨時可以對中國實施全方位斷網斷服(癱瘓或崩潰式)打擊的高壓態勢和突破能力,遏制、阻撓、破壞、延宕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的數字化轉型發展和建設網絡強國、智慧中國。
我國網信空間領域長期追隨美國發展戰略和技術路線形成的盲目崇拜與迷信“專家”的慣性思維,導致管理理念與治理方法的嚴重滯后、深度困擾,自立自強的阻力、壓力和摩擦力巨大,自主創新的張力、拉力、向心力明顯不足。
我國現有網絡信息基礎設施投資浩大,覆蓋廣泛,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依賴性、依附性、依存性極強,長期被動受制,牽一發而動全局。至少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間,推倒重來,重(新)構(建)或廢棄(另起爐灶),既不現實,也不可能,更無必要。
在缺乏科學實踐驗證(證實和證偽)的情況下,強制性、排他性地自上而下規模部署IPv6,存在戰略導向失誤和技術路線錯誤,引發危害與威脅我國建設網絡強國和數字經濟轉型發展深層次、大范圍、多元化、潛在性的可預見及不可預見的安全問題,愈來愈嚴重危殆。
逆勢相對頹勢而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頹勢令人沮喪,敢于和善于逆勢而上,才能變被動為主動,化消極為積極,以不變應萬變。主動,就是振奮精神、自主創新;積極,就是破除迷信、求真務實;無論美西方怎樣變著法兒遏制、打壓、圍困、封殺我們,堅定不移地維護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底線、紅線、生命線,絕不動搖、決不改變。
建設網絡強國,主權是原則和底線,安全是核心和關鍵,發展利益是目標和歸宿。安全是綱,綱舉目張。網信領域新興的安全科學(SOS:Science of Security)、信息和通信技術(ICT)、運營和服務技術(OST)研究課題,構成不同科學、學術與技術領域跨域結合與聯合的網信技術和服務的創新探索,拓展了強化網絡基礎設施和數據信息主權與安全的治理能力,以及網絡強國、數據強國的新渠道、新思維、新境界、新天地。
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是克敵制勝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要從戰略科學的視角、視野和視界,果斷退出和擯棄“規模部署IPv6”的戰略誤導、技術羈絆,堅決從網信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層面務實介入,重新整合技術、資金、市場、政策、管理、治理等各方面抗打擊的積極資源,特別是我國優秀的創新技術和人才資源,破除崇洋媚外、反對個人迷信,不拘一格降人才,力求以最小的代價,高質量、高效率、高速度、低成本地推進我國建設網絡強國,為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轉型發展提供高安全性的基本保障與全方位服務,奠定繼往開來的未來網絡系統創新的基礎。
逆勢而上,必須堅持和實現最大限度地保護我國的數據主權和安全,最大限度地安全利用既有的網絡信息基礎設施,最大限度地構建獨立自主運行的“適應、并行、制衡”系統平臺,最大限度地推進“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網信空間領域的互聯互通。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要敢于對美國人造的互聯網“釜底抽薪”,集成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優秀技術和產品,盡快打造我國創造并自主可控的網信安全架構設計、標識和域名解析系統、數據保護超算系統、信息通信傳輸系統、漢字操作(輸入)系統等。
建議:堅決落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中辦發〔2022〕27號),積極打造國家文化專網,構筑基于漢語言文字和文化傳承的中華民族網絡信息空間和數字底座。可以在京津冀、長三角和大灣區先行試點、快速鋪開。
3、我國必須盡快建立抵御、制衡、反擊美西方網絡信息戰爭的軍民聯合作戰體系。
美俄網絡戰爭的最大亮點,是美國政府、軍隊與互聯網大資本的“軍民聯合行動(作戰)”。可以預料,這樣的“軍民聯合行動”同樣會針對中國,而且“斷網”會作為打擊中國的“重手”、“重拳”。投靠美國的漢奸認為,斷中國的網,不用擔心中國斷世界的網;斷中國的網,中國的網民將哀聲一片,必然引起全國性大范圍的社會混亂和動亂。
在美俄網絡戰爭中,雙方都采用了主動出擊、主動應戰、先發制人的網絡作戰戰術方法,這個共性特點,值得收集案例做比較分析和戰前推演。
俄羅斯以雇傭軍形式組建了多支網信特種作戰部隊,配合俄軍抗御美西方的網絡作戰行動。“到敵人后方去”,“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無論對美國、歐洲或烏克蘭進行的任何網絡輿論戰、信息戰、心理戰、混合戰、“破襲戰”(精準攻擊)等,都是網絡作戰整體的一部分。
與職業網軍相比,非職業的“網絡游擊隊”能夠發揮令對手出其不意的作用,能在對手疏忽之間追蹤、溯源其目標位置。我國民間亦不乏“網游”高手,曾有民間自愿組織的“紅客聯盟”,聲名顯赫。相關部門應迅速鼓勵、培養和扶植民間“網絡游擊隊”,配合我專業部門、網軍,抵御和反擊“匿名者”以及臺灣“1450”這樣的政治性職業黑客,很有必要,勢在必行。
承擔網絡信息安全責任和任務的央企國企,應當主動組建網絡信息安全和數據安全保護的專業“防守反擊”隊伍,加強個人網戰素質和團隊協同網絡作戰的訓練,接受國家戰時統一指揮,承擔承接第一時間應對“斷網斷服”的“消防”、搶救和善后任務。重點應關注直接關聯民生的交通(高鐵、地鐵、高速公路、城市道路交通指揮)、電力(輸、供電)、銀行(現金支取和非現金支付)等行業。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任何計算機網絡,只要采用或基于互聯網DNS域名解析系統、TCP/IP協議和協議族單一結構信息通信供應鏈系統的技術方法、標準和路徑,無論與公眾互聯網是物理隔離還是邏輯隔離,無論采用什么數字密碼、“防火墻”,都難以避讓和排除重大安全隱患。因此,無論國家、單位、個人的重要數據,凡是生成、存放在計算機系統中的,一定要做脫機存儲備份,必要時,只能使用(從來)不上網、不聯網的單機操作。
建議:各地迅速建立和強化戰時應急通訊系統。包括傳統的長途電話和市話系統,如載波、微波專線通信,有線廣播電視網絡;傳統的電報系統,如電傳(telex)、摩斯電碼、明碼呼叫,約定密鑰;傳統的機要通信,如紅機系統,機要專遞等。
四、結語
我國亟須立即進入網絡信息空間領域的戰時狀態。
對美國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網絡信息戰爭幻想和臆測,都極其危險,徒勞無益。
面對美國的網絡戰爭,我們必須要有變劣勢為鋭勢,化頹勢為攻勢,轉弱勢為強勢扭轉乾坤的大智大勇,充分做好人才和技術充分必要條件的準備。伴隨著競爭和斗爭,網絡戰爭也許總在進行時,沒有最終結束時;今天的優勢,明天也許是劣勢;曾經做贏家,未必不會變成輸家。
水無常形,兵無常勢。太多的未知因素和信息不對稱,限制了人們的思維能力,同時,也寬泛了人們的思考空間。
網絡戰爭沒有現成的教科書,投入實戰,戰爭中學習戰爭,是最好的教科書。
2022年7月24日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移動通信聯合會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網】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現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絡時代發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牟承晉|美網戰我,我當若何?——俄烏網絡作戰于我之警醒和啟示
2022-07-25?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