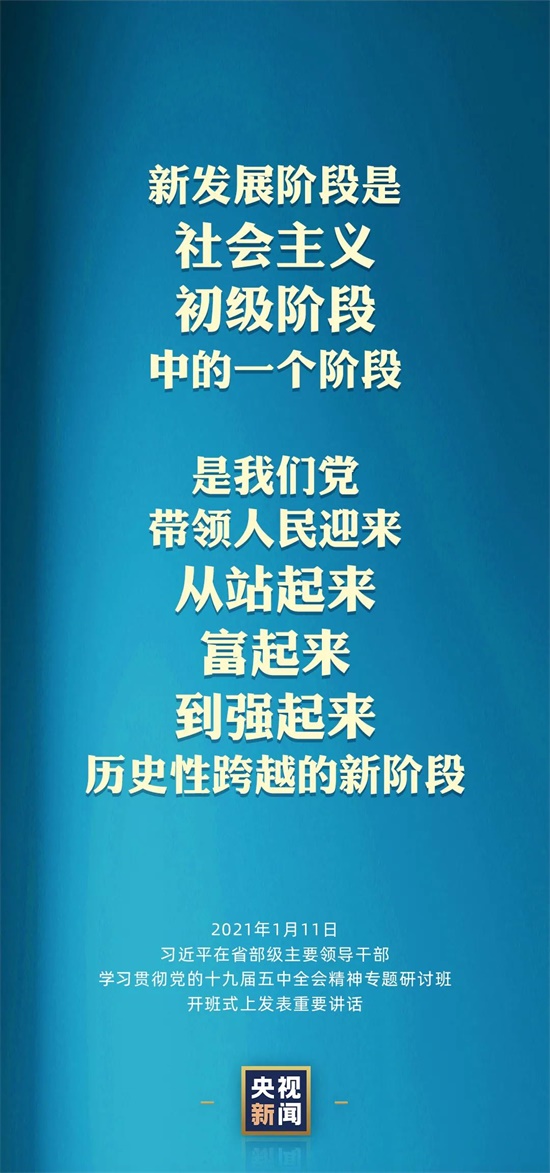弗朗西斯·福山|文
《民主季刊》創刊于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在政治學上,“第三波”專指1970年代以來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塞繆爾·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闡述了這個概念)尾聲:彼時柏林墻已倒塌,蘇聯行將解體;南歐和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已經開始轉型,東歐正加速偏離共產主義,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和前蘇聯的民主轉型則剛剛開始。
總體來說,在過去45年,全球民主化進程取得了很大進展,1970年民主選舉國家僅35個,而2014年則達到110個。
近年來,全球民主國家表現差勁有目共睹
然而,正如拉里·戴蒙德(LarryDiamond,美國政治學家)所指出的,2006年以來民主開始衰退,“自由之家”(FreedomHouse,是一個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總部位于美國華盛頓特區)對民主國家的測評分數每年呈遞減趨勢。特別是2014年,民主的表現更是差強人意。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讓人們對阿拉伯世界即將到來的終結充滿期待,他們當年處于第三波浪潮之外。可局勢卻最終惡化成埃及出現新的獨裁統治,利比亞、也門和敘利亞呈無政府狀態,而敘利亞和伊拉克也出現了新的激進伊斯蘭運動:伊斯蘭國(ISIS)。
很難知曉是否就如股市回調一樣,我們在向全球推進民主方面也經歷著短暫的挫折。也難以知曉2014年的這些事件,是否預示著全球政治出現更廣泛的轉變,民主的替代品是否正在崛起。
不管是哪種情況,近年來全球民主國家表現差勁有目共睹。糟糕的表現始于最發達、最成功的民主國家,如美國和歐盟,它們經歷了1920年代末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似乎陷入了一段時間的增長緩慢和收入停滯狀態。與此同時,從巴西、土耳其到印度,一些新興民主國家在許多方面的表現也讓人失望,內部抗議運動對這些國家產生深遠影響。
反對專制政權的自發性民主運動在公民社會持續興起,如烏克蘭、格魯吉亞、突尼斯、埃及等。但是這些運動從未成功領導并建立穩定、運作良好的民主國家。值得追問的是,為什么在世界各地,民主表現得如此讓人差勁?
未能建立治理良好的國家,是民主的致命問題
在我看來,過去30年民主遭遇的眾多挫折在于一個重要因素,與制度化失敗有關——在許多新興和已有的民主國家,國家能力沒能跟上受歡迎的民主責任制的步伐。相對于從一個威權政體轉型成一個有定期、自由和公正選舉的政體,從一個世襲或新世襲式國家轉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會更難。未能建立現代化的、治理良好的國家,是近來民主轉型的致命問題。
現代自由民主國家包含三種基本要素:國家、法治和民主責任制。
首先,國家是對強制力的合法壟斷,可以在特定的領土內行使權力。國家集中并使用權力來維護和平、保護社會免受外敵侵略、執行法律,并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
法治是一套規則,反映了社會價值觀,不僅約束公民,也約束那些可以運用強制力的精英。如果法律不限制強者,它就相當于只是行政部門的命令。
最后,民主責任制試圖確保政府的行為是為社會的整體利益考慮,而不是簡單地為了統治者的自我利益。它通常由一定的程序才能達成,如自由和公正的多黨選舉,盡管程序責任制并不總是與實質責任制一致。
一個自由民主國家能夠平衡這些潛在的沖突要素。國家產生并行使權力,而法治和民主責任制確保權力用于公共利益。沒有約束體系的國家是獨裁國家。一個處處充滿約束而無權力的政體是無政府主義。
正如塞繆爾·亨廷頓所言,一個政體在限制權力之前,首先必須行使權力。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話說,“軟弱的管理是糟糕的管理的代名詞;假如政府軟弱無能,不管它理論上是什么樣子,實際上它就是糟糕的政府。”
世襲制國家與現代國家還有進一步的重要區別。現代國家渴求公正,基于公民權利平等地對待每個人,而不是看他們是否與統治者有個人關系。相比之下,世襲制國家中,政體被看做一種個人財產,公共利益與統治者的私人利益沒有界限和區分。現今完全世襲的社會已不復存在,因為沒有人敢聲稱擁有整個國家的所有權,就像過去的國王和女王那樣。
然而,現在仍有許多看起來是現代政治的新世襲國家,這些國家事實上仍采用分贓式盜賊統治,為內部人士謀取利益。新世襲主義可以與民主共存,產生廣泛的操控和裙帶關系,讓政客與其支持者共享國家資源。在這樣的社會中,個人從政不是為了追求公共利益,而是中飽私囊。
國家運轉依靠的是高壓政治,這就是為什么國家權力讓人們恐懼和仇視。眾所周知,邁克爾·曼區分了“專制權力”和“基礎性權力”,前者與高壓政治有關,后者指提供公共物品、照顧公共利益的能力。這種區分可能會讓我們認為,“好”的國家擁有基礎性權力,“壞”的國家利用專制權力。
事實上,高壓政治對所有國家都很重要。成功的國家將權力轉化成權威——公民深信國家行為合法而自愿服從。但不是所有公民都愿意服從法律,哪怕是最合法的民主政體都需要警察來執行法律。如果沒有人因為違法而進監獄,就不可能完全控制腐敗。簡單通過立法不能保證執法能力,還需要進行人力培訓,建立制度性規則,來管理人們的活動。
國家無法提供高質量公共服務,會引發民主合法性的喪失
過去25年的經驗教會了我們什么?那就是在這三個體系(指前文所述國家、法治和民主責任制)中,民主比法治或現代國家更容易構建。換句話說,現代國家的發展沒有跟上民主制度發展的步伐,導致出現了不平衡的情況:新興民主國家(有時甚至是發展完善的民主國家)無法跟上公民對國家高質量服務的要求。反過來,這也引發民主的合法性喪失。相反,中國和新加坡等國家能夠提供這些服務,這使得它們在世界各地的聲望不斷提高。
阿富汗和伊拉克最近的經歷說明了這個問題。美國分別于2001年和2003年侵略和占領了這兩個國家,隨后在國際社會幫助下,美國在兩國組織民主選舉,產生新的政府。盡管兩國的民主質量——特別在阿富汗,2009年和2011年的總統選舉被控嚴重造假——被很多人質疑,但至少民主程序已經形成,建立了具有表明面上合法的領導機制。
然而,阿富汗和伊拉克均沒有發展成現代國家,無法保衛領土免遭內外部敵人侵犯,也無法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服務。兩國均受內部叛亂困擾,2014年美國訓練的伊拉克部隊在伊拉克北部遭到ISIS沖擊而潰散。兩國都被極高程度的腐敗困擾,進而阻礙了他們提供政府服務的能力,削弱了自身的合法性。美國及其盟國對兩國進行了巨額的國家建設投資,效果似乎也很有限。
國家建設的失敗在烏克蘭暴亂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2004年橙色革命迫使烏克蘭重新進行總統選舉,當時的總理亞努科維奇被反對派候選人尤先科擊敗,西方民主伙伴們歡呼雀躍。但是,新的橙色聯盟軟弱腐敗,并沒有改善烏克蘭政府管理的總體質量。因此,2010年在被許多觀察人士看做自由公正的選舉中,亞努科維奇擊敗尤先科,重新當選。
亞努科維奇的統治伴隨著更多的掠奪行為,2013年末他宣布,暫停與歐盟簽署協議,轉而尋求加入普京主導的亞歐經濟聯盟,隨后,烏克蘭首都基輔爆發了新一輪抗議活動。同時,普京已經在俄羅斯鞏固了日益狹隘的規則,樹立了自身在俄羅斯的地位,使得2014年2月亞努科維奇下臺后,俄羅斯完全吞并克里米亞成為可能。
我認為,目前俄羅斯和烏克蘭新政府及其西方支持者之間的沖突,與其說是民主本身產生的矛盾,不如說是現代政治秩序與新世襲式政治秩序的沖突。
毫無疑問,克里米亞被吞并以后,普京在俄羅斯更受歡迎,并且在下一任總統選舉中很可能會獲得壓倒性的勝利。然而俄羅斯民眾所面臨的真實選擇卻是另一回事——是選擇由客觀的、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政府來領導社會,還是選擇由腐敗的、試圖利用國家謀取私人利益的政治精英聯盟來統治社會。
全球民主國家的合法性不是取決于民主體制的深化,而是取決于提供高質量治理的能力。烏克蘭如果不能解決讓尤先科下臺的腐敗之風,它將無法生存。
過去30年間,民主已經深深扎根于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如今巴西、哥倫比亞和墨西哥等國所缺少的是提供教育、基礎設施和公民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
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也是如此,印度目前飽受普遍的裙帶關系和腐敗困擾。2014年,印度果斷地轉向人民黨領袖納倫德拉·莫迪,希望他能提供堅決的領導,建立強有力的政府,取代過去十年來無能腐敗的國大黨領導的聯盟。
對民主轉型的一種誤解:認為國家的現代性與零腐敗相聯系
到目前為止,在民主轉型方面有大量的文獻資料,多數最初發表在《民主季刊》上。也有小部分文獻討論了如何從新世襲制度轉型成現代國家的問題,盡管過去十多年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這些文獻反映了概念上的赤字,即對根本問題存在本質上的誤解。
例如,有一種觀點傾向把國家的現代性與零腐敗聯系起來。當然,腐敗在很多社會是一個巨大的問題。盡管腐敗水平與糟糕的國家表現有高度的相關性,可兩者完全不同。
一個相對廉潔的國家不能提供基本服務,可能僅僅因為它沒有這樣的能力。例如,沒有人會認為,幾內亞、塞拉利昂或利比里亞一直無法處理最近的埃博拉疫情,是因為他們的公共衛生系統中腐敗之風盛行。相反,問題是這些國家的人力和物質資源不足——醫生、護士、醫院供電,以及干凈的水資源等缺乏。
因此,相比零腐敗來說,“國家能力”更能描述什么是國家現代性的核心。現代國家提供各種復雜的服務,讓人眼花繚亂,從保存經濟和社會數據,到救災、預報天氣和控制飛機航路。所有這些活動都需要在人力資源和物質條件方面進行巨額投資,保證政府操作;簡單的零腐敗無法做到這些。
此外,對于歷史上強大國家能力形成的方式,卻亟待闡明。
眼下,國際團體就如何追求優良執政形成了某種共識,該共識可體現在諸如參與式預算(社會公眾能參與決定部分預算決策的協商機制)、開放政府伙伴關系(全球范圍內鼓勵透明有效、負責人治理的項目)及全球數不勝數的追求政府透明化的組織所提出的計劃之中。
這些舉措背后的理論便是,優良的政府管理來自更上層樓的透明度和負責制。以上舉措認為,市民對政府腐敗及瀆職行為更加了解后,會出于憤怒而要求更好的國家表現,而這將進一步推動政府進行自身改革。換句話說,更優質的民主體現為解決政府腐敗、國家能力不足的方案。
這一策略的唯一問題在于,我們缺乏經驗證據來證明歷史上或當前現有高效政府正是經由這種途徑產生的。
許多擁有相對高效政府的國家——例如中國、日本、德國、法國及丹麥——在專制條件下曾構建出一種現代“韋伯式”的官僚機構;而最終成為民主國家的政體之所以能繼承高效國家機構,僅僅是因為后者恰好在轉型中保留了下來。
建筑現代政府的動機并非迫于了解國情、受到動員的草根市民的壓力,而是迫于通常出于國家安全考慮的精英團體的壓力。查爾斯·蒂利(美國政治學家、社會學家)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戰事造國家,國家造戰事”,這句話不光總結了早期現代歐洲的大部分情況,還概括了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正是當時的戰亂)導致了公元前三世紀一統天下的秦作為一個非個人化的國家崛起。
無獨有偶,我們同樣缺乏證據顯示,當前致力于通過提高透明度和負責制,以推行優良統治的當前捐贈方及非盈利組織,能夠對國家表現施加相當程度的影響。
有理論認為,提高政府工作可見度與政府最終輸出成果的質量應當是正相關的,這一理論建立在諸多大而無當的假設之上:諸如,市民會關心政府差強人意的表現(而不是滿足于從以德治國的舉措中獲益);他們能夠組織政治性質活動對政府施壓;國家的政治機構能夠準確無誤地將草根情緒傳遞給政治家,并使其負責;最后一點,政府實質上具備按市民要求運行的能力。
民主與現代國家建立這兩者的先后順序,決定了政府的質量
國家現代性與民主之關系的淵源遠比當代理論認為的要復雜。我在馬丁·舍夫特(MartinShefter)率先建立的框架之下,于別處撰文時提到過,民主(根據選舉權的推廣程度進行衡量)與現代國家的建立,這兩者之間先后順序,決定了政府的長期質量。
如果現代國家政權的鞏固早于選舉權的推廣,國家通常能在現代繼續存活;如果民主早于國家改革,則往往會招致裙帶關系的泛濫。這一點在美國這一率先賦予全部白人男性選舉權的國家得到佐證,在這之后,美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高度泛濫的侍從制政治體系(在美國歷史上被稱為“政黨分肥制”或“政黨庇護制”)。
在19世紀的美國,民主和國家質量很明顯是不相匹配的。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在一個收入、教育程度較低的民主國家中,比起許諾推行程序化的公眾政策,個人化的選民激勵手段(即裙帶關系的核心)更能動員選民參與投票。
不過,當經濟發展到更高水平時,情況發生了改變。高收入的選民更難被個人化的賄賂所收買,并且,他們更關心程序化的政策。除此之外,高水平的發展通常由市場經濟的發展所驅動,后者為個人財富提供了來自政治之外的創收選擇。裙帶關系猖獗的臺灣選舉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結束;自那之后,臺灣選民擁有更多財富,不那么好賄賂了。
盡管在人均收入較低時,民主充當了裙帶關系的推手,在國家變得富裕時,它能開辟道路,創建更高質量的政府。
再次以美國舉例:截止到19世紀80年代,美國迅速地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城市工業社會,通過鐵路等新技術緊密聯結成一個龐大的大陸市場。經濟發展催生了新的經濟參與者——城市從業人士,更為復雜的商業利益體,以及更普遍的中產階級個體——他們都期望更高質量的政府,同時與現有政黨分贓制的利害關系非常薄弱。
一場發自草根的運動使美國政府于1883年通過了《彭德爾頓法案》,該法案樹立了聯邦官僚機構中擇優上崗的原則,后任總統諸如西奧多·羅斯福(執政時間為1901-1909年)及伍德羅·威爾遜(執政時間為1913-1921年)都大力推行。
在那之后的幾代中,政黨首領及政治機器的發展勢頭不減,但時至21世紀中葉,在政治活動的推行下,它們在美國絕大多數城市中都逐漸銷聲匿跡。如果當代民主國家如印度、巴西要解決政黨庇護及腐敗的問題,它們需要遵循一條類似的途徑。
不過,美國有一個今日許多新興民主國家所不具備的重要優勢,那就是它一直以來都具備強大的警力,并且能實施政府通過的法律。這一能力扎根于《普通法》,于殖民地時期繼承自英國,隨后在獨立之前很好地實現了體制化。美國各個層面的政府始終能在抑制犯罪方面維持相對強大的警力。
這一強制性權力基于對法律正當性的強大信念,因此得以在絕大多數地方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權威。實施能力構成了國家能力與法律規約間的重合領域,對于處理腐敗問題是至關重要的。政府官員的行為取決于激勵機制——并不僅僅是通過工作換取足夠的薪酬,而是畏懼違法招致的懲罰。許多國家之所以存在逃稅受賄的行為,是因為違法者入獄的可能性太小。
自2003年格魯吉亞發起玫瑰革命之后,薩卡什維利政府在眾多前線鎮壓腐敗:管理交警、懲處避稅以及取締罪行猖獗的犯罪團體“法網竊賊”。主要舉措是提高透明度和執法積極性(例如在網上公布政府數據,提高警員工資十倍之多),有效的實施依靠不一樣的警察機構,它們高調地公布對高層官員及商人的逮捕。
等到了薩卡什維利任期結束之際,這一高度提升的警察權力被多方面濫用,從而引發了一場政變,于是畢齊納·伊萬尼舍維里及格魯吉亞夢想政黨聯盟獲選上臺。
權力濫用不應該掩蓋國家強制權力保障高效執法的重要性。遏制腐敗需要全面扭轉國民整體對行為標準的期望——如果我身邊人人都在受賄,那我要是不分一杯羹,就是個傻子。在這樣的情形下,恐懼比良好意愿或經濟獎勵更為有效。
在玫瑰革命之前,格魯吉亞是前蘇聯腐敗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如今,在數項政府舉措之下,它已經躋身最不腐敗國家之列。很難舉出不執行足夠強權、同時管理得當有效的政體。在當代,如果在提高透明度和負責制的同時,不努力加強執行力的話,推行優良政府管理的行為注定是要落敗的。
關于民主的研究,還要重新考量現代國家機構的誕生及衰敗
塞繆爾·亨廷頓在《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寫道,政治維度上的發展常常未能跟進社會現代化進程,從而招致政治無序。國家機構相應地也無法跟進民主機構的發展。
這一結論對于美國及其他進行民主推廣的民主國家,具有若干重要的啟示。在過去,它們強調通過支持專制國家中的民間社會組織,從而確保公平競爭,并歡迎獨裁制轉型的可能。
然而,創建一個可行的民主政權還需要兩大階段,從而確保最初抵制獨裁者的動員力量得以體制化并轉化為長期可行的執行方式。
其一是將社會組織動員起來,建立可參與、競爭的政黨。民間社會組織通常著眼點過于狹窄,并且沒有致力于動員選民——這是政黨所獨有的領地。缺乏建立政黨的能力,解釋了為什么在諸如俄羅斯、烏克蘭、埃及等轉型國家,自由派常常在選舉中敗北。
第二個必需階段則關乎國家建立和國家能力。一旦民主政府當權,它必須處理政務——也就是說,它必須發揮合法的權威,向民眾提供基礎服務。
推行民主的團體在初期動員和轉型上更上心,忽略了民主統治的諸多問題。如果不具備出色管理的能力,新的民主政府會辜負追隨者的期望,從而推翻自己的合法性。誠如美國歷史顯示,忽視國家現代化的民主化進程,實質上會導致削弱政府的執政表現。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國家現代化只能在專制獨裁的條件下得以完成。的確有許多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先完成了國家建設,然后才完成了民主化建設——亨廷頓將之稱為“專制過渡”——但這并不意味著這對當今國家來說是一條可行的策略,畢竟當今社會對民主的訴求與期待更高了。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