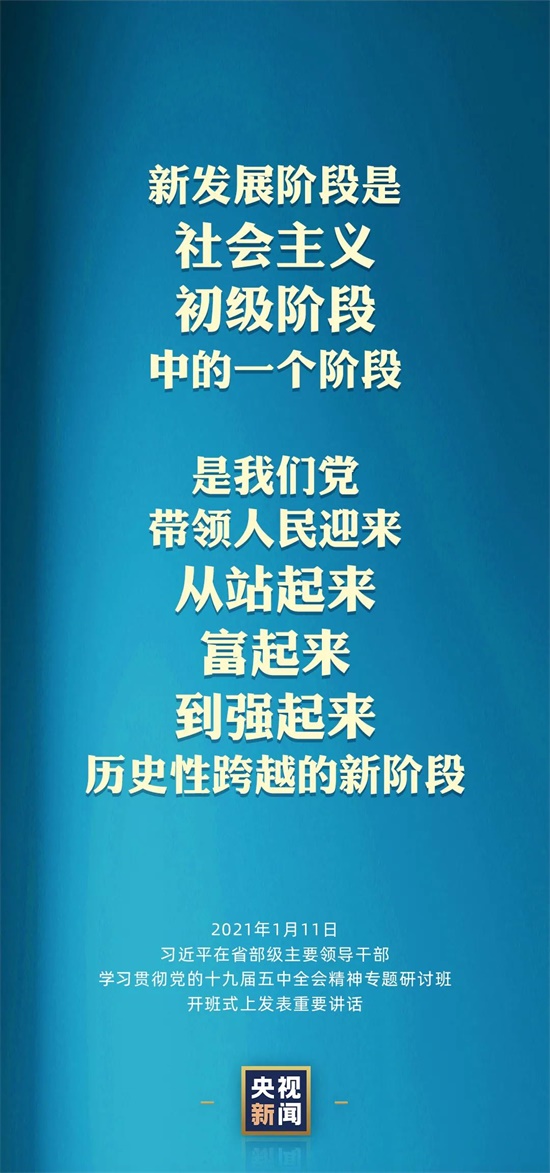在文化大革命時(shí),我是北京景山學(xué)校的一名中學(xué)生,1968年8月報(bào)名去插隊(duì),作為北京知青來到內(nèi)蒙古牧區(qū)。當(dāng)時(shí)北京知識(shí)青年插隊(duì)去邊疆地區(qū)的人數(shù)很多。我插隊(duì)的地點(diǎn)是內(nèi)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旗沙麥公社,那五年的時(shí)間我們?cè)谶@個(gè)純蒙古族草原牧區(qū)當(dāng)牧民,住蒙古包、騎馬放羊,在不同季節(jié)逐水草游牧,知識(shí)青年努力學(xué)習(xí)蒙語,努力適應(yīng)草原游牧生活。當(dāng)年的這段經(jīng)歷給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那時(shí)的牧民非常歡迎毛主席派來的知識(shí)青年,給我們安排蒙古包、畜群,在生活條件方面給我們安排得很好。當(dāng)時(shí)北京的學(xué)校都停課,也沒有參加高考上大學(xué)的可能性,我們這些中學(xué)生們都憧憬著上山下鄉(xiāng),希望能夠在這個(gè)廣闊天地中有一番作為,到農(nóng)村牧區(qū)去就是為了接受“再教育”,向貧下中農(nóng)學(xué)習(xí)。我們當(dāng)時(shí)就是這樣做的。
在插隊(duì)期間我們必須學(xué)蒙語,因?yàn)槟莾撼舜箨?duì)書記會(huì)說幾句漢話,整個(gè)大隊(duì)沒有什么人會(huì)說漢話,所有的日常生活交流、生產(chǎn)活動(dòng)安排都是使用蒙語,我沒有學(xué)習(xí)蒙文,采用的辦法是用漢字標(biāo)注蒙語口語。牧民們跟知青的關(guān)系都很好,也很愿意教我們。
到了1968年底、1969年初的時(shí)候,在內(nèi)蒙古發(fā)生了針對(duì)“內(nèi)蒙古革命黨”(簡(jiǎn)稱“內(nèi)人黨”)的政治運(yùn)動(dòng),也叫做“挖肅”運(yùn)動(dòng),當(dāng)時(shí)滕海清是內(nèi)蒙古的軍管會(huì)主任,不久這個(gè)政治運(yùn)動(dòng)從城市擴(kuò)大到草原牧區(qū)。我所在的沙麥公社也來了軍管會(huì),傳達(dá)說根據(jù)上面的材料認(rèn)為我們大隊(duì)有人被懷疑是“內(nèi)人黨”,開列了幾個(gè)人的名字,要求監(jiān)管起來。怎么辦?我們大隊(duì)有52名來自北京的知識(shí)青年,在這件事上產(chǎn)生了很大的分歧。親眼見過北京“文革”初期斗“走資派”的過程,我們的頭腦清醒了一點(diǎn),覺得事情恐怕沒有這么簡(jiǎn)單。當(dāng)時(shí)我們大隊(duì)的知識(shí)青年分裂為兩派,曾有十分激烈的爭(zhēng)論,也許正因?yàn)椴糠种嗟牡种疲谖覀兇箨?duì)沒有發(fā)生過激的行為。在“挖肅”正式宣布平反之后,知青的兩派和解了,而且知青和牧民之間的關(guān)系也并沒有出現(xiàn)大問題,很快恢復(fù)到“挖肅”原來的良好關(guān)系。
我是1973年離開的,到70年代后期所有知青都陸續(xù)返回北京,但是一直到今天,知青和大隊(duì)牧民還保持聯(lián)系,關(guān)系很好。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鄉(xiāng)”無意中構(gòu)建起草原蒙古族社區(qū)與北京之間的感情紐帶,以知青為主組織的“草原戀”歌唱團(tuán)實(shí)際上寄托著一代北京知青對(duì)那片草原和牧民們的無盡眷戀。我們大隊(duì)的知青每隔一兩年就串聯(lián)幾個(gè)人一起回大隊(duì)去看看當(dāng)年的牧民朋友,有的還帶著自己的孩子,我也去了多次,我最后一次去是2003年,臨走時(shí)牧民送我一件新的蒙古袍。我們大隊(duì)的牧民漢語不太好,現(xiàn)在牧民們到北京來看病,聯(lián)系醫(yī)院、找大夫,都是我們知青在幫忙。當(dāng)年插隊(duì)的時(shí)候,我們向牧民孩子學(xué)說蒙語,他們向知青學(xué)說漢語,大家在生活和生產(chǎn)活動(dòng)中彼此互助。我們從北京帶了理發(fā)推子,所以大隊(duì)的牧民要理發(fā)都來找各蒙古包的知青,做了好吃的飯就相互送一些,有的蒙古老人把我們當(dāng)作自己的孩子來關(guān)心,感情就像一家人。所以,我所認(rèn)識(shí)和理解的民族關(guān)系,是在這五年草原生活中和這些純樸善良的蒙古族牧民們的朝夕相處中體驗(yàn)出來的。
我原來不是專門研究民族問題的,在美國(guó)學(xué)習(xí)期間我的主修是人口學(xué),當(dāng)時(shí)博士論文選定的題目是人口遷移。在考慮具體調(diào)查地點(diǎn)時(shí),由于我對(duì)內(nèi)蒙古有插隊(duì)情結(jié),我選擇了內(nèi)蒙古作為調(diào)查地點(diǎn)。我除了在北京居住的時(shí)間最長(zhǎng)之外,其次就是在內(nèi)蒙古生活了九年,后來在美國(guó)學(xué)習(xí)和訪問先后居住了七年,內(nèi)蒙古可以算作我的第二故鄉(xiāng)。1985年我到內(nèi)蒙赤峰地區(qū)農(nóng)村開展人口遷移的戶訪調(diào)查,那時(shí)基層的民族關(guān)系很好,沒什么矛盾。1985年我在赤峰調(diào)查過的那些村子,1989年,1995年和2005年我又多次回訪和開展追蹤調(diào)查,見到當(dāng)?shù)氐母髯宕迕褚廊挥X得很親切。我個(gè)人的感覺是,在農(nóng)村牧區(qū)的基層社區(qū)不應(yīng)該存在什么“民族”矛盾的,人們之間的相處,看的是對(duì)方這個(gè)“人”,而不是他的“民族成分”。
1987年我從美國(guó)回到北京大學(xué)任教,這一年夏天我去西藏開展社會(huì)調(diào)查,在拉薩我感到當(dāng)?shù)厣鐣?huì)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些不穩(wěn)定因素。這年春天,八角街派出所被騷亂人群縱火燒毀。
那時(shí)候我在拉薩老城區(qū)各居委會(huì)進(jìn)行戶訪調(diào)查,了解當(dāng)?shù)鼐用竦木蜆I(yè)、收入和居住條件等情況,和老城區(qū)4個(gè)街道辦事處的街道干部進(jìn)行座談,他們都是本地藏族,我有一個(gè)藏族助手幫我翻譯,他們也能說一些漢語。當(dāng)時(shí),這些基層藏族干部向我們?cè)V說最多的、他們表示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撥亂反正”。在其它地方的“撥亂反正”、落實(shí)政策主要是平反冤假錯(cuò)案,在拉薩是什么情況呢?
參加座談會(huì)的十幾個(gè)街道辦事處的干部跟我們講,達(dá)賴集團(tuán)那些人過去是農(nóng)奴主和貴族,一個(gè)干部講述達(dá)賴這些貴族過去是怎么壓迫、剝削他們,他的一個(gè)姐姐就是被農(nóng)奴主賣掉的,再也沒找到。共產(chǎn)黨來了,他們就全心全意跟著共產(chǎn)黨,盡管那時(shí)候農(nóng)奴主禁止農(nóng)奴參加解放軍組織的學(xué)習(xí)活動(dòng),他們還是偷偷去參加。1959年達(dá)賴集團(tuán)叛亂的時(shí)候,他們堅(jiān)決支持解放軍。“民主改革”解放農(nóng)奴,他們才真正翻了身,分到房子,有了工作。但是“撥亂反正”之后,他看到共產(chǎn)黨把有些農(nóng)奴主又請(qǐng)回來了,還給他們安排政協(xié)、人大、政府的職位,動(dòng)員他們回來定居。這些貴族回來以后神氣得很,耀武揚(yáng)威。為什么共產(chǎn)黨的政策又變了?這些街道干部對(duì)此很不理解。當(dāng)時(shí)老城區(qū)有許多貴族的房子,1959年這些貴族跟著達(dá)賴去了印度之后,新政府就把這些流亡貴族的房子無償分給了原來的奴仆和農(nóng)奴。現(xiàn)在,為了給這些貴族“落實(shí)政策”,政府要求街道干部動(dòng)員居住在這些房子里的居民們搬出來。他們說:“我們?cè)趺慈プ鲞@種工作?”,“共產(chǎn)黨的天怎么變成這樣了?”現(xiàn)在,那些當(dāng)年叛逃的農(nóng)奴主回來以后神氣極了,要求政府對(duì)他原來的房產(chǎn)和當(dāng)年沒能帶走的金銀細(xì)軟給予賠償。政府也確實(shí)在清理核實(shí)當(dāng)年對(duì)叛逃貴族產(chǎn)物進(jìn)行沒收、分配的情況,然后以現(xiàn)金方式給予賠償。
1989年西藏自治區(qū)出版了第一本《西藏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統(tǒng)計(jì)年鑒》,后來改名為《西藏統(tǒng)計(jì)年鑒》,《年鑒》中“西藏自治區(qū)銀行現(xiàn)金支出情況”表中有一項(xiàng)叫“國(guó)家對(duì)個(gè)人其他支出”,是除了當(dāng)時(shí)的工資、獎(jiǎng)金之外支付給個(gè)人的“其他支出”,1994年這一項(xiàng)的金額達(dá)到3.1億元。我在其他自治區(qū)的統(tǒng)計(jì)年鑒里都找不到這一項(xiàng),其它省市自治區(qū)都沒有這一項(xiàng),這就是支付給回國(guó)貴族的“補(bǔ)償金”。這些藏族干部給我講了一件事,有個(gè)回來的貴族,政府給他支付了上千萬元的補(bǔ)償。過了一個(gè)月,他又來找政府,說我上次給你們的清單里忘記寫一條項(xiàng)鏈,值100萬元,結(jié)果政府又給他補(bǔ)償了100萬元。對(duì)于這種作法,這些藏族干部表示無法理解。聯(lián)絡(luò)和團(tuán)結(jié)境外流亡的藏族人員,希望他們回歸參加國(guó)家的建設(shè)事業(yè),消解境外達(dá)賴集團(tuán)的影響力,這無疑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有些做法在客觀上傷害了那些農(nóng)奴出身、長(zhǎng)期鐵了心跟共產(chǎn)黨走的藏族干部和他們?cè)谌罕娭械耐牛@樣的政策就會(huì)帶來長(zhǎng)遠(yuǎn)的嚴(yán)重后果。
我們?cè)谖鞑厮降母鱾€(gè)地方,藏族基層干部都感到共產(chǎn)黨的政策變了,有些當(dāng)?shù)厝顺靶@些干部,說他們跟共產(chǎn)黨跟錯(cuò)了。有個(gè)村里的藏族女積極分子,過去跟著政府參加“土改”,“文革”時(shí)期也跟著去拆寺廟。政府落實(shí)宗教政策,撥錢對(duì)寺廟重新修建,風(fēng)向變了,有些信教民眾就嘲諷和疏遠(yuǎn)這位女積極分子,她覺得在村里抬不起頭,現(xiàn)在變得特別虔誠,給寺廟捐獻(xiàn)很多錢,還經(jīng)常去無償為寺廟勞動(dòng)“贖罪”。這些藏族干部向我們講述這些事時(shí),他們講的不是漢族和藏族之間的問題,不是民族問題,而是階級(jí)問題,他們認(rèn)為共產(chǎn)黨的階級(jí)政策變了,過去愛農(nóng)奴,現(xiàn)在愛貴族,階級(jí)立場(chǎng)變了。他們認(rèn)為共產(chǎn)黨的宗教政策也變了,1950年代宣傳宗教是迷信,那些活佛是些騙子和剝削者,“破四舊”時(shí)鼓勵(lì)拆廟,而現(xiàn)在活佛成了香餑餑,成為政府的上賓,說這是尊重宗教,反而把這些在解放軍進(jìn)藏時(shí)積極支持解放軍、1959年支持政府平叛的藏族積極分子冷落在一邊,這使他們?cè)诿癖娧劾锍闪诵Ρ_@些出身農(nóng)奴家庭的藏族基層干部向我們抱怨、傾訴時(shí)的無奈表情,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即使那年拉薩發(fā)生了街頭騷亂,我在這些交談中也沒有感覺到這些矛盾的本質(zhì)是民族問題。
1997年我到新疆去調(diào)查,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出了1990年的巴仁鄉(xiāng)事件。我在南疆喀什調(diào)查的時(shí)候,地委統(tǒng)戰(zhàn)部長(zhǎng)是一個(gè)當(dāng)年16歲跟隨王震大軍進(jìn)疆的漢族干部,他在喀什地區(qū)當(dāng)過十幾年公社書記,維語非常好,還自學(xué)阿拉伯語,那時(shí)有個(gè)維族小伙子給他趕輛驢車,他背著水壺到各村去安排生產(chǎn)、處理問題,是個(gè)艱苦樸素、全心為群眾辦實(shí)事的干部。后來中央政策要求新疆全區(qū)從公社一級(jí)撤出全部漢族干部,他才離開那個(gè)公社。他調(diào)走的時(shí)候,當(dāng)?shù)鼐S族群眾非常依依不舍。1980-1990年期間,南疆4地州外流干部9817人,其中93.3%是漢族干部。等到90年代各地不斷發(fā)生惡性事件,基層信息不通,政府又決定再次向鄉(xiāng)鎮(zhèn)一級(jí)派駐漢族干部,但是此時(shí)派來的年輕漢族干部的政治素質(zhì)、維語能力、工作作風(fēng)遠(yuǎn)遠(yuǎn)趕不上前幾年撤出的老一代漢族干部,出現(xiàn)無法彌補(bǔ)的斷層。真是既有今日,何必當(dāng)初!
這位統(tǒng)戰(zhàn)部長(zhǎng)帶著我去了喀什的4個(gè)縣。在葉城時(shí),他和縣委統(tǒng)戰(zhàn)部長(zhǎng)(回族)陪我去當(dāng)?shù)氐那逭嫠隆G逭嫠麻T前的一條街是賣各種東西的市場(chǎng),當(dāng)時(shí)我站在一個(gè)掛滿各式小刀的架子前面,一個(gè)十歲左右的女孩從我前面走過,碰到了掛刀的架子,架子開始搖晃,攤主是個(gè)十三四歲的男孩,原來他是臉朝著另一個(gè)方向的,大概感到架子晃動(dòng)趕快扶住了架子,隨即揮著拳頭對(duì)我用維語大喊大叫,那個(gè)碰了架子的女孩就站在兩步外看著我們,她知道是自己碰的,但一句話都不說。在這個(gè)陌生男孩的眼里,我看到的是仇恨,在圍觀者的目光中我也看不到一點(diǎn)善意。旁邊的縣統(tǒng)戰(zhàn)部長(zhǎng)二話不說,趕快把我拉走。素不相識(shí),怎么會(huì)是這樣呢?我作為異國(guó)人在美國(guó)生活了幾年,從來也沒有遇到這樣的場(chǎng)景。
我們到了另外一個(gè)縣,汽車沒有開進(jìn)縣政府院子,而是開到城區(qū)一個(gè)鎮(zhèn)辦公室,在那里開會(huì)時(shí),好像會(huì)場(chǎng)上沒有維吾爾族出席。討論的議題之一是如何使當(dāng)?shù)鼐S族負(fù)責(zé)干部對(duì)近期發(fā)生的幾起暴力恐怖事件給予公開譴責(zé)。1996年5月喀什艾提尕清真寺主持阿榮汗·阿吉大毛拉被暴徒用刀砍成重傷,1997年上半年新疆各地有42名各族干部群眾被暴徒殺害,但是這個(gè)縣的維族縣長(zhǎng)就是不愿意公開對(duì)這些事件表態(tài),最后以開除黨籍和公職逼著他做了一個(gè)講話錄音,這次會(huì)上決定要一天12小時(shí)把這個(gè)錄音在縣城里用大喇叭播放。我當(dāng)時(shí)想,這位縣長(zhǎng)也是我黨的負(fù)責(zé)干部,他為什么會(huì)有這么大的顧慮呢?
當(dāng)時(shí)政府已經(jīng)開始對(duì)各地基層社區(qū)的講經(jīng)點(diǎn)進(jìn)行清查取締,這些在地下講經(jīng)點(diǎn)學(xué)習(xí)的人統(tǒng)稱“塔里普”(學(xué)經(jīng)學(xué)生——相當(dāng)于阿富汗的塔利班)。喀什地區(qū)約有1.2萬這樣的“塔里普”,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只是學(xué)習(xí)《古蘭經(jīng)》和《圣訓(xùn)》,但是其中少數(shù)人確有“圣戰(zhàn)”言論或者有暴力行兇記錄,這類人大約有八百多人,他們?nèi)绻x開戶籍所屬村子必須向政府申報(bào)。也是在這次會(huì)上,一個(gè)基層干部報(bào)告,某村一個(gè)維族女干部向政府匯報(bào)了該村有個(gè)地下講經(jīng)點(diǎn),政府派人去取締了,后來這個(gè)維族女干部就受到了鄰居的圍攻。與會(huì)者在會(huì)上討論應(yīng)當(dāng)采取什么方法來保護(hù)她。
列席這次會(huì)議給我的感覺是,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執(zhí)政快五十年了,怎么現(xiàn)在我們?cè)诳h城開一個(gè)政府的工作會(huì)議,還像當(dāng)年土改工作隊(duì)那樣要開小范圍保密的會(huì),來研究怎樣保護(hù)支持我黨工作的少數(shù)積極分子,討論怎樣爭(zhēng)取大多數(shù)群眾。到了這個(gè)時(shí)候,我發(fā)現(xiàn)新疆表現(xiàn)了比較嚴(yán)重的民族關(guān)系問題,民族身份成了社會(huì)矛盾、政治態(tài)度中的重要因素。
我自己的專業(yè)背景是社會(huì)學(xué),思考問題時(shí)的出發(fā)點(diǎn)不是從抽象的理論出發(fā)來解釋民族問題,我是在自己的社會(huì)調(diào)查經(jīng)歷中——親眼看到的事實(shí)以及和普通人的交談——發(fā)現(xiàn)中國(guó)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民族問題。這樣的民族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不管是呼和浩特、拉薩還是烏魯木齊,當(dāng)時(shí)只有革命派和造反派之分,而不管是革命派和造反派,內(nèi)部既有漢族也有少數(shù)民族,當(dāng)時(shí)發(fā)生矛盾的雙方不是以民族來劃分,而是以政治態(tài)度來劃分的。但是到了文革結(jié)束后,在“撥亂反正”時(shí)期政府和國(guó)家領(lǐng)導(dǎo)人特別提出“要落實(shí)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此后政府文件、領(lǐng)導(dǎo)人講話中的提法就開始以“民族”為單元,“民族話語”開始占據(jù)重要位置,慢慢地許多問題的討論和講述就逐漸演變成以“民族”為主題,對(duì)許多社會(huì)問題的分析也開始從“民族”角度來解讀。少數(shù)民族的“民族意識(shí)”的強(qiáng)化削弱了中華民族的整體認(rèn)同。
現(xiàn)在我們面臨的情況和50年代的形勢(shì)是完全不一樣了,即使有些政策在50年代行之有效,但是到了90年代情況已經(jīng)完全改變,當(dāng)年的許多口號(hào)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感召力了。原來人們心目中的階級(jí)弟兄情誼、革命同志情誼是超越了“民族身份”認(rèn)同的,而現(xiàn)在很多人凡是遇到包含有“民族”因素的問題和社會(huì)矛盾,凡是涉及人員具有不同的民族身份,很多人都會(huì)從“民族關(guān)系”的角度來解讀。
當(dāng)然,如果矛盾雙方都屬于同一個(gè)民族,這個(gè)問題就不存在。譬如許多中央大企業(yè)在處理與地方關(guān)系時(shí)是很霸道的,這些大企業(yè)的老總有的都是部長(zhǎng)級(jí),關(guān)系“通天”,省委書記和省長(zhǎng)也要敬他幾分,他們?cè)趺磿?huì)把地方官員當(dāng)回事?怎么會(huì)去考慮地方群眾的利益?他們想的就是如何追求企業(yè)的高額利潤(rùn)。勝利油田在山東開礦采油就是這樣,沒有給當(dāng)?shù)刎?cái)政和民眾帶來什么利益。但是山東的漢族百姓對(duì)勝利油田的反感,不會(huì)聯(lián)系到“民族”問題,這就跟維吾爾族對(duì)中央企業(yè)在新疆開采油氣的看法不一樣。山東漢族居民會(huì)說政府官員剝削老百姓,央企剝削我們基層社會(huì),而新疆的維吾爾族就會(huì)說這是漢人掠奪維吾爾族的資源。
群體性事件在沿海省份也很多,有的是反對(duì)建設(shè)造成環(huán)境污染的工廠,有的是對(duì)政府強(qiáng)拆的抵制,有的是對(duì)公安野蠻執(zhí)法的抗議,有時(shí)聚居的人群規(guī)模也很大,也有燒警車、沖擊政府辦公樓的暴力事件,但是目標(biāo)很明確,總是針對(duì)直接相關(guān)的政府機(jī)構(gòu)或具體企業(yè),而且這些群體性抗議事件不會(huì)以殺人為目標(biāo)。而烏魯木齊的“7·5事件”則是以另外一個(gè)民族的任何成員為目標(biāo),你是一個(gè)漢人,這就構(gòu)成了我要?dú)⒛愕娜坷碛桑悴槐刈鲞^什么,我也不必認(rèn)識(shí)你。你長(zhǎng)得像漢人,我就要?dú)⒛恪_@種行為是典型的種族主義、種族清洗的行為。納粹要消滅猶太人,也不管這個(gè)猶太人具體是什么人或做過什么事,是猶太人就該殺而且可以殺。極端主義的“圣戰(zhàn)”要?dú)?ldquo;異教徒”,這個(gè)性質(zhì)是一樣的。所以,漢人地區(qū)的群體性抗議事件和新疆以鮮明的“民族”特征的群體性暴力事件的性質(zhì)和造成的社會(huì)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現(xiàn)在我們遇到的很多社會(huì)問題,它的起因很可能是央企的霸道行為或者基層干部的素質(zhì)問題,但是同樣的原因、同樣的行為在漢族地區(qū)和在新疆、西藏、內(nèi)蒙古帶來的后果不一樣。今天人們之間不再是階級(jí)弟兄,他們現(xiàn)在頭腦當(dāng)中最強(qiáng)烈的認(rèn)同意識(shí)是自己的“民族身份”,發(fā)生任何事情時(shí),都會(huì)考慮這里是否涉及不同民族之間的問題。之所以會(huì)出現(xiàn)這樣的現(xiàn)象,就是因?yàn)樵瓉淼囊庾R(shí)形態(tài)認(rèn)同基礎(chǔ)(共產(chǎn)主義理想、無產(chǎn)階級(jí)革命、階級(jí)弟兄等)已經(jīng)被徹底破壞了,在“撥亂反正”以后“民族”變成了最重要的認(rèn)同身份。現(xiàn)在人們對(duì)自己自治區(qū)的認(rèn)同超過對(duì)國(guó)家的認(rèn)同,而“中華民族”這個(gè)概念在一些人心目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我們的“民族理論”講“中華民族”嗎?所以在今天的中國(guó),人們最核心的認(rèn)同對(duì)象的結(jié)構(gòu)和定義都已經(jīng)改變了,很多問題都是以民族身份來解讀。
在50年代,當(dāng)時(shí)各民族的“民族”意識(shí)是相對(duì)比較淡薄的,那么我們各民族的“民族”意識(shí)今天怎么會(huì)發(fā)展到如此強(qiáng)烈?我覺得,至少從一個(gè)方面來講,自上世紀(jì)50年代開始的民族理論教育、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的宣傳,不管是政府編寫的“民族理論”教科書,還是在學(xué)校教室里的“民族”宣講,還是制度上的“民族識(shí)別”與身份認(rèn)定,都把56個(gè)“民族”這個(gè)群體身份高度凸現(xiàn)出來并政治化了,而隨后實(shí)施的各種民族優(yōu)惠政策,文革后“撥亂反正”時(shí)的“落實(shí)民族政策”,這些也都在潛移默化地不斷強(qiáng)化中國(guó)各族民眾內(nèi)心的“民族”意識(shí),也必然會(huì)削弱和淡化各少數(shù)民族對(duì)中華民族、對(duì)國(guó)家的整體認(rèn)同。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gè)人觀點(diǎn),不代表本站觀點(diǎn),僅供大家學(xué)習(xí)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yíng)利性網(wǎng)站,如涉及版權(quán)和名譽(yù)問題,請(qǐng)及時(shí)與本站聯(lián)系,我們將及時(shí)做相應(yīng)處理;
3、歡迎各位網(wǎng)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wǎng),依法守規(guī),IP可查。
作者 相關(guān)信息
馬戎:漢語學(xué)習(xí)與中國(guó)少數(shù)族群的現(xiàn)代化
2017-10-14馬戎:“民族意識(shí)”的強(qiáng)化削弱了中華民族的整
2015-03-22馬戎:“民族意識(shí)”的強(qiáng)化削弱了中華民族的整
2015-03-22內(nèi)容 相關(guān)信息
江宇:只有社會(huì)主義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五大“新發(fā)展理念”
2021-01-12李磊 | 郡縣制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政制的基本框架
2021-01-11?郭松民 | 美國(guó)露出了“資產(chǎn)階級(jí)專政”的底色
2021-01-10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理念:大國(guó)領(lǐng)袖的深邃思考
2021-01-09?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wù) 新前景 ?

? 國(guó)資國(guó)企改革 ?

? 雄安新區(qū)建設(shè) ?

? 黨要管黨 從嚴(yán)治黨 ?

 國(guó)產(chǎn)航母研制總指揮胡問鳴被審查,讓人真的驚出一身冷汗!
國(guó)產(chǎn)航母研制總指揮胡問鳴被審查,讓人真的驚出一身冷汗! 國(guó)產(chǎn)航母研制總指揮胡問鳴被審查,讓人真的驚出一身冷汗!
國(guó)產(chǎn)航母研制總指揮胡問鳴被審查,讓人真的驚出一身冷汗! 李毅深圳演講
李毅深圳演講
 【太可怕】這么多小學(xué)生參加基督教活動(dòng),必須要管!
【太可怕】這么多小學(xué)生參加基督教活動(dòng),必須要管! 文子稻:對(duì)印急不得,對(duì)臺(tái)拖不得!中國(guó)大局已布下,做好隨時(shí)統(tǒng)一的準(zhǔn)備
文子稻:對(duì)印急不得,對(duì)臺(tái)拖不得!中國(guó)大局已布下,做好隨時(shí)統(tǒng)一的準(zhǔn)備 肖志夫:美國(guó)遏制中國(guó)“十大任務(wù)”即將出爐 中國(guó)如何應(yīng)對(duì)
肖志夫:美國(guó)遏制中國(guó)“十大任務(wù)”即將出爐 中國(guó)如何應(yīng)對(duì)? 社會(huì)調(diào)查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