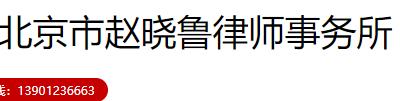【作者盧曉】
觀察者網(wǎng):最近一些企業(yè)在宣傳中使用帶有“瞇瞇眼(slanty eyes)”元素的廣告創(chuàng)意,引起網(wǎng)友比較激烈的反饋和討論,如果說“三只松鼠”引起第一波輿情可能是它未能預(yù)料到的話,奔馳在輿論熱點已經(jīng)產(chǎn)生的情況下,仍然我行我素,在您看來,奔馳為什么會在這個時間節(jié)點上出現(xiàn)這樣的操作?
盧曉:實際上在最近的大眾討論中,許多分析非常到位,很多文章追溯到19世紀(jì)的英國殖民者對中國人形象的刻畫,包括傅滿洲的形象,以及李小龍當(dāng)時對這種丑化的揭露和抵制。第一,這是一個審美標(biāo)準(zhǔn)的問題;第二,這種審美的沖突已經(jīng)存在很長時間,但零星、散狀、多發(fā),沒有引起大眾如此集中的關(guān)注和討論。這次奔馳、三只松鼠的操作并不是“突然”引起關(guān)注的,而是有一個很大的背景和體系,我在此前出版的專著《品牌賦能 國際精品品牌戰(zhàn)略》的序言中就提到過一個問題:東西方思想文化的二元均衡。第一個觀點,近代以來的數(shù)百年,西方在殖民主義和工業(yè)化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逐步在全球范圍內(nèi)建立起思想文化上的主導(dǎo)地位。西方在朝鮮半島、日本、東南亞等傳統(tǒng)上東方思想文化占主導(dǎo)的地區(qū)進行侵占和殖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這些地區(qū)在美蘇冷戰(zhàn)背景下出現(xiàn)民族自決,逐步實現(xiàn)獨立,但這是主權(quán)和行政上的表面獨立,特別是在思想文化上,它們還是被殖民的狀態(tài)。但在全球?qū)用嫔希幕I(lǐng)域確實存在兩種思想體系,東方是不容任何觀察者忽視和否認(rèn)的另一極,幾千年來的傳承脈絡(luò)是真實存在的,誰也無法隔斷和消除。近代中國由于落后挨打,200多年來一直處于落后狀態(tài),這套思想體系不論好壞,也一直處于弱勢狀態(tài),因為硬實力不行,我們再宣傳這套文化的先進,沒有說服力,也沒有追隨者,這是非常現(xiàn)實的問題,自“五四”以來,我們一直在對這套思想文化體系進行反思。這種狀態(tài)的止損點,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全新的面貌在全世界亮相。雖然經(jīng)濟實力不行,但我們以一個主權(quán)獨立國家的身份重新站起來。“站起來”這個說法非常形象,可能我們底子薄、狀態(tài)不好、弱不禁風(fēng)、面臨諸多困難,包括很多國家遏制我們,不希望我們站起來,但我們的確是站起來了。可能當(dāng)時西方實力強,站著的人多,但作為東方體系的領(lǐng)頭者,我們重新站起來了,這跟沒站起來的時候完全不同。隨后,我們經(jīng)過前三十年艱苦卓絕的斗爭,打下國防和工業(yè)基礎(chǔ),又經(jīng)過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以經(jīng)濟建設(shè)為中心高速發(fā)展,在政治上、軍事上、經(jīng)濟上都逐步站起來了,但是在文化上,我們?nèi)匀粵]有以代表東方思想體系的身份強勢起來。所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政治上站起來了,經(jīng)濟上站起來了,文化上也要站起來,物質(zhì)層面站起來了,精神層面也要站起來。第二個觀點,當(dāng)下的時間點確實孕育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質(zhì)變,很多人對這句話的理解還不夠深刻。西方已經(jīng)強勢了數(shù)百年,東方已經(jīng)弱勢了數(shù)百年,這個格局一直在發(fā)生潛移默化的變化,出現(xiàn)了此消彼長的過程,實際上朝著東西方文明發(fā)展的均衡狀態(tài)發(fā)展。此前在東方弱勢的時候,很多事情雖然也發(fā)生,但我們不敏感,至少我們的大眾不敏感,而隨著東方實力的增強,體量的增大,很多人心理層面發(fā)生了變化,自然而然變得非常敏感。這種敏感,并不是業(yè)內(nèi)人士敏感,是由于東方文明的政治、經(jīng)濟各方面的綜合實力提升,產(chǎn)生公眾認(rèn)知能力的提升,導(dǎo)致普羅大眾的覺醒和敏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敏感的發(fā)聲者是年輕人,是90后、00后,他們沒有那么多歷史包袱,沒有過去遺留的思維慣性,年長一點的人可能早就見過了,覺得這次發(fā)生的事情跟以前一樣,司空見慣,本該如此。但現(xiàn)在的年輕人沒有這些經(jīng)驗,看到這個現(xiàn)象覺得很錯愕,因為從一個平視世界的正常人視角來看,從一個正常人與生俱來的樸素審美來看,被描繪成這種形象,都會有一種被攻擊的感覺,他們反問,為什么要接受一個不屬于我的形象?為什么要承擔(dān)一些不該承擔(dān)的東西?
【“當(dāng)代藝術(shù)家”岳敏君的作品在2017年被拍出高價】
這種年輕人的內(nèi)心感受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在東西方動態(tài)博弈的過程中得到了激發(fā),尤其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他們的聲音能夠被放大,更易于得到共鳴。如果在之前的歷史階段,即使有人有這樣的感受,發(fā)出這樣的聲音,可能也會被湮沒,無法激發(fā)更多人的共鳴。
觀察者網(wǎng):可能在李小龍那個時代和環(huán)境中,他發(fā)出的聲音就沒有在當(dāng)時激發(fā)那么大的回音,但是現(xiàn)在,我們看到許多分析文章都提到了李小龍,這似乎是一種超越時空的回音。
“我覺得美國應(yīng)該展示真正的東方文化,你自己看看兄弟,美國劇里中國人都是長辮子像猴子跳著,被美國人追趕著快快,眼睛還要弄成斜眼,我認(rèn)為這是非常過時的。”——李小龍
盧曉:李小龍在上世紀(jì)六十年代就直面這種沖突,他當(dāng)時作為一個東方人,站在西方文化體系中最強大國家的文化中心,可以說是站在漩渦的正中間,比我們今天的感受更深。當(dāng)時他能夠發(fā)出這樣的聲音,我認(rèn)為能夠證明兩點,第一,他不糊涂;第二,他非常有勇氣。當(dāng)時去美國的中國人,包括大量全世界其他民族的人,很多就變成了依附者,他們第一步是按照西方(給某個民族)設(shè)計的文化形象,100%地改造自己;第二步是被改造后,再以自身被改造后的形象反過來影響他的母文化。第一步是被同化,第二步是變成工具。以這樣的標(biāo)尺去觀察李小龍,首先,他不糊涂,拒絕同流合污;第二,他有勇氣發(fā)聲。有些海外華人雖然也不糊涂,不同流合污,但是他考慮自己的生存和利益,就選擇沉默,這是很多海外華人的普遍狀態(tài),據(jù)我觀察,第一代海外華人大多是不糊涂的,但第二、第三代就說不定了。當(dāng)然以前肯定也有華人選擇發(fā)聲,但是李小龍作為一個公眾人物,擁有更多發(fā)聲的機會和平臺,他在采訪時表達的觀點可以被鏡頭記錄下來,可能當(dāng)時沒有引起多么大的關(guān)注或反響,但在近半個世紀(jì)以后,又被明眼人發(fā)掘出來,這就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產(chǎn)生了一種跨越時空的共鳴。觀察者網(wǎng):但今天,李小龍當(dāng)時就評論為“過時”的事情,還有人在做。
盧曉:是的,比如說這些海外的廣告公司找一些中國女孩子來拍,有的當(dāng)事人發(fā)聲喊冤,在我看來,這多少有點揣著明白裝糊涂,當(dāng)事人自己當(dāng)時難道沒有感受嗎?他可能為了掙這個錢,就裝糊涂了,這就是個人選擇,這樣的工作,有人愿意做,有人不愿意做。如果往深了說,在日本侵占中國的時候,也拉攏文化界,有人選擇屈服合作,也有人選擇不屈服。中國文人的思想層面中,是有民族氣節(jié)存在的,當(dāng)然,民族氣節(jié)我們要倡導(dǎo),但不可能要求所有人,當(dāng)事情臨到每個人面前,各人有各人的選擇。但是在今天這個時代,我覺得這種選擇變得更容易了,而不是更困難。觀察者網(wǎng):可能也正如您說的,在時代變化的過程中,這種事情可能給個人或企業(yè)帶來的后果也發(fā)生了變化,有人可能沒有預(yù)期到這么嚴(yán)重的后果。
盧曉:是的,有些注意觀察的人,已經(jīng)意識到時代變化了,但對大眾來說,認(rèn)知還需要一個過程,或者說每個人的覺悟是不一樣的。可能大家在各自具體的工作領(lǐng)域中就沒有體會得那么深,現(xiàn)在覺醒的公眾越來越多了,又有了互聯(lián)網(wǎng)這樣一個快速傳播的工具。尤其是如果沒有疫情,沒有貿(mào)易戰(zhàn),可能這種變化的過程還沒那么快,現(xiàn)在有那么多顯性的事件來觸動大家,客觀上加速了公眾的覺醒和中國文化崛起的進程。觀察者網(wǎng):如果我們談得更具體一點,為什么像奔馳這樣的跨國企業(yè)和像三只松鼠這樣的民營企業(yè)身上會發(fā)生這樣的事情?
盧曉:實際上和他們廣告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供應(yīng)鏈體系有關(guān),這個產(chǎn)業(yè)的淵源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受西方文化價值觀影響的這一波從業(yè)者,他們學(xué)習(xí)了西方先進的東西,但沒有做選擇和甄別,接受了西方的同化,也全盤接受了作為丑化中國的工具這個角色。他們?nèi)狈钚↓埖恼J(rèn)識高度、敏感度和勇氣。當(dāng)然,這不能只怪廣告創(chuàng)意團隊,品牌形象最終的把關(guān)人是公司,這些公司在中國市場上,首先就要有作為中國人的同理心,90后、00后們根據(jù)常識都能作出的價值判斷,公司公關(guān)團隊卻沒有感知,這不能怪別人。但這又引出另一個重要的問題,今天整個“主流”創(chuàng)意體系,從培訓(xùn)到生產(chǎn)的鏈條,都是跟著西方文化價值體系走的,如果從業(yè)者自己沒有一定的功力,對這個問題沒有思考,沒有一定的經(jīng)驗積累,他們提不出一套既是中國的,又是正能量的東西。在文化領(lǐng)域,“現(xiàn)代”與“西方”要解耦,關(guān)于現(xiàn)代中國的審美和價值觀的形象,應(yīng)該是一個正向的形象,而不能是一個負(fù)面或者附庸的形象,一個被西方刻意扭曲固化的工具不能被反過來植入中國主流審美的建構(gòu)過程,最后定義中國的“主流”。我想說的是,第一,現(xiàn)代中國自己的形象標(biāo)準(zhǔn),必須是既能代表人類正向?qū)徝溃帜艽碇袊藢徝拦沧R的,而不能由別人來定義中國的審美;第二,目前這個領(lǐng)域中國很弱,我們自己正向輸出能力太小,這種審美必需有大量實物載體,這就與我現(xiàn)在正在推動的事業(yè)有關(guān),中國具有國際水準(zhǔn)的企業(yè),所提供的產(chǎn)品和服務(wù),就是這種審美的承載者,這個過程,與中國走國際精品品牌道路的品牌企業(yè)逐漸發(fā)展壯大是同一個過程。觀察者網(wǎng):可能這也是一個戰(zhàn)斗的過程?
盧曉:我認(rèn)為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因為畢竟全球市場目前是一個公開的市場。實際上西方也不是故意專門欺負(fù)中國,他們對全世界其他民族都是這樣的,這是西方文化思想和能量的外延,涉及到中國時,如果中國在這個領(lǐng)域為空,別人既成體系的觀點和已經(jīng)成熟的工具自然就會進來占領(lǐng)。在這個領(lǐng)域中,很多問題是認(rèn)知問題,可能我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認(rèn)知過程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空白,在改革開放40多年中,我們在經(jīng)濟領(lǐng)域里在補課,有些已經(jīng)進入到了全球第一陣營中,所以面臨了西方的打壓。但另一方面,在精神文明和文化價值觀的建設(shè)過程中,我們雖然有一些傳統(tǒng)的東西還在堅持,但是與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結(jié)合的精神文明建設(shè)還很欠缺,要補的課遠遠比物質(zhì)方面還要多,因為這方面不可能立刻有產(chǎn)出。
【中國當(dāng)代畫家吳冠中(1919-2010年)作品《周莊早市》】
觀察者網(wǎng):這方面我個人長期來有一個觀察,文化方面的變化要比經(jīng)濟和科技方面的變化滯后一段時間,可能是十幾年。之前我在一次采訪中也了解到一個觀點,要講好中國故事,或者要做好媒體傳播,很多時候要依靠理論工具支撐,但是很多經(jīng)濟方面的實踐肯定是領(lǐng)先于經(jīng)濟理論的提煉的,而提煉出來的經(jīng)濟理論要為大眾接受,還需要一個過程,所以這方面可能確實需要不少時間。
盧曉:你說的是一個客觀規(guī)律,我現(xiàn)在就在這個規(guī)律的基礎(chǔ)上,既做一名理論創(chuàng)建者,又做一名這一理論的實踐者和推動者,就現(xiàn)在的事態(tài)來做相應(yīng)的對策,因為中西方的相關(guān)博弈已經(jīng)開始了。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全球經(jīng)濟分工中做底層配套,承載很大一部分低附加值、勞動密集、高污染、高耗能的工作,40多年來,我們逐步升維,向產(chǎn)業(yè)鏈的上游攀爬,逐步走向高附加值,追求結(jié)構(gòu)性優(yōu)化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實際上我們觸及了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利益,挑戰(zhàn)了西方文明的和工業(yè)化社會規(guī)則體系的制定者和最大受益者。原來他們切給中國一塊蛋糕,但中國現(xiàn)在要在這一塊的基礎(chǔ)上,切一塊更好的蛋糕。為什么中國會去做這個動作,而日本、韓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不敢做呢,因為他們是附庸,輪不到他們來制定規(guī)則,只能被動接受。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不接受的西方制定的規(guī)則和分配,東西方是人類文化上的兩極,博弈過程因此產(chǎn)生。中國現(xiàn)在已經(jīng)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這是我們東方文明提出來的,而不是西方,西方的發(fā)展建立在把其他民族當(dāng)成附庸進行掠奪的基礎(chǔ)上,但東方的思路自古以來就不是這樣,鄭和下西洋沒有掠奪任何人,而是推動正常的貿(mào)易往來,互惠互利,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點提出后,在全球獲得了很大的反響。但這觸碰了原來規(guī)則制定者的既得利益,因而對中國群起而攻之,被遏制、打壓、丑化、妖魔化等等,都是正常現(xiàn)象,因為兩個拳手已經(jīng)上了擂臺,在博弈過程中,中國還沒有成長到與對方勢均力敵,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解決兩個實際壓力,一是自己要成長,二是對方要打壓。現(xiàn)在我們在政治、國防、科技、經(jīng)濟等硬實力方面已經(jīng)有了很大提升,也意識到了軟實力方面的問題,已經(jīng)提出了高質(zhì)量發(fā)展道路,但是中國具體要把自己塑造成怎樣的形象,還沒有成型。文化創(chuàng)意領(lǐng)域并不能空幻呈現(xiàn),必須有載體,這些載體就是所有與衣食住行有關(guān)的產(chǎn)業(yè)和企業(yè),比如紅旗的汽車,華為的手機,我們舉出這些民族品牌,因為它們既走了高質(zhì)量發(fā)展道路,同時又呈現(xiàn)出中國東方文明現(xiàn)代化、全球化的一種先進審美形象。對于打著中國品牌名義,打著中國文化價值觀旗號來創(chuàng)造產(chǎn)品和服務(wù)的人,我們要做鑒別,并不是所有自主品牌都一定是對我們產(chǎn)生正向作用的。有的自主品牌被偷梁換柱,用一個丑化的形象來進行售賣推廣,也會有一部分市場,一部分西方人認(rèn)為我們就是這樣的,這部分市場會產(chǎn)生共鳴;有一部分被洗腦、同化之后,反過來作為工具的人,也會認(rèn)同并為之買單。但這部分市場一定不是我們真正的主攻市場,東方文明有自己的價值體系,自己的哲學(xué)體系,西方既得利益者中比較敏感的一批人對此是非常忌憚的,他們會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干擾我們,但讓我們被動接受或者蒙騙我們接受,是不可能的。觀察者網(wǎng):包括給這些丑的東西創(chuàng)造市場,賦予它經(jīng)濟效益。
盧曉:是的,特別是當(dāng)代藝術(shù)領(lǐng)域是重災(zāi)區(qū)。凡是對中國形象的正面塑造作品,就無人問津,而做一個灰暗的,丑化的,反映“問題”的,就有人捧場,因為這符合這個世界的規(guī)則制定者們的需要,這是他們認(rèn)定的中國應(yīng)該呈現(xiàn)出來的狀態(tài),所以他們會買單。
【2007年,岳敏君及其作品登上《時代》雜志封面】
這種博弈是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巔峰的斗爭過程,雖然不見血,但某種意義上比見血的斗爭產(chǎn)生的能量要大得多。在這個過程當(dāng)中,他們是不可能讓李小龍這樣的聲音被放大的,但是也沒必要把他完全擦掉。他們遏制他的發(fā)展,反向利用他的影響,在當(dāng)時來說,反而是更高階的策略。但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到來,對方當(dāng)時可以遏制一個李小龍,現(xiàn)在遏制不了千千萬萬的李小龍。反之,如果沒有中國年輕人的覺醒過程,李小龍也就是時代無數(shù)塵埃當(dāng)中的一個微小亮點。中國在物質(zhì)基礎(chǔ)極大豐富的情況下,在精神層面是不可能被奴役的。

【盧曉認(rèn)為,烏合麒麟這樣的年輕人站出來是一件好事】
觀察者網(wǎng):但仍然需要時間?需要一個過程?
盧曉:是的,中國當(dāng)代藝術(shù)領(lǐng)域是塌陷性的,雖然有人炒作,但真正的時代精品實在太少。大家雖然覺醒了,意識到丑化的東西不行,但能夠被大眾接受的美的東西在哪里?這個問題我們之前談到過,就是“國潮”突然一下子火了,這并不是因為“國潮”有多么強的價值創(chuàng)造能力,但最起碼它不是丑的,雖然有些傳統(tǒng),有些落后,但是經(jīng)過重新包裝推出,公眾還是認(rèn)可的。這和我們本次事件中,許多年輕人不接受丑化符號的覺醒,是同一個潮流的不同表現(xiàn)形式。未來在電子、汽車、文創(chuàng)、服飾領(lǐng)域,如果有能夠走精品路線、擁有高附加值,又能夠承載正向?qū)徝赖漠a(chǎn)品或服務(wù)出現(xiàn),今天的年輕人中當(dāng)然會有很多有支付能力的人會買單。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要全面推動的事業(yè),它不是單一維度的,不是一個具體技術(shù)層面的問題,不是物質(zhì)層面的一些創(chuàng)造,而是體系性的,是打通物質(zhì)和精神層面的高質(zhì)量和高附加值的創(chuàng)造,這是我們現(xiàn)在最欠缺的。這個陣地,我們不去占領(lǐng),人家就會去占領(lǐng)。這個陣地不僅在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而且在所有城市、城鎮(zhèn)、廣大農(nóng)村和“一帶一路”,這關(guān)乎14億人的共同利益,考驗14億人的共同智慧。
【當(dāng)代藝術(shù)家蔡國強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的作品】
觀察者網(wǎng):我再追問一個問題,現(xiàn)在漢服逐漸掀起潮流,山東曹縣已經(jīng)作為一個產(chǎn)業(yè)中心逐步興起。我們是否期待漢服潮能夠承載中國傳統(tǒng)服裝文化現(xiàn)代化的使命?因為我們今天穿著的西方式的現(xiàn)代服飾也不是從一開始就現(xiàn)代化的,它也經(jīng)歷了幾百年的發(fā)展演變過程。另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觀察對象是日本,因為日本的一些傳統(tǒng)服飾有過改良,成為相對比較現(xiàn)代化和高端的東方式服裝,我們是不是可以借鑒這個過程?
盧曉:對于你說的現(xiàn)象,我的主要觀點是,不支持,但樂見其成。因為原來中國傳統(tǒng)服飾已經(jīng)被毀掉了,要復(fù)興,就要先復(fù)刻,要復(fù)刻,就會出現(xiàn)山東曹縣現(xiàn)在的產(chǎn)業(yè)。復(fù)古的服裝產(chǎn)業(yè)變大了,“漢服”變得更主流了,接下來就會有年輕人研究如何創(chuàng)新的問題。我推動高質(zhì)量發(fā)展戰(zhàn)略20多年,曾經(jīng)見證了各個領(lǐng)域的創(chuàng)新過程,第一步就出創(chuàng)新成果是可能的,但是這要求非常高的綜合素質(zhì),民眾的接受也要有一個過程。漢服產(chǎn)業(yè)的成長,下一步就是漢服的現(xiàn)代化,如同“國潮”現(xiàn)在大行其道,下一步就是“國潮”的精品化。在文化領(lǐng)域首先要有一個恢復(fù)的過程,恢復(fù)到一定基數(shù)了,產(chǎn)生一定經(jīng)濟效益了,被公眾認(rèn)可了,下一步才是與時俱進的往前發(fā)展。這個過程,漢服和國潮都要經(jīng)歷。我不完全認(rèn)同復(fù)刻這件事情,因為復(fù)刻并不是創(chuàng)新,它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倒退,但是要想產(chǎn)生創(chuàng)新就要有基礎(chǔ),復(fù)刻和重復(fù)的過程是必不可少的一個步驟。因為我們是一個不斷創(chuàng)新的大國,有不斷的提升自己的思想體系,所以只要產(chǎn)生復(fù)刻,就是好事。

【山東曹縣漢服產(chǎn)業(yè)(央視《經(jīng)濟半小時》節(jié)目截圖)】
第二,你提到日本服裝的問題,日本的情況并不是沒有意義的,可以借鑒,但是要警惕。因為其借鑒意義不是全部,而是一部分。日本傳統(tǒng)服裝有一個現(xiàn)代化的過程,這是被認(rèn)可的,明治維新以后,因為日本“船小好調(diào)掉頭”,成了西方的附庸,并且產(chǎn)生了作為附庸的現(xiàn)代化效應(yīng),使它能夠迅速發(fā)展起來。但是從底層邏輯來講,日本是一個附庸的受益者。它是一個優(yōu)秀的附庸,起初作為中國的附庸,通過中國的這套體系跟西方抗衡,被打敗后,被西方變成了附庸,又學(xué)習(xí)了西方的先進文化,雖然可以說它學(xué)習(xí)了東西方的先進性,但是也存在問題,因為這都不是日本的原創(chuàng),而是別人思想體系的一部分,我并不否認(rèn)日本做的這個事情有正向的一面,但它不是整體性的、根源性的和底層的,只是飄在上面的一個局部。這個局部對于中國來講,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絕對不是我們應(yīng)該照搬的,它不可能解決我們?nèi)康膯栴},我們的問題,還要我們自己解決。說回漢服和國潮的話題,我不完全贊同,但也不否認(rèn),這個過程只是我們要做的事情的基礎(chǔ),有這個基礎(chǔ),才能走第二步、第三步,所以我對于國潮的態(tài)度是“樂見其成,但不贊成”。至于奔馳和三只松鼠的問題,實際上他們是全盤接受西方思想文化體系,包括其中丑化中國的部分。高質(zhì)量發(fā)展過程中,首先,我們要強調(diào)做自主品牌;其次,自主品牌呈現(xiàn)的文化價值觀和美感是不是正向?第三,在正向的基礎(chǔ)上,區(qū)分大眾消費品和高端消費品(精品),這是兩個不同的消費市場,高附加值的高端消費市場是我們要去占領(lǐng)的方向,但中國現(xiàn)代文化價值觀中的高級美感是什么?誰來呈現(xiàn)這種?這是個問題。現(xiàn)在市場上出現(xiàn)了一些“偽中國品牌”或者“偽中國精品品牌”,他們聲稱自己是高端自主品牌,占據(jù)了這個概念的位置,但實際上呈現(xiàn)出來的,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丑的,也就是用西方體系定義的“東方高級美感”來占據(jù)這個市場位置;另一種沒有這個功力來呈現(xiàn)出“東方高級美感”,達不到這個精度,只是一個粗制濫造,但是占據(jù)高級美感的市場位置。據(jù)我觀察,目前這兩種情況還是市場主流,真正能夠承載現(xiàn)代中國正向文化價值觀的產(chǎn)品和服務(wù),還很稀少,還需要時間。但是這個時間過程并不是兩三百年,也不是一二十年,而是近幾年就會出現(xiàn)“變局”,各個領(lǐng)域里都會有這樣的頭部企業(yè)意識到這個問題,然后付諸實踐,最后做大做強,他們會取得巨大的經(jīng)濟效益,同時產(chǎn)生巨大的社會效應(yīng),與漢服、國潮等等現(xiàn)象產(chǎn)生共振,共同構(gòu)成東方思想文化體系復(fù)興的大勢。但這個過程也不會是敲鑼打鼓自動完成的,因為我們已經(jīng)登上了擂臺,正在與西方進行見招拆招的博弈,目前在力量對比上,我們有強的地方,也有弱的地方,但總體上弱的地方比較多。擂臺過招只要沒有被打死,就是經(jīng)驗的成長。我從事推動中國精品品牌成長的事業(yè)已經(jīng)20多年,各個時間段產(chǎn)生的效應(yīng)和反饋是不同的,如果沒有到今天這個時間點,如果我們沒有做之前的工作,如果沒有經(jīng)歷很多事情,今天我們的討論很多人肯定也聽不明白,因為沒有感同身受。所以,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經(jīng)到來,許多事情都在產(chǎn)生共振。(作者系國際精品品牌戰(zhàn)略研究院院長、教授,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wǎng)【作者授權(quán)】,轉(zhuǎn)編自“觀察者網(wǎ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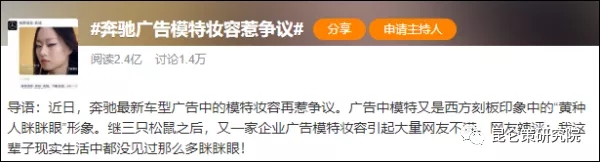
















 周江勇落馬,沒那么簡單
周江勇落馬,沒那么簡單 譚勁松教授等建議設(shè)立“大學(xué)生星期六志愿服務(wù)日”
譚勁松教授等建議設(shè)立“大學(xué)生星期六志愿服務(wù)日” 張文木 : 湯因比歷史研究肩負(fù)“特別文化使命”,中國應(yīng)知己知彼
張文木 : 湯因比歷史研究肩負(fù)“特別文化使命”,中國應(yīng)知己知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