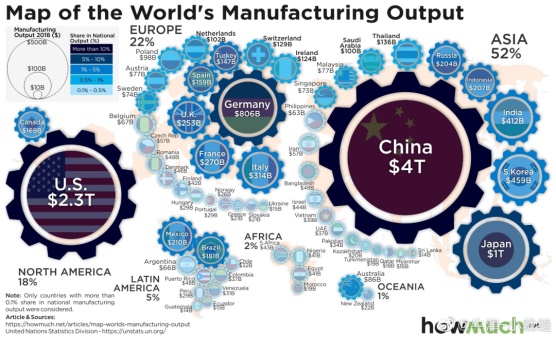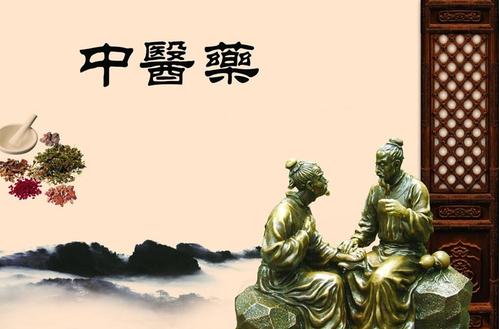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3日-星期六
黨史研究要更好地發揮資政育人的作用,對黨史研究者來說,有兩個問題應該明確。一個是靠什么資政育人,一個是怎樣研究才能更好地去資政育人。
回答第一個問題,應該明確和堅持“三個方向”。
一是靠梳理和闡發黨的基本理論資政育人。黨史研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強,其最高境界應該是梳理和闡發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理論探索及其重要成果,目的是以科學理論武裝人。需要說明的是,黨的基本理論常常是通過黨在工作實踐中提出和貫徹的重大決策和政策體現出來的。有人不免產生疑問,決策和政策是否算作理論?其實,黨的決策和政策一頭通向理論,一頭影響實踐。和在書齋里從事理論思考的純粹學問家不同,我們黨關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理論立足實踐,通過一系列重大決策和政策體現出來,來自實踐又回到實踐中去驗證,最后才進行理論上的總結和升華。這是不僅要認識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事理論創新的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特點。
二是靠總結和分析黨的歷史經驗資政育人。挖掘、梳理、揭示我們黨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經驗,包括某些教訓,是黨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在不同歷史時期,我們黨為了推進黨和人民的各項事業,為了應對這樣那樣的風險考驗,為了實現不同階段的目標任務,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時期,在治黨、治國和治軍各個方面,殫精竭慮、艱辛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展現了不凡的政治勇氣和智慧。通過研究把它們展示出來,在今天和將來都是最能說服人、教育人的寶貴財富。
三是靠研究和宣傳黨史人物和事件資政育人。黨的歷史是由一代又一代黨員的具體奮斗創造出來的,是由一個又一個具體的重大事件連接起來的。黨史研究自然應該通過敘述具體的人和事,傳播黨的奮斗歷史,展示黨的光輝形象,弘揚黨的優良作風,以此來感染人、影響人,進而增加人們的“紅色記憶”和“紅色感動”,凝聚人們對黨的奮斗歷程和風采的認同,培育和引領崇高的風尚。
回答第二個問題,應該強調黨史研究必須重視并善于利用“兩只翅膀”。
第一,重視并善于利用科學理性的翅膀,才能更加深刻地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
強調科學理性,是為了防止黨史研究空對空、簡單重復或自說自話,以至憑自己的興趣和偏好去“戲說”的不良風氣,進而使研究者更加自覺地以準確和深入為標準,在黨史領域馳騁。所謂科學理性,就是要求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的經驗、黨史人物事件等,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放到我們黨當時面臨的主要矛盾中,放到我們黨當時的認識水平上,來闡發、分析、揭示和評價。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這樣的研究,才可能有“真貨”,有歷史的質感,才能夠更貼切地說服人、教育人。比如,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對于如何搞社會主義,一開始并不清楚,也不能要求前人在起點上就必須清楚,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都有一個逐步延伸進步和豐富完善的探索過程。認識真理、宣傳真理、認同真理、由少數人認同到多數人認同,都必然有一個過程。黨史研究就應該把這個過程講清楚,并把不同階段的探索特點連接起來。這樣的研究,彰顯了實事求是,彰顯了科學理性,既有歷史的力量,又有邏輯的力量。在今天的背景下,黨史研究如果只是排列材料、引述文件,顯然不行了。必須要有相應的思考力度和理論靈魂,而不是各種材料和觀點的簡單重復或組合,才能拎出史實的“魂”或“核”來,做到高屋建瓴,讓人感覺有新意,能夠盡量深刻地資政育人。顯然,不重視并善于利用科學理性這只翅膀,這樣的效果難以達到。
第二,重視并善于利用個性文情的翅膀,才能更加生動地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
強調科學理性并不排斥個性化的研究和著述風格,黨史研究是可以做到有文有情有個性的。歷史著述和文學表達的關系是一個老得不能再老的話題。它們本為一體,至少在司馬遷以前,那時的史書實際上多是文學著述。有聲有色的《項羽本紀》,即是一例。班固以降,史書就沒味道了。宋代司馬光創“通鑒”體例,圍繞一個專題一個事件詳述其來龍去脈,尚有可取之處,但終究在敘述風格上去司馬遷甚遠。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新的文化時代,到20世紀40年代,那時歷史學家的作品多有斑斕絢爛的色彩,可讀性很強。至今讀吳晗的《朱元璋傳》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也能激起心底的波瀾。這樣的歷史著述發揮的資政育人作用更為生動和具體。
講科學理性不一定會使研究者的思維和筆法干巴巴的。胡喬木在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撰寫《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時就提出:要寫出感人的場面,寫出黨史人物的細節,寫得有聲有色;行文要有懸念,有照應,有精辟的議論,有大開大合的章法。凡此等等,都是在提倡個性文情,以求黨史研究的新變和突破。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出來之前,出版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喬木讀后,給了“有質有文,陳言大去,新意迭見”的評價。胡喬木對黨史研究論著的這些倡導和期望,是值得注意的。除了嚴肅的宏觀論著,研究黨史人物和黨史重大事件,更需要有文有情有個性了。黨史研究的成果畢竟需要延伸到社會上才能發揮資政育人的作用。研究黨史,不僅僅要著眼于“理”,立足于“事”,更要有“人”。無論明理還是說事,終歸都要涉及人。理有曲直,事有情節,人有個性,在研究中扇起個性文情的翅膀,讀者閱讀起來就可能既有理性思考又有感情介入,資政育人的效果就會更明顯。如果把本來生動具體并且感人的黨史人物和事件,搞得無文無情無個性,指望以此資政育人,自然效果有限。
黨史研究要重視并善于利用個性文情的翅膀,一是要尊重和準確把握史實,二是要有理論識見,三是要有個性化的表達。第一點是基本要求,不用說。關于第二點和第三點,關鍵在于研究者筆下的內容必須是經過自己的眼睛和大腦轉換出來的。這個轉換靠的是理論上的眼光識見。也正是在轉換中,方能看出史實的內核,看出黨史的底蘊,看出黨史的“詩”意,從而彰顯作者的個性化表達。
陳晉: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來源:長安街讀書會微信公眾號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