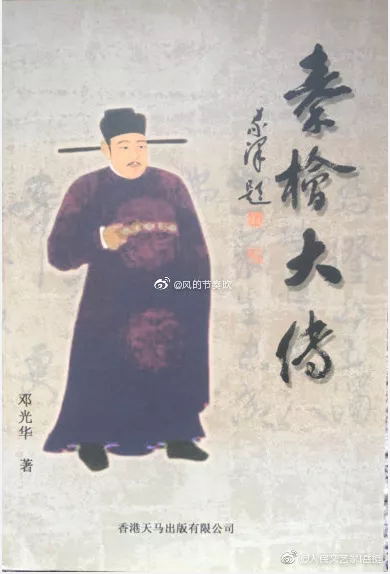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23日-星期三
近來一部打著紀念抗美援朝幌子的電影上映,上映第一天豆瓣評分僅有6.9分,各路網友紛紛吐槽,該劇不尊重歷史,更不懂中國人民志愿軍如何會被稱作“最可愛的人”。原本,對于這樣在劇情上粗制濫造的歷史虛無主義電影,徐郎是一定要買票進入電影院先觀后評的,但是由于宣傳方用力過猛,導致在其公開宣傳(包括水軍的無底線吹捧)的素材中暴露了大量的問題,我個人覺得已經沒有必要去花錢惡心自己一番。此外,很多比我高明的大家,已經在方方面面指出了電影所存在的問題,再去覆蓋一遍,猶如拾人牙慧,沒有新意。
但是就宣傳材料中所見,徐郎發現,這部電影在志愿軍指戰員之間的稱謂、口頭禪等臺詞的設置上,存在著嚴重的“國軍化”傾向。這也是近些年來,國內歷史革命題材、抗戰題材電影所存在的通病。這類臺詞的出現,完全是因為其編劇和導演是在用國軍思維來理解我軍的勇敢作戰精神為何物!他們將粗魯視為勇敢和大無畏,將粗鄙等同于“有種”,進而引申為富有戰斗力!然而共產黨的軍隊之所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其精髓在于講政治,而不是這些導演所理解的那樣。以粗鄙下流的言語來彰顯軍人的戰斗能力與大無畏不怕犧牲的魄力,實際是對我黨領導軍隊的法寶——毛澤東思想,囫圇吞棗,甚至是一竅不通,因此就對歷史胡亂意淫!
講到這里,也許有人會說,中國人民志愿軍包括了大量的國民黨起義軍隊和俘虜,他們的素質參差不齊,因此,粗鄙的現象在志愿軍中肯定是存在的。這樣的說法看似有理,實際上是經不起推敲的。首先,剛剛從國軍起義過來的戰士,有一部分確實是存在罵人等不好的習慣的,但是那也是暫時的。當他們感受到了我軍的紀律和行為規范以后,尤其是經過政委的一番思想政治工作和解放軍同志們的耐心幫助(比如訴苦大會)之后,就不會繼續像他們在國軍時那樣。不僅稱謂、用語變得文明,行為也由自由散漫變為有紀律講政治,并且時刻以此為榮,因為那是那個時代的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鮮明特質!而且這一轉化過程,是極其迅速的。徐郎的外祖父在1944年參加抗日,后來在俘虜和改造國軍的過程中,親眼目睹了這些。
高戈里老師在《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的一書里,系統地講述了188萬國民黨軍在解放戰爭中被改造的故事。包括長春起義的曲曲折折,思想改造的是是非非。在后來的抗美援朝戰爭中,這些起義過來的同志血灑漢江,為保衛祖國、捍衛和平立下了汗馬功勞。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看這本親歷者采訪史。
今天,隆重推薦牛戈老師的《“弟兄們”還是“同志們”》一文,就是要通過講清楚我軍指戰員在稱謂上的講究,來駁斥在如今火熱的歷史虛無主義影視劇,將被它們國軍化的我軍形象還原過來。牛戈老師擅長軍事歷史和歷史武器的考究,他的微信公眾號是“牛戈文草”,有興趣的可以關注一下!
來源:
“弟兄們”還是“同志們”
牛戈
《亮劍》《集結號》等影視作品中,李云龍、谷子地等,每每“弟兄們”、“弟兄們”地招呼戰士們,高腔而又高調,那派頭很霸氣,很酷!
這樣的稱呼很時髦,很有反傳統的殺傷力,很能獲取同樣不喜傳統而追求新奇的觀眾的青睞,因而很能收取不錯的票房。但這是與史實嚴重不符的。這樣的處理方法,已經不是妥與不妥的問題,而是穿幫,是硬傷了。
作為影視作品中的角色,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言語標簽的。什么是言語標簽?也就是什么身份的人說什么身份的話。比如老舍的《茶館》、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游園驚夢》等等,人物一出場,什么旁白也不用,只是張口一句臺詞,他是個怎樣的角色就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這便是言語標簽的作用。
不用這個標簽倒也沒啥,大不了使作品的藝術水準黯然失色,但若用錯這個標簽就是驢唇不對馬嘴,大錯而特錯了。打個比方,如果影視中的奉軍,沒有“媽了巴子”的標簽,頂多使作品失去些許生動的特色,而若張口閉口“丟他媽”,你認為那還是奉軍嗎?
這個道理,對于一般的觀眾,都好懂,因而導演也不敢這么忽悠,那為什么他們就敢讓李云龍谷子地口口聲聲“弟兄”“弟兄”的忽悠呢?問題出就出在好多人對歷史上中共軍隊的言語標簽是什么沒搞懂。
戰爭時期的中共軍隊中,“同志”,是其區別于所有別的軍隊的最典型最鮮明的言語標簽,沒有了這樣的標簽,也就沒有了中共軍隊的特色,而若再使用當年極力摒棄的“弟兄”的標簽,那自然也就是嚴重的失實了。
有人可能會說,一個稱呼,有那么嚴重嗎?今天我軍很多連長營長不也常模仿著李云龍這么喊的嗎?我的回答是,有那么嚴重。今天可以這么喊,不代表以前可以這么喊,今天的言語環境已經遠遠不是戰爭年代我軍內部的言語環境了。
首先,喊不喊同志,在中共軍隊中不是無所謂,而是有所謂,大有所謂。
早先,“同志”二字,并不唯共產黨軍隊所獨用,在國軍的正式講稿與文牘中,“同志”二字出現的頻率也是很高的,但在日常的生活與工作中,高頻率地使用這兩個字,卻唯共黨共軍所獨有。
在當年的中共軍隊內部,稱“同志”,是區別于舊的軍隊的表現,是左的象征,是敢于叛逆的勇氣,是人們努力追求的時髦,因而便形成與今天正好相反的用語心理,被高調地大用特用,乃至形成鮮明特色。而“弟兄”一稱,因為在國軍和舊的軍閥軍隊中盛行,在當時是被視為落伍的、陳腐的稱呼,因而被避而遠之,加之那時人們普遍存在著寧左勿右的思想,于是便象避瘟神一般地棄之不用。
戰爭年代稱呼“同志”,和全國山河一片紅時的五六七十年代又有不同,不是隨便對一個陌生人問路都可以喊的,那時的“同志”就是黨內黨外公認的中共的專用符號,什么人能喊、必須喊,什么人不能喊,對任何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來說,都是心知肚明,有一把尺子的。在一份署名曹壯父的于1928年寫給中央的報告中,在介紹黃安地區紅軍情況時,有這樣的文字,“他們都把黨看得十分尊崇,即非同志亦不自知為非同志,如果發覺自己為非同志,即十分懊喪,因此對他們的稱謂一定要呼‘同志’,”1946年3月5日,出獄第二天的葉挺給中共中央發電申請入黨,黨中央毛澤東在給葉的回電中,對于是稱葉挺將軍還是稱葉挺同志,斟酌再三,反復修改,最終以“親愛的葉挺同志”落筆。所有這些,都再好不過的說明了當年“同志”一稱的有所謂、大有所謂。
在一些老電影中,有關同志一稱的使用,也說明了這兩個字的分量。比如《獨立大隊》中的草莽英雄馬龍,就因為劉司令員來信中一句“馬龍同志”,便令其感嘆“劉司令沒把我當外人”,從此跟定共產黨,并在其后的臺詞中,故意顯擺地反復使用“劉司令同志”這樣夸張且不太合語法的稱呼,就同樣說明了中共軍隊中同志二字的標簽意味。再比如《紅色的種子》中,當與新四軍做過買賣的商人錢福昌第一次見到準備派往敵占區的華小鳳時,剛剛張口稱呼一句“同志”,便立即被不想暴露身份的華小鳳打斷:“我不是同志,我叫錢秀英。”這一方面說明了“同志”二字不是那么隨便喊的,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在群眾心目中,“同志”所賦予的共軍獨具的標簽意味。
在民國時期,沒有哪支軍隊能象中共軍隊這樣具有那么鮮明的政治特色了。在當時,一個人,不管他參軍前是土匪還是洋學生,是扛活的要飯的還是富家公子,只要加入中共軍隊,他就要接受熔爐般連續不斷的強化灌輸,用今天貶一點的說法,就是強行的政治洗腦,就是強迫性地換舌頭。在這樣的強化政治訓練下,他的包括稱呼在內的用語習慣,也就會很快形成鮮明的特征。這個特征,不論對于敵、我、友,都是判定其是否共軍一個很重要的言語識別方式。侵占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就有以被審訊者是否在下意識中使用“同志”這樣稱呼作為判定其是否“共產匪”的教條。同樣是老電影的《英雄虎膽》,其中有一個細節,說的是打入敵人內部的我偵察科長在審問一個冒充我軍偵察員的敵匪時,就因為該敵下意識的一句“我們共產黨當官的當弟兄的都一個樣”,從而斷定其不可能是我軍人員。這是很真實的。因為如果真的是我軍人員,特別是只有老兵才能充當的偵察員的話,刻意想冒充共軍的他的嘴里是絕對不會說出這“弟兄”二字的。
其次,在中共軍隊中用“弟兄”替代“同志”,不是沒問題,也不是小問題,而是大問題。
也許有的人會說,稱呼一聲“弟兄”也要上綱上線嗎?沒錯。在當年,這極有可能會上鋼上線。為什么呢?因為你既然參加了共軍,你用什么言語來說話,還不僅僅是你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而是你必須要這么做的問題,這是考察你政治立場的一條重要標準。
中共軍隊有一個與眾不同的政治生活,即接二連三的大大小小的整風。這種整風,在中共軍隊的發展史上是比打仗都重要的事,即是在敵后嚴酷的游擊狀態,什么都可以耽誤,而整風絕對不能耽誤。比如被影視翻拍了無數遍的抗戰時期堅持冀中敵后的九分區武工隊,在斗爭那么殘酷、那么需要在敵后堅持的情況下,需要整風時,也要脫離戰斗崗位去參加整風;還有比九分區更艱苦的十分區聯合縣,即使在干部奇缺、又急需補充堅持敵后的情況下,因為整風的需要,卻仍要抽調干部去參加整風。由此可見其對純潔干部思想作風的無比重視。除了這一類較大的整風,還有許多小的整風,隔三差五的支部民主生活會、黨小組會,那也是整風,是整風的小規模化、基層化。整風整什么,整每個人的言行中有沒有軍閥殘余觀念,整有沒有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整有沒有與中共軍隊言行不符的作風。大到正規場合的發言表態,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牢騷,甚至吃飯穿衣說夢話,都在整肅之列,而且是職級越高的人整的越厲害,整的越頻繁。整風怎么整,批評與自我批評。九分區敵后武工隊的小隊長,也就是長篇小說《敵后武工隊》的作者馮志,就是因為在遠離根據地堅持敵后時自作主張為每個隊員購買了一條毛巾這么一件小事兒,而又在自我批評時沒有主動檢討,因而受到組織的批評與斗爭,也就因此而被調離武工隊的。
在今天,既使在中共體制內部,象老畢那樣在聚會時辱罵領袖的現象也并不鮮見,可在三四十年代,甚至一直到七十年代以前,誰敢?在鋤奸、反特乃至肅反的陰影沉重地籠罩在人們頭上的紅軍、八路軍中,誰敢?在當時,因為一句話說的不注意而被同吃一鍋飯同住一張床的身邊人檢舉揭發,因而受到大會小會批評幫助是經常的事,因此遭下課乃至更嚴重處分的事也并不罕見。在這樣的氣候下,即使你一百個不愿意喊“同志”,你也要隨著大家猛喊大喊,即使你特別地想學著國軍那樣喊一聲“弟兄”過過癮,你也得把它噎回去。要是誰敢象李云龍那樣,別說張口閉口“弟兄們”,就是他不小心喊那么一聲,那么這一段時期的支部民主生活會、黨小組會上,他這聲“弟兄們“可能就會成為全體同志的靶子,那么他就要一次又一次地、大會小會地認識、反省、檢討、再認識,直到徹底改正。不改行不行?不行。不改你就交出兵權,一邊呆著去。四方面軍最能打的一個軍長余天云,就不尿這一套,那怎樣?對不起,別說軍長了,連長都沒你的份,被一擼到底,最后成了孤家寡人,自殺身亡。寧都起義后,二號三號人物董振堂趙博生能夠得到重用而一號人物季振同反遭罷黜,固然可能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有待挖掘,但季沒能像董趙表現的那么左而在言辭舉止中處處表現的軍閥習氣,不能不說是他被懷疑乃至被肅殺的一個原因。在中共這支特別講政治的軍隊里,在肅反的陰影嚴重籠罩的三四十年代,像李云龍那樣刻意表現自己的軍閥作風又高調叫喊“弟兄們”的,也就只能存在于新潮編導們的意淫中而已。
就如同街邊女郎的服裝發型需要變來變去以吸引人們的眼球一樣,影視圈的亮點也被經常的顛倒輪回從而不斷刺激觀眾的味蕾。當年作為陳腐代名詞而遭摒棄的“弟兄”,如今就在《亮劍》《集結號》的領導下翻身變成了時髦,從而成為某些文化人賺取票房的賣點。但也就像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一些無知少女穿著從洋垃圾中撿來的妓女服裝招遙過市還自以為得意一樣,影視圈玩弄的所謂新花樣也未必真的都是新的東西,有些可能就是從垃圾堆里重新撿回來的,只是許多觀眾分不清楚而已。
不管編導演們如何為了票房而罔顧史實地追逐迎合不斷變化著的時髦,歷史卻永遠只有一個,而且是艮古不變的。戰爭年代中共軍隊的言語形態,也是如此,它是怎樣的就一直是怎樣的,不管誰喜歡不喜歡。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蔣躍飛:讓抗美援朝的偉大精神化作 民族復興的強大動力 ———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禮贊
2020-10-27?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