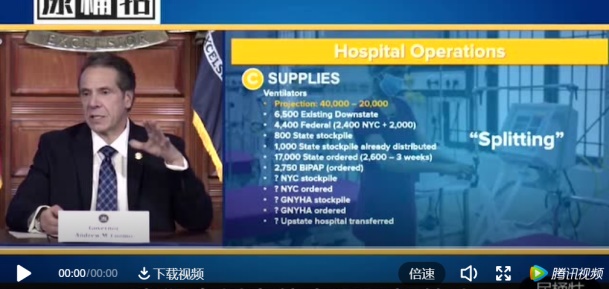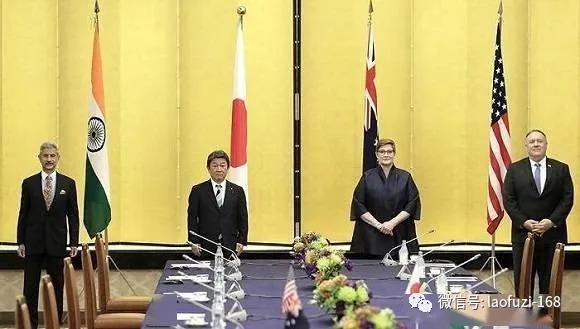【1984年4月,還沒當總統的老布什就在日內瓦對蘇聯裁軍代表伊茲拉埃良說:“你們下一個領導就是戈爾巴喬夫”。圖為1988年美國曼哈頓,老布什和里根一起帶著戈爾巴喬夫見世面。】
【譯者按】本文原名《一種非戰爭手段——大國顛覆策略卷土重來》(A Measure Short of War - The Return of Great-Power Subversion),原載于美國《外交事務》雜志2021年7-8期。作者是Jill Kastner是倫敦的獨立研究人員,William C. Wohlforth是達特茅茨學院政府學教授。在文章中,作者將顛覆策略分為三個層次,列舉諸多實例,探討自古希臘以來大國顛覆策略的典型實踐及其優勢與不足,展望這一政治手段的前景,可說是一篇關于顛覆問題的歷史導論。作者指出,“只有在大國極其衰弱的情況下,對其進行顛覆才能產生效果”,這顯然是有說服力的。當然,單從原標題看,作者要表達的核心思想,是美國在享受了蘇聯解體后二十多年“只顛覆別人,不被人顛覆”的尊榮地位后,已然面臨被顛覆的處境,必須有所應對。作者甚至認為中國與俄羅斯一樣,正在加入美國顛覆者的行列,但沒有舉出中國參與顛覆美國的任何事例,相反倒是談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試圖顛覆中國的失敗經歷。對于此類西式流行性迫害幻覺,我們不必苛責,不妨更多地關注文章中論述的西方國家慣用顛覆手法,加強自己的反顛覆武器建設。譯文中括號內的注釋和補充,除標注“原注”者外,均為譯者所加。
大國政治中的顛覆與反顛覆
吉爾·卡斯特納 威廉·C·沃爾福斯 作
地球村過客 譯
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某外國政權設法對美國民主的這一神圣儀式施加一種似乎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在社交媒體上,一伙拿著薪水的俄國“巨靈”(譯注:原文為troll,本是北歐傳說中的山精,此處用于指網絡信息戰中的輿論專家等)煽動分歧不和,散布對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莉·克林頓的有害謊言,并且試圖壯大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川普的支持隊伍。與克里姆林宮關系緊密的有權有勢的俄羅斯人以承諾提供克林頓的負面信息相引誘,尋求接觸川普及其下屬。由國家贊助的黑客竊取并散布了她的競選助手的私人郵件。他們進而攻擊了所有50個州的選舉系統,甚至設法攻入選民數據庫。這些介入行動值得警惕。“我們已經遭到攻擊;我們身處戰爭之中,”2017年,在由一個自稱“調查俄羅斯委員會”的群體發布的視頻中,演員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嚴肅地宣布,這個群體受到前國家情報局長詹姆斯·克拉帕爾(James Clapper),以及中情局前代理局長邁可·摩萊爾(Michael Morell)等美國情報界老專家的支持。紐約時報的一條新聞標題宣稱“俄國網軍”已經“入侵”了美國。外交政策專家預言一波由極權國家發起以打擊其對立民主國家的數字化顛覆活動正在來臨。“當下的數字生態環境為操縱行為創造了機會,這種操縱行為已經超出了各民主國家的反應能力,有時甚至達到了挑戰的程度,”布魯克林研究所的阿莉娜·波利雅科娃(Alina Polyakova)在2019年的一次國會委員會上作證說,“所有民主國家都是現在或者未來潛在的攻擊目標。”美國政策制定者慌忙作出反應。奧巴馬政府在其最后幾個月里驅逐了35名俄羅斯外交官,沒收了俄國外交財產,而且誓言美國將在自己選擇的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進行報復。2018年,國會設立了一個全新的機構——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作為國土安全部的一個部門——以防止未來的類似入侵。2016年的總統大選本會是一記當頭棒喝,但是大家不必大驚失色。俄國的操縱行動只是有歷史記錄以來就存在的一種政治手段的最新事例。顛覆——即介入別國國內事務以削弱或操控一個敵手——從來都是大國政治學的一部分。乍看起來不正常的,是蘇聯解體后有一個特殊的美國單獨主導世界的短暫時期,此時的美國似乎不為競爭對手的惡性攪局行動所困擾,這主要是由于彼時并競爭對手。現在,美國的主導地位已經開始衰落。大國競爭局面重新出現——大國的顛覆活動也隨之卷土重來。在國際關系中,普遍認為“顛覆”是試圖直接對一個外國的國內政治施加影響,使其偏離(該國)所期望的方向,從而獲得某種好處的行為。通過操縱另一個國家國境內的事件,一個顛覆者希望改變現政權的政策——或者改變該政權本身。顛覆活動會混雜戰爭入侵和間諜竊密,但并不能明晰地歸屬于后兩類情況之中。它缺乏戰斗和軍事威脅的公開性,以及間諜和情報收集的被動性,以及外交和高壓政治的虛文性。它是秘密的、主動的和無禮無法的。顛覆活動可以依其嚴重性而分為三級。第1級跟宣傳相關,這個手段跟說話本身一樣古老。1570年,教皇皮尤五世發布詔書,宣布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為異端,并號召虔誠的英國天主教徒廢黜她,這樣他就是在進行顛覆性宣傳。同樣真實的事例,是冷戰期間“自由電臺”對蘇聯進行反共廣播。第1級顛覆活動可以包括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選舉中反對派候選人或者政黨的承諾,例如1948年斯大林公開支持美國第三黨候選人亨利·華萊士向哈里·杜魯門競逐總統職位。它也可以包括削弱一個在任者。在19世紀的歐洲,德國首相奧托·馮·俾斯麥強烈反對英國首相威廉·格萊斯頓參與歐洲事務,以至于開展了旨在損毀格萊斯頓國內聲譽的口誅筆伐——一場反對格萊斯頓的抹黑宣傳運動。正如俾斯麥之子赫伯特1884年在一封信中所說,該計劃將“把格萊斯頓拍死在墻上,讓他不能再胡言亂語。”他又說,這個首相的聲譽,“甚至在愚蠢的英國選民中也將一踏糊涂。”顛覆活動進一步加劇,就進入了第2級。這一級的形式仍然是隱蔽的,但是包括了虛假信息,這是一種更加有力的宣傳手法。例如在1980年代,克格勃與東德斯塔茲(譯注:Stasi,民主德國國家安全局)合作,散布謠言稱HIV是美國在一項生物武器項目中研發的;1983年,他們將這個消息發表在一份印度報紙上,并最終被其他地方的主流媒體所采用。在兩年內,這個故事已經在全非洲和其他地方廣為散布,至今還有人相信。偽造是第2級顛覆活動的常用策略。1981年,在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被一名槍手襲擊后,克格勃行動人員散布虛假消息,暗示華盛頓是暗殺企圖的幕后黑手。最近,在網絡上虛構并不存在的人物,成了另一種策略——但跟俄國在2016年創造的手法不是一回事。早在2011年,美國軍方就開始在反恐怖主義的戰斗中實施此類行動,研發軟件來編造用外國語言講述的虛假故事用以反擊網絡上的極端主義。第2級顛覆活動也可能包括暗中向反對勢力或者利益群體提供金錢或物資支持。實施顛覆活動的國家希望,這些群體或許能夠在境外的幫助下,改變顛覆目標國的政策或者煽動不和。修昔底德講述說,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對薩摩斯島的陰謀者許諾以波斯人的資金援助,誘使他們推翻本國的民主制度。雅典人“敦促薩摩斯島上最有權勢的人與他們合作,嘗試在那兒建立一個僭主政權,而無視薩摩亞人剛剛通過一次國內起義而避免了被一個僭主所統治,”他寫道。更為晚近的事例,是在1929年的英國,蘇聯給予工黨一筆秘密資助,工黨與自由黨聯合,隨后在國會選舉中贏得了足夠的選票組建政府。冷戰期間,蘇聯試圖幫助它認為會更為友善的美國總統候選人。1960年,它帶著一張支持清單,直接找到阿德萊·史蒂文森門上;又于1968年直接與赫伯特·漢弗萊接觸,為其耗費巨大的競選活動提供財政支持。(原注:這兩位候選人都婉拒了它的幫助。)莫斯科也致力于削弱被它認為具有敵意的候選人。1984年,克格勃開展了一次全面行動,運用有影響力的代理人、掩護組織和虛假信息,讓美國公眾相信羅納德·里根的再度當選將意味著戰爭。除了針對選舉制度之外,克格勃還試圖使美國民權運動激進化,以引發國內動蕩。它試圖通過散布關于小馬丁·路德·金不當行為的信息,使其名譽掃地,它還密謀為更激進的民權領袖宣傳造勢。當然在此期間,中情局也在蘇聯扶持異見人士,為他們偷運被禁止的材料,提供金錢、公關服務,為俄羅斯、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民族主義者和具有改革思維的共產黨人提供出版渠道。第3級顛覆活動是暴力的:武裝和資助叛亂分子,破壞基礎設施,暗殺反對派。1570年代,當尼德蘭的新教徒起義反抗西班牙統治時,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秘密幫助他們雇傭瑞士和其他軍隊為新教事業而戰。在北愛爾蘭動蕩時期,蘇聯向北愛爾蘭共和軍提供金錢和武器,妖魔化那些竭力阻止北愛分裂潮流的倫敦官員。在冷戰初期,美國也力圖通過為波羅地海國家和烏克蘭叛亂者提供后勤和物資支持而顛覆蘇聯。它也試圖對共產主義中國采取類似的策略,支持西藏的叛亂分子。在這三個層次中,顛覆的目標可能有所不同。顛覆性行動可以通過誘發內部不和,使一個目標政權無法專注于追求其他領域的利益,而使之受到削弱。這正是伊麗莎白資助雇傭軍去幫助荷蘭新教起義者所要達到的效果——她希望西班牙會被起義折騰得精疲力竭,只好擱置推翻她而在英國恢復天主教地位的計劃;這也是今天俄國在西方民主國家支持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運動所想要達到的效果。或者,一個國家可能意圖通過秘密支持另一個國家國內爭論的某一方而改變該國的對外政策。冷戰期間,莫斯科通過其掩護組織,對西方反戰運動提供后勤的、組織的和財務的支持。更加晚近的事例,是它或許介入了2016年英國脫歐運動,鼓動英國公眾投票脫離歐盟。有些時候,顛覆活動有一個貪大求全癖(maximalist)的目標:改變政權本身的性質。1875年,俾斯麥制造了一次戰爭恐慌,暗示德國將要對法國發起一次預防性打擊。他的目標是威嚇法國選民不要選擇保守的君主派,他們如果獲勝,顯然將在整個萊茵地區形成更加強大的大國競爭者。這個策略見效了。法國媒體很快習慣于將俾斯麥稱為“法蘭西的大選舉人”。歷史上各國如此經常地采用顛覆策略,一個原因是:與通常的政治手段相比,它的耗費和風險都要小得多。通過顛覆以削弱對手,對均勢與戰爭來說,是一個便宜的替代物。通過顛覆改變對手的政策,對于高壓政治、威懾和外交手段來說,是一個便宜的替代物。如果你能夠通過散布宣傳說辭,收買政客或者部署互聯網“巨靈”而獲得微妙但實實在在的收益時,為什么還要征召一支軍隊并入侵一個敵對國家呢?如果你能輕松地與對手內部的反對派群體聯手,而他們亟盼你給予幫助并努力分散當權者的力量,你為什么要把自己捆綁在一個有風險的聯盟里,或者為了增加遏制對手的手段而弄得入不敷出呢?即使顛覆活動取得的成效比傳統政治手段要小,它也仍然是有吸引力的。畢竟,在一個大國對手相互競爭的環境中,各國都存在削弱他國的動機。既然大國主宰國際政治,即使在一個大目標上取得一點小成效,也得值得為之付出的。顛覆活動也意味著靈活性:一個國家可以對一個對手施加壓力,以改變其行為,而無須把大炮推到邊境上或者進行成本巨大的引誘或退讓。如果問題激化,可以降低顛覆活動的等級或者裝做不知情,這在一個變動不居的環境中給予顛覆者更大的行動空間。只有愚蠢的將軍才會僅僅為了看看他到底能夠走多遠而發動一場戰爭,但是一個顛覆者卻可以這樣做。顛覆活動可以釋放一些導致國家相互攻擊的恐懼感和受挫感,于是起到安全閥的作用。它是一種有誘惑力的非戰爭手段;如果武裝沖突的成本高得無法承受,那么顛覆活動則不失為一種提高國家地位的替代辦法。換言之,顛覆活動是國際關系中的鬣狗。它潛行在法理世界的邊緣,等待渾水摸魚的機會,但卻缺乏在開闊地帶進行攻擊的勇氣。正如鬣狗在自然界的食物鏈上處于關鍵地位,顛覆活動也在國際政治競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很多案例中,它使得各國避免在戰爭與和平之間二選一,使得它們用引發動蕩但或許較不危險的方式削弱其競爭對手。顛覆活動也使得受害者可以作出有節制的反應。受到顛覆活動困擾的大國們會保持克制,這正是因為他們發現這種政治手段(即顛覆)確實是有用的,因此不愿采取(激烈的)行動導致其永遠被從政治工具箱中移除。從今天的后見之明來看,1980年代里根政府對克格勃強化政治戰的反應顯得很溫和:只是創設了一個部際小組,公開揭露蘇聯散布虛假信息的活動。這種克制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美國此時也忙于顛覆蘇聯。一份已解密的1987年文件概述了中情局的一個計劃“旨在利用當前蘇聯‘公開化’政策以及電子通訊革命,這兩項進展為我們的秘密行動計劃提供了一個深度影響蘇聯受眾的空前機會。”另一份解密文件記述了1987年的一次白宮會議,顯示美國政府印制了冒稱來自某個共青團組織的小冊子。“六千冊已經偷運進入蘇聯,”這份文件說,“要求支持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計劃,但是要求進行超出現政權容忍界限的民主改革。”因此毫不奇怪,里根政府顯得沒興趣去懲罰蘇聯的類似行為。這些是顛覆活動的優點,但是它也得付出成本。最為明顯的是招致報復,而且目標國家越大,報復也就越重。局勢升級,無論偶然的還是蓄意的,都是真正的危險,特別是實施第3級顛覆活動時,目標國家的紅線可能被突破或者局中人可能越過其信仰的邊界。更為不明顯但也許更為重要的是,由于顛覆活動的進行,相互間的信任可能會遭遇潛在的破壞。相互信任在國際關系中是至為重要的。即使在死敵之間,一丁點兒相互信任也使得合作和緩和具有可能性。顛覆活動得冒毀滅信任的風險,而且與諸如軍事集結或者組建新聯盟等傳統行動相比,它可能更容易做到這一點,傳統行動只有在目標國家隨后采取錯誤行動時才導致損害。顛覆活動也不足以及時正確地展示一個國家的意圖。通過增強自身實力或者揮舞傳統的胡蘿卜和大棒以改變另一個國家的行為,通常是更加安全和容易的。一個國家通過此類傳統的政治手段,能夠展示它對于對手并非始終懷有敵意,而是只有在對手采取進一步行動時才準備予以打擊。然而,顛覆活動使得這樣的信息更加難以傳送。一旦顛覆活動已經實施,顛覆者再也不可能宣稱自己實際并無敵意,目標國家也不可能改變其行為以避免懲罰。加害者通常否認自己與顛覆活動有關,這一事實使得問題更為復雜難解。一個政府很難假裝一方面沒有從事某項活動而另一方面又答應中止該項活動。另一種成本是不易觀察到但更富于爭議的。實施顛覆活動的政府會因為損壞最受珍視的國際關系規范即主權而備受責罵。這個規范,通常認為成形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它認為諸國都在其疆界內擁有終極權威,因此其他國家不得介入。對很多學者來說不證自明的是,觸犯這一規范的后果(譯注:即觸犯者受到懲罰),可以起到遏制顛覆活動的效果。但是正如現實主義學者指出的,真正起作用的是各國行使其主權的實力,而非規范自身。畢竟,早在反對此類行為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成立之前,各個國家就強烈反對其對手在其疆域內進行的敵對性行動了。而且迄來已經發生了大量的顛覆活動,甚至是由那些聲稱尊重主權規范的國家所實施的。規范是一種會在強力面前屈服的約束。當然,在某些時候,一個國家進行顛覆活動的成本超出了收益,因此決定退卻。潛在顛覆者的必備技巧是正確地計算成本,特別是對手可能采取的報復行動。畢竟一個國家的小怒火可能會觸及另一個國家的紅線。當一個大國要擺平一個弱小國家時,成本—收益分析通常會有利于大國,因此如果這種不對稱性足夠顯著的話,那么可以預測較強的國家會運用顛覆手段。大量事例表明,當存在這樣一種力量不平衡狀況時,顛覆活動就會層出不窮,從蘇聯在阿富汗到美國在伊朗和智利都是這樣。政治科學家亞歷山大·唐尼斯(Alexander Downes)和林賽·奧羅爾克(Lindsey O’Rourke)已經清點出自自1816年以來一個國家企圖導致另一國家政權更迭的事例逾100個。不必驚奇的是,沒有一例發生在和平時代的大國中。畢竟,政權更迭是一件嚴重的事情。如果一個大國采取行動,試圖導致另一個同級別大國的政權更迭,這兩個國家幾乎必定已經——或者即將——處于交戰狀態。然而在戰爭時期,成本收益分析卻是不同的,因為多數成本沒有效益。既然戰爭已經開始,對于報復和升級就較少引起關注;也不必再擔心顛覆活動所帶來的壞名聲可能阻礙雙方合作。因此,大國們趨向于在戰爭的熱度中猛烈傷害對方。法國和英國在拿破侖戰爭期間瘋狂地相互顛覆,資助對方疆域內傾向于自己的政治勢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有一個針對沙皇俄國的內容廣泛的顛覆計劃,最終的結果是它用火車將弗拉基米爾·列寧送到彼得堡的芬蘭車站,點燃了革命之火,使俄國退出世界大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培植了第五縱隊——向其政府的敵人效忠的外國公民——以損害法國和蘇聯。但是如果大國競爭對手們并不處于戰爭狀態,顛覆活動就通常保持在沸點之下——有所用而且無處不在,但是并不導致局勢突變。在整個十九世紀,奧地利、德意志和俄羅斯帝國擔心法國或者英國會支持波蘭獨立,從而威脅到他們的領土完整。但是他們的恐懼并未變成現實,因為巴黎和倫敦的領袖們知道這些帝國為了阻止波蘭獨立而不惜一戰。在同一個時期,英國也擔心俄國有意將印度納入其不斷壯大的帝國,因而會削弱不列顛在印度的地位,但俄國沒有這樣做。在所有這些事例中,各大國的內心里都為其大國對手準備了刀子,但他們決定不使用它們。在和平時期,顛覆活動的成本簡直過于巨大:相互信任的毀滅,以及受到報復和局勢升級的現實可能性。大國是難纏的目標。這是顛覆的基本模式,但也還有變型。一個大國通常會在其對手虛弱時下殺手。公元前464年,當一場毀滅性的地震導致斯巴達發生暴動,斯巴達要求其他希臘城邦幫助平息叛亂,但是拒絕了雅典4000人的隊伍,因為害怕他們會轉變立場而支持叛亂者。(原注:修昔底德評價說雅典人“進取和革命的性格”構成一種獨特的威脅。)1875年,法國正從普法戰爭后蒙受失敗和占領后恢復元氣,俾斯麥就決定操縱其國內政治。1950年代,共產主義中國尚未從革命和戰爭中恢復,中情局就武裝并唆使流亡緬甸的國民黨軍隊連續發起對中國云南省的侵擾。顛覆出現變型的另一個原因,是目標國家對顛覆活動有一定的容忍程度——亦即在目標國家中,支持敵國的代理人可以利用法律和政治權利進行廣泛活動。冷戰期間,各國共產黨構成了一個世界性的網絡,這使得莫斯科滿懷希望,卻令西方各國首都憂心忡忡。例如法國共產黨擁有廣泛的支持,并將支持蘇聯關切的問題作為自身固有的一項關鍵使命。該黨隨時準備執行斯大林的命令,例如組織反對馬歇爾計劃的大規模罷工。法國的實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削弱,不能有信心地阻斷莫斯科對該黨的影響,因此只能對這一國內威脅采取防御策略,這常常意味著對法國共產黨的暴力壓制。但是顛覆活動很快就退潮了。在查爾斯·戴高樂領導下,法國政府在克里姆林宮眼中成了遠比法國共產黨所能提供的任何東西都有價值的外交資產,因此在冷戰的剩余時間里,法共被降到了附屬的地位。顛覆活動也隨著兩個大國關系的狀況而起落。競爭對抗越是激烈,可能搞顛覆的國家就越少擔心其可信度是否受到損害;因為合作的前景已經很暗淡。這正是美國外交官喬治·坎南在冷戰開始時審視美蘇對立問題的方式。坎南認為顛覆活動沒有多少消極面——它肯定比預防性戰爭或者永久性的歐洲聯盟更為便宜而且更少風險——這是他為什么提議將顛覆作為美國戰略的核心任務。因此在1948年致總統的一份絕密備忘錄中,他建議華盛頓“鼓動俄國各個具有不同觀點的民族的發展,或可有助于調整現今蘇聯的行為,進而允許各顯示出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能力和決心的民族恢復其生活方式”——換言之,煽動蘇聯民族主義的烈火,進而是分裂主義的烈火,導致莫斯科在冷戰中甘居下風。然而,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最終被證明是難以顛覆的,而且它對顛覆活動作出升級回應的威脅也是完全可信的。坎南高估了斯大林的反對派們的支持率,低估了這位獨裁者鎮壓反對派的能力。經過一段時間,美國外交家們開始相信,如果實施第3級顛覆活動,就不可能與莫斯科延續必要的外交關系,因此華盛頓在冷戰的剩余時間里就集中精力從事第1級和第2級顛覆活動。(原注:例如,它沒有試圖再度派武裝叛亂分子向蘇聯境內滲透。正是由于這些原因,1980年代,一個與巴基斯坦聯合向蘇聯塔吉克斯坦派遣中情局支持的阿富汗穆斯游擊隊員的計劃被中止了。)相比較而言,中國是一個更有誘惑力的目標。它實力遠遜于蘇聯,而且(與美國)的外交往來本來就很弱,不必費心去維持。因此,中情局從1950年代末到整個1960年代對西藏叛亂分子進行援助扶持。這項行動直到1972年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實現對北京的外交首訪時才被擱置。大國使用顛覆策略的變型也取決于它們的相對優勢:當與其他可用的政治手段相比,只要顛覆活動還具有吸引力,那就各國就會一直選擇使用顛覆策略。如果影響力能夠公開而且廉價地獲得,顛覆活動則會失去一些光彩。在冷戰早期,美國感覺自己用以影響蘇聯的選項甚少,因此顛覆策略在當時美國政客心中的份量很重。后來,當外交和貿易往來增多時,華盛頓有了更多的手段向莫斯科施加壓力。到了單極時代,隨著民主大步前進,美國愈發感覺對顛覆活動的需求甚少了。政策制定者們覺得,資助非政府組織宣傳民主,比將此任委于中情局更好。正如全國民主促進會的共同創建人亞倫·韋恩斯坦(Allen Weinstein)在1991年所說,“今天我們所做的很多事情,在25年前是由中情局秘密開展的。”最后,新技術的出現,將為顛覆活動的開展提供全新的機會,因此暫時攪亂成本—收益分析。喬納斯·古騰堡在十五世紀中葉完善的活字印刷業開始了一場信息和觀念大規模傳播的革命,其中包括嚴重顛覆天主教會的并開啟新教改革這樣的事件:1517年,馬丁·路德將其“95條論綱”釘在威騰堡一個教堂的門上。幾十年后,威力漸增的火藥以及轉輪打火手槍的發明,使得刺客能夠單槍匹馬接近目標予以殺傷。尼德蘭的威廉一世在1584年遭此厄運,這促使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禁止將機械火槍帶入任何皇家宮殿500碼的范圍內。但是隨著時間流逝,近來軟目標也被硬化了。印刷品催生了審查制度和反宣傳;手槍催生了裝甲和保鏢。歷史上的這個循環不斷自我重復。曾有一個時期,美國官員認為無線廣播將是削弱蘇聯的潛在工具。然后是復印機,接著是個人電腦。但是在每個時期,莫斯科都能作出反擊,對外國無線電臺進行干擾,管控復印機和其他技術的銷售。鐘擺總是要擺回來的。從這段漫長歷史的背景來看,2016年的事件顯然并非不正常。美國陶醉于自己后冷戰時代的全球主宰地位,放松了警惕性,忽略了大選前人們關于對于關鍵性基礎設施的警告。新的技術——互聯網—為其他大國提供了一種可以試試看的嶄新、廉價而強大的顛覆武器,因而創造了一種暫時的不對稱性。結果,這個顛覆活動的目標國家現在發現自己正手忙腳亂地加強防范,研究新的辦法進行報復并提升對方顛覆活動的成本。歷史提醒我們,當今要讓某個大國真正易于被顛覆,就得使其(實力)受到嚴重削弱。除非發生戰爭、革命或國家崩潰,否則沒有任何大國——既非美國,也非中國或俄國——可能衰落到能被顛覆的地步,例如法國在普法戰爭之后的那般境況,俾斯麥才能夠如此有效地攪局。只有在大國極其衰弱的情況下,對其進行顛覆才能產生效果。但是與過去二十多年相比,今后程度較輕的(大國相互間施加的)影響和干擾將更為常見,這純粹是由于在特殊的美國單獨主導世界的非常時期后,世界已經回歸到常態。換言之,顛覆策略已經在政治技巧的諸多工具中重新找回了合適的位置。但是,顛覆活動也由于近年來的其他趨勢而得到加強的。其中一個趨勢是當前競爭對手們所呈現的意識形態色彩日益濃厚,各對立國爭論的重大問題不僅有各自的國家利益,而且也有他們的國家治理制度。正如在十六世紀的宗教戰爭或者二十世紀的冷戰中,競爭對手們將對方看作有悖法理的,他們于是就更堅決地運用顛覆手段。另一個趨勢是美國國內分離勢力的崛起。關于政治和經濟平等的意見紛爭不斷擴大蔓延,將使不滿群體成倍增加、社會缺陷隨處可見。由于美國公眾的觀點不可調和,川普時代的傷口仍然疼痛,這個國家的敵人將有新的機會實施顛覆行動。但是我們還得說:事情向來如此。各個國家總是受害于內部的脆弱點,外國勢力可以利用之。俄羅斯總統弗拉迪米爾·普京很高興從法國的現狀中得到益處:盡管瑪麗娜·勒龐的全國陣線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國內運動,卻正好在削弱歐洲(一體化)計劃方面迎合了俄國的利益。1980年代,蘇聯找準機會支持真心實意的歐洲和平活動人士,他們反對在歐洲部署新的導彈,鼓吹凍結核軍備。同樣,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美國官員也毫不猶豫地與堅定不移的自由派改革者實現了利益聯合,并從中受益。這種后冷戰時代的趨同思維——該觀念認為歷史站在民主和美國實力的一邊——必須讓路于對充滿競爭的現實的直率評估。顛覆史也應解釋我們為什么要對新技術放寬心態。無疑,有一天某個顛覆者會運用現在尚未引起警覺的新技術。從印刷術到無線電,從蠟紙油印機到互聯網,技術變革已經穩定地開辟了操縱和顛覆的新途徑——也促成了筆跡和牙齒印模的新技術。最近幾年,深度偽造術——偽造看起來真實的視頻片段——已經預示著令人恐懼的假信息被采信的前景。但是各國將找到新的辦法進行回溯還原,或許利用搞出深度偽造品的人工智能作為摧毀深度偽造品的工具。對顛覆心存憂懼的人也應記住,政治和政治手段尚能管住顛覆。顛覆是采用其他方法的大國競爭的延續,就新出現的美國與中、俄競爭的性質來看,各方確實需要進行大量合作。在氣候變化、軍備控制和核擴散方面,大國們必須齊心協力。中國和俄國想在世界舞臺上得到的許多東西,都得與美國及其盟友協商后達成交易。美國的大國對手們肯定明白,如果他們依賴顛覆手段造成自身信譽受到損害,就不可能與美國達成協議。成本—收益分析的老規則將仍然是適用的,可以防止顛覆手段被無節制地濫用。歷史只能詮釋過去,也有助于解說現在;但它不能預言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有可能用以探究未來的顛覆活動。大國競爭將永遠伴隨著一定程度的相互干涉,因為各個國家無論承認與否,都會發現它是有用的。就像對間諜活動一樣,各國政府不愿意放棄自己手中有價值的政治手段,雖然它們在口頭上如何大談遵從規范、注重小節。這個世界并不是進入了一個顛覆的新時代。它從來就沒有離開過舊時代。
(作者:吉爾·卡斯特納,倫敦獨立研究人員;威廉·C·沃爾福斯,達特茅茨學院政府學教授。譯者:地球村過客。來源:昆侖策網【原創】,譯者授權發布)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習近平簽署主席令,《中醫藥法》正式頒布
習近平簽署主席令,《中醫藥法》正式頒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