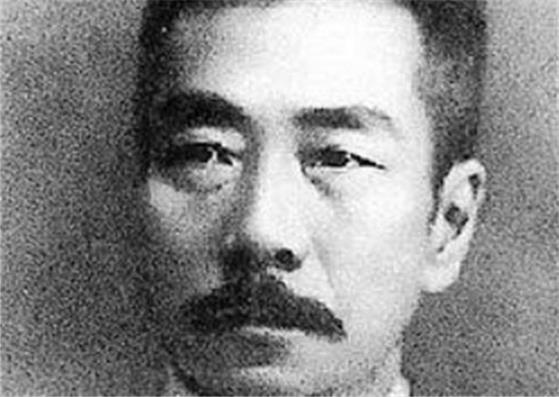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7日-星期三
編者按:偉人心懷坦蕩,但偉人的言行如被“人為”地剝離歷史的特定場景或被“人為”地與特定歷史場景錯位、混淆,必將歪曲歷史。黃宗英以“現場見證人”“親聆者”身份吸引眼球發表“編排”的《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一經發表,抹黑毛澤東、詆毀中國共產黨、歪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奇談怪論絡繹不絕,更有別有用心者推波助瀾。在信息傳播迅捷便宜的今天,這樣的文章讓不少不明真相的讀者、不少無暇查證的讀者可能產生了混亂的認識,至今不絕。本文《黃宗英“親聆”版“毛羅對話”追蹤調查》的作者以為人民還原歷史、還偉人以公道為使命,耗時14年,赴“毛羅對話”事發地上海調查考證,眾多確鑿資料證明:黃宗英的《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一文,完全不符合歷史真相。現予再次登載,以饗讀者,以正視聽。
黃宗英“親聆”版“毛羅對話”追蹤調查
秋 石
2002年~2003年期間,黃宗英發表了基本內容大致相同的《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簡稱《對話》)一文。該文的核心內容是: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與各界代表人士座談,他在回答羅稷南“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會怎么樣”的疑問時說:“要么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該文發表后在華人世界引起了強烈反響,有成千上萬篇文章與之呼應,各種抹黑毛澤東、詆毀中國共產黨、歪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奇談怪論應運而生,其負面影響至今仍很大。筆者對黃宗英“親聆”版“毛羅對話”的歷史真相進行了長達14年的調查,現將調查結果提供出來,敬請指正。
一、黃宗英“親聆”版“毛羅對話”的撰寫和發表
首先應搞清黃宗英撰寫《對話》的來龍去脈。2003年8月,陳明遠主編的《假如魯迅活著》在文匯出版社出版,該書收入了丁東的文章《有關“毛羅對話”的一些事》。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對話》的撰寫和發表并不是黃宗英個人回憶那樣單純,而是有明確目的和多人謀劃的結果。
下面是《有關“毛羅對話”的一些事》的摘錄:
去年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出版了一本書《魯迅與我七十年》。有一次去看戴煌先生,他對我提起這本書,說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買到。我從他家出來,在不遠處的三味書屋就買到了一本。書店營業員告訴我,這書賣得挺好的,就兩本了。我趕緊告訴戴煌先生,讓他去買。誰知他并不是要買一本,而是要買十幾本,分送朋友。他的用意很明確,就是想讓朋友們看一看書末提到的“毛羅對話”。我理解戴老的心情……
周海嬰書中講述的“毛羅對話”,口氣并不十分肯定。一是因為當事人羅稷南已經去世;二是周海嬰雖然見過羅稷南,卻不是直接聽他所述,而是聽別人轉述。
然而,不久此事便引起了爭議。質疑者的文章我沒有全看過,但其中謝泳、陳晉兩個熟人的文章是讀了的。
后來,鐘沛璋先生也寫了文章:《假如魯迅活到1957年》,在“毛羅對話”的基礎上立論。此文要收入文集,請李銳先生作序。李銳在序中又提到此事。如果“毛羅對話”是假的,這些文章都成了空中樓閣。有一次,在一家餐館的開業慶典上,李銳、李普兩位老先生說起此事,談到謝泳、陳晉為什么要質疑“毛羅對話”的真實性。
……
接著,我又聽陳明遠先生說,還有更重要的證人:黃宗英是當事人,毛羅對話時她在場。于是,我和《老照片》的主編馮克力一起與黃宗英聯系,請她為《老照片》寫一篇文章,說明當年的見聞。黃宗英老師在電話中表示:這件事還得慎重考慮。
在此期間,李銳、李普、戴煌、鐘沛璋等老前輩都希望黃宗英能夠出來作證,并通過黃宗江轉達他們的建議。一些親友也為此多次鼓勵她動筆。黃宗英年逾古稀,臥病在床,身體衰弱,但是思維很正常,記憶很清楚,對45年前的這一件事印象非常深刻;她手指不靈便,寫字有困難,想以口述的方式,讓人代筆。陳說,這件事很重要,還是請她親筆撰寫為好。黃宗英嚴肅認真地回憶,并查找了當時的報紙,幾次執筆,寫成了那篇《我親聆羅稷南與毛澤東對話》。
從以上摘錄可以看出:黃宗英最初認為“這件事得慎重考慮”,采取了回避的態度;后來又以手指不靈便、寫字有困難為由,想以口述方式,讓人代筆;最后,經過一些人的鼓動和一些親友尤其是胞兄黃宗江的多次鼓勵,才動筆撰寫《對話》;參與鼓動黃宗英的主要有李銳、李普、戴煌、鐘沛璋等,還有來回穿梭傳話的丁東、陳明遠等人。
2002年~2003年期間,《對話》在《文匯讀書周報》(上海)、《南方周末》(廣州)、《同舟共進》(廣州)、《世紀橋》(哈爾濱)等報刊登載。顯然,這樣大規模的刊發,絕不是作者投稿所致,而是有人運作的結果。
二、黃宗英《對話》發表時仍有九位談話參加者健在
黃宗英在《對話》中說:“這段‘毛羅對話’,我是現場見證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還活著的人也聽到這段對話。”這給人一種感覺,似乎撰寫《對話》時其他談話參加者都不在世了,黃宗英是唯一健在的現場親聆者。然而,按《解放日報》1957年7月10日刊登的與會36位人士名單,筆者先后查找到撰寫《對話》時依然健在的九位談話參加者。黃宗英對45年前的“毛羅對話”內容記得那樣清楚,竟然想不起同時聽到“毛羅對話”的健在者(假如真有“毛羅對話”),這應該是不可能的。
這九位參與者是(以健在時間長短為序):
陳鯉庭,著名戲劇、電影導演,生前一直居住在上海,2013年8月27日(《對話》發表11年后)病逝于上海華東醫院,享年103歲;
王元美,著名戲劇、電影編劇,生前一直居上海,是與黃宗英長期過從甚密的好友,2012年8月4日(《對話》發表10年后)病逝于上海華東醫院,享年98歲;
丁忱,原中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上海工商學院院長,2011年(《對話》發表9年后)去世,去世前定居海外,享年92歲;
談家楨,著名遺傳學家,中科院院士,復旦大學教授,2008年11月1日(《對話》發表6年后)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享年99歲;
蔣學模,著名經濟學家,復旦大學教授,2008年7月18日(《對話》發表6年后)病逝于上海華東醫院,享年90歲;
葉寶珊,全國政協原常委,原上海市工商聯副主委,2008年4月20日(《對話》發表6年后)病逝于北京,享年89歲;
吳中一,工商界著名人士,全國政協原委員,原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市工商聯副主委、民建上海市副主委,2006年(《對話》發表4年后)在香港去世,享年96歲;
李國豪,著名橋梁學專家,多屆全國人大代表 ,第六屆上海市政協主席,原同濟大學校長,2005年2月23日(《對話》發表3年后)病逝于上海華東醫院,享年92歲;
陳銘珊,全國政協原常委,原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2003年7月19日(《對話》發表次年)病逝于上海,享年87歲。
上述撰寫《對話》時依然健在者中,健在時間最長的是陳鯉庭、王元美。陳鯉庭不僅是黃宗英的同行,而且是幫助她走上影壇的伯樂。王元美是著名電影編劇,與黃宗英同為上海市的專業作家,黃宗英稱其為大姐。黃宗英與陳鯉庭、王元美長期在同一座城市居住和領取離休工資,《對話》發表10年內都依然健在。如果《對話》講的是事實且想增強其真實性,為何不向近在咫尺的他們求證或請他們聯名發表,又為什么用“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這一類似是而非的模糊說法,來佐證和加固自己是所謂的唯一健在的歷史現場見證人的身份呢?
從當時的文字報道和照片看,參與談話的上海各界代表人士共36人,他們圍坐在毛澤東的四周,談話現場的空間很狹小,毛澤東講話時現場不可能很嘈雜,每個人說的話應該都能聽清楚。《對話》發表前后,這九位健在的與會者沒有一位公開發表相關意見,更沒有人證實或附和《對話》內容。
三、《對話》的描述與黃宗英當時的感受有強烈反差
在《對話》中,黃宗英描述了她聽到“毛羅對話”時的感受:“震顫”,“血液循環失常”,“震撼心靈的一瞬間”,“嚇得肚子里娃娃險些蹦出來”。她還說:“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憊得幾乎暈厥,只覺得腹中胎兒在伸胳膊踢腿。我擔心已驚動了胎氣。作為母親,我怕自己的精神負擔影響到即將出世的寶寶”,因而“請假休息了三四天”。然而,《對話》關于談話當晚黃宗英的表情描述與實際歷史上三天后黃宗英所談的感受有強烈反差,這從當時留下的照片和當年《文匯報》的報道中可以看出。
1957年7月7日晚,毛澤東與上海36位各界人士的談話剛結束,就一起步出會議廳前往小劇場的通道上,準備觀看經典越劇《追魚》。由徐大剛拍攝的現場照片顯示,走在頭排的共五個人,從左至右依次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居中者為毛澤東,毛澤東右側是王元美、黃晨、黃宗英。照片中黃宗英面帶笑容,微微側身仰望毛澤東,看起來心情輕松、愉悅,完全看不出她在《對話》中描述的驚恐不安的表情,甚至與她當初描述的情形恰好相反,這恐怕不是用掩飾或裝扮等可以解釋的。
1957年7月10日,也就是所謂“毛羅對話”后的第三天,文匯報社邀請13位參加7月7日談話的人士進行座談。1957年7月12日,《文匯報》以《和毛主席一次親切會見——上海市科學教育文學藝術界人士應本報邀請座談感想》為題,用一個半版的篇幅報道了包括黃宗英在內的13位人士談的感受。
黃宗英是如此介紹她的感受的:
我對毛主席印象特別深的一點是:毛主席非常關心每個人的工作和生活。有的以前見過的,他一看見就叫得出名字,知道在搞什么工作;有的初見,但在臨別一一握手時,主席都叫得出姓名了。
毛主席和我們坐在一起,問起每個人的情況,有時說一些自己的意見。他的談話是這樣親切簡單而有力。在談到反右派斗爭問題時,他說右派給我們上了一課。毛主席并說,自己也受到了教育。又說,右派把整風搞亂了……
毛主席這次到上海來,對上海人民是很大的鼓舞,很多人知道我們見到毛主席,紛紛問起毛主席的健康,毛主席談了些什么?……他們也希望多從報上知道毛主席的消息。
我和趙丹在七·七晚上見過毛主席后,第二天一清早,就把這大喜事告訴了我們的孩子,孩子也高興極了,問我們:“毛主席為什么找你們談話啊,你們是勞動模范嗎?”我們聽了很慚愧,我們對孩子說:“我們不是,是毛主席要我們好好工作,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毛主席的召見,對我們將永遠是最有力的鼓舞,最嚴格的督促。
從以上表述可以看出,毛澤東在談話中“親切簡單而有力”,黃宗英對參與座談感到很榮幸、很興奮,這與她幾十年后在《對話》中的表述大相徑庭。
四、《趙丹傳》印證了黃宗英參加談話后的真實感受
《趙丹傳》的作者是倪振良。倪振良系上海崇明人,編審、作家、教授,中共黨員,先后在國家教委《人民教育》雜志社、中國《民主與法制》雜志社、香港《大公報》社、《中國老年報》社、香港《文匯報》社等供職,是以嚴謹著稱的記者型作家。20世紀80年代初,倪振良著手收集資料撰寫《趙丹傳》,其時趙丹已經逝世,作為趙丹夫人的黃宗英是相關資料的主要提供者。《趙丹傳》后記有這樣的說明:“在蛇口荔園,在京中賓館、在我家斗室,宗英先后與我傾談了5次,向我提供了大量珍貴素材。”1985年,倪振良根據他與黃宗英多次面談獲得的資料,撰寫出版了國內第一部《趙丹傳》。2008年1月,作者又在團結出版社出版了“將刪去的章節、內容——增補了進來,還了《趙丹傳》的本來面目,這或許是本書的又一‘增值’所在”的32萬字增訂本《趙丹傳》。
我們有理由相信,以下引用《趙丹傳》的文字均出自黃宗英本人口述。
趙丹還十分清楚地記得,就在《海魂》攝制期間,毛澤東主席來到了上海。
趙丹與黃宗英應邀前往中蘇友好大廈,和上海科教、文藝、工商界知名人士一起,接受毛主席的接見。那是1957年7月7日,正值全黨“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之際。
毛主席來到了電影工作者代表中間,緊挨趙丹、黃宗英坐了下來,旁邊有沈浮、黃晨、鄭君里、應云衛等。毛主席和大家親切交談。他說:我相信,我們中國人多數是好人,我們中華民族是好民族。我希望造成這么一種局面,就是又集中統一,又生動活潑;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應當提倡講話,應當是生動活潑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評意見的,言者無畏,不管你怎么尖銳,怎么痛罵一頓,沒有罪,不受整,不給你小鞋穿。小鞋子那個東西穿了不舒服……
毛主席又說,學校教育,文學藝術,都屬于意識形態領域,都是上層建筑,都是有階級性。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干部的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這是一個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不成的。愿同志們都加入這個隊伍……
聽了毛主席的這一番話,趙丹的心情難于平靜……趙丹是黨外人士,對黨的整風等事,本來就不聞不問,現在更噤若寒蟬了。不想,毛主席接見了他們,請大家提批評意見,還說是言者無罪,不給穿小鞋。足見毛主席對趙丹及周圍的同志們還是信任的。
上述毛主席和大家的親切交談,字里行間透著歡愉、和諧的氛圍,交談的內容尤其是“言者無畏”、“沒有罪,不受整,不給你小鞋穿”等表述與“毛羅對話”沖突。
《趙丹傳》還描述了另一個場景:
時值盛夏,天氣異常悶熱,黃昏時分,樹上的蟬仍然熱得知知直叫。趙丹剛洗過浴,身上又汗沁沁的了。他搖著扇子,走到陽臺上,見院子里、馬路上,到處是赤身露臂的納涼的男女。他家的書房里卻還亮著燈,宗英正孤燈獨掌,伏案走筆呢。
趙丹搖著扇子,從陽臺走到屋里進了書房,說:“宗英,這么熱的天,你還悶在房里寫什么呢?”
即將分娩的宗英一面直著身子在那里寫,一面說:“今兒毛主席說,日后要轉入和風細雨的黨內整風呢,我寫點斷想。”
趙丹一聽,想到自己還不是個黨員,心里不是滋味,就說:“宗英,你可算加入了工人階級的文學家、藝術家隊伍了,可我呢,還是個李鼎銘(黨外人士)先生。”
“那也一樣可以做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魯迅先生不就是黨外布爾什維克嗎?”
“我也一直這樣想來著,不過,大伙都入了黨,就我在黨外,總不是個事吧。”
“那你就努力唄!”
趙丹笑道:“請夫人多多關照。”
宗英抽手打了他一下。正在這當兒,一個身材豐腴的女子悄然從敞開著的房門走了進來,恰見阿丹與宗英打打鬧鬧,撲哧一聲笑道:“唷,還真熱乎!”
趙丹與宗英被這冷不防的來人嚇了一跳,定神瞧,她穿深色繡花旗袍,一頭烏發披散在腦后,正沖著他倆在甜甜地笑,“周璇,璇子!”趙丹與宗英喜出望外,一齊喊出來。
上述輕松、歡快的場景與《對話》透露的驚恐形成鮮明對照,與《對話》描述的粗暴訓斥的場景——“禁不住怯怯地問阿丹:‘沒聽到批判羅老的提問嗎?’“阿丹神色嚴厲地“劃”我一記:‘儂笨伐?!格事體攤出來啥影響?’”——格格不入。
此外,倪振亮一生從未見過周璇,自然無從知曉周璇與趙丹、黃宗英夫婦住在同一幢樓、同一層樓且相鄰而居,若非黃宗英親口向倪振良講述,后者不可能寫得如此生動、傳神。
五、《對話》指認的那個“右下角一”不是羅稷南
羅稷南是“毛羅對話”的重要人物。《南方周末》在刊載《對話》時,配發了當年《光明日報》登載的照片和黃宗英改寫的文字說明。由黃宗英改寫的文字說明是:“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與上海文藝界人士座談。毛主席身后左一為黃宗英,左二為趙丹,左四為應云衛,照片右下角一為羅稷南。原刊1957年7月11日《光明日報》。侯波攝。”
黃宗英選這幅照片并改寫文字說明的目的是告訴讀者自己當時所處的“位置”,也就是黃宗英本人理直氣壯宣稱的那樣:“那我就要拿出證據,證明我所處的位置確實能夠聽到、聽清楚毛羅之間的這段對話。”然而,多年來經人們仔細辨認,黃宗英指證的這個“照片右下角一”的人并不是羅稷南,而是復旦大學經濟系教授漆琪生。這個事實是曾與漆教授長期朝夕相處的學生鄧偉志辨認出來的。
2011年9月28日,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行的以“歷史記憶與城市精神”為題的敬老崇文論壇上,著名社會學家、十屆全國政協常委鄧偉志做了題為《真實是回憶錄的生命》的演講。在講到回憶錄在史實上為什么會產生說法不一的問題時,鄧偉志把這種現象分為記憶錯誤、隔代誤傳、代筆誤聽和以訛傳訛四種類型,在分析“以訛傳訛”類型時說:
親歷者所歷、親聞者所聞、目睹者所睹,應當是真實的,但實際上也未必都是準確的。因為,人一般說只能是立于一個方位。一個方位不等于全方位。不是全方位就容易有局限性、片面性。前些日子盛傳毛澤東講魯迅在今天會坐班房的說法。有位當事人硬是講,毛澤東是對坐在當事人斜對面的羅稷南講的。可是拿照片一查,坐在當事人斜對面的不是身材高大微胖的羅稷南,而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經濟學家。從這位經濟學家的性格和專業追求上分析,他是不會提這類同專業相關系數比較小的問題的。看錯人,聽錯話,只能說明那當事人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再說,參與了的更不等于就是充分理解了的。對不理解的人和事、言與行完全可能做出不那么準確的描述。至于道聽途說的,更會演化為“眼睛一眨,老母雞變鴨”。
作者:秋石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號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