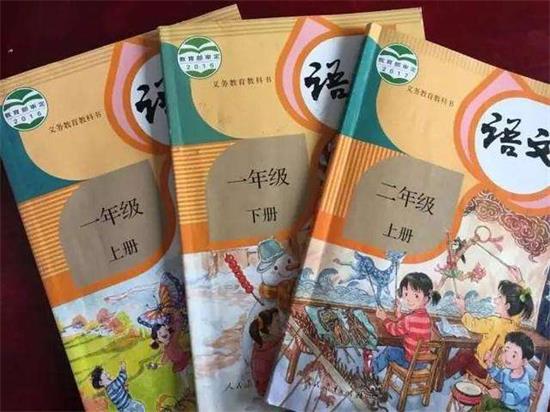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24日-星期四
編者按: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就是把一切財富貨幣化,為的就是投資的便利,因此,資本的運動方才表現為“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而它的基礎就是債務關系的永不斷裂。
——韓毓海
自斯密以來,經濟學家們一般認為:貨幣不過是交換的產物,先有交換,后有貨幣,隨著交換的擴大,或者說為了使交換更有效率,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方才“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有趣的是,當沒有辦法解釋一個事物及其發生的時候,經濟學家們往往就乞靈于“自然而然”,因此,他們的這種“自然而然”總是很神秘的。
關于分工與交換,以及作為“交換中介”的一般等價物的產生,斯密這樣說:“例如,在一個狩獵或者游牧部落里,一個人比其他人更擅長制造弓箭。他經常用弓箭和族人交換家畜或者野味,最終他發現,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食物,比他自己親自捕獵到的還要多。因此,從自身利益出發,他開始把制造弓箭作為主業,從而成為一名軍械師。另一個人則因擅長建造小草房或可移動的房屋而被鄰居邀請幫忙建屋,同樣用家畜和野味作為報酬,最后他也發現以此為業對自己更為有利,從而成為了一個房屋建筑師。依此類推,第三個人成為硝皮者或者制革者,皮革是原始社會主要的服裝原材料。由此,可以用自己的剩余勞動產品交換他人的剩余勞動產品的可能性,激勵了每一個人專事于一種勞作,并且激發了他們有助于其事業發展的天賦才能。”
這種典型的“經濟學家講故事的方式”聽起來似乎挺不錯的,但是包括斯密在內的經濟學家們卻從來就沒有告訴過我們:這樣的“狩獵或者游牧部落”究竟在何時、何地真正存在過。而人類學家告訴我們的卻是完全相反的事實:格雷伯和波蘭尼反復研究了世界各地的狩獵和游牧部落,結果發現:在那里普遍存在的絕不是交換關系,而是一種人類學圈子里通稱的“輻輳—再分配”的社會關系,即所有人都把自己的勞動產品匯集起來(如同輻輳一樣),然后再由酋長或者部落長老進行再分配。
馬克思的觀點則更獨特,在他看來,沒有分工和交換,也可以有貨幣。把財富“貨幣化”最初的起因不過就是為了攜帶方便,這個道理其實非常簡單,一方面,強盜和小偷最希望把不義之財趕快變成貨幣,“貨幣化”起初與銷贓同源(想一想搶劫了圓明園的英法聯軍,為什么立即就在廢墟上拍賣他們的戰利品),另一方面,幾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有把自己的所有財產變成首飾戴在身上的習俗,而這就是為了在不斷的遷徙中攜帶方便。因此,與其說貨幣起源于交換,還不如說將財富貨幣化是為了財富便于“移動”。
馬克思別具一格地指出:
游牧民族最先發展了貨幣形式,因為他們的一切財產都具有可以移動的,因而是可以直接讓渡的形式,又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使他們經常和別的共同體接觸,因而引起產品交換。6
貨幣不過是在商品交換中充當一般等價物的東西,是類似于語言中的介詞那種“本身沒有意義卻能使意義產生”的東西—這是伊斯蘭學者安薩里的斷見,是從在中世紀占支配地位的伊斯蘭商業貿易活動中總結出來的學問。但是,采取同樣主張的斯密卻生活在與安薩里完全不同的時代,即工業革命的前夜。斯密代表的也并不是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商人階級,而是代表歐洲工匠和行會這個階級,所以斯密對安薩里的斷見做了一個小小的修正。斯密說,貨幣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商品交換”的中介,而是“勞動產品交換”的中介,即手工業品和農產品交換的中介。這一修正是很重要的,因為斯密對奢侈品、對一切非勞動產品,即那些不屬于小生產者和手工業者的東西均嗤之以鼻,這個修正表明,在貨幣理論方面,斯密確實是比安薩里更進了一步。
那么什么是貨幣呢?亞當·斯密是在勞動產品交換或者勞動交換,即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他的貨幣理論的。因此,他認為,貨幣是“衡量生產商品所耗費的時間”的尺度:
對擁有某商品但不用于自己消費,而是用以交換其他商品的人而言,該商品的價值等于交換或者支配的勞動數量。因此,勞動是所有商品可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7
而這也就是對“勞動價值論”的完整闡述。
所謂商品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特別是“勞動價值論”,這些都是亞當·斯密提出來的,而不是馬克思的發明。長期以來,人們把這當作馬克思的發明則是完全錯誤的,這與其說是往馬克思臉上貼金,還不如說是在佛頭上著糞。
馬克思的創舉恰恰是從質疑亞當·斯密、質疑“勞動價值論”出發的,也就是說,馬克思質疑的恰恰是這樣的看法:貨幣是衡量社會勞動數量的尺度。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的出發點就是對勞動價值論的批判和質疑,并在這種批判與質疑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以貨幣為完成形式的價值形態”論。如果覺得馬克思的這個說法太拗口,我們不妨也做一次“恩格斯”,把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的出發點說成是“資本價值論”。
近代西方意義上的貨幣絕不是交換的產物,因為這種貨幣是好戰政府和金融家聯合的造物,它是資本統治和國家權威的象征。這種貨幣的誕生劃出了一個時代。
按照羅馬法和日耳曼法律,無論何種性質的政府,其最根本的作用均在于確保其屬地范圍內的“債務”可以得到公平處理,在這個意義上,政府既是最大的債務人,也是全體屬民彼此之間債務的信用擔保人。政府正是通過稅收創造了貨幣,而所謂稅收不過意味著屬民通過繳納自己的物品償還政府的保護和服務,并以此確認屬民與政府之間的債務關系,而這正是西方政治的本質。
馬克思說,貨幣并不是一個(交換)中介,而是“權威”的隱喻。所以他才說貨幣是“象形文字”,具體說,貨幣是政府債務的隱喻,貨幣在物品身上打下印戳,一件物品只有取得了貨幣的形式,只有打上這個印戳,它才能成為“商品”。而這個印戳、這個“象形文字”絕不是別的什么,而就是建立在政府債務基礎上的銀行券。我們只要隨便拿一張紙幣來看看就可以對此一目了然。
政府的債務創造了貨幣,貨幣創造了“商品”,而不是“商品”創造了貨幣。
什么是現代意義上或者西方意義上的貨幣?它并不是“交換的中介”,簡而言之,這種貨幣就是一張借條、一張欠條。
如果我們更為嚴格地把貨幣理解為一個記賬工具,那么它如同時間和空間一樣,就僅僅是一個抽象的衡量單位,像1小時、1分鐘、1立方米一樣,是我們無法觸摸的極其抽象的東西,那么,這樣一個計量標準衡量的對象是什么呢?
簡而言之,這就是債務,而不是勞動。
那么貨幣衡量的是哪一種債務呢?貨幣衡量的就是政府的債務。
現代意義上的貨幣都是依托于政府的債務而發行的,現代貨幣經濟就是政府國債的產物。
貨幣、貨幣經濟和市場經濟都是在政府債務的基礎上被創造出來的,貨幣的價值絕不是生產某一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的度量,而是對發行者信用和接受者信心的度量,因為它反映的是政府與銀行之間的信用關系,進一步說,反映的是銀行與民眾之間的信用關系,當然,這種關系的實質就是債務。而這一問題的實質早已經被阿克頓勛爵一語道破,他說:“當前的問題不在于人民與政府的關系,而在于人民與銀行的關系。英格蘭銀行已經由銀行家的銀行變成了政府的政府,英格蘭銀行作為絕對的權力,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大衛·格雷伯曾經這樣精辟地闡釋了第一種世界紙幣通貨(英鎊)的產生:
只有在亨利不償還債務的時間段內,欠條才能充當貨幣使用。事實上,這正是最初建立英格蘭銀行(第一家成功經營的現代化中央銀行)的邏輯基礎。1694年,一個由英格蘭銀行家組成的財團,借給國王一筆120萬英鎊的貸款。作為回報,該財團在紙幣的發行上獲得了王室批準的壟斷權。這就意味著對于王國中任何希望向財團借錢的居民,或者希望把自己的錢存入銀行的居民,財團都有權用國王的欠條來進行支付。這實際上使得新的王室債務流通起來,或者叫作“貨幣化”。對于銀行家來說,這件事意義非凡(最初的那筆貸款,每一年他們都能向國王收取8%的利息;同樣,他們也可以向所有借錢的客戶按8%的利率收取利息),但是只有在國王尚未償還最初的那筆借款的情況下,整個體系才能存續。直到今天,王室仍然沒有償還那筆貸款;它不能被還清。一旦那筆貸款被還清,英國的整個貨幣體系將不復存在。8
正是通過把王室的債務貨幣化,銀行才發展起來,正是依托政府的國債制度,貨幣(銀行券)經濟才壯大起來。
在英國,銀行以王室的欠條為基礎,壟斷了紙幣發行權,并使自己發行的銀行券成為社會交換的唯一尺度,從此,一切存貸行為都必須以接受銀行券為前提,即以接受國王的欠條為前提。從表面上看,這里的好處是,在需要現金時,你能夠隨時在銀行兌取,以至于亞當·斯密也這樣說:“負債于銀行,比手里有多少錢才能辦多少事要好得多。”實際上,在這樣的社會形態里,每個人都成為廣義的負債者,即銀行的負債者。這樣一來,一個以銀行券為交往尺度的商品社會,最終把一切社會關系都轉變為存貸者與銀行之間的關系—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的關系。所以,這個社會的基本社會關系既不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關系,也不是這個商品與那個商品之間的物的關系(如果是那樣,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拜物教”),而是彼此孤立的社會生產者之間“互相預付”的關系,以及銀行與國家之間的債務關系。
什么是資本?斯密說:資本就是能夠帶來預期收入的那一部分儲備,預期收入的實現必須通過商品生產與交換。
而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就是把一切財富貨幣化,為的就是投資的便利,因此,資本的運動方才表現為“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而它的基礎就是債務關系的永不斷裂。
資本是怎樣積累的呢?真實的歷史告訴我們:資本絕不是在抽象的市場競爭中積累的,因為從“世界市場”誕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以民族國家為本位的。世界市場競爭首先表現為國家間圍繞著貨幣化的財富(資本)而進行的殘酷競爭。譚其驤先生在1981年曾發表過一個重要的學術講話,這就是《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其中他說道:“中國”這個說法是在鴉片戰爭之后隨著賠款制度而流行起來的,因為此前我們一般不自稱“中國”,而是自稱“天下”,為什么在鴉片戰爭之后才流行用“中國”這個說法呢?一是要清楚地界定賠款人的責任,在《南京條約》的賠款人那一欄里,你總不能寫“天下”吧?二是要界定我們自己的權利在哪里,以維護我們的權利。三是認識到世界是列國競爭的市場,我們只是其中的一員。
16世紀以來,西方列強首先通過暴力支配下的各種不平等條約,確立起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的債務關系。如果那些國家敢于廢除這種債務關系,就立即對其進行無情的軍事打擊和經濟封鎖(即將其從國際關系中分離出來),而這就是國際關系的經濟學本質。同時,資本積累又是通過把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變成無產階級來實現的,雇傭合同的實質也就是工人向資本家借貸的契約,而這里的信用抵押物就是工人自己—“他們的勞動力本身”。
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均是歐洲各國之間債務關系破裂的結果。債務的懲罰不可避免地導致戰爭,這是由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根本缺陷決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比較深刻地汲取了這個歷史教訓,轉而以馬歇爾計劃援助戰敗國,而不是通過債務和賠款勒索它們,美國以馬歇爾計劃代替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似乎是“以德報怨”。這樣一來,美國的勝利也就由單純的軍事勝利轉變為道德和道義上的勝利,而美國的信用和信譽也因其在戰后歐洲重建中所承擔的“道德責任”而扶搖直上。
基于歐洲經濟重建和冷戰的需要,西方世界需要一個新的貨幣金融體系向歐洲的工業、貿易之復興注資,需要用這個新的信用體系代替舊的金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誕生意味著美元雖然尚與黃金相聯(每盎司35美元),但更重要的是美元的實質、美元的真正基礎是美國道德責任和美國信用的“貨幣化”,正是后一點劃出了美元本位與黃金本位之間的真正區別。
因此,1971年8月15日,當理查德·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的時候,這并不意味著美元體系崩潰的開始,因為美元的力量從根本上說并不來自黃金的支持,而是來自美國信用和道德責任的支持。由于尼克松劃時代地改善了與中國的關系,并實現了從越南的體面撤軍,這反而極大地改善了美國的形象,并順勢把四處伸手的蘇聯逼向了道德破產的窘境,而且隨之而來的中國改革開放更使美元獲得了巨大的海外市場支持。這都是因為尼克松和美國的領導班子深刻認識到:世界對美元的信心比黃金更重要,而中國的支持比黃金的支持更重要。實際上,1971年以來,美元并沒有因為與黃金脫鉤而走弱,恰恰相反,隨著蘇聯的崩潰,美國的國際信用達到了高峰,美元的霸權地位也隨之走向了高潮。
資本不過就是道德化的貨幣。今天,馬克思這一簡明扼要的論斷非但沒有隨著美國淪為世界上最大的負債國而有絲毫的改變,恰恰相反,其真理光芒在當代世界更加熠熠生輝。實際上,在我們的時代,只要美國不公開宣布放棄自己的債務承諾,而是信誓旦旦地堅稱美國一定會償還自己的債務,那么就沒有誰真的敢讓美國償還債務,因為那樣做等于摧毀國際信用制度,除將招致美國無情的暴力懲罰外,自己還必將背上敲詐勒索的罪名,扮演令人不齒的“夏洛克”形象。而只要債務鏈條永不斷裂,美國定期付出的不過是利息而已,隨著美元的貶值,這種利息將日益微不足道。
在今天的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中國擁有強大的經濟和貿易能力,即使連美國也不懷疑這一點,但是很少有人相信中國擁有把自己的道德責任和信用轉化為貨幣的能力—這里的貨幣也就是指像美元那樣的世界貨幣。恰恰相反,中國最富有的精英階層往往是最聲名狼藉的“土豪”,他們與中國歷史上的商人階級一樣,具有把金錢轉化為權力的能力,但他們也與中國歷史上的商人階級一樣,從來沒有把道德信用轉化為金錢的能力。于是,在世界輿論界,中國“土豪”的暴富與其道德上的破產似乎是一個比翼齊飛的進程,而美國和日本正對此樂觀其成。
無論今天的中國如何宣傳“中國道路”、“中國震撼”,中國道路也不可能建立在GDP總量之上。除非中國人有能力像馬克思那樣,擁有世界視野,把五千年中華文明、偉大的中國革命與建設和改革的經驗上升為一個理論整體,以此申訴中國經濟發展的合法性。否則,所謂“中國道路”在西方人眼里依舊還是另類,富起來的中國人無非是些“土豪劣紳”而已。
在馬克思看來,信用能夠轉化為貨幣,這個過程是自然的,但是經濟與貿易水平卻不能自然而然地轉化為信用,這同樣是自然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盧梭的名言就是對的:“金錢固然可以買到一切,但卻不能培養風尚和公民。”而馬克思的話則揭示了這樣的真理:資本主義的秘密就在于把道德轉化成了貨幣。而與馬克思相反,斯密卻總是假定人在自然狀態下會如何,這就是經濟學家講故事的一般方式,而這種扯淡的方式也是馬克思所批評的“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因為經濟學家們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們,這種“自然狀態”究竟是在何時、何地真實地存在過。
盧梭的名言是: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而不在枷鎖中。實際上,人一生下來就不在自然狀態下,而是困在特定的制度中、生活在特定的制度條件下。馬克思說,在自然狀態下,每個人都可以說他自己的語言、發明他自己的語言,這起碼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但事實是,現實中每個人都只能學說某種語言,都必須遵守既定的語言制度和規范,正如人們今天總是認為英語是“最自然規范的語言”一樣。
這是馬克思超越一切經濟學家,特別是亞當·斯密傳統的根本點。馬克思是站在斯密的終點上進行思考的。
來源:《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克思》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