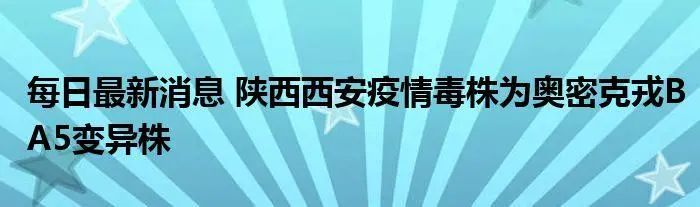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21日-星期一

一、產權改革和股份制改造。村民成為股民,成員權變為股權,這些正在改變著村社成員權的意義,使得成員間的關系從資源共享、勞動聯合轉型為資本聯合,也使得成員和村莊的關系聚焦于分紅。這將深刻影響鄉村共同體的建設。
二、隨著新時期基層社會治理的推進,村莊對集體經濟有客觀的需求,鄉村振興需要以盤活集體為起點,否則村莊既難以擔負已經貨幣化的行政成本,也無法協調、整合村民手中的閑置資源,更難以激發內生性的發展。
三、農業生產力發展依賴資源的整體性,土地集體所有制恰恰契合了農業生產力的這一特征,能夠產生制度性紅利和系統性紅利。在實踐中出色的往往是“黨政社群企”多元一體的村莊,這樣的多元一體性有利于村莊平衡內生性和外生性發展。
四、貴州省畢節市鄉鎮黨委統領合作社的實踐開辟了一條可推廣的鄉村再組織化道路。畢節實踐突破了村社集體經濟的局限性,走向村與村的合作,鄉與村的聯合。在此基礎上,有望進一步形成縣-鄉-村三級聯辦合作經濟組織的格局,以國有組織作平臺,建立新型縣域經濟。


綜述還指出“畢節實踐突破了村社集體經濟的局限性”,這句話看似語不驚人,卻是一個不容易得到的歷史性突破。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農村工作受全局關注的重點主要在村,如大寨村、華西村、小崗村、南街村、滕頭村、賈家莊等,新時代廣受關注的貴州塘約村黨支部領辦“村社一體”的合作社,也是村。然而即使重建了黨組織領辦的村集體合作社,還存在“一個村的單打獨斗問題”。畢節實踐“突破了村社集體經濟的局限性”,這是新時代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突破性實踐。把目光和思索聚焦到這一突破的進展,就更清晰地看到了畢節實踐的意義。
以下是綜述里介紹王宏甲講座的概述:
國家一級作家王宏甲講述了貴州省畢節市的鄉鎮黨委統領合作社的實踐。鄉鎮黨委統領合作社,統領的是村一級的合作社,與常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區別在于——黨委統領合作社應當是所有村民的家,沒有權利拒絕任何一個村民參加。農民專業合作社有其進步性,但多是強強聯合的產物,沒有吸納貧困戶,貧困戶最后仍在單干,而辦集體經濟,首先是要把所有貧困戶吸收進來,以強弱聯合凝聚鄉村社會。而不管哪一級集體經濟,都要黨的領導。
在貴州省貧困人口最多的畢節市,如果不是依靠發展集體經濟把貧困農民組織起來,那么其脫貧攻堅任務將非常艱巨。從2017年開始,畢節市首輪選擇350個村黨支部,試點學習安順的塘約經驗,兩年后形成本土經驗,結果表明,組織起來比沒有組織好。不能忽視“組織起來”的力量,組織起來就有社會分工,就有社會進步。其中,集體合作社的1.0版本是成立村集體合作社,解決農戶單打獨斗問題,但成立村級合作社還存在一個村的單打獨斗問題。
于是發展出2.0版本的鄉鎮黨委統領合作社,解決村莊單打獨斗的問題。其中畢節七星關鴨池鎮最有示范意義,其做法是:提出鄉村振興首先是產業振興,為了避免村莊之間同質化經營導致惡性競爭,由鎮一級的合作總社領導26個村合作社,在鎮合作總社設立五個專班,分別是產業選擇、人員培訓、資金籌措、經營管理、市場開發。四個字概括為“兩統一干”,鄉鎮統前后兩端,村合作社干中間。通過合作總社把鄉村聯合起來,實現鄉和村的有機結合,進而面對市場,做綠色發展的新型集體經濟。集體經濟具備信任優勢,如果存在產品滯銷問題,就是打了鄉鎮黨委書記的臉。由此建立一個整體有機的運作模式。
下一步3.0版本則是要解決鄉鎮單打獨斗的問題,發展縣、鄉、村聯辦的集體經濟,形成縣、鄉、村三級合作的經濟組織格局,以國有組織作平臺,建立新型縣域經濟。以前倡導“龍頭企業+”的模式,但是企業是逐利的,將農民的勞動算作成本。農民的勞動要創造價值,就不能按照按資分配的模式,要變成按勞分配為主、按資分配為輔,讓農民當家作主。集體經濟真正的龍頭是黨委,可靠的同盟軍是國有經濟,因為國有經濟不像有些外來企業帶著盈利、剝削的目的而來,隨時又會跑路。因此,王宏甲倡議推廣縣域國有經濟。

在這樣一個900多萬人口的多民族的深度貧困地區,能走出這樣一條路,對各地都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畢節沒有否定原來的農村改革,而是在此基礎上靠黨的領導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走出一條統分結合、重建集體經濟和鄉村共同體的道路。
“分”的改革對擺脫貧困、實現鄉村振興發揮了積極的但也是有限的作用,所導致的農民分散化使他們無法為長遠的、集體的利益共同奮斗。要實現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必須要加強“統”,把農民按照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總目標組織起來。領導農民進行這樣的“統”,實行統分結合,推進鄉村振興,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工作中的歷史使命。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呂新雨主張在發展轉型的脈絡里,理解塘約道路和畢節實踐的意義,分析了為什么這些實踐需要黨的領導。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在這個轉換過程中,中國需要一個再組織化過程,其中有個問題需要重新討論,即以什么原則進行再組織化?
對鄉村來說,第一種是資本下鄉塑造鄉村,外來資本如龍頭企業也是一種組織力量,但有利有弊。
第二種方式是精準扶貧,從城市輸入第一書記(尤其是東部對西部)使鄉村發展獲得市場空間和資源,但并不長久。
第三種方式是黨組織的資源直接注入鄉村。從塘約道路、煙臺實踐到畢節實踐,黨的組織建設的延伸成為鄉村再組織的資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為鄉村提供了一種非市場的資源,農民不需要為黨組織的組織成本付費,這個組織是將內生型發展和外生型發展結合起來。在精準扶貧的實踐中,有很多基層組織為了應對自上而下的政治壓力,使得村莊內生的組織資源不足或者組織動力不夠,從而整個村莊缺乏內生性發展動力,不能夠真正解決貧困問題,這也是為什么大家擔心當扶貧資源撤出,鄉村會產生大規模的返貧。接下來鄉村振興要建立長效機制,其中核心的一點是組織資源的再生和可持續。
從外循環到內循環再到內外雙循環,鄉村的角色不可或缺,農工商在地化和東西部協作的意義超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法則。中國的精準扶貧是社區型的,所有的“社區成員”必須進入到精準扶貧乃至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尤其是鰥寡孤獨也能夠進入到勞動創造財富、勞動創造價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造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尋找鄉村振興的破局之道,再造一個可持續的、綠色發展的、所有人都從中獲得勞動收入的鄉村振興體系,這個體系是能夠和內外循環聯動的體系。這種新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落腳點就是新型集體經濟。
清華大學教授嚴海蓉把中國集體經濟的制度經驗放置在國際上關于“公共”(或者叫“公地”)的理論探討上,認為中國經驗不僅對我們探索中國鄉村振興之路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也能對世界的普遍問題起到借鑒性的作用。
1968年,美國生態學家G. 哈丁發表題為“公地的悲劇”的文章,前瞻性地在全球范疇提出了“公地”的前途問題,把“公地”的命題延展到世界人口問題、公共環境、公共資源(如大氣、海洋)。哈丁的“公地的悲劇”與亞當·斯密關于“看不見的手”的命題相反。亞當·斯密認為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能夠達成一致性。約一百年后,哈丁的命題恰恰指出了個體利益、個人自由與社會公共利益的矛盾性,如果放任個體利益和自由,這些“公地”都會面臨無法避免的悲劇。美國政治經濟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在世界各地的公地維護中發現了多種合作制度實踐。這些實踐表明,公地的悲劇是組織化缺位的悲劇,克服公地的悲劇,關鍵不是取消公地,而在于通過組織化建立聯通個體和共同體利益的長效關系。
從廣義的農業資源來說(包括農牧漁),中國可能擁有世界上最大量的“公地”,中國農業“公地”的管理有著豐富的經驗和教訓。總結中國實踐經驗,既關乎中國農業資源的未來、關乎鄉村振興的前途,也對世界公地的管理有著重要的意義,將會是中國對世界的重要貢獻。(中國可能擁有世界上最大量的“公地”,意為中國國有和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編發】轉編自“宏甲文章”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昆侖策網】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現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絡時代發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王宏甲|河南葉縣:新時代全縣推進黨組織領辦新型集體經濟的典型 ——兼論新型集體經濟的特征、現實需要和遠大前途
2022-03-15?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