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從理論到政策實踐:解決當前經(jīng)濟問題的一把鑰匙,兼談深化改革的途徑》系列文章之二。本系列文章之一鏈接為:《不能把“新的更高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神秘化、遙遠化》】
【系列摘要】《資本論》對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方式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三者關(guān)系的論述,得到了歷史的檢驗。在市場經(jīng)濟中產(chǎn)生的合作生產(chǎn)方式,與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始終同在,適應“新的更高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生產(chǎn)力所決定的生產(chǎn)方式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獨立性,構(gòu)成“私有經(jīng)濟優(yōu)越于公有經(jīng)濟”假象。馬恩對合作生產(chǎn)的論述有助于我國公有經(jīng)濟存量的主體回歸。中國工人階級在市場經(jīng)濟中的一系列生產(chǎn)方式創(chuàng)新,需要非私有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加以鞏固,它反映了企業(yè)發(fā)展的內(nèi)在規(guī)律,又有解決我國宏觀經(jīng)濟堵點的戰(zhàn)略意義。發(fā)展合作生產(chǎn),要尊重企業(yè)的市場主體和員工勞動主體,實質(zhì)上是尊重商品生產(chǎn)中活勞動的主體地位,是解決企業(yè)的發(fā)展瓶頸和發(fā)展戰(zhàn)略的內(nèi)在規(guī)律體現(xiàn)。它以市場為檢驗。
【本文摘要】生產(chǎn)力是通過生產(chǎn)方式而釋放出來的;生產(chǎn)力的活躍性決定了生產(chǎn)方式的多樣性、靈活性、協(xié)調(diào)性;生產(chǎn)方式中人與人關(guān)系的變化,勞動者和勞動資料及勞動成果的聯(lián)系緊密程度,有時會超過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的作用;生產(chǎn)方式需要適當?shù)纳a(chǎn)關(guān)系來鞏固、維護,生產(chǎn)關(guān)系對生產(chǎn)方式有深刻的、長久的作用力;生產(chǎn)方式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各自作用有一定的獨立性。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只能是自發(fā)的市場經(jīng)濟的對立物,決定了經(jīng)濟為本體,政治是靈魂。馬克思“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方式-生產(chǎn)關(guān)系”原理經(jīng)過了一百多年實踐的證實,特別是改革開放實踐的證實。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產(chǎn)方式一樣,把社會生產(chǎn)力及其發(fā)展形式的一定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jié)果和產(chǎn)物,并且是新的生產(chǎn)方式由以產(chǎn)生的現(xiàn)成基礎(chǔ);同這種獨特的歷史規(guī)定的生產(chǎn)方式相適應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chǎn)中所處的各種關(guān)系——具有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zhì)。”[1]馬克思在此提出,新的生產(chǎn)方式以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為基礎(chǔ),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決定了生產(chǎn)方式的獨特,與之相適應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具有歷史的暫時性質(zhì)。有經(jīng)典學術(shù)文章沖破傳統(tǒng)教科書觀點指出:“理解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關(guān)鍵,是正確理解馬克思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方式-生產(chǎn)關(guān)系原理。[2]觀察經(jīng)濟歷史,也可以發(fā)現(xiàn)隨著生產(chǎn)資料的創(chuàng)新,隨著生產(chǎn)社會化程度的提高,提高效率有諸多因素,而貫穿于生產(chǎn)、消費、分配、流通環(huán)節(jié),主動勞動還是被動勞動的生產(chǎn)方式,是最根本的因素,同時,為了適應這一點,也要求生產(chǎn)關(guān)系相應不斷變革。這個特點無論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經(jīng)濟,還是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jīng)濟或者市場經(jīng)濟中,都是十分鮮明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認識到了這一點。美國在不影響壟斷寡頭利益的前提下,數(shù)以千萬的員工參與了員工持股;而社會主義做了不同性質(zhì)的變革。列寧在十月革命4周年之際,最先提出:“要借助于偉大革命所產(chǎn)生的熱情,靠個人利益,靠同個人利益的結(jié)合,靠經(jīng)濟核算。”[3]毛澤東通過總結(jié)鞍鋼憲法,對公有制條件下的生產(chǎn)方式的組織建立,對捍衛(wèi)活勞動的主體性有著更為深入的認識和探索。這些探索無一不反映在生產(chǎn)方式上。縱觀我國生產(chǎn)資源由計劃和市場配置探索的歷史,筆者理解的生產(chǎn)力決定生產(chǎn)關(guān)系、生產(chǎn)關(guān)系反作用于生產(chǎn)力的作用形式可以歸納為以下:1,生產(chǎn)力是通過生產(chǎn)方式而釋放出來的。無論是建國初期,以人力、畜力為主的集體經(jīng)濟力量興修水利工程,農(nóng)田基本建設,還是今天以客戶體驗引導的日新月異的電子科技創(chuàng)新。2,生產(chǎn)力的活躍性決定了生產(chǎn)方式的多樣性、靈活性、協(xié)調(diào)性。科技和管理的創(chuàng)新提升著勞動者統(tǒng)御、運用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復雜程度,首先通過生產(chǎn)方式改進而表現(xiàn)出來。例如從人力、畜力的農(nóng)村能源到集體經(jīng)濟時期的小水電小火電,再到今天特高壓大電網(wǎng)條件下的農(nóng)村電氣化和衛(wèi)星信息傳輸條件,決定了不同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3,生產(chǎn)方式中人與人關(guān)系的變化,勞動者和勞動資料及勞動成果的聯(lián)系緊密程度,有時會超過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的作用。例如在公有制企業(yè)中,官僚主義令人際關(guān)系等級化,損害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勞動與成果的不能緊密聯(lián)系,影響生產(chǎn)效率;在私企中,除了體現(xiàn)資本本能996式的強制性勞動,也有設法使勞動與成果緊密聯(lián)系的生產(chǎn)方式優(yōu)化,產(chǎn)生較高的生產(chǎn)率,在危機和競爭陰影下,代表資本利益最大化的經(jīng)營管理者擅長這一點。這種生產(chǎn)方式的優(yōu)化,和分配、消費領(lǐng)域的福利化同步,是現(xiàn)代發(fā)達資本主義為巧取并壟斷剩余價值,對工人階級采取的有組織的容忍和妥協(xié)政策,也是社會民主黨及社會主義陣營內(nèi)部產(chǎn)生修正主義,荒謬否定剩余價值論的經(jīng)濟基礎(chǔ)憑借。4,生產(chǎn)方式需要適當?shù)纳a(chǎn)關(guān)系來鞏固、維護,生產(chǎn)關(guān)系對生產(chǎn)方式有深刻的、長久的作用力。由手工勞動、個體勞動組成的聯(lián)合勞動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義時,在一定的階段內(nèi),小部分生產(chǎn)資料的私有或個體、家庭經(jīng)營的生產(chǎn)方式,有助于釋放生產(chǎn)力,這是私有經(jīng)濟作為補充的存在理由,毛澤東同志直至晚年也在維護不影響集體經(jīng)濟主體的自留地制度[4]。而類似蓋茨車庫創(chuàng)業(yè)階段,以計算機為主要生產(chǎn)資料時,最適合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是合伙共享而非雇傭制。互聯(lián)網(wǎng)經(jīng)濟時期,大數(shù)據(jù)的社會化不允許數(shù)據(jù)資源私有壟斷,就必須進行公有制改造。在企業(yè)生產(chǎn)方式數(shù)據(jù)化轉(zhuǎn)型中,在資本投資回報制約下,“打工人”的流動率和創(chuàng)新投入不足逐漸成為企業(yè)發(fā)展瓶頸時,也必須非私有改造,才能培育企業(yè)后勁。在房地產(chǎn)投資狂潮裹挾虹吸實體經(jīng)濟,金融壟斷出現(xiàn)時,投資并不必然推動技術(shù)進步,成為經(jīng)濟減速直至停滯的根本原因,實行國有重組改造,才能維護和鞏固高效的宏觀物質(zhì)資料生產(chǎn)方式。5,生產(chǎn)方式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各自作用有一定的獨立性。企業(yè)所有制變動后,人際關(guān)系發(fā)生質(zhì)變,對生產(chǎn)方式的作用是根本的,但不是立竿見影的。還要取決于能否鞏固或建立持久的適應生產(chǎn)力釋放的生產(chǎn)方式。在《經(jīng)濟學手稿1857年-1858年》中,馬克思對新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產(chǎn)生做了清晰的敘述,其辯證唯物史觀的思維方式,對于今天我們摸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有深刻指導意義。馬克思指出,“必須考慮到,新的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不是從無中發(fā)展起來的,也不是從空中,又不是從自己產(chǎn)生自己的那種觀念的母胎中發(fā)展起來的,而是在現(xiàn)有的生產(chǎn)發(fā)展過程內(nèi)部和流傳下來的、傳統(tǒng)的所有制關(guān)系內(nèi)部,并且與它們相對立而發(fā)展起來的”。[5]馬克思的這一段論述也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只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對立物[6]。它不可能從資本主義“母胎中發(fā)展起來”,例如亦步亦趨西方,對內(nèi)復制過剩與需求不足,產(chǎn)生大規(guī)模失業(yè),或復制二戰(zhàn)后西方的“金融爆炸”打開的暴利驅(qū)動的不動產(chǎn)和建筑業(yè)投資,對外復制金融壟斷,爭奪世界市場。而對于俄、中東方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必須與資本主義“相對立而發(fā)展”,唯有這樣,才“可以不經(jīng)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7]我國在發(fā)展商品經(jīng)濟,培育市場主體中,付出了十九大提出的“巨大的代價”,是在容納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商品經(jīng)濟條件下的揚棄,這種對立、揚棄,以經(jīng)濟活動為主要任務,為本體,又以習近平強調(diào)的政治第一為靈魂。這種政治第一,就是毛澤東詮釋的,而不是形而上學理解的、政治分歧者歪曲的、違法的階級斗爭為綱,只有這樣,社會主義才能產(chǎn)生更強大的生命力。從一百多年的實踐看,馬克思的“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方式-生產(chǎn)關(guān)系”原理從三個方面得到了證實。1、馬克思認為,生產(chǎn)資料共同所有的生產(chǎn)方式,作為“新的更高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通過合作生產(chǎn)方式,在馬克思時代就已經(jīng)“自然而然”的產(chǎn)生了。馬克思在評價工人合作工廠時指出:“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zhì)生產(chǎn)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chǎn)形式的一定的發(fā)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chǎn)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chǎn)方式中發(fā)展并形成起來。”[8]但是,在無產(chǎn)階級掌握國家政權(quán)之前,它只有先進的實驗意義。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1886年談到,在保證全社會利益前提下,“在向完全的共產(chǎn)主義經(jīng)濟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guī)模地采用合作生產(chǎn)作為中間環(huán)節(jié),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9]2、無產(chǎn)階級專政國家建立,工農(nóng)階級掌握勞動資料后,極大地解放了生產(chǎn)力,同樣是東方落后農(nóng)業(yè)國的俄國和中國兩國(恩格斯晚年稱中國是“同家庭工業(yè)結(jié)合在一起的過時的農(nóng)業(yè)體系”[10]),在革命和戰(zhàn)后,經(jīng)濟爆發(fā)性增長,在社會平等中,人口、壽命的躍升和工業(yè)化速度在人類歷史上罕見。和建國時期相比,蘇聯(lián)于五十年代,中國于七十年代壽命接近翻番。這一時期,我國公有制的生產(chǎn)方式,主要是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領(lǐng)導和組織方式在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的運用。28年革命實踐積累的黨的領(lǐng)導、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等工作作風,優(yōu)化了公有制生產(chǎn)關(guān)系,共產(chǎn)黨員骨干的奉獻作用,促進了各行各業(yè)勞動創(chuàng)新,這些現(xiàn)象經(jīng)濟學不能解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計劃經(jīng)濟時期的生產(chǎn)方式,鞏固了公有制生產(chǎn)關(guān)系,極大地促進了生產(chǎn)力。同時,由于中國封建農(nóng)業(yè)社會重農(nóng)輕商的自然經(jīng)濟思想影響,商品經(jīng)濟落后。存在著長官意志,包括把重農(nóng)抑商、小生產(chǎn)的絕對平均主義誤為馬克思主義純潔性,以及滋生官僚特權(quán)等原因,不遵守等價交換的價值規(guī)律時有產(chǎn)生,阻礙勞動者和勞動資料、勞動成果更加緊密的機制性聯(lián)系的建立,這些現(xiàn)象局部或階段性存在,違反唯物史觀。這就說明,社會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生產(chǎn)力所決定的生產(chǎn)方式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始終是歷史的和暫時的,對其調(diào)整沒有止境,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的整頓、改革、開放,其宗旨就是完善社會主義。它的歷史途徑是,為了尊重商品生產(chǎn)中的活勞動主體,必須從發(fā)展商品經(jīng)濟入手,承認商品經(jīng)濟等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活躍生產(chǎn)方式,同時抵御商品占有規(guī)律向生產(chǎn)資料占有規(guī)律演化,限制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堅持公有制和自主聯(lián)合勞動為主體的市場經(jīng)濟;必須在斗爭中擴大開放,在備戰(zhàn)中爭取和平。第一代領(lǐng)導人晚年對此做出了對立統(tǒng)一的嚴重警告,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峽谷的中國方式,但是在此后的實踐中,受到實用主義真理觀指導,走入混淆社會主義本質(zhì)和任務的二元論,產(chǎn)生了私有經(jīng)濟存量占優(yōu)的一定程度的經(jīng)濟基礎(chǔ)質(zhì)變。3、蘇聯(lián)修正主義國家解體后,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為了發(fā)展商品經(jīng)濟,解放生產(chǎn)力,從初建勞務市場到培育勞動力市場,包容了勞動力作為特殊商品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接納全要素生產(chǎn)觀,邊緣化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私有經(jīng)濟飛速發(fā)展,直至出現(xiàn)產(chǎn)業(yè)壟斷到金融壟斷,與國家分庭抗禮;國際壟斷資本排斥資本對等流動,單向擴張、滲透等因素,產(chǎn)生了境內(nèi)私有經(jīng)濟存量占優(yōu)的“五六七八九”繁榮。土地集體所有和住房等公有制遺留,令城鄉(xiāng)剩余勞動力降低了再生產(chǎn)成本,支撐了以低廉價格橫掃世界市場式的剩余價值輸送,暫時緩和了進口國階級矛盾,同時,又沖擊西方制造業(yè),加快了美國等西方經(jīng)濟由實向虛,增加了進口國失業(yè)壓力。中國科學院國家健康研究組2013年發(fā)布的《國家健康報告》揭示,美國有52.38%的GDP通過霸權(quán)獲得,而中國損失的霸權(quán)紅利占GDP比例達51.45%[12]。從長遠看,順應了進口國資本虛擬化和寄生性,加劇了其社會矛盾。剩余價值向外輸送積累了外匯儲備,也使境內(nèi)貨幣天量增發(fā),助長市場盲目性,刺激了制造業(yè)產(chǎn)能和房地產(chǎn)過剩,而庸俗經(jīng)濟學GDP指標的采用[11],始終混淆著物質(zhì)財富和泡沫,所發(fā)展的巨大生產(chǎn)力,被無時不刻地導入到社會兩極分化中去,2019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chǎn)總值達到一萬美元,但六億人月入不足千元。對此,黨內(nèi)產(chǎn)生過盲目性,例如2007年即宣布“絕對貧困現(xiàn)象基本消除”[13]。十八大后,扶貧攻堅工作全面展開,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了解決相對貧困問題。與此同時,在商品經(jīng)濟并不發(fā)達的中國,廣泛吸收了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中社會化大生產(chǎn)元素。雖然這個過程被新自由主義思潮用私有化和市場萬能論竭力改造為資本主義補課過程,公有經(jīng)濟存量嚴重削弱,但保留下來的公有經(jīng)濟體在被培育為成熟的市場主體,抵御私有資本自發(fā)形成壟斷的過程中,還是發(fā)揮了主導作用。大型國有資本和依托公有土地成為投資主體的地方政府,形成強大的國家資本主義經(jīng)濟力,積累了工業(yè)反哺農(nóng)業(yè)、消除絕對貧困,彌補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破產(chǎn)凋敝、提高公共服務和對外發(fā)展一帶一路的實力。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以紅色文化最終回歸統(tǒng)領(lǐng)位置為標志,依靠意識形態(tài)的反作用力,節(jié)制雇傭勞動制度,在一定程度內(nèi)為活勞動個體自由流動在不同所有制企業(yè),擇優(yōu)參與合作創(chuàng)新的生產(chǎn)方式提供了條件。這種自由,不同于馬克思時代的無產(chǎn)階級的雙重自由,支持了活勞動創(chuàng)新的生產(chǎn)方式,少數(shù)先鋒企業(yè)順勢而為,建立生產(chǎn)資料合作共有的公有形式,形成了“新的更高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成為解放、迸發(fā)生產(chǎn)力的典范。總體來看,在實現(xiàn)十五大政治報告提出的“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公有制實現(xiàn)形式”方面做出了生動創(chuàng)新。[1]《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1第2版,第994頁[2]吳易風:馬克思的生產(chǎn)力一生產(chǎn)方式一生產(chǎn)關(guān)系原理,《馬克思主義研究》(1997年第2期)[4]參見紫虬:也談毛澤東同志與“割資本主義尾巴”,《紫虬視野》2020.4.19[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電子版,235-236。[6]參見紫虬: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只能是改造、變革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和封建殘余的結(jié)果——變革和約束雇傭制,《紫虬視野》2020.3.18[7]恩格斯:《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1894年,《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440頁[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1974.11,第285頁[11]參見《孫冶方:關(guān)于生產(chǎn)勞動和非生產(chǎn)勞動、國民收入和國民生產(chǎn)總值的討論》《經(jīng)濟研究》1981年第8期[12]中國新聞網(wǎng)2013年01月08日
【待續(xù):《從理論到政策實踐:解決當前經(jīng)濟問題的一把鑰匙,兼談深化改革的途徑》系列文章之三《毛澤東同志在“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方式-生產(chǎn)關(guān)系”理論實踐上的創(chuàng)新》】
(來源:昆侖策網(wǎng)【原創(chuàng)】)
【本公眾號所編發(fā)文章歡迎轉(zhuǎn)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chuàng)權(quán)利,請轉(zhuǎn)載時務必注明原創(chuàng)作者、來源網(wǎng)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zhàn)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gòu),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wǎng)》,網(wǎng)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wǎng)站,如涉及版權(quán)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lián)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wǎng)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wǎng),依法守規(guī),IP可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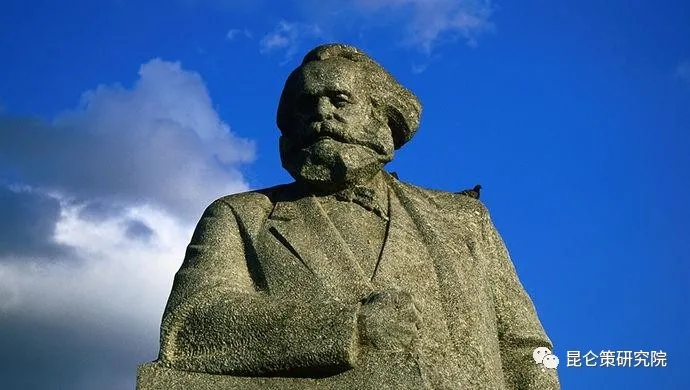







 大變天!中國連夜宣布,誰也沒料到來的這么快!
大變天!中國連夜宣布,誰也沒料到來的這么快! 司馬南:從華為的角度看螞蟻
司馬南:從華為的角度看螞蟻 肖志夫:美國遏制中國“十大任務”即將出爐 中國如何應對
肖志夫:美國遏制中國“十大任務”即將出爐 中國如何應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