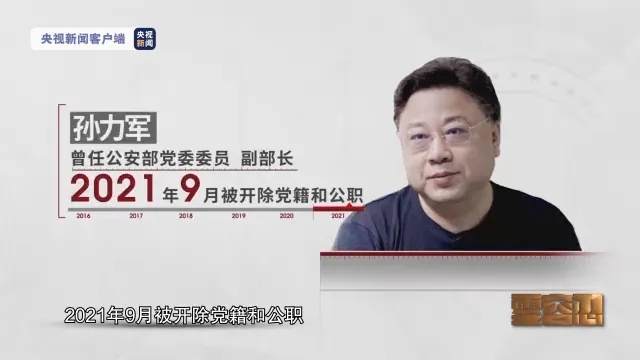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2日-星期五
如果說2014年中國宏觀政策的重點是貨幣政策工具的創新,那么2015年財政領域債務的“開門關窗”、切割重組將成為宏觀政策一道新的風景。正如我們在年度策略報告《涉過險境,便是晴天》中指出的,債務甄別和置換的實質在于中央地方債務并表,但短期債務重組與接續中風險猶存,亟需我們投以更多關注的目光。過去四十年,全球主要經濟體在宏觀政策上均有重貨幣、輕財政的傾向。而中國稅制內生的順周期性,以及國債市場的不發達,使得常規財政政策的逆周期對沖效果相對乏力。2014年,中國實際赤字率為1.8%,并未達成年初設定的2.1%的目標;2015年,新預算法實施、地方債務置換以及財稅改革推進,無疑會對今年財政政策的方向和節奏產生重要影響;而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密切互動與創新耦合,或許日漸成為我國宏觀調控領域的“新常態”。對2015年的中國財政政策,我們有不得不說的“八大猜想”。
猜想一:積極財政政策實為“中央積極、地方緊縮”
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定調積極的財政政策,赤字率由2014年的2.1%提升至2.3%。如果把財政預決算賬上劃撥出去但未使用的財政支出從赤字額中剔除,同時加上因會計重復列支不能反映在報表上的結轉項,“一增一減” 2015年真實赤字額將比2014年多出7000億元,赤字率也相應提升到2.7%。
然而,今年的財政擴張卻可能呈現中央積極而地方緊縮的結構差異。中央財政擴張意圖明顯,除赤字額大幅提高1700億元,還加大了預算內資金對基礎設施的支持。對地方政府來說,其內源融資面臨著財政收入增速進一步下滑,土地財政模式逐步走向尾聲的壓力,外源融資則被關進“預算的籠子”,要求增量債務必須通過地方債券的陽光渠道。新增貸款大幅下滑,城投債發行門檻提高,6000億元新增債券額度顯然難以彌補其他融資渠道的收緊。
我們估算,2015年7%左右的增長目標對應著15.7%的基建投資增速和13萬億的資金需求。以往來看,基建投資資金主要來自于自籌資金(58%)、國內貸款(20%)和國家預算內資金(13%)。因此,預算內資金的積極并不足以對沖前兩項的下滑,中央積極而地方緊縮的綜合效應仍可能是緊縮。
猜想二:地方財政收入步入個位數增長時代
2014年全國財政收入增長僅8.6%,是1994年分稅制以來首次出現個位數增長;地方政府本級財政收入實現增速9.9%,掙扎在兩位數的邊緣。我們判斷,2015年地方政府本級財政收入和全口徑財政收入都將全面進入個位數增長時代。這主要源于如下幾方面的判斷:1)實體經濟再下臺階的壓力。今年工業生產、消費、投資、企業盈利等或將在2014年基礎上進一步回落,這將使得相關的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等主體稅種增速繼續放緩。2)物價,特別是PPI的全面負增長,拖累名義稅收的增長。2014年全年PPI為-1.9%,而2015年前兩個月累計同比增長-4.6%,雖目前環比降幅有望收窄,但全年同比依然是大概率負增長。3)營改增帶來結構性減稅效應。國稅總局數據顯示,2014年營改增帶來1918億元的稅收減少,而2015年還將有生活服務業、金融業、建筑業和房地產業四大行業實施營改增,會對地方政府的稅收構成不利影響。4)房地產市場疲軟拖累相關稅收。商品房銷售額的下滑會使得房地產營業稅、契稅、房地產企業所得稅的增速下降。
2015年是實施全口徑預算的第一年,除了一般的公共預算收入之外,政府性基金收入、社會保障收入和國有資本經營收入也需在預算框架下規范收支。從歷史數據看,社保基金收入相對穩定,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占比總財政收入不足1個百分點,因此分析政府性基金收入顯得尤為重要,而政府性基金的90%以上是國有土地出讓收入。2014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增速僅實現3.2%增長,較2013年的44.6%大幅回落。若以房地產銷量作為土地出讓收入的領先指標,我們測算2015年土地出讓收入或將下降14%。因此,從全口徑預算來看,地方政府收入步入個位數增長也是大概率事件。
猜想三:營業稅退出歷史舞臺而消費稅改革提速
2015年財稅改革領域的重頭戲是稅制改革。從邏輯上看,稅制改革在整個財稅改革體系中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在2014年基本完成預算領域改革之后,今年的重心自然會在稅制改革上。特別地,2015年是既定實施全面“營改增”的最后一年,生活服務業、金融業、建筑業和房地產業四大行業也將實施增值稅。營業稅變成增值稅會降低相關行業稅負,會對這四大行業盈利形成正向貢獻。
除了營改增之外,消費稅改革也是2015年的重要領域。2014年底,兩月三次上調成品油稅收,就是對消費稅稅率的調整。消費稅改革的方向是,在征稅范圍上將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費的商品納入征收范圍,同時將已淪為大眾日用品的消費品調出。我們預計,在巨大的財政收入壓力下,具有結構性加稅效應的消費稅調整,會比個稅和房產稅的調整來得更快。
猜想四: 今年起中央將對地方部分存量債務并表
債務置換、PPP和重組是目前地方存量債務化解的三大主要出口:1)對于有一定收益或者可以改造成有較穩定現金流的項目,用“使用者付費 +補貼”模式通過PPP來解決,最終轉化為企業債;2)純公益平臺包含的地方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則通過債務置換的方式解決,即發行地方債券;3)以信貸為主的債務可以適時進行債務重組。該思路意味著,對于純公益項目的非貸款債務,可以通過債務置換的方式來拉長久期,降低利率,以化解風險。從特定角度來說,這是中央對地方存量債務的主動并表,實現了政府部門內部杠桿率的轉移。
財政部近期批復的今年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置換范圍是,“6.30”審計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中在2015年到期的部分。這一批復額度占今年全部到期的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53.8%,且至少覆蓋非銀行信貸類債務。而在今年1.9萬億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到期債務中,大約有50.8%為銀行貸款(按“6.30”審計公布數據推算),或將進行債務展期;剩下9000億元的非信貸債務則將通過發債來償還。這與3月8日財政部新聞發言人確認的,“近期財政部已下達地方存量債務1萬億元置換債券額度”是基本相符的。而按2015年到期量的53.8%進行分配,則今年有7個省市的債務置換額度會超過500億元,分別為江蘇、湖北、四川、廣東、浙江、北京和上海。
若仍以到期量和53.8%的比例來計算,則2016-2017年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置換規模會有所下降,分別為7000億元和4500億元左右。但若考慮到“6.30”審計后至2014年末新增地方債務的到期,預計明后年的置換額度會有所增加。
猜想五:今年新發行地方債券或為1.6萬億
從2015年開始,財政部將對地方債實施和國債一樣的余額管理。也即“在限額內當年到期債務可以借新還舊,不再采取在發債額中扣抵”。這就意味著,今年5000億的一般債券和1000億的專項債券僅是新增余額。如果再加上1萬億元的債務置換發行,實際最終發債規模可能達到1.6萬億,而非市場所理解的6000億。與2014年中央代發的4000億相比,2015年地方債發行量將翻兩倍。
此外,最終公布的地方債務甄別結果或將大幅擠出水分。關于2015年的地方債務甄別結果,媒體有過多次報道,上報額度與“6.30”審計結果相比幾近翻番。目前債務甄別仍在第二輪“擠水分”過程中。事實上,從財政部提出的3萬億置換額度來看,基本與“6.30”審計公布的政府負有直接償還責任的債務規模相當。那這是否意味著,自“6.30”審計以來新增債務多數未被認定為直接債務?或者意味著,最終公布的新增債務中的水分會被大幅擠出?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當然,不排除財政部后期還會繼續出臺債務置換的措施。但地方政府將新增債務一股腦兒“撂攤子”的做法顯然將會受到抑制。
猜想六: 今年或為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元年
在土地財政收入減少,地方債務融資規范的背景下,PPP將成為化解地方政府存量債務,以及今后城鎮化基礎設施和市政公用事業建設的重要融資渠道。地方政府債務中有一定收益的項目將主要通過PPP來解決,而這部分主要集中在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以及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尤其是其中的非貸款類資金來源。我們基于“6.30”審計結果大致估算,未來可以通過PPP繼續的存量債務規模為1.7萬億,其中2015年約為3000億。而在增量方面,由于地方新增發債規模受限,顯然PPP會成為融資主力軍。
從公布的12省市政府工作報告看,已披露的PPP投資額已超過萬億。這主要集中在軌道交通、供水、供暖、供氣、市政建設、管網改造等以“使用者付費”為主的有收益流的項目上。然而,鑒于法治和政府信用等軟環境尚待完善,政府與社會資本的合作仍將“任重而道遠”。
猜想七:國庫現金管理或將加大流動性的不確定性
在地方財政收入增速下滑背景下,地方需要探尋更多的資金來源。而國庫現金管理擴展到地方,正是盤活財政存量資金的重要方式之一。今年2月財政部批復了上海、北京、深圳、廣東、黑龍江、湖北等六地開展地方國庫現金管理,隨后上海率先公布第一期400億元的國庫現金公開招標。
地方國庫現金將會增加基礎貨幣供應,因而會增加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截止2014年底,我國金融機構財政存款余額3.57萬億。如果按照Baumol最優庫底資金模型計算,那么今年在留出最優留底資金后,大約可以釋放1.1萬億的財政存款(基礎貨幣)。當然這不會通過一次招標完成,而是多次的,這樣在流動性的釋放上也會更加平滑。當然,這種財政存款存放方式的變化,即由大部分時間存放央行賬上,轉變為更多時間存在商行賬上,會給整個貨幣市場流動性環境帶來重大變化,也會對央行流動性管理的量級和節奏帶來了更多訴求。無疑,這需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好的銜接。這也為我們一貫的主張,即“貨幣的背后,財政是根子”尋到了不錯的注腳。
猜想八: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互動將更為積極
2014年PSL等貨幣政策工具創新,已經彰顯了央行將總量貨幣政策與結構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調控思路。當然,市場對結構性貨幣政策的效果將信將疑,對創新貨幣政策工具投放的流動性期限偏短也多有詬病。但正如不日之前小川行長所言,“央行要把這個增量的資金注入到經濟體中,注入時尋找最缺少資金的地方,找結構優化上最需要的地方”,“這些政策的評估,我認為需要一段時間,我們看到了有不少正面的效果”,這樣結構性貨幣政策至少在一開始環節是能起到“指哪流哪”的效果的。因此,央行仍會延續將總量與結構貨幣政策并重的調控思路。而在采取結構性貨幣政策的同時,往往指向了財政政策本應發力的方向。比如,由于國開行重回政策性銀行的定位,預計今年國開行再貸款除了投向棚改之外,還會進一步向水利、鐵路等基建投資領域擴展。
傳統上財政工具在調結構方面更為直接有效。2015年財政領域的一些變化也會涉及到貨幣總量層面。例如,國庫現金管理擴展到地方政府,財政存款從央行賬戶向商行賬戶上的“騰挪”,會對央行流動性管理的綜合評估帶來重大影響;而長久期地方債券的置換發行,連同央行有關SLF、MLF、1年期再貸款、3年期PSL等流動性管理工具的放量擴容,將進一步豐富中國的收益率曲線,為貨幣政策框架從量到價的轉型創造條件。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