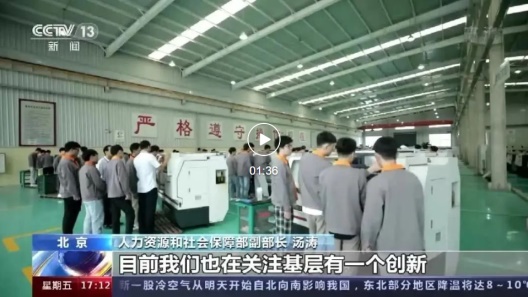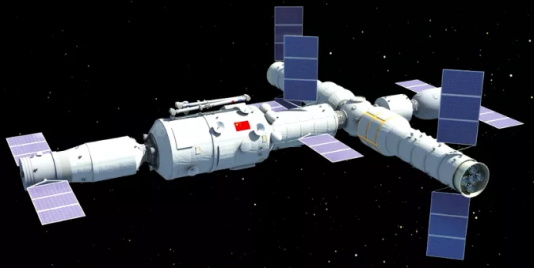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3日-星期六
西方科技革命和資本主義崛起之謎
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會誕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馬克斯•韋伯和道格拉斯•諾斯等思想家對“李約瑟之謎”的經典解釋是“資本主義制度誕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言下之意是“科學革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會導致一場以牛頓力學和拉瓦錫化學為代表的科學革命?
西方傳統理論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當然是尋找西方文明獨特的“自由、民主”制度基因。但無論是韋伯強調的法治精神還是諾斯強調的產權與契約精神,其實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而非原因。
正如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大師熊彼特所說:“所謂‘資本主義的新精神’這樣的東西是根本不存在的……封建社會包含著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胚芽。”那么為什么這個胚芽沒有在東方破土而出?換句話說,是什么樣的“氣候條件”讓資本主義胚芽在歐洲茁壯成長呢?
當我們了解到歐洲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早期都毫無例外是一部遵循叢林法則的“戰爭?商業”循環加速器,以上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正如著名經濟史學家布羅代爾所指出:“戰爭制造資本主義。”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斯文•貝克爾特(Sven Beckert)在《棉花帝國》一書中也揭露:西方早期的資本主義形態就是戰爭資本主義,即用戰爭攫取商業利潤,再以商業利潤支持戰爭這樣一種循環擴張模式。而服務于這一擴張模式的資本主義政治、金融、財政、司法制度,也都是這個“戰爭?商業”循環加速器所刺激和倒逼的產物。
資本主義是一個歷史演化過程。資本主義的今天不等于它的昨天。不能把它長期發展演化的結果(比如法治、民主、大工業與福利社會)當成它萌芽的原因和先決條件。
我最近的一本新著[1]提出需要思考以下相關問題:(1)如果資本主義的昨天十分邪惡和丑陋,今天的西方應該如何對待資本主義才剛剛起步的發展中國家?(2)如果發展資本主義的代價十分巨大,西方是否還有理由和底氣要求發展中國家必須采納資本主義方式來發展經濟?(3)如果發展中國家只有用西方當年的戰爭與掠奪模式才能發展出資本主義,今天的西方國家有權阻攔嗎?(4)今天的發展中國家有沒有可能不重蹈西方資本主義的覆轍,開啟和完成自己的科技與工業革命?
近代西方文明vs古地中海文明
人們通常提及的“西方文明”,其實是一個很不準確的地理和文化概念。通常所指的“西方文明”是“古地中海文明”和“近代歐洲文明”的集合。這兩個文明在時空關系上極為不同,卻被流行歷史觀有意無意地混淆了。“古地中海文明”泛指最早的古埃及、古巴比倫、古蘇美爾、古黎凡特、古安納托利亞這類中東和北非地區的文明(包括尼羅河三角洲和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以及后來的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古地中海文明”體系是由膚色較深、頭發偏黑、個子較矮的南高加索人種創造的(古希臘人并非今天的白種人)。而“近代歐洲文明”是由北高加索人(以阿爾匹斯山以北的法蘭克人、日耳曼人、盎格魯-撒克遜人為主體)在古羅馬帝國滅亡后發展出來的,北高加索人(白人)代表的“近代歐洲文明”,也可以統稱為“基督教文明”,雖然基督教發源于中東地區,之后才傳入歐洲。
接受了基督教并將其發揚光大的北歐人并不能自喻為古地中海文明的天然繼承者。阿拉伯文明對古地中海文明的繼承關系先于基督教文明,阿拉伯人所代表的伊斯蘭文明曾經覆蓋過整個地中海區域,其后日耳曼人、法蘭克人、盎格魯-撒克遜人所代表的基督教歐洲文明才覆蓋了古希臘-羅馬文明擁有過的地域。況且自十字軍東征以來的西方文明,在其萌芽過程中從東方文明(阿拉伯、中國、印度)所直接吸收的養料,一點也不亞于(甚至超過)它從古希臘-羅馬文明所吸收的養料。
我在書中討論的“西方文明”,是指近代西方進入中世紀后的“基督教歐洲文明”。西方崛起之謎,是指以西歐白人國家為主體的“近代基督教世界崛起之謎”,而非古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之謎。
歐洲的軍備競賽和科學革命
社會需求才是推動科學革命和技術變革的最大動力。歐洲近代史上自文藝復興后造成經常性大規模國破家亡的最大原因,就是綿延500年的熱兵器戰爭。其歷史主線是,延續了近200年的十字軍東征運動(11-13世紀),在破壞了絲綢之路的阿拉伯貿易網絡、掃清了歐洲通往東地中海貿易樞紐的“路障”以后,由于火藥的傳入和基于火器的熱兵器戰爭,點燃了歐洲版“春秋戰國”時代的野火,導致了歐洲中世紀封建秩序的瓦解和近代歐洲國家競爭體系的形成。它最初萌芽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城邦國家,然后通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航海和全球殖民競賽,擴展到西歐和北歐。
這個國家競爭體系之下的激烈軍備競賽,導致中央集權的形成與國家力量對科學技術和熱兵器研發的大規模投入,使得與熱兵器相關的科技人力資本和知識積累由量變到質變,最終引爆了一場“科學革命”——包括基于炮彈力學原理的伽利略——牛頓物理學革命,和基于火藥爆炸的氧化燃燒原理的拉瓦錫化學革命。同理,也是通過這個國家競爭體系內的激烈商業競爭、殖民競賽,以及相伴隨的貿易戰、金融戰、間諜戰、技術剽竊、全球市場開拓和由產業政策帶動的產業鏈急劇升級,引爆了工業革命。
這是一條社會動力學演化之路,其歷史視角把歐洲近代在力學理論和化學理論方面的突破,看作一條歷史的因果鏈,即火藥傳入歐洲以后引發的熱兵器戰爭,最終導致歐洲民族國家的誕生和規模化國家競爭體系的形成;延續幾百年的激烈軍備競賽,又導致了國家力量對科學技術的長期投資并形成強大的“戰爭需求”拉動力量,不僅促成了伐木、采煤、煉鐵、冶金等工業的迅猛發展,更為關鍵的是促成了“彈道力學”與“火藥化學”這兩場科學革命的爆發——就像20世紀的計算機、互聯網與航天科學的突飛猛進,是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陣營“太空與核武”軍備競賽與地緣政治爭霸的產物。
20世紀冷戰期間的激勵軍備競賽模式,其雛形早在十字軍東征結束后的文藝復興時期就已經誕生和萌芽了。而爆發在17世紀的經典力學革命和18世紀的化學革命,不過是歐洲這場延續發育好幾百年的跨國軍備競賽的自然產物與碩果。
科學革命為什么爆發在西方
目前,學術界對于科學革命為什么爆發在西方而非東方的解釋有數種相互關聯的流行理論。一種理論認為,“東方專制主義”妨礙了中國古代出現科學思維與科學理論;另一種理論認為,中國自古就沒有產生古希臘數學那樣的公理體系和一神教那樣的宗教信仰,以及中世紀那樣的亞里士多德經院哲學傳統,因此不可能產生科學革命。這個理論面對的巨大挑戰之一是:同樣是繼承和吸收了古希臘數學知識和“猶太-基督”一神論傳統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為什么沒有能夠產生牛頓經典力學革命和拉瓦錫化學革命?
另一種流行理論認為,雖然天主教和伊斯蘭教都具備一神論的理性思維傳統,但是由于它們都不像路德和加爾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樣支持“思想自由”,因此不可能產生科學革命。這個理論也面臨兩大挑戰:挑戰之一是由于新教是排斥科學的,都是激烈反對當時的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的新思維和哥白尼的日心說理論。挑戰之二是,無論是伽利略的經典力學理論還是拉瓦錫的氧氣燃燒理論,都恰好分別誕生在天主教占統治地位的意大利和路易十五統治下的法國,而不是新教占統治地位的荷蘭、瑞典或德國北部的城邦國家。
還有一種流行的解釋科學革命的理論,基于愛因斯坦在1953年提出的一個觀點:“西方科學的發展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文藝復興)。在我看來,人們不必對中國的賢哲沒有走出這兩步感到驚奇。人類居然作出了這些發現,才是令人驚奇的。”
這是目前為止“西方中心論”解釋科學革命較為客觀公正的“非西方中心論”視角。不過愛因斯坦這個觀點所提供的理由仍然面臨諸多挑戰。
首先,18世紀的化學革命雖然與實驗方法密切相關,但與古希臘數學無關。化學革命恰恰是由法國火藥局局長和杰出的煉金術士拉瓦錫引發的,而且比牛頓的經典力學革命晚了整整一個世紀。為什么?
其次,究竟什么是文藝復興以后才開啟的科學實驗傳統?人們喜歡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那么伽利略通過反復測量鐵球在斜面滾動的實驗,究竟想要獲得何種力量?而且,雖然培根提出了系統觀察和實驗的方法論,但近代物理學的實驗傳統并不是由培根所在的新教國家(英國)開啟的,而是在天主教統治下的意大利開啟的,是由伽利略和他的前輩(比如塔塔格利亞)這些天主教徒開啟的。那么,伽利略們開啟這樣一個科學實驗傳統背后的動機是什么呢?是企圖用數學與實驗證明上帝的存在,還是有某種更加世俗的實用主義動機?
再次,古希臘文化和數學古籍被拜占庭帝國保存得好好的,為什么延續上千年的拜占庭希臘文明(公元330-1453)卻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而是等到伽利略的出現?伽利略所處的時代為科學的迅猛發展提供了哪些古希臘所不具備的社會條件?
答案顯然不在于“文藝復興”時期的翻譯運動本身——因為它不外乎將阿拉伯文獻中的古希臘知識翻譯成拉丁文而已,尤其是拜占庭的希臘人不需要通過這種翻譯就能閱讀古希臘數學文獻。答案也不在于北歐的宗教改革運動——伽利略并沒有受到新教的影響,而且一直是在天主教占統治地位的意大利工作和研究。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愛因斯坦關于科學革命為什么爆發在西方的觀點需要回答,即無論在古中國、古印度、古羅馬、古希臘、古埃及、古巴比倫,還是亞里士多德自然哲學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歐洲,人們對大自然的認識都更加著重于理解與人們日常生活、生產勞動、氣候變化、繁衍生息密切相關的五彩繽紛的大千生命世界,比如鮮花為什么在春天盛開,蟲鳥為什么在夏天啾鳴,楓葉為什么在秋天變紅,雪花為什么在冬天飄零;天氣為什么有四季變換周而復始,人生為什么有喜怒哀樂生老病死;以及“我是誰?從哪里來?往那里去?”諸如此類的人生哲學問題。當面對如此多無法回答的自然哲學與倫理哲學問題時,哲學家和神學家都不可能像伽利略那樣關注兩個不同大小的鐵球如何在斜面滾動,從高空下落時的加速度等運動力學問題。即便是礦物學家和煉金術士,也只關注巖石的性質、成色和紋路。
伽利略這位卓越的自然哲學家和天主教徒所畢生關注的焦點之一,恰好是計算和理解不同重量的球體如何在不同傾角的斜面按不同速度滾動,以及鐵球如何在地球重力作用下做拋物線運動的彈道學問題,從中突破對拋射物體運動規律的認識。為什么?這就迫使我們回到戰爭,回到伽利略所處的充滿戰火的文藝復興時代。
事實上,伽利略在其經典名著《關于兩門新科學的對話》的第一頁就開宗明義昭示了“科學革命”的“戰爭密碼”:“……威尼斯人在著名的兵工廠里進行的經常性活動,特別是包含力學的那部分工作,對好學的人提出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
伽利略創立的這兩門“新科學”,一門是材料力學——它是基于威尼斯兵工廠軍艦設計上對幾十門重炮對船體結構、材料的受力情況所進行的靜力學幾何原理分析,另一門是鐵球的運動力學——它是基于炮彈飛行的拋物線軌跡在慣性作用下的勻速運動和重力作用下的勻加速運動所進行的數學分析。通過在威尼斯兵工廠大量實驗,伽利略為這兩門新科學奠定了數學基礎。他成為經典力學革命之父,最早把嚴格的數學分析與物理學結合的第一人。他不僅系統地借鑒了那個時代的阿拉伯-古希臘數學知識去解決戰爭中遇到的物理學問題,并發現和論證了新的物理學定律,即炮彈飛行的慣性定律和炮彈自由落體的勻加速定律,從而打開了通向現代精密物理科學和變量數學分析的大門。這本經典名著是伽利略專門題獻給他科研活動的贊助人——陸軍元帥、總司令、魯埃格地方長官諾阿耶伯爵的。
可見,如果沒有火藥傳入并點燃戰火紛飛的歐洲,伽利略不會去思考裝載幾十門沉重火炮的戰艦受力(靜力學)問題,更別說炮彈飛行的彈道學與動力學問題,拉瓦錫也不會去思考火藥燃燒和爆炸背后的化學機制問題,從而科學革命也就不可能發生。
國家力量和近代科學革命
為什么科學革命沒有爆發在火藥的發源地——中國?歷史上各國各民族都在打仗,為什么偏偏是歐洲人發明了“數、理、化”?
答案并不單單是古希臘數學知識的缺乏——因為拉瓦錫的化學革命不需要古希臘數學;也并不是實驗歸納方法的缺乏——因為中醫理論、中藥配方、針灸原理、《本草綱目》和《天工開物》都體現了實驗歸納法在古代中國知識體系中的系統應用;何況,實驗方法論鼻祖培根通過采用系統性羅列現象來找出背后原因的歸納法,不僅自己在科學發現上毫無建樹,而且這種方法論的哲學表述也是由阿拉伯傳入的。
問題的根本答案,是中國基于火藥-火炮的高烈度、高頻率戰爭和圍繞這種使用熱兵器的新型戰爭而展開的“國家競爭體系”的缺乏。只有處在這樣一種高烈度、高強度、高頻率的熱兵器戰爭和國家競爭體系中,才能激發出社會精英和國家力量對數學、物理、煉金術和其他科學知識的巨大渴望、需求、扶持和投入:因為精確描述炮彈的變速軌跡,需要代數和平面幾何;全面理解火藥爆炸和物質燃燒的機理,需要非常豐富的煉金術知識和大量耗時、耗錢、耗人工的化學實驗,需要國家扶持的專門實驗室(與今天見到的大規模化學實驗室沒有本質的不同)。因而企圖統一歐洲的法國路易十四在17世紀初斥巨資成立法國科學院,路易十五斥巨資成立“法國火藥局”“拉瓦錫國家實驗室”和巴黎高等軍事學院。而中國明朝和清朝都沒有這樣做,所以在科技上落后了;然而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這樣做了,因此趕上了歐洲列強。
任何文明都具有兼收并蓄其他文明的能力,一旦社會需要,就會向別的文明學習和借鑒。正如中國古人不怕千難萬險前往“西天”取經,也正如意大利人不怕千辛萬苦將阿拉伯數學翻譯成拉丁文一樣。既然所有文明都具備向別的文明學習的精神,中華文明也就不需要自己獨立發明佛教或古希臘數學——當年如果需要的話,完全可以通過絲綢之路向阿拉伯文明學習、引進更加先進的數學。可中國早期歷史上向西方學習和從事文化交流的社會精英,比如張騫、玄奘、班超以及后來的宋明理學大師們,并沒有這樣做。為什么?
出產《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本草綱目》和《天工開物》的古代中國,沒有產生對“變速運動中的炮彈軌跡”進行精確數學描述的社會需求,沒有產生對火藥及其化學成分集中研發和規模化生產的需求。而近代中國經受了鴉片戰爭的屈辱和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無情打擊,終于激發出了這種意識和需求,提出用精密科學“賽先生”拯救中國的口號。中國的國家力量才開始籌建兵工廠、理工科大學、軍事學院、科學院,并公派大批留學生赴日、赴歐、赴美學習數學和科學,與17世紀的法國和英國派學生去意大利拜訪伽利略一樣。這反映了當下中國對科學與數學的巨大社會需求——意識到落后就要挨打,意識到科學與軍事技術的密切關系。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城邦國家,也是在嘗夠了炮彈的滋味以后才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否則但丁和馬基雅維利便不會強烈呼吁實現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達•芬奇和伽利略也不會如饑似渴地學習軍事工程技術和數學了。
問題的關鍵不是誰先發明了歐氏幾何,而是誰先產生了把數學應用于軍事和槍炮工業、應用于描述炮彈軌跡的社會需求。正是因為這種巨大社會需求的缺乏,使得最先發明火藥的中國沒有產生科學革命。
其實,中國歷史上戰爭最頻繁的春秋戰國時期,恰好也是中國歷史上科技飛速進步的時期。但是,冷兵器時代的戰爭對科技進步的推動作用,在進入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熱兵器時代已經過時,近代火藥-火炮與古代弓箭的差別,相當于當代的核彈-反導技術與當年的火炮-城堡技術的差別。
火藥與火炮技術是在中世紀末期和文藝復興初期才傳入歐洲的。而火器的傳入,使得歐洲在十字軍東征和文藝復興以后,進入了一個類似于中國歷史上的歐洲版“春秋戰國”時代,引起一系列深刻的社會、政治、軍事、經濟制度變革,把與火藥和火炮相關的制造技術和物理化學原理推向極致,從而爆發一場“軍事革命”和“科學革命”,為叢林法則下適者生存的歐洲國家贏得一場遠比“春秋戰國”時代還要慘烈百倍的國家暴力競賽和軍備競賽,為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激勵與推力。
基礎科學與藝術一樣,都具有很強的公共品性質,需要國家力量有意識地投入并為其創造平臺——包括類似科舉制度和科學院體制在內的科學人才吸納機制,以及政府采購、軍工產業政策和一系列崇尚征服大自然的意識形態的推動。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繁榮是這種“政府贊助”活動刺激的產物;伽利略對物理學和天文學的研究,也離不開威尼斯兵工廠這個試驗基地和酷愛戰爭的羅馬教皇、意大利宮廷和歐洲貴族的長期贊助。這也是為什么哪怕蘇聯計劃經濟時期根本沒有所謂“民主、自由、法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言,但是因為有斯大林國家意志的投入,蘇聯時期的科學和數學成就不僅超越俄國歷史上的彼得大帝時期,而且超越同時代的自由歐洲,與同時代的超級大國美國并駕齊驅。
國家競爭體系和“李約瑟之謎”
為什么頻繁的戰爭和歐洲國家競爭體系朝著科學革命的方向演化?牛頓經典力學理論和拉瓦錫的化學理論與火藥和炮彈之間,究竟有什么必然邏輯聯系?瓊斯、蒂利、肯尼迪、帕克、霍夫曼、歐陽泰和“軍事革命”理論的支持者們,包括主張科學革命是工業革命的必要條件的莫基爾(Joel Mokyr)都沒有給出解釋,或者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我在新著中將沿著瓊斯、蒂利、肯尼迪和“軍事革命”理論家們開創的思路,拓展他們的理論。首先通過對十字軍東征、文藝復興和大航海時代的重新剖析,揭示它們的戰爭資本主義屬性,以及歐洲軍事重商主義發展模式的產生;然后通過“戰爭?商業”循環加速器下的軍備競賽,在“國家競爭體系”這個框架內解釋科學革命的爆發,解釋它為什么發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
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包括行政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私有產權制度與社會福利制度)的演變,也是受這個國家競爭體系推動和倒逼出來的。
同理,賈雷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提出的,歐洲自古以來就因為不利的地理條件而四分五裂,和中國自古以來就因為有利的地理條件高度統一的觀點,也不足以解釋為什么歐洲的崛起和它對中華文明的超越,只是近代500年才發生的事情,而不是2 000多年前或更久以前就已經發生的事情,因為歐洲和中國的地理條件在過去幾萬年以來就一直沒有變化過。
采納“國家競爭體系”這個概念框架,而不是韋伯和諾斯的文化與制度決定論,也可以幫助一大批“反西方中心論”學者解脫他們所面臨的一個邏輯困境,即如何在充分承認東方文明對近代西方崛起不可或缺的貢獻,以及中國的商品生產與交換能力直到19世紀初仍然大大領先于歐洲這一歷史事實時,同時解釋近代歐洲為什么有能力實現對東方文明的全面反超和碾壓,尤其是解釋“科學革命”為什么發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這個“李約瑟之謎”。
[1]《科學革命的密碼——槍炮、戰爭與西方崛起之謎》,東方出版中心2021年12月出版。
來源 | 《經濟導刊》2021年12月刊
作者 | 文一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講席教授,中國人民銀行五道口金融學院訪問教授。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